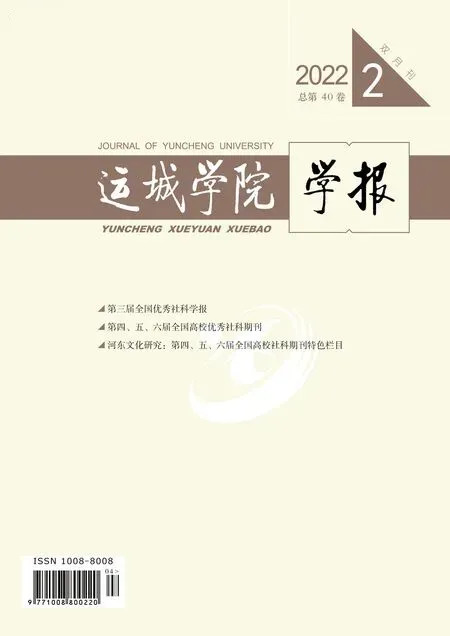论河东词人“稷亭二段”的楚辞接受
2022-03-17吴昊
吴 昊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段克己(1196-1251)、段成己(1199-1282)兄弟,金朝河东南路绛州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人,是金元之际声名卓著的遗民词人,被称为“稷亭二段”[1]102,作品合编为《二妙集》流传至今。二段以词享誉文坛,近代词学家张尔田赞曰:“二妙词近接遗山,远宗稼轩,较诗尤为高妙,直金源时一作手。”[2]77二段词之所以能够和辛弃疾、元好问相提并论,与其对屈宋楚辞的接受密不可分。对于二段词与屈宋之间的脉络关联,学界尚未予以关注,本文即针对此问题作一专论。
一、二段的人生经历及其词体创作
段氏是诗书传家的河东望族,克己、成己自小深受家学熏陶,勤苦读书,才名早著,幼时便得文坛盟主赵秉文赏识,以“二妙”称之。哀宗正大(1224-1231)年间,二段赴汴京应试,同中词赋科进士,知贡举者恰是赵秉文。赵秉文爱其才华,亲书“双飞”二字相赠,为之扬誉。可惜的是,二人虽金榜题名,仕途却并不顺利,只因彼时金朝江山已危如累卵,大厦将倾。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铁木真挥师伐金以来,金军便连战皆北,疆界日蹙。此后二十余年,金廷内忧外患不断,内部政变、起义轮番动乱,外部遭蒙宋联合夹攻,中都、汴京相继陷落,至天兴三年(1234),哀宗完颜守绪与末帝完颜承麟皆在蔡州围城中身死,金祚遂绝。二段读书、扬名、高中的前期人生历程,与国家由盛转衰并逐步走向灭亡的历程完全同步。兄弟二人登第后尚未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金廷已荡然无存。如同克己《赠答封仲坚》诗所言:“念昔始读书,志本期王佐。时哉不我与,触事多轗轲。”[3]390他本有心以满腹经纶去济世拯民、匡扶社稷,奈何时乖命蹇,惨逢家国沦丧,以致报效无门。
金亡之际,克己、成己带着壮志难酬、回天乏术的失落与幽愤敛迹于龙门山(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芹溪之侧,与同道结社赋诗,谈文论学,吟啸林泉,不问世事,成为遗民文人群体的中流砥柱。流传至今的二段词作,绝大多数都作于金亡后的隐居时期。故而,麦秀黍离的故国悲思,沧桑变幻的身世伤感,安贫守志的孤洁操守便成为二段词的核心思想内容。抒故国悲思者,如克己《满江红》:“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4]136以客观纪实的沉痛笔触再现了战争的酷烈场景,着墨冷峻而词情哀切。又如成己《望月婆罗门引》:“长安倦客,不堪重整旧朝衣。天香尚带馀霏。盖世虚名何用,政尔畏人知。爱青山屋上,面面屏围。”[4]150以“长安”代指故都,流露出故国不堪回首、只愿埋名山野的无限怅惘之感。写身世伤感者,如克己《水调歌头》:“月自于人无意,人被月明催老,今古共悠悠。壮志久寥落,不寐数更筹。”[4]135又如成己《满江红》:“人已老,身犹客。家在迩,归犹隔。纵语音如旧,形容非昔。”[4]148二词皆有惋惜年华空逝之意,倏忽间人已迟暮却无所作为,唯有自悲自悼,徒然吟叹。表孤洁操守者,如克己《蝶恋花》:“早是残红枝上少。飞絮无情,更把人相恼。老桧独含冰雪操。春来悄没人知道。”[4]140以老桧经霜历雪而苍翠依然的坚韧品质寄寓自已清贞不阿的高洁风操,以树喻人,托兴遥深。又如成己《满江红》:“谁把秋香,偏著意、植根姑射。尘土外、鲜鲜元有,可人容质。日久渐随芜共没,岁寒还与松同洁。”[4]148赞扬菊花能如松树一般与寒冬顽强抗衡,意旨则与克己《蝶恋花》同揆,克己以桧喻人,成己则是以菊、松喻人,暗示自己亦将与菊、松同样不畏霜寒、不改品性。
不难看出,在二段笔下,词体已经跳脱出偎红倚翠、娱宾佐欢的传统婉艳题材,而是传承了苏轼指出的“向上一路”[5]29,即在词中张扬主体意识,表达自我胸臆,围绕作者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去构建词境,凝聚词心。因之,对二段而言,词体不仅仅是其放怀山水、自娱遣兴的优游歌咏,也是其剖白衷曲、独抒情志的恳切宣言,更是其砥砺名节、磨琢品德的刚正篇章。毫无疑问,在二段的文学创作体系中,词体承载着巨大的精神意义,担荷着崇高的生命价值。也正因如此,为实现美政理想而上下求索、九死无悔,不论命运如何蹭蹬多舛都始终心怀家国、志洁行廉的楚臣屈原郑重地走进了二段的词体创作视野。屈原之为人,是忠君爱国、争光日月的品行模范,屈原之楚辞,是金相玉式、名垂罔极的诗歌经典,自秦汉以来,其人品与文品就持续影响并塑造着历代骚人志士的道德文章。站在社会的角度,每当时局变易、江山危殆之际,屈原精神往往会重新得到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时代思潮。站在个人的角度,每当人生坎壈缠身、前路茫茫之时,文人墨客们也总会翻开楚辞以寻觅心灵的慰藉或奋斗的动力。二段身历山河破碎之深痛,备尝理想幻灭之煎熬,遂与千载之上行吟泽畔的逐臣屈原产生了直抵心魂的情感共振。而且,其通过词体所要着重抒发的故国悲思、身世伤感、孤洁操守等主题,无一不可从楚辞中寻得思想源头。故而,二段在词体创作中引入与楚辞相关的语言、意象以借古喻今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甚至苦心孤诣之举。
二、二段词对楚辞的多元接受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论及楚辞对后世文学之影响,曰:“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6]163强调了楚辞在鸿大体制、瑰艳文辞、模山范水、香草比喻等多个层面广泛沾溉后人,其对词之影响亦如是。以充分把握楚辞的丰富艺术特征、细致领悟楚辞的深刻思想内涵为基石,二段词的楚辞接受呈现出层次清晰、形式多元的饱满格局。
首先,是最基础的语汇承袭。如克己《鹧鸪天》所言“波间容与”[4]144,成己《临江仙》所言“秋兰无处采,流水满芳洲”[4]155,“容与”“秋兰”“芳洲”等词汇即带有较为鲜明的楚辞色彩,取自《离骚》“纫秋兰以为佩”[7]2,《湘君》“采芳洲兮杜若”“聊逍遥兮容与”[7]46,50等句。又如克己《满江红·寿卫生行之》下片曰:“无一物,为君贺。歌我志,君须和。问人生底事,必须奇货。好对青山倾白堕,休嗟事业违人些。怕他时、富贵逼人来,妨高卧。”[4]137词中韵脚为“贺”“和”“货”“些”“卧”,可知“些”字并不读为“xiē”,而是读为“suò”。每句结尾缀以“些suò”字,是《招魂》所创的独特体式。沈括《梦溪笔谈》曰:“《楚词·招魂》尾句皆曰‘些’。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8]110可见,“些”是具有明确楚地风格的特殊字眼,克己以“些”为词韵,显然是对《招魂》传统的直接继承。运用楚辞语汇,是二段词接受楚辞最浅显的层次,只是说明二段对楚辞文本相当熟悉,而词作意旨则与所涉及的楚辞篇目并不存在明显关联。
其次,是借用楚辞的创作形式为自我表达服务。这种情况体现于克己的两首《水调歌头》。词曰:
清秋好天气,禾黍已登场。群心思答神贶,吉日复辰良。神既来兮庭宇,飒飒西风吹雨,仙仗俨长廊。巫觋传神语,出户舞伥伥。刲肥羜,沥桂酒,奠椒浆。一年好处须记,此乐最难忘。风外渊渊箫鼓,醉饱满城黎庶。健倒卧康庄。夜久群动息,风散一帘香。
双龙隐扶辇,千骑纵翱翔。云旌翠蕤摩荡,遥指白云乡。风驭飘飘高举,云驾攀留无处,烟雾杳茫茫。小立西风外,似听珮锵锵。暮天长,秋水阔,远山苍。归途正踏明月,醉语说丰穰。但愿明年田野,更比今年多稼,神贶讵能忘。君可多酾酒,吾复有新章。[4]135-136
这两首词与屈原《九歌》一脉相承。《九歌》本是楚地民间祭神所用祭歌,屈原以为“其词鄙陋”[7]42,遂润饰修订使之词章焕发。《九歌》十一篇,前十篇分别祭祀十神,最后一篇《礼魂》则是“前十祀之所通用”的“送神之曲”[9]45。因之,《九歌》的整体结构便可以分为前十篇的迎神曲与最后一篇的送神曲两大部分。克己词前首曰“神既来兮庭宇”,为迎神词,后首曰“归途正踏明月”,为送神词。其创作形式与结构安排显然是以《九歌》为参照模板,遣词造句如“吉日复辰良”“沥桂酒,奠椒浆”等也多有摭拾、化用《九歌》原文之处。克己借用《九歌》祭祀神灵之框架,表达的却是自己对四海升平、黎庶饱暖的热忱期盼。迎神词所言“醉饱满城黎庶”,送神词所言“但愿明年田野,更比今年多稼”皆在在表明了其填词之初衷。即使以布衣之身幽处山林,克己仍对生民稼穑之艰难念念不忘,并为之祀神祝祷。其忧国忧民之情、心怀天下之意于此二词中发露无遗,而此情此意也正是屈原精神的现实写照。
再次,是运用楚辞中蕴藉深微的特定意象以感慨言志,借屈原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这是二段词接受楚辞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二段与屈子虽遥隔千古却心魂呼应的部分。克己有咏菊词《满江红》曰:“雨后荒园,群卉尽、律残无射。疏篱下、此花能保,英英鲜质。盈把足娱陶令意,夕餐谁似三闾洁。”[4]137时值深秋,气候肃杀威厉,百花调残,园荒草腐,而当此万物萧条之际,却偏有一丛菊花睥睨秋霜,凌寒独放,自保其“英英鲜质”而不败。该词表面写花,实则写人,以秋气之凛然喻国家形势之衰微,以菊花之自保喻自身之持节。屈原在《离骚》中言其“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7]8张铣注曰:“饮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洁以合己之德。”[10]606指出屈原之所以餐菊饮露,为的是以其锤炼自己孤标傲世、清高香洁之品德。克己词同样着眼于屈原之“洁”。词中反问“谁似”,其实是“我似”,表明其愿以屈原为标杆反躬自省、检视内心,激励自己亦当如屈原一般不论身处何境都永葆高洁之品格,维护心灵之净土。
成己词中,亦有两处用到《离骚》中的“餐菊”意象,一为《大江东去·寄卫生袭之》:“过眼一线浮华,辱随荣后,身外那须此。便恁归来嗟已晚,荒尽故园桃李。秋菊堪餐,春兰可采,免更烦邻里。”[4]148二为《江城子·季春五日,有感而作,歌以自适》:“百年光景霎时间。镜中看。鬓成斑。历遍人间,万事不如闲。断送馀生消底物,兰可佩,菊堪餐。”[4]150成己笔下的“餐菊”,与克己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自然是以“餐菊”作为自我修洁、培育情操的物质象征,其不同在于,成己在词中更突出归隐青山的重要意义。不论是《大江东去》中对卫袭之的谆谆教诲,还是《江城子》中自己的所思所感,成己都在述说繁华如梦幻,世事如云烟,唯有兰、菊不可辜负。与其耽溺荣名、役役营营,不如早早栖身于流水青山之怀抱,侣春兰而友秋菊,在以菊为餐、以兰为佩的逍遥出尘生活中不断陶写情抱、涵养品性。《大江东去》有“便恁归来嗟已晚”之句,提醒卫袭之早日抛却红尘烦扰,归卧山林。《江城子》下片再次重复曰:“便恁归来嗟已晚,那更待,买青山。”[4]150二词用语重合,旨趣相近,如此反复书写,可见成己对高蹈林泉的确有念兹在兹之向往。
除了“餐菊”,克己还用及《离骚》的“荷衣”意象。《离骚》曰:“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7]13王逸注曰:“言己进不见纳,犹复制裁芰荷,集合芙蓉,以为衣裳,被服愈洁,修善益明也。”[7]14可见,与“餐菊”相似,屈原以荷为衣的目的仍在于护持其志行之“洁”。而且,“荷衣”是屈原之“初服”,即“未仕时之服”,[11]8说明屈原也曾设想若谗佞当道、理想难伸,便引身而退,但仍要不改初衷,始终保持内心的芳洁之志。克己有《月上海棠》词曰:“弊衣旋补荷盈沼。算骑鹤扬州古今少。休苦似吴蚕,刚把此身缠绕。君知否,我自无心可了。”[4]142该词作于蒙古乃马真后二年(1243),距金亡已有十载,克己已习惯山中隐逸岁月且领悟到所谓“骑鹤扬州”之类仕途、财富不过是梦幻空花,汲汲于名利地位只是如吴蚕一般作茧自缚,不如山中藜藿自甘之乐。“弊衣旋补荷盈沼”有以荷补衣之意,衣虽故弊,却得荷香为之增色,故其洁净高华之内质任何锦衣丽服都难望项背。可以说,克己此词精准再现了“荷衣”意象原初蕴蓄的深微托旨,即使退处乡野,亦必守节自持。用舍行藏可改,而修洁操守不可改。以荷为衣,坚毅不屈,克己与屈原于此达成了思接千载的可贵默契。
屈原在《卜居》为自己置身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7]166的溷浊时代而痛苦忧虑。克己《鹧鸪天》词则曰:“瓦釜逢时亦转雷。春江得雨浪崔嵬。不才分作沟中断,偶对溪山一笑开。”[4]144金启华认为其词传承屈原之旨,暗指“小人得志,贤士无名,只得改朝换代”,是写“亡国之愁”。[12]139不过,克己此词有题曰:“上巳日,再游青阳峡,用家弟诚之韵。”[4]144明言词为游览青阳峡之时与弟成己唱和之作,且为组词,共三首,而在成己词中亦有《鹧鸪天·上巳日陪遁庵兄游青阳峡》四首。整体而言,这七首词主要是对青阳峡的山水丽景进行多角度刻画,并伴以优游览胜的畅达心怀,若将克己词中的“瓦釜逢时亦转雷”解读为深重的亡国之恨,似与组词的整体旨趣不协。“瓦釜”一句固然以《卜居》为典源,不过,在该词中克己的直接取材对象当为黄庭坚《又戏为双井解嘲》:“山芽落硙风回雪,曾为尚书破睡来。勿以姬姜弃憔悴,逢时瓦釜亦鸣雷。”[13]976意在说明其家乡分宁出产的双井茶虽出于偏远乡野之处,但品质极佳,不可轻视。黄庭坚淡化了“瓦釜雷鸣”这一典故在《卜居》中强烈的对抗性,仅仅以之表示在不同的时机中优劣能够互相转化。克己在词中步武黄庭坚之思路,其言“瓦釜逢时亦转雷”当是为下句“春江得雨浪崔嵬”作铺垫,以突出青阳峡雨后波澜迭起的壮阔江景,而不必过于深解。
另外,克己在《大江东去·送杨国瑞西行,兼简仲宣生》词中涉及到宋玉之作。其词曰:“悲哉秋气,觉天高气爽,澹然寥泬。行李匆匆人欲去,一夜征鞍催发。落叶长安,雁飞汾水,怕见河梁别。”[4]138起首三句化用了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泬寥兮天高而气清”[7]176-177等句,并还原了《九辩》所营造的萧瑟凄清之氛围,只不过宋玉悲秋是为其坎壈失志而惆怅自怜,克己则是为知交远别而怅惘心伤。其情由虽异,而感怆实同。
以上论述中作为例证的二段词,都直接关涉楚辞的具体篇章及其具体语句、具体意象,但这并不能涵括二段词接受楚辞的全貌。克己另有《鹧鸪天》词曰:“愁不寐,夜难朝。广陵散曲屈平骚。从今有耳都休听,且复高歌饮楚醪。”[4]144与前文所引词例不同,在此词中,不再提及具体篇章,“屈平骚”是作为一个整体意象被克己赋予情感,并与《广陵散》意旨相宣。本质上,《广陵散》与《离骚》分别寄寓着嵇康与屈原命途多舛、理想难成的痛切与感愤之情,二者相并,克己之深意不难想见。故国已矣,无路请缨,即使日日沉溺于广陵曲、屈平骚之中也不过是徒劳叹恨,不如自此“休听”,去高歌纵饮,一醉解愁。在看似放达的表象之下,词中隐含的却是克己面对山河倾圮却无可奈何的深悲剧痛。成己同时创作的《鹧鸪天》步韵词则曰:“须富贵,是何朝。一杯聊慰楚人骚。逢花堪赏应须赏,座有佳宾尊有醪。”[4]154同样是以“楚人骚”作为整体意象,只不过,在成己词中,楚骚的寄托意义被弱化。既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如今也只能以杯酒告慰楚魂,而生活仍当继续,不如且在宾朋美酒间聊度岁华。克己、成己固然都因社稷沦亡而隐居自适、守节自持,但对比而言,克己更留恋往昔而表现出较多故国悲思,成己则更珍惜未来而关注当下生活。成己另有《临江仙》词曰:“自古兴亡天不管,屈原枉葬江流。”[4]154则是抛开楚辞作品,直接以屈原其人为抒情意象,传达出兴亡无常、世事沧桑的无限感慨。
不难看出,在二段词中,楚辞以多种不同面貌频繁现身,有直接单纯的语汇因袭,也有翻旧出新的形式借鉴,还有最重要的寄托传承,即借助屈骚意象含蓄渊永的托兴之旨以充分表现自我胸壑。或者径直将楚辞整体、将屈原个人都用作内涵丰厚的词体意象,同时在屈原以外也注意到了宋玉悲秋独具的深远意蕴。综合而言,二段词的楚辞接受有着逐步递进的意义层次,有着灵活多变的呈现手法,以传达词旨为根本而运化得宜,做到了张炎强调的用事应“不为事所使”。[14]261而且,在屈宋楚辞的加持与增色之下,二段词的境界与意旨的确得到了重要的审美升华,弥漫于二段词中的故国悲思之怀、身世伤感之意、孤洁操守之诚也都因楚辞意象的深入助力而益发巩固并显著彰明。
三、二段词楚辞接受的词学史意义
二段在词体创作中主动接受屈宋楚辞影响并非戛戛独造,而有其深长的词史传统。晚清词论家沈祥龙《论词随笔》曰:“屈、宋之作亦曰词,香草美人,惊采绝艳,后世倚声家所由祖也。故词不得楚骚之意,非淫靡即粗浅。”[14]4048强调了楚辞“香草美人”的创作手法对增强词体艺术表现力的巨大作用。如其所言,词体自唐五代萌生之初便与楚辞渊源匪浅,中唐词人张志和《渔父》词便有“反著荷衣不叹穷”[15]25之言,在词史上最早运用《离骚》“荷衣”意象表现自己退处江湖、修身养性之闲适。不过,纵观整个唐五代词史,张志和对《离骚》意象的运用并未得到发扬,因为自晚唐温庭筠、韦庄以来,剪红刻翠的闺思恋情之作占据了词坛主流,与之相应,宋玉《高唐赋》中楚王神女之间的艳情故事成为词人写及男欢女爱之时最为钟情的高频意象,此类作品如李存勖《阳台梦》“楚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15]444牛峤“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15]510等等,举不胜举。与宋玉作品的热闹景象相比,屈原在唐五代词坛则要落寞许多。即使到了北宋初期,在柳张晏欧等婉约词大家的笔下,宋玉比屈原更受重视的情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屈、宋的所有作品之中,《高唐赋》以绝对优势占据着词坛影响力的榜首位置。
直至苏轼以天然绝世之姿赫然登上词坛,这一绵延近二百年的沉滞局面才被打破。苏词之中,有《江城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16]136-137用《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7]58表疆场击敌之勇;有《殢人娇》“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16]720用《离骚》“纫秋兰以为佩”[7]2表修身清洁之志;又有《归朝欢》“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16]699用屈原之名及《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7]50表放逐失意之伤。苏词对楚辞的多方位接受使其脱离了偎红倚翠的狭窄领域,且使屈原在词史发展中的地位得到巨大抬升。至南宋,辛弃疾继苏轼之后更上层楼,将词体创作对楚辞的接受推上顶峰,其词中如《蝶恋花》“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17]1879《山鬼谣》“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17]1886等等借屈原酒杯浇自我块垒之作多达近四十首,且往往能以屈原不同作品寄托不同深意。应当说,苏、辛词运用楚辞相关意象,于其中倾注了自己真实的人生感触与现实思考,与唐五代时期宋玉《高唐赋》意象以艳情为底色广泛流行存在着本质不同。再至金末山河播乱之时,元好问以旷逸雄才振起词坛,隐然有自比苏、辛,接续传统之志,其词如《摸鱼儿》“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4]75《最高楼》“任年年,藜藿饭,芰荷衣”[4]79等为屈辞意象赋予深沉的自我情感,也是苏、辛风旨的直接嗣响。
二段与元好问生当同时,共历社稷崩解之烟烽,同有故国覆亡之怆痛,且同为遗民文人之翘楚,故三人词作之思想内容与风格情韵皆有相近之处,尤其是词中对屈宋楚辞的接受方式更加如出一辙。前文所引张尔田之言称二段之词“近接遗山,远宗稼轩”,张尔田如此立论,固然是着眼于诸人在词体创作中整体呈现出的刚劲风裁与峻洁品格,但毫无疑问,对楚辞相关意象的精当运用也是塑造诸人词风词品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二段词中绝无绮筵绣幌、裁花剪叶的靡靡之音,其作品不论寄友、送行、祝寿、感怀、咏物,抑或登览山川、伤叹节序,皆是“缘事而发”,[18]1756有着客观真切的现实触媒及肺腑思感。正因如此,楚辞对于二段而言不是一种刻板固化的意象工具,而是仍然鲜活跃动的生命书写,是勾联古今、上溯屈宋的精神通路。其对楚辞意象的运用也与苏轼、辛弃疾、元好问等人一样,是以屈宋之心为心,以屈宋之感为感,从而将身心体悟与楚辞意象糅合为一,使楚辞成为自我情志抒写的绝佳媒介。若以楚辞接受为考察视角纵览千秋词史,可以发现,河东词人“稷亭二段”以其卓荦词才在金末元初之际的艰难时局中高擎苏、辛传统之大纛,与金词殿军元好问同辉共映于衰世词坛,使苏、辛一脉饱含身世之慨与家国之志的壮伟词风得到延续与传承,其有功词林,不可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