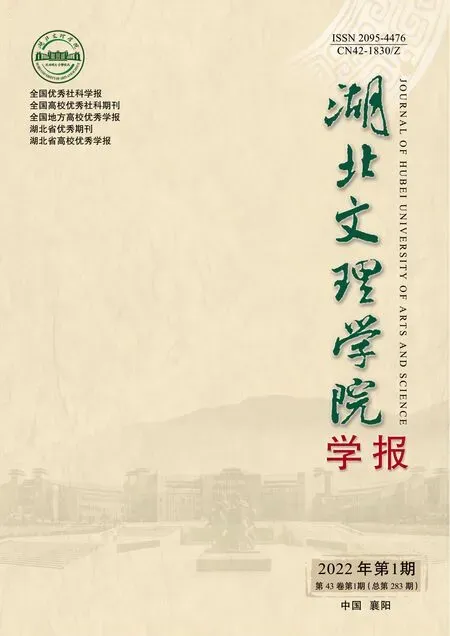西厢故事演变中的婚恋观
2022-03-17陈禹锡
陈禹锡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著名美学家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自序》提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作为“一代之文学”代表的《西厢记》,其文学史意义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其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西厢记》的故事本事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经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发展,加之王实甫的个人创作,逐渐成为我们现今所阅读到的版本。在这漫长的积淀与发展中,渗透于文本字里行间、借主人公之口发出针对社会现状的感慨与呼吁构成了文本独特的思想价值。
作为作者主观心灵的映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即使是同一题材,也会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异。因此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观念的演变可以作为研究一个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料,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研究西厢故事中婚恋观演变的真正原因。
一、西厢故事中爱情的演变
在西厢题材故事的演变中,不变的是故事始终以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为主线。崔张爱情在《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三部作品中经历了如下变化:从单方面的爱恋到两情相悦;从为了功名甘心舍弃爱情到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从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悲剧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本部分主要从爱情的主动性、爱情的坚定性、爱情的结局三个方面来分析西厢故事中爱情的演变。
(一)爱情的主动性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崔张的爱情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单向求爱逐渐发展为双向互动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崔张二人的诗文互答的变化。
《莺莺传》的崔张爱情关系中,张生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也就是说爱情的走向和结果是以张生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现在书信诗文中,张生从《春词》二首赠诗开始,莺莺回以《明月三五夜》并当面斥责张生不合礼,却又自荐枕席,之后杳无音讯。张生作《会真诗》三十韵以文挑之,莺莺陷入纠结的境地,直至认可了这段关系,两人开始在“西厢”共寝。然后就是二人的分别——重聚——再分别。张生留在京城后寄信给崔莺莺,其后面对莺莺字字泣血包含相思的书信和象征爱情的信物,张生始终没有再回复。
从引诱莺莺开始,到得以定下私情,再到最后的始乱终弃结束。酒席初见,张生便痴迷于莺莺的美艳。这里我们并不否认张生对莺莺存在着爱情,但这种爱情,更多的是一种“猎艳”心理的驱使,是一种生理本性,本能的对于美好事物的欲望和妄图占有。此时张生作为爱情主动的一方,他的一见钟情、他的赠诗表情、甚至是他的无礼逾墙,都无不体现他对于莺莺这般美好少女的渴望。初见时,张生被莺莺的美貌惊住,在席间试探着同莺莺说话,却没有得到莺莺的应答。进而恳求红娘,又写诗表达自己的爱慕。而在张生成功与莺莺建立私情后离开,面对莺莺几欲泣血的诗篇,他并未做出任何回复,反而是将字字泣血的相思之信,传阅给身边的朋友。可以说这里的崔张爱情,是单向的。
《董西厢》中的崔张爱情,出现了由单向向双向过渡的趋势。首先,在莺莺与张生依韵唱和的场景(卷一)中,张生吟诗向莺莺表达思慕:“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2]38-39莺莺依韵而和:“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2]42诗韵唱和作为爱情发生的契机,体现了男女主人公的相配——不仅是外表上的才子佳人,更是灵魂和精神层次的契合。其次,在《董西厢》中,长亭送别和张生及第是崔张爱情道路上两个重要节点,莺莺也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份爱情的安全感实则把握在张生手中。因此,此时莺莺的赠诗寄信,不同于《莺莺传》中将幽怨的心思隐藏起来,而是通过书信的方式,主动和张生进行情感的沟通。张生也与《莺莺传》中有了不同,在考取功名之后,还写诗给莺莺报喜。这种手法一方面突出了崔张二人对待这份感情的“真”,另一方面也推动着剧情走向圆满,而非最初“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模式。
而在《西厢记》中,爱情关系则表现为明确的双向互动。诗文自始至终都是二人相合。从爱情发生的条件来讲,崔莺莺作为矜持的封建社会的贵族女性,虽然没有张生那么主动大胆,但依然无时不在体现着对于人性解放的向往和对封建礼教束缚的讽刺。作为封建贵族家庭的小姐,莺莺能见到的适龄男子少之又少,压抑的人性在见到年龄相仿而又风流倜傥的才子时,便无法控制,也许是因为好奇的“回顾觑末”最终促成了妙龄少女与倜傥才子的爱情。“回顾觑末”就如神来之笔一般点出了莺莺的主动。
(二)爱情的坚定性
在二人对待爱情的坚定性方面,在《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莺莺传》中,张生是个“始乱终弃、轻薄负情”的书生。他初会莺莺就“见色起意”而失了原本的风度。当听闻红娘的要求,要依常理而先媒后合之时,他甚至急不可耐地大呼,表示如果要按:“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3]780后来在红娘的帮助下,采取私下定情的方式,心愿得偿,却最终抛弃了莺莺。可以说这里张生对莺莺主要是从欲望的角度,想要将美好事物据为己有。张生从来没想过要为莺莺的一生负责,或者说从一开始,在意识到了莺莺的出身无法为他的科举荣身之路提供更大的帮助时,他便已经做好了负心的准备。在仕途与爱情的抉择中,张生心中对于功名的渴望高于一切,于是他不仅抛弃了莺莺,还将自己对莺莺产生的感情归结为莺莺的“妖”而惑己,把自己醉卧温柔乡的行为和对莺莺的难以忘怀说成是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把自己在短暂的沉溺后重新回归求取功名视为“改过”。这里的张生是一个始终将仕途功名放在最高地位的唐代士子形象,是那个时代文人士子形象的典型化代表。对于爱情,他是不坚定的。
到了《西厢记诸宫调》,张生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说《莺莺传》的张生,是一个将婚姻视作功名垫脚石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在董西厢中,张生便是一个在爱情中迷乱痴傻甚至可以为爱而死的人,这也是董西厢从根本上区别于《莺莺传》的地方。在《西厢记诸宫调》中,虽然崔张相恋的时间、地点、事件(琴声传情、隔墙唱和、红娘传书、跳墙遭斥等情节)均出自《莺莺传》,但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张生的“痴”,他一直遵循着与莺莺的承诺。尽管一开始,张生为爱痴傻,也被老夫人责难得痛苦不堪,但当与莺莺定情后,爱情的主动权实则已经掌握在了张生手中,可他的心,从未离开过莺莺分毫。在最后面对郑恒的阴谋和老夫人的恼怒,令郑恒莺莺成婚的时候,他甚至打算与莺莺同死。这份坚定,是《莺莺传》中的张生完全没有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张生对于功名的愿望更为迫切,但这种迫切,是基于对莺莺的爱——想要给莺莺更好的生活,努力去改变“小生目下身居贫贱”的现状[2]251。这也是张生形象改造策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男主人公张生的形象,在《西厢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董西厢的基础上,王实甫着力刻画了他情痴志诚的一面。这里的张生本是“学成满腹文章”,正待进京应试求取功名的书生。但当佛寺初见莺莺,一眼便已是“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4]9般地呼道“我死也!”初遇,便已是对莺莺爱慕得如痴如狂。这样,爱情的发生便有了其必然性,爱情也随即成了张生生命的全部,他把爱情看得比功名更重要。而当险些失去爱情时,他便寻死觅活,甚至被红娘嘲笑为“银样镴枪头”。痴傻疯魔较之董西厢更甚,这里的张生对莺莺锲而不舍、至死靡它。为了这份感情可以放弃功名利禄,甚至放弃生命。张生俨然一幅“疯魔”之样,但也恰恰是这“疯魔”,体现出张生对于爱情的志诚,寄托了作者对真情的理想。爱情之于张生已不是《莺莺传》中见色起义地想要拥有,而是他生命之源,是点亮他生命的蜡烛。似乎就是为了这爱情而生,他炽热执著而不畏缩。尽管与莺莺身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他为了爱情,可以舍生忘死——普救寺被围,他坚定地站出来,冷静理智;但一旦面对与感情相关的事,他便束手无措起来。解围后面对老夫人的毁约,他不知该如何做,甚至跪地请红娘帮忙,他的“志诚”打动着身边的人。最后终于在红娘的帮助下,赢得了心上人的芳心。在私情被发现后,老夫人提出不招白衣之婿的条件,要求他求取功名。三番两次的刁难并未击退他对真情的坚守,求仕成功后也并未始乱终弃。以毒誓表明心迹,最后与郑恒当场对证才证明了自己的真心。这里的张生,较之董西厢中对待爱情的态度更为炽热,在爱情与仕途的矛盾中,经历了一个由功名至上到爱情至上的转变。张生对于爱情的态度,也从不坚定发展到坚定。
爱情的女主人公对于这份感情,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莺莺传》中,女主人公崔莺莺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子。对于爱情的态度,莺莺始终处在弱势的一方。面对定情后的被抛弃,也只能是寄诗寄物抒发忧思,盼情郎能够回心转意,早日回到自己身边。而在《西厢记诸宫调》里,她发展成了一个为了爱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藩篱的少女。《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则更为丰满——在面对老夫人赖婚时,不再是“兄似不胜酒力”的无奈接受,而是大胆与封建家长抗争;在功名和情感方面,也更加地轻功名而重情感。例如在长亭送别时,不同于董西厢的“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而是要求无论是否求得功名,都要“疾便回来”;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西厢记》中的莺莺也更为大胆炙热——从一个凄楚卑微的痴情人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大胆、为了爱情与封建礼教积极抗争的少女,更为饱满,更为鲜活,也更具有生命力。
(三)爱情的结局
《莺莺传》中,崔张爱情的结局是“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3]785,痴情女子最终遭遇了情郎的负心。她陷于一个无奈又无助的被动地位,一封封字字泣血的信笺最终换来的不过是“德不足以胜妖孽”。
到了《西厢记诸宫调》,结局的走向开始发生变化。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时代观念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原本始乱终弃的悲剧被重新塑造成了一出有着浪漫色彩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将唐代士子不但别婚高门、始乱终弃,还解释为“善补过”的错误观念进行了纠正,同时还增添了许多戏剧化的情节,将故事塑造成在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基调下,充满着乐观和浪漫的爱情故事。
《西厢记》则有了更丰满的塑造。从最初的佛殿奇遇,张生被莺莺的美艳震撼而做出了种种痴傻的举动:险些跟进莺莺的梨花院、“尚未娶妻”的自我介绍、相思而精神恍惚、喜极跳墙等情节,都将原有的悲剧题材全方位地喜剧化。王季思先生在《悲喜相乘》一文中,认为“一个剧本之为悲剧、喜剧、或悲喜剧,同它的结局关系最大。《西厢记》如果结束于长亭分手,就会是一部以生离结局的悲剧。”“而《西厢记》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喜剧。”[5]由原有的爱情悲剧转为爱情喜剧,也是西厢故事在演变中的重要变化。
二、西厢故事中婚恋观的变化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再到《西厢记》,文本中所呈现的爱情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深层次来讲,体现的是作者的婚恋观的变化。西厢故事中的婚恋观究竟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莺莺传》——舍情而求仕
《莺莺传》讲述了莺莺与张生私定终身后,又遭遇始乱终弃的“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悲剧故事。而张生在负了莺莺之后,不但对莺莺的相思无动于衷,甚至是将莺莺寄与他的信笺传阅给身边的好友,完全不避讳二人过去的私情。这里通过张生对莺莺的绝情,可以看出整个文人阶层对于诸如此类别婚高门风流韵事的看法——不乏为酒后谈资,屡见不鲜了。
在《莺莺传》中,崔家不是相国门第这种高门大户,所以在崔张二人的婚姻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因门第差距导致的矛盾,老夫人的阻挠也并不突出,因此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恋情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一方——张生。至于张生始乱终弃的原因,文中作了一定的交代——“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3]785。张生与好友谈到,是因为莺莺是如此的美艳动人,如同“尤物”一般。而这种“尤物”,不祸害自己,也一定会祸害他人。而自己的品德修养和意志力,不足以战胜如此“妖物”,所以只好忍情抛弃。这里,连好友都“皆为深叹”,他却可以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轻松道出,张生的绝情可见一斑。同时也借张生之口,表达了“美人祸水”的思想,即所谓“不妖其身,必妖其人”[6]。对于张生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作者在文中给出的评价是——“善补过”,即善于及时改正错误,没有造成不可估计的后果。这也正反映了元稹的封建意识束缚下的婚恋观——即对于婚姻中男女双方是否两情相悦、男方是否遵守承诺并不重视,而是更多的考虑这份婚姻所能带来的现实利益,当面临更大的利益之时,便绝情地舍弃原有。所以当张生意识到崔家的门第很可能成为他以后攀附高枝的拖累时,他便果断舍弃了与莺莺的爱恋。其实这并不是作者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唐代社会文人才子的主流价值观,即功名至上,把婚姻视为功名的踏板。因此在这里,作者要为张生的行为进行辩护。
(二)《西厢记诸宫调》——对情的回归
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莺莺传》的封建观念。他不仅写了崔张二人大胆追求爱情,而且创造性地将结尾改成了恶人自食其果,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但值得注意的是,“董西厢”这里,对于爱情的观念并未像王实甫一样,振聋发聩地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而是提出了“自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论断。可以看出,在董解元眼中,爱情是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功名利禄不应成为阻挡爱情、破坏爱情的绊脚石。才子就理应与佳人相配,这里所追求的是一种生理的和谐和郎才女貌的相配。但是董解元把崔张之爱,简单地与“报德”连在一起,仍未能摆脱“门当户对”的枷锁。这就决定了作品中反对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不彻底性,也正是这种不彻底性,成为王实甫《西厢记》与《西厢记诸宫调》根本的不同。
(三)《西厢记》——真情能战胜一切
王西厢基于诸宫调的情感色彩,把“怜才爱色”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深化为高举“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景,反封建的色彩也更加突出。在戏曲的一开场,就做出了两个极为重大的改动,这两个改动也是《西厢记》中王实甫所要表达的“真情能战胜一切”的重要体现。其一,与之前两个版本都不同的是,王实甫在一开篇就借老夫人之口,点出莺莺与郑恒已有婚约的事实,甚至是“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这就已经表明崔郑二家十分确定的关系了。因此莺莺与张生的私情所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违背父母之命,更是对封建社会既定法理的一种反抗与挣脱。爱情的结局也上升到一种——只要真情长在,“万古长完聚”的大团圆。以崔张的爱情来战胜封建的伦理束缚,这也就是《西厢记》不同于此前的西厢故事的最突出地方。其二,则是莺莺与张生初遇时所迸发出的爱情的火花。《莺莺传》中,元稹只是简要交代了在酒席上二人的初遇,可在《西厢记诸宫调》中,是这样交代二人初遇的:“转过荼蘼架,正相逢着宿世那冤家。”[2]26《西厢记》则更为直白:“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4]9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暗示了读者——二人其后必有感情的纠葛。崔张二人的一见钟情甚至有天命、前世、轮回等思想的影响,为这份感情平添了一抹浪漫与必然,也体现了作者在编撰这份感情时所倾注的理想。
《西厢记》中,作者对待反抗封建的行为是宽容、同情,同时,对未来也寄寓了美好的期许,在美满大团圆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美好的婚姻要基于真情,而真情最终会战胜封建的禁锢。对封建婚姻制度中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婚恋观做出了批判,从而赋予崔张故事以反封建的战斗意义。
三、西厢故事中婚恋观变化的原因
(一)时代观念的变化
“佳人和配才子”和“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不仅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董解元和王实甫个人的呼吁,更是整个金元时期人们的普遍观念。
在《莺莺传》中,才子与佳人最终没有善终的主要原因,在于门阀制度对婚姻中男女双方门当户对的要求。当张生意识到崔家的门第可能无法为他科举荣身之路提供帮助,甚至会成为累赘时,作为创作主体的元稹站出来为主人公的行径进行了辩护——“善补过”。虽然“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却都对张生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因为这种观念是当时唐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就是将功名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受时代的社会背景(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影响。创作主体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社会的变动必然直接影响作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
从社会背景来讲,唐代与金元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唐代,科举制度被视作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重要方式,改变了魏晋以来所谓的“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颠覆了所谓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对于封建国家的发展和实力的提升、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这种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弊端,由于每年能够中进士的不过二三十人,不少考生就通过托人情、走后门以及中举之后与原有官僚门第结为姻亲的方式来稳固自身的地位。在唐代士子眼中,与婚姻紧密相连的是仕途,而非爱情。所以,《莺莺传》甚至同时代的《霍小玉传》中这类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故事,并不能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反而更多的是理解和接受。
宋金之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人们更关注这些出类拔萃的幸运者们对待人生与家庭的态度。与此同时,门阀制度的衰落使得门当户对的婚恋观念逐渐让位于男女双方的两情相悦。如果说在唐代,人们将别婚高门的始乱终弃看作是无伤大雅的风流韵事,那么在宋金时期,当通过科举改变了命运的士人抛弃发妻,另觅新欢之时,往往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为随着科举的逐渐发展,权势腐化了许多士人的灵魂,当面对富贵与良心的选择时,不少人选择了前者,从而俨成风气。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壮大,人们理所应当地将同情倾注在处于弱势的受害者一方。因此,宋金以后的婚恋观,更强调爱情的如一和坚定,而原来别婚高门的现象,也多为人所不齿。反映在作品中,也就成就了董解元对张生的改造——将张生变为痴情人,也恰恰是婚恋观的变化在作品中的重要体现。相似的例子还有著名的南戏《赵贞女与蔡二郎》,讲述的是蔡二郎考中状元之后,抛弃了前妻赵贞女,贪恋富贵而入赘相府。赵贞女苦苦上京寻夫,还被蔡二郎派人杀害,于是人神共愤,蔡二郎遭雷劈而死。可见在宋金时期,市民阶层对于痴心女子负心郎故事中的负心郎给予了空前的谴责。不仅仅是现实社会层面中的谴责,甚至包含阴间地府谴责,让负心的人遭受天谴、地府审判、不得善终。这说明当时市民阶层的愿望主要是通过强烈的谴责和复仇来表达对负心者的憎恶。尤其是在董解元和王实甫生活的元明时期,当旧有的封建伦理长期束缚着人们,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这时封建礼教也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反抗,体现在社会上,就是高扬人性大旗的市民文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二)创作者的个人因素
作品是作家心灵的主观投射。作品中观念的变化不仅受社会大背景影响,同时也受创作主体的个人遭际和心态的影响。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婚恋观的演变,说明和创作主体有着直接的关联。
作为《莺莺传》的作者,元稹15岁时就中举,21岁初仕河中府,25岁登书判,26岁授校书郎,28岁列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元和初,应制策第一。元和四年(809)为监察御史。一生宦海浮沉,从地方司马到中书舍人,元稹一直是以入仕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的。[7]这就不免带有当时社会的文人阶层的价值观念,也就是我们前文中所说——当面临爱情与仕途的抉择,他们会毅然选择后者。
而王实甫的人生则有很大不同。他早年也曾入仕,但无奈官路坎坷,做官的愿望屡屡遭阻。后经常出入于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是个不为封建礼法所拘,与市民阶层、甚至倡优都有密切交往的文人。晚年辞官归隐,过着吟风弄月的肆意生活。可以说王实甫始终是游离于入仕与出仕之间,与下层人民的来往使得他接受了更多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如前文所说——对于负心郎的谴责和批判。金元时期的文人阶层,因过分追名逐利所做出的负心行径已遭到市民阶层的谴责。于是,改写原有的题材,保留原有的框架,将谴责矛头指向士子,以自责换取市民阶层的理解成为当时文人阶层为了挽回阶层形象所做的努力。同时,将爱情的主动权置于女性之手,而更多地凸显男性的弱势地位和迫不得已,使得民间对士人阶层由憎恶转为怜悯和同情。这种出自文人之手的改写,实则意在重新树立文人阶层的自身形象,缓和与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于是便有了张生形象的改变和渗透在文本中的崭新的婚恋观。
通过剖析对比《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风气,而这种社会风气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无论出于文人阶层自身的改变还是市民阶层的要求,从“善补过”的爱情悲剧,到“自是佳人,和配才子”的过渡阶段,最后到王实甫“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西厢故事的婚恋观经历了由舍情逐名到爱情至上的变化,结局也由悲剧发展为赋予美好愿景的大团圆,反映了文人阶层对于真情的逐渐重视和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在中国文学史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