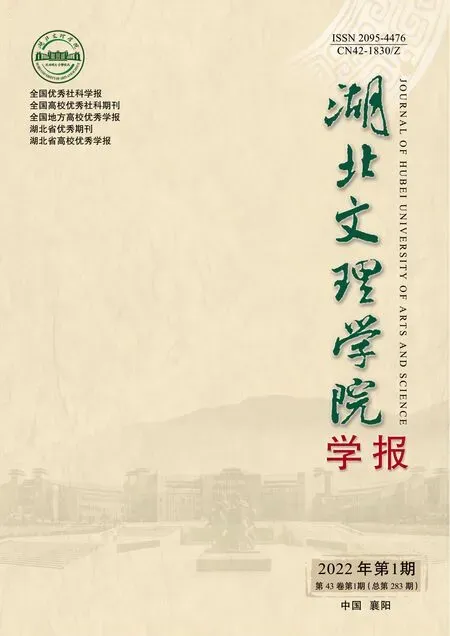光未然“文艺的民族形式”观论析
2022-03-17陈燕桦
陈燕桦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抗战期间,“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历时三年有余,光未然亦积极参与其中。1940年4月21日,他出席了“文学月报社”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召开的“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并于同年5月15日,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期“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特辑”发表了文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该文集中表现了光未然的文艺民族形式观,甚至可以说是他20世纪30至40年代文艺创作与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见解,受到了茅盾的肯定和赞赏。在当前有关“民族形式”的研究中,可看到一些研究者评论光未然的观点,如戴少瑶《“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1]、袁盛勇《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2]、谭桂林等著《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中西之争》[3]、毕海《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与文化政治:“民族形式”文艺论争及相关问题》[4]、龚刚《文艺民族化思潮的当代反思——以探究民族形式论争的文学史意义为中心》[5]等,但仍缺乏专章专论的考辩与分析。鉴于此,本文试作述评。
一、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的修删谈起
茅盾在1940年8月5日致孔罗荪的信中主要谈论了“民族形式”的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光未然的《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殊见用力之劬,亦颇多警辟之论”,但另一方面又表异议,“惟于指陈旧形式句法之巧妙,语汇之丰富处,其中有数点,鄙见有与不同。如所举《蟾宫曲》之连用‘一声’、‘一会’……以及《宝玉问病》之连用‘一阵’、‘一面’……等之‘一字格’,我觉得并不可爱……恰当好处用一二,颇觉可爱,多用则成为文字游戏。凡文字游戏,于形式上虽似新奇,实则有伤于感情之真挚也。至于双声叠韵,则以南方之吴语系语言而论,似乎并不多;双声叠韵似乎还是在文言文字较多,故此点亦值得再讨论。”[6]223-224据此看,茅盾很可能只是指陈个人的观点,然而,饶有意味的是,笔者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初刊本与《张光年文集》第三卷所收录的版本加以比对,可以发现作者在晚年编订文集时对《文学月报》的初刊本作了一些修删,显而易见的修改是,删除了每节正文前的内容提要。为了使文章更臻于完善,光未然还修正了别字和标点符号,替换、删除或增补了更为流畅、准确、严谨的用词和句子。以上是小范围的修删,大范围的修改则体现在某些句群或段落被大幅度地删除,其中就有茅盾所指出的数点。
1981年茅盾逝世时,光未然在纪念文章《热诚的关怀和鼓励——怀念茅盾的几件事》中情感真挚地回忆了当年茅盾在致孔罗荪的信中肯定《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一事,“这使我深深感受到前辈的鼓励。可是当我反复研读这封来信,并重阅一下自己的文章,我脸红了。我感受到鼓励之中的批评和鞭策:我的文章过分从形式上看问题,旁征博引的地方越发显出自己见识的肤浅。”[7]75-76光未然所指出的“过分从形式上看问题”实则对应了茅盾所不认同处。作为后辈,在全国多地都围绕“文艺的民族形式”展开激烈论争之时,得到文坛前辈茅盾的认可,可以想象这对于光未然来说有多激动人心,即便几十年后步入晚年仍对茅盾的鼓励感念于心,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份深切的情感,何况光未然“从三十年代中叶开始在文坛学步时候起……一直把茅盾看成自己的文学导师之一。”[7]75
直至2001年3月30日,光未然还在《张光年文集》第三卷所写的引言中特别提到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最近重读我的这篇关于民族形式的论文,自觉太冗长;引用大量文学史料包括许多诗词歌谣段子不必要,今概删去。至于当年的论点有对有不对,就不必改动了。”[8]2他自言由于文章“太冗长”及有许多不必要的引例,故删减。笔者认为光未然所说固然构成修删的部分原因,但同时也与茅盾的批评存在一定关联。他曾公开表明茅盾的批评对他而言是“鼓励之中的批评和鞭策”,或许正是这份“鼓励之中的批评和鞭策”于有形与无形之中促成了他在晚年编订文集时,对《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这篇“少作”进行了修删。这一面是听取他见,一面也是检讨自身。当然,光未然晚年文艺民族形式观的调整和发展也是修改的重要原因,因为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建构的结果。1987年光未然在《光未然歌诗选》自序中所言恰可印证这一点,“认识是没有穷尽的,这个否定之否定也是没有止境的”,“古人有‘悔其少作’(悔其少年时代的幼稚作品)之说,历来很多诗人、作家都有过这种体会。这是一种进步,或迂回曲折的进步,不同消极的忏悔。”[9]5可见,修删作品,对他而言是一种成长。如今看来,光未然当时的某些主张可能过时了,但毋庸置疑,在战时那场围绕文艺民族形式展开的论争中,他做出了应有的探索与努力。因此,笔者试图基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初刊本去溯源光未然抗战时期的文艺民族形式观。
二、光未然寓居重庆参与的“民族形式”座谈会
重庆展开“民族形式”的讨论,一般认为始于1939年12月26日戈茅在《新华日报》发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一文,而随后以向林冰与葛一虹为主展开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的讨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民族形式”论争推向了高潮。身处“民族形式”论争的中心地——重庆,光未然以论争见证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基本上全程目涉了重庆文艺界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在对该问题进行探索与思考的过程中,他积极参与了重庆文艺界有关“民族形式”的座谈会,这体现了其民族形式观的其中一个侧面,以下逐次而论。
(一)参与“文学月报社”组织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
1940年4月21日,光未然出席了由“文学月报社”发起的“文艺的民族形式座谈会”,该座谈会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召开,出席者还有叶以群、向林冰、陈纪滢、葛一虹等人,罗荪任主席。座谈会召开的目的主要是想打破重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偏于局部问题的状况,“希望从这个会里开一个头,使大家的意见有一次交换的机会。”[10]在座谈会上,光未然的主要观点有二:首先,他认为“民族形式是文艺活动发展到现在必然提出的问题,推进文艺运动,创造新的果实,是不能当成意见之争的,而是要很严肃地在文艺创作的实践中来解决这一个大问题”[10],如何理解文艺的民族形式,无疑是论争参与者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问题。而在光未然看来,当前“民族形式”既是文艺发展的关键、瓶颈,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文艺实践。其次,他指出“关于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问题,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以来,文艺大众化的任务并没有达到,这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民族形式的问题,没有把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联在一起看的缘故”[10],这道出了光未然对文艺大众化和文艺民族形式因果关系的看法,只有解决了文艺民族形式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文艺的大众化。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呼吁与探索,实际上贯穿了光未然战时文艺创作与实践的整体历程。总的来说,光未然此次座谈会发言的诉求也正是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应于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中推进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文艺的大众化,而不应止于口舌上的对峙或者理论上的探索。
(二)出席“新华日报社”发起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
1940年6月9日,《新华日报·文艺之页》开展了有关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座谈会,《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任主席,光未然列席其中,此次座谈会主要为了听取有关文艺民族形式问题“新的意见和想法”[11]。座谈会纪要于1940年7月4日以《民族形式座谈笔记》发表在《新华日报》第四版。光未然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针对两个问题:第一,“民族形式是不是已经有了的问题”。对此,光未然反对唯中国传统旧文艺或唯五四新文艺发展的道路,强调“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所走的道路还不够,如果把这二十年来新文艺运动的收获一笔抹杀,我们叫他是‘疯子’。反过来,如果把过去的缺点一概不承认,统统拾它起来,仿佛都是民族形式了,我们叫他为‘妄人’”[11]。显然,不管是“五四”新文艺,还是文艺旧传统,光未然均主张以客观中正的态度审视之。在文艺面临新的时代要求之下,如何吸收和改造文艺发展中的“新”与“旧”,无疑是当前亟需解决的文艺发展困境,此举归根到底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文艺在抗战中的作用。第二,对于“民族形式是不是通俗化的问题”,他认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不等同于民族形式,但文艺的大众化需要依靠普及国民教育以及作家自觉创作面向广大农民的文艺来实现。处于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大众”革命力量的发现与动员,无论是对政界还是文界来说,均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光未然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对接了这种导向性号召。
(三)参与“戏剧春秋社”开展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
1940年6月20日,光未然还参与了由“戏剧春秋社”发起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到会者还有阳翰笙、葛一虹、田汉、常任侠等。座谈会纪要刊于《戏剧春秋》1941年第1卷第3期。座谈会上,光未然作了较为详细的发言。首先,光未然谈到了延安文艺界对于“民族形式”讨论的意见分歧,有论者指出“光未然提到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民族形式’是从‘文艺的旧传统出发’还是从‘五四以来新文艺传统出发’这一问题上,实则已触及到‘民族形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一论争中的核心问题。”[3]142对此,光未然认同由于“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民族性格有极壮烈的发挥,民族生活有急剧的改变”[12],因而更应当注重文艺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调和。“民族形式”问题不仅仅是形式问题,还是内容问题。其次,光未然否定了民粹派的偏向,又强调不应过分倾向“文艺的国际性”,“民族性的发挥愈充分对国际艺术的贡献愈大,愈强调艺术的国际性愈应该发扬民族性”[12],这揭示了艺术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对“国粹主义者”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但又持论“每一现实主义者都应该把继承民族文艺传统而使它更丰富、健康、发展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头上。”[12]而在如何创造民族形式的问题上,光未然强调“从现实生活汲取,从国际遗产吸取,从民族传统发展,从民间文学采撷,乃至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进步的世界观,都是缺一不可的”[12],依此吸纳多种文化资源中的优秀成分,并将之融汇于“民族形式”的整体创作上,也是一种不易偏颇的策略。
以上三次座谈会是当时寓居重庆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对“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文艺大众化路径集体的宝贵探索。从光未然参与的系列座谈会,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时居重庆的光未然,并没有置身于事外,而是力图通过座谈会这个途径与其他人进行意见交换,以期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拓展和深化。光未然上述三次座谈会的发言,虽各有论述的重心,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如何实现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可以说是特定的时代环境、文化背景与光未然个人创作实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座谈会上的片段发言,难以展现光未然文艺民族形式观的全貌,欲探其完整的理论体系还需结合具体文论来加以观照,尤其是长文《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
三、光未然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见解与贡献
茅盾对孔罗荪说:“顷得读《文学月报》第五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兄等之努力,殊为钦佩。而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特辑,尤感兴趣。光未然之长文(指《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引者注)及座谈会诸公之高论,大部分皆与鄙见相合。”[6]222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特辑”中,茅盾特别指出了光未然的长文《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可见该文在某种程度上乃特辑文章之重要代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在结构上颇具体系性,呈现了光未然立足于自身文艺创作实践与现实考量的基础上对文艺民族形式的理论建构。如果说,《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集中表现了光未然战时的文艺民族形式观,那么1940年10月15日再刊于《文学月报》以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文章《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则体现了光未然以“鲁迅对中国文学遗产的看法和整理工作”为个案对《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加以深化。其后,他在云南搜集整理彝族支系阿细人的创世史诗《阿细的先鸡》(1)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时名为《阿细的先鸡》,195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改为《阿细人的歌》。,则是其身体力行发掘和传承文艺民族形式的重要体现。以下基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结合光未然其他相关的文论和实践,撮要述之。
(一)戏剧“民族形式”的探索
长文《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谈到了有关戏剧民族形式的观点,光未然除了强调需要沿着“话剧”与“歌剧”两条路继续前进之外,还特别指出了“抗战中生长起来的戏剧新形式,街头剧,活报剧之类,她们能够更生动更迅速地反映现实,今后也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发展。”[13]此观点与其1937年10月20日在上海《新学识》发表的《论“街头剧”》所提一致,“在救亡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急需广泛展开的今日,各种‘街头剧’的大量创作,被迫切而又迫切地需要着。”[14]76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光未然在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就参加了由进步青年组织的“秋声剧社”,1935年协同友人组织了“拓荒剧团”。他所写的独幕剧《胜利的微笑》《阿银姑娘》及田汉的《水银灯下》,曾作为“拓荒剧团”的“国防三部曲”在汉口公演,引起了文化界的瞩目。1938年,光未然结集出版了《街头剧创作集》,这部集子具有总结先前戏剧创作演出经验与指引当前戏剧发展的双重性质。同年1月20日徐子明便于《大公报·战线》刊载了有关光未然《街头剧创作集》的书评,“自从‘街头剧’的口号叫了一年余以来,就没有看到一本‘街头剧’专集的出版!现在有了,那就是光未然先生的《街头剧创作集》……这本书的特点,不仅在‘街头剧’剧本万分缺乏的今日,提供几个新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对于‘街头剧’理论的建立。”[15]后来,1938年10月,光未然还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深入晋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及1940年2月21日出席了由“文协”主持的“对于目前戏剧工作之意见与感想”的戏剧晚会。以上,之所以赘述光未然戏剧创作活动方面的经历,意在说明他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中对戏剧方面所提出的观点,并非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其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戏剧演出和创作经历的理论总结。纵观光未然的整体人生历程,他虽以“革命诗人”自许,但实际上作为戏剧家的经历(包含戏剧创作、戏剧评论、戏剧演出),在时间线上更为久远。
(二)诗歌“民族形式”的实践
在诗歌方面,光未然认为“我们的诗歌一定要走到群众中间去,教育着和锻炼着大众的诗人。这就不得不依托于街头诗和朗诵诗歌的方式。我们的朗诵诗歌和诗歌朗诵运动,在今后将要得到大规模的开展,而且更进一步和音乐结合起来。”[13]提倡音乐化的朗诵诗,可以说是光未然抗战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色,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便脱胎于朗诵诗《黄河吟》。在文章即将收笔之际,光未然还不忘再次提醒:“在诗歌的民族形式的创造上,就必须扩大诗歌工作与诗歌朗诵运动,而在朗诵方式和朗诵工作的组织与进行上,也要酌量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13]光未然篇末这一吁求实际上是其诗歌民族形式主张的重述。笔者曾对光未然抗战时期的朗诵诗创作与诗歌朗诵活动进行考察,综合种种分析,得出以下拙见:“光未然作为朗诵诗人群体中贡献较为突出的一位,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有朗诵诗的相关创作,之后更是诗作迭出,其中既有应时而生的急就篇章,也有苦心孤诣的宏篇佳作,在那高旷的笔墨和质朴的诗行里充溢着战斗的激情。抗战期间,光未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动而辗转多地进行朗诵诗的宣传与推广,其中以武汉、延安、重庆、昆明等地为主。故而,在某种程度上说,透过光未然的朗诵诗创作实践,我们可以窥见战时朗诵诗发展的概况甚至全貌。”[16]就诗歌而言,朗诵诗确实是光未然实现战时诗歌大众化和探索诗歌民族形式的重要途径,而“革命诗人”的身份则成为了其最为人熟知的历史角色。
(三)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的认识
对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的论争,他认为:“我们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经过清算经过批判以后的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全部,包括各式各样的旧形式,和旧形式的各式各样的独特的要素,和五四以来的新形式的健康的要素,加上此刻还未被民间旧形式所包纳的,然而已经在大众中间创造着运用着的,表现新事物新感情的生动活泼的语法和样式。”[13]当时文艺界对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的讨论正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大致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是以向林冰为主的肯定“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17];二是以葛一虹为主的将“旧形式”视为“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18],强调应当“继续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艰苦斗争的道路,更坚决地站在已经获得的劳绩上,来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新形式——民族形式。”[18]以是观之,光未然持论较为客观。笔者认为光未然对此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受到上述两种极端主张的干扰,反而取得了二者的平衡,这是他对于传统文艺与五四新文艺何以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切体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和方法论意义。茅盾在《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回应了光未然的主张:“不久以前,大后方发生了关于民族形式的一场‘论战’。据我所见的材料,论争的焦点是民族形式的所谓‘中心源泉’的问题。有人提出了民族形式不得不以民间文艺形式为其中心源泉的主张,并就‘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成就,大众化通俗化,‘旧瓶新酒’,乃至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等等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大正确的议论。这一切,在郭沫若、潘梓年、光未然等先生的批评以后,可说已经得到了解答,‘民间形式’之不能看作民族形式的所谓‘中心源泉’,实已毫无疑义。”[19]对于旧形式、民间形式,光未然认可其中的优秀成分,但同时又否定将其作为文艺发展的唯一源泉,而是主张“综合论”的观点。在写作《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之前,光未然就与臧云远去听过民间艺人山药旦的大鼓,并于《新蜀报·蜀道》发表文章《介绍山药旦先生的新作<杀家哭庙>》,大赞该作“的确是一个杰作”,呼吁大家应辩证地看待旧形式,在创作实践中加强旧形式的研究与创造性运用,以“创造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作品”[20],这说明光未然对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的认识是建基在切实的考察中。
(四)对鲁迅发掘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思考
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中,光未然即指出鲁迅的《阿Q正传》的开篇和章法是“正确地运用旧习惯的实例”[13]。随后1940年10月15日,光未然在《文学月报》第二卷第三期之“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上发表了文章《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该文虽是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悼文,但文章论述的主题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见解与贡献,显然承接了其此前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中的思考。在此略加延伸的是,凌孟华在论述光未然的诗歌《鲁迅逝世三周年挽歌》时(2)该诗刊于《新新新闻旬刊》之《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谈及了《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一文并没有被刘可兴、石琳琳等光未然年表、著作书目编者所提及的遗憾,强调“张光年资料收集与研究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学界欠着一笔旧账”[21]。循此回望当前学界的光未然研究,或许《黄河大合唱》的光环太过于耀眼,致使既有研究大部分均围绕《黄河大合唱》来一谈再谈,不免忽视了光未然在其他方面的历史成就,这确实需要相关研究者多加关注与开掘。
对于鲁迅与“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关系,详读当时“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鲁迅逝世后,左翼文化界迅速组织了一系列文化纪念活动,树立起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界的地位……鲁迅的作品逐渐被看作是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典范性文本,构成了‘民族形式’学习和模仿的目标。大多论者有意识地勾连起鲁迅与传统文艺之间的联系。”[4]65-67光未然也是众多纪念者与追慕者之一。在上编“鲁迅对于传统的见解”中,光未然开篇即提纲挈领地指出:“鲁迅,是第一个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存在的人,也是第一个认识了传统文化的意义的人。”[22]结合鲁迅作品的具体论述,光未然归纳了鲁迅对于处理旧形式问题的见解,即把否定旧文化和研究文学遗产区分开来;采用旧形式应当立足于现实主义和文艺大众化;对刚健、清新、写实的民间形式应多加关注;旧形式与西欧艺术可以相互融合等等。实际上,这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在下编“鲁迅整理文学遗产的工作”中,光未然肯定了鲁迅对于整理文学遗产的严正态度,指出“鲁迅整理中国文学遗产的业绩,最为世所重的自然是《中国小说史略》”[22]。在文章的结尾处,光未然对鲁迅表达了诚挚的崇敬之情,强调鲁迅一边韧性战斗着,一边还“替我们做了这样多的整理遗产工作的优秀的范例。这些优秀的成果,连同他的其他方面的光辉的述造,连同他的毕生不屈不饶的战斗精神,都将转过来成为我们民族的最宝贵的遗产,留给后代的人们来承继,来发扬光大。”[22]可见,光未然对鲁迅的历史定位是多方面的,但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上,他凸显鲁迅在整理文艺遗产方面的功绩,无疑起到了坚实的榜样支撑作用。
(五)搜集、整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
光未然对于文艺民族形式的倡议不止于口号的呐喊,而且落实到了他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实践中,正如他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篇末所呼吁的那样:“一些新鲜活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东西,都不是在书斋中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群众生活中和群众工作中创造出来的。”[13]光未然在上述所论的《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一文中评价鲁迅时也说:“他的不朽处,实不仅在于他的文学上的成就,更不仅在于整理中国文学遗产的工作。”[22]同时他也认同“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最为悠久的,而整理文学遗产的工作也最难着手”[22],但他却在抗战的艰难时世中不遗余力地对彝族史诗《阿细的先鸡》进行了搜集和整理,这段深入“民间”的经历,促使光未然对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文艺有了新的体认,是其从实际行动发掘文艺民族形式的体现。其中的原因,一方面缘于光未然对民间文学与民族形式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自始至终,民间文学总是在文艺传统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艺的源泉”[13];另一方面则由于光未然希望“把一向惯用的小众化的诗语言解放到大众化的诗语言的程度”[23]95。
《阿细的先鸡》是流传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西山一带彝族支系阿细人的著名创世史诗,同时也是他们民族具有标本性质的文化艺术之歌,蕴含着阿细人丰富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光未然本着“把他们的声音广播到全世界”[23]91这样一种庄严的责任感,第一个使用文字搜集、整理、记录了《阿细的先鸡》,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工作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得《阿细的先鸡》从传播层面上获得了新生命,同时也进一步延伸了对文艺民族形式的探索。笔者认为光未然辑录的版本虽显稚嫩,但却为后来如袁家骅、“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等关注及研究以《阿细的先鸡》为代表的阿细人的民歌及其语言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开端。
光未然上述有关民族形式的见解与贡献,既回应了时代对文艺的叩问,同时也是其在文艺与时代的互动中探索出了自我的认识,从而在抗战时期众多有关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观点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其实,无论是早期倡导街头剧、朗诵诗和朗诵诗运动,还是民族形式论争时发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乃至之后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阿细的先鸡》,均是具体的接近民众的文化工作,而这很大程度上关涉到光未然对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性质与意义的认识与界定,“它不仅是创作方法上的问题,而且是文艺政策上文艺路线上的问题;不仅是通俗化大众化的问题,而且是提高中国文艺水准的问题;不仅是利用旧形式或创造新形式的问题,而且是清算并承继民族文艺的优良传统,发扬并广大之的一种继往开来的责任问题”[13]。如此一来,将光未然战时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实践联系起来看,实则体现了其连续相生、步步紧扣地对文艺民族形式进行思考和建构,其意义已远不止于对“民族形式”问题本身的探索。
战时文艺界对文艺“民族形式”的吁求,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大众化和实践性,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所接受和践行,光未然即积极参与其中。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民族形式的探索并不止于论争热烈之时,在论争开展之前就已有相关的创作与实践积累,在论争退潮后仍不遗余力地搜集和整理民间的文学形式,直至晚年,还结合新的认识修订文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龚刚的回答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民族形式论争虽然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关于民族形式与民族化路线的探索并未终结,而且延伸到了新的世纪。”[5]当然,这自是别一话题,留待后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