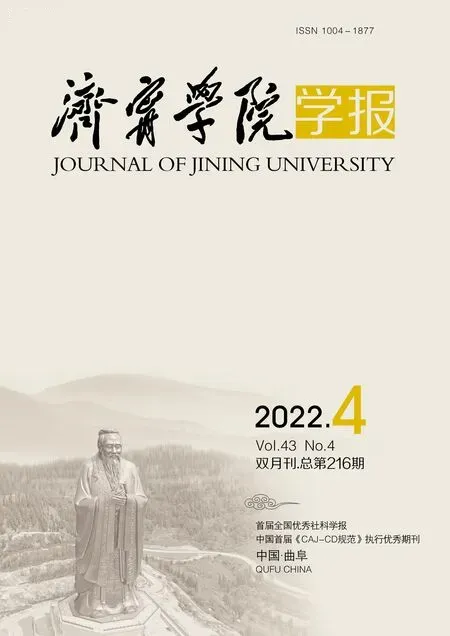文类·文体·艺术手法:林语堂论《水浒传》
2022-03-17陈智淦
陈智淦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和五四时期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林语堂是一位通才。他虽然身兼作者、学者、编辑和译者等多种角色,但其古今、中西兼通的学者身份往往为林语堂研究者所忽略。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认为,林语堂学问驳杂,“在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辞典编辑法、目录学各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上”[1]237-238,林语堂不仅在语言学的专业研究领域中贡献卓著,而且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研究领域亦有涉猎。林语堂自小博览群书,广泛接触中外文学遗产,“因而在作品中往往引证中外、杂谈古今,以炫示他的博学多才”[2]240。就中国古典文学而言,林语堂尤其推崇、偏爱明清文学。林语堂的生活艺术观及幽默、性灵、闲适的审美趣味与明清小品有关,其红学研究论著《平心论高鹗》也是别具个性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集中体现。国内学者王兆胜认为,除了《红楼梦》,“林语堂对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可能主要停留在阅读、了解和使用层面”[3]47;也有学者认为,林语堂的学术研究成就不会比他的文学创作成就逊色,“林语堂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事实上,他的学术上的成就要高于文学上的成就”[4]8;季维龙、黄保定在谈及林语堂及其著译时也指出:“林语堂和他的大量著译,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主要事业是在文化思想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方面。”[5]3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未有专文系统探讨林语堂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其它古典小说的评述。实际上,林语堂阅读明清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札记最早见于1913年12月他在大学就读期间刊发在《约翰声》英文版第24卷第9期的一篇文章《中国小说》(ChineseFiction)。他在该文中认为,一些伟大的中国小说克服种种偏见,至今都没人能否定它们的存在[6]18-19。1930年1月,林语堂在演讲稿《论现代批评的职务》中表示,现代大学教育制度需要提倡思想,理想的大学毕业生不但需要具备渊博的学问,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一位头脑清楚思路通达的人,对于普通文化事物,文学、美术、政治、历史有相当批评的见解”[7]7。换言之,一位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人也应该对现代思想、政治、文学等形成自己的认识。林语堂主张文学批评者需具备一定“批评的智力”或“批评能力”,因此,他对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不可能停留在浅层维度上。在明清小说中,林语堂对《水浒传》的研究深度仅次于《红楼梦》,但国内外学术界并未有系统探讨林语堂对《水浒传》文学类型、文体语言、艺术手法、作者及其创作过程、读者、版本考证等问题的文章。1933年9月,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首次英译《水浒传》70回全译本AllMenAre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分别由纽约的约翰戴公司(又译庄台出版公司)及伦敦的梅休安出版社出版,畅销欧美。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出版后,林语堂即刻在《白克夫人之伟大》一文中向中国读者介绍赛珍珠及其代表作《福地》,但并未论及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从1934年1月至1935年4月,林语堂在中、英文评论文章中三次盛赞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的翻译质量[8]129-130。这些文章侧重介绍赛珍珠及其《水浒传》英译本的翻译问题,都没有直接评论《水浒传》。因此,林语堂在民国时期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单篇文章、各种著述和译著等材料中对《水浒传》的评论亟待进行系统梳理。
美国著名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认为,每一件艺术品必然涉及作品(文学作品)、艺术家(作家)、世界和欣赏者(读者)等四个要素[9]4。他提出的上述文学批评四大要素的理论已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6)国内著名学者李赋宁指出:“美国斯坦福大学已故比较文学教授刘若愚先生曾运用艾教授的四大要素论阐述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参见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赋宁《中文本序》,第1页。一般而言,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一个自足体。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认为,单独对这个自足体加以研究并不过时,因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去分析研究实际的作品”[10]149-150。他们赞同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反对的内容与形式的传统二分法,主张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应该包括文类(即文学类型或文学种类)、文体(学)、艺术手法(艺术观点、叙述技巧)等。林语堂同样非常重视对《水浒传》作品本身的分析。本文拟以林语堂评论《水浒传》的文本史料为基础,以其《水浒传》作品的“内部研究”为线索,全面系统梳理其对《水浒传》的判断性文字论述,从中管窥林语堂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审美倾向,以便为其中国古典文学知识体系、阅读史的研究及完整构建其独具特色且产生一定影响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话语的图景夯实基础。
一、《水浒传》之文类
文学类型或文学种类可简称为文类。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非常重视该问题,在《文学理论》中曾单章进行探讨,它“不仅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因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种类特性是由它所参与其内的美学传统决定的……文学类型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秩序的原理……不是以时间或地域(如时代或民族语言等)为标准,而是以特殊的文学上的组织或结构类型为标准”[10]258-259。换言之,文学类型理论假设每一部作品都属于某一类型,并与其它作品紧密联系,具有继承性;文学类型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新作品的增加而改变。亚里斯多德与贺拉斯的古典类型理论作为范本,他们提出的悲剧、史诗、喜剧、讽刺等传统旧称一直沿用至今,现代文学理论倾向于把想象性文学区分为小说、戏剧和诗三类。艾布拉姆斯和哈珀姆尽管对文学类型划分模式的任意性表示担忧,但他们同样认为,“文学类型的区分仍是文学话语中不可或缺的”[11]301。文学类型的探讨应该更具包容性,他们指出“文学类型划分交叉的多层次,以及单个文学作品又[可以]被划分为众多的亚类”[11]297。
1929年10月7日,林语堂在《新的文评序言》一文中反对文学作品的文学体裁之说,“文评家将文分为多少体类,再替各类定下某种体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为方便起见,尽可分门别类,为权宜之计……”[12]153-154他认为,艺术作品的体裁格律之说理论上也不能成立,“因为每样艺术创作就是一特别作家特别时境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使本人轮回复生,也绝不能再做同一个性的文章”[12]154。换言之,为艺术作品分门别类是权宜之计,就艺术作品本性而言,每一个艺术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水浒传》等这些具有口头文学传统的虚构性作品的文类划分不但困难而且也不太重要,加拿大著名的文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同样认为,“与口头语言和听众有关的文类是很难用英语来表述的”[13]309。
1935年2月20日,林语堂在《小品文之遗绪》一文中强调,“中国好的散文,大部分全在白话小说,但此种散文,多半叙事,而非议论”[14]44。可见,他所认同的散文文学类型包括小说。1935年7月31日,林语堂在《说本色之美》一文中再次表示对文人包办文学的憎恶,“其实在纯文学立场看来,文学等到成为文人的专有品,都已不是好东西了。历朝文体,皆起于民间,一到文人手里,即失生气,失本色,而日趋迂腐萎靡”[15]3。相反,《水浒传》这类取自于民间文学传统的作品才是具有本色之美和文学价值的佳作。他说,除了一般民谣山歌远胜于文人所作的诗文之外,“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愤而著者自遣,排弃一切古文章笔法,格调老套,隐名撰著,不当文学只当游戏而作的”[15]3。换言之,林语堂认为,《水浒传》这类优秀作品往往能够排除文学种类彼此之间的区分,创作者在已有类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用随手可用的文学技巧进行创作,从而体现所有美学技巧,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文学作品给予人的快乐中混合有新奇的感觉和熟知的感觉。”[10]270
尽管林语堂反对文类之分,但他在《吾国与吾民》(1935)第7章《文学生活》中出于写作的便利,他还是对中国的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分门别类地进行介绍,并依据故事内容对中国的小说进一步细分。他说:“总而言之,尽管《红楼梦》或许代表了中国小说创作艺术的高度,但它也仅代表小说的一种类型。”[16]274林语堂根据中国小说各自的内容,进一步把它们分为8种类型。其中,《水浒传》(《四海之内皆兄弟》)为冒险小说最著名的代表。“我曾按中国小说大致的大众影响力顺序对它们进行分类。一系列街头小巷‘流动图书馆’的普通小说表明,冒险小说,即中文所说的‘侠义小说’,很容易位居榜首。在教师和父母如此经常设法阻止侠义、铤而走险的行为的社会里,这肯定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然而,从心理角度上这却是最容易解释的。在中国,侠义之人容易累及家族,陷入与警察或县官的纠纷中,他们被逐出家庭而步入下流社会;而侠义之士则太关心百姓疾苦,而且他们常替穷人或无助之人打抱不平,不得已而干涉他人事务,他们被逐出社会而步入‘绿林’(即‘盗匪’之称)。因为如果父母不和他们‘断绝关系’,鉴于法律保障缺失,他们容易毁坏家庭。在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社会里,一个人坚持替穷人和被压迫者打抱不平,他的确是‘坚不可摧’的硬汉。很明显,那些留在家里和留在体面社会中的人是那类不会陷入家庭‘断绝关系’之人。因此,中国的这些‘良民’非常崇拜绿林好汉,犹如纤弱妇人崇拜面孔黝黑、满脸胡须和胸毛蓬蓬的彪形大汉。闲卧榻上阅读《水浒传》而崇拜李逵勇敢和英勇行为,还有比这更安逸和更兴奋的事吗?记住,卧床阅读中国小说总是常事”[16]275-276。1937年,林语堂又在《生活的艺术》第10章《享受自然》引用张潮警句来描述《水浒传》:“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17]325可见,林语堂在谈及《水浒传》文学类型的问题时更注重描述读者对小说文本所作的反应。
1948年2月,林语堂首次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撰写一篇长达4300字的英文序言。他再次在该序言中借张潮的警句,即“《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这一深刻而简洁的格言来论述读者对该小说偏爱的缘由。他认为,如何理解“怒书”是理解该书对中国人为何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关键点。“这部小说包含了一种微妙但并不完全奇怪的儒家学说,即暴政时期不服从的权利和反抗的权利……不公道的政府和正义的盗匪一旦对抗,古今读者始终同情盗匪;实际上,这部小说变成了歌颂盗贼行为以及把法律作为武器的盗匪……这些草寇英雄内部表现出极高的荣誉、团结和忠义,大众对这伙盗匪无不表示钦佩。这种忠义在他们的誓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8]xiii-xiv。林语堂结合12世纪的讲史话本《宣和遗事》、14世纪元曲《黑旋风双献功》的故事情节以及16世纪李贽所写的《忠义水浒传》序言等文史资料,详细而客观地阐述《水浒传》为何是“一部怒书”的具体原因,“《水浒传》显然是一部怒书,它让百姓发泄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人们在听到这些草泽英雄敢于反抗政府并揭竿而起的故事时,为何会找到些许慰藉并有感同身受的欣喜,便不难理解了”[18]xv。可见,感同身受或贴近读者的内心世界就是他对张潮警句中所说的“《水浒传》是一部怒书”的理解,这和他认同的西方表现派的观点如出一辙。
总之,林语堂虽然反对文学体裁之说,但他既认为中国优秀散文存在于白话小说《水浒传》等作品中,又沿用普通分类法对中国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类型进行划分,并以小说故事内容为基础,结合读者反应批评的“感受文体学”论证《水浒传》为何属于冒险小说(侠义小说)或“怒书”。林语堂对《水浒传》似有互为矛盾的文学类型研究,无不体现了“能引起我们对文学的内在发展的注意”[10]271这一明显的文类研究价值之所在。
二、《水浒传》之文体
林语堂以对比研究的视角分析《水浒传》的创作语言,并非传统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学研究,而是以对比语言学为基础的现代文体学研究的体现,“因为文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将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当时语言的一般用法相对照”[10]191。语言学家出身的林语堂认识到,语言的研究对于《水浒传》的研究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
林语堂对语言观、语言学的关注始于其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他不断在校刊Echo(《约翰声》)上以英文发表《我们为何学习中文?》(Why We Study Chinese,1912年11月)、《汉语拼音》(The Chinese Alphabet,1913年4月)、《中国文学语言》(The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1914年11月)、《中国文学语言(续)》(The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1914年12月)、《我们的大学行话》(Our University Jargon,1915年1月)等多篇语言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1967年,他在《重刊语言学论丛序》中承认,虽然自己从语言文字学的“本行”“走入文学”,但他在数十年里“始终未能忘怀本行,凡国内关于语言文字学的专书,也时时注意”[19]序,1。因此,林语堂在创作《京华烟云》(1939)中才能完美地呈现北京话以及宁波口音、四川口音、福州口音、厦门口音和苏州方言等多种地方语言的听觉盛宴。
林语堂得益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一般语言学的全面基础训练,他深知语言研究的重要性绝不局限于对词或短语的理解。林语堂早年身陷文言与白话之争的文学革命漩涡中,关注那个时代的普通口语,尤其是下层百姓的日常用语、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社会方言、阶级方言)等问题,林语堂非常重视地方方言的研究,曾加入中国方言研究会并担任主席。从20世纪20年代起,林语堂多次表达自己推崇《水浒传》创作语言的观点。
1920年2月,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曾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刊发英文文章《文学革命与何为文学?》(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What Is Literature?)一文。他认为,大众教育的便利性是方言的巨大优势,作为与文言文相对的白话,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完全可以利用好方言,并引之入文。他以《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为例进行论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学观念的更新,“我们应该回头重新判断并重新评价虚构文学领域的民族成就;本着新学精神,我们应该对曹雪芹、施耐庵等民族文学巨匠(the kings of our literature)保持敬畏和钦佩之情。和这些巨匠一样,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大胆使用方言,因为方言是我们思想和感情最自然、真实和有力的表达”[20]29。林语堂认为,以《水浒传》等白话小说为代表的白话文学为文学革命播下了种子,施耐庵等白话文人的历史贡献不容抹杀。林语堂以《水浒传》等作品为例提出的这些观点具有历史的前瞻性,这比胡适1927年4月在《国语文学史》以及1929年6月在《白话文学史》中的系统梳理要早。胡适在1929年谈及当时国语文学形成的历史背景时说:“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红楼梦》……已经在社会上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时机已成熟了,故国语文学的运动者能于短时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21]引子,2
1933年10月1日,林语堂在《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提倡使用语录体的文学创作主张。语录体除了用于撰写政界演讲、书札之外,也可撰写小品文和诗歌。他认为,寒山子的诗就是语录体,“寒山子诗比白话诗质直……寒山之诗如说话,故好(东坡以词说理,亦复如此)。当今白话诗如作古文,故不好”[22]82-83。除了举寒山诗为例之外,他还举《水浒传序》的起句为例说明语录体的优势,“贯华堂古本《水浒传序》起句曰:‘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亦忽然之言也。此三语皆语录体,作白话文者,肯如是说法乎?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盖语录体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22]82。换言之,林语堂认为《水浒传序》较接近语录体,语录体是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桥梁,它具有文言和白话所不具备的优势。
1934年6月20日,林语堂在《论小品文笔调》中认为,西方散文中的小品文(familiar essay)和学理文(treatise)可分别视为表达个人思想感情、主观的“言志文”和非个人的客观的“载道文”。他翻译西方小品文笔调为“闲适笔调”“闲谈体”“娓语体”。作为《人间世》主编的林语堂专门提倡这种娓语式笔调。1934年10月5日,林语堂在《怎样洗炼白话入文》又进一步提出语录体为大众语,即白话文。他认为,“凡一国之文字必有其传统性,欲入大众口中之文字尤必保存其传统性”[23]11。他反对国语有毒,更不赞同明清小说有毒之说,他以幽默的口吻说:“谈大众语者非努力看大众所看之章回小说不可。今且有人主张‘改造’《水浒》《红楼》而去其毒,吾以为狗尾续貂的勾当仍是不做好。能改《水浒》者惟有啃窝头之山东第一流才子,非吃洋点心之青年……大众语弟兄非但《水浒》《红楼》要看,乃并张恨水《啼笑姻缘》亦不可不看矣。”[23]12大众语的写作与白话并无区别,林语堂以使用口语体为例的中外古今作家为例说,“Ernest Hemingway以美国口语写作小说,亦维妙维肖,实亦不异《水浒》《红楼》描写口吻之绝技”[23]12。林语堂在该文中还举例说明,元、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传奇、戏曲都是中国的平民文学代表,使用大众语,“所以注意白话文学者,正可在旧戏曲小说中研究其用字取材”[23]17。林语堂还引用李渔《闲情偶寄》第2卷《词曲部(下)》中的《时防漏孔》原话,“故笠翁推《水浒》文字第一。‘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长最大而寻不出丝毫渗漏者,惟《水浒》一书。’(少用方言)……曹雪芹,施耐庵,王实甫,汤若士皆是前例”[23]18。可见,林语堂完全赞同李渔视《水浒传》为使用顺口语言的典范。在他看来,《水浒传》等古典小说都是洗炼白话入文的典范,施耐庵等也是把文言和白话运用自如的优秀作家代表。
1935年11月1日,林语堂在《提倡方言文学》一文中指出,“所谓方言文学并弗是想取国语而代之,也弗是叫大家勿要写国语”[24]172,国语与方言尽管互为反义词,但他并不认为二者互不兼容。和胡适一样,林语堂认为国语文学成型的趋势是基于白话或方言文学的成熟。林语堂在该文中还主张白话与文言应该调和好,二者不是互相取代或竞争关系。相反,白话完全可以吸收文言里简约凝练的语言,明清小说、戏曲等作品中的白话、成语完全可以为写作所用,小品文的写作尤其如此。换言之,时隔15年之后,林语堂对方言文学所持的观点与其在1920年留学欧美时对方言文学的前景持正面看法如出一辙,即“和文言一样,方言文学应该能够给予读者相同的文学美感,也应该能够给予读者同样的审美享受”[25]36。
1948年2月,林语堂在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再版时写的英文序言中声称,《水浒传》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兴起的标志。他直接引用胡适的观点概括《水浒传》的语言特色:“小说很晚才进入到中国文学的范畴,因为中国学者写作所用的文言文现已不再使用,语言为刻板的陈腔滥调所束缚,非常不适于讲述故事,对话尤为如此。胡适博士对该部小说的产生和演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说,‘这部七十回《水浒传》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浒故事的大成,并且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18]xvi
可见,从1920年至1935年,林语堂除了在其间提出语录体为文言和白话的过渡语阶段之外,林语堂在白话文运动中多次以施耐庵用白话或方言创作小说《水浒传》作为例证来表明自己的语言观。如余娜所言:“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内部研究的重心放在语言上。他一直致力于新文学的白话建设,努力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寻找可供汲取的资源。”[26]56林语堂对《水浒传》中方言、白话的推崇和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国语文学运动时提出的主张一脉相承,这是他积极参与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见证。
三、《水浒传》之艺术手法
林语堂有关《水浒传》写作语言的论述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期刊期间提倡性灵文学和1928—1929年间译介西方表现派代表人物克罗斯(Croce)、斯宾加恩(Spingarn)等人的论调一脉相承。尽管林语堂对《水浒传》的语言赞赏有加,但对金圣叹点批《水浒传》却不屑一顾。
早在1928年9月20日,林语堂在翻译美国表现派文评家斯宾加恩《新的批评》一文时赞同译文中的观点,即艺术作品的格调作风与表现密切相关。他在翻译时多处添加译者按语,以中国的文学家和文论进行对比阐释,即阐发研究法,在翻译探讨“风格的学说(the theory of style)”内容时对比提及桐城派所讲的“文章义法”,在此部分长达6行的译者按语中,他举《水浒传》等为例表达自己的立场:“中国的什么‘书评’‘眉批’‘题赞’都是这一类的玩意,虽金圣叹也脱不了这个窠臼。什么文章百法,起承转合,首尾呼应,先事后波,此是伏笔,此是反衬,这是横云断岭,横桥锁溪,那是奇峰对插,锦屏对峙,这是近山浓抹,远树轻描,那是浪后波纹,雨后霡霂。试问是否这些章法笔法读好,便能著一部《三国》《水浒》?”[27]629林语堂在翻译这些文学批评理论时能有意识地用它来阐发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很难说具有系统性或完整性,但他能从中发现前人所未见的奥妙,这说明他不是被动地教条地接受西方文论,而是自觉运用西方文论阐述中国文学,这种“阐发研究法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起着重要作用”[28]296。尽管林语堂不赞同金圣叹的评点,但他对中西理论进行有意识的比较不容忽视,他完全有理由被视为中国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1929年10月4日,林语堂在《新的文评序言》一文中表示反对起承转合之法,他再次表示:“古文笔法是最无用的勾当……用这种章法的眼光,去读《红楼》《水浒》,正如瞎子摸象鼻,永远摸不着头脑,最多不过像金圣叹的满口‘妙甚’‘妙甚’叹其神化莫测。记得从前看金圣叹批《水浒》,到林冲将遇害一段,明明白白是作者故意造作牵强失实Melodramatic之处,金圣叹只记得在那里称叹布置之奇妙,转折承伏之得法。试问转折承伏,一抑二抑,一结二结的手段学好,就能做出一部《水浒》《红楼》吗?”[12]154-155他认为中国某些文评家与西方表现派仅是理论相近而已,甚至主张“性灵说”的袁枚的某些主张“简直是与表现派理论背道而驰”[12]156。
1933年1月1日,他在《文章无法》一文中引用中国浪漫派批评家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篇》、袁子才《书茅氏八家文选》等文的观点说明,写文章与作八股完全不一样。林语堂虽然赞赏金圣叹借施耐庵之手而写的《水浒传序》,但对金圣叹点批《水浒传》并不以为然,他第三次表示,“凡人不在思想性灵上下工夫,要来学起承转伏做文人,必是徒劳无补……金圣叹本为吾所佩服,惟少读所批《水浒》,专在替施耐庵算‘一伏’‘二伏’‘一承’‘二承’,啧啧称叹,试问施耐庵撰《水浒》行文时,果曾知其一伏二伏乎?若不然,则所谓笔法,并无真实意义。且学了起承转伏的人,便能撰一本《水浒》吗?”[29]2461933年11月1日,他在《论文》一文中认为,作者真情感的流露,即“会心之倾”“会心之语”才能打动读者,而非千篇一律的无情感的修辞章法。他称这种令读者触景生情的文章最为上乘,并以施耐庵《水浒传序》为例说:“会心之语,一平常语耳,然其魔力甚。似俚俗而实深长,似平凡而实闲适,似索然而实冲淡。”[30]172换言之,林语堂简单地理解克罗齐“艺术即表现直觉”的美学理论为直抒胸臆,语言学出身的他高度辩证地看待语言使用问题,这与金圣叹点批《水浒传》作者创作时刻板、造作的手法格格不入。
林语堂极度推崇17世纪的明末文学。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在《烟屑》一文中称:“明末文学观念大解放,趋于趣味,趋于尖新,甚至趋于通俗俚浅,收民歌,评戏曲,传奇小说大昌,浩浩荡荡而来,此中国文学一大关头也。故十七世纪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放光明。而世人不察,明末清初文学史当从头做起也。”[31]38同年12月16日,林语堂在《记翻印古书》中称明末清初的这种文学笔调为“闲散笔调”或“萧散笔调”,他极力赞赏明末文人道:“明末人懂得尺牍之佳境(时人尺牍保存不少),又懂得笔调之清趣,又能评小说传奇,又能搜山歌淫词,民间文学……毛声山之《评琵琶记》与金圣叹之《评水浒》,笔调见识,可谓一脉相传。”[32]320可见,林语堂在此之前虽然多次表示反对金圣叹点批《水浒传》的方式,但有意思的是,时隔3年后的他此时又表示赞赏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文字笔调。这或许是他自己所说的不可调和的“一团矛盾”的体现,即“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33]53。
总之,《水浒传》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审美评价必然存在多义性和包容性,即其丰富、广泛的审美价值就存在于作者活动的时代。林语堂在其所处的时代同样难以做到在不同时段保持审美评价信条的一致性,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一部艺术作品的成熟指的是它的包容性、它的明晰的复杂性、它的冷嘲和紧张性等,小说与经验之间的对应和符合关系决不能用任何简单的逐项相应配对的方法来衡量。”[10]285金圣叹和林语堂采取以小说的虚构世界与其各自所处的不同现实世界的经验进行比较,或是出于即兴式的感性判断,或是出于理性的推论性判断,两种判断没有必然的对错或矛盾,每一种评价方式都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四、结语
林语堂虽然不以学者身份自居,但他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异常另类。在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内各类报刊文章热衷于讨论现代小说或发表外国文学的译介文章,而林语堂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并未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甚少深入研究西方小说,但他却以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评论并向国外读者译介《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有限度地平衡了当时大量翻译引进外国小说作品的趋势”[26]62。林语堂在国内外刊发的大量文章对《水浒传》文学作品本身进行了具体实际分析与评价。语言学出身的林语堂在大范围综述基础上分析《水浒传》的文类问题,反对文学体裁之说的林语堂结合读者反应批评的“感受文体学”论证《水浒传》为何属于冒险小说(侠义小说)或“怒书”。同时,他极力赞赏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特色,认为这些小说的方言、俗语直接入文,为文言白话融合提供了典范,以此肯定中国古代小说的价值。此外,他以鲜明的阐发研究法评价金圣叹点批《水浒传》也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和合理性。总之,林语堂以现代思想和跨文化的视野阐释《水浒传》的内在价值,他对小说《水浒传》文类、白话语言、艺术手法等论述是其进行中国古典小说内部研究的重要例证之一,也是他向国内外读者和学术界传递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见证。学术界有识之士应该进一步系统梳理林语堂对《水浒传》文学批评要素的论述以及展开他对《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中国其它古代经典小说的研究,从而逐步完善林语堂作为学者型作家的形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