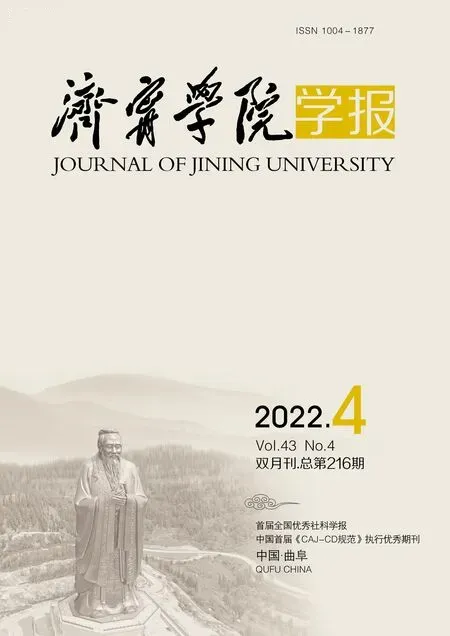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探析
2022-03-17孙雪岩范凯迪
孙雪岩 范凯迪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新西兰虽非大国,但在世界女权运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新西兰妇女早在1893年就获得了选举权,新西兰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仅自1997年以来,新西兰就出现了三位女总理,分别是珍妮·希普利(Jenny Shipley)、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和现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2000年,新西兰的主要国家领导人职务如总督、总理、议长、首席大法官一度皆为女性所占据,这充分体现了新西兰的性别平等。细究新西兰女权运动发展史,我们发现,20世纪60至80年代初的第二波新西兰女权运动,上承19世纪初追求政治选举权的新西兰第一波女权运动,下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西兰第三波女权运动,值得学界关注和思考。
一、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兴起的背景
(一)第一次妇女运动的不彻底是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的伏笔
新西兰第一次妇女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在争取普选权和参政方面取得一定突破。1919年,新西兰通过了《妇女议会权利法案》(Woman’s Parliamentary Rights Act),新西兰妇女获得了参选下院议员的权利,工党成员伊丽莎白·麦库姆斯(Elizabeth McCombs)于1933年成为新西兰史上首位女性国会议员;新西兰妇女在1941年又赢得了参选国会上院议员的权利,工党成员玛丽·朱阿韦尔(Mary Dreaver)、玛丽·安德森(Mary Anderson)于1946年当选。1947年,玛贝尔·霍华德(Mabel Howard)又成为新西兰首位女性政府内阁部长。尽管如此,新西兰妇女在工资、教育、福利和家务等方面与男性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所享受的民主权利并不充分,这就为新西兰女性进一步争取平等权利提供了条件。
(二)二战及战后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刺激了新西兰新一轮女权运动的到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新西兰女性地位的提升。二战期间,新西兰妇女就业人数激增,一些传统上男性职业的工会也开始接纳女性会员。新西兰妇女在工厂里生产军需品,并担任空袭警卫、消防员和疏散员,出现了女性消防车、火车和有轨电车司机。另外,一些妇女从事爱国主义社区活动,如为新西兰海外作战部队编织、缝纫、烘焙以及包装包裹。75000多名新西兰妇女参加了“妇女战时服务队”(Women’s War Service Auxiliary)(4)该组织由新西兰女权运动者艾格尼斯·班尼特博士(Agnes Bennett)和珍妮特·弗雷泽(Janet Fraser)建立,目的是对为战争服务的妇女进行协调和指导。,该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战时食品生产。新西兰的帕克哈族和毛利族妇女也被要求登记参加必要的战时工作。据统计,1939年9月,新西兰全国范围内有180000名女性劳动力,到1943年增加至228000人[1]17。此后,新西兰妇女日益成为新西兰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妇女们却因性别仍然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社会总就业率榜首仍然被男性牢牢霸占,妇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从事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在家庭生活方面,受社会主流观念的影响,妇女仍然处于依附地位,家庭暴力行为也频频发生。因而,她们强烈反对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希望她们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维护,希望自身的价值能够在社会中得到体现。这种对正当权益的要求,使得她们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兴起。
另外,反对越战运动和青年反文化运动也冲击和批判了新西兰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二、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的内容
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大量游行、抗议运动和请愿活动,设立了大批女权主义团体,掀起了颇具反抗色彩的女权运动。
(一)“酒吧解放”运动
女权主义运动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是新西兰在酒吧、俱乐部等社交场所进行男女隔离。新西兰大多数酒店的公共酒吧皆为专属于男性的空间。在这些场所,女性不享有接受服务的资格,只能在酒水更贵的休闲酒吧饮酒。20世纪7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主义运动人士掀起了“酒吧解放”活动。运动于1970年8月率先于奥克兰的布里托马特(the Britomart)展开,1970年9月继而在惠灵顿的新城酒店(New City Hotel)爆发。1971年6月,女权主义者闯入新西兰大北方酒店(Great Northern Hotel)的小酒馆,引发了混乱。尽管酒店管理层极力反对,但女权主义者一度占得上风。当年8月,该酒吧的执照持有者将酒吧变更为“私人酒吧”,根据新西兰法律规定,私人酒吧经营者可拒绝为任何他指定的人提供服务[2]101,酒吧解放运动及新西兰女权运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到20世纪80年代,将女性排除于酒吧之外的做法在新西兰最终消失了,酒吧解放运动也表明新西兰女性对传统上妇女只能做家庭主妇感到不满,新西兰社会习俗也在发生变化。
(二)“反选美比赛”运动
20世纪70年代新西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选美比赛”运动。在女权主义者看来,选美比赛是对女性的物化,将女性变成纯粹的身体和性对象,并纯粹根据相貌来评分。这里面包含了强烈的性别歧视,应该被废除。新西兰女权主义者克里斯汀·雷恩指出,选美比赛和女性的物化对她们的自尊有负面影响[3]58。1971年,新西兰小姐选美比赛在奥克兰举行,并在电视上进行现场直播。“争取平等”妇女团体在市政厅外进行了抗议活动,反对将女性身体物化。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抗议者切断了音响系统的电源,以至于新当选的新西兰小姐在开始其胜选演讲时麦克风失灵。1972年,新西兰小姐比赛在达尼丁举行。由70名妇女组成的“达尼丁”妇女团体(Dunedin Collective for Women)在会场周围打起横幅,上书“欢迎参加性爱表演”。对选美比赛的抗议在新西兰持续了整整十年。抗议活动发生在选美比赛收视率很高的时期,反选美者提出的观点慢慢影响了公众对选美比赛的看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选美比赛在新西兰已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
(三)“堕胎合法化”运动
“堕胎合法化”运动成为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浪潮中的重要活动。新西兰“堕胎合法化”运动非常激烈,贯穿了整个70年代。尽管对于堕胎问题,新西兰社会具有相当高的接受度,但堕胎实际上是非法的。在新西兰《犯罪法》中,堕胎是一种严重罪行,除非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而堕胎。因此,当时在新西兰堕胎只在危急的情况下才进行。在20世纪60年代,每年有多达300名妇女在堕胎之后被送进医院。女权主义者认为堕胎是“妇女的选择权”,1971年成立了新西兰堕胎法改革协会(ALRANZ)。新西兰堕胎法改革协会避免使用“按需堕胎”一词,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生育和养育问题。1973年,更为激进的妇女“堕胎合法化”运动展开了,旨在废除所有堕胎法。1977年,《避孕、绝育和流产法案》(Contraception,Sterilization and Abortion Act)获得通过。
(四)反对就业歧视、争取同工同酬运动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女权主义运动走向高潮,女性团体对仅依靠同酬立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深感不满。她们认为仅靠同酬立法不足以解决妇女在工作上面临的不利条件及歧视问题,呼吁各行业都应该扩大妇女的参与度。针对女权主义者的这一呼声,新西兰于1972年颁布了《学徒法修正案》,消除了女性学徒数量增加的立法障碍。1975年,为了回应女权运动人士对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面临的不利处境的持续关注,新西兰职业训练局(职训局)成立了妇女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for Women),该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推出“积极行动”计划。新西兰劳工部也实施了一些救济活动,通过“积极行动”运动试图扩大女性的就业范围,但收效甚微。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迫于女性团体游行示威的压力,新西兰1983年出台《学徒法》,1984年政府正式实行女学徒招聘激励计划。这一系列举措扩大了女性的就业范围,并确定和增加了非传统工作领域的培训和就业机会,在女性就业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五)毛利妇女争取主权运动
相对于新西兰的欧洲移民,毛利族是非主流民族。毛利族妇女在这一时期领导了争取主权运动,呼吁消除性别与种族歧视,复兴毛利文化,保留毛利族语言,争取毛利人主权。毛利妇女福利联盟(Maori Women’s Welfare League)以及300个分支机构在新西兰全国范围内的急速扩张表明毛利妇女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她们将女性权益扩展到公共领域,并通过与国家直接谈判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毛利妇女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1977年在惠娜·库珀(Whina Cooper)和乔·霍克(Joe Hawke)的领导下,毛利部落占领奥克兰的堡垒点,要求将土地归还给旺加努伊。这标志着激进女权主义的出现,也意味着一种新形式的激进主义打破了传统[4]。1979年,新西兰第四届全国联合妇女大会在汉密尔顿举行,在此会议上,自诩为黑人妇女活动家的毛利妇女与白人女同性恋、分裂主义者结成联盟,反对等级制度、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精神分离和种族主义,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转喻联系[5]21。在整个大会期间,她们通过一系列破坏性行为(如涂鸦、大声吟唱等),表达了对新西兰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不满。1981年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南非跳羚橄榄球巡回赛上,由毛利妇女领导的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与警方发生冲突。在毛利人不断抗争下,新西兰第四届工党政府在1985年实施《怀唐伊条约修正法案》,以解决毛利人提出的重新获得土地的要求,这在毛利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经不懈的努力,毛利妇女福利联盟成功说服新西兰政府将毛利语列为新西兰官方语言之一。
除了上述的活动外,此时期的女权主义者也通过非官方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对参政议政中妇女明显处于劣势的局面,女权主义者建立了妇女解放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团体进行抗议、游说等活动,以提升妇女在政治方面的话语权。如在奥克兰和惠灵顿成立了妇女宪章协会(Women’s Charter Associations),协会呼吁新西兰妇女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争取平等权利,推动新西兰社会废除一切性别歧视。1970年,作为国家发展规划工作的一部分,由米里亚姆·戴尔担任主席的妇女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就影响妇女的事项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1975年的国际妇女年迎来了“联合国妇女十年”(5)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当年举办了国际妇女世界会议,会议规定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其三重目标是促进平等、将妇女纳入发展方案以及承认妇女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方面的重要性。在新西兰国内,大会制定的具体目标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到男女之间选择的转变,帮助妇女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内外的能力和贡献,使妇女有信心尝试新的活动,并提高对其他国家妇女问题的认识。“她们通过向议会及其工作小组提交请愿书、写信给议会成员等方式,以政治团体组织的身份表达了妇女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要求”[6]389。
三、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初,新西兰社会女权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重新审视女性的价值、社会地位,并给予妇女更多的同情、尊重与理解。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影响上,这一波的运动远超19世纪末新西兰女权主义运动。这一波女权运动,也展现出了不同于19世纪末那次女权运动的特点。
首先,波及领域和范围更为广泛。19世纪末的新西兰女权主义运动专注于争取女性的选举权。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除政治领域外,还涉及经济、教育、文化、艺术、思想、生育、健康等方面,几乎渗透于新西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均是19世纪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所不可比拟的。而且,除了白人妇女外,毛利妇女也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涌现出大量妇女组织并发挥了有效作用。1970年,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成立了该校第一个妇女解放组织“妇女解放阵线俱乐部”。同时期,奥克兰也成立“争取平等妇女组织”。随后不久,达尼丁、克赖斯特彻奇、惠灵顿和北帕默斯顿迅速形成新的女权主义团体。1972年4月,新西兰第一次全国妇女解放大会召开之后,女权主义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妇女解放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新西兰家庭主妇联盟、国家妇女组织、妇女选举游说团等。这些妇女组织主要运用法律手段与女性歧视行为作斗争。作为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妇女组织在教育、就业和争取社会福利方面为妇女争取利益,代表妇女与政府或立法组织进行讨论和沟通,广泛利用非政府论坛开展活动,成为政府与非政府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
再次,指导思想呈现多元化。受当时国际上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新西兰女权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20世纪60至80年代,新西兰女权主义运动涌现出了多个派别,此起彼伏,交相辉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自由派、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派。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女权运动重新站上历史舞台,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体系。受其影响,新西兰涌现出一批由左翼成员组成的妇女解放组织。例如,奥克兰、惠灵顿的劳动妇女联盟和妇女工会就属于社会主义派女权团体。1972年成立的新西兰妇女全国组织是自由派女权主义在新西兰复兴的开端。自由派女权主义的宗旨是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使女性进入新西兰社会的主流,让女性在机会平等的原则下生活。激进派女权主义的代表是新西兰“女权主义运动”组织。与其他的女权主义理论相区别,激进派女权主义的理论来源于女权运动的实践斗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把父权制看作压迫的根源,主张废除现有的性别体系以实现解放。根据这一宗旨,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男女平等的真正要求是消除自由社会中的父权制[7]57。同时她们还认为,一部分人缺少从女权主义角度看问题的视角,呼吁大家要通过“女权运动”看到自己的特殊之处,将自己与那些具有改革热情的女性分开[8]9。1975年,激进女权主义者开始建立激进女权主义核心小组,并在1976年至1978年建立了激进女权主义专属网站。
四、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的影响
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推动了新西兰的社会变革,并加速了新西兰社会妇女地位的提升,对新西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在政治方面,女权运动提高了新西兰妇女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国家党形成了由女性担任副总统的传统,工党妇女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其活动的权力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两大政党都选举了女性担任领导人,分别是1982年的国家党主席苏·伍德、1984年的工党主席玛格丽特·威尔逊。她们既是女权主义者,也是政党组织的成员。1933年新西兰国会仅有一位女性议员,但到1984年女性议员的占比就超过了10%,并且这一时期女性参政率有了明显的提升。针对女权运动者要求的增加议会中的女性代表以及在政党议程上优先考虑妇女问题,新西兰工党政府作出回应,1985年在内阁中设立妇女事务部,专门负责妇女问题,首任部长由玛丽·奥·里根(Mary O’Reagan)担任。
其次,在经济方面,女性的就业率和经济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就业范围更为广泛。1972年的《同工同酬法》保护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女性雇员具有同工同酬的权利。1976年,新西兰赋予妇女“无过错离婚”(no-fault divorce)的权利,并明确规定离婚后妇女可获得夫妻共同所有财产的一半。女性就业已不再局限于传统行业,在高新技术和高层管理职位中也经常看到女性的影子。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妇女逐渐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女性生理特征造成的就业限制逐渐消失,女性就业渠道增多。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事过去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工作,性别分化体系正在向性别平等体系转变。
再次,在教育方面,进入到高校进行深造的女性数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学习的专业也很广泛。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年轻女性离开学校的时间比同龄男性更早,学历也更低。与男性相比,年轻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更小。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年轻女性与男性有了同样的获取更高教育水平的资格,也能接受高等教育。1975年只有25%的医科学生是女性,但到1988年,这一数字已增至60%。类似的增长也发生在接受律师、牙医、会计师和中层管理人员培训的相关专业中[9]85-116。值得注意的是,自1977年以来,有44个(约占总额的42%)罗兹奖学金名额(新西兰特波凯塔拉大学)颁发给了在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女性。40%的卢瑟福纪念博士奖学金授予了在剑桥攻读学位的新西兰女性群体[10]4。此外,女博士、女教授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她们在很多领域创造了非凡成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量社会调查显示,“只有极少数的女大学生认为接受大学教育是为了组建更好的家庭铺路,将近一半的人则认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准备”[11]56。
最后,在认知方面,女权运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新西兰社会对妇女的成见。长期以来,媒体、杂志、电视广告和节目都有意无意地强化妇女的传统女性特征。妇女们从多个方面尝试打破陈旧的观念,改变以往那些错误的、有辱人格的陋规。同时女性认识到,要想改变形象,必须扩大和加深公众对妇女的了解,妇女对自己的重新评价也是反对性别歧视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妇女研究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由于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她们给媒体带来的压力以及运动引起的公众意识的提高,使得媒体在报道妇女问题时更加谨慎。不仅对妇女传统形象的宣传和描绘越来越不受欢迎、吸引力也越来越低,而且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媒体上出现了有关堕胎和儿童保育等妇女问题的文章。由于女权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报道关注女性在家庭之外的角色和生活。更重要的是,随着女权主义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妇女的问题和要求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报道帮助人们重新思考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妇女形象,拓宽视野,更多地关注妇女问题。
五、结语
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的女权运动是外部冲击与内在反省共同作用的产物。受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新西兰社会经历了剧烈变革,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既有的思想也受到欧美女权主义理论的冲击。这些都成为女权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助推剂。而且此时期的女权主义运动者也吸收了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经验,对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缺陷进行了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运动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斗争的途径、方式以及规模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新西兰女权运动的目标远比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目标明确和具体,已不再满足于获得选举权,而是波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如要求参政比例的平等权、男女就业机会平等和同工同酬、同等的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权以及性权利的平等。这场运动对新西兰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以及家庭生活模式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新西兰政府对女性的关注显著提高,社会和妇女群体自身都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历史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另外,新西兰女权运动对太平洋区域的其他国家产生了一定的“蝴蝶效应”。毋庸讳言,这一时期新西兰女权主义运动也存在一些不足:理念上,将女权主义简单化,把争取平权视为与男性争权夺利,仍带有传统的“男女有别”观念;结果上,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女孩在接受高等教育或研究生学习方面仍面临诸多障碍,毛利族和非白人血统的女性低学历比例仍明显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