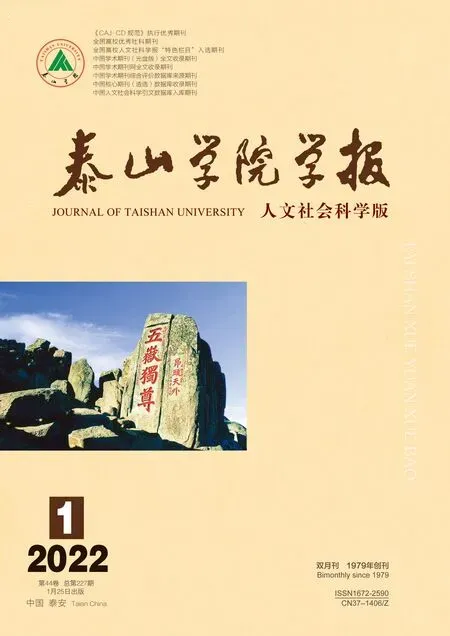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佛教起源与发展辨析
2022-03-17李震
李 震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泰山自古便为东方名山,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泰山其地不仅仅以道教闻名,早在魏晋六朝时期,佛教便于此地形成规模,并从整体的历史进程看来呈现出持续发展之势。本文旨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泰山佛教及其后来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探析,主要从玄学思潮,泰山本土信仰,道教思想,以及泰山羊氏家族的崇佛等多角度展开论述。
一、玄学思潮对泰山佛教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在思想界占有主流地位,诸多士族名士与山林学者在批判与继承两汉经学的基础上大谈玄学。佛教方面,南朝之前,般若学在中国盛行。魏道儒先生说:“般若类经典强烈的怀疑论特色和否定权威的倾向。就这一方面说,般若学与玄学的批判精神是合拍的。”①魏道儒.佛教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避世清谈的玄学与假有、性空的般若学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玄学一方面打破了儒教的条框,另一方面又给佛教注入了新的生机。
从中土整体性佛教的发展看来,般若学一时盛极,东晋皇帝请高僧讲般若经是为常事,如竺法济的《高逸沙门传》载:“元、明二帝,游心虚玄,托情道味。”简文帝尤其擅长清言玄学,为此他去瓦官寺听竺法汰讲《放光般若经》②杜继文.佛教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此处可见玄佛之间的共通之处,爱好玄学的皇帝亦对般若学百般爱惜。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佛教信仰传播,各朝建寺造像、举办法会之风盛行,虽然南朝之时佛教的主要议题逐渐向佛性论转折,但是般若学仍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魏晋时期的般若学仍是作为佛教中的显学流行于鲁地,而擅长般若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郗超。高平郡(今山东济宁)人士郗超作为东晋权势倾朝的名士具有不凡之卓识,“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③(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郗超善于玄学,亦精于般若,当时支遁是般若即色宗的代表,郗超大致持相同观点。④赵凯球.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佛教概说[J].文史哲,1994,(3).“晋郗超《奉法要》所述,约与支译同”。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作为玄学名士的郗超,其地位与名望对山东地区佛教般若的流行起到助推作用。另外,泰山地区玄佛共修的名士还有北齐羊烈。从造像碑刻中或可以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在僧传中我们无以窥探僧朗、法定等魏晋高僧具体在泰山传授何法,但是从宏大的泰山经石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②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书刻之作者学界有大致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明代孙克宏认为其出自韦子琛之手;第二种是清代聂剑光认为出自王子椿之手;第三种是现人王思礼、赖非主张是安道壹所作。以上三种说法之作者均为北齐人士。,泰山北山崖壁上刻有的《摩诃般若经》、《文殊般若经》、徂徕山的光化寺将军石上所刻《大般若经》以及梁父山映佛岩上的《般若波罗蜜经》等等,很明显得知般若学在泰山佛教中亦是占据主流。泰山地区的般若学在玄学的渗透提领下得到可观的发展。
《高僧传》在僧朗的附传中载有:“时太山复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游陇,长历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数论,著《人物始义论》,亦行于世。”③(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此段言意僧朗时代的泰山丛林中,还有另一位史料可循的僧人名叫支僧敦,其有著作《人物始义论》。有关支僧敦所著此书,《高僧传》中并无记载其内容,而其他传记中亦无处可寻,至今早已亡佚。但慧皎在康僧渊的附传中有记载康法畅曰:“畅亦有才思善为往复,著《人物始义论》等”④(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可见支僧敦所著之书与康法畅同名,如此内容而言也可见一斑。“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康法畅答道:‘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常在。’”⑤(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康法畅也善于清谈,并且持有魏晋其时象征清谈的标志——拂麈。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中记:“清谈的象征是拂麈”。其人不慕名利、无所欲求,谈话间亦泰然自若,且与喜好言谈、沉心老庄的权贵士族庾亮有所交往。此外,载其“每遇名宾”,说明他与当时的大多名士贵族都曾有往复。正如法畅的《人物始义论》一书就是品评当时贵族人物、玄学名士的论作,对同时代下的人做评,须要接触相识方能著此等作。故泰山支僧敦所著的《人物始义论》亦应如此。这样我们对于支僧敦的人物生平与交游对象便也清晰了起来,“少游陇,长历荆雍”⑦(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僧敦曾游历荆州与雍州等当时名士云集的军事政治重镇,想必也结识了不少同气相求之友,并且其性应与法畅无差,善长并乐于与诸多名士之流清谈,此来彼往之间玄释相互渗透。如此知其所受时下名士的玄学思潮颇深,随在泰山的布道中,难免会影响其地佛教的发展。
二、泰山本土信仰对佛教的影响
泰山自古就是著名的神山。汉武帝泰山封禅,其目的之一便是求仙,对泰山的封禅被当作是成仙的步骤。⑧时孟.3-6世纪泰山文化对佛教的影响[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五经通义》曰:“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⑨(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可见,人们自古就认为泰山之上存有神仙。在超自然的鬼神崇拜下,泰山在古老东方世界的地位日益高涨,随之产生了泰山本土的神仙信仰,也就是逐渐形成了存在于泰山地区的原生性宗教。杨倩描先生在《南宋宗教史》中提到:“当创生性宗教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原生性宗教势必会受到排挤。”⑩杨倩描.南宋宗教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而创生性宗教在发展之初是要依附于原生性宗教的。在泰山一隅,创生性宗教(佛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原生性宗教(本土信仰),泰山既有长生成仙之地一说,又有魂归之地一说,而后者的说法或对泰山佛教的植根发展产生的影响更甚。
东汉纬书《孝经·援神契》中载:“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古人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归于山岳,而泰山就是死后魂魄的归属之地,“魂归泰山”一说起源于魂归蒿里。颜师古《汉书注》其中有:“死人之里谓之蒿里……或者见泰山神灵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①黄 节.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蒿里山是死去之人的归处,其正位于泰山的脚下。魏晋时期的民众一直延续了“魂归蒿里”的观念,不过因为蒿里山名气不如泰山,遂逐步有了“魂归泰山”的说法,②时 孟.3-6世纪泰山文化对佛教的影响[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泰山“魂归”与“治鬼”等本土信仰渐趋形成。如《三国志·管辂传》有管辂谓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③(晋)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泰山佛教的引入要从东晋僧朗说起,在此之前,泰山作为死后魂归处的观念早已深入时人内心,泰山佛教能够顺袭发展,恰好是因为佛教中的某些教义与本土之信仰相契合。佛教重视人的死后世界,转世与轮回,其基本教义“四谛”中的灭、道二谛注重的就是人的归宿和解脱之路,而业报轮回亦为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随佛教中的“地狱”名词开始在中国流传,泰山逐渐与“地狱”一词建立起了联系。安世高在《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中首提“泥犁、太山地狱道”,另外在此一经中出现若干有关泰山(太山)地狱的词汇:“若人作恶得恶若干罪,或入太山地狱中,或堕饿鬼中,或堕畜生中。”“从是得五恶,何等五?一者不慧,二者少知,三者不为人所敬,四者入太山地狱。入太山地狱中,考治数千万岁。五者从狱中来出,生为人愚痴无所识知。”④(汉)安世高,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A].大正新修大藏经[Z].第17册.自始一来,泰山本土信仰中的死人归处便与佛教中六道之一的地狱道相契合了。此后的僧人都不约而同承认了“泰山地狱”的观念,翻译出了众多与泰山地狱有关的经典。周郢先生在《泰山“佛教山”的形成与变迁》列举出描述泰山(太山)地狱的译经有《六度集经》、《佛说三摩竭经》、《五母子经》、《佛说四愿经》、《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佛说优填王经》、《出曜经》、《佛说自爱经》以及《鬼子母经》等。⑤周 郢.泰山“佛教山”的形成与变迁[J].地域文化研究,2019,(2).另外还有诸如佚名译《大爱道比丘尼经》:“投命太山地狱之罪,难可堪任。生时不学死当入渊,老不止淫尘灭世门,呼吸而尽何足自珍。”⑥佚 名,译.大爱道比丘尼经[A].大正新修大藏经[Z].第24册.支谦译《佛说八吉祥神咒经》:“是人终不堕太山地狱饿鬼畜生中也,是人终不望取罗汉辟支道而般泥洹,必当逮得无上平等之道。”⑦(吴)支 谦,译.佛说八吉祥神咒经[A].大正新修大藏经[Z].第14册.沮渠京声译《佛说谏王经》:“身死魂神常入太山地狱。”⑧(北凉)沮渠京声,译.佛说谏王经[A].大正新修大藏经[Z].第14册.等等。当然,佛教中的地狱与泰山本土的“治鬼”还是存在差异的,即佛教中的地狱道相比于泰山府君来说其对恶人的惩治力和威慑力更大。从《鬼子母经》可以窥探到:“佛复问:‘汝有子知爱之,何故日行盗他人子?他人有子,亦如汝爱之,亡子家亦行道啼哭如汝,汝反盗人子杀豼之,死后当入太山地狱中。’母闻是语,便恐怖。”⑨佚 名,译.佛说鬼子母经[A].大正新修大藏经[Z].第21册.从母亲恐惧的感受中便能够知晓地狱道对于恶人的惩治的严峻。
佛教中的“地狱观”,以及三界六道、业报轮回等思想,恰与泰山自有的“魂归”“治鬼”有共通,有一点不同的是佛教更加看重因果报应,其地狱道对恶人的治罪更加残忍,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出现两者共同管理的局面。魏晋时人皆知泰山有府君,处泰山幽冥掌管鬼魂,佛教到来之后,给本就是幽极之地的泰山植入了地狱场景并随之影响渐大,泰山府君与阎罗王共同在此刑罚治鬼并无违和。佛教在泰山的快速发展与形成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依附泰山本土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三、道教思想对泰山佛教的影响
泰山先为道教名山,道教思想早在此地生根已久。秦汉时期,寻仙之风大兴,泰山之中仙洞良多,聚集了诸多寻仙方士,这些齐地方士的思想后来逐步演变为道教。①白如祥《泰山方士与道教的产生》一文中,指出道教是由齐学演变而来。齐学就是海岱之学,海即胶东沿海,岱即泰山。道教中对神仙的崇拜,就有来自于东方的、以渤海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为中心的海岛神话,此也是道教神仙思想的两个源头之一。自汉代道教创始以来,其后便有道士稷邱君、崔文子等在泰山传道布教。另《抱朴子·遐览》中载有五岳真形图,凡是道士隐栖修炼须佩戴之,如此一切毒物便莫能靠近,图中的五岳之一便有泰山,可见泰山于时早就作为道教元素之一了。
在僧朗移卜泰山之前,在泰山中便有道士张忠隐居修行已久。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为了躲避永嘉之乱而隐匿于泰山,时间大概是310 到311 年,早于僧朗四十年左右。在僧朗带来佛教之前,张忠一直在泰山修行并收有弟子,《晋书·张忠传》记载:
由此可知,张忠适好幽静之地,修行道家的养生之术,凿地为洞以居,据说其取名为“隐仙洞”,冬天裹袍,夏天则只系一衣带,坐修之时身体僵直宛若尸体。其行为被弟子纷纷效仿,弟子所住洞室距其六十余步,每五日朝拜一次。他们的此种修行方式,与古代印度一些宗教通过闭思冥想、降低物欲以追求心灵升华的苦行做法类似。张忠的思想核心是“至道虚无”,他不研读经典,通过肢体动作教授弟子,弟子们观其形、知而退。这种方法后来影响了僧朗,通过僧朗又使得后世泰山的沙门子弟继承。
351年,僧朗至泰山,“与隐士张忠为林下之契,每共游处”。③(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后居泰山,与隐士张忠共处”。④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僧朗与张忠神交于泰山,僧朗从张忠这位忘年老友的言行与思想中,吸收到道教思想,并且运用到自己僧团的教化中。后世有如禅宗而言,其教外别传及不立文字的做法,均与道教的些许作风有关联,泰山禅宗北派专精于笃践实履的坐禅修行则更甚如此。唐代居于泰山的降魔藏禅师虽伏膺于神秀,但其不依文字,以形相教的方式远不同于神秀的重视研读经典,相反,与张忠和僧朗的授业之法相似,《宋高僧传》载:“师寻入泰山。数年,学者臻萃,供亿克周,为金舆谷朗公行化之亚也。”⑤(宋)赞 宁.宋高僧传(上)[M].北京:中国书店,2018.佛教的小乘一切有部的禅数之学,其对后世的禅宗尤其是以神秀为代表的禅宗北派影响甚为深刻,而禅数之学恰如同道家的呼吸吐纳之术。东汉安世高来华,“宣译众经,改梵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⑥(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其中所译《安般守意经》中的“数息观”就是在修禅的过程中集中注意力在呼吸之上,从一数到十从而达到心神安定,“一息乱者是外意过,息从外入故;二息乱者是内意过,息从中出故。三、五、七、九属外意,四、六、八、十属内意”。⑦(汉)安世高,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A].大正新修大藏经[Z].第15册.可见,与此道家修行方式接近的注重坐禅渐悟的禅宗北派能够在泰山地区植根与发展,与泰山佛教在历史发展中吸取的道教思想不无关联,而其渊源便可追溯到魏晋时期。
四、羊氏崇佛对泰山佛教的推动
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中心发生了转移,即从汉代的学校制度到家族,且家族是受限于地域的。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从博士的传授之风息止后,逐渐形成了以地域为界限的家族教习风气,此时的世家大族内文化思想的活跃与传承甚浓。汉季以降,泰山地区最大的豪族为羊氏一族,其家族成员多操刀制锦于魏晋南北政权,在泰山及周围地区有着不凡的影响力。作为于时名门望族,其族内的育学之风繁盛,思想传承延绵,羊氏自东汉以来就以经学传家,“以经术传家,享盛名于魏晋,衰于南朝”。②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2002.除此之外,羊氏家族又多言清玄、尊崇佛道。佛法自汉传入东土便植根滋生于此,虽然其些许教义与传统的儒教纲常大相径庭,但羊氏家族面对新的思想学问,有着绰然的包容态度以及良好的学习能力,羊氏一族的崇佛对泰山地区佛教的稳固与延展起到了莫大作用。
有关泰山羊氏家族与佛教存在之关系的记载,要从羊祜说起。在《晋书·羊祜传》中有:
祜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③(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学者张春慧指出羊祜的这种表现属于前世记忆,是佛教中轮回的一种,但这则史料所记叙儿时的神异内容的真实性仍然存疑④张春慧,周晓冀.泰山羊氏崇佛论述[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5).,周郢先生在《泰山羊氏文化述略》指出羊祜金环轶事的原型系出佛典中的鹤勒那尊者的故事,这则故事使得羊氏家族染上了浓厚的佛教色彩⑤周 郢.泰山羊氏文化述略[J].岱宗学刊,2000,(2).,这个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北齐之时的羊烈,确是真正的佛教修习者,在出土其墓志铭中有:“入老室以练神,安庄领以全朴。睿如冲壑,豫若涉川,遂注道佛二经七十余卷,仍似公纪作释玄之论,昭晋无已。”“言为世范,行成士则;尤畏四知,能除三或”。⑥罗新等.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6.从中可以得见,羊烈曾注道教佛教经书七十多卷,且敬畏四知,能除三或(三惑)。张春慧在其文章《泰山羊氏崇佛论述》以及纪东佐在其硕士论文《魏晋南北朝泰山羊氏儒释道思想研究》中认为“三惑”为佛教中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是天台宗对烦恼的三种分类。按照墓志铭行文的前后对照,此处的“四知”“三惑”应该对照前文的“言为世范,行成士则”,意思为(羊烈)言行和举止都能够作为时人的模范,那么“畏四知,除三或”则为谈话间能够敬畏“四知”而行为上能摒弃“三惑”。所以对于羊烈墓志中“三惑”的记载,笔者更倾向于范晔《后汉书·杨震传》中赞杨震父子所言:“杨氏载德,仍世柱国。震畏四知,秉去三惑。”⑦(宋)范 晔.后汉书[M].(唐)李 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此“四知”为“天知、神知、尔知、我知”,而此“三惑”则是“酒、色、财”。诚然,墓志铭中此段描述并无心刻画羊烈之崇佛,但仅从羊烈的注经就足以证明其佛教造诣不凡了。而除此之外,羊烈“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⑧(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可见羊烈还曾为当地女子建造寺院度为比丘尼。
在出家女众中,亦不乏羊氏家族者,如《比丘尼传》中所记之道馨与僧念,⑨《比丘尼传》:“竺道馨,本姓羊,太山人也。志性专谨与物无忤。沙弥时常为众使口恒诵经,及年二十,诵《法华》《维摩》等经,具戒后研求理味,蔬食苦节……”“僧念,本姓羊,泰山南城人也。父弥州从事吏,念即招提寺昙睿法师之姑也。圭璋早秀,才监明达立德,幼年十岁出家,为法护尼弟子,从师住太后寺。”以及1983 年11 月在新泰出土的东魏兴和三年(541)羊银光造像碑,其背面所刻有:“清信女佛弟子羊银光造像一躯”的字样,说明羊氏女银光亦信奉佛教。⑩周玉茹.从泰山羊氏家族女性奉佛事迹看东晋南北朝士族门风的演变[J].佛学研究,2018,(2).总之,魏晋家族传习之风盛行,尤其像泰山羊氏之类的大族,其尊崇发扬的思想文化在一定地域内的影响是不俗的,羊氏家族成员的译经、出家受业以及在泰山地区的刻经与造像等等,都推动了佛教在泰山此地的发展与壮大。
五、结语
魏晋南北时期佛教初传东土,其在上至帝王、下到兆民的社会阶层都有不少信众,从佛教的整体性发展看来,无论是在汉族政权内亦或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中,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持上升发展的态势,而区域性的佛教发展亦是如此。作为孔孟之乡、儒学重镇的山东,泰山地区佛教的发展一方面在于时代背景下儒学的式微,另一方面就是其他思想的渗透以及相关人物的推动。僧朗法师个人的威严与影响力之于泰山佛教起到了开辟性的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泰山地区佛教于后世绵延发展的基石;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显学,不仅对整体性的佛教产生了影响,泰山地区亦复如此,般若学的发展就是佛玄相互渗透的结晶。除此之外,泰山僧敦也善于清谈玄学,在其佛法弘化中亦会受到玄学的影响;泰山本土信仰中的魂归之地与佛教地狱观的两相契合,又使得佛教在泰山地区得到良性的传播与发展;泰山佛教在北魏太武灭佛之后复能兴起,离不开道教的兼收接纳,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吸取了道教思想,唐北宗的一支僧众能够扎根于此并且形成特色,离不开此一时期从道家思想中汲取的营养;羊氏家族作为泰山地区的名门望族,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不言而喻,羊氏崇佛,在泰山地区所做之善行善举、造像刻经,更加促进了佛教在泰山地区的发展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