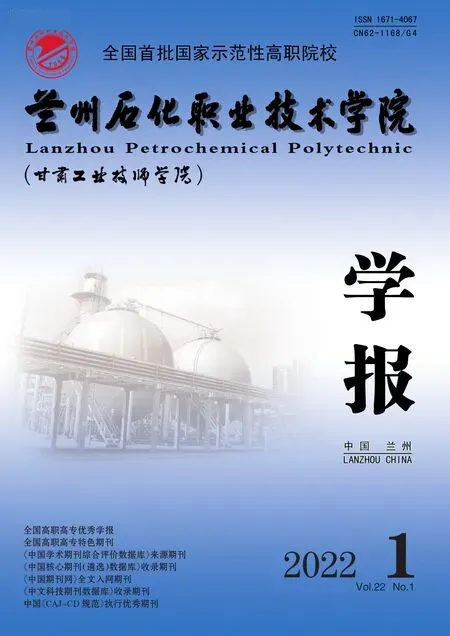分行、空格、标点等书面形式对卞之琳诗歌节奏的作用
2022-03-17周淑红
周淑红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甘肃 兰州 730207)
分行和标点符号的使用是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的形式特点,这类书面形式同时也是构成新诗韵律的重要影响因素。标点符号不仅作为语法手段,有助于语意表达的准确和丰富,更能指示语音的延长与停顿,形成特殊的节奏;分行和空格实际上是通过对语言时间分布的有意指示,破坏了日常化的、散文式的语言行进时间,构成了一种新的、陌生化且富有意味的时间体验。
“虽然,自由诗(又称“开放形式”)没有固定的格律、韵式、诗节形式,但是它们可以从词语、短语或者语法结构的重复等方式获得节奏,也可以从词语在纸面上的排列以及别的方式获得节奏。”[1]适当合理的运用分行、空格和标点符号等书面形式能够成为塑造节奏效果的一种灵活新巧的手段。
卞之琳的新诗创作,在节奏方面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尝试,其中也包括有意地使用标点、分行、空格这样“非典型”的韵律手段来影响节奏。
1 标点
卞之琳利用标点符号控制诗歌节奏的尝试多数借助的是括号。括号中的内容在诗歌中作为插入语出现,能给予上下句的诗行以停顿的暗示,其本身又带有“音量稍低”的声音效果(作为补充说明,或是类似旁白的作用,读者会不自觉地将其与正文区分,从而减低括号中内容的声音的响亮程度),再配合前后文以及诗歌整体的气氛,对于节奏有着微妙的影响。
使用“戏剧化笔法”为诗歌营造画面感和生动的情景氛围,是卞诗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手法多借助括号来表现,如《投》:
也说不定有人,
小孩儿,曾把你
(不爱也不憎)
很好玩地捡起,
像一块小石头,
向尘世里一投。[2]
“也不爱也不憎”作为插入语,类似戏剧的画外音,语调轻、节奏快,打乱了整体悠长绵延的调子,带来一种灵巧、轻快的声音体验,整首诗显得更加活泼隽永、灵动有味。又如《落》:
在你的眼角里,一颗水星
我发现了,像是(正逢黄昏天,
当秋风已经在园径上走厌,
嘘一口长气,倚一丛芦苇)
天心里含着的摇摇欲坠
摇摇欲坠的孤泪。我真愁,
怕它掉下来向湖心直投。[2]
括号切断了“像是……”后的喻体的出现,拉长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插入语的环境描写正契合整首诗冷寂、忧郁的气氛,同时带来了时间的延宕感,情绪更添一份惆怅。
类似的括号使用还在《距离的组织》、《道旁》等诗中出现,除了内容上描绘情境之外,节奏上制造停顿,声音与画面相互映衬,营造氛围。
《入梦》一首,括号对音量效果构成影响:
设想你自己在小病中
(在秋天的下午)
望着玻璃窗片上
灰灰的天与疏疏的树影,
枕着一个远去了的人
留下来的旧枕,
想着枕上依稀认得清的
淡淡的湖山
仿佛旧主的旧梦的遗痕,
仿佛风流云散的
旧友的渺茫的行踪,
仿佛往事在褪色的素笺上
正如历史的陈迹在灯下
老人面前昏黄的古书中……
你不会迷失吗
在梦中的烟水?[2]
“在秋天的下午”给人一种朦胧的感受暗示,括号内以稍低的音量朗读,因此从这句开始,后续的诗句也连带着不自觉地产生了音量的变化,模拟出整首诗所表现的将睡未睡、睡意迷蒙的感觉。台湾诗人商禽的《梦或者黎明》与这首诗的主题和节奏表现有类似之处,“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的括号内插入语周期性重复,同样营造了一种半梦半醒的朦胧氛围,将梦的感受描绘得十分生动。
《尺八》中,
(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2]
“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的设问穿插在诗行间重复了两遍,在诗歌内部形成一种“复调”,类似歌曲的伴唱或者合唱中的另一个声部,给整首诗以交错的韵律,减缓了整首诗没有隔行的紧凑感,配合着下一句“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的绵长声音,带来悠长回环的韵律效果。
《寒夜》一首:
一炉火。一屋灯光
老陈捧着个茶杯,
对面坐的是老张。
老张衔着个烟卷。
老陈喝完了热水。
他们(眼皮已半掩)
看着青烟飘荡的
消着,又(像带着醉)
看着煤块很黄的
烧着,他们是昏昏
沉沉的,像已半睡……
哪来的一句钟声?
又一下,再来一下……
什么?有人在院内
跑着:“下雪了,真大!”[2]
若抛去括号内插入语的部分,这首诗的音韵十分整齐,一句两个或三个顿,押韵密集:“灯光”、“老张”、“飘荡的”、“很黄的”;“茶杯”、“热水”、“半睡”。如果在朗读时,将括号省去不读,整首诗便会始终保持在一种舒缓的、慢悠悠的节奏中,但括号的插入,在整体节奏的同一性中加入了变化的因素,也呼应了后文“钟声”的插入、“有人在院内跑着”将这份昏然欲睡的气氛打破。同时,加入括号内部分的朗读,整首诗的节奏更类似于打瞌睡时“渐渐要睡着-猛地惊醒-又渐渐要睡着”的状态,具有生动的模拟效果。
除了括号外,破折号有延长语音的作用,在诗中也有特别的节奏表现,如前文提及的《落》:
你想说不要紧?可是平静——
唉,真掉下了我这颗命运!
“平静”后的破折号,延长了这个词语的意义感受,与下一句句末的感叹号相配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面的平静被乍起的坠落所打破,被延宕的“平静”只是勉力维持的伪装,而最终还是“掉下了我这颗命运”,命运激起的波澜就如同感叹号给人的感觉一样突然而惊异。又如经典的《无题二》:
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
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
衣襟上不短少半条皱纹,
这里就差你右脚——这一拍![2]
破折号带来的短暂停顿类似乐谱中的“附点音符”,比一个字的音长稍短,不影响句子总体的节拍数,却能带来更加跳跃、富有俏皮感的节奏效果。李章斌分析:“关键在于行中破折号的使用,其实把它去掉,‘拍子’还是四拍,不影响所谓‘格律’的构建;但是这样的话,‘这一拍’就太顺溜地滑过去了,这个破折号在时间上起到停顿的作用,而且,通过停顿的短暂一瞬,描绘‘你’脚先到了,但还没踩下的瞬间,暗示着对“你”的到来的隐秘期待和款款深情。”[3]
2 分行和空格
分行对于现代诗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几乎成为了诗歌与散文相区别的本质性手段。分行通过视觉的排列引导读者体会诗歌不同于散文的独特的节奏,同时运用有意的停顿塑造声音效果。卞之琳认为分行“行不是断在可以大顿一下地方, 而是为了把各行削齐或者是凑韵,硬把多余的行尾跨到下一行头上”、“那样间 或有意做了,倒也可以达到特殊的效果。”[2]
前文提及的《入梦》,事实上整首诗按语法成分来分析就是一句话,而频繁的跨行使诗句的时间效果一再延长,拖慢了声音的速度,带来曲折回环的阅读体验,模拟出逐渐进入梦乡迟缓、恍惚的感觉。《落》则利用分行带来的停顿,强调了“摇摇欲坠/摇摇欲坠的孤泪”的重复,加强了悠扬婉转的语调。再如《水成岩》:
水边人想在岩上刻几行字迹:
大孩子见小孩子可爱,
问母亲“我从前也是这样吗?”
母亲想起了字迹发黄的照片
堆在尘封的旧桌子抽屉里,
想起了一架的瑰艳
藏在窗前干瘪的扁豆夹里,
叹一声“悲哀的种子!”
“水崽,水哉!”沉思人叹息
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2]
首句的隔行,破坏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冒号后面,并没有接着写出水边人在岩上刻下的是什么内容,而代之以一个隔行的停顿,留下空白,耐人寻味。“叹一声‘悲哀的种子’!”一句则前后都有隔行,产生了一个时间较长的停顿,声音形式与其内容“叹息”达成了一致。“母亲想起”两节,两句一分行,加强了回忆悠远、时间绵长的表现效果,类似于陈世骧所言的“时间在诗中的示意作用”[4],“字迹发黄的照片”、“尘封的旧桌子”、“干瘪的扁豆夹”都暗示着时间的悠长久远,分行引导的停顿又在语音上加深了这样的感觉。
《圆宝盒》
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
或他们也许也就是
好挂在耳边的一颗
珍珠——宝石?——星?[2]
一句长句被分隔成三行,节奏被再三延宕、拉长,最后以响亮的顿挫收束。“诗句的长与短、整与散,因错综参差的对比而产生鲜明的节奏感”[5]
《白石上》
你不妨再坐一会儿
在白石上,
听浅湖的芦苇
(也白头了)
告诉你旧事
(近事吧)
一遍看远山
渐渐的溶进黄昏去……[2]
频繁的分行延长了诗句的时间长度,语调绵延舒缓,配合括号内的插入成分,增加停顿和曲折感,更凸显诗中营造出的朦胧、恍惚的氛围。
除了常见的分行手段,卞之琳还灵活地运用句中的空格,创造了鲜明而独特的节奏效果。《一块破船片》中,
潮来了,浪花捧给她
一块破船片。
不说话,
她又在崖石上坐定,
让夕阳把她的发影
描上破船片。
她许久
才又望大海的尽头,
不见了刚才的白帆。
潮退了,她只好送还
破船片
给大海漂去。[2]
空格带来了节奏的延宕,在朗读诗歌时,读者会自觉地拉长行间的停顿;“不说话”、“她许久”之前几乎跨行的空格,生动地表现了沉默和等待把时间拉长的感觉。而最后“给大海漂去”一句的空格又模拟出破船片随海浪漂走的运动感和距离感,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作用下表现出生动的韵律效果。另外,句首空格又带有类似音乐中的“弱拍开头”的作用,让空格后的部分在朗诵时速度稍加快,应用在短分句上,整首诗的节奏快慢更加错落灵活。《奈何》一首,
“我看见你乱转过几十圈的空磨,
看见你尘封座上的菩萨也做过,
叫床铺把你的半段身体托住
也好久了,现在你要干什么呢?”
“真的,我要干什么呢?”
“你该知道吧,我先是在街路边,
不知怎的,回到了更加清冷的庭院,
又到了屋子里,重新挨近了墙跟前,
你替我想想看,我哪儿去好呢?”
“真的,你哪儿去好呢?”[2]
标题括号的补充说明是“黄昏和一个人的对话”,空格体现出了“对话”的微妙的空间感和距离感,诗中的“我”似乎是与另一个人对面相谈,空间的相对位置产生了声音的错位;又似乎是恍惚中的喃喃自语,因而一来一回产生了微妙的延迟与停顿,仿若心中的回音,与重复的节奏形成了“二重唱”。有意安排的空格放大了这种感觉,整首诗情感内容与声音节奏契合得十分巧妙。
3 结束语
卞之琳在其诗歌创作中,尝试的创造韵律的方式是非常新巧和丰富的,本文所举的例子仅仅是从书面形式这一个方面进行了粗浅的解读。事实上,一首诗歌的韵律感来源于多个方面,整体的节奏效果是押韵、重复对称、分行排列等等各种手段综合作用、听觉和视觉相互配合造成的复杂审美感受,分行和标点这类书面形式对节奏的影响本身比较细小、微妙,竖版和横版的排列方式的差异,也可能造成读者感受的细微差别[6-8]。大巧不工,卞诗技巧本身运用得精妙适宜,多种技巧相互配合浑然一体,因而带来了技术性分析的困难和过度解读的可能性。
当今新诗创作中,分行依然是常用且重要的节奏手段之一,然而也不免有滥用之嫌,卞诗在书面形式运用上的精细和严谨、对节奏塑造的积极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