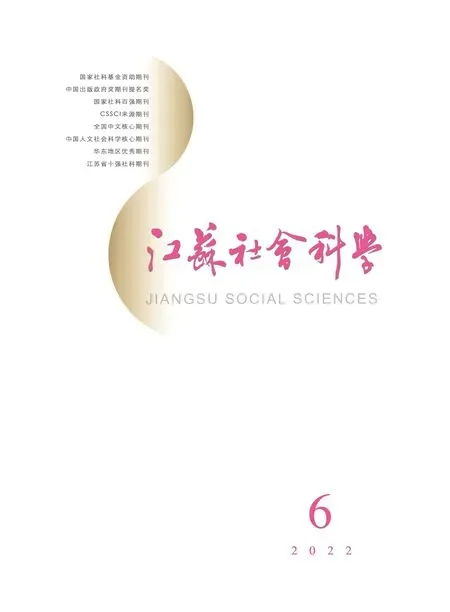“文脉”与“人脉”:清代“四王”绘画源流及“复古”真相探究
2022-03-15顾楷之
顾楷之
内容提要 清代“四王”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对其艺术成就的评判,有两个极端:一是清代艺坛对“四王”绘画的推崇,及对其正统地位的捍卫;二是民国之后艺术界甚至思想界对“四王”绘画的极力否定和贬斥。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研究中,关于“四王”绘画“复古”的论断,几乎众口一词。通过相关绘画史的梳理,发现“四王”绘画特殊的思想渊源,究其根本是“文人画”思想经由宋、元的发展和明代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接力,其间又以其“人脉”的机缘,“无缝对接”地传承给了清代“四王”。通过大量绘画实证、画跋内容及文献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四王”绘画的“文脉”与“人脉”的双重路径。“四王”复古的实质是特殊的朝代更替中满汉文化传统混乱对接,传统文人在新王朝谋求身份认同和文化正统之路的绘画实践。
清代“四王”的绘画艺术、地位及其对中国绘画发展的影响,一直是中国绘画史研究的重要命题,其中对“四王”绘画复古的探讨是长期以来该研究的重点。“四王”即“复古”似乎已成定论,也成为学界否定“四王”绘画的主要依据,这多少使得“四王”研究多囿于图式表象,而忽略了由明至清“文人画”的“文脉”和“人脉”对“四王”绘画双重规导的深层历史原因的挖掘。
就“四王”的“人脉”来说,以王时敏直接师承董其昌为源头。而董其昌以“南北宗论”[1]俞剑华:《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承接宋代“文人画”理论思想之“文脉”,完成了由宋代兴起的“文人画”理论及其思想的传承,经元代黄公望等的实践,由董其昌以“南北宗论”的理论及其规导的画法接力,打开了“文人画”思想传承发展的通道。这一方面成就了“四王”的“复古”画风,另一方面又因“四王”正统画法地位的确立,从而统摄有清一代的画坛,使其后中国画发展“衰蔽极矣”[1]王立翔:《书与画——康有为与万木草堂藏画目》,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成为一种宿命。
为了探究“四王”“复古”画风的真相,我们对“四王”与董其昌的“人脉”与“文脉”的关系、“四王”画风“复古”之“古”以及作为“四王”绘画思想渊源的“南北宗论”的分析,进行梳理和论证。
一、“四王”对董其昌“人脉”与“文脉”的传承
清代“四王”为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王时敏(1592—1680),江苏太仓人,字逊之,号烟客,晚号西庐老人。王鉴(1598—1677),江苏太仓人,王世贞曾孙,字玄照,后改字元照、圆照、元炤,号湘碧、染香庵主、弇山后人。王翚(1632—1717),字石谷、臞樵,号乌目山人、耕烟散人、清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又号石师道人[2]俞丰:《四王山水画论辑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397—408页。。其中王鉴为王时敏子侄,王原祁为王时敏孙,王时敏与王翚为师生关系。“四王”画派因其血缘或师承关系的紧密连接,比其他画派有着相对更为一致的画学思想和绘画呈现。王时敏作为清代“四王”之首,在绘画理论上对董其昌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其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堪比明代董其昌对宋代“文人画”理论的承续和接力。他又是“四王”与董其昌“人脉”的直接开启者。王时敏祖父为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王锡爵,与董其昌同朝为官,不仅相互熟悉,还曾嘱托董其昌指教王时敏。据史料载,王时敏和其后的王鉴,还是董其昌“画中九友”[3]中国历代绘画流派大系编委会:《画中九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版,第1页。成员,可见“四王”派系与董其昌关系之紧密,以及学术思想脉络的一致性[4]顾伟玺、顾楷之:《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发展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62页。。王时敏与王鉴都亲炙董其昌,是董其昌画学思想脉络的直接传承者。恽寿平在《瓯香馆画跋》中曰:“娄东王奉常烟客,自髫时游娱绘事,乃祖父肃公属董文敏随意作树石以为临摹粉本,凡辋川、洪谷、北苑、华原、营丘树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语拈提,根极理要。”[5]毛利和美:《中国绘画的历史与鉴赏——瓯香馆画跋》,二玄社1985年版,第215页。关于王时敏与董其昌的交往,任道斌的《董其昌系年》还有一些考证:1626年秋,王时敏作《幔亭秋色图》“为思翁年伯所许可”[6]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1627年春,董其昌至王时敏“鹤来堂”,“相与审定家藏古今法书名画,留有旬日”。是年,董其昌及陈继儒分别为王时敏《仿云林笔意轴》题跋,董跋曰:“逊之于长安邸数见之,遂能奇真;当今名手不得不以推之”[7]孙文忠:《清初“四王”对中国画发展的积极意义》,《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对王时敏临习倪画大加赞赏。陈继儒跋曰:“写倪迂画者,启南老,征仲嫩,王尚玺衷之矣”[8]宋建华:《王时敏画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陈继儒(1558—1639),是明代著名文学家、画家,著述颇丰,以博学名倾天下,黄道周给崇祯帝上疏曾将之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相比,认为顾“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可见陈继儒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然而陈对王时敏的评价竟然将其与吴门画派的两大巨擘文征明和沈周相提并论,认为王时敏和沈、文临习倪瓒各有所得,而王折中了沈、文的“老”“嫩”,别成一格。陈继儒在明代文坛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倡导“文人画”,与董其昌同执“南北宗论”,他对王时敏的赞誉为王时敏画坛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同年夏,董其昌、陈继儒于太仓观王时敏所藏黄公望《秋山图》,董其昌有“杂坐无宾主,清言见古今”[9]马躏非:《董其昌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之句,王时敏有“老友不期至,清言何以加”[10]吕少卿:《论王时敏的书画交游与画学思想》,《艺术百家》2006年第3期。之语。其后,是年夏秋之际,董其昌跋王时敏《武夷山接笋峰图》云:“今见逊之此图,追踪子久,烟云奔放,林麓深密,实为画中之诗。”[1]朵云编辑部:《清初四王画派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第531页,第711页。跋王时敏《层峦秋霁图》云:“逊之玺卿尝闻沈石田《岚容川色》之妙,为此欲拟之,已先得其神照矣。”[2]蒋志琴:《“王逊之玺卿”之“玺卿”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年第4期。其间,董其昌还大赞王时敏《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不若逊之此图,气韵位置,遂欲乱真也”[3]董其昌:《容台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68页。,又在传王时敏收藏的王蒙《山水》题云:“逊之学山樵,几过于蓝,意犹未尽,便欲拔其帜矣。”[4]朵云编辑部:《清初四王画派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第531页,第711页。1629年,据《董其昌系年》载,是年,其昌已与王时敏结为姻亲,并在王时敏《山水》题曰:“逊之尚宝以纸索画,经年漫应,非由老懒,每见近作,气韵冲夷,动合古法,已入倪迂黄痴之室,令人气夺耳。”[5]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以上记载和跋文足可证董其昌与王时敏过从之密,且更有“逊之老亲家”的特殊的“人脉”关系。由其题咏交往则能凸显董之“文脉”对“四王”的浸淫和沾溉。可以说二者的师承和姻亲关系使得二人在画学思想上保持了相当紧密的一致性,均以“南宗”“文人画”作为正统,同声相应,在绘画面貌上也颇有交集。
关于“四王”对“文人画”“文脉”的承续,从他们的画跋画语中也可得证。王时敏《西庐画跋》提出“与古人同鼻孔出气,下笔自然契合”[6]陈辞、陈传席:《中国名画家全集古代卷》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古人”是谁呢?其实质也即董其昌“南宗”一路。如王时敏题画曰:“书画之道……董巨逸规,后学竞宗。”又曰:“石谷此图……全以右丞为宗,故风骨高奇。”[7]邵琦:《王翚画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王原祁也说:“画家自晋唐以来,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发其蕴,至宋有董巨,规矩准绳大备矣。”[8]朵云编辑部:《清初四王画派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第531页,第711页。此也与董其昌“南宗”同为一辙。王鉴《染香庵跋画》则云:“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舍此则为外道。”[9]俞丰:《四王山水画论辑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王鉴视董巨为正宗,反映其理论、思想及其规导的画法,皆合于“文人画”之轨辙。“舍此则为外道”,所谓“外道”则为“四王”极力反对的,王时敏说:“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邪诡不可救挽。”[10]刘建龙:《正脉:娄东王时敏、王原祁家族暨艺术综合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后记附录1。“古法茫然,妄以己意衒奇,流传谬种,为时所趋,遂使前辈典型,荡然无存,至今日而澜倒益甚。”“四王”之“正道”即董其昌“南北宗论”中所推崇的“文人画”大家们的“正统”画法,以董源、巨然和“元四家”为首,正是清代画坛“家家子久,人人大痴”的前奏。
二、关于“四王”“复古”之“古”
关于“四王”绘画之“复古”,几成学界众口一词的评判,卢辅圣先生在其《“四王”论纲》一文中评论道:“摹古、仿古和拟古,无疑是四王画风的特色。”[11]《清初“四王”画派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江宏在《夺神抉髓 重开生面——“四王”山水画仿古倾向浅议》中说:“‘四王’几乎是保守绘画的代名词……与他们师古、仿古的绘画倾向有关。”那么“四王”“复古”之“古”的真意究竟何在呢?绘画艺术之“古”究竟又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于“复古”的解释是“恢复古代的制度、风尚、观念等”[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10页。。就中国画来说,复古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前代中国画的思想、观念的认同与继承;二是对前代绘画风格、技法的延续。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四王”复古的道路显然过于偏狭,而理论界普遍共识的“四王”复古,究其根本,是“文人画”衣钵之再传,亦明代董其昌“南宗”所规导的专师一门,又受“文人画”影响而耽于笔墨、囿于匠技而已。关于这一点,前文董其昌屡为王时敏画作题跋的内容已多涉及,清人张庚《国朝画征录》中亦云:“太原王时敏……资性颖异,淹雅博物,工诗文,善书,尤长八分,而于画有特慧。少时即为董宗伯其昌、陈征君(继儒)所深赏。于时宗伯综揽古今,阐发幽奥,一归于正方之禅室,可备传灯一宗。真源嫡派烟客实亲得之。”[1]张庚:《国朝画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而“四王”唯师董巨、独尊“南宗”的状况,作为“四王”之一的王翚则有所自觉。他在《清晖画跋》中就提出:“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2]俞丰:《四王山水画论辑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第141页,第209页。王翚相当于在“正统”的道路上,扩展了师法的范围。正如美国学者高居翰所言:“拿王翚来说,他的绘画技能精到,但不是正统派嫡出,而是为正统派所吸取进去的,因此,他就不像王原祁和其他人那样,对正统派一往情深,而是想在错杂的流派中创造一个‘大综合’,它包括但不只是局限于正统派。”[3]朵云编辑部:《清初四王画派研究》,高居翰《王原祁与石涛:有法与无法的两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675页。王翚的画学思想应算作视野较为开阔的“师古”主张。《清晖画跋》中有一则画论,反映出王翚对当时画坛现状的思考:“嗟呼!画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洎乎近世,风趋益平,习俗愈卑,而支派之说起。文进、小仙以来,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后,吴门之派兴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精,后学风靡,妄以云间为口实。琅琊、太原两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远近争相仿效,而娄东之派又开。其他旁流绪沫,人自为家者,未易指数。要之承讹藉舛,风流都尽。翠自龆时搦管,仡仡穷年,为世俗流派所拘牵,无繇自拔。大抵右云间者深讥浙派,祖娄东者辄诋吴门,临颖茫然,识微难洞。”[4]俞丰:《四王山水画论辑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第141页,第209页。
由此可见,王翚清醒地意识到“画道至今日而衰矣”,并将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自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认为是“流派”太多、门户之争导致鱼龙混杂、以讹传讹。关于明末清初画坛的混乱无序,另一位正统派大师王原祁也做过评价,他在《雨窗漫笔》(约成书于1700年稍后的时间)中有一段话:“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至吴门、云间,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赝本溷淆,以讹传讹,竟成流弊,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5]俞丰:《四王山 水画 论辑 注》,上海 书画 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第141页,第209页。当时与“四王”正统派艺术观点对立的“清初四僧”之一石涛,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难得地跟正统派保持了一致。石涛1699年在画上的一段题跋描述了同样的状况:“今天下画师,三吴有三吴习气,两浙有两浙习气,江楚两广中间,南郡秦淮徽宣淮海一带,事久则各成习气,古人真实面目,实是不曾见,所见者皆赝本也,真者在前则又看不入。”[6]杨琳:《试析“搜尽奇峰打草稿”》,《美术教育研究》2012年第16期。在如此混乱、真假难辨,甚至以假为真的境况下,正确的传统和真正的传派中掺杂了错误的古代风格形象,在各地的大小画派中谬种流传,以致画家们“临颖茫然,识微难洞”,无所适从。而这一现象是满汉文化仓促对接的混乱在画坛的典型体现。明末清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这一时期满族政权对汉族政权的取代是文人们首先必须面对的巨大考验,对于文人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的种种艰难和不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弱势文化取代强势文化的主导权所带来的文化错乱和文化归属问题,以及文人身份认同的失重感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一时期画派的混乱不过是改朝换代、满汉文化对接和文化重置所带来的影响在画坛的体现。另外,这一时期绘画也遭遇空前丰富的思想冲击,绘画行家与戾家的分野、欧洲绘画的影响、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仿古问题等都使得这一时期的画坛充满了无序、错乱和动荡。
画家们忙于归附各种口号和派别,忙于在一套新的政权体系和不可预期的文化语境中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而“四王”“四僧”“金陵八家”后来的不同艺术风格呈现,正是他们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归属的外在体现。总体来说,“四王”选择的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们主观上希望置身政权变换影响之外的初衷,敌不过政府的强势,遂在半推半就中与政权达成了合作。政治和文化身份的归属是他们“复古”的底色,跟新政权合作意味着艺术风格的中庸,也意味着个体的挣扎和无奈。“四王”们接受的都是正统儒家修齐治平的教育,满汉文化的激烈碰撞使得社会处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替之下。这一社会情境与宋太祖第十一世孙赵孟在宋代覆灭后所面临的处境是一致的,而“四王”们的心态与赵孟当时的心态也大同小异。赵孟 认为在蒙汉政权交替之下,“为往圣继绝学”需要位高权重的人继承发扬汉文化这一文化脉络。所以赵孟反复挣扎之后,选择北上仕元,他曾言:“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1]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25页。可见,他的选择有着家国天下的社稷之心,是超越了一姓王朝的文化大义所在。在文化上,他提倡复古,提出“宗唐得古”的观点,匡正了南宋诗坛“以挥写翰采、敷陈俪语为能事,偏重于词章”的“科词习气”[2]管琴:《论南宋的“词科习气”及其批评》,《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赵孟在元朝统治的夹缝中,主张文化思想、伦理规范、社会秩序等由内而外回归正统,试图以“复古”的外衣保全汉文化的正统,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家国责任感。当把“四王”放在这样的语境中重新审视的时候,或许可以理解他们绘画“复古”的文化选择,不过是在“复古”的外衣下保留一点正统汉文化的火种。因此他们才对画坛良莠不分、真假混淆的混乱状况感到如此愤懑和无奈。而他们复古所复的“正统”是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四王”的学术视野、鉴识能力,以及能否接触到大家真迹,都关系到他们所复的“古”是否正统,是否是真的正统。而于此,“四王”有着天然的优势,王时敏、王原祁作为明代首辅王锡爵的后人,其家藏前代大家书画是常人不可及的,而王翚是王时敏的学生,王时敏的家藏他也得以饱览。另外,王翚祖上几代均染指丹青,王士祯《居易录》有载:“王翚四世祖王伯臣擅长花鸟,师崔白画风,为沈周所称道。”[3]王云五:《居易录谈 附居易续谈》,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页。《常熟县志》载:“王伯臣之子王载仕山水花鸟皆擅,为当时名流所推崇。”[4]桑瑜:《弘治常熟县志》,广陵书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王载仕“邑诸生,志尚高雅,隐居白茆。山水人物画俱擅长,与严道士交酬唱无虚日,晚年结茆桃源涧左。孙即石谷”[5]田艺珉:《清初四王摹古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在这样的家学渊源和师承之下,“四王”具有广博的学识和远远高出同侪的书画鉴识能力。虽然“四王”的复古在具体实践上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例如王原祁是将自己放在单一的风格传统中,尽力地践行从他的祖父王时敏那里接受的正统观念,而王时敏的正统是传自董其昌和董其昌所认定的“南北宗论”中“南宗”的那些大家们。王时敏说要“于古人同鼻孔出气”[6]李来源、林木:《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王原祁更甚:“然落笔时不肯苟且从事,或者子久(黄公望)些子脚汗气,于此稍有发现乎?”[7]俞丰:《王原祁画论译注》,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可见,王时敏祖孙是在董其昌划定的“南宗”“文人画”的圈子里打转。作为“四王”历史时序中最靠后的王原祁,提出了“正宗法派”的概念:“余弱冠时,得先大夫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于子久为专师,今五十年矣。”[8]俞丰:《四王山水画论辑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王原祁年少时即受到他的祖父王时敏的指授,以“董巨”为“正宗”。其实质仍然是董其昌“南宗”一脉的代名词。王时敏说:“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唯董宗伯(董其昌),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形神俱得,吾孙其庶乎?”[9]《清初“四王”画派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董其昌得其神,王时敏得其形,王原祁形神俱得,传承线路极清晰,宗法的源头即“南宗”一路,董、巨及黄公望。
而王翚则走上了全面师古、综合师古的道路,他说:“已从师得指法,复于东南收藏好事家纵揽右丞、思训、荆、董、胜国诸贤,上下千余年,名迹数十百种,然后知画理之精微,画学之博大如此,而非区区一家一派之所能尽也。由是潜神苦志,静以求之,每下笔落墨,辄思古人用心处,沈精之久,乃悟一点一拂,皆有风韵;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阴阳之辨,傅色有今古之殊。于是涵泳于心,练之于手,自喜不复为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1]俞丰:《四王山水画论辑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第141页。
这一方面反映出王翚将宗法前人,从古人那里找法门视为根本出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不像王时敏祖孙那样对正统有着深深的执念,他想在错综复杂的流派中寻求一种“大综合”的道路,在包括但不仅限于正统派的传统中寻求突破之路。但从中可以发现,先贤之“澄怀味象”“以形写神”“山水以形媚道”“心师造化”“可忘笔墨,惟有真景”之思想皆由此“隔绝”了,由宋开始的“文人画”及其理论已经将传统山水画引上另一条道路。这条路一脉相承,由宋之始,经元之发展,至明之董其昌以“南北分宗”与之“接力”[2]顾伟玺、顾楷之:《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发展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2—89页。。所谓“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精,后学风靡”[3]俞丰:《王翚画论译注》,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这样的认知,纵使王翚“纵览右丞、思训、荆、董、胜国诸贤,上下千余年,名迹数十百种”也未能使其明白,“画道至今日而衰矣”的真正原因乃“文人画”及其理论之脉,因其挟有极其强大的政治文化地位和不可比拟的社会历史资源而笼罩了千余年的中国画坛。悲乎!王翚这样一位对独尊一脉有所警觉,对其危害弊端有所觉悟的重要人物,在观览千余年众家名迹之后,也曾有这样的感悟:“然后知画理之精微,画学之博大如此,而非区区一家一派之所能尽也。”[4]俞丰:《四王山水画论辑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第141页。但其下又说“乃悟一点一拂”云云,仍然是停留在“文人画”“技”的“玩弄笔墨”的状态。
“四王”中的王原祁是继董其昌之后,在“文人画”一脉的纵向发展轴线上又一个坐标级的人物。王原祁在清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官至户部左侍郎,主持编辑《佩文斋书画谱》[5]王原祁、孙岳颁、宋骏业、吴暻、王铨:《佩文斋书画谱》,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深得皇帝赏识,曾奉命主持《万寿盛图》[6]宋骏业:《康熙万寿盛典图》,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1—42页。的创作。王原祁作为直接师承董其昌的王时敏的孙子,是董其昌“文人画”理论的嫡传,可谓“家”学渊源深厚。这个“家”学正是由宋滥觞的“文人画”及其理论,历元至明经董其昌的“接力”,又由“四王”之首王时敏与其实现了“无缝对接”而系于一脉。仅王原祁即专师子久历“五十年矣”,在清代或可谓具有了明代董其昌的地位,而成为由明至清的“文人画”思想及画法的直接“接力”者。这也使得“四王”师古,独宗一门,耽于笔墨,徒事匠技做派,而渐渐疏离传统绘画的真正“古”意,由此也决定了其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历史宿命。
三、“四王”绘画思想之渊源——南北分宗
董其昌在《画旨》[7]董其昌:《画旨》,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中首先提出了“文人画”,并分列了“文人画”一脉的诸代大家。南宋“文人画”以唐王维为宗,取水墨渲淡一路。董其昌依托佛教的“南宗”“北宗”,提出了绘画南北分宗的“南北宗论”。如此,使自宋以来的“文人画”理论更趋体系化和深入化。所谓“南宗”“北宗”为佛家禅宗的分宗,在唐代开始形成,“南北分宗”是指北方神秀的“渐悟”也即“北宗”,南方慧能的“顿悟”说也即“南宗”。在禅悦盛行的宋代,“南宗”的影响愈发显著,又产生了“五家七宗”,即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等五家,临济宗又分出了黄龙派和杨歧派,与五家合称为“七宗”。禅宗在宋代盛行,宋代的“文人画”家苏轼、米芾等皆对禅有很深的体悟,更是谈禅的高人。“南宗”的“顿悟”说,更加注重个人的体悟、灵感和某种意念的生发的偶然性。作为宋代“文人画”理论创建者之一的黄庭坚,在《题赵公侑画》中即说:“余未尝识画。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此岂可为单见寡闻者道哉。”[1]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集部》,上海涵芬楼出版1911年版,第50页。“未尝识画”“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显示出以“禅”来体味绘画,由此影响和规导了其有关“文人画”的理论和观念。关于宋代“文人画”绘画思想以及画理画法的形成,“禅悦”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需要强调的是,“南宗”禅悦的盛行,客观上为“文人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生根成长的土壤。在明代,“南北宗论”的提出,并非董其昌一人,还有万历年间的莫是龙、陈继儒及沈颢。
根据史料记载,莫是龙在《画说》中首先提出了绘画“南北宗”的概念。他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2]汤垕、杨慎、李开先、莫是龙:《古今画鉴、画品、中麓画品、画说、杂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37年版,第4卷。莫是龙明确指出,画之南北二宗,乃借用禅家的南北分宗,并进一步说明“南北”并非地域概念的南方北方的画家。莫是龙的“北宗”画家和“南宗”画家的划分与董其昌的“文人之画”画家与非“文人画家”的划分出于一辙。“文人画家”即莫是龙说的南宗,而非文人画家则为“北宗”。莫是龙除了分宗,其中论及“王摩诘始用渲淡”,指出用水墨渲淡,无疑是从绘画表现形式上对南宗的绘画形式进行了界定。所谓“钩斫之法”,实际上就是山水树石结构的表现,被指为“存形”“画工画”,依此则列出了“二李”及至南宋的马远、夏圭等。
陈继儒在《偃曝谈余》中也说:“山水画自唐始变,盖有两宗:李思训、王维是也。李之传为宋王诜、郭熙、张择端、赵伯驹、伯骕以及于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皆李派。王之传为荆浩、关仝、李成、李公麟、范宽、董源、巨然以及燕肃、赵令穰、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板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至郑虔、卢鸿一、张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马和之、高克恭、倪瓒辈,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3]陈继儒:《销夏部偃曝谈余》,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其中还有“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云云。根据这些材料可以肯定,“画之南北宗”完全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并非仅仅是从画法以及文人和非文人来划定,而是以禅宗的幽淡、天真、淡泊、虚和来品定绘画,划分“南宗”和“北宗”。所谓“不食人间烟火”“另具一骨相”皆以禅心佛性来品评、论述、解析绘画。例如,沈颢也说:“禅与画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时。气运复相敌也。南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出韵幽淡,为文人开山。若荆、关、宏、璪、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之沈、文,慧灯无尽。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若赵干、伯驹、马远、夏珪,以至戴文进、吴小仙、张平山辈,日就狐禅,衣钵尘土。”[4]周星莲、沈颢、秦祖永:《临池管见画尘 绘事津梁》,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20年版,第11页。
综上所述,“南北宗论”不可否认地因禅悦思想直接规导和影响了绘画风格方式,这与宋代欧阳修的“萧条淡泊”,苏轼、黄庭坚之参禅识画,米芾之尚意于平淡天真形成于一脉。此外,董其昌提出的“文人画”与苏轼的“士人画”也为一脉相承。总的来说,“南北宗论”作为对绘画流派或绘画史现象及风格流变传承脉络的梳理,于画史颇有贡献。但“南北宗论”的提出并非一种学术理论的建构或一个重要观点的阐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完成了对宋代“文人画家”山水理论的“接力”,使由宋以下的“文人画”理论至明代再度借助禅学而成为“正统”,其几乎统摄了当世以及其后的画家的思想及艺术追求。葛路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中提出:“南北宗论是文人画思潮的一种反映。创论者接受了苏轼、米芾等人的审美影响。王维本来不是唐代名列前茅的画家,因为苏轼推崇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又说‘吾于维也无间言’,影响了后代。此外,米芾推崇董源一派绘画对元明也很有影响。黄公望说山水画必以董为师。董其昌讲,他‘非不好元四家画者,直溯其源委,归之董巨’。在这种思潮下,南北宗论一出现,就为文人画家所同意。”[1]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事实上,“南北宗论”不仅仅是为“文人画家所同意”,更是宋始滥觞的“文人画”及其理论,因为有董其昌等在明代的“接力”,使其依托禅学以及宋元以来的酝酿发展,形成了更具系统化的理论,从而使“文人画”及其思想、画法、观点的所谓“正统”地位更加得以确立,并又因其与清代“四王”的“人脉”与“文脉”的承续关系,从而直接规导和影响了“四王”绘画风格。
通过前文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四王”绘画的主脉是对“文人画”思想及其艺术方式的继承,是“文人画”“文脉”与“人脉”双重规导下“正统画法”的必然结果,是改朝换代的历史情境下、满汉文化混乱对接中,“四王”作为传统文人做出的文化抉择和身份定位,这使得四王的“复古”有了更深厚的基础和更复杂的背景。“古”之为何,前文已有陈述,绘画之“古”就是古人的理论思想、绘画风格、画理画法等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所形成的绘画传统。任何一家一技一思想虽其为古,但不能代表真正的“古”即传统。王时敏祖孙和王鉴的家族“仿古”是独尊“一脉”,耽于“文人画”笔墨和造型设境的方式方法,乃“文人画”及其理论文脉的承传者。其“仿古”之“古”仅仅是文人画“南宗”一路的董、巨,最后又落到黄子久。此乃专仿一门、一家,而非真正仿“古”。他们甚至认为“溯源董巨,六法如是”“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2]俞丰:《王鉴画论译注》,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30页。“以子久为专师,今五十年矣”[3]王原祁:《王原祁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350页。等等,并视董巨为“正宗法派”。其他的则“因知时流杂派,伪种流传”(王原祁),“妄以己意衒奇流传谬种”“人多出新意,谬种流传”[4]陈传席、陈辞:《王时敏》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王时敏),“画之有董巨……舍此则为外道”[5]俞丰:《王鉴画论译注》,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30页。(王鉴),等等。如上几则可见“四王”是通过董其昌而承续“文人画”思想之“正宗”,其他的则是关乎“种”的纯不纯的问题,如云“谬种”“伪种”“外道”,并视“……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戒之”[6]王原祁:《雨窗漫笔》,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王原祁)。他们的“正宗”“纯种”即是“董巨逸规”,实际上即是由宋始自元而下,至明代以南北分宗“接力”的“文人画”理论及思想的一脉相承。而这一正宗正统之脉因其平和中庸的个性与清朝政权达成了合作,挟以个人的政治、文化、社会地位而被尊奉为“正统画法”,由此统摄影响了中国画坛数百年。至于石涛、四僧,皆于近世得到肯定褒扬的研究与发掘,在当时皆有“民间异类”之嫌,不像当下这样名声显赫。“四王”经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至王原祁,清初“四僧”的时代已然过去,具有“自我”精神的强烈个性创造的遗民画家都已去世。至此,“四王”主要以王原祁为代表,其影响力及至民国时期,由此也引发其时清醒之士要革“王画”之命。
如果站在绘画史的高度来看待“四王”诸家,或其亦属无辜。“四王”因受到“文人画”思想的规导和影响,几至以其为“祖宗”,并上升到保其“种”的纯粹的执着境地。但是“四王”复古的初衷与赵孟复古的初衷当属一致,都是为了在少数民族入主政权的语境下保存汉文化的正统地位,延续他们所认为的“正统”绘画的火种。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显然他们的所谓“正统”使得中国绘画发展的道路愈显狭窄。他们专师“南宗”一路,并非抉其精髓,而是于艺术方式及形式上过度执着于笔墨形式,从而不断剥离中国画“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由技入道”的本体精神。由此,我们不得不慨叹“文人画”这一历史“文脉”对中国传统山水画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更慨叹于这一理论和艺术形式竟会于其后的漫长历史中际会不同的历史时事和重要“人脉”而得以生存发展,并始终占据着无可匹敌的正统地位。而关于“四王”绘画源流及其“复古”真相的探究,当下仍然具有意义。它既有助于我们依据绘画史实,重新审度和辨析“四王”绘画的画风成因及历史地位,也有助于我们以其绘画史实镜鉴当下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