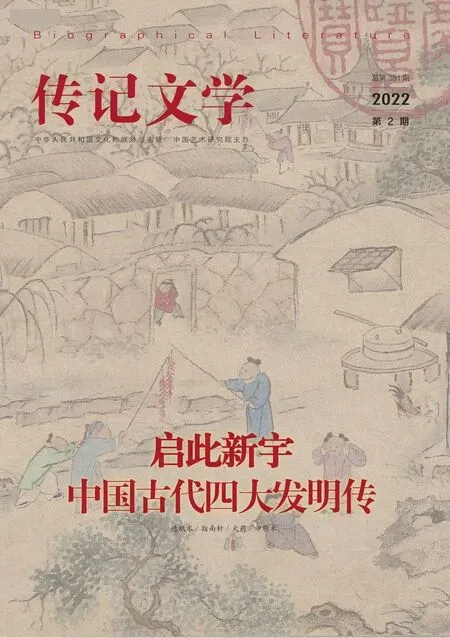公木先生的为人和治学(二)
2022-03-08赵明
赵 明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研室研讨和小酒馆聚餐:平易近人的公木先生
公木先生把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工作,给了文艺、教育事业,给了青年,给了一切需要他帮助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是学者、诗人,又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些,是与他完全陌生的人,无论是在路上、书店、邮局、公交车(除了公务,公木先生参加其他活动概不要车)上或餐馆等处与他相遇,都不会想到面前这位平易近人、慈蔼和善、穿着朴素的老人,会是万人传唱的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东方红》的歌词作者。
公木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与普通人无异,甚至比普通人更简单。家里饭桌的菜一般是芹菜、豆芽之类蔬菜的轮换,要摄入蛋白质就是永远不变的豆制品和鸡蛋。鱼、肉不是没有,而是难得一见。公木先生与吴翔老师不是素食主义者,但实际成了标准的“素食者”。二位老师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简单、节俭,是革命年代艰苦奋斗传统的延续。待到“文革”结束,已近古稀之年的公木先生又患上了糖尿病,并且不可逆转,糖尿病将同他“终生为友”。和他相濡以沫的吴翔老师就开始严格遵守医嘱,陪他共同采取了苛刻的“饮食管控”。我去他家,有时谈事忘了时间,起身要走,恰赶上午饭时间,我也就不再推辞这份特制的“保健午餐”。有时,因怕老师和师母说我挑拣,我甚至自我鼓励:“这是勤苦奋斗的午餐,也是保健防病的午餐!加油!努力加餐!”
在熟悉公木先生的同事和朋友们印象中,吴翔老师持家节俭是出了名的。在“庆祝公木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暨从事创作学术活动五十五周年”的会上,我曾听到与公木先生有逾世之交的杨公骥先生讲了公木先生艰苦生活的往事,其中说起吴翔老师直到50年代都不知“味素”(即味精)是什么、如何用时,听者多感难以置信,但这绝非是一句笑谈。
我们教研室每周都有一次业务学习研讨,安排在其中某天下午,话题多是讨论古典文学或当前学术界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那是一个思想活跃、激情迸发的时代,公木先生很愿意参加这种讨论,也经常发表独到的见地。公木先生的到场,大大激发了与会老师们的兴趣和热情。每逢研讨的那天,好像在过一个“学术节日”。几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很快结束了,能量消耗完了,肚子也空了,但兴奋和激情并未消退。于是有人提议,会后再到“四分局”附近的饭店“撮一顿”“整一口”,“曲终奏雅”。这建议里就包含着给处在“饮食管控”中的公木先生提供一个“解禁”的小机会,公木先生也心领神会。于是,研讨结束后,几个人便总是簇拥着公木先生来到“四分局”。
80年代,“四分局”对于吉林大学的学子和教工来说,就像当年的王府井之于北京市民、中街之于沈阳市民、中央大街之于哈尔滨市民一样,都是都市的繁华区、商业圈。稍有不同的是,“四分局”作为商业圈,它的级别较低,只供一隅需求,并非面向全城。但对于整天奔忙于工作、学习,无暇去远处购物的吉大师生来说,“四分局”几乎能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需求。这个生活功能区,不仅有商场、邮局、医院、幼儿园等,还有一个摆满蔬菜、水果和肉、蛋、鱼、虾等副食的露天市场。几家很红火的小饭店也开在市场边的街面上,来此光顾的自然都是“吉大人”和他们的家属。特别要提的是,在菜市场里的小饭店旁,有一处独特的,令我至今难忘的美食景观:汽油灯下,有一个身体瘦弱,眼睛浑浊,头戴白帽的老头,推着一辆车子。车上面的玻璃柜里,竖着一串串熏制成金黄颜色的豆皮卷。因为是祖传秘方制成,又诚信不欺,这个物美价廉、被“吉大人”冠名“老韩头豆皮卷”的“超级美味”,便成了白天投入紧张教学科研工作,晚上想喝口小酒的中青年教师的最爱。每天都有一批批带着对晚餐美好向往的师生来到“四分局”,就是为了那串色香味俱全、蜚声远近的“老韩头豆皮卷”。
当陪同公木先生一行人选了一处很洁净的小饭店后,我一般便立即跑到“老韩头”那里去。刚好他推车才到,我迎上去抢先买上20 串刚出炉的豆皮卷。进了饭店,已经落座的老师们,包括公木先生,都看着我举起的豆皮卷发笑了。我把豆皮卷放到桌上,诱人的香味便弥散开来,大家便不待菜肴上齐,就向接待我们的老板要了两瓶“银瀑”啤酒外加半斤散装白酒。紧接着,这家饭店招牌的熘肉段、烧茄子、炒粉丝、炒土豆丝等,也都陆续上齐。大家举杯,能喝点白酒的就喝两盅散装;愿喝啤酒的,九台出产的“银瀑”,就是当年长春市最好的啤酒。
一向同来的郭石山先生是湖南人,和公木先生年龄相仿,在30年代做报人,常在报端发表诗作,50年代到吉大中文系任教,主讲唐诗宋词。郭石山先生颇具长者风范、诗人气质,是性情中人,喜饮酒赋诗。他和公木先生一样为我们所爱戴,是可以无拘无束表达意见的良师益友。
有一次,公木先生和郭石山先生都喝了点酒。尽管公木先生喝的是啤酒,两位师长也都意兴盎然,借酒兴谈诗论词。说到好酒诗人时,两人一致“点赞”的竟是陶潜,而不是每日高唱“将进酒,杯莫停”,被余光中称作“酒入豪肠,七分月光,三分剑气”的李白。因为二人共同的感受是:太白固然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诗人,他的《将进酒》更是他“兴酣落笔”、“诗成啸傲”的千古绝唱,但就“酒的蕴味”而言,太白之酒近仙,非凡人可饮;而陶潜之酒则近人,是村民百姓皆可饮的。两相比较,五柳先生的酒,味道更“醇”。陶潜的诗和他本人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真醇”的诗美和人格美。
一晃40年过去了。当年教研室的“热点讨论”、“四分局”小饭店聚餐、散装白酒、二位先生饮酒论诗、“老韩头豆皮卷”,还有东北流行菜熘肉段、烧茄子等,都带有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特色。经历了的人,对于那段“迎春”历程,都会留有深刻而独特的记忆。
古松返青的“归来诗人”:公木先生的淬火和反思
公木先生经常对人说,写诗对他来说是业余活动,他的本职一直都是教师。从青年到老年,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即使职务有教育长、所长、系主任、校长这样的变动,但他的本职和责任始终是在教坛上。“教坛”和“诗苑”,本职和业余,对他来说又是紧密关联的。这关联正如他自镌的座右铭:“以爱塑人,以诗化魂。”
在“新时期”伊始,公木先生就发出了热烈的歌唱。尽管诗作不是很多,但他却以独特的风采,成为新诗苑中一棵“返青的古松”,和艾青、臧克家、田间、苏金伞、卞之琳、严辰、蔡其矫、邹荻帆、阮章竞、程光锐、绿原、牛汉、陈敬容、辛笛等诗人一起,站在了“归来诗人”队列的前排。其中《棘之歌》《俳句》《申请》《眼睛》等,在诗坛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稍后两三年,也就是在公木先生研读老庄,思考和撰写《老子说解》的过程中,他的诗作也随之进入了哲理思考期。此时,公木先生内心的烈焰和激情,开始逐渐转化为冷静的思索和深沉的思考,坎坷、磨难、历练、覃思以及他的学术思考向哲学领域的延伸和求索,也都使他对历史、社会、人生、自我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因此,从这时起,在公木先生的创作中,“哲思”与“诗情”开始交汇到诗章中,他的诗有了新的超越,这便有了情怀和覃思的交响——《真理万岁》,以及《读史断想三题·未来学》中留下的隽语:“假如记忆的仓库倾圮,/想象的能源便发生危机;/假如追求的航道迷斜,/理想的灯标便势必毁灭;/假如义愤的火山窒息,/心灵的显像便陷于凝滞。/于是创造失去动力,/生命失去意义,/艺术失去光辉,/假恶丑扬扬得意,/历史舞台将为疯狂独据。”
公木先生的这些新篇在诗苑的出现,令关注他的朋友、学生和读者,无不明显感受到了他诗情中闪烁的覃思之光,诗界和诗论家也多把它们作为公木先生反思的结晶。我更喜欢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眼睛》,认为它神情毕现地绘出了坎坷历尽,坚强、睿智的诗人双眸深处的淬火经历。

1983年5月,公木与艾青(左)、冯至(右)谈诗
《眼睛》载于《诗刊》1984年第11 期,是作为和陈敬容的同题诗而发表的,两诗各具特色。公木先生的诗,是读了孙犁的《眼睛》有感而发的。二者的诗,都把眼睛看作是人类心灵的窗户,都从概括人生的体验出发,从婴儿、青年、中年、老年眼睛的不同中判断人们心灵世界的变迁。相同的是,二者都把婴儿的眼睛描写为“清澈的”,把青年人的眼睛描写为“热烈的”,而对中年和老年的判断就大不相同了。在孙犁的诗中,“中年人的眼睛是惶惑的”“老年人的眼睛是呆滞的”;公木诗则写“中年人的眼睛严峻的”“老年人的眼睛是睿智的”。前者是浓重悲伤、经历创痛的画像;后者则是执着坚毅、洞知豁达的画像,实则就是公木先生的自绘像。二位老作家在人生的行旅中,都经历了苦难、坎坷,但作为诗人、学者进入晚年而成为“智者”和哲人的公木先生,似乎更超脱了痛苦,趋于一种恬静平和的心态,往事在他眼中,不过是“一本摸索断线了的百科书/一张偿付过了的账单/苦辣酸甜都已中和为平淡”(《眼睛》)。公木先生在晚年,确乎如此,他谅解了所有对他个人造成伤害的人,而他刚正无畏的情怀和内敛的燕赵侠骨,又使他每逢看到年轻人遭遇困厄、身处逆境时,便会发声。对于后来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北岛等人的出现,他较早就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和热切的评论。他甚至为舒婷获得全国性的大奖著文投上了重要而公开的一票。对朦胧诗,他始终认为既要理解和支持,也应引导和提升,裨助其融入中国当代文化多元汇集的主潮之中。他在1983年2月发表于《芒种》的《诗论四则》中就提到:“诗,无妨朦胧,但必须能令人猜懂。诗,都有点谜语的意味,只要形象新鲜,合情合理。”后来,他还在《〈朦胧诗〉二人谈》中说道:“……朦胧作为一种风格,从来不成疑问,朦胧美即在日常生活中,亦是经常体验到的……困难在于有些作品读不懂……这是一;再者,有些诗似乎猜出了一点意思,却又感到这个意思实在不够意思……”晚年的公木先生,更如海岸的一座礁石,任浪涛撞击,海潮起落,依然沧桑无畏地守护着身后绿地上的几株新苗。
诗人论诗:公木先生眼中的诗歌长河
公木先生以诗名世。他作词的歌曲,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曲)等,在几代人中广为传唱,他的诗歌也在中国当代诗苑中独具特色。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公木先生还是学者、诗歌评论家、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专家。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不是那种静坐书斋、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一生都没有那个条件,或者说,即便有了那样的条件,他也执着于对现实的关注,执着于审视历史与未来两端。他就是那种站在历史与未来交叉点上的学者,在他的视野里,总是前瞻古人,后思来者。他拳拳服膺的是如下箴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中而不知外,谓之鹿砦;知外而不知中,谓之转蓬。”(《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序言”)公木先生就是视野兼具古今中外的学者。作为当代诗人,公木先生不仅为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写出了大量切中肯綮的评论文章,而且能够在正本清源的工作中梳理好今古承嬗和发展的脉络,让读者得以眺望一条源远流长的文学之河在千回百转、奔腾向东的流程中,展现出了多少令人悲欢激赏的景观。
公木先生的评论打破了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分离和隔阂,他的诗论,上起于诗歌萌生与成熟期的先秦。他认为:夏、商时代的诗歌仍处萌生状态,直到周代“制礼作乐”,以迄百家争鸣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真正的诗歌成熟了,形成了以汉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以儒、道、诗、骚为代表的不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意识,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由两汉至明清,经历了拓展与发展期,古典诗歌掀起了四次高潮:古典诗歌的第一次高潮产生于魏晋时期。魏晋时期冲破了两汉儒学一尊的思想桎梏,在“人的觉醒”带来的“文学的自觉”中,迎来了以慷慨使气、言志缘情、田园山水、南妍北质、声病之学、骈俪之说等为特征的第一次诗歌高潮。至中国封建社会如日中天的唐代,古典诗歌达到了第二次高潮。唐代时南北一统,民族融合,儒道释并存,诗律理论成型,科举的“以诗取士”等所开创的格局,终于出现了百花争艳、群星丽天、各呈异彩的诗国大观。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高峰。“百花齐放”的唐诗,又是可堪与战国的百家争鸣相互辉映的文化景观。唐诗高峰之后的宋诗,仍然风韵犹存,在承续唐诗中实有开新和发展的表现,即如论者所言:“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锺书《谈艺录》)盖亦艺术趋新求变规律的合理体现。如合诗境与词境于一体而观之,宁说是更胜一筹。唐诗高峰后宋诗的迴澜扬波,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三次高潮。尤其在诗歌理论造诣上,境界、韵味、妙悟、意象诸说日益成为诗歌美学的重要范畴和主要特色。严羽的《沧浪诗话》实是唐宋之后综论诗学的标准典籍,至此中国诗歌古典主义已成为终结。

公木先生与本文作者(1993年摄于青岛)
之后则是古典诗歌流变的分化与深化时期。经历了辽、金、元至明清,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由诗的前进运动和基本风貌来看,诗歌已从古典主义中分化出来,并在不断深化中朝着近代目标演进。古典主义,百足之虫,千尺之躯,虽死而不僵;但就主体而言,诗歌则适应着元明以降商业空前繁荣,城市消费日益发达,市民阶层逐步兴起的潮流,古典诗歌形成了第四次高潮。大都会为中心的“古白话”形成并成为书面语言,一种新的社会潮流在悄然运行。这直接反映在王阳明心学解体的过程中,并折射到艺术美学领域:“爱”“欲”“性”“情”“心”“私”“我”,等等,都被积极肯定,公开倡导。强调个人感性存在,重视男女情欲问题,明确表达了自然人性论的近代倾向,于诗歌上则表现为贵“本色”、崇“性情”、尚“童心”、扬“性灵”,鼓吹“自我立法”、“师心不师古”。文艺潮流同样五花八门,或倡言“平易”(公安派),或追求艰涩(竟陵派),却共同呈现出对传统诗教的背离。在技巧上,公开提倡“趣”“险”“怪”“浅”“俗”“艳”“谑”“骇”“出其不意”“冷水浇背”,一反“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在形式上,体裁多样化益发彰显。除了传统的诗词歌赋外,更风行散曲、套数、诸宫调、鼓书、弹词、山歌、小调,以及杂剧、传奇与剧诗。质言之,在中国诗歌流变的长河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性转折,这亦即从古典谐和走向近代崇高的开端。但这一开端的初潮,不久就为清朝的保守文化政策强力遏制,没有能够像西方的“文艺复兴”那样形成主峰巨浪,以至随着“康乾盛世”的回光返照,一直并未绝迹的古典主义大有再度抬头的趋势。
公木先生认为,中国诗歌近代化以至现代化进程的到来,是与中国走向近代的外铄特点分不开的。沉沉酣睡中的天朝迷梦是由英国的鸦片贩卖和西方列强的炮舰打破的。在西学东渐中,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先后传来,构成近现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双重主题变奏交响的主旋律。“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高扬了这一旋律。
对于“五四”以来起于白话文运动的“诗体解放”所掀起的第一个浪潮,公木先生曾用概括而优美的文字,描绘了一路上的波峰浪谷、竞逐风流:
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开创了纪念碑式的作品。他从《星空》走下来,写出了革命的《前茅》,从而涌现了一个斑驳陆离的诗群:包括曾醉心于象征手法的穆木天、冯乃超;“狂飙”式的高长虹、柯仲平;“璎珞”式的戴望舒、施蛰存;起步于“湖畔”的应修人、冯雪峰;以及“暴风雨的歌者”蒋光慈、钱杏邨、孟超、黄药眠、柔石、胡也频等,宛如群星丽天,杂花生树,在起点上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但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下,却共同走上了战斗的道路。
以上是对新诗中“自由派”的简要概括。对于另一种主张诗要有格律的派别——新格律诗派,公木先生也对其代表人物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作品所表现的“诗美”作出了精彩的评析:
徐志摩、闻一多同属于“新月派”诗人,他们的诗作都是“拿来”西诗形式而又羼入文言辞藻并有鲜活的口语入诗。所不同的,是风格上的差异:前者是轻快而偏向浪漫;后者是凝重而贴近现实。
这些,都是对20世纪20 至30年代中国自由派诗人和格律诗派代表人物总揽全局而又切中肯綮的诗评。此后,他对各时期的代表诗人如萧三、艾青、田间、臧克家、何其芳、鲁藜、袁水拍、蔡其矫、张永枚、流沙河以及以舒婷、北岛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也都以不同形式作出了精彩的评论。这些诗评,正如臧克家在给公木先生的信中所说:“你是诗人,又是学者,出语自然不凡。”公木先生不仅是一位具有理论建设意识的学者,写出了大量关于现代诗歌的评论文字和理论文章,而且在学者和诗人当中,他又是为数不多能把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对接的学者。
公木先生有关诗歌和诗论的著作,内容丰赡系统,其中包括中国古典诗歌史论、现代诗歌评论以及论民族传统与新诗歌发展道路的三大系列。此外,他所撰写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也应归入这一系统。由丁元、张朔、黄准主编,中国香港雅园出版公司出版的《公木诗学经典》,收录了公木先生百万字的论诗著述,用“纵览古今,体大虑精”来概括公木先生宏大系统的诗学论著,应不是溢美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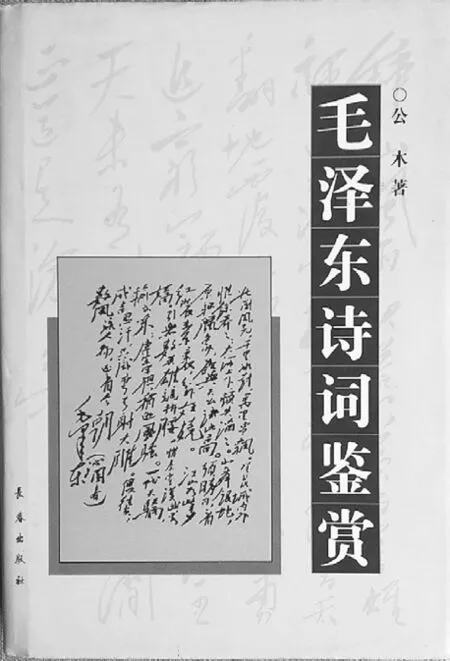
公木:《毛泽东诗词鉴赏》
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公木先生进入晚年,他多年的思考趋于沉淀与升华,最终结晶为瑰丽恢宏的诗学论著——《第三自然界概说》。这是一部诗的美学、诗的哲学。我无法对这部极诗国之浩瀚,穷艺术之灵奥,宗教、科学、艺术穿透往来,“三个自然界”相互渗透,芸芸滔滔,尽寓美因,覃思睿智,皆通艺境的著作作更多的评述,只想指出:漫步芳草如茵、繁花似锦的“第三自然界”,那千汇万状的诗歌景观,足以令人流连忘返,于悲欢激赏中得大快乐。大块文章,皆供我读,自待有心之人自领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