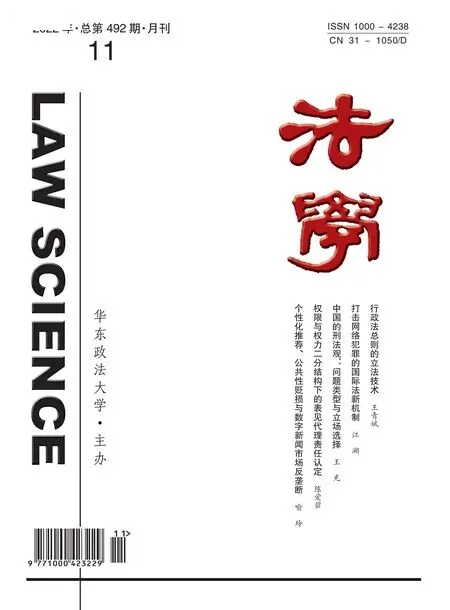个性化推荐、公共性贬损与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
2022-03-04喻玲
●喻 玲
新闻业生产的信息构成一种公共知识,〔1〕参见徐桂权:《新闻:从意识形态宣传到公共知识——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媒介研究及其理论意义》,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2期,第38页。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有助于社会成员融入公共生活,并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统一意见,是加强社会团结之利器。〔2〕See William A. Galston,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Civic Educ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4, Issue 1, 2001, p. 224.当新闻在社会中依然被视为“第四种权力”而被构造、尊重时,急遽发展的算法个性化技术却正在通过操作和改变新闻的生产方式来重新描绘新闻的价值。不论是封闭、专业、稳定的新闻生产方式,〔3〕参见姜华、张涛甫:《传播结构变动中的新闻业及其未来走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第185页。还是幽微精妙的蕴含意识形态与市场双重属性的新闻商业模式,〔4〕参见刘杨:《习近平谈文创产业:守正创新,坚持正确导向》,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8/content_5544382.html,2022年3月16日访问。也不管是至尊至贵的新闻媒体,还是身为“信息被动接收者”的消费者,但凡数字新闻生产、传播所涉之处,算法个性化推荐技术之手都可以巨细无遗地对其加以操纵和把控。此际,新闻媒体俨然已不再是原初的那个“公众的看门人”,〔5〕参见彭增军:《算法与新闻公共性》,载《新闻记者》2020年第2期,第49页。而是一个正在向寄居其中的数字新闻平台及其所构建的算法KPI不断妥协的“信息贩售者”。
在现代社会,新闻的价值和功能为何?个性化新闻推荐是如何颠覆新闻生产方式的?数字平台基于何种逻辑来控制新闻的供给并控制新闻业的生产?新闻媒体如何与公共性渐行渐远?新闻公共性的回归是否假借平台反垄断之手即可实现?数字新闻平台反垄断的出路为何?种种疑问,皆因新闻与新闻业已被个性化推荐算法颠覆而成为尖锐的时代课题。对此,本文无意也无力以兼及社会、经济、科技、伦理与法律关系互动的宏大叙事方式进行完整作答,只想以此为背景,以促进新闻公共性提升为目标,对该以何种反垄断方式来应对算法技术给新闻市场竞争带来的挑战展开理论探讨,对结合数字新闻市场构建的技术基础及其内含的竞争本质进行反思,借此助力平台反垄断目标实现的理念与方法更新,〔6〕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2022)》第22条。以期为同样深陷新闻公共性危机的各国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一、数字新闻市场构建的技术基础:个性化推荐
个性化新闻推荐是指通过大数据技术收集消费者个人数据与行为数据,探寻消费者的“内容消费足迹”,准确预测消费者的阅读兴趣偏好,为不同消费者推荐不同的内容,进而提升个性化阅读体验、获取流量、促成交易的互联网信息服务。〔7〕See Christopher Townley, Eric Morrison and Karen Yeung, Big Data and Personalised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EU Competition Law, Yearbook of European Law, Vol. 36, 2017, p. 699.个性化新闻推荐已成为数字社会最主要的一种新闻推荐方式。〔8〕参见舒悦、尹莉、李梦雅:《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载《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1期,第102页。
(一)个性化新闻推荐的优势
当盈余被成功分享,新闻生产便开始了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旅程,社会内容信息生产总量呈“指数级”爆炸式增长。但是,新闻的生命周期很短,如何将在其短暂的生命周期内传递给对它们感兴趣的消费者,是新闻平台所面临的难题。〔9〕参见项亮:《推荐系统实践》,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推荐系统是防止消费者陷入过度信息选择障碍的技术防线。”〔10〕Shuai Zhang, Lina Yao, Aixin Sun and Yi Tay, Deep Learning Based Recommender System: A Survey and New Perspectives, ACM Computing Surveys, Vol. 1, No. 1, 2018, p. 2.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人们将搜索引擎视为信息过滤机制的经典策略,但搜索引擎属于被动的信息过滤机制,无法主动响应消费者的阅读意愿,因而不能提供个性化的结果,〔11〕参见陈昌凤、师文:《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的技术解读与价值探讨》,载《中国编辑》2018年第10期,第10页。这为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崛起创造了技术成长空间。起初,算法仅被用于运算和数据处理,伴随数据的迅速增长、数据分析服务行业的急剧发展以及数据质量和可用性的显著提高,算法亦迭代到“自我学习算法”阶段,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显著增强。因此,今天算法已在商业决策与商业预算分析实践中被普遍运用。数字新闻的生产绝非传统意义上孤立的“机械式”活动,〔12〕参见张海超:《算法新闻生产中的把关及伦理问题研究》,载《传播力研究》2018年第20期,第217页。算法不仅仅是机械地按照消费者偏好的预先设定值安排新闻生产与推荐,还需要对实时采集的与注意力消费相关的各种数据(阅读内容、屏幕停留时长等)予以快速反应,甚至需要通过对不同消费类型的注意力吸收数据进行分析、模仿、训练,以提升其个性化推荐的精准度及广告植入的可接受度。简言之,个性化信息服务演进成为提升消费者信息消费体验的竞争策略,〔13〕See Shuai Zhang, Lina Yao, Aixin Sun and Yi Tay, Deep Learning based Recommender System: A Survey and New Perspectives,ACM Computing Surveys, Vol. 1, No. 1, 2018, p. 16.个性化推荐算法犹如一座桥梁,便利了两岸的供给者与消费者,其广泛运用改变了新闻生产者、传播者与消费者互相联系的方式,也使得新闻市场向着数字化的方向演化。〔14〕See Thomas H. Cormen, Charles E. Leiserson, Ronald L. Rivest and Cliあord Stein,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MIT Press,2009, p. 5.
(二)个性化推荐算法的类别
除了具有推荐系统过滤信息、解决冷启动问题的一般功能,个性化新闻推荐作为推荐系统的子任务,还肩负着促进信息与消费者需求精准匹配的重任。作为推荐系统中最核心的技术,个性化推荐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平台推荐系统性能的优劣。
在个性化推荐系统中常使用的算法有五种:第一,基于内容匹配的推荐算法。其程序逻辑是建立消费者模型,推荐与模型相似度高的内容。用于建立该模型的属性包括:(1)年龄、性别、学历等消费者人口统计属性;(2)收藏和发表的评论等消费者的兴趣属性;(3)住址、环境特征等消费者的位置属性。用于建立内容模型的属性包括关键词、主要人物、内容形式等。建立新闻“标签化”和“标签”再精细化是基于内容匹配推荐算法的应用方向,比如“宠物标签”再精细化为“猫”或“狗”,又如“法律标签”再精细化为“经济法”或“民商法”。基于内容匹配的推荐算法的结果专业化程度高,但新颖度较低。第二,基于消费者行为的推荐算法。其程序逻辑是采集消费者数据、分析消费者行为“足迹”、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为其推荐“可能感兴趣”的新闻。消费者行为数据的采集范围既包括点击、阅读、收藏、评论、转发等显式行为,也包括网页浏览时间、鼠标轨迹等隐式行为。平台收集的消费者行为的数量越多、范围越广、类型越多样,对消费者兴趣和需求的了解就越全面,对消费者偏好的预测就越精细,推荐结果的精准度也就越高。第三,基于社交网络的推荐算法。其程序逻辑是依靠如亲密程度或互动频率等指标计算消费者间的相似度,将相似度较高的消费者所感兴趣的新闻纳入推荐候选的集合中,从而向目标消费者推荐感兴趣的新闻。〔15〕参见陈豪、王泽珺:《个性化推荐算法综述》,载《企业科技与发展》2019年第2期,第56页。该类算法可增加个性化新闻推荐的可信度,因为相较于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的结果,消费者显然更信任与自己有社交关系的好友的推荐。向目标消费者输出推荐物品的同时,标注该结果是来自目标消费者的8个好友,显然更能让消费者心动。比如,微信公众号中被标注“10位朋友分享”或“28位朋友读过”的文章更容易被消费者点击阅读。第四,基于深度学习的推荐算法。其程序逻辑是从样本中学习数据集具有的本质特征,或从多源异构数据中获得统一表征,向目标消费者推荐感兴趣的新闻。〔16〕参见黄立威、江碧涛等:《基于深度学习的推荐系统研究综述》,载《计算机学报》2018年第7期,第1621页。例如,Facebook“收集了大约16亿人的数据,包括‘赞’和社交联系,其利用这些数据来推测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如投票习惯、关系状态、与某些类型内容的互动以及人们对特定内容的感受。”〔17〕Maurice E. Stucke and Ariel Ezrachi, How Your Digital Helper May Undermine Your Welfare, and Our Democracy,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32, No. 3, 2018, p. 1277.与其他推荐算法相比,深度学习可以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需求、项目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历史交互,因而能够给出更高质量的建议。第五,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其程序逻辑是发挥群体的智慧和遵循“相似的物体具备相似的性质”的特点,通过收集消费者点击、兴趣分类、主题、兴趣词等相似性数据,找到相似消费者或物品。该类算法可分解为协同(利用群体之间的相似性来做推荐决策)与过滤(从可行的内容推荐项中将消费者喜欢的内容找出来)两个步骤。〔18〕参见张志军:《社交网络中个性化推荐模型及算法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35页。该类算法原理简单、思想朴素,易于分布式实现,可以处理海量数据集,利于解决“信息茧房”问题,虽然推荐精准度较高,但是冷启动问题、稀疏性问题〔19〕数据稀疏性问题指如果用户对商品的评价非常稀疏,那么基于用户的评价所得到的用户间的相似性可能不准确。冷启动问题是指若从来没有用户对某一商品加以评价,则这个商品就不可能被推荐。系统可扩展性问题指随着用户和商品的增多,系统的性能会越来越低。参见王维国:《个性化推荐——人民网发展的利器》,载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316/c403195-28203859.html,2022年4月10日访问。也犹如阿喀琉斯之踵,让其难以独当一面。
(三)个性化新闻推荐的技术逻辑
在数字社会,人们将个人信息视为一种商品,他们愿意放弃一些个人信息,以换取个人利益,个性化推荐系统因此而生。在此系统中,平台收集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数据作为推荐系统的输入,反过来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20〕See Arik Friedman, Bart P. Knijnenburg, Kris Vanhecke, Luc Martens and Shlomo, Privacy Aspects of Recommender Systems,in F. Ricci, L. Rokachand B. Shapira (eds.), Recommender Systems Handbook, Springer Science, 2015, p. 658.
从目标上看,个性化新闻推荐以识别阅读意愿为目标,既包括阅读的欲望,也包括所能承受的注意力价格(保留价格),前者通常体现在消费者对新闻的浏览时间、关键字的使用和搜索频率以及与已收藏内容的相似性;后者通常体现在消费者的注意力消费水平及消费者的比价习惯。对于同样的新闻,受消费者偏好、预算及预期收益大小判断的影响,个体的阅读意愿相去甚远。〔21〕See Oren Bar-Gill, Algorithmic Price Discrimination: When Demand Is a Function of Both Preferences and (Mis)Perception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86, No. 2, 2019, p. 226.从流程上看,在消费者登录平台后,个性化新闻推荐技术包括如下三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收集分析消费者个人属性数据与消费行为数据,识别消费者的阅读意愿。其价值在于将注意力消费需求与新闻内容初步匹配。平台业务不同、功能有别,推荐特征组合不同,数据收集的范围也会存在差异。综合而言,平台收集的信息基本包括:(1)消费者的点击或查看行为;(2)背景信息,如位置或情绪;(3)消费者朋友、家人或同事等社交信息;(4)年龄和职业等人口统计参数。〔22〕See Arjan Jeckmans, Michael Beye, ZekeriyaErkin, Pieter Hartel, Reginald Lagendijk and Qiang Tang, Privacy in Recommender Systems, in Social Media Retrieval,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2013, p. 5.平台利用数据挖掘和算法分析工具对阅读记录、上网痕迹进行跟踪、分析,初步绘制包含消费者偏好、习惯、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画像。
第二步,基于受众阅读反馈的模型检验与召回。其价值在于打破传统新闻时代内容输出处于从生产者到受众单向流通的僵局。平台在初步了解消费者阅读意愿的基础上,结合新闻的静态特征与动态特征,前者包括关键词、主题分布、发布时间等,后者包括新闻热度、新闻评分、累计点击量、消费者位置等,〔23〕参见王绍卿、李鑫鑫等:《个性化新闻推荐技术研究综述》,载《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020年第1期,第26页。以及在对消费者的初步内容投放反馈(是否阅读、阅读时长、转发点赞等)的基础上,进行内容投放策略召回,提升消费者、环境与信息的完美匹配程度。召回策略设计要求“性能极致”,一般超时不能超过50毫秒。〔24〕See A. Spangher, Building the Next New York Times Recommendation Engine, https://open.blogs.nytimes.com/2015/08/11/building-the-next-new-york-times-recommendation-engine/, last visit on Feb. 23, 2022.
第三步,过滤噪声,实施个性化新闻推荐。其价值在于最终确定注意力交易价格,完成交易并验证交易效率,为未来技术与交易架构改进提供支撑。消费者的信息需求是个性化新闻推荐的原动力,〔25〕参见谢新洲、王强:《个性化新闻推荐发展动力及趋势研究》,载《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6期,第4页。前两步为基础,通过删除停留时间短的点击等方式过滤噪声,并通过模型验证和反馈,推测出消费者的阅读意愿,索取消费者能够支付的最高注意力价格。其规则在于,阅读意愿较低的消费者获得较低的交易价格(较少的注意力消费),或调整推荐内容;反之,阅读意愿较高的消费者则获得较高的交易价格(较高的注意力消费)。
总之,尽管数字平台都将被推荐算法视为“黑匣子”或“商业秘密”,对其算法的工作细节讳莫如深,〔26〕See T. Bucher, The Algorithmic Imaginary: Exploring the Ordinary Affects of Facebook Algorithm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20, No. 1, 2015, p. 31.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平台都广泛使用“混合过滤”系统,综合利用不同推荐算法,以克服单一算法之下在数据稀疏、消费者评价不足、系统扩展时产生的系列问题。推荐系统在推荐内容、推荐方法、推荐对象等各个方面都朝着越来越多元的方向发展,消费者、物品、系统冷启动问题得以解决,〔27〕参见项亮:《推荐系统实践》,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海量的新闻内容在消费者层面得以过滤,人与信息的精准匹配度越来越高,消费者粘性也越来越强,注意力朝着数字平台汇集。个性化新闻推荐既能为消费者找到与其需求相匹配的内容,又能为内容找到与其属性相匹配的消费者,成为抓住消费者注意力的最根本方式。〔28〕参见舒悦、尹莉、李梦雅:《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载《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1期,第102页。
二、数字新闻市场的竞争:注意力的获取与分配
“个性化内容推荐的力量如若巧妙运用,会在潜移默化中给新闻媒体接触消费者施加一套行为约束规则。”〔29〕[美]詹姆斯·韦伯斯特:《注意力市场:如何吸引数字时代的受众》,郭石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消费者不是完全理性的,但内容推荐机制确为理性之物。平台借助个性化内容推荐以及运行该系统所依托的注意力吸收与运作机制成为数字新闻市场的无形之手,为消费者提供固定的数字新闻菜单,改变消费者行为,塑造消费者偏好,让消费者更容易被分类和操控。“垄断的微小因素惯于开不可预期的逻辑玩笑,其产生的后果与它们表面上微小的重要性是不相协调的”,〔30〕[美]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周文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在数字新闻领域亦是如此。
(一)注意力市场的搭建
注意力经济正日益成为一种消费产品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来复制的经济,但该经济形态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生存难题——人的数量有限导致注意力必定是一种稀缺资源。与高速增长的数字新闻结伴而来的是,无限的内容供应与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之间不断尖锐的矛盾成为新闻传播市场的主要矛盾。〔31〕参见刘燕南:《数字时代的受众分析——〈注意力市场〉的解读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3期,第168页。在这个内容丰裕而注意力稀缺的时代,赤裸裸地去吸引或攫取注意力会招人鄙视,〔32〕参见[美] 吴修铭(Tim Wu):《注意力经济——如何把大众的注意力变成生意》,李梁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77页。广告技术穷其所有给消费者带来的也只会是恶劣的体验,且广告商未必能因此获益,〔33〕同上注,第382页。相形之下,平台通过成功搭建一个全新的注意力交换市场成功化解了上述难题。
注意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多边市场,包括平台、消费者、新闻媒体、广告商四类主体,其中的平台是市场的中央计划者。平台渴求注意力及其背后的利益,本质上是注意力商人,但它又深知“赤裸裸地去吸引或攫取注意力会招人鄙视”,故在这个新型市场中,平台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出现,而是构建一个“观念市场”,通过“个性化”标签为注意力市场披上“公共领域”的外衣,让深受广告困恼的消费者放松警惕,最终交出自己放置在广告市场之外的注意力。〔34〕参见[美]詹姆斯·韦伯斯特:《注意力市场:如何吸引数字时代的受众》,郭石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155-157页。其实从原则上,人们对于中央计划的形式没有任何意见,只是不喜欢糟糕的中央计划。平台企业以“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创造出全新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市场,打造出更加大型的中央计划市场——注意力交换平台。随着这一趋势的延续,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是通过“去中心化”的集中创造和管理的网络进行协调的。〔35〕参见[美]亚历克斯·莫塞德、尼古拉斯·L. 约翰逊:《平台垄断:主导21世纪经济的力量》,杨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67-68页。无所不知的中央计划者——平台,只需要考虑现有的所有信息,并决定如何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分配资源〔36〕同上注,第44页。便取得了自由市场永远无法企及的市场效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随着网民数量的爆炸式增加,新闻受众变革为新闻生产者和传播者,而新闻的消费却越来越集中在以平台为核心的新媒体手中。〔37〕参见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6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0页。
(二)平台获取注意力之道
在商业实践中,广告犹如转换引擎,总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效率将注意力这种“经济作物”变成工业商品。注意力市场上贩售两种类型的注意力:一是作为原材料的注意力。从“注意力给予者”获得,消费者用之换取平台提供的内容或新闻服务。“原材料”模式的注意力交换,类似于物物交换,此际平台不是交易媒介,而是交易主体。二是作为产品的注意力。以注意力信息的形式(广告受众)出售,是平台资源的一部分,平台以之吸引广告商。〔38〕See Paweł Drobny, The Attention Markets as a Challeng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Prace Naukowe Uniwersytetu Ekonomicznego We Wrocławiu, Vol. 63, Issue 5, 2019, p. 33.来自消费者的注意力是注意力市场存在的根基。平台通过为消费者提供足以补偿广告带来的任何滋扰的、有价值的内容,以低买高卖方式贩卖消费者的注意力,并从中获得收益。
为了掠夺更多的注意力、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平台有意识地采取了如下诸多策略:(1)粉饰定向内容,导致消费者信息选择失灵。于消费者而言,平台本应当交易的“指南针”,帮助消费者在日益复杂和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迅速捕捉符合其消费偏好的信息内容。然实际情况是,平台为了流量而“投其所好”,不但偏向于传播标题或关键词与新闻内容大相径庭的新闻,抑或是用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新闻标题或关键词来吸引消费者点击阅读,于是出现了大量充满噱头、欺骗点击率、“标题党”类型的新闻产品,越具煽动性的内容越容易得到传播并被算法优先排序。〔39〕参见高薇:《平台监管的新公用事业理论》,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92页。(2)构建评估困境,导致消费者交易决策失灵。消费者可准确评估任何商品的质量差异,迅速向公众告知质量退化,是市场有效竞争的前提条件。〔40〕See Maurice E. Stucke and Ariel Ezrachi, Competition Overdose: How Free Market Mythology Transformed Us from Citizen Kings to Market Servant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20, p. 20.但在数字平台主导的新闻市场,这两个条件都难以成立:其一,新闻产品是一种体验商品,除非完成了阅读,否则人们很难从外观上评价数字新闻的质量。其二,数字新闻产品质量评价受到偏好、阅历、学识、理解能力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消费者难以准确、客观地对质量作出评价,也不能轻易识别质量的下降。〔41〕See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84, Issue 3, 1970, p. 500.(3)推行成瘾机制,导致消费者消费理性失灵。平台吸引和保持注意力的关键是通过实时数据分析来进行生理性操纵,制造成瘾,尽可能增加消费者花在平台上的时间,维持“注意力循环”。〔42〕See Julia Brailovskaia, Jürgen Margraf and Volker Köllner, Addicted to Facebook?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Narcissism in an Inpatient Sample, Psychiatry Research, Vol. 273, No. 7, 2019, p. 54.尼尔·埃亚尔在其名著《上瘾》中提出了一套“接触—行动—获益—投入”的致瘾模型,认为擅长培养消费者习惯的公司往往不会将成本投入广告营销方面,而是将产品的设计理念与消费者个人情感等方面紧密连接在一起。〔43〕如脸书、推特、抖音等公司都采用了一套旨在通过斯金纳式的操作条件来塑造消费者行为的推荐算法。参见[美]尼尔·埃亚尔、瑞安·胡佛:《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钟莉婷、杨晓红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0页。设计“能让任何人上瘾的工具”,“最好地刺激对成瘾至关重要的神经物质的释放”,〔44〕Gregory Day and Abbey Stemler, Are Dark Patterns Anticompetitive? Alabama Law Review, Vol. 72, No. 1, 2020, p. 3.深受科技公司高管们的学习和追捧。成瘾改变了大脑的回路,临床研究报告表明,注意力的过度使用会导致难以戒断和人际冲突的增加等典型成瘾症状。〔45〕See Julia Brailovskaia, Addicted to Facebook?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Narcissism in an Inpatient Sample,Psychiatry Research, 2019, Vol. 273, No. 7, p. 55.
(三)注意力收益分配与新闻商业模式创新
在前数字新闻时代,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备受广告商宠爱,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随着数字浪潮的来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从印刷媒体转向更大程度的在线参与,导致新闻媒体的发行量和读者人数下降,广告收入大幅下降,财务状况出现断崖式下滑。〔46〕See UK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Overview of Recent Dynamics in the UK Press Market, 2018, p. 78.与此同时,新闻媒体还受到来自大型新闻聚合平台、搜索服务提供商和社交网络市场进入的冲击,流量(注意力)尽数流向平台,广告收益也随之转向数字平台,〔47〕See OECD, Competition in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s, 2020, p. 9.平台根据利己的规则分发流量与广告收益。当广告商纷纷逃离传统媒体转向数字平台时,最初的新闻生产者若不追随平台算法KPI,就没有机会得到任何补偿,传统新闻媒体习以为常的极高利润率便不复存在。另外,当新闻业惯以为之的内容质量取胜的竞争战略难以维系,在数字平台新闻业搭建的注意力交易市场,新闻生产者可以最低的成本接触大量客户,从而获得直接或间接的广告收益是时代给新闻媒体的另外一种机遇。质言之,在个性化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颠覆了新闻生产供应模式后,新闻商业模式也难逃被时代裹挟变革的命运,“不安分”的新闻媒体已然朝着参与平台流量分配与广告收入再分配的商业模式迈进。
但需注意的是,注意力货币化的方式丰富,注意力竞争也异常激烈。在流量竞争中,新闻生产者为数不多的可行商业战略就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尽可能多的内容,即实施总成本领先战略,哪怕以质量下降为代价。由于内容生产数量过多,有学者称之为“峰值内容(peak content)”,新闻业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其正在“峰值化”的内容生产数量,〔48〕See Martin Wright, Peak Content: The Collapse of the Attention Economy, https://www.mediamergers.co.uk/peak-content-thecollapse-of-the-attention-economy/, last visit on Feb. 26, 2022.所以只能进一步削减成本、降低质量、裁员、停业,〔49〕See UK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Overview of Recent Dynamics in the UK Press Market, 2018, p. 78.新闻公共性危机与职业化危机由此而生。
事实上,在线服务的竞争是“玩家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出为代价追逐流量的游戏”。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可以预见“峰值化”生产所滋生的是一个供过于求的、内容充斥的市场,这只会导致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上升,直到生产这种商品(新闻)变得完全不经济。〔50〕See UK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Overview of Recent Dynamics in the UK Press Market, 2018, p. 78.当千帆过尽,“峰值化”生产给新闻媒体预留的仍是四伏的危机。
三、数字新闻公共性贬损
(一)新闻公共性的价值
“公共”指一个关心公共利益并有能力对其进行民主讨论的团体,“公共性”是公民社会思想的核心。〔51〕See Michael Edwards, Civil Society, Polity Press, 2004, p. 61.新闻立命之本在于“公共性”,阿伦特认为,公共性的本体价值有二:一为“透明”或“无遮蔽”,即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为在场的人所见所闻;二为“公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即没有人仅仅是观众,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主体。〔52〕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5页。“发展共同利益、让与部分私人空间、换位思考并据此开展社会协作等,是有效治理、切实解决以及和平解决社会分歧的关键公共属性。”〔53〕Michael Edwards, Civil Society, Polity Press, 2004, p. 61.将此二者以工具化的方式在新闻领域铺展,新闻公共性工具价值除了提供信息外,还应当包括新闻所具有的公共性使用价值——搭建公共领域,保障公众参与,进而实现社会监督、舆论引导、价值弘扬、传播思想与涵养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功能。这种使用价值是新闻与所有其他信息相区别的重要标识。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寓居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搭建“不同群体和不同利益——包括不同语言、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少数群体——能够通过辩论、讨论、结社来表达自己意见的公共领域”。〔54〕Council of Europe, Recommendation No. R(99)1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o Member States on Measures to Promote Media Pluralism, 1999.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构成,他们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而本身就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55〕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公共领域的繁荣程度对民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只代表某些“真理”、如果不同的观点因排斥而被压制,或者如果某一组声音比其他声音更响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56〕See Michael Edwards, Civil Society, Polity Press, 2004, p. 61.在公共领域,市民间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进行公共交往。〔57〕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8页。在各自领域中已取得支配地位的新闻媒体,对其受众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大到不容被忽视,因此“新闻媒体要接受自己作为信息和讨论的共同载体的责任”。〔58〕[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此外,新闻公共性所具有的另一个重要工具价值是它不仅构成了个性化推荐技术可以对新闻或新闻媒体进行商业化利用的现实基础,如通过假新闻传播真广告,通过提供娱乐赢得利润,而且是新闻得以俘获被认定为网络空间硬通货——注意力的主要利器。当新闻媒体对娱乐和“生活忠告”乐此不疲,抑或新闻媒体被广告侵袭,甚至新闻本身就是一种超级广告的时候,文化批判型公众也转变成文化消费型公众,转变成同质性、肯定性和顺从性的“单向度的人”,〔59〕参见[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以往区分于公共权力领域、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便负起广告的功能,也失去了其独有的特性。〔60〕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1页。因此,在人们已经发现并可利用新闻这一“社会特殊信息身份证”来识别不同类型信息的数字科技时代,为维护国家对其特殊身份标识利用所享有的权力,法律上仍有必要通过公共性保留机制的建构来进一步发挥其身份标识所暗藏的多元社会价值。
(二)公共性贬损在数字新闻市场的映射
新闻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建构过程,〔61〕参见黄文森、廖圣清:《同质的连接、异质的流动:社交网络新闻生产与扩散机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2期,第18页。但个性化新闻推荐通过“投其所好”以及“避其所不好”式的同质化新闻传播,将消费者网罗至自己麾下从而剥夺公众“成长”所必需的距离,也限制了公众发表言论和反驳的机会。作为消费者的“公众”之批判逐渐让位于“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甚至有关消费品的交谈,即“有关品味认识的测验”也成了消费行为本身的一部分。〔62〕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197页。公共领域退缩,社会间距被极大拉近,新闻成为消费者流量追随、注意力获取的利器;在算法时代,新闻业正面临全面工具化的危机,〔63〕参见任玥:《新闻生产社交化与新闻理论的重建探讨》,载《新闻文化建设》2021年第6期,第87页。文化正面临被技术垄断的危机。
第一,新闻产品结构失衡。根据公共性强烈程度,新闻可分为公共新闻与非公共新闻。公共新闻,也称硬新闻,是指对公民参与公共辩论和为民主决策提供信息相关的问题或事件的报道,或者是在地方、地区或国家层面上对公民具有公共意义的当前问题或事件的报道。〔64〕See Art. 52A, The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Treasury Laws Amendment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 Act 2021, Part IVBA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其题材比较严肃,往往更关系国计民生及人们的切身利益。〔65〕See D. Wilding, P. Fray, S. Molitoriszand E. McKew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Platforms on News and Journalistic Content,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Report, 2018, p. 18.非公共新闻,或称软新闻,是指以市场为中心的新闻,主要包括专题文章、社会花边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和人们感兴趣的故事等。〔66〕参见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数字新闻市场的产品结构失衡不但表现为内容空洞的“软新闻”比例上升,还表现为原本严肃的政治新闻与司法新闻等“硬新闻”趋于“软化”。〔67〕如在全国“两会”期间,一些媒体娱乐化倾向突出,对代表委员中的明星大肆报道,深挖其花边新闻、行为穿着等内容,而对于民情民意的议题避而不谈,甚至恶意曲解制造爆点。硬新闻数量的充足性是新闻业行使“第四权力”——公众看门人〔68〕参见彭增军:《算法与新闻公共性》,载《新闻记者》2020年第2期,第49页。的必然要求,其可见度的显著淡化给不良信息的肆意流通留存了空间,导致新闻内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丧失,亦削弱了新闻的公共价值属性。
第二,新闻内容质量下滑。这主要表现为新闻多样性被破坏与不当内容(inappropriate content)增加。其一,新闻内容多样性是新闻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它有助于确保公民的消息灵通、能够科学行使公民权利。内容多样性既包括新闻内容本身的多样性,也包括新闻来源和视角的多样性。〔69〕See J. Strömbäck, In Search of a Standard: Four Models of Democracy and Their Normative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 Vol. 6, No. 3, 2005, p. 331.“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70〕[美]凯撒· R.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在算法被特定目标操控时,过滤异质信息的机制便可以引导人们完全避开重要的公共问题,或者分化公共讨论,从而抑制建设性的辩论。〔71〕参见[美]伊莱·帕里泽:《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方师师、杨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前言。进一步言,舆论本是社会公众感兴趣的内容所形成的信息,但从数字新闻产生过程看,此舆论已非彼舆论,因为算法不完全中立,它偏袒“流量”,“热点”未必是多数消费者的选择。不真实的“热点”容易误导公众,也切断了少数人参与讨论的机会,使需要发声的弱者游离在数字公共领域边缘,其重要证据就是不同的边缘化群体或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人缺乏多样性。〔72〕路透社的研究表明,在德国,“老白人”过度主导报道,传统地方和区域新闻媒体报道越来越局限于少数主题(如地方政治和犯罪);互联网网站和搜索引擎最热门的主题是“本地信息”、天气、住房甚至“要做的事情”。See Reuters Institute, The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1,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1-06/Digital_News_Report_2021_FINAL.pdf, p. 10.其二,信息无序是新闻质量下滑的主要表现之一。近年来,大部分新闻质量的下滑与信息无序相关。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成年人都担心新闻质量问题,四分之一的成年人不知道如何核实网上信息的真实性。〔73〕See UK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The Cairncross Review: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Journalism, 2021, p.7.恶信息(malinformation,以造成伤害为目的散布的虚假信息)、错信息(misinformation,无恶意散布的虚假信息)、假信息(disinformation,因疏忽或过失散布的虚假信息)〔74〕参见左亦鲁:《假新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545页。被统称为信息无序(information disorder)。当坏信息变得像好信息一样普遍、有说服力和持久时,就会产生连锁伤害反应,导致信息无序,信息无序是社会危机的放大器。〔75〕有些研究中称之为不当内容(inappropriate content)、假新闻(fake news),较之于这二者,信息障碍是更为中性、所含信息量更大的术语,正日益被更多的研究人员所使用。See The Aspen Institute,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Disorder Final Report, 2021, p. 3.
现代工业社会的冲突主要源自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两种异质资本的对立。〔76〕See David Swartz,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67.新闻业是一个产生文化的机构,文化资本是这一领域的制度化资源,其最重要的文化产品是高质量的新闻报道,这是一种具有极大社会价值的公共信息,关乎社会政治与民主。〔77〕See Wilding, P. Fray, S. Molitoriszand E. McKew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Platforms on News and Journalistic Content,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Report, 2018, p. 39.文化资本要求新闻业恪守公共属性、职业逻辑,经济资本要求新闻业融入市场逻辑、流量竞争,通过流量的货币化分得更多广告收入。数字平台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迫使新闻媒体向市场力量让步,经济资本的力量削弱了新闻领域的公共属性,正是这些属性赋予了新闻媒体“作为时事的监督者、人民的声音和专家”的文化权威。
(三)新闻公共性修护目标:二元平衡面向
数字新闻革命使众多新行动者得以参与新闻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公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机会,非专业人员在新闻生产领域深层渗透,但在公众广泛参与度提升的背后次第铺陈的却是公众辩论减少、信息搜索干预、新闻流动被引导等恶化公共领域环境的现象。在市场与资本的夹击下,公共领域式微,公共领域被“重新封建化”,自由、平等、理性的交流空间逐渐让位于各种市场流量、资本力量搭建的舞台。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沦为台下看客,但“超级平台”的政治主张、经济诉求却通过“伪公共领域”被合法化。
数字平台搭建了一个特殊的注意力交易市场,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模式,作为这个市场的中央计划者,其在数字新闻市场的主导地位日益增长,数字新闻市场异质资本间的矛盾也越发显著。目前,新闻市场逻辑相对于职业逻辑取得了暂时性胜利,若不能有效扭转这种局面,加大公共新闻的供给,提升新闻质量,经济资本的胜利必将对社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78〕See P. J. Boczkowski, News at Work: Imitation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Abund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p.147-148.“反垄断的目标是完善竞争市场的运作绩效”,〔79〕Frank H. Easterbrook, The Limits of Antitrust, Tex. L. Rev., Vol. 63, No.1, 1984, p. 1.垄断的实质是控制供给,〔80〕参见[美]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周文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数字新闻市场的反垄断任务也理应从改变新闻产品的供给格局入手。
“政治公共领域要确保形成多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公众意见”,〔81〕Jürgen Haberm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 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16, Issue 4, p. 415.公共领域萎缩、理性的公众意见难以形成,导致新闻公共性贬损成为数字新闻市场失灵的集大成者,金声玉振,莫出其中。新闻公共性价值的商业化利用是数字新闻市场快速发展的支柱,它可被反向利用——无限制地掠夺消费者注意力,也可加以正向利用——增加公共新闻、提升新闻质量进而发挥新闻所应具有的全部社会功能。概言之,新闻公共性修复要实现两种平衡:一为公共性新闻与非公共性新闻之间的供给平衡;二为不同质量之间的新闻供给与收益的平衡。
(四)新闻公共性修护工具:二元规制面向
依据传统的经济理论,铺展于市场失灵、自由竞争之上的反垄断法与基于公共物品提供、政府干预之上的管制理应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制手段,二者不仅泾渭分明,原则上应分受不同性质的政策(竞争政策或产业政策)调整,而且势如冰炭,难以在同一规制关系中并存。这种理论上的分野虽在现实中多有贯彻和体现,但与之相反的冰炭同炉的情况在现实中却从不缺位。在传统新闻市场中,由于新闻产品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市场属性,新闻的提供素来为各国所重点监管,在新闻演进的历史过程中,管制从未缺席。在数字新闻市场,新闻公共性贬损由垄断催化而生,该市场的反垄断问题不仅仅要解决效率问题,还要解决包含新闻公共性贬损以及新闻信息无序在内的更广泛的问题集,这并非反垄断法能独当一面之事。因此,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不应局限于适用反垄断法,作为一种反垄断方法和理念上的转变,其可同时将大型数字企业作为一种“新公用事业”进行管制。〔82〕参见高薇:《平台监管的新公用事业理论》,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84页。
兼顾形式平等与实质公平的管制与反垄断法二元规制模式,虽可为数字新闻市场的反垄断问题提供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和价值上的必要性支撑,但仅有这种理论性支撑尚不足以将这对矛盾的组合驯化成一种法律上的现实,二元规制模式的生成还需有一种能统筹协调不同法益关系、妥善处理管制与反垄断法内在矛盾的规范手段上的支持。质言之,通过反垄断来提升新闻公共性既要受到管制这一兼采积极的义务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组合的调整,又要接受反垄断法这种消极的义务性规范的调整,而构成二者相互衔接界面的是管制与反垄断规制的权力配置。
这种二元规制模式之所以能为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提供规范手段上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制与反垄断法之间的相互补充与协作。这种相互补充与协作可能性在于:(1)从来没有绝对不受管制的市场,所有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管制。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项。一个国家必须对私人确定价格、产出和质量的机制进行选择,从本质上讲,这种对竞争进行的调整也是一种管制,与价格管制并无二异。〔83〕同上注,第789页。(2)反垄断法不是数字平台市场反垄断的完美工具。伴随双边市场的发展,平台企业表现出明显的跨市场经营、网络外部性与截然不同的价格结构后,适用于单边市场中的反垄断规则应用于双边市场时可能完全失效。〔84〕See David S. Evan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Vol. 20, 2003, p. 365.(3)单一反垄断法规制模式不是数字新闻平台市场反垄断的完美工具。置身于数字新闻市场,该市场的竞争失序问题主要聚焦在平台对注意力市场拥有的独立定价、制定规则、控制准入、分配资源等权力所构成的平台生态对传统经济形态的颠覆,而基于价格变量、产出效果、效率考量而生成的反垄断法律规则难以对其反竞争行为进行有效监管,更难以填补数字新闻市场公共信息的缺口,也无法阻止平台竞争扭曲进而导致垄断。〔85〕参见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149页。
上述既分又统的结构关系与二者在规范功能上的互补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必然关系的恒常连接(constant conjunction)。〔86〕See A. Stroll and R. H. Popkin, Philosophy, Oxford, 1993, p. 268.这种恒常连接从新闻公共性修复的角度上看,既表现为法律可根据不同规制关系的特点、技术变化、经济发展、社会变化来动态地厘清管制与反垄断权力的边界,也可表现为数字新闻平台的管制偏离政治游说、俘获,走上法治化轨道。若无此合法性证明,因为管制进行利益再分配而导致的不公平和市场控制力量难免会给数字新闻市场的反垄断带来“政府失灵、一种成本高昂的替代”的批判与“政治过程的结果、满足产业压力集团的自我利益”〔87〕[美] 丹尼尔· F.史普博:《规制与市场》,余晖、何帆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的正当性质疑。管制对反垄断法的补充作用在于管制可为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拟追求目标的实现提供两种支持。一是反垄断法是救济性和随机性的,通过法律规制来救济行为的结果,侧重校正事后的市场秩序;但管制是控制性和政策性的,通过法律规范来控制行为的过程,侧重维护事前和事中的市场秩序。〔88〕参见张占江:《自然垄断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以电力行业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64页。二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秩序和对数字平台构建的严密规范体系,体现了微观秩序支持宏观秩序、合乎法律性对更为宽泛的合法性的支持。二是管制对反垄断法的支持还表现为,若无管制这一深入社会各种价值平衡的权力触手媒介,单纯依赖反垄断法本身无法弘扬其作为宏大价值目标和强大经济调整功能的“超级法”之应有功能。〔89〕参见孔祥俊:《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宏观定位——基于政治、政策和法律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 2021年第2期,第91页。而有了管制义务和赋权的功能加持,反垄断法不但能以更高的效率实现对垄断行为的禁止和对竞争秩序的维护,而且可通过将其自生的威慑力渗入管制之中,并借助管制规范的再规范来实现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的多元化目标。
正是通过管制与反垄断这种既重形式公平又重实质正义、既控制竞争结果又控制竞争过程的规范组合,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这些相互悖反的价值于此形成一种合而两利、分则两伤的辩证关系,并为当前所处的这样一个既谋技术发展、商业创新,又求文化长青、有效治理的数字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规制构造:以新闻公共性补救为目标
对于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这样一种有着多元规制目标、二元规制任务与二元规制工具的法律关系综合体来说,意欲对其进行有效调整,既需要法律上为其有效运行提供必要的外部制度保障,更需要从其内部着手解决其所内含的对市场经济活动直接介入与间接引导之间的分权制衡问题、效率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平衡问题,以避免管制对数字新闻市场主体自治的过度干预和平台权力、技术垄断对文化或权利的过度侵蚀。
(一)管制层面:以管制保障公共新闻供给
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选择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90〕参见[美]丹尼尔· 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将数字新闻平台作为新公用事业进行管制需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管制对象是谁?二是如何管制?
1.管制对象:构成“新公用事业”的数字新闻平台
“公用事业是指经营一系列对社会而言非常重要以至于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力量管理的关键网络设施的企业。”〔91〕William Boyd, Public Utility and the Low-Carbon Future, UCLA L. Rev., Vol. 61, 2014, p. 1620.新公用事业则是一种部分借鉴传统公用事业管制理念、方法,但不主张展开全面管制的折衷方案。〔92〕See K. Sabeel Rahman, The New Utilities: Private Power,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Public Utility Concept,Cardozo Law Review, Vol. 39, Issue 5, 2018, p. 1654.数字新闻平台规模经济、范围效应、网络效应带来的“赢家通吃”属性符合传统上适用于公用事业监管的理由,因为新闻平台垄断下的新闻行业与许多自然垄断行业一样,存在很大的进入壁垒和竞争障碍,并且缺乏重建的经济合理性。新闻生产者、消费者对数字新闻平台的高度依赖使其愈发成为数字生活的必需品,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也引发了限制自由参与、公平竞争的担忧,不论是基于对数字新闻平台基础设施属性的考量,还是基于促进公共领域构建、新闻公共性价值的考虑,将特定数字新闻平台视为新公用事业并施加一定的公共义务都是必要的。
近年来,为了解决广泛存在的不当内容的困扰,各主要司法辖区正在逐步建立对具有数字基础设施属性平台的特殊监管规则。该领域的先行者为欧盟,其《数字服务法案》对“在促进公共辩论和经济交易方面发挥了核心和系统性作用”的超大型在线平台课以实质性义务,以提升数字市场公平性。欧盟管制对象的认定标准是经营核心业务、对市场有重大的影响、为其他商业主体提供必要渠道的平台,平台近三年营业额达到65亿欧元以上、市值在650亿欧元以上、月活跃消费者达到4500万人(相当于欧盟人口的10%)或年活跃的商业消费者达到1万人以上。〔93〕Se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0/31/EC, COM/2020/825 final.其他国家相关立法框架基本以欧盟为模板,分别提出了“涵盖平台(covered platform)”、〔94〕S.2992 -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hoice Online Act, October 18, 2021.“战略市场地位”(strategic market status)等新的规则。〔95〕See CMA, CMA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s Consultation ‘A New Pro-Competition Regime for Digital Markets’, 2021.需注意的是,上述规则针对经营各种业务的数字平台,对中国而言,是否需要对所有业务平台普遍采取这种管制尚需进一步讨论。但是,对于具有公共性的数字新闻平台,由于其作为新闻发布、阅读渠道和公众进行辩论、表达门户的重要性,有必要采取新公用事业管制使其承当起公共领域的责任。在作为新公用事业的数字新闻平台的认定标准方面,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变化过快,规定一个过于具体的标准可能易于过时或者漏掉某些重要的平台,所以可将此项认定的权力交给监管机构,由监管机构综合考虑平台规模、对公众的影响力、基础设施属性、其他主体对平台依赖程度等因素进行认定。
2.管制内容:保障公众参与的义务设定
如果说平台自治、行使私权力是一种面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那么对平台私权力的限制和问责更应该成为平台反垄断的变革方向,通过增加非歧视性义务、保障公众参与的机会,打造“无遮蔽”的公共领域。最常见的公用事业管制政策包括价格和服务无歧视义务、设置费率限制、课以资本化和投资要求。在这三项传统政策中,费率设定和投资要求难以实施且很难对症解决数字新闻市场显著的公共新闻供给不足的矛盾,所以非歧视最有现实意义,〔96〕See Lina Khan,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Yale Law Journal, Vol. 126, No. 3, 2017, p. 798-799.因此,数字新闻平台管制可以从设置非歧视义务展开。
(1)非歧视开放义务。其一,公平接入义务。数字新闻平台已成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是新闻媒体接触公众的门户,也是公众阅读新闻内容的关键渠道,其开放性和可参与性对新闻公共性价值实现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目前已经采取措施着力促进平台开放。例如,2021年9月,工信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要求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百度、华为等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分步骤、分阶段推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97〕参见栗翘楚:《工信部深入推进互联互通分享链接或将告别复制乱码》,载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914/c1004-32227032.html,2022年3月18日访问。但“互联互通”的依据大多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紧急应对措施,具有显著的短期性、政策性,平台企业对此也多持“表面整改,实则观望”的态度,反垄断应有的合规引领功能尚未能发挥。对此,有必要在数字新闻领域要求符合新公用事业标准的新闻平台履行开放义务,通过推动多样化、无歧视的公共领域参与保障作为公众阅读和表达门户的数字新闻平台实现其公共职能。平台开放的对象包括竞争性新闻平台、新闻生产者和新闻消费者。平台开放义务体现为不得以合约或技术方式施加过度的限制,阻止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进入、转向或者多归属。当然,这种开放并非无差别、无原则的开放,平台可以为维护平台生态而设定公平、非歧视的限制规则,但该限制规则应当为促进平台系统整体价值所必需,并且不能以严重限制竞争和公众参与为代价。
其二,促进数字生产资源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数据不单是资源,更成为企业重要的资产,掌握丰富的高价值数据资源日益成为抢占未来发展主动权。”〔98〕中国信通院发布:《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4.0)》(2019),第III-1页。数据是新闻业竞争的核心要素,数据开放对于促进数字新闻行业的公平竞争至关重要。“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数据开发利用……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9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数据安全法》第7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为进一步缓解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与供应替代性威胁,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和共享利用,打破数据壁垒,要求作为新公用事业的新闻平台具有对合格新闻生产者开放数据是构建平台和谐生态的重要内容。首先,开放的前提是经过消费者授权同意,不违反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其次,开放的生产资源内容应限定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服务与数据,如满足普惠性、稀缺性的平台公共服务及脱敏的原始数据等。对于公开数据,数字新闻平台没有正当理由不得禁止爬取。最后,数据共享应该通过专有API访问的形式及时、持续地提供,数字新闻平台对所共享的数据负有同等质量保障义务。
(2)非歧视收益分配义务。随着网民数量的爆炸式增加,新闻受众变革为新闻生产者、传播者,新闻的消费却越来越集中在以平台为核心的新媒体手中。〔100〕参见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6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0页。掌握分配大权的平台在分配“注意力”收益时,紧握决定权、话语权,平台规则即“群体指定的分配规范”。根据英国国会的调查,“高度依赖平台流量的新闻出版商经常受到不公平对待,这限制了出版商将其内容货币化的能力,并威胁到新闻媒体的可持续性。”〔101〕UK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The Cairncross Review: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Journalism, 2021, p. 78.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的调查报告也发现,传统新闻制作人和出版商因数字经济冲击而面临大范围失业、倒闭,公共新闻产品的持续供给陷入严重危机。〔102〕See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Final Report, 2019, p. 321.
新闻媒体的直接盈利能力与新闻业独立发展的要求仍相去甚远,注意力收益的不合理分配已成为制约新闻媒体公共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发挥的主要瓶颈。〔103〕参见潘爱玲:《我国文化产业融资难问题与对策建议》,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汇编(2013年)》,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2页。为了缓解新闻媒体的生存困境和促进新闻公共性,澳大利亚出台了《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性议价法案》,授权政府介入澳大利亚新闻媒体与脸书、谷歌等互联网科技巨头之间的议价能力失衡问题,以确保澳大利亚新闻媒体能够在平台驾驭的分配体系之下,就其原创内容获得合理报酬。〔104〕See 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Treasury Laws Amendment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 Bill 2021.目前,世界各地的司法管辖区都在考虑如何进行注意力变现(monetize)受益的分配变革。〔105〕例如,加拿大正在着力推进数字新闻付费政策,See D. Ljunggren, Canada Vows to Be Next Country to go after Facebook to Pay for New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ustralia-media-facebookcanada-idUSKBN2AI349, last visit on June 30, 2022. 美 国提出了澳大利亚式的媒体付费谈判法案,See K. Cox, US Lawmakers Propose Australia-Style Bill for Media, Tech Negotiations, https://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21/03/us-lawmakers-propose-australia-style-bill-for-media-tech-negotiations/, last visit on June 30, 2022. 法国竞争管理局(Autorite de la Concurrence)裁决,谷歌使用法国出版公司和新闻机构的新闻内容必须要支付相应的费用,See Rosemain,M., Exclusive: Google’s $76 Million Deal with French Publishers Leaves Many Outlets Infuriated,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ooglefrance-copyright-exclusive-idUSKBN2AC27N, last visit on June 30, 2022.唯有站在促进文化繁荣与民族文化自信的高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短期问题——利益分配,倘若听任平台设定分配规则,扮演“群体指定的分配规范”角色,那么注意力市场(包括数字新闻市场)的微恙必成沉疴宿疾。〔106〕参见马健:《论文化规制》,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22页。
重新分配注意力收益利益是数字新闻产业健康、扶持发展的必然选择,该制度也值得中国借鉴。其制度逻辑为:要求数字新闻平台与新闻生产者就新闻付费展开集体谈判,提升注意力价值分配的公平性,保障传统新闻机构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促进新闻公共性和新闻业的可持续性。集体谈判的展开遵循六大规则,即市场议价、强制仲裁、技术变化通知的一般要求、非差别化要求、市场外包许可、标准报价。〔107〕See The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Treasury Laws Amendment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Act 2021, Art. 52.
(3)非歧视技术对待义务。算法技术虽释放了信息传播的潜能,但也深刻影响了传播内容的分类、优先、推荐和判定。〔108〕See David Beer, 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 Participatory Web Cultur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 New Media and Society, Vol. 11, Issue 6, 2009, p. 995.逐利至上的数字新闻平台掌控下的算法排序产生了诸多问题,包括偏向自产内容、贬低公共性新闻导致供给结构异化,或者观点、内容上具有过度偏向性,没有为多样化来源、多元化立场保留必要空间,这导致新闻从业者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不少从业者指出,数字新闻平台经常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修改新闻推送算法,对其他经营者新闻内容的可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109〕See Terry Flew, Platforms on Trial, Intermedia, Vol. 46, Issue 2, 2018, p. 24-25.对此,我国已作出了初步尝试。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4条规定:“提供算法推荐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遵循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为了进一步强化新闻平台非歧视对待义务,应对作为新公用事业的数字新闻平台算法作出更为具体的公平排序义务。首先,作为新公用事业的新闻平台应公平对待新闻生产者,不得利用算法对平台自产内容优先展示和推送,不得通过降级来排挤特定经营者。其次,平台需要公开算法排序和推送的标准,该标准应当合理、公平、非歧视,并且符合公共利益而非完全商业化,要为不同立场、不同来源的公共性新闻保留必要的空间,以平衡公共性新闻与非公共性新闻。最后,在可能影响特定经营者及其新闻内容在平台上的排序和可见性的平台算法变更之前,提前告知新闻生产者,给予其必要的调整时间。为了促进平台算法非歧视性,可考虑引入行业组织、第三方机构等作为外部监督者对算法进行审计和评估。
(二)反垄断法层面的修正:以竞争促进新闻质量提升
公共性损害填补思维的引入,为数字新闻领域反垄断规制提供二元规制模式的同时,也为基于公共性修复目标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完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即一种直面数字新闻市场提供零价格服务的现实、升级传统以价格为主的反垄断分析工具、聚焦新闻质量评估来检视竞争效果的辩证思维。基于此种辩证思维方法,反垄断法在评价数字新闻市场竞争行为的竞争效果时,既应强调“赢家通吃”与数字新闻市场失灵、消费者隐私保护与个性化推荐精准性、新闻多样性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之间的区分和对立,又要重视注意力高质量消费与消费者隐私保护增强、新闻多样性提升乃至数字新闻市场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统一,并对各要素间关系的动态变化加以必要的考虑,进而实现数字新闻平台公共性与私利性的相对统一。遵循上述规制思维,反垄断法层面的修正之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转变传统价格竞争损害评估的思路,将难以量化评估的注意力、隐私、质量(包含多样性)损害融入现有的法律框架。为此,要着力回应数字新闻市场损害的特殊性,开发新的测量方法,消解反垄断法的适用障碍。
1. 注意力损害评估。以注意力损失为基础来构造垄断行为的反竞争效果分析框架时,既应看到注意力损害与传统损害之间的分与别,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统与合。因为从本体来看,注意力不是法律概念,学术上也缺乏统一认识,实践中对注意力多寡与损害更加难以测量。尽管二者外观相异,实则内在有着惊人的一致,即损害皆由精神损害与经济损害构成。直接的精神损害源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其总量取决于我们的认知能力,在使用过多时也会过载或耗尽。〔110〕See Matthew B. Crawford, The World Beyond Your Head: On Becoming an Individual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 p. 23.经济损失则因为“信息的丰富将导致注意力的匮乏”,〔111〕Herbert A. Simon, 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 40.“注意力数量受到认知能力的约束,一旦信息的可获得供给超过这个自然上限,西蒙斯设想的信息供给和注意力供给之间的反比关系将成立。”〔112〕John M. Newman, Antitrust in Attention Markets: Objections and Responses, Santa Clara L. Rev., Vol. 59, 2019, p. 743.“人们有固定的时间分配给各种活动,如果他们花更多的时间从事无报酬的活动,他们赚钱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收入也会减少。”〔113〕Gary S. Becker,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Vol. 75, 1965, p. 501.此即经济损害。对注意力损害测量不能通过传统方法,而是要引入新的经济学工具。一是评估反竞争行为发生前后的广告数量,以考察平台是否因反竞争行为而能够投放更多的广告而不致损失客户。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内容产品,纯粹依靠“购买”赢得关注,其通常被视为产品退化的一种形式,注意力商人(新闻平台)的收入也取决于它能卖出的广告数量。因此,注意力商人通常会以适当比例混合广告和其他内容,在使其收入最大化的同时,不会因过度降低产品质量而减少消费者数量。广告是反映人类时间和注意力的典型交易方式,广告商向注意力商人支付的费用可被视为进入消费者头脑的费用,〔114〕See Tim Wu, Blind Spot: The Attention Economy and the Law, Antitrust Law Journal, Vol. 82, Issue 3, 2017, p. 865.广告的显著上升可视为对消费者注意力损害的替代指标。二是计算垄断行为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消费者剩余减少是评估垄断行为危害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剩余等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而在价格为零的注意力市场,可以通过内容对于消费者的价值与消费该内容的货币成本的差额来计算。〔115〕See David S. Evans, Attention Platforms, the Value of Content, and Public Policy,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54,Issue 4, 2019, p. 787.内容价值无法直接计算,一种较好的方式是根据时间分配经济理论(the economic theory of time allocation),将边际报酬(marginal wage)作为时间价值的替代指标,乘以消费者在内容上消耗的总时间。〔116〕See Gary S. Becker,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Vol. 75, No. 299, 1965, p. 516-517.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大规模实验方法进行计算,即通过发放大量问卷进行调查,分析支付多少金额作为奖励可以使消费者放弃使用某种数字产品,从而估计出该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117〕See E. Brynjolfsson, F. Eggers and A. Gannamaneni, Measuring Welfare with Massive Online Choice Experiments: A Brief Introduction,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108, 2018, p. 473-476.这些方法虽然不够精确,但仍具有参考价值。
2. 隐私损害评估。为顺利通过并购审查,数字平台会对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出不会降低隐私保护标准的承诺,但“市场主导者的隐私承诺谎言”往往不攻自破,因此,隐私作为一种反竞争效果裁量因素终被纳入反垄断案件之中,如欧盟Google/DoubleClick案〔118〕在此案中,当Google提出合并方案时,人们对Google将拥有的数据访问能力,特别是对能够通过用户的浏览活动与个人身份联系起来表示担忧。Google向欧盟委员会承诺,在交易后不会将DoubleClick收集的互联网用户数据与整个Google生态系统收集的数据相结合,不会降低用户隐私。但2016年Google违反承诺,开始将DoubleClick数据与其他Google服务收集的个人信息相结合,有效地将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与其在Google Maps上的位置信息、Gmail信息、搜索历史信息以及其他许多Google产品上的信息相结合,即整合数据,用于个性化广告推荐,这严重损害了互联网的匿名性。See Google/DoubleClick, Case COMP/M.4731,Commission decision of March 11, 2008.、德国Facebook案〔119〕See Bundeskatellamt, Decision under Section 32(1) German Competition Act (GWB), B6-22/16, February 6, 2019.。隐私损害评估的探索方向有三:一是将隐私视为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在微软/领英的合并案中,欧盟委员会认为:“隐私是竞争的一个重要参数,而该合并将限制消费者在隐私方面的选择”;〔120〕Case M.8124 - Microsoft/LinkedIn (n 36), paras. 338-347.二是将隐私作为一种隐性价格,主张将个人数据的披露概念化为消费者为使用免费商品和服务而支付的非货币价格;〔121〕See Daniel L. Rubinfeld and Michal Gal, The Hidden Costs of Free Goods: Implications for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titrust Law Journal, Vol. 80, No. 3, 2016, p. 521-562.三是直接拓展质量外延,以涵盖基于隐私的竞争,〔122〕See Erika M. Douglas, The New Antitrust/Data Privacy Law Interface, Vol. 130, 2021, p. 647-684.这也是欧盟委员会、加拿大竞争管理局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做法。众所周知,在相关市场界定中,假定垄断者测试要借助SSNIP(价格上涨测试)或SSNDQ(质量下降测试)完成,前者面临数字服务“零价格”不能进行涨价测试的困扰,后者面临执法机构不知应将何者记入“质量”的难题。“只要消费者认为隐私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与隐私有关的问题就可以在竞争评估中得到考虑”,〔123〕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Approves Acquisition of LinkedIn by Microsoft, Subject to Conditions IP/16/4284(6 December 2016).将隐私融入质量,那么收集更多的质量可视之为质量下降,这就能为相关市场界定SSNDQ测试方法困境的克服提供理论支持。但是,不同消费者对隐私的敏感性不同,收集更多的数据,隐私不敏感型消费者可能不会认为服务质量下降,而隐私敏感型消费者会持不同看法,甚至会因此放弃使用某些功能。要客观地评价信息成本过高带来的损害并非易事,目前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隐私损害评估工具,“隐私损害无法测量仍是将隐私纳入反垄断法框架的障碍之一”。〔124〕Nils-Peter Schepp and A. Wambach, On Big Data and Its Relevance for Market Power Assess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 Vol. 7, Issue 2, 2016, p.120-124.
虽然隐私损害无法直接衡量,但可以寻找替代指标进行侧面评估。一是定性分析方法。执法机构可以通过比较行为发生前后的隐私政策、消费者协议、数据收集情况、实际权限等进行质量评估,进而计算“隐私价格”。评估隐私质量基本框架的搭建可以借鉴OECD的做法,关注如下六项指标:第一,收集最小化,即收集哪些数据、数据范围是否实现了最小化;第二,使用最小化,即数据用于什么领域、存储多长时间、与谁共享;第三,透明度,即在数据收集和使用方面向消费者提供了哪些信息、信息披露是否具有可读性和易理解性;第四,消费者控制,即消费者能否方便地访问、修改、删除和移植自己的数据,消费者有哪些选择;第五,安全性和隐私设计,即有哪些安全措施来保护数据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意外丢失、破坏,以及平台是否使用了隐私增强技术(PETs);第六,默认设置是否有利于保护隐私。〔125〕See OECD, Consumer Data Rights and Competition - Background note, DAF/COMP(2020)1, para. 139.二是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主要采用联合分析法(conjoint analyses),这种方法通过评估产品的某些特征对消费者的选择和支付意愿的影响来对非价格因素进行测量。〔126〕See Paul E. Green and V. Srinivasan, Conjoint Analysis in Marketing: New Developments with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54, No. 4, 1990, p. 6.联合分析法依赖于经济实验,这些实验通过“控制变量”使消费者面临“假设但现实的选择问题”,〔127〕Stephen Hurley, The Use of Surveys in Merger and Competi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Vol. 7,No. 1, 2011, p. 49.从而模拟消费者在实际购买中进行决策时面临的情况。〔128〕See Daniel McFadden, The Choice Theory Approach to Market Research, Marketing Science, Vol. 5, No. 4, 1986, p. 282.具体操作分成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组织一次消费者调查,以识别相关的价格和非价格属性,并确定不同属性对产品选择的影响程度。在Facebook/WhatsApp案例中,委员会使用这种方法确定了消费者通信应用的产品属性和属性级别。〔129〕See Gergely Biczók and PernHui Chia, Interdependent Privacy: Let Me Share Your Data,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Cryptography and Data Security, Springer, 2013, p. 342.第二步,竞争主管机构可以通过调整产品包含的属性和级别,设计不同的应用程序。第三步,要求消费者对这些应用程序进行选择,并给出相应的分数。根据实验中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排名情况,执法机构可以通过多变量回归分析(multi-variable regressions)估计消费者在产品选择过程中的每个属性及其级别的效用和相对重要性。竞争主管机构可以衡量消费者愿意为某种程度的产品非价格属性(如隐私)支付多少费用,进而对其进行量化评估。
3.新闻质量的评估。新闻质量是指新闻媒体及其新闻内容(对象)在培育政治公共领域方面的优劣,确保形成具有多样性的、理性舆论的引领作用。〔130〕See Philipp Bachmann, Mark Eiseneggerand Diana Ingenhoあ, Defining and Measuring News Media Quality: Comparing the Content Perspective and the Audience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27, Issue 1, p. 13.“尽管人们就新闻质量对社会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但在如何定义、操作和衡量新闻质量方面仍存在很多困惑。评估新闻质量的抽象标准是新闻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公众讨论进而加强了民主舆论形成和决策的过程。”一般来说,人们根据相关性、情境化、专业性和多样性指标进行新闻质量评估。〔131〕同上注,第13页。
(1)多样性指标的评估。新闻多样性很难被量化,但新闻内容的窄化、社会成员共有知识的窄化、社会成员认同感的降低一定不是新闻与文化多样性所追寻的指标。近年来,新闻多样性的评估问题逐渐为主要司法辖区的监管机构与学界所广泛关注,如欧盟发布了《媒体多元化和媒体自由》〔132〕报告指出:“媒体多元化包括合并控制规则、广播内容许可制度、媒体所有权的透明度、编辑自由、公共服务广播机构的独立性、记者的职业状况、媒体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妇女和少数群体获得媒体内容的机会、意见的多样性等。”See European Parliament, Committee on Civil Liberties Justice and Home Aあairs 2018, Report on Media Pluralism and Media Freedom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17/2209(INI), 2018.,ACCC发布了《数字平台对新闻和新闻内容的影响》。学者们多认为,“度量指标可以包括消费者与对立政治观点的接触、跨意识形态的引用或与具有对立观点的人之间的联系”,〔133〕N. Helberger, K. Karppinenand, L. D’Acunto, Exposure Diversity as a Design Principle for Recommender System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21, No. 2, 2018, p. 200.这为数字新闻领域的多样性评估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评估标准:一是主体多样性,保障相关市场具有足够的独立媒体,以确保能够生产具有观点、视角的新闻;〔134〕同上注,第200页。二是暴露多样性,媒体平台必须保障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新闻能够获得公平的呈现机会;〔135〕同上注,第196页。三是选择多样性,保护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包括选择阅读相同观点和不同观点、接触主流内容和“长尾”内容的机会。〔136〕See Robin Foster, News Plurality in a Digital Worl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2, p.49.
(2)其他内容指标的评估。新闻质量受到多因素的影响,ACCC认为,除了多样性指标,新闻质量的指标还可以分为内容评价指标、观众参与度指标和组织因素指标,并为此开发了一套较为实用的测量标准。其一,内容评价指标。新闻内容的科学评价是新闻专业度测评,也是数字平台服务实践满意度测评,更是新闻社会功能实现度测评,是提升新闻公共性的关键指标。世界主要司法辖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如英国CMA、韩国KFTC等普遍采取了一套由ACCC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137〕See Philipp Bachmann, Mark Eisenegger and Diana Ingenhoあ, Defining and Measuring News Media Quality: Comparing the Content Perspective and the Audience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27, Issue 1, p. 22.该指标体系是ACCC在进行大量学术文献整理、市场调研、专家访谈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新闻质量评价标准开发的具有三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之下有六或八个二级指标的实施方案,该套指标的设置全面、科学,取值定义严谨、合理。〔138〕See D. Wilding, P. Fray, S. Molitorisz and E. McKew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Platforms on News and Journalistic Content,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Report, 2018, p. 86-87.我国尚未制定相关质量评估体系,笔者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可对此予以借鉴,通过市场调查,结合新闻业专家、记者、其他从业人员以及消费者的意见,设计一套更符合我国数字新闻市场发展现状的评估标准,在具体案件中对新闻质量是否下降进行科学规范、系统全面、精准少误的评估。其二,观众参与度指标。该指标设计旨在鼓励消费者参与,由表述(是否考虑观众的关注点、观点、经历、贡献、愿望和需求)、参与(是否考虑观众的个人和集体的智慧)、交互性(是否提供相关内容的链接、评论或提出反馈)、社区(是否提供消费者论坛和社区空间、是否促进社区对话和公共辩论)、定制(是否为消费者提供定制体验)五大子指标构成。其三,组织因素指标。该指标设计旨在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性,由独立性、自立性(编辑人员享有不受商业和政治干预的独立性)、社区领导(对意见领袖的影响、告知公众意见和进行辩论的能力)、定价能力和独有消费者的数量(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对新闻市场的渗透)、编辑部资源和新闻活动的测量(相对于业务规模的记者人数、至少有5年经验的足够数量的记者、内容与广告的混合比例、用于原创新闻的空间比例、员工撰写的内容与新闻机构生产内容的比例)四大子指标构成。
五、结语
新闻业兼具市场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但伴随技术的高歌猛进,在平台强大市场力量的控制下,在“讨好式信息分配”的技术逻辑的主导下,“看得越多,越愚昧”,“读得越多,越偏激”,新闻公共性贬损,传统信念贬值,根植于个性化新闻推荐技术的数字平台“很有可能成为人类刻板印象的最大集群”,文化被推入波斯曼所形容的“不给道德领域里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指引”的技术垄断文化境地。〔139〕参见[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2-55页。数字新闻市场正面临市场竞争机制被扭曲、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功能衰减的双重危机。
通过对此双重危机的理论分析与应对策略阐释,我们既看到了精妙的算法、平台的兴起与普及深化了市场竞争并为公众与信息的精确匹配带来诸多便利与实惠,〔140〕参见[英]阿里尔·扎拉奇、[美]莫里斯· E. 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又看到了手握消费者数据、个性化推荐技术与注意力交易市场生杀予夺大权的数字新闻平台在其所搭建的注意力交易市场悄无声息地将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伤害至深。对此,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乃至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如何才能保障新闻生产者生存与发展基本权利之时不忘其社会“瞭望者”之初心?在管制与反垄断法并用之间将如何平衡方能不负数字平台致力创新、追逐竞争之本心?监管者的重心与利器又将于何处安放方能不违其维护正义、塑造文化强国的真心?这些是数字新闻市场反垄断时最需要坚守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