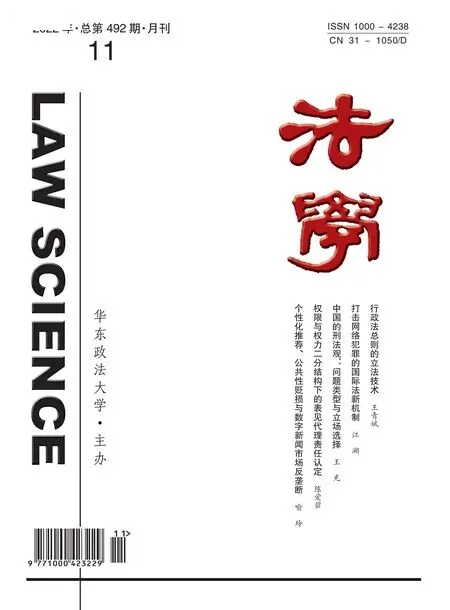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的表见代理责任认定
2022-03-04陈爱碧
●陈爱碧
我国《民法典》第172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此条延续原《民法总则》第172条、原《合同法》第49条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由于该规定表述相当宽泛,导致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规则并不清晰,主要体现为在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效力问题上学界与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72条,代理权界定实为表见代理责任认定之前提。但在当前关于表见代理责任认定的研究中,代理权界定的合理性问题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传统代理权构造融合了代理内外部关系,与表见代理的制度目的相悖。若不解决传统代理权的结构缺陷,表见代理规则将很难实现保障交易安全这一制度目的。本文意在将研究前置一步,探讨当前表见代理责任认定之困与代理权界定的内在关联,反思现行代理权概念的不合理性,提出重新界定代理权之合理方法,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表见代理责任认定难题的新路径。需说明的是,因表见代理仅存在于意定代理中,故本文所称代理权仅指意定代理权,特别注明包括法定代理权的除外。
一、传统代理权构造下表见代理责任认定之困
关于代理权的界定,我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代理权基于本人对代理人的授权产生,代理人享有代理权即可以本人名义为意思表示,并使其法律效果归属于本人。〔1〕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22-623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432页。梁慧星教授虽然认为本人授权行为是一种法律事实,但亦认为代理权来源于本人授权,其法律效力首先体现为本人承担代理行为效果。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40-242页。基于这一代理权构造,表见代理属于无权代理,表见代理责任亦被排除于法律行为责任范围之外。“信赖原则与自我约束原则共同构成了法律行为交往中的基本原则”,〔2〕[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因此表见代理责任往往被归为信赖责任范畴中的权利外观责任。在权利外观责任中,“为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法律状态被视为存在”。〔3〕[德]C. W.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据此,表见代理责任的目的即保护相对人对代理权表象的信赖,使善意相对人可向本人主张有权代理之效果。
问题在于只有合理或者正当的信赖才能被保护,〔4〕参见许德风:《意思与信赖之间的代理授权行为》,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第44页。因此持权利外观责任观点者须对合理信赖予以界定。由于本人意思自治与相对人信赖保护是表见代理中的两大核心价值,故合理信赖的界定问题往往被转换为这两种价值的平衡问题,并进一步体现为是否应当在表见代理责任认定中考虑本人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应当考虑本人因素,并就如何界定本人因素这一问题,形成了本人可归责性要件、信赖要件、代理权通知要件三种主要观点,但三者都未能提供清晰的判断标准及理由。
(一)模糊的本人可归责性要件
关于本人可归责性〔5〕另有学者以“本人与因”指称表见代理中的本人因素。参见谢鸿飞:《代理部分立法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制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72-73页。之内涵,我国学者的阐释深受德国法影响,主要存在诱因说、过错说、风险说三种学说。〔6〕德国法相关学说介绍,参见冉克平:《表见代理本人归责性要件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1期,第73-74页。其中,过错说已逐渐式微,诱因说与风险说则不乏支持者。
依诱因说,表见代理责任的成立须本人对权利表象的成立具有一定原因,或者说权利外观的形成与本人具有一定关联。〔7〕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9页;吴国喆:《权利表象及其私法处置规则——以善意取得和表见代理制度为中心考察》,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5页。诱因说是基于与因主义这一归责原理。如果仅基于与因这一客观事实认定信赖责任成立,排除对伦理因素的考量,则从正义衡平角度考虑可能有失合理性。因此,学者在阐释与因主义时往往融入危险主义或过失主义的成分,如此一来,与因主义已经难以维持其作为独立的信赖保护归责原理的地位。〔8〕参见孙鹏:《民法上的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以归责要件为中心》,载孙鹏:《民法理性与逻辑之展开》,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1页。
风险说主张本人可归责性在于本人风险范围内的因素造成了代理权外观。若仅以谁更有控制风险的能力界定本人风险范围,这意味着将交易安全置于至上的地位,并不符合正义衡平之要求。故关于本人风险范围的界定,有学者主张考察如下因素,即本人是否制造了不必要的风险,本人与相对人相比较谁更容易控制产生代理权表象之风险,由哪一方承担风险更符合公平原则。〔9〕参见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载《法学》2013年第2期,第63-65页。有学者主张重点考虑“风险现实化前谁更可能控制此风险以及在风险现实化后谁更应承担风险”。〔10〕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67页。依据上述主张,风险说实质上吸纳了与因、过失等归责事由。但是,与因、过失、风险这些归责事由能否统合、如何统合等问题并未得到充分论证,因此风险说易因过于空泛而失去规范功能。例如,在行为人盗用代理权外观证明的情形中,在同样持风险说的学者中有的认为此时成立表见代理,〔11〕参见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载《法学》2013年第2期,第63页。有的却认为在一般情形下不能成立表见代理。〔12〕参见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70页。即使是持风险说者,亦认为风险归责原则与具体情形中的结论之间仍存在较为遥远的逻辑距离。〔13〕同上注,第67页。
此外,有学者主张本人可归责性可以包含所有可作为归责基础的事由,归责性程度系各归责原则确定的归责性程度之叠加。〔14〕参见叶金强:《表见代理构成中的本人归责性要件——方法论角度的再思考》,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5期,第39-41页。这一主张并未解决各归责原理存在的上述问题,无法为本人可归责性的界定提供更进一步的规则指引。
(二)过于弹性的信赖要件
基于本人可归责性界定上的困难,一些学者主张借鉴法国法上的表见代理规则,将本人可归责性纳入信赖要件。〔15〕参见刘骏:《法国新债法的代理制度与我国民法总则代理之比较》,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2期,第75页;罗瑶:《法国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研究——兼评我国〈合同法〉第49条》,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4期,第69-70页;冉克平:《表见代理本人归责性要件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1期,第78-79页。1962年,法国最高法院在“加拿大国家银行案”(Banque canadienne nationale C.Directeur général des impôts)中确立了独立于侵权责任的表见代理理论,明确表见代理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保护相对人对代理人代理权的合理信赖。〔16〕See Séverine Saintier, Unauthorised Agency in French Law, in Danny Bush & Laura J. Macgregor (eds.), The Unauthorised Agent: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5-26.因此,法国法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仅有两项,即存在代理权外观以及相对人的合理信赖。〔17〕参见罗瑶:《法国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研究——兼评我国〈合同法〉第49条》,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4期,第60页。
然而,信赖这一要件仍不能解释信赖保护的正当性问题。对此问题的探究可能仍然会回到本人可归责性上。有法国学者认为:“第三人受到保护,那是因为他的积极作为,躲在权利的脆弱的保护伞下消极无为的人就只能受委屈了。”〔18〕[法]雅克·盖斯旦等:《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04页。我国亦有学者认为,若权利外观不可归责于本人,则相对人信赖可被排除出合理的范围。〔19〕参见杨芳:《〈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6期,第168页。此外,法国法同样面临信赖过于弹性而难以界定的问题。即使法国各下级法院对相对人信赖的判断都受制于最高法院,但何谓信赖仍然不清晰,这反过来限缩了表见代理规则的适用。〔20〕See Séverine Saintier, Unauthorised Agency in French Law, in Danny Bush & Laura J. Macgregor (eds.), The Unauthorised Agent: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0.可见,将本人可归责性归入信赖要件对问题的解决无实质性助益。
(三)代理权通知要件的局限性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持代理权通知要件观点者认为,表见代理与法律行为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能将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问题简单还原为权利外观责任的一般原理。在此基础上其提出,我国《民法典》第172条中的“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实际上是指本人对外作出了旨在证明代理权存在的通知,而关于代理权通知的成立与效力问题应类推适用意思表示成立与效力规则。〔21〕参见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78页。
持代理权通知要件观点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德国法影响。《德国民法典》第171、172条规定了构成表见代理的两种情形。其第171条规定:“以特别方法通知第三人或以公告方法,表示授予代理权于他人者,于前一情形,对于特定之第三人,于后一情形,对于任何第三人,应负授权人责任。未以同一表示方式撤回其代理权前,代理权仍有效存续。”第172条规定:“授权人交付授权书于代理人,且代理人向第三人提示该授权书者,与以特别方法通知其授权者有同一效力。于授权书返还授权人或经宣告无效前,代理权仍有效存续。”在这两种情形下,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都与代理权通知相关。德国通说认为,该代理权通知属于准法律行为中的观念通知。〔2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页;[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08页。在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上,亦有诸多德国学者主张引入法律行为规则。〔23〕参见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87页。
但是,我国《民法典》第172条与德国法中的表见代理规则相去甚远,简单移植德国法方案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将我国《民法典》第172条中的“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解释为本人对外作出代理权通知,实质上是一种目的性限缩。目的性限缩的法理在于“非相类似的,应为不同的处理”。〔24〕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判断两项事物是否为“同类事物”不能仅依据逻辑学上的判断,关键是两者在与法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相互一致。〔25〕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持代理权通知要件观点者试图脱离权利外观责任的一般原理解决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问题,回避了法评价问题,导致在将“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解释为本人作出代理权通知的论证中出现了逻辑断层。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代理权通知的存在与效力判断须类推适用法律行为规范,这可能导致其规则缺乏体系性。类推适用的法理是“相类似的,应为相同的处理”,〔26〕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其与目的性限缩一样都有赖于法价值评断。因此,代理权通知是否存在以及效力如何,须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审查,以确定其在多大范围内与意思表示相似、可准用哪些规定。显然,采取这一方式很难构建起具有逻辑一贯性的规则体系。
综上,将表见代理责任视为权利外观责任,意味着本人承担表见代理效果并非基于本人意思,而是基于法律的价值判断。然而,无论是持本人可归责性要件、信赖要件观点者还是持代理权通知要件观点者,都尝试将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与本人因素联系起来。但对于这一联系的正当性依据以及判断标准上述观点未能予以有效阐释,导致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极易沦为个人价值判断之间的角力。而在表见代理责任认定中引入法律行为规则这一趋势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将表见代理责任视为权利外观责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尽管如此,该观点仍然具备逻辑上的有力理由。原因在于,在传统代理权构造下,表见代理只能被视为无权代理,进而被排除于法律行为责任范畴之外。然而,若代理权界定本身就不合理,那么表见代理责任属于权利外观责任这一判断的存在基础亦值得质疑。因此,要从根本上认识并解决表见代理责任认定问题,还需从代理权界定这一源头问题入手。
二、代理权重构之必要性
(一)传统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的缺陷
如前所述,我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代理权基于本人对代理人的授权产生,代理人享有代理权即可以本人名义为意思表示,并使其法律效果归属于本人。这意味着代理权兼具双重功能。一方面,代理权的有无决定代理人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代理权的有无又决定本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前者涉及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风险分配,属于代理内部关系范畴。后者涉及本人与相对人之间的风险分配,属于代理外部关系范畴。可见在传统代理权构造中,代理内外部关系交织在一起。
由于代理权具有上述双重功能,确定代理权的存续及范围对代理人和相对人而言都至关重要。代理人须知悉自己的行为是否在代理权范围内,相对人须知悉自己的交易对象是否为本人。两者知悉的内容可能不一致,但基于意思表示解释的一般原理,代理权的存续及其范围应当以授权意思表示的受领人即代理人的理解为准。如此一来,相对人可能遭受不测损害。可见,传统代理权的双重功能构造与保障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相冲突。
这一冲突导致表见代理规则的构建陷入了艰难处境。表见代理规则的目的是通过阻断内部关系对外部关系的影响保障交易安全。但基于传统代理权的构造,在认定代理人无代理权时,外部关系就已经受到内部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表见代理规则隔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无疑大大增加了法技术上的难度。加之我国《民法典》第172条对表见代理规则的表述相当宽泛,未像《德国民法典》那样以列举方式详细限定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因而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对表见代理规则构建的不利影响就更加凸显。
(二)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的合理性基础及其丧失
传统代理权之所以采取双重功能结构,根本原因在于其规则构建深受自然法学派思想的影响,重逻辑演绎而轻价值目的,在此过程中交易安全价值未被充分顾及。
我国现行法中的代理权构造主要受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的代理权规则影响。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上的代理权规则构建与代理在私法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罗马法并未建立直接代理制度。在罗马法观念中,依他人行为而变动自己的法律关系并非当事人所愿。〔27〕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17世纪,近代自然法理论始祖胡果·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提出:“代理人的权利直接来源于本人,他的行为基于本人的委任。”这一论述成为大陆法系现代代理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28〕参见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代理人权利来源于本人的委任这一论断,使代理制度具备融入私法体系之基础,同时也使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初具雏形。
19世纪中后期德国法学家拉邦德提出区分论,进一步强化了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依据区分论,代理与委任为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代理权仅规定代理人“可为”的范围,“应为”之义务由基础关系规定。区分论阐明了这一认识,即代理权是法律上的能权(das rechtliche Können),在一定条件下得直接对另一法律主体产生法律效果。〔29〕参见[德] 汉斯·多勒:《法学上之发现》,王泽鉴译,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同时,拉邦德认为代理权来源于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授权契约,但后世德国学者将代理权授予行为认定为单方行为。〔30〕参见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66页。无论代理权授予行为是契约行为还是单方行为,都属于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见,区分论建立在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基础之上。尽管当今通说认为区分论的功能是保障交易安全,但这并非拉邦德提出区分论的初衷。对拉邦德来说,“法律科学的唯一任务是‘纯粹思考’,即从法律概念中通过合乎逻辑的推演得出结论而无须考虑其社会功能与价值的一种方法”。〔31〕See W. Müller-Freienfels, Legal Relations in the Law of Agency: Power of Agency and Commercial Certaint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13, Issue 2, 1964, p. 201.在此背景下,区分论采取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也就不足为奇。
区分论确立了德国法上的现代代理制度。有学者认为,该理论终结了19世纪前半叶德国关于代理一般性承认的学说争议,使德国立法者能无后顾之忧地在民法总则中确立代理之体系定位以及代理的一般原则。〔32〕参见陈自强:《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相应地,《德国民法典》在代理权规则设计上亦采纳了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德国民法典》第164条首句便规定:“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本人名义所为之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其第167条第1款则规定:“代理权之授予,应向代理人或向对之为代理行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为之。”
我国原《民法通则》采纳了德国法的区分论,〔33〕参见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72页。也就当然地继受了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原《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采取这种表述方式是为了体现本人与代理人的平等地位,而非对代理权作为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依据的否定。〔34〕参见齐珊、斯鸣:《〈民法通则〉中的代理制度》,载《法学杂志》1988年第6期,第11页。同时,原《民法通则》第64条规定本人授权为代理权来源。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亦为当时学界主流观点所采纳,〔35〕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81页;江平主编:《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159页。并为原《民法总则》以及《民法典》所延续。原《民法总则》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此与《德国民法典》第164条规定极其相似。同时,原《民法总则》第163条规定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源于本人委托。上述规定皆为《民法典》所承继。
基于上述梳理,可见传统代理权的塑造是基于代理如何融入私法体系这一问题意识,运用概念法学研究方法演绎而成。如今,上述问题意识及法学方法都不再适用。我国实证法已经确立了代理制度在私法体系中的地位,代理属于法律行为范畴已成为共识。在法学方法上,概念法学已失去支配性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更强调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之法学方法。在此背景下,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的合理性基础逐渐丧失,而其对交易安全的威胁更值得关注。
(三)代理权双重功能问题的解决路径:代理权重构
解决代理权双重功能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依据代理人对本人授权意思表示的理解决定相对人与本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变动。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彻底的解决路径是重构代理权,分离代理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和本人法律关系的变动依据。保守的解决路径则是维持传统代理权结构,但将外部关系中代理权的存续及范围交由外部关系中的事由决定。这一外部关系中的事由要么是本人的外部授权,要么是法律规定。与之对应的两种解决方案即外部授权与代理权法定。然而,保守的解决路径虽然在制度成本方面具有优势,却不能真正解决代理权双重功能问题。
1.外部授权方案的逻辑困境
依据外部授权这一解决方案,外部关系中代理权的存续与范围由本人的外部授权决定。《德国民法典》便采取这一思路,第167、170条规定了外部授权。除此之外,德国学者弗卢梅认为,本人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71、172条发出意定代理权证书通知,系代理权授权表示。〔36〕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84页。迪特尔·施瓦布将此进一步阐释为两次独立授予代理权,即内部授予代理权与对该内部授予代理权的向外通告,两者并列存在。但外部的代理权授予除了设定代理权外,还以有利于相对人的方式创设了一个特别的信赖构成要件,这一构成要件不会仅因代理人和本人之间的关系变故而被轻易勾销。〔37〕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39-540页。
我国实证法并未规定代理权的外部授予,但有部分学者以外部授权理论解释表见代理规则,以期达到与代理权外部授予相同的效果。如有学者主张对原《民法总则》第172条采取限缩解释,认为表见代理仅包括授权型表见代理、权限逾越型表见代理、权限延续型表见代理三种类型,而这三种类型都可以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被解释为本人的授权行为。〔38〕参见迟颖:《〈民法总则〉表见代理的类型化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9页。另有学者主张,原《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的“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终止后”三种情形,即代理权“外有内无”“外大内小”“外存内亡”三种情形,都属于有权代理。〔39〕参见娄爱华:《私刻公章与被代理人责任》,载《法学家》2020年第3期,第112-113页。
但是,在传统代理权构造下将表见代理解释为外部授权会面临两大逻辑难题。其一,若代理权已被内部授予,则不可能出现同一代理权的再次授予。正如学者指出的:“本人既已为内部授权,代理人即获得授权,逻辑上,另外一个授权行为实属多余。”〔40〕陈自强:《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正因为如此,德国通说认为,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71、172条发出意定代理权证书通知属于准法律行为。其二,在传统代理权构造下,代理权授予系以代理人为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而外部授权中代理权的存续与范围却取决于相对人的理解,这显然与意思表示原理冲突。对于《德国民法典》中的外部授权规则,亦有德国学者指出其与意思表示理论相悖,并认为这只是在利益衡量基础上基于便利性考虑作出的实用性规定。〔41〕See W. Müller-Freienfels, Law of Agenc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6, Issue 2-3, 1957, p. 175.鉴于上述逻辑难题,外部授权理论并不能被用以解释中国法上的表见代理规则。
2.代理权法定方案之不足
依据代理权法定这一解决方案,外部关系中代理权的存续与范围由法律规定。代理权法定与区分论相结合确实能够实现代理内外部关系的完全分离。英国学者施米托夫曾指出,在区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陆法系代理法的做法是,尽最大可能地、准确地对各种中间人的权限范围作出规定,其中以《德国商法典》的规定最为详尽。〔42〕参见[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事实上,拉邦德提出区分论也是受到德国商法中经理权制度的启发,该经理权便是法定的且不受当事人限制的代理权。〔43〕See W. Müller-Freienfels, Legal Relations in the Law of Agency: Power of Agency and Commercial Certain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13, Issue 2, 1964, p. 197.
早在我国原《民法通则》时期,已有学者提出职务代理权来自于特定职务的观点,〔44〕参见江平主编:《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更有学者明确提出商事代理权的权源包括法律规定、章程规定等。〔45〕参见肖海军:《商事代理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1期,第70-71页。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亦有不少学者主张代理权法定的观点。如有学者提出意定代理中的代理权基于本人意思发生,该本人意思既可以体现为本人授权行为,也可能体现为本人依据其与代理人之间的雇佣、委托等合同关系对代理人身份的确认,在后一种情况下代理权的存在和范围应当依据法律规定、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基础关系等确定。〔46〕参见尹飞:《体系化视角下的意定代理权来源》,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61页。即使在原《民法总则》颁布后,仍有观点主张商事代理的代理范围不完全取决于本人意思,而为法律规定。〔47〕参见郑泰安、钟凯:《民法总则与商事立法:共识、问题及选项——以商事代理为例》,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2期,第80页。
但是,代理权法定无法成为代理权双重功能问题的一般性解决方案。首先,代理权法定方案规制成本过高。实践中的代理权类型繁多,法律显然无法对所有类型的代理权范围逐一作出规定。事实上,主张代理权法定的学者大多数也仅以商事代理权尤其是商事代理权中的经理权为讨论对象。其次,代理权法定方案难以提供逻辑一贯的规则体系。代理权法定意味着代理权不再来源于对意思自治的贯彻,而是来源于法律对代理中特定关系和行为过程的价值评判。如果未提出应予以考量的价值以及价值衡量标准,价值评判就难以展开。而且,这一价值评判须依具体情境而定。因此,像持代理权通知要件观点者一样,代理权法定方案亦难以构建起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规则体系。
由上可见,在维持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这一前提下,将代理权的存续及范围交由外部关系决定,并不能有效解决代理内外部关系混杂的问题。由此,采取重塑代理权这一解决路径实现代理权双重功能的彻底分离就甚有必要。
三、代理权重构方案: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
(一)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的基本构造
为解决代理权双重功能结构问题,基于分离代理权双重功能这一思路,可将代理权改造为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这一改造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将代理权分离为代理权限与代理权力。其中,代理权限系代理人以本人名义为代理行为的资格,代理权力系代理人可以改变本人法律地位的能力。因此,代理权限是代理人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决定了代理人是否须对其改变本人法律地位之行为向本人承担责任。代理权力系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依据,决定了本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发生变动。第二步是以本人对代理人的授权作为代理权限来源。代理权限的存续及范围界定系以代理人为受领人对本人授权意思表示的解释。如经解释认为,本人同意代理人以其名义为代理行为,则代理人享有代理权限。第三步是以代理行为中本人的效果意思(以下简称“本人效果意思”)作为代理权力来源。代理权力的存续及范围界定系以相对人为受领人对本人效果意思的解释。如经解释认为,本人同意承担代理行为效果,则代理人享有代理权力。
运用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可以更清晰地辨析代理权限与代理权力的区别。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将权利家族分为“权利”“义务”“无权利”“特权”“权力”“责任”“无资格”“豁免”八个概念。〔48〕参见[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8页。依据该权利理论,代理权力是一种权力,与其相关的是本人的责任。代理人享有该权力意味着代理人意志所能支配之事实改变了法律关系。代理权限是一种特权,与其相关的是本人的无权利。代理人享有该特权意味着其有权以本人名义为法律行为,且无须为此承担责任。
在两者关系上,代理人享有代理权限则必然享有代理权力,反之则不然。无法想象本人同意代理人以其名义为代理行为,却不同意承担代理行为效果。但另一种情形却并不鲜见,即本人未向代理人表示同意其以本人名义为代理行为,却使相对人相信本人同意承担代理行为效果。因此,代理人有代理权力并不意味着其必然有代理权限。如果代理人享有的代理权力与代理权限范围相同,则其行为构成有权代理。如果代理人既无代理权限,也无代理权力,则其行为构成狭义无权代理。如果代理人有代理权力而无相应的代理权限,则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可见,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与传统代理权构造的最大差异在于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依据的不同。在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对代理行为效果归属的解释将回归法律行为理论,这意味着在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上,解释理论与结果都将发生重大改变。那么,这一回归是否合理就涉及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的正当性论证。
(二)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的正当性依据
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的核心在于通过区分代理权限与代理权力分离代理内外部关系,并将本人效果意思作为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依据。
1.学理基础论证:符合代理本质
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依据的理论构建与对代理本质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而以本人效果意思作为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依据更符合代理本质。
关于代理本质,主要存在如下五种学说。第一种学说为本人行为说。该说认为,本人形成法律行为的意思,代理人相当于本人的“机关”,将本人意思表达出来。第二种学说为代表说。该说认为,代理行为中代理人作出了意思表示,本人通过授权行为的效果归属意思得以承受代理行为效果。第三种学说为共同行为说。该说认为,本人通过授权行为实施了一部分意思表示,代理人通过自己行为又实施了一部分意思表示,因此代理是本人授权行为与代理人代理行为的结合。第四种学说为媒介说。该说主张代理人发出的是本人意思表示,代理人只是本人的表示媒介人。与本人行为说不同,媒介说主张意思和表示整体上归属于本人,不问本人自己能否有效形成或表示出由代理人表达出来的意思,由此代理概念可以统合法定代理与意定代理。〔49〕关于以上学说的介绍,参见[德]福·博伊庭:《论〈德国民法典〉中的代理理论》,邵建东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第2期,第89-92页。第五种学说为统一要件说。该说系在共同行为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认为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本人的效果意思(经由授权行为)、代理人的补充和具体化、代理人的表示意识与代理人的表示行为。〔50〕参见李双元、温世扬主编:《比较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通说认为《德国民法典》采纳了代表说。〔51〕参见[德]福·博伊庭:《论〈德国民法典〉中的代理理论》,邵建东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第2期,第89页。代表说亦成为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52〕参见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87-588页;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36页。代表说与本人行为说、共同行为说都形成于19世纪,并建立在意思说的基础上。根据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意思说,作为意思自治的意思只能对表意人本人产生效力。而代表说之所以成为通说,主要是因为本人行为说、共同行为说无法解释法定代理,代表说则不存在这一局限性。〔53〕参见王浩:《论代理的本质——以代理权授予时的意思瑕疵问题为契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第615页。20世纪以来发展出的统一要件说、媒介说都未能撼动代表说的通说地位。针对统一要件说,批评意见认为其不能解释法定代理是一大缺陷。〔54〕参见汪渊智:《论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载《晋阳学刊》2014年第1期,第123页;李双元、温世扬主编:《比较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195页。针对媒介说,批评意见认为,将代理人加入的意思纳入本人意思之列显然牵强。〔55〕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页。
可见,对意思自治内涵以及代理概念统一性问题的理解是影响代理本质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时至今日,对代理本质的探讨不应再受意思说或代理概念统一性问题的束缚。首先,意思自治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对意思自治的理解不再限于行为人依自己的直接意思产生法律效果。如今,意思自治“仅是指各人可免受外部势力的强制而形成自己的法律关系,并不涉及法律关系形成的具体方法”。〔56〕Vgl. Stüsser, Die Anfechtung der Vollmacht nach bürgerlichem Recht und Handsrecht, 1986, § 3, S. 39. 转引自王浩:《论代理的本质——以代理权授予时的意思瑕疵问题为契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第620-621页。这意味着本人作出意思表示并不必须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人行为。其次,代理概念统一性问题亦不应成为构建代理本质理论的掣肘。法定代理与意定代理虽不乏相同之处,但两者的差异更为显著。法定代理的作用在于补充私法自治,保护意思能力不足之人,而意定代理的作用在于扩张私法自治,使本人可假手他人从事交易。〔57〕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415页。因此,意定代理的代理权范围界定、无权代理、表见代理等规则皆不能当然适用于法定代理。为追求代理概念的统一而忽略法定代理与意定代理本质上的不同,实为重体系而轻目的,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在破除意思说与代理概念统一性要求的束缚后,统一要件说显然更符合代理本质。从代理实践角度观察,代理是本人意思与代理人意思结合之产物。一方面,代理人须遵循本人意愿行事。另一方面,代理人须有独立判断的空间,否则代理制度将失去活力。可以认为,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本人组成了一个临时组织体,代理人充当了本人的替身,因而有能力实施足以改变本人法律地位的法律行为。〔58〕参见申海恩:《私法中的权力:形成权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因此,学者虽然批评统一要件说无法解释法定代理,却也认为其揭示了本人和代理人与代理行为的共同联系,系对意定代理的一种合理解释。〔59〕参见李双元、温世扬主编:《比较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但是,不论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形成过程如何,该意思表示中的效果意思须源自本人。如果认为该效果意思可来自于代理人,则意味着代理人可以凭自己意志为本人决定法律效果,这显然与意思自治原则相悖。只有本人表达了效果意思,才能表明其自愿与相对人形成法律关系。该效果意思即使经代理人补充或具体化,仍在本人效果意思范围之内,并不构成对本人意愿的强制。
综上,统一要件说更符合代理本质。基于统一要件说,本人效果意思经代理人补充或具体化后,与代理人的表示意识、表示行为结合,共同构成了代理行为中的本人意思表示。因此,本人承担代理行为效果的依据在于本人的效果意思。
2.比较法考察
以本人效果意思作为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依据在比较法上不乏实例。其中,英美代理法的做法可谓典型。英美代理法区分真实代理权(Actual Authority)与表见代理权(Apparent Authority)。依据《美国代理法(第三次)重述》中的界定,真实代理权基于本人授权和代理人同意而产生,此时代理人具有影响本人法律关系的权利,表见代理权是代理人可以影响本人法律关系的权力。〔60〕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2.01, comment c.不管是否存在真实代理权,只要存在表见代理权,相对人即可主张由本人承担代理行为效果。关于表见代理权的性质,英美法上主要存在两种争议观点,即合同客观理论和禁反言责任。两种观点虽然在表见代理责任效力上有所区别,但在构成要件上都要求具有来自本人的表示。〔61〕See Michael Conant, Objective Theory of Agency: Apparent Authority and the Estoppel of Apparent Ownership, Nebraska Law Review, Vol. 47, Issue 4, 1968, p. 678.
在德国法中,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亦与本人意思密切相关。在有权代理以及外部授权情形中,这一点自不待言。在表见代理中,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亦与本人意思有关。《德国民法典》第171、172条将表见代理与代理权通知联系起来。德国司法实践发展出容忍代理权,即被代理人没有向代理人明确授予代理权,但是他却知道后者以代理人身份出面并在这当中听任其作为代理人担责。〔62〕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页。从相对人角度观察,代理权通知与本人容忍行为都应被理解为本人已表明其明知且同意代理行为效果的发生。如本人不知道无权代理行为,但若尽了足够注意是能够知道并阻止这一事实发生的,将构成德国法中的表象代理权。尽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大多赋予表象代理权以代理效果,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做法提出了异议,原因在于表象代理权不符合《德国民法典》第171、172条对代理权有意识的公示之规定。〔63〕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33页。而且学说上认为表象代理权一般不产生履行请求权,只有部分学者提出在商业领域可存在例外。〔64〕参见[德]C. W.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页。因此,德国法中构成表见代理的主要情形事实上都要求本人向相对人表明其明知且同意代理行为效果的发生。
3.制度实益分析
在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上,与权利外观责任观点相比,以本人效果意思作为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依据这一解决方案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符合“同等事物同等处理”之平等原则。“私法自治的本质,在于通过法律框架内的自主行为实现的个人自决。”〔65〕许德风:《意思与信赖之间的代理授权行为》,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第45页。只要承认代理属于私法自治范畴,就应肯定代理行为效果的产生是基于相对人与本人意思表示的一致。基于统一要件说,此处的本人意思表示由本人与代理人这一临时组织体发出并归属于本人。表见代理与有权代理的区别仅在于,该临时组织体发出的意思表示与本人对代理人的授权意思表示内容是否一致。但本人对代理人的授权意思表示仍停留在临时组织体内部,尚属本人支配范畴,与相对人无关。相对人所信赖的是这一临时组织体所发出的意思表示。在这一点上,表见代理与有权代理并无区别。因此,对这两种情形下代理行为效果是否归属于本人采取同一判断标准符合平等原则。
第二,为表见代理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效力认定提供更清晰的理论依据与判断标准。根据这一解决方案,本人之所以承担代理行为效果,系因其具有追求代理行为效果产生的意思。对该意思的存在及效力的判断,应适用意思表示解释及效力规则。尽管在意思表示解释及效力判断中亦存在信赖与自治的价值取舍问题,但现行法对此已形成相对成熟、完整的评价体系,具有相对明晰的规范框架,可避免表见代理的责任认定沦为论者个人的价值判断。
对此,兹举一例予以说明。假设甲授权乙以6万元的价格求购丙的花瓶,但甲在联系丙时,误说成已经授权乙以9万元的价格求购,乙以甲之名义与丙订立以9万元买卖花瓶之合同,该买卖合同效力如何?在持权利外观责任观点的学者看来,这构成代理权通知错误。针对代理权通知错误是否可类推适用意思表示错误规则,学者之间颇有争议。有学者持肯定观点,〔66〕参见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88页。亦有学者持反对观点,认为不管该代理权通知是否可撤销,都不影响表见代理责任的成立。〔67〕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制度中的积极信赖保护——兼谈我国民法典总则制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第1167页。依反对观点,上述示例中甲不得撤销其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但若甲亲自与丙订立买卖合同,本欲以6万元求购却误说成9万元求购,则甲可以撤销该买卖合同。在这两种情形下相对人的信赖并无区别,其受保护的力度却不同,理由何在?
对此,有学者认为区分的理由在于逻辑层面,因为本人撤销的是授权通知,不是代理人的意思表示,而且其认为外部授权被内部撤回时,若未及时通知相对人则代理行为对本人发生效力,如允许因代理权通知错误而撤销代理行为,将有违平等原则。〔68〕同上注,第1167-1168页。另有学者认为区分的理由更多在于价值层面。与无代理的买卖合同关系相比,在有代理的三方关系中对相对人信赖的保护程度要更高,因为后者要着眼于维护代理制度本身的价值。〔69〕参见许德风:《意思与信赖之间的代理授权行为》,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第39页。意定代理制度的功能在于补充本人意思自治,故为维护代理制度价值,应由本人承担因使用代理人所产生的风险,避免增加相对人的交易成本。若给予相对人较一般交易当事人更强的保护,这意味着本人须承担原本属于相对人领域的风险,已超出维护代理制度价值之所需。
如以本人效果意思作为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依据,上述逻辑障碍将不存在,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亦会受到适度限制。依据意思表示解释与效力规则,在上述示例中,甲在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以9万元求购花瓶,但其可以错误为由撤销该意思表示。如果甲向丙表示授权乙以9万元求购花瓶,随后对乙表示撤回该授权却未告知丙此事,乙仍以甲之代理人身份以9万元向丙求购,则对丙而言,甲具有以9万元求购花瓶之效果意思,该代理行为对甲生效,但甲同样可以错误为由撤销该意思表示。在上述两种情形下,相对人处境相同,所适用的法律规则一致,受法律保护的程度亦相同。由此可见,以本人效果意思作为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依据,能够限制价值判断上的任意性,并获得逻辑一致的规则体系。
除在表见代理责任认定方面具有实益之外,将本人效果意思作为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依据还有助于简化代理制度、整合代理体系。一方面,这一构造切断了代理内部关系对外部关系的影响,无须借助代理权法定、外部授权等制度即可实现对相对人的保护。另一方面,若相对人明知或应知本人无承担代理行为效果之意思,则依据法律行为规则,本人无须承担代理行为效果,此时亦无须借助代理权滥用理论迂回实现对本人的保护。因此,表见代理、代理权法定、外部授权与代理权滥用等制度都可以在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实现整合。
四、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表见代理责任的具体认定
(一)表见代理责任的性质与构成要件
在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表见代理责任属于法律行为责任,其构成要件包括两方面,即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实施代理行为、代理人享有代理权力。我国《民法典》第172条中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可理解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限、超越代理权限或者代理权限终止”,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可理解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限”,此时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力。
1.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实施代理行为
代理权限存续及其范围的确定,系以代理人为相对人对本人授权意思的解释。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40条,本人授权可采取明示或默示方式,或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时以沉默方式作出。其中,默示方式即以可推断之行为授予代理权限。在某人受雇从事某项通常与代理权限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且未特别排除其代理权限时,即存在代理权限的默示授予。例如,本人雇佣店员出售商品,即可推断其授予店员出售商品之代理权限。
由于代理权限完全属于代理内部关系,不具有保障交易安全功能,故在基础关系与代理权限授予行为的关系上是否仍须采纳区分论,须予以重新审视。一方面,代理权限授予行为的独立性仍有必要保留。在实践中基础关系的产生、消灭与代理权限的授予、撤销并不必然同步。有代理权限而无委任之情形固然难以想象,有委任而无代理权限之情形却并不少见。保留代理权限授予行为的独立性,有利于对不同情形作出更精细的分析,仍具有法技术上的价值。另一方面,代理权限授予行为不应具有无因性。代理权限与基础关系虽然在形式上分离,但在事物本质上难以被完全切割。基础关系中本人发出的指示即应为代理权限范围之限制。若基础关系消灭或无效、被撤销或者因其他原因不生效力,本人通常亦不会希望代理权限继续存在。因此,代理权限的存续及范围应受制于基础关系。
2.代理人享有代理权力
代理权力存续及其范围的确定,系以相对人为受领人对本人效果意思的解释。对本人效果意思的考察应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首先,是否承担代理行为效果属于本人自主决定的范畴,故本人效果意思存在与否须依本人行为判断。常见之行为类型包括签发授权委托书、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将代理人置于某种通常伴有代理权限职衔地位的场合或本人直接向相对人表示已授予代理人以代理权限等。在实践中,易引发表见代理纠纷之常见情形,包括本人交付已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交付公章或签发空白委托书等。加盖真实、有效的公章虽不同于意思表示本身,但至少意味着特定意思表示归属于名义人。〔70〕参见陈甦:《公章抗辩的类型与处理》,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40页。签发空白委托书与此相似。“签发人通过签字通常使人们可以看出这是他自己的意思表示,而且,原则上也必须这样对待。”〔71〕[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99页。故在一般情形下,在空白合同书上加盖公章、交付公章或签发空白委托书都可视为本人已表明其具有效果意思。
若本人无任何行为,则不存在本人效果意思。此时,即使行为人自行出具代理权声明或伪造、盗用授权委托书或公章,其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至于本人明知他人以其名义实施代理行为而不予反对,原则上应不构成表见代理。效果意思属于意思表示的组成部分,对效果意思的判定仍然属于意思表示判定范畴。因此,本人明知他人以其名义实施代理行为而保持沉默时,除非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交易习惯中存在特别规定,否则不能将该沉默视为本人同意为意思内容承担责任。除此之外,所谓表象代理亦不属于表见代理,因为本人在不知道代理行为存在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存在效果意思。
其次,判断效果意思是否存在应以相对人为受领人并结合意思表示整体进行解释。自我负责意思不可能与意思内容割裂,不论具体内容的自我负责并非真正的意思自治。正如学者所言,印章在显示特定意思表示归属者的同时,也彰显、影响该特定意思表示的解释。〔72〕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释语境中的印章及其意义》,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4期,第168页。因此,针对效果意思的解释不能与意思内容的解释分离而单独为之。据此,若本人签发空白委托书,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擅自填充并向相对人出示,相对人不知亦不应知道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则应解释为本人同意承担代理行为效果。于本人加盖或交付公章的情形,在解释上略有不同。公章通常有其使用范围,相对人对此不得不察。因此,若代理人在公章通常使用范围内超出代理权限使用公章,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越权外,应视为本人同意承担代理行为效果。若代理人在公章的通常使用范围之外超越代理权限使用公章,则不能对其行为作出相同解释。例如,项目资料章仅用于开工报告、设计图纸会审记录等有关工程项目的资料上,不能认为本人交付项目资料章即表明其同意承担借款合同的法律效果。〔7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
在代理权力与基础关系的关系上,因代理权力取决于相对人对本人效果意思之解释,与基础关系并无关联,故代理权力的存续与范围不受基础关系影响。
(二)表见代理责任的效力
1.对本人之效力
关于表见代理责任对本人的效力问题,当前学界争议主要集中于本人可否主张表见代理效果这一问题上。有学者持肯定说,认为本人可通过证明表见代理成立而使代理行为有效。〔74〕参见张家勇:《论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的双层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第141页。多数学者持否定说,但认为本人可通过追认达到与表见代理相同的效果。〔75〕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30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
对此,在比较法和区域统一示范法上亦有两种不同规定。例如,在《美国代理法(第三次)重述》及《欧洲合同法原则》中,本人与相对人皆可主张构成表见代理。而在英国法、苏格兰法、《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只有相对人可主张构成表见代理,但是如果本人起诉要求第三人承担代理行为效果,则很可能被视为对无权代理行为的默示追认。〔76〕See Danny Bush & Laura J. Macgregor, Comparative Law Evaluation, in Danny Bush & Laura J. Macgregor (eds.), The Unauthorised Agent: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92-395.可见,上述两种规定的实际效果都是本人得以直接向相对人主张代理行为效果,但在具体构造上存在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法等将表见代理责任视为禁反言责任,美国法等将表见代理责任视为合同责任。这表明关于本人可否主张表见代理效果问题的争论意义更多地体现于规则逻辑层面而非实质效果层面。
然而,上述持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学者多认为表见代理责任为权利外观责任,由此导致其在论证逻辑上各自存在不足。持肯定说者未能说明如何基于权利外观责任推导出本人有权主张代理行为效果的结论。持否定说者则认为表见代理制度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而设,故仅善意相对人可主张表见代理效果。但是,赋予相对人向本人主张表见代理责任的权利,已使相对人的信赖获得保护。否定本人主张表见代理的权利,这意味着相对人无须对自己的意思表示承担责任,这已经超出保护相对人信赖之合理范畴。可见,基于保护善意相对人这一前提,逻辑上并不能导出本人无权主张表见代理行为效果这一结论。同样持权利外观责任观点,不同学者的论证结论却截然不同,在论证逻辑上亦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这再次证明该观点在规则构建上的不明晰性。
在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表见代理责任属于法律行为责任,只要构成表见代理,本人即有权主张由相对人承担法律行为效果。在判断表见代理是否成立时,已经依据意思表示效力规则对本人意思自治与相对人信赖保护作了权衡,不应再对本人利益予以额外限制。这一结论与肯定说相同,但在论证逻辑上更清晰。
2.对相对人之效力
若表见代理成立,则相对人可主张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于本人。问题在于相对人是否享有选择权,即不主张表见代理责任,转而主张无权代理责任。在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只要表见代理成立,相对人就须承担法律行为责任,并无选择主张无权代理的权利。但对持权利外观责任观点的学者而言,对此问题的判断并无清晰的规则可循,只能再次诉诸于价值衡量。其中,持肯定说者认为,如果否定相对人的选择权,将导致相对人无法撤回其意思表示、无权代理人受到表见代理规则的保护等不当后果。〔77〕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31页。还有学者认为,相对人放弃表见代理的请求,改为主张无权代理责任,即表明其放弃了信赖利益,法律应当尊重其选择,况且该选择没有损害本人利益。〔78〕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83页。
然而,上述理由都存在可商榷之处。首先,在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下,使相对人有权撤回其意思表示将破坏原有的利益均衡结构。善意相对人的撤回权与本人的追认权形成均衡关系。既已构成表见代理,则无本人追认之余地,此时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已经确定,不应再赋予其撤回权。其次,使无权代理人受到表见代理规则的保护并非不当。表见代理责任规范之主要目的系保护相对人利益,而非惩罚无权代理人的过错。无权代理人是否存在过错,不应影响表见代理规则的适用。而且从代理人角度而言,对相对人承担无权代理责任与对本人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相比,孰优孰劣,因具体案情而异,不能一概认为后者优于前者。再者,否定相对人的选择权不影响其选择自由。在纠纷发生后,相对人可自行决定依据表见代理或无权代理规则提出诉请,其享有实质上的选择自由。〔79〕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页。若相对人依表见代理规则提出诉请却无法证明其主张,则由代理人承担无权代理责任。但若相对人依无权代理规则提出诉请,而代理人证明构成表见代理,则相对人之诉请不应得到支持。最后,赋予相对人选择权有可能损害本人利益。若相对人有选择权,则其可以在交易条件对其不利时按无权代理之规定撤回其行为,借此逃避责任、损害本人利益。
可见,否定相对人选择权更符合利益均衡之要求。在表见代理中相对人是因为相信本人具有效果意思而为代理行为,使本人承担代理行为效果足以保护其信赖,赋予相对人选择权反而可能引发相对人的投机行为。在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基于法律行为规则即可得出否定说之结论,避免像持权利外观责任观点者一样陷入价值之争。
综上,在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下,表见代理成立后本人可向相对人主张合同责任,相对人则无主张无权代理责任的选择权。这不仅符合利益衡平的要求,亦符合对现行法规范的解释。我国《民法典》第172条规定表见代理的效果为“代理行为有效”,从法解释角度亦应解释为表见代理成立后,双方都须承担代理行为效果。〔80〕参见张家勇:《论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的双层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第141页。如果本人与相对人皆不愿承担代理行为效果,可协商解除合同,此乃意思自治的应有之义。
五、结语
在代理制度中,本人的意思自治体现于两方面。一是本人同意承担代理行为效果,从而改变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本人同意代理人以其名义为法律行为,从而改变其与代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两种意思的受领人与内容皆不相同,彼此独立。传统代理权概念将这两种意思混为一体,混淆了代理内外部关系,导致表见代理理论的发展陷入困境。
本文主张区分上述两种本人意思,将传统代理权重构为权限与权力二分结构。代理权限的存续与范围取决于以代理人为受领人对本人授权意思表示的理解,代理权力的存续与范围取决于以相对人为受领人对本人效果意思的理解。表见代理的本质是代理人拥有代理权力却无相应的代理权限,表见代理责任属于法律行为责任,其构成要件与效力判断都应适用法律行为规则。采取这一解决思路,针对表见代理责任的认定可以构建起相对明确、逻辑一贯且符合代理本质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