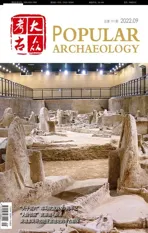“人骨侦探”克莱德·斯诺
2022-03-03韩涛杨子怡
文 图/韩涛 杨子怡

克莱德·斯诺(1928.1.7—2014.5.16)
法医人类学是体质人类学以及现代法医学的分支学科,它运用体质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法律或司法实践(法律制订、侦查、审判等)涉及的个人特征识别、鉴定(如种族、性别、年龄、身高、面貌特征等)等问题,为案件侦破及审判提供证据。法医人类学与医学(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考古学、生物学、动物学等学科密切相关。
2014 年5 月16 日,享誉世界的法医人类学家克莱德·斯诺(Clyde Snow)去世了,享年86 岁。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发掘被埋藏的真相,倾听骨骼的述说,将罪犯绳之以法,让罹难者沉冤昭雪。斯诺的人生仿佛一本以正义为基调写就的“人骨传记”,而他本人也因为破获了20 世纪许多重大的案件被誉为“人骨侦探”。
埋在心里的种子
1928 年,克莱德·斯诺出生于美国德州沃斯堡,在一个叫罗尔斯(Ralls)的小镇长大,他的父亲维斯特(Wister)是一名乡村医生。斯诺童年时经常与父亲一起往来于各个农场之间行医,在本该充满天真童趣与幻想的时光里,斯诺见证了无数人的出生、伤病、衰老与死亡。斯诺12 岁时,父亲带着他去新墨西哥州打猎,遇到了声称在树林里见到一堆白骨的打猎人,这些人带领一位当地的警长和他们去了现场。当大家都认为那堆骨头是鹿骨时,维斯特医生站出来一手拿着一根长骨,一手指着它说:“我敢保证,这是一个男人的右腿骨。”此时的斯诺站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充满自信的面容,突然意识到如果没有父亲的指认,这个人也许会被当作一只受伤死去的野鹿永远留在这里,直到被遗忘,那多么悲哀啊!这一刻的小小悸动成为了一颗种子,埋在斯诺的心中。
像那颗被土壤深埋的种子一样,斯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方向。上学时他沉迷于戏谑音乐和饮酒,“坦白地说,我那时就喜欢玩,我是那种喜欢到处漂泊的人。”斯诺高中时因为恶作剧而被学校开除,被父母送到罗斯韦尔新墨西哥军事学院后,仍无心学业,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毕业。大学毕业之后,斯诺也数次改换深造学校与专业,直至1967 年在亚历桑那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如果把一切归结为命运的阴差阳错,那么斯诺几次改弦易辙所学过的考古学、医学、动物学、灵长类生物学,以及他在空军服役的经历,都为他以后从事法医人类学工作积累了经验和知识。那颗种子也终于在多年后破土而出,长成树木,并且舒展枝桠,延伸向广阔的天空。
调查坠落的灾难
克莱德·斯诺“人骨传记”中的第一章当属空难调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斯诺作为一位体质人类学学者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兼职,当飞机失事时他用专业知识去鉴定识别遇难者,分析飞机坠毁原因、环境;同时也通过制造假人模拟冲撞,来帮助飞机设计安全座椅、改良逃生线路和安全程序等。博士毕业第二年他就成为了实验室的领头人。
在20 世纪60 年代斯诺开始调查空难的时候,还没有人从事这种工作,可谓是首开先河。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坐飞机不在胸前衣兜里挂笔的习惯,“万一飞机坠落,这支笔可能刺穿我的心脏。”斯诺面对疑问时这样回答。
1979 年5 月25 日,浓烟裹挟着失去一台引擎和一部分机翼的美国航空191号航班在库克郡上空坠落,飞机上271人在恐惧绝望中冲向死亡,地面上也有2人牵连其中。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航空灾难,273 个生命体瞬间变成1 万多片肢体残骸,没有心脏和脉搏的跳动,没有血液的流通,没有声音,没有笑容,没有遗言。
遇难者的遗骸混杂在一起溅落开,见证了无数离别与团聚的停机场很快变成了巨大的停尸场,遇难者家属却只能对着虚无的空气和令人绝望的现场空嚎。寻找和匹配尸体的各个部分并确认他们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库克郡验尸员的邀请下,斯诺飞往芝加哥,每天工作18 小时,用了5 周时间来辨认这些人的身份。
坠机事件中,大多数遗骸被严重烧焦,以至于不能区分彼此,面对大量的肢体残片,斯诺找到了迅速有效的鉴定遇难者的方法。他招募电脑程序设计员开发了一套数据库,用来收集储存尸体碎片的信息,如骨头的长度、特殊痕迹等,之后把遇难者的身体特征、医疗和牙齿记录与这些信息相匹配,输入相关的尸体信息时,程序就会显示出10 个和数据最相关的乘客的信息。斯诺使用X 射线、遇难者生前照片以及家属陈述检查了超过1 万块肢体残片,当他的工作团队收工时,在273 个遇难者中只有29 个个体不确定身份。

美国191 号航班坠地后引发爆炸
在这之后,斯诺主持设计的程序被许多法医人类学家广泛应用。空难的调查是斯诺职业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宝贵经验的一部分。
揭开沉寂的真相
克莱德·斯诺幼年时期的那颗种子在光阴里栉风沐雨,慢慢成长为一棵能够遮蔽一片阴凉的大树。从1967 年到2014 年他去世为止,斯诺带着装满专业工具的小皮包,用丰富的知识和机智的头脑解决了许多历史谜团。
1963 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枪手射杀,然而数小时后警方指认的凶徒亦被枪杀,民众中因而衍生了各种阴谋论。多年后,特别调查委员 会(HSCA) 邀 请埃利斯·克利(Ellis Kerley)和克莱德·斯诺加入,用科学方法验证被枪手射杀的是否真的是肯尼迪总统。面对这个挑战,两位法医人类学家采用了到现在都经常使用的方法来核实尸体的身份——X光片对比。他们将法医拍摄的X 光片与肯尼迪总统生前在医院拍摄的X 光片进行比较。经过正位、侧位的影像比较,他们观察了“额窦”的形状及位置。最终斯诺出席国会作证,证实死者确定是肯尼迪总统,从而终止了各种流言。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一个在奥斯维辛进行恐怖试验、造成上万人遇难的“死亡军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门格勒与其他几个纳粹头目逃亡南美洲,之后又辗转几个国家,最后定居巴西。1979 年,67 岁的门格勒因意外溺水而亡,被葬在恩布(Embu)。1985 年,巴西当地有人指认死者沃尔夫冈·格哈德(Wolfgang Gerhard)的坟墓之下埋葬的是门格勒的尸体。

颅相重合法验证约瑟夫·门格勒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门格勒真的已经死亡,那么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他残忍杀害的逝者将得到安息,受害者家属也可以聊以慰藉。假如他并没有死,那么恐惧与气愤将永远不会消除。
根据法医人类学的知识,斯诺和他的团队很快判断出这具埋在恩布的尸骨为男性,死亡年龄、身高和种族都与门格勒一致。紧接着,他们在骨骼上的细微之处又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这具人骨的前门牙有一条缝隙,牙齿中有纳粹时期的填充材料,同时其左手食指骨骼扭曲,膝盖骨上有已经愈合的骨折痕迹。这些骨骼特征加上死者帽子型号的大小对比,斯诺认为这很可能就是门格勒,但这并不能当作决定性的证据,因为也有可能只是巧合。
紧接着团队运用了一种被称作“颅相重合法”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他们对照颅骨上30 个不同点的肌肉厚度参数,用粘土把针粘在这些点上,同时用白点标记应有的肌肉厚度,之后把这个颅骨和门格勒的照片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当把颅骨的图像调得和照片一样大,再将其放在照片上面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照片上的皮肤在每一个点上都与针上的白色标记相重合。“铁证如山,毋庸置疑,这就是他。”斯诺安慰大家,“不用再为这件事失眠了。”
“小丑杀手”约翰·韦恩·盖西(John Wayne Gacy)1972—1978 年间对至少33名年龄在14—21 岁的男性进行了性侵犯和谋杀。他家的地基夹层被用来藏尸,警方在夹层中找到29 具遗骸,这些遗骸被混杂在一起,且因为受害者年龄相仿,无法辨认。凶手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人的身份,因为在他眼中,人和物品是一样的。斯诺利用复原颅面骨骼基础上的画图辨别出这些遇害者的身份。
在18 世纪末开始的“西进运动”中,美国政府派遣第七骑兵团团长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中校率军进攻印第安人。卡斯特孤军深入,遭到印第安人主力的围攻,最终殒命,队伍几乎被全歼。面对卡斯特的坟墓,斯诺仅从一块碎骨和一粒纽扣便辨认出,这是在小巨角战役(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中和卡斯特中校一起殒命的侦查员,而非中校本人。
玻利维亚发现了“火车大盗”布奇·卡西迪(Butch Cassidy)的墓葬,斯诺被邀请前去进行鉴定。布奇·卡西迪对火车“情有独钟”,1896—1900 年间,他与8名同伙抢劫了数十列火车。为逃脱追捕,卡西迪逃往南美洲,1909 年死于玻利维亚。然而这次鉴定最后以民众的失望而告终,因为从几块欧洲人的衣服碎片中,斯诺证实这具人骨是一个名叫齐默尔曼(Zimmerman)的德国采矿者。
捍卫人权的卫士
“人身上有206 块骨头和32 颗牙,它们每一个都有故事。”斯诺说。
斯诺对暴力冲突事件中的遇难者,尤其是那些被埋在万人坑中的遗骸有很强的责任感,他想知道他们的名字、死因、曾经经历过什么,他们是死于弯刀、刺刀,还是子弹?他想还原历史的真相,想澄清一些谣言,不只是侦破受害者被焚烧或掩埋的个体凶杀案,还包括阿根廷、危地马拉、伊拉克等国当权者实施过的大屠杀。斯诺不仅仅是一个替骨骼发声的法医人类学家,更是一位勇于捍卫人权的卫士。
1976—1983 年,阿根廷军政府残酷镇压和迫害反对派。在这段被称为“肮脏战争”的时期里,军政府纵容军队以威胁、恐吓等手段来应对国内民众的罢工、游行抗议等,他们逮捕市民,不经审讯就将他们囚禁在监狱里,或者滥用刑罚折磨无辜的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民众的生命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飘浮。据统计,这期间有1 万多名阿根廷人神秘失踪,杳无音信。
1983 年,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劳尔·里卡多·阿方辛(Raúl Ricardo Alfonsín)当选总统,他开始惩处在“肮脏战争”时期犯有反人类罪行的军人集团,成立调查团寻找失踪者的下落。民众普遍认为这些失踪者已经被杀死,他们被掩埋在只有一个西班牙文“N.N”标记的乱葬岗里。埋在这里的人没有编号,没有名字,更没有记录着他们存在过的墓志。
1984 年5 月,在斯诺开始阿根廷调查后不久,他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各种形式的谋杀中,没有哪一种比政府屠杀国民更令人发指。现代的那些连环杀人犯能残害的最多也就上百人,相对的,当国家政府要残害它自己的国民时,死亡人数往往需要用很多辆卡车装载。”然而,斯诺补充道:“嗜血的政府和狂妄的杀人犯有一点是相同的,由于过分自大而留下来了一系列线索。如果适当进行收集、保存以及分析,它们就像是留在坟墓上已经签了字的认罪书。我们最钟爱的小说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有一句话:‘快!华生,斗争已经开始了。’也许现在对世界各地的法医科学家来说,都应该加入这场最大的斗争。”

斯诺在法庭上
在斯诺来到阿根廷之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农人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用推土机挖掘,无意破坏了一些骨骼和证据。斯诺把当地的一些学过人类学或考古学的学生组织起来,教他们如何系统发掘以及如何倾听骨骼的话语。
乱葬岗里沉寂的残骸,和年轻学生们春草一般生机勃勃的生命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本该像他们一样感受生活的人如今却融入泥土,学生们必然会感到痛苦、同情和无助。他们发现了头骨,那些头骨嘴巴大张着,发出无声的呐喊,而一条蚯蚓从骨头上的弹孔中爬出来,无情而冷漠。“白天干好你的活儿,晚上痛哭一场。”斯诺叼着大烟斗说,烟雾同时模糊了他的眼睛。在斯诺的帮助下,这些学生坚持了下来。他们找到了这些无辜者生前被处决和虐杀的证据:颅骨上的弹孔、手臂和手指处因为防御而造成的骨折等。
1985 年4 月,斯诺在法庭上为检察官指控阿根廷军政府领导人的谋杀作证,让民众明白死于独裁政府的罹难者并不只被“写在纸上”,而是“曾经有血有肉”的。最终根据斯诺提供的重要证据,5 个前领导人被捕入狱。20 世纪80 年代,斯诺帮助阿根廷政府建立了国家法医科学中心。
1991 年,危地马拉高地的一棵鳄梨树下,一组人正在筛土,找寻大约10 年前在这里被谋杀的遇难者遗骸,领导这场发掘的正是克莱德·斯诺。带着宽阔的大檐帽,这个63 岁的德克萨斯人密切观察着发掘进度,他用随和的态度和幽默感冲淡了发掘现场的紧张和压抑情绪。“也许有些坏蛋没有被送上法庭,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些犯罪事件确实在危地马拉发生过。”斯诺说,“头骨上有弹孔,这是不能狡辩的事实。”
斯诺操着缓慢的德州口音,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当被问及在危地马拉面对不欢迎他调查的那些人时是如何避免麻烦的,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块大金属徽章,上面写着“伊利诺伊州验尸官协会”,危地马拉民间巡逻队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戴上这枚徽章就好了。危地马拉的人权组织称至少有90 个人死在危地马拉中部高地上分散的小村庄里,截至当年7 月,斯诺的团队已经在那儿挖掘出了27 具遗骸。
回到美国后,他继续领导几个团队来鉴定识别死于恐怖袭击中的平民,比如1995 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和2001 年世贸中心袭击案。2006年,他作为专家证人出席审判萨达姆·侯赛因的法庭,描述了他在形成于1991 年的万人坑中,鉴定出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遗体。
斯诺始终秉持人文关怀开展工作,他不只对遗骸进行鉴别,同时给死者的亲人带去慰藉,而对被掩埋的个体,他也总能给予恰当的安葬。他的妻子说:“这是他生活的驱动力—人权,他生活的首要激情在于捍卫人权。”
到斯诺在俄克拉荷马的家里参观的客人都会发现,斯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没有区别,布满人骨的工作台就在卧室的旁边,而他的长腿狗Thunder 卧在工作台的下面。斯诺经常叼着烟斗游走在骨骼和电视机、咖啡机之间,有时手里还拿一个头骨,那是他在与骸骨交谈。

斯诺在危地马拉

斯诺在拼合头骨
“骨骼不会遗忘,它们不说谎,它们就在那,它们有故事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