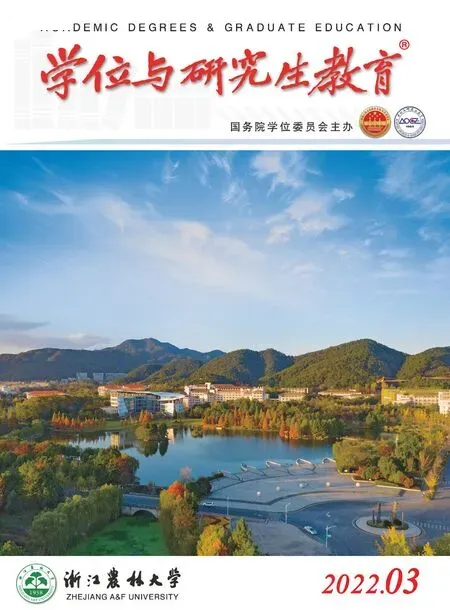论学术自觉与学问之路
2022-03-02陈伟武
陈伟武
一、学术自觉与自学
知识的积累和传承有一定的规律,学习是人类的一种重要能力。从知识的学习到知识的创造,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模仿是允许的,有时还是必需的。如《红楼梦》出了名,就有《续红楼梦》《红楼前梦》《红楼后梦》等等;《少林寺》火了,就有《少林小子》《南北少林》。诗文创作的模仿祖述前贤有深远的传统。陈永正先生指出:“诗文家摹拟袭用前人,初时似觉不大光彩,甚至以此互相攻讦。……但后来这已成文人的惯技。其实,不必忌讳,摹拟前人佳作,是学诗必由之径。习诗如同习字,临摹古代名家碑帖,先力求逼肖,然后才取其神韵。几乎所有需要讲究技法的文艺门类,不从摹拟入手,则终生只能作门外观,难以升堂入室。”[1]89
学术自觉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自我期许,是一种人生定位。若想做一个有作为的学者,一定要有清醒的学术自觉,上天入地,焚膏继晷,对创造性的研究有强烈的进取心,将学问的追求变成永不止息的内驱力。纯粹的学者不应有掠美、抄袭之类的失范行为。“立志”很重要。毛主席说过:“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梁漱溟先生说:“……从那维新前进的空气中,自具一种超迈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又说:“由于这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何事,很少需要人督迫。……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最要紧的是在生活中有自觉。……向上心是自学的根本,而所有今日的我,皆由自学得来。”[2]77-78
大约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到中学毕业,我就长期阅读《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是学到不少时事知识。后来做简帛兵学文献研究,与小时候这种阅读恐怕也有一些关系。1975年读高中一年级时,听了校长林绍文先生一次讲话之后,我还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评“胸无大志”》。那时语文课本收的古文篇目极少,语文课许慈祥老师讲的一篇补充材料叫做《陈涉起义》,出自《史记·陈涉世家》,其中有一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沐风栉雨,砥砺前行。古人说:“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1991年秋,我考上在职博士生,从曾宪通先生习战国秦汉文字,陈永正先生惠赐墨宝,我请求写的内容是《淮南子·本经》的话:“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沚斋先生跋语还谬赞说“足见器度”。2012年夏天,博士生王辉(号小松,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即将毕业,我为他书写的赠联是:“博士亦尝种地,小松当可参天。”这固然是对学生的殷殷寄望,看作夫子自道也未尝不可。
大家进入研究生阶段,对人生目标、学习目的和个人的能力特点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了更好把持自己的能力,这就是“自觉”。有了“自觉”,才能“自主”,才能“自决”,才能更好地“自学”(但千万不能“自经”)。可以说,人的一生中自学比起被动地受教占了更大的比例。老师的传授反而是短暂的。研究生期间虽说有导师,但导师的作用仅仅是引导而已。《荀子·劝学》篇说过:“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荀子原话的大意是,道德好的人,求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素养,道德差的人,求学是为了让人知道。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其他诸项实现的基础。既要“独善其身”,德才兼备,又要有家国情怀,“兼善天下”。有理想,有抱负,有大局观,不做井底之蛙,关心时事政治。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中有许多治国理政的篇章,至今还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自觉方能体现反省精神,朱熹说:“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3]在实现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体现自身的个人价值。
二、读书与选题
陈永正先生说:“在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漠视,知识传承体系的断裂,致使人们,包括‘读书人’在内,已经不大读‘书’了,学者不学,更成为高校文科的症结,研究者每倚仗电脑,搜索网络资料,黏贴成文,并以此为能事。作为一位注释家,一位社会的文化传承者,须博闻多识,贯通古今,解读‘四部’之要籍,有深厚扎实的学问功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总体的认识。”[1]4真可谓语重心长,振聋发聩。年轻人如何完成研究生学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无论如何,刻苦读书、练好基本功是必要的前提。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容庚先生1940年12月25日在日记中写道:“并世诸金石家,戏为评骘: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4]容老能成为大学者,引以为傲的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曾师经法先生说:“(容庚、商承祚)二位前辈长期从事古文字资料的搜罗和撰集工作,他们擅长字形分析和强调第一手材料、注重实证的严谨学风,对我影响至深,特别是容庚先生一贯倡导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至今仍是自己克服困难的座右铭。”[5]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朱东润先生说:“我敢说我绝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做一位古文家的意思。可是韩愈那两句‘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的思想,对我是起着莫大的影响的。”[6]上大学之前,我学过一年的木工,跟我姐夫学的。从前,我姐夫的爷爷去几十里外的山区亲戚家当学徒,学习木工手艺。整整三年只学了一个品种——制作摆放棺材的条凳,练就了过硬的榫卯基本功。平时人们形容事物格格不入是“圆凿方枘”。而我姐夫的爷爷在附近乡村名气颇大,做的木器是榫头与卯眼契合,恰到好处。不用钉子,不用楔子,却坚固无比。
人们常用“学海”“书海”来形容知识海洋之浩渺广博。要读的书真如恒河沙数,而能读到的书却非常有限。老作家孙犁建议人们多读选本是有道理的。但做学问只读选本远远不够。读选本可当作一种重要的读书方法,对某一方面的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或对某一专题的材料有一个精要的掌握,以此为向导,再作更全面更深入的阅读和探索,这才是治学的正确途径。读书做学问,有打井式的,长期做一个题目,打持久战。本科毕业论文做的题目,硕士论文接着做,博士论文继续深入,掘地三尺,“批深批臭”。出土秦代简牍的考古遗址有“睡虎地”,也有“放马滩”。有老师开玩笑说某位学者“十年都睡在睡虎地里”。其实,如此治学真能出成绩。这位学者治学的认真和毅力都值得钦佩,专著进了国家社科成果文库,还晋升为教授。这样治学属于炖老火靓汤的烹饪法。苏东坡《和子由论书》诗曰:“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另一种方法是撒网捕鱼法,先广撒网,再慢慢收拢,纲举目张。读书可使人改变气质,明辨是非,洞悉高下。书读多了,“识”才会高。也可选定若干题目,围绕题目来读书。真的是“戏法人人有,变化各不同”。
结合我本人的问学之路,谈点感想供大家参考:苦练内功,先易后难,由浅入深,亦雅亦俗。我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6年第1期发表了《〈诗经〉同义动词说例》,算是入道之始。1988年 5月参加广东省语言学会年会,写了一篇《骂人话研究》的论文,算是文化语言学的学习心得,1992年正式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时改名为《骂詈行为与汉语詈词探论》。写《〈古陶文字征〉订补》这篇会议论文,用了八个月时间。《〈甲骨文字诂林〉补遗》,都是自己为了读书而做的题目。《简帛文献中的残疾人史料》原是题为“古代残疾人与礼、俗、法”的讲演稿。博士论文《简帛兵学文献探论》,是研究古人如何杀人的学问,后来一段时间治简帛医药文献,是研究古人如何救人的学问。将汉语史与古文字、古文献紧密结合起来研究,逐渐形成自己治学的特点。回首前尘往事,读了一些杂书,只是走了不少弯路。《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是与曾师经法先生联合主编的书,此书是中山大学老中青三代学者二十多人十五年艰苦奋斗的结晶。我的体会是:态度决定一切。在一个团队中,需要有合作的精神。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性情论》说:“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7]讲的也是奉献的精神。
叶燮《原诗》说:“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为依傍,寄人篱下,以窃其余唾。窃之而似,则优孟衣冠;窃之而不似,则画虎不成矣。”[8]若无新见,文章大可不必作。写出来的东西要“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郑天挺先生说过:“在技术科学中,某些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也适用。如在技术改革和研究中,每讨论一个问题,都要从对你的整个事业有无作用着眼,然后把问题分成若干小的单元,再从三方面加以研究:一、这个选题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二、能否和别的题目合并?三、能否以别的东西取代它?”[9]容庚先生说:“有题目我还不自己做,还留着让你做?”自己读书多了,题目都做不完,用不着去抄袭剽窃。陈永正先生说过:“我像你们这般年纪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题目,还可给别人出题目。”要寻找学术的问题点、焦点,开拓新材料,寻求新方法,作出新考释。蔡鸿生先生说:“从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可以悟出学理: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历史认识一定要坚持整体认识,包括纵横、内外的观察。这当然要花大力气。做学问应从容、宽容。从容,才可慢慢探讨,从难从严要求自己。宽容,是指对他人;对古人固不宜苛求,对今人也不要苛求。在当今的学术和教学的评估体制下,从容是非常难做到,于是有人寻找种种捷径,如用第二、三手资料,或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综合别人的成果而没多少新意,甚至抄袭,改头换面,乔装打扮,招摇过市,这是不能做好学问的。”[10]明目张胆的抄袭,巧取豪夺,故意隐匿、淡化或抹杀他人的学术贡献,都不是真正读书人应有的行为。
三、“炼眼”与“养心”
读书要“炼眼”,“眼”即眼力,见识。裘锡圭先生说:“我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深感治学应有三种精神:一、实事求是;二、不怕苦,持之以恒;三、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11]
读书还要“养心”。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不古。”“心”太难懂了。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心性学说就已在中国流行。《孟子·告子上》说:“心之官则思。”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心是谓中》篇说:“人之有为,而不知其卒,不惟谋而不度乎?如谋而不度,则无以知短长,短长弗知,妄作衡触,而有成功,名之曰幸。幸,天;知事之卒,心。必心与天两事焉,果成,宁心谋之,稽之,度之,鉴之。”[12]中医的“心”似乎比西医的“心”含义更宽泛。西医的“心”指心脏,有时为了更明确,就直接说“心脏”,不说“心”。二十多年前我为了赶博士论文,总觉得胸闷,一坐到书桌前就透不过气来,跑去校医院看中医科,医生说是“心悸”,B超结果是“左心室心律不齐”。大毛病也不是,只能说“我心脏不好”,不说“我心不好”。心脏不好是病人,心不好是坏人,当病人还是比当坏人好。
裘锡圭先生在接受青年学者访问快结束时说:“该讲的都讲了,最后强调一下我的主要意思。我不反对提倡或引进好的理论、方法。但是我感到,就我比较熟悉的那一部分学术界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理论或方法,而是研究态度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学术健康发展,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我不是说自己在这方面就没有问题,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何况还不可避免会有认识上的偏差。大家共勉吧!”[13]裘锡圭先生引用《吕氏春秋·诬徒》:“善教者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14]师法古人,师法今人,博古通今。《论衡·谢短》篇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一心前行,必有善果。学术之路很漫长,跋涉前行,总能修成正果。《西游记》中的白龙马都能修成正果,马是畜生,我们是人,为什么不能呢?
做学问要调节好心态,先难受,后享受。“炼眼”就是长学问,“养气”就是长精神。比“养气”更根本的是“养心”。我有一水仙花盆,用于春节期间,一到夏天闲置在侧,于是买来小睡莲,以清水供养茶几上,差不多每天早上到工作室之前,路经小区或校园树下,拣数朵鸡蛋花置于花盆中,鹅黄的花与睡莲嫩绿的叶相映成趣。以前饶宗颐先生喜欢给人题字:“如莲华在水。”语出《法华经》。如此境界我们难以做到,先来个“如鸡蛋花在水”,倒也不错。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谈道:“《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我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惟是苦(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的极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字相对的是一个‘忧’字。然而说‘仁者不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其明白,是何而为然?经过细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动念。”[2]91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多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尤其要善于苦中作乐。陈永正先生说过:“西瓜就让别人去抱吧,自己捡点芝麻算了。”有平和的心态,往往能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台湾著名医生、病理学之父叶曙先生说过:“不过也有像不修边幅的人一样,满不在乎升等不升等,心想只要我有学问、有能力,万年副教授又有何妨?优秀台大人中,各院都有这一类的名士。……像上述的人物,称之为超俗的逸士固无不可,要说他们都是些懒于写论文而又怯于争先的懦夫,你也无法为他们辩解,不幸优秀台大人中,便不乏这种人物。”[15]老先生的话,确实值得我们警省。
四、学术自律与学问境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对学术规范问题曾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参加者有梁治平、邓正来、杨念群、徐友渔、朱学勤、陈少明、王缉思、钱乘旦、雷颐、朱苏力、陈平原、陈来、林毅夫、刘东、周国平、童世骏、樊纲、丁东、谢泳等著名中青年学者。杨玉圣先生对这场影响深远的学术争鸣作了很好的评述[16]。进入二十一世纪,葛兆光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提问:“中国学术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吗?”[17]学术失范的现象触目惊心,名利地位的诱惑成了学术不端滋生的社会土壤。张昌平先生在《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自序的结尾说:“我的一些文字及观点有时会有意无意地被有的学者‘雷同’,或者被更高明的学者在‘错误的观点’这样的话之后作出引注,暗示读者该错误源自于我而不是我已经提出他正在论述的东西。对此我也曾经郁闷,但念及这种特殊的方式或许也算得上是对于学术的一点贡献,最终释然。”[18]刘钊先生在《古文字构形学》的后记中说:“这篇博士论文迟迟没有出版,也使得学术界的某些人得以故意装作没看见,从而不加解释注明地任意取用。台湾学者邱德修先生曾热心建议我在台湾出版该论文,并开玩笑地说:‘再不出版就要被人偷光了。’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19]考释一个甲骨文奖十万元,确实能刺激人的神经。学术不端的学者,与运动场上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很相似,都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对待人生。人穷志不穷,不坠青云之志。古人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没有污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金杯银杯不如学界同道的口碑。自己的骨头要长肉。我们要适应环境,顺时而作,将自尊、自爱、自重、自律当作毕生追求,不因某些诱惑而出现学术不端。没有失范行为的学术人生,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缺乏学术自觉的人肯定自律不严,未来的学问境界肯定高不到哪里去。我们深为一些前辈学者惋惜,平生严谨治学,一旦失范,终致贻人话柄。
有了学术自觉,珍惜自己的羽毛,自尊自爱,才能自律。不做帮凶,不推波助澜,不当枪手。自己勤奋读书,勤于思考,题目都做不完,就不会生出妄念,想去抄袭、剽窃别人的成果。
要把学问做好,必须有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金岳霖先生在讲到清末民初美国人在中国办雅礼大学时指出:“学校教育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头一点要强调,它的对象是青年,不是老年。老年就是争取到了也没有用。要占领的是青年的什么呢?意志、情感、思想,或者两个字:‘灵魂’。古人对于这两个字是有某种迷信的,这里的意义只是前三者的代名词而已。前三者非常之重要,占领了它也就是占领了整个的人。这也就是说,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制造了许多黄脸黑头发而又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当然这只是极其初步的美国人,单靠在中国办学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20]“为谁服务”的问题、“把自己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一定要讲的。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年轻人要有理想,有担当,有作为。读书要有大局观:了解学术史,大至一个学科的发展脉络,小至某一知识点、问题点的研究史、演变轨迹。写文章要开门见山,要讨论哪个问题,在书或论文开头,人家看你的概述,大致就可知道你的学术背景的深浅。一个人治学的“格调”“气象”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炼好本领,把学问做大,看看到底是翻江倒海卷巨澜,还是激起学海的一点小涟漪。
刘梦溪先生说:“人文科学的作用不是现在时,而是将来时,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宋代大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真是一语中的之言。如果很多人都有机会念书,就会形成集体的文化积淀,每个人都有人文方面的修养,这样的人群的气质就不同了。……另外学术还是一种象征,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讲过,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王国维说一个国家有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而大学,就是拥有最高学术的学府。……陈寅恪的一个文化理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大儒。总之人文科学的作用,对个人来说是变化气质,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则是可以转移风气。”[21]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22]前不久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彭玉平教授在第七届全国中文学科博士生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指出,博士生阶段大体相当于第二境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向幸福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