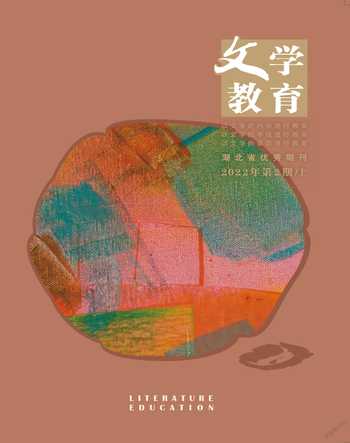加缪存在主义视角下《永生》的死亡观
2022-03-01黄小凡
黄小凡
内容摘要:死亡是博尔赫斯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本文以博尔赫斯短篇小说《永生》为例,同时联系加缪《西西弗神话》中的存在主义精神结合分析,可以看出博尔赫斯对死亡的哲思,对虚无主义和荒诞生活的反抗。
关键词:博尔赫斯 死亡观 反抗
《永生》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与博尔赫斯其他短篇小说相比,该小说篇幅相对较长,这无疑给予了博尔赫斯更大的创作空间。在《永生》中博尔赫斯详细阐释了他对于死亡复杂而深刻的认识。作品中,博尔赫斯以一位平庸者追寻永生、得到永生、回归死亡的经历为主要叙述对象,通过主人公的磨难与得失,寄寓了博尔赫斯关于死亡的哲思;表现出博尔赫斯对虚无主义的反抗和超越;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哲思又和加缪一直抱有的对荒诞生活积极反抗的西西弗斯精神产生了共鸣。因而,本文将结合加缪《西西弗神话》中的反抗精神对博尔赫斯笔下的《永生》进行分析,探究博尔赫斯独特的死亡观念,对虚无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待荒诞生活的态度。
一.寻回幸福——永生旅程中的死亡观
在《永生》中,博尔赫斯讲述了主人公罗马执政官鲁福的两次旅行,这两次旅行将主人公的人生分成三个部分:逃避死亡、恐惧永生和重获死亡。主人公的这一段旅途看上去犹如一个圆环,毫无收获,重回起点,其实博尔赫斯在其中深藏了他的死亡观。
1.逃避死亡追寻永生
小说用第一人称,从罗马执政官“我”受到启示踏上追寻永生的旅途开始。起初的“我”是罗马帝国一个平庸的军团执政官,没有什么功勋,不受皇帝或长官重视。“我”对自己平庸无聊的生活感到了厌倦,重复的生活使“我”越发厌恶与恐惧死亡的到来,于是决心踏上旅程去寻找传说中的永生之城,以期获得无限的时间,逃避死亡,寻获生命的意义。
在通往永生的路上,“我”历尽艰辛:先后经历了沙漠中的酷暑、猛兽、队伍中的瘟疫、士兵哗变、与亲信走散等各种磨难,最终除了坐骑一无所有。自身与世界的一切联系被剥离,甚至连思想都一片混沌。饥渴难耐的“我”进入了濒死状态,被“我”认为是“穴居人”的群体所救,与一个追随我的“穴居人”一道走入了永生之城。
在这次旅途中,永生之城的入口初看像是对经受磨难的主人公最高的奖赏,但之后博尔赫斯揭示出的永生令人恐惧的真相让我们了解到,这无穷无尽的磨难似乎是崇高的死亡对“我”最后的挽留。
2.永生带来的恐惧
获得了无尽的生命,首先带给“我”的却不是希望,而是想将“我”的理性剥夺的残酷:前代永生者们铸造的“无休无止,难以容忍,复杂得到了荒唐的程度”[1]118的宫殿没有任何秩序与理性可言,令人恐惧。在其中待得时间过长,甚至模糊了“我”关于家乡和时间的记忆。
在与前代永生者,现在退化为穴居人的大诗人荷马交流后“我”意识到,自己得到的无尽生命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断进行尝试,实现一切人生目标的美好;而是连以前唾手可得的平庸都会被消磨殆尽的虚无:“在永生者之间,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在将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预兆。”[1]123这种漫长时间中地重复造就了一个严峻的结果:永生者已经完全抛弃了作为人的高贵和尊严,人在获得永恒生命的同时,物质与精神的一切都已经在无尽时光的磨蚀下消解殆尽了。所以作家写道“一个永生的人能成为所有的人,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1]122“我”不愿就此沉沦,于是选择了反抗,选择寻回属于自己的死亡,寻回有限的生命和生命的意义。
3.寻回死亡的幸福
在“我”追寻死亡的旅途中,并没有像追寻永生一样经历特别的磨难,并未受到超越时代的苦厄,只是换了许多普通人的身份,做了許多以前不会去做的事:以士兵的身份参与战争,记录水手辛伯达的航海,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书写了不同的故事,为了寻回死亡饮下“我”所见的所有河水。死亡就这样不期而至,完全不似永生到来那般奇诡。甚至如果不是受伤,“我”都无法发现它的来临。
当死亡的高潮悄无声息地降临在“我”身上时,当初一切只是重复的行为重新变为了独特,人生重新拥有了高潮与低谷,“我”感到了巨大的幸福。勇敢面对死亡才能迎来生的意义——博尔赫斯的作品为读者揭开了这样的生活真相。作家展示了悲剧性,荒诞性的生活下有始有终的有限生命是多么重要,从生到死的每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
博尔赫斯在《永生》中正面探讨了生与死之间的联系:死亡在作品中与永生相对立,成为一种潜在的,将人定义为人的重要能力。像小说中写到的那样:“不久之后,我将是众生:因为我将死去。”[1]125在博尔赫斯看来,死亡是主人公的最终追求,也是普通人得到幸福的重要来源,作家精确地刻画出主人公人生短暂但又被诸如荣誉、功勋等外物奴役的悲剧性生存状态。为了摆脱这种荒诞的生存困境,主人公历尽艰辛去寻求永生,在得到永生之前,永生对主人公来说意味着无限可能,可以借此彻底摆脱死亡的威胁,获得精神上的永久安宁;在得到永生之后,永生显露出了残酷的真实面目,死亡却表现出了它人生最强劲音符的本质:有限生命中自然到来的死亡是为人生赋予意义,脱离荒谬回环的一种幸福的方式,也是博尔赫斯反抗生命中虚无主义拷问的重要武器。
二.对抗虚无——直面世界的真实
在《永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博尔赫斯花费大量篇幅构想了以荷马为代表的一类肉体永生者。博尔赫斯将这些永生者的状态描述为:“绝对的平静”,[1]122达到这种平静的代价就是任由所有的生命意义被时光消磨殆尽。荷马他们毫无动静,目光呆滞,物质世界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在博尔赫斯的认知中,肉体的永生是对人实质的消解,“……事物的映像不会消失。任何事情不可能只发生一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转瞬即逝。”[1]123永恒的生命看似带来了庞大的可能性,但最终却会将永生者推向一切努力都被时间消解的地狱。
永生者们只能将自己无限的生命赋予无限地思考,但每天徒劳地思考,不能对现状造成任何改变。面对无尽的生命带来的绝望与精神折磨只能忍耐,以至于逐渐失去了理性和语言能力。永生者们的这种“思考”与其说是一种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寄托,一种另类的宗教。加缪在阐述人如何反抗荒谬的世界时,用“哲学的自杀”对虚无主义进行了定义。加缪认为,“哲学的自杀”是一种虚无主义,在选择“哲学的自杀”的人那里,“现实世界是荒谬和虚幻的,只有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将肉身和生命皈依于宗教,才能得以永久性的解脱。”[2]这种将人生意义,一切可能皈依于名为“思考”的宗教的逃避行为,与主人公想要追寻的,通过不断实现新的人生目标,丰富自身生存意义的精彩生命完全背道而驰。主人公恐惧永生之后所要面对的虚无,恐惧那一切都被消解的既定命运,因此,他选择了反抗,选择了相信“有一条赋予人们永生的河;某一地区应该有一条能消除永生的河”。[1]123
《永生》故事中,主人公对“哲学的自杀”进行的成功反抗,正是博尔赫斯借人物之口说出的对虚无主义的反抗態度。
长久以来,博尔赫斯被认为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因为他的笔下“流动着十分精致的孤独和虚无主义精神”[3]博尔赫斯受到多次感情失败;无法挽回的因病致盲;不可知论者的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广泛阅读中接触的叔本华,尼采等的哲学思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对虚无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悲观,虚无主义色彩。但将虚无主义标签贴在博尔赫斯身上无疑是片面的,因为博尔赫斯虽然处在在虚无主义影响下,但他不愿就此沉沦,不愿向虚无主义逃遁,通过对死亡意义的思索展示出了他对虚无主义的反抗。博尔赫斯没有任由外界的各种影响支配自己,对前人的超越一直是博尔赫斯作品的显著标签之一。博尔赫斯以文学为刀枪,在需要表达自己时写作,将创作作为自己的“宿命”。让主人公作为自己的化身,表明自己抗争的态度,去寻求摆脱虚无诅咒的那条河流。博尔赫斯认识到了世界的可悲源自它的真实,但他依旧选择接受真实,面对真实,而非用虚无主义逃避真实。
死亡是博尔赫斯反抗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催生出了博尔赫斯对死亡的拥抱和推崇。博尔赫斯曾借亨利·詹姆斯之口将死亡形容为“这桩非同凡响的大事”,[4]在面对虚无主义对世界一切皆无意义的拷问时,博尔赫斯用死亡标记生命,用有始有终的生命彰显人生意义,从虚无的“永生者”回归幸福的“荒诞人”。
三.拥抱死亡——从永生者回归“荒诞人”
博尔赫斯的哲学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悲观主义倾向,但在这种悲观主义思想的底色之下,博尔赫斯将死亡与反抗荒诞生活联系起来。他在与阿根廷存在主义作家萨瓦托的对话中直言:“我赞成自杀”[4]162这看似是博尔赫斯提升了自杀在其思想中的地位,想通过放弃生命寻求一种逃避。但现实生活中博尔赫斯虽然多年来一直在心理上尝试自杀,面对人生困难一次次觉得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依旧鼓起勇气走向生命自然的终结。因为在博尔赫斯看来,慢慢接受死亡,面对死亡之前的痛苦是“需要更大的勇气”[4]162才能做到的事。面对死亡的挑战,博尔赫斯认为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有尊严的回应。才能从死亡手里取回我们应得的勇气和尊严。博尔赫斯对待死亡的这种态度和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展现出的对待死亡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加缪认为,从生到死才是一个完整生命的应有状态,这种态度也集中体现在他笔下的“荒诞人”西西弗斯身上。所谓荒诞人便是“不为永恒做任何事,又不否定永恒的人。”[5]69加缪思想中的“荒诞人”人生的意义便来自“虽然确信他的自由已到尽头,他的反抗没有前途,他的意识可能消亡,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时间内继续冒险。”[5]69西西弗斯在面对绝望境地时,依旧勇于反抗,对荒诞的世界保有热情,这种热情使他主宰了自己的人生,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而《永生》中的主人公又何尝不是博尔赫斯笔下的西西弗斯呢?面对人生的荒诞,博尔赫斯笔下的执政官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都认清了生活的本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反抗。最初执政官对自己平庸生活的荒诞本质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简单的想通过延长自己的生命摆脱平庸生活,寻求生的意义,看到世界不同侧面,却坠入了永恒生命的陷阱,陷入虚无,与本来的愿望背道而驰。执政官永生后一切的行为,都是之前已经发生或之后将会发生的。此时的执政官已经失去了人生意义的所有依托。所以执政官选择反抗,再次踏上旅途寻回死亡。
博尔赫斯在作品中流露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他不希望纯粹的肉体不朽,反而希望表达一种虽然肉体死亡,但精神依旧在荒诞中长存的奋力。虽然死亡代表了肉体活力的休止,但也是人一生中最独特、最强烈的符号。博尔赫斯在作品中多次明确地表达了不死的人生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这一观点,寻求永生意味着人生意义的消解,意味着人生只是无限的重复和循环。延长生命只意味着延长痛苦,因为“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 [1]123在博尔赫斯的认知中,拥有死亡这个休止符,人生才拥有追寻意义的必要。永生会夺取人生的这个休止符,在永生的消解之下,一切记忆中的形象都已消失,博尔赫斯因此认为,死亡不是恐怖的而是具有价值的,死亡能够实现不朽和精神超越,没有死亡,也就无法体现人的尊严,人生的高潮源自死亡自然的出现。博尔赫斯一生中努力建构与践行的“死亡哲学”展示了他对死亡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死亡交织着悲观与乐观、代表人生的崇高与尊严,自然而来的死亡是弥足珍贵的。人类的任何选择和行动都不能改变个体的最终死亡结局,死亡的必然和不可避免充满宿命论的悲观色彩。所以,博尔赫斯也曾悲观的看待死亡;但最终,博尔赫斯找到了死亡的意义,乐观地拥抱死亡:在死亡的瞬间人可以达到一生命的完整状态,所有人生经历进入升华状态。通过死亡,人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有尊严地回应荒诞生活,为个体生命注入价值。认识到世界的可悲与荒诞,我们依旧鼓起勇气面对死亡,反抗荒诞。
文学作品中,对死亡与人生意义关系的研究是永恒的主题之一,关注如何死,就是关注如何生。综上所述,博尔赫斯小说的死亡观表现在对死亡的平然和拥抱的态度,死亡不是恐怖的而是具有价值的,有限生命的自然死亡能够实现精神超越。没有死亡,人无法从荒诞的生活手中取回尊严。死亡是个体通向不朽的一种方式,是人一生中最强的符号和纪念。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博尔赫斯提倡的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既接受生,也接受死,通过自然的死亡标识出人生的意义,用死亡这一武器勇敢的反抗荒诞,并不倡导因为人生荒诞无谓地放弃生命,不顾物质世界肉体的努力而一味寻求精神的长存在博尔赫斯看来也是不可取的。这种接受生死,拥抱生死,在过程中寻求生命意义观念不失为博尔赫斯的一种昂然的人生气概。
参考文献
[1][阿]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小说集[M].王永年、陈泉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2]李元.论加缪的“荒谬”概念[J].北京大学学报,2005(1).
[3]赵秀霞.抵达虚无以后——博尔赫斯的精神突围[J].北方文学.2015(21).
[4][阿]奥尔南多·巴内罗整理.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M].赵德明译.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5][法]阿尔贝·加缪.西绪弗神话[M].沈志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