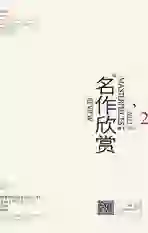《使女的故事》母亲形象书写
2022-02-28昝天怡
摘 要:《使女的故事》以架空的国家——基列国为背景,从使女奥芙弗雷德的第一人称叙述,采用倒叙式叙述模式讲述女性被按照功能划分等级,沦为生殖工具。小说主要塑造了三类母亲形象,传统压抑的母亲、异化极端的母亲、觉悟反抗的母亲,她们同为母亲却形象各异,在自我与母亲身份之间挣扎。通过观照书中的母亲形象,能够发现父权社会下母亲形象的复杂性与身份的矛盾性,同时有益于母亲群体乃至女性的真正觉醒与解放。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 母亲形象 叙事艺术
《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奥芙弗雷德的第一人称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残忍、专制、野蛮的基列国,尤其是充当生育机器的“使女”们噩梦般的经历。小说中的女性,无论地位较高的大主教夫人,还是地位低下的使女、嬷嬷、马大,面对政府的强制性的统一分配管理,她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所有女性都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整个故事通过奥芙弗雷德的思想、视线、聆听以及对话展现于读者眼前。美国学者福霍尔特a从《使女的故事》深入地理解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生物学的对比哲学是如何影响基列共和国的性政治,或者从反乌托邦角度探讨《使女的故事》中城市空间的转型。我国学者多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这部小说,如张冬梅、傅俊b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与自然有着独特联系,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关怀和女性意识,张继英c则从从女性主义叙事角度探讨小说中女性话语权威。
母亲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母亲身份迄今为止依然被认为是女性必须要承担的最重要的身份。女性本身的独立性价值受到严重的损害,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通常被认为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在父权文化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母亲仅仅被看作是繁衍后代的生物体,是“缺席的在场”d。对母亲的书写往往是讴歌母亲具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孩子即使牺牲个人的幸福也在所不惜。严格秉承母爱伦理规范是社会对身为母亲的女性的职责期待,母亲的自我一旦出现就会被打上“自私”的标签,以其不称职而备受谴责。《使女的故事》出版于1985年,正值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是母亲角色转变的重要阶段。作者阿特伍德的母亲——玛格丽特·基兰在阿特伍德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兰并非传统式母亲,她骨子里是个“游牧民”,“不爱刻意追求物质上的舒适,砍柴、取水、生火、洗衣、做饭,这一切都难不倒她。在孩子们面前,她永远是一个积极乐观、敢作敢当的女汉子形象”e。《使女的故事》中有三类母亲形象,首先是站在顶端的大主教夫人们,未经历分娩之痛而成为母亲,她们是传统压抑的母亲;其次是奥芙弗雷德的亲生母亲,她是极端女权运动的代表女性,将女性放在男性的对立面,她作为母亲却疏于承担母职,只在回忆里出现;最后是以“使女”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女性,她们只是“行走的子宫”、生育机器,内心充满矛盾,渴求并探索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反抗与妥协之间来回挣扎的反抗觉悟型母亲。同被称作母亲,却形象迥异。小说粉碎了母亲的神话,驱散笼罩在母亲身上的光芒。女性反抗男权社会所建构的家庭模式对于她们的压制,她们不再受传统母亲身份的束缚,勇敢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确立女性的主体性。长期以来,社会以“好母亲”的标准塑造作为母亲的女性,一旦她们的行为有所偏离,她们便被边缘化而饱受唾弃。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对“母亲”这一身份的多重表现进行深层次的解读,针对书中“母亲”群体的解读,改变固有的认识,希望能够让读者从更多角度理解“母亲”。
一、传统压抑的母亲:大主教夫人
社会地位最高的大主教夫人们看似表面风光,内心深处却充满辛酸无奈。她们在家里没有话语权,还要目睹并配合丈夫和使女的“授精仪式”,生活里她们能做的事就是织围巾和装病,以此来打发无聊的生活。小说的主要情节是通过奥芙弗雷德的第一人称叙事向读者缓缓道来的。在她的口中,大主教夫人作为“家庭天使”的典型代表,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空间,亦无力表达自我。局促的交流空间、受限的交流权利,失去表达自我的话语权,使得她们压抑着自己的喜怒与欲望,自欺欺人式地充当着父权社会的“传教士”。她的第一人称叙事有两面性:一方面,主人公以主观性、个性化的口气叙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她试图努力客观、冷静地展示自己的所见所闻。奥芙弗雷德在疏远受述者(读者抑或是倾听这盘磁带的人)时,告诉人们她是在讲故事,而故事难免会有虚构和片面。这样的坦白事实上没有增加她与受述者的距离,反而更显其诚实和可靠性,令读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去体味主教夫人内心深处的矛盾性。
《使女的故事》中,使女“珍妮”生下了孩子,其他来祝贺的大主教夫人们对着“珍妮”的主教夫人说:“她真像是你的女儿,你一定也这么认为,家里的一个成员。”f说完这句话夫人们发出了一阵笑声。轻轻的几句话,看似一带而过,却蕴含深意。不仅使女诞生的孩子属于大主教夫人,连使女自己也是大主教夫人的女儿。可是作为“母亲”的主教夫人却让使女和自己的丈夫发生关系,扭曲复杂的家庭关系如同镣铐束缚着大主教夫人的身体。她们带着复杂麻木的情感面对使女和刚出生的婴兒。第一人称是《使女的故事》的主导叙述声音,通过奥芙弗雷德对主教夫人话语的再现,整个句子带有讽刺意味。这种叙事方式能触发读者从叙述者的角度体会基列专制政权的荒诞与残暴,同时也展现了奥芙弗雷德的观察力量;作为其他人物的观察者和他们目光的过滤器,奥芙弗雷德具有穿透力的眼光洞察出外在表象的内在含义。奥芙弗雷德见证了主教夫人的前后两张面孔,在使女“珍妮”离开后,主教夫人的口气立刻变了:“全是些小荡妇,但你也不能过于挑剔。毕竟她们生的孩子是交给你的,对不对?”g这句话出自大主教夫人们之口,通过奥芙弗雷德的转述,其中难免缺少些情感词。这里的大主教夫人们按照《圣经》的引导成为孩子的母亲,强迫自己流露出母爱,但是她们内心仍然对此充满鄙夷。她们夺过使女的孩子,却还要辱骂使女为“小荡妇”。大主教夫人们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只因父权给予她们母亲这一身份,但是她通过对使女的咒骂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当大主教夫人拥有使女生下的孩子后,她“低头俯视着婴儿,似乎她是一束花,一件战利品,一个贡品”h,她们将孩子视为自己的一种附属品,是父权制度下的必需品。而教养女儿的过程又是在灌输基列国的教条抑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类母亲在叙述者口中已经被父权社会内化成为维护父权利益的帮手,她们压抑自己的欲望甘作男性的代言人,将自己的怨愤加诸在同为女性的她者,努力按照男性的需要塑造女儿及自己。她们最终会被拥有觉醒意识的女儿“杀死”,被时代抛弃。
二、异变极端的母亲:“我”的母亲
在基列国的社会制度下,奥芙弗雷德的母亲是挑战父权的罪人,她在书中不配拥有姓名。波伏娃i强调成为母亲并非女人的天职,她在书中呼吁女性走出家庭寻找母亲身份之外的自我。奥芙弗雷德的母亲将“自我”摆在母职之前,更是将女性置于男性的对立面。叙述者“我”与故事的虚构主人公“我”为同一个人。她讲述的都是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所叙述的事件经过了个人意识的过滤,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情绪。但第一人称叙事有利于女性的自我言说,叙述者将女性个人的声音推到公众面前,公开争取社会地位,建立女性权威。无论是叙述过去的事还是讲述当前的遭遇,使女奥芙弗雷德能让读者感受到她真诚的态度、平和的心境,小说大量使用现在时态,使故事更具即时感,仿佛讲述者就在我们对面声泪俱下,侃侃而谈。书中穿插着奥芙弗雷德对自己母亲的追忆,回忆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往事当作现实,又在现实与回忆、当下与过去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交叉,从而突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奥芙弗雷德的回忆叙述中,她的母亲不是一个父权制度下尽职尽责的传统“好”母亲,在回忆与现实交织的叙述里,她的母亲似乎是一个愿为女性事业牺牲的好母亲。
“我”的母亲是第二次极端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记忆中“我”的母亲常听禁歌,“我”也常常受母亲的“熏陶”,“‘我’的母亲还有一台可以放这类东西的机子,声音刺耳,时好时坏。朋友来时,她常常放禁歌给她们听,边听边喝酒。她会在周六带着‘我’去广场,打着带我出去玩的旗号实际上去烧那些情趣杂志”。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忙忙碌碌,忙着游行,忙着捍卫女性的权利,“我们”总是在不停地搬家。“我”的母亲是一个向往自由的女人,“刚毅勇猛、斗气十足”j,她用自己的一生努力换取“男人下厨房削萝卜”k。《使女的故事》中使女奥芙弗雷德作为叙事的“中心”,对于叙事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所处的社会阶级,各种压迫与羞辱形成了重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视觉观察和回忆阐释成为奥芙弗雷德的另一种语言,一种不用文字交流的手段。“厨房弥漫着发酵粉的味道,勾着我缕缕怀旧之情,让我想起别的厨房,别的属于我的厨房,那厨房闻起来有母亲的味道,虽然我的母亲不做面包。”l这是奥芙弗雷德的回忆,嗅觉记忆里面有“我”母亲的味道,从这一叙述中,可以看出“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她虽不擅厨艺,但是我记住了她在厨房的味道,是“我”记忆中母爱的味道,书中从未提及过“我”的父亲。显而易见,“我”的出生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在奥芙弗雷德的叙述中,只有母亲的记忆,男性处于失语状态,也证明了“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可以管理其他角色的声音,这就显示出一种叙述结构的优越感,突顯了我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而使其他声音保持沉默,因而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威。m对于“我”的母亲而言,男人不过是几秒钟制造精子的机器,“我”是因为她“想要才生”n的。“我”的母亲将女性放在男性的对立面,仿佛誓死要分出个高下。母亲有着女性鲜明甚至极端的主体意识,她给小时候的奥芙弗雷德种下女性觉醒意识的种子,为奥芙弗雷德后期的反抗埋下伏笔。
三、觉悟抗争的母亲:使女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次女性运动浪潮以来,母亲身份成为女性主义者纷争的重要话题。使女们触犯父权礼教,但因有着健康的子宫而被“上帝”选中孕育下一代,“她便永远不会被送到隔离营”o,她们不过是毫无意识的“行走的子宫”。波伏娃早在《第二性》中就以“事实与神话”为题,从生物学的角度驳斥了将女性等同于子宫的观点。她对主流母亲话语的颠覆性挪用将母性从女性不言而喻的本能转化成陌生的、非本能的东西。女性不是为了成为母亲而存在,使女更不是繁衍的工具。
双重性被定义为女性主义或者女性所固有的特性。申丹认为双重性是女性不得已的选择。唯有这样的选择,女性才能“在男性与女性、中心与边缘进行协调”p,尤其是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在《使女的故事》中,小说并未采用线性叙事模式而是采用现实的倒叙。作者在故事开头没有交代时间,读者几乎感觉不到故事中发生的事与奥芙弗雷德所处的现实在时间上的距离,只是在小说结尾,读者才发现这一事实。叙述者“我”站在现在某个选定的时间点,“回顾已经发生的一串真实事件或者虚构出来的事件”q。“我记得自己在大声尖叫,不过这都是感觉而已,说不定只是喃喃低语。她在哪儿?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8奥芙弗雷德在梦中回忆自己与女儿分别的场景,撕心裂肺,却不甚明晰,记忆开始模糊,她开始怀疑当时的场景,两个问句问出了母亲的心声,以及守护孩子的执念。为达到制造悬念的效果,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主角的“我”一般会小心地保持距离。叙述者会选择过去的“我”作为聚焦者,回顾就成为现场再现,这样我们就有了双重视角,而叙事线条在双重视角叙述下由受述者自行整理。在基列文化的煽动下,奥芙弗雷德迫使自己认为:“他们是对的,就当她已经死了是要容易得多。我不必苦苦盼望,不必做无谓的努力。何必用头撞墙呢?”s她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试图说服自己不要再思念女儿,就把自己当成没有灵魂的躯壳,这样自己或许会过得好些。这恰恰证明了父权社会通过分离母女间的联系,打破女性之间的团结,从而使自己得以存续。沃尔特斯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他认为“母女关系是家庭生活的桥梁,足以改变传统的家庭结构”t。可是一切都被父权拆解得支离破碎,分离已久的母女再次相见恍如陌路,父权制度笼罩着母女关系的阴影令人胆战心惊。奥芙弗雷德因年少时缺少母爱的影响,成年后的她更愿意去做一个关心家庭的母亲。奥芙弗雷德回忆女性被剥夺工作、财产权后,她“没有参加那些游行,卢克说那种事情徒劳无益”。卢克希望奥芙弗雷德“替家人着想,替他和女儿着想”@ 1,奥芙弗雷德确实说服自己妥协并回归家庭,她开始忙于家务,动手烘烤食品,围绕着家庭生活,放弃去捍卫女性权利的宝贵机会。在回忆过程中,奥芙弗雷德早已涕泗横流,她明白妥协与让步只会让自己深陷泥潭。使女们所有的一切都被标准化、固定化、统一化、计划化。奥芙弗雷德原本生活的社会忽然发生巨变和坍塌,随之而来的一切社会秩序被重新规划、建立。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坍塌,见证了女权运动发展的她心中早已被其母亲埋下女性意识的火种,那间狭小的房子的地板一角刻着的拉丁语“别让那些杂种骑在你的头上”,成为她走向反抗父权的助力。奥芙弗雷德在思想深处拒绝成为一个“行走的子宫”,她渴望成为一位男女平权社会下的母亲,反抗父权,为树立健康自由的母女关系而努力。
Zerilli指出,波伏娃实际上“将传统叙事中母性一成不变的含义变成多样性”,阿特伍德笔下的“使女”挑战了“单一的母性欲望”@ 2,使母亲身份不再仅仅肩负着父权社会推崇的生育功能,而是成为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的主体。唯有母亲作为主体存在,才能促使女儿获得自己的主體性,唯有母亲与女儿联合起来,女性才能真正地觉醒解放。
四、结语
在众多男性作家笔下,母亲形象起着道德感化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守护神,但女性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主体性。在丧失主体性的同时,一些女作家也意识到母亲主体性的重要性,开始书写女性在摆脱母亲身份过程中的挣扎。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对叙事方式的创造性使用,给足读者想象的空间。在这盘“磁带”中,读者跟随奥芙弗雷德的讲述,进行空间与时间的多次转换。女性小说家将目光转向母亲,使之从沉默的幕后走出来并逐渐获得自己的话语。第二次女权浪潮过于极端,造成两性关系紧张,社会上的极右势力以保护妇女之名,行迫害妇女、扼杀人性之实,建立基列国。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肩负“母亲”身份的大主教夫人在基列国成立后,甘愿被限制在家中,将时间耗费在花园中,将自身的痛苦转移到其他女性身上,延续着新一代,继续灌输“父权至上”的病态思想,成为父权制度的帮凶。奥芙弗雷德的母亲是第二次极端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着极强的女权意识,是否成为母亲掌握在自己手上。她对奥芙弗雷德的影响极强,以至于奥芙弗雷德通过对母亲的回忆来强化自己反抗父权的决心。但作为母亲,她疏于对女儿的陪伴与爱护。以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使女们在基列国成立之前和之后对两性关系的认识逐渐清晰,她们既反感女权主义者的行为,又在失去权利时感到愤然。在遭受长期侮辱与压迫的情况中,对下一代的担忧以及作为母亲的责任感,使得她们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拒绝成为“行走的子宫”,开始反抗基列(父权)政治。阿特伍德通过第一人称倒叙的叙事艺术展现生态恶化下的三类母亲形象,描述了母亲这一角色在思想伦理道德压迫下的艰难。母亲这一群体不是局限在父权社会的刻板印象中,母亲们在面对自我与母亲身份时充满矛盾。《使女的故事》还原了母亲的真实面目,使母亲形象从文化符号回到本真状态,力求能给现实母亲以最公正的对待。
aFaurholt, Gry. Deny None of It: A Biocultural Reading of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M].Evolutionary Studies in Imaginative Culture, 2021:13.
b张冬梅、傅俊:《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144页。
c张继英:《〈使女的故事〉的女性主义叙事技巧》,《文学教育》2009年第10期,第28页。
dKaplan, E. Ann. Motherhood and Representation: The mother in popular culture and Melodrama[M].London:Routledge,1992:3.
e袁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学女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fghjklnoq! 8 s@ 2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陈小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第145页,第145页,第139页,第140页,第52页,第138页,第145页,第134页,第43页,第72页,第209页。
iDe Beauvoir, Simone. The Second Sex [M].London: Lowe and Brydone, 1953.
m姜麟:《叙述声音、叙述视角中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卡洛林·莫当〉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4页。
p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第4页。
tWalters, Suzanna Danuta. Lives Together / Worlds Apart: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Popular Cultur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8.
@ 1 Zerilli, Linda M.G. A Process without a Subject: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ulia Kristeva on Maternity[M].British and Canadian Studies, 1992:123.
作 者: 昝天怡?,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当代戏剧。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