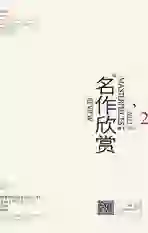折射的空间
2022-02-28雷昭利
摘 要:作为第三代诗人的张枣,无论是从诗歌创作来看,还是就其诗学研究而言,对现代汉语诗歌都有着特殊贡献。当前国内外的张枣诗歌研究对其成名作《镜中》的讨论较多,但大部分只着眼于对语言风格、古典性、抒情主体及诗歌主题的分析,而很少探究此诗结构的微妙之处。通过文本细读和意象分析发现,全诗以镜子为核心建立了对称性结构,将所有的内在意象都嵌入了这个镜像体系,彼此相互交织纠缠,呈现出一个立体的诗境空间,丰富了汉语新诗的文本建构样式。
关键词:《镜中》 对称结构 新诗
张枣(1962—2010),中国当代诗人,学者和诗歌翻译家。代表作有《镜中》《何人斯》《卡夫卡致菲丽丝》《与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等,出版有诗集《春秋来信》《张枣的诗》,随笔集《张枣随笔选》,学术著作及译作若干。国外早已有张枣诗歌的翻译作品,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于1999年出版了张枣的诗集《春秋来信》的德译本;澳大利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西敏于21世纪初翻译了张枣后期的一些诗歌,如《哀歌》《木兰树》等;法国译者兼诗人菲奥娜·施·罗琳2015年出版了《镜中》一书,汇编了她关于张枣诗歌的英文译作,如《镜中》《灯笼镇》等。
国内学者对《镜中》的分析多从抒情主体、戏剧化、轻与重、现代性与古典性以及知音观念等角度解读此诗的诗学价值,如姚亮(2012)探析了诗中的轻与重是如何得到平衡的,周东升(2019)则从“皇帝”一词出发,对《镜中》的抒情主体进行了辨析与反思。而聚焦全诗结构进行诗学阐释的文章为数不多,有代表性的如:王东东(2019)指出本诗以镜子为中心的对称语言结构,但对诗歌结构所呈现的对称性特征阐释得并不完整和系统;李倩冉(2020)对开头和结尾“构成相框式的环形结构”进行了探讨,但仅限于首尾结构。国外学者大多集中于张枣诗歌的对话性结构、诗歌互文性、文化差异、现代性书写等方面的探讨,对《镜中》的诗学分析关注不多。如德国学者苏姗娜·格丝(2000)分析了《今年的云雀》一诗与德语诗人策兰、布莱希特之间的互文性,以及其中的对话结构和文化差异。美国华裔学者奚密在《论现代汉诗的环形结构》(2008)一文中,举例分析了从新诗源头到新生代派现代汉语诗歌的环形结构。此文虽没有将张枣的诗歌作为例证,但是据文本分析可以看出,《镜中》同样具有此结构特征。美国学者约翰·泰勒在《安提奥赫评论》发表的《汉语新诗的幽秘》(The Intricacies of the New Chinese Poetry)一文中指出张枣对新诗艺的引入十分突出,体现了中西诗学的交流与互动(2013)。因此,通过对国内外张枣诗歌研究的梳理发现,此前研究虽有涉及《镜中》的对称性结构及回环性特征,但还未结合诗歌文本做出细致和完整的阐释,并且很少注意到全诗对称交织的立体空间结构。本文将采用文本细读和意象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中西诗歌特点,分析此诗的对称性结构和诗境空间。
一、以镜为核心的对称框架
《镜中》一诗是张枣的成名作,也是其最广为流传的作品。提到“镜子”这个意象,“虚幻、对称、 延伸、梦”等一系列词语就会蹦入我们的脑海。张枣选择“镜子”这个意象,本身就包含着对称性。全诗以镜子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对称框架,将所有内在意象都嵌入了一个镜像体系。诗人也主动挑选那些具有对称性的意象来营造这样的镜像感。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镜,景也。”镜子的主要功能是反映,只要有充足的光线,物质实体都能在镜子中投射出来。基于它的特点,古代产生了特定的象征义。《庄子·德充符》里写道:“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a鉴指的就是镜子,虽然明面上是在说镜,实际上却引申出自省、净身的含义。与此同时,从纳西索斯的水中镜到拉康的镜像理論,西方文化也同样意识到镜子的特质为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审视自我的机会。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不仅会看到自我的外部形象,还可能会暂时把镜中的“我”当成意识“我”的肉身。人可以与镜中“我”展开对话,进行自我交谈,这个时候,“我”既是主体又是他者(镜中的“我”是被观察的他者),二者经由镜子进行了分离,形成一种对称性。实际上,镜中“我”本就是虚幻的投影,只不过暂时被意识“我”捕捉,被当成是另一个物质实体。
那么诗人镜中呈现的主体是什么呢?纵观全诗,第一人称抒情主体并没有明确出现,只能在字句中隐隐知道“我”的存在,比如“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看她骑马归来”等,人称转换技巧的使用让全诗有了阐释抒情主体的更多可能性。站在不同诠释角度,抒情主体可能就是“她”,或者就是“皇帝”,或者是“我”“她”“皇帝”三者同时共存的情况。诗意的空幻虚泛给阐释带来了麻烦,但也因此扩展了其呈现的宇宙。此诗抒情主体的探寻有多种解读,因偏离本文主旨便不再赘述。
诗名《镜中》提纲挈领地点出了“镜子”意象的重要性以及整体的诗境空间。以镜为核心的对称框架使全诗形成了一个光线投射的场域,目光/光线的投射也就是欲望的投射,这是一个情感、心理和意识的空间。b镜子的世界中,时间、空间、情感、心理、意识、现实、梦幻都是彼此对话和联结的。无论是用眼睛“看”还是描写“窗外”之景,都是与镜子同等功效的替代物,反映了事物的两个维度。从整体看,这首短诗巧妙地抓住了镜子的特性,把所有的意象、叙事、情感都置于镜中折射的空间进行交织与纠缠,形成一个复杂幽深、瑰丽精巧的诗境空间。
二、解析对称结构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后悔本是一种抽象情绪,给人一种沉重感,但轻薄的梅花以有形承载了无形,以轻感化解了重感。其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不同之处在于,李煜将自身的愁苦悲恨化为滔滔春水,冲决而出,绵延不绝,张枣却将这悔意化为梅花的坠落,轻盈飘逸,成泥作尘,最后风过无痕,杳无踪迹。前者是情绪的宣发,后者则是情绪的隐忍,所以才会以轻化重,使悔与愁更隐秘,同时也更深沉。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结尾是对开头两句的往复,形成结构上的闭环,“建立了一种空间结构感和诗的整体性”c。据奚密的研究,这种结构在现代新诗中较为常见,且“具有空间感、自我循环、挫折感的审美效果”d。环形结构的使用,与对称性结构交相辉映,加深了此诗的空间感。从“落了下来”到“落满南山”,这是悔意的加深、隐忍的释放。梅花和南山意象的选择构建了诗境的古典感,并且梅与悔在音形上的相近,剥离了其固有的语义,完成与悔意的联结。梅花和南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都具有隐逸传统,象征着高洁脱俗的品质。比如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辞官返深林;林逋以梅为妻,隐居西湖。“环形结构的自我回旋在体现西西弗斯式困境的无法解决时,也以闭合的方式对困境进行了美学上的封存、搁置和取消。”e据说张枣在1984年写《镜中》的时候,还在攻读英美文学的硕士学位,当时意气风发的他也许面临着某种困境,而梅花和南山隐含的品质则是他对彼此困境的回应与收束。
除了开头结尾构成“相框式的环形结构”,整首诗以镜子为核心建立了对称性结构。从诗中两次直接写“看”的内容可以发现,观者眼中的“她”和外部的“她”构成了一个对称性,这个对称是经由观者的眼睛来实现的,眼睛就是镜子。“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这里也有“一岸”与“另一岸”的对称性,同时暗含着观者与“她者”在空间上的隔离。并且由于所见的“她”一定是背对着游过去的,和《诗经·蒹葭》篇的伊人一样,音容体貌皆无,但不同的是,“她”主动地线性移远,而“伊人”的行踪飘忽不定。她游到河的另一岸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意境上也是相似的,事实被虚化,空间上的距离渲染了一种思忆想象的情景,营造出一种朦朦胧胧的虚幻感,这和镜像虚幻的本质是统一的。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述到“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水一方”是企慕的象征,结合张枣写此诗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环境,这个“她”可能是青春时追求的美好爱情或某种反抗危险现实的理想。明显可以看出,此处的对称关系体现了欲望的投射,而诗人将抒情主体的心理状态交由读者来想象与补充,构思独特且微妙。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不如看她骑马归来”,观者在始发地看“她”从目的地骑马回来,和前面“看她游到河的另一岸”拉大空间距离正好相反,距离感缓慢消逝,且非常自然地伴随着对她神态动作的正面描写(“面颊温暖”“羞涩”“回答”)。与前面有所不同,归来的“她”是与观者眼中的“她”面对面进行对称的,这和我们面对镜子时的状态一致。“登上一株松木梯子”,这里是空间在高度上的延展与回应,和“梅花便落了下来”构成垂直维度的向上运动与向下运动,经由中间河面的对称与相嵌。“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镜中常坐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平时坐在镜子前的位置,这里没有直接表达成“让她坐在镜子前”,而是陌生化为坐到镜中的虚位,符合全诗对称性的建构。“望着窗外”,窗这个意象也具有典型的对称性。正如林徽因在《窗子以外》里感叹,书斋生活与外部世界几乎是隔绝的,“隔着一个窗子,你能了解多少外面的世界”f,窗子可能意味着隔离。而望向窗外的动作便意味着原有视角的打破与扩大,在这个过程中,窗内的主体感知与窗外的客体物像经由窗户形成某种统一与融合,完善了主体对外在世界的认识。这和我们面对镜子,完善对自我形象的感知是同样的心理过程,也是一种虚与实的对称。望向窗外的动作也确实带来了视觉上的扩大,“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此时悔意更满,惆怅更浓。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固然”在这里是一个让步转折连接词(“不如”前可以加上“但/但是”),先承认某种公认的观点或刚发表的看法,然后提出新议论来表明说话者的真正意图。诗中首先承认了危险的事是美丽的,随后又提出“不如看她骑马归来……回答着皇帝”,做出判断的抒情主体在向我们表明后者的行为比前者更好。值得思考的是:此抒情主体为什么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好?我们先来思考前者:危险的事为什么美丽?换言之,美丽的事为什么危险?如果成为理想自我是一件美丽的事的话,逃离舒适圈是危险的;如果追求自由是一件美丽的事的话,打破枷锁桎梏是危险的;如果追求真理是一件美丽的事的话,与主流观点相对立是危险的。美丽与危险往往是一对共生体,人总要承担风险才能同时享有美丽,这就是美丽的代价。抒情主体并没有选择冒风险,而是决定去看“她”骑马归来,面色红润,身体温热,低着头,娇羞地回答着皇帝的话。这个场景中“骑马”和“皇帝”意象的出现,让笔者联想到皇帝带着皇室成员出门狩猎时的情景,一下子增添了几分古典感。“皇帝”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人都必须对其俯首称臣,而羞涩的“她”可能是他的一个妃嫔,表面上看,这是温馨的充满爱意的特写镜头,让人体会到美好而青涩的感情。实际上,这可能寄托了此抒情主体对理想自我的向往(成为自己的皇帝)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但这也是危险又美丽的事情。为什么后者还是更好?前文提到,“看她骑马归来……回答着皇帝”,“看”这个动作本身意味着观者与“她”以及“皇帝”的分离,以及眼睛之镜呈现的虚幻性,这里只不过是抒情主体的想象罢了,比起真正去做这些危险而又美丽的事情,不如在脑海里幻想一下就能实现,这样起码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岂不更好?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或许全诗正是在后悔没有真正去做这些美丽而危险的事情。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永远”这个词可能想要启示我们,前面讲述的“她”其实一直存在于镜中那个被看的、虚幻的世界里。最后“让她回到镜中常坐的地方”,“常坐”也表明了虚幻的世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詩歌到这里,以镜子作为谜底,已然是尾声。无论怎么后悔,怎么想象,怎么追忆,“她”的一切都只是昔日幻影罢了。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发展状态,张枣也许是通过这两句诗反映了汉语诗歌传统与欧美现代诗的镜像关系,而他的选择是“回到镜中常坐的地方”,主张对古典的回归与融合。
三、结语
第三代诗人群体中,张枣是为数不多掌握多门外语的创作者,他时常阅读和翻译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文学作品。所以对他而言,“用汉语写作必定意味着去与非汉语文化和语言进行辨析。这类辨析直接作用于他诗歌构图的形式和结构上”g。虽然《镜中》是其早期作品,但其中流露出的中西融合性已初见端倪。西方诗歌的诗境空间受到数学几何学的影响,具有立体性,而汉语诗境空间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混沌浑圆。h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镜中搭建的对称空间具有鲜明的立体性,所有意象支撑起了这个棱角分明的镜像体系,反映了西方诗歌对张枣创作的影响。
张枣自觉地将中国古典与现代性相融合,无疑是百年新诗历程中最具开创性的诗人之一。《镜中》这首成名作,已微微折射出他的某些诗歌技艺,如人称转换、空间构建等。全诗的对称性结构以镜为核心,眼、窗、梯子及其他同等功效的意象贯穿其中,交织纠缠,最后首尾闭合,构建了一个分明立体的诗境空间。这体现了张枣对诗歌结构的精妙设计,也为新诗写作者提供了独特的灵感构思。对于读者而言,这无疑也是一场极致的汉语审美体验。通过研究他的早期成名作,我们得以窥见其关于如何扬弃西方现代诗写作经验、如何展现汉语古典美学因素的思考与探索,从而助力汉语新诗在新时代的良性发展。
(本文得到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吴群涛老师指导,谨此致谢)
a〔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中华国学文库 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2页。
b王东东:《语言与文化:诗歌细读的两面——以张枣〈镜中〉为中心》,《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40—46页。
cd奚密、宋炳辉:《论现代汉诗的环形结构》,《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第135—148页。
e李倩冉:《被悬置的主体——论张枣》,《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第145—152页。
f林徽因著、梁从诫编:《林徽因集 诗歌·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期,第131页。
g〔德〕顾彬(Wolfgang Kubin):《综合的心智——张枣诗集〈春秋来信〉译后记》,《作家》1999年第9期,第39—41页。
h兰甜:《论张枣诗歌中的“空间”》,云南师范大学2015年学位论文。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国际比较视域下鲍勃·迪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批准号:19B559)及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帕蒂·史密斯摇滚诗歌对朋克运动的影响”(批准号:17YBA388)的阶段成果
作 者: 雷昭利,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