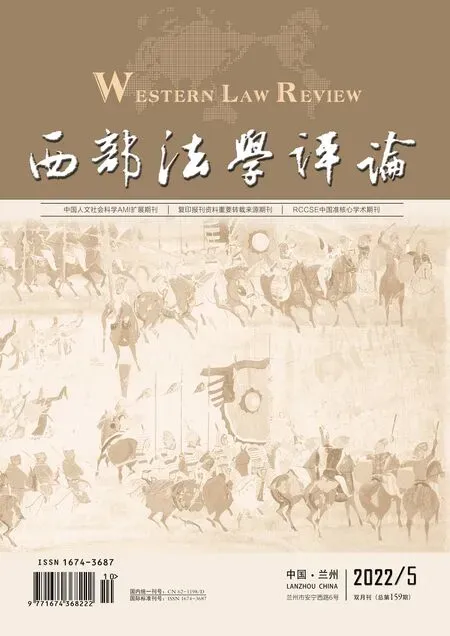《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适用研究
2022-02-26谭宇航
谭宇航
一、问题的提出
规制“混淆行为”一直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规则之一(1)《巴黎公约》第10条之2—(3): “下列各项应特别予以禁止:(i)具有采用任何手段对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产生混淆性质的一切行为。”,在我国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混淆条款”专门规制,“混淆条款”经2017年修法后由封闭式条款转变成开放式条款,对可受保护的商业标识类型及构成混淆的情形均作出开放性规定。从保持“混淆条款”适用有效性与一致性看,如何理解受“混淆条款”保护的商业标识类型、如何认定“混淆条款”规制的行为、如何适用第四项兜底条款,具有探讨意义。从协调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看,“混淆条款”与《商标法》均发挥着保护商业标识功能,我国《商标法》几经修改,由“注册制”逐渐转轨为“注册与使用混合制”(2)一个突出例子是《商标法》第4条:“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如何澄清它们的关系,亦需要关注。尽管我国实务界与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作出诸多回应,但它们大多数关注“混淆条款”的个别部分,譬如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语境下的“有一定影响力”(3)参见刘继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定影响”的语义澄清与意义验证》,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辨析“混淆条款”继续保护注册商标的进路(4)参见刘维:《论混淆使用注册商标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制》,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7期。,探讨作品标题、自然人姓名、作品元素的保护等(5)参见杜颖:《广告语的商业标识功能及其法律保护》,载《法学》2018年第2期;孔祥俊:《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及其保护——兼评“乔丹商标案”和相关司法解释》,载《法学》2018年第3期;彭学龙:《作品名称的多重功能与多元保护——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3项》,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未全面研究“混淆条款”各类适用问题,亦未深入探讨“混淆条款”与《商标法》在保护商业标识上的异同性。本文认为,研究需遵循两个基本脉络:既要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内部确立“混淆条款”的基本适用思路,也要从外部比较《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制度关系。
从内部看,“混淆条款”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部分,遵循《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的适用思路,需分层判断“原告存在值得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实施损害该竞争利益的行为—被告损害行为具有不正当性”(6)黄武双、谭宇航:《不正当竞争判断标准研究》,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10期。,并有如下三点基本认识:(1)“混淆条款”并非宽泛保护各类竞争利益,而仅保护原告通过商业标识反映的竞争利益。原告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竞争利益,它们不由“混淆条款”保护。(2)“混淆条款”规制被告利用标识而产生混淆可能性的行为。主流观点对混淆持宽泛理解,不仅包括来源混淆,也包括关联、赞助混淆,不仅包括售中混淆,也包括售前、售后混淆。(7)参见彭学龙:《商标混淆类型分析与我国商标侵权制度的完善》,载《法学》2008年第5期;邓宏光:《商标混淆理论的扩张》,载《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10期。若被告行为不属于任何一种混淆,即便该行为损害或利用原告声誉,亦不受“混淆条款”规制。(3)被告行为的不正当性来自于其具有混淆可能性,只要存在该结果,即可认为行为损害了原告竞争利益、相关消费者利益。也需合理确定规制范围,避免对被告及其他同类经营者使用商业标识造成不当阻碍。
从外部看,规制不正当竞争与保护商业标识的规范长久以来具有密切关联,前者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制止各类侵夺或损害他人商誉的不公平行为,后者则专门通过保护某些商业标识而实现保护其所承载的商誉的目标。(8)Se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Unfair Competition 3d, 1995, section 9 Definitions of Trademark and Service Mark, d. Doctrinal development.二者在认定标识近似性、商品或服务类别类似性、混淆可能性、合法抗辩事由上更有着不少共通规则。两者亦存在区别:《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竞争法,旨在规制行为而非保护权利,第1条明确其根本目标是打击各类损害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混淆条款”规制的范围相较更广,未注册商标、企业字号、商业外观等各类商业标识均可能获得保护,关键是考察市场主体是否实施了商业标识混淆行为。《商标法》是典型的权利法,以“注册制”作为法律基石之一,第2至5章包含大量关于商标注册的管理性规定,籍此保证商标权的稳定性与清晰性。《商标法》亦日益将商标使用作为赋予商标权、确定商标权强度的关键一环,强调商标的生命在于使用,保护商标不是保护符号而是保护商誉,“商标的实际使用是获得商标权的实质要件。”(9)邓宏光:《我们凭什么取得商标权——商标权取得模式的中间道路》,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5期。总之,《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均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以保障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作为具体目标,但在实现路径上,前者落脚于维护商业道德、促进公平竞争,后者落脚于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权,这种异同性将具体体现到两法保护商业标识、规制混淆行为的路径上。
在这种内部与外部视角结合的基础上,本文将分析“混淆条款”的适用思路,围绕可受保护的商业标识、混淆行为的认定、兜底条款的适用展开分析。
二、“混淆条款”保护的商业标识
“混淆条款”第一至三项分别列举可受保护的商业标识类型。直观上,第一项与商品或服务相关,第二项与主体相关,第三项与互联网相关。2017年修法时,不少观点对“混淆条款”的类型化划分提出改进意见。(10)参见徐升权:《〈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稿中的商业标识条款评析》,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5期;陈丽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研究——以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8期。尽管这些观点有助于法律规范清晰化,但商业标识的类型化既不存在最好情形,也不存在穷尽情形,这是因为市场中的商业标识从不同角度看将有不同属性,并会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而发生类型增减,采取任何规范用语均较难准确、完整地反映现实生活。(11)譬如近些年新产生的商业标识便包括APP名称、APP图标、电子游戏中的游戏元素等。因此,应将第一至三项的类型作为示例性规范,以保持《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的灵活性与全面性,它不采取“法律赋权→主体有权”的演进逻辑,不能因某类型商业标识未被明确列举而当然排除出保护范畴。(12)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各版本草案采取的用语看,亦能得出立法者对可受保护的商业标识类型持宽松的态度,修改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
应从反方向出发,讨论“混淆条款”是否不保护某种商业标识——只要不属于不保护的情形,均有可能获得保护。违反法律或侵害他人权益的商业标识明显无法获得保护,另有如下三类需探讨:(1)因其他法律已经提供保护,“混淆条款”不应提供重复保护;(2)因商业标识对展开竞争有重要意义,“混淆条款”提供保护应谨慎;(3)因商业标识未产生“有一定影响力”,“混淆条款”暂时无法提供保护。
(一)“混淆条款”提供保护不应重复
有些商业标识因可获得其他法律保护,不应再由“混淆条款”提供重复保护。“混淆条款”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类型化条款,体现着该法的优缺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管不管法”“杂烩法”(13)参见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定位》,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优点是可规范各类市场行为,实用性较强,缺点是在多数情况下要求个案权衡,模糊性较高。因此,若其他法已对商业标识有相对明确的规定,法院完全可引导原被告在该法下围绕相关争议焦点展开辩论,没有必要再叠床架屋地适用在利益边界界定、应受规制行为认定上更不清晰的“混淆条款”,这种“继续保护”既扩大自由裁量权,也浪费司法资源,“类型化条款可能引发误选和寻租两类特殊的司法成本”。(14)蒋舸:《〈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条款的反思与解释——以类型化原理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尽管作者的语境是批判“互联网专条”,但类型化条款不当制定或适用有着共通原理。相反,若其他法律无提供保护,无论是该法在特定情形下不提供保护,抑或是该法因立法局限性而未提供保护,“混淆条款”则有可能提供保护,再按自身规则判断是否实际应提供保护。是否构成重复保护,值得探讨如下两方面。
1.“混淆条款”与《商标法》的关系
《商标法》对注册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权利产生、权利边界、侵权认定均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其法律条文、司法解释、裁判案件远多于“混淆条款”。《商标法》第57条、第13条禁止他人在相同或近似类别上使用相同或近似注册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对已注册驰名商标则更提供跨类保护。优先适用《商标法》,制度清晰性更强、成本更低。对地理标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这类兼具私有与公共属性标识的保护尤为如此,其所需求的制度不仅是“应否禁止某些主体使用标识”,更是需要建立起一整套“标识注册、使用、管理、维权”制度,以保证真正具有相应技艺或来自相关地域的各市场主体可使用标识反映、维护它们内部共有的商誉。“混淆条款”作为行为禁止性规定,在回应这类问题时显然存在制度供给不足。
应注意在上述原则之外,注册商标(及未注册驰名商标,下同)保护有一定复杂性。由《商标法》处理各类在市场中以混淆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混淆条款”不处理涉及注册商标的混淆行为,这当然是理想的制度构建。但现实却不理想:因受旧“混淆条款”第1项及《商标法》第58条影响,两法均保护注册商标,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年版《〈反不正当竞争法〉解释》第13条仍采用该观点。故澄清“混淆条款”不对注册商标提供重复保护,应考虑这种现实环境。有观点认为:“《反法》第6条是专为制止商业标识仿冒的混淆条款,无论注册商标还是未注册商标,只要以致人混淆的方式实施商业标识的仿冒,均可纳入该条的范围。”(15)刘维:《论混淆使用注册商标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制》,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7期。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在于抓住了“混淆条款”的本质,但欠缺从“混淆条款”与《商标法》的互动关系看待问题。本文认为,“混淆条款”与《商标法》提供的保护具有进退互补关系,若《商标法》扩张,“混淆条款”便应相应地收缩,相反亦然——在保证法律规制的不重叠与完整性的情况下,无所谓必须交由“混淆条款”抑或《商标法》保护。典型是市场主体将他人商标文字作为企业字号注册企业名称的,若法院认为这种注册行为本身或其后必然伴随的该市场主体使用该企业名称行为,属于《商标法》第48条“商标使用”并具有混淆可能性,则可适用《商标法》第57条禁止。相反,若法院认为仅企业名称注册行为本身或非突出使用企业名称行为均不属于《商标法》第48条“商标使用”,但这些行为仍具有混淆可能性,则可适用《商标法》第58条并转致“混淆条款”规制。司法实践认为,被告将企业名称突出使用的行为构成《商标法》第57条意义上的商标侵权(16)参见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有限公司诉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晓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29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未将企业名称突出使用但仍具有混淆可能性的行为构成《商标法》第58条与“混淆条款”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17)参见百威(中国)销售有限公司诉江西蓝色柔情啤酒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17015号民事判决书。,并分别以此为基础,在原告商标知名度较高、被告有明显攀附意图的情形下,要求被告变更其企业名称。这种区分保护注册商标的法律依据清晰、《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进退互补关系明确、规制范围完整,可以沿用。由此可推论,那种认为“混淆条款”完全不应处理侵害注册商标行为的观点,其成立的必然前提是:将所有在商业中使用注册商标、具有混淆可能性的行为认作商标侵权,用《商标法》第57条规制。否则,即便市场主体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具有混淆可能性,但《商标法》未将这些行为纳入规制范围,“混淆条款”亦不处理任何侵害注册商标的行为——法律漏洞便出现了,法律规制并不完整。
总之,对于这种因《商标法》适用有限性而导致的规制真空,“混淆条款”为维持商业标识已形成的公众稳定认识及市场秩序而禁止混淆,为注册商标继续提供保护,完全具有正当性,不与《商标法》冲突,反而对《商标法》作恰当补充。各国均不排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继续保护商标,WIPO《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第2条第2项规定:“下列内容尤其可能被造成混淆:(i)商标,无论注册与否……由于在受混淆影响的消费者看来,商标是否注册并不相关,因此依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保护应对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一视同仁。”(18)《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条款和注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7年发布。美国长期将反不正当竞争规定与商标保护混同适用,在《兰姆法》第43条(a)中为未注册商标、商业名称、商业外观提供与注册商标同等的保护,籍此禁止一切有混淆可能性的行为。欧盟《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第6条第2项规定:“如果在实际情况下,考虑到商业行为的所有特征和情况,它导致或可能导致普通消费者作出他在其他情况下不会作出的交易决定,并且它涉及……与竞争对手的任何产品、商标、商号或其他显著标志的混淆,也应被认为具有混淆性。”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2条也有类似规定。(19)《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2条:“本法中使用的‘不正当竞争’一词指以下任何一种:(i)通过使用商品或业务标识(指属于一家企业的商品的名称、商号、商标、标记、容器或包装,或一个人的商品或业务的任何其他标识)而与他人的商品或业务造成混淆的行为。”
2.“混淆条款”与《民法典》的关系
《民法典》第1012条至第1017条保护自然人姓名权及法人、非法人组织名称权,第1018至第1023条保护自然人肖像权,“混淆条款”在满足特定条件时亦保护姓名、肖像,但两者保护依据、路径不同,不构成重复保护。
《民法典》主要是从人格权角度保护这些客体,只要原告能证明被控行为使用的姓名、肖像起到指代原告的作用,所有人均能获得平等保护,免于人格受到现实或潜在侵害,“基于人格权,权利人对其人格利益享有支配的权能,并可以对抗第三人,只要权利人对其人格利益的圆满支配状态受到了不法侵害,其都有权提出相关请求,以恢复此种圆满支配状态。”(20)王利明:《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混淆条款”则强调姓名、肖像作为商业标识指代来源、表征商誉等属性,不是在它们考虑有无承载市场主体的人格利益,更不是保护姓名、肖像本身,原告即便能证明存在指代关系,但若这些商业标识指代关系弱、承载商誉少,“混淆条款”的保护程度便较低,不倾向于认定存在混淆可能性。譬如将不知名的自然人肖像用于广告宣传,这种行为属于“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受《民法典》第1019条规制。但该肖像并不具有表彰商品或服务来源或商誉的作用,他人使用该肖像不会使相关公众产生错误的来源、关联、赞助关系认识,故不受“混淆条款”规制。
《民法典》保护人格而涵盖对人格经济利益的保护,“混淆条款”保护商业标识则基于纯粹的经济利益:《民法典》保护人格尊严、承认人有权自决其事,“混淆条款”保护完全基于姓名、肖像的指代来源、表彰商誉功能。人格与人相生相存、自然产生,指代功能则产生于市场主体稳定、良好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混淆条款”更关注姓名、肖像的市场使用、相关公众认知情况。这种差异可对比《民法典》第1012条对姓名的保护与第1017条对笔名、艺名的保护发现:前者对姓名的保护仅要求“自己的”“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后者则增加“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立法者正是考虑到笔名、艺名等“可能会带来巨大利润”,与各民事主体均享有的“公民在公安户籍登记机关登记的姓名,法人、非法人组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企业名称”不同,故增加了与“混淆条款”高度近似的文字表述,并指出后者法律适用“参考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规定进行理解”。(21)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http://gfhaif09ba5fb70664558h00xcuwwuuncq6vq5.fcxb.oca.swupl.edu.cn/lib/twsy/twsycontent.aspx?gid=A290592&tiao=1017,2022年6月30日访问。
由此可见,那种坚持“平等保护”的观点认为同样是姓名、肖像,一个使用者无义务避让另一个使用者,显然不正确——“混淆条款”保护姓名、肖像是为了激励市场主体辛勤投入、维护相关公众稳定认识,而非为了保护人格。“混淆条款”承认与尊重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对各类商业标识的保护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只提供与它们所承载商誉对等的保护,弱者当然有义务合理避让强者。(22)至于是否存在一般性的“标识型人格权”,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但可以肯定“混淆条款”不以这种或有权利为基础。“混淆条款”与《民法典》人格权相关条款尽管均涉及姓名、肖像保护,但它们从不同路径出发,“姓名的商品化权益之所以应作为一种不同于姓名权和人格权的独立财产权益,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源于两种保护的根本差异,以及如何处置更能够实现制度配置的优化。”(23)孔祥俊:《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及其保护——兼评“乔丹商标案”和相关司法解释》,载《法学》2018年第3期。
(二)“混淆条款”提供保护不应损害竞争
“混淆条款”本身未规定不予保护的商业标识类型,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将通用性商业标识、描述性商业标识、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要的形状及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商业标识排除出保护范围,籍此为其他市场主体保留自由与有效竞争的空间。其表述基本与《商标法》第11条、第12条一致。缺乏显著特征应如何理解?采取与《商标法》第11条、第12条一致的理解是恰当的:为在排除保护那些因有其他功能而使指代功能不易发挥的商业标识。原告为获得保护,需提供更充分证据证明商业标识实际发挥指代功能(至于指代功能的强度则是有一定影响力因素的适用问题)。
不少商业标识具有其他功能:商品包装、装潢具有美学功能,巧克力因包装好看而吸引消费者;界面分区具有方便用户操作功能,微信划分四个分区能使用户快捷浏览聊天、好友、朋友圈、个人信息;作品名称具有描述作品主题主旨功能,“傅雷家书”指傅雷与其家人的往来书信。它们是否缺乏显著特征?应以市场主体使用其他替代形式展开“有效竞争”的难易程度为判断标准——不要求替代设计为竞争所必须,不是达到不存在替代设计的程度,而是要避免“保护将会使竞争对手遭遇与声誉无关的重大竞争劣势”。(24)TrafFix Devices, Inc. v. Marketing Displays, Inc., 532 U.S. 23, at 32—33 (U.S. 2001).美国最高法院在该案推翻了“竞争必要”标准,采取了更宽松的标准认定功能性设计。竞争对手面临的劣势越大、展开有效竞争的难度越大,越可认定商业标识缺乏显著特征,原告负有越重责任证明商业标识实际具有指代功能。换言之,“混淆条款”仅规制市场主体可合理避免的来源混淆,不能因保护商业标识而产生阻碍竞争的不利后果。“产品的技术特征适于表明产品来源,而该技术特征又为生产模仿产品所必需的,则对这种来源欺骗必须予以容忍,不能适用第4条第9项a。如果模仿者能够采取措施避免来源欺骗(可能性),并且该措施是模仿者能够合理承受的(适当性),则该来源欺骗是可避免的。来源欺骗是否可以避免,需要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25)范长军:《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是否存在替代形式是程度的权衡,具体应从“成本—效益”两方面出发,既要考察市场主体使用替代形式的成本,分析是否存在现实可得的替代形式及数量、开发替代形式的各类投入及难度等,也要考察市场主体使用替代形式的效益,分析替代形式是否同等有效可靠、是否满足市场特定环境与需求等,“决定是否属于功能性的关键是,那些满足实用需求的替代设计或提供类似优势的替代设计的可得程度。”(26)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Unfair Competition 3d, 1995, section 17 Functional Designs, b. Functionality.一般而言可分类探讨:对于具有美感功能的商业标识,可更容易认为存在替代形式,因为美是丰富的,不存在唯一绝对认识。对于具有技术功能的商业标识,是否存在替代设计则需作更多权衡,考察该设计是否使产品得以运行或使产品更便宜、更快、更轻、更强劲等,因为作出技术上同等、消费者认可的替代形式受客观条件限制。(27)对于曾获得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的设计,有观点认为应直接排除其作为商业标识受到保护的可能。参见梁志文:《论设计保护的功能性原则》,载《现代法学》2019年第5期。我国“混淆条款”与《商标法》立法与司法尚无该类规则。本文认为,“混淆条款”的根本目的是要规制“混淆行为”,在该设计存在诸多可用替代设计、设计因长期使用与特定商品或主体建立了稳定联系、他人完全使用同样设计且未标注清晰区别性标识时,显然存在值得规制、符合利益平衡的“混淆行为”,即在一个非常窄的情形仍可适用“混淆条款”。对于描述商品或服务属性的商业标识,则需要结合词汇含义、公众认识、商品或服务销售方式与渠道等认定替代用语是否合理可得。应结合商业标识的整体情况判断:若具有显著特征的部分仅占商业标识的轻微一部分,整体仍有可能缺乏显著特征;若这种显著特征部分在商业标识中相当突出,是相关公众关注的焦点,则可使整体具有显著特征。另外,可结合被告所表现出来的使用意图判断商业标识是否缺乏显著特征:若被告使用该商业标识显然是为了攀附商业标识所承载的商誉,错误地向公众表示存在来源、赞助、关联关系,则可推断商业标识具有显著特征;若原告仅能证明被告有意模仿,则不能得出前述推论,因为这种模仿可能是基于商业标识的美感功能、技术功能、第一含义进行。总之,以上规则与《商标法》相关规则保持一致。
(三)“混淆条款”仅应保护“有一定影响力”商业标识
部分商业标识即便确实被经营者用于发挥指代功能,但它们不一定均能使消费者实际识别出特定产品或服务来源、特定市场主体:“傅雷家书”作为汇编傅雷与其家庭成员通信的作品标题,因长期有不同汇编者、出版社合法出版,未与特定汇编者或出版社建立稳定联系。(28)参见应急管理出版社有限公司与傅敏、合肥三原图书出版服务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终955号民事判决书。“泥人张”因创始人的徒弟及后代从业者越来越多,已无法在这些泥塑从业者中识别出特定企业或个人。(29)参见天津市泥人张世家绘塑老作坊、张宇诉陈毅谦等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及虚假宣传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0016号民事判决书。
“混淆条款”与《商标法》考量商业标识影响力的立场不同。有观点认为:“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仅仅是一种法益,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其赋予任何权利,只有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才能予以调整……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的特殊性在于,它本质上是未注册商标。”(30)王太平、袁振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商业标识保护制度之评析》,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5期。该观点注意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是权利法,但随后简单地把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标识理解成未注册商标,未继续分析“混淆条款”与《商标法》深层性差异。本文认为,根源在于两法保护立场不同:“混淆条款”要求受保护的商业标识“有一定影响力”,是为了提供与商业标识指代功能强度对等的保护,保护需要以商业标识实际获得的影响力作为基础——是彻头彻尾的使用制。《商标法》仅考虑待注册商标有无“固有显著性”、申请人有无真实使用意图,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申请人便能获得注册商标权,在相同或类似类别上排除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是以注册制为基石。“混淆条款”是在市场环境实际形成后,即商誉已在该商业标识上积累、经营者竞争优势已产生、消费者对该商业标识指代功能已产生稳定认识后,提供相应法律保护,承认这种市场环境。“混淆条款”偏向于“激励支援型”规则,目标是维护如下市场秩序:市场主体应恰当使用各类商业标识,以反映属于该市场主体或该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品的商誉,不能以消费者混淆的方式使用其它商业标识,破坏消费者对各类商业标识所具备指代关系的既成认识。《商标法》更多包含创造市场环境的功能,市场主体只要符合注册条件便可赋予边界相对清晰的商标权,便有权独占使用商业标识,随后通过勤勉经营而使商业标识实际发挥指代功能,商标权的范围则再应根据市场主体实际使用情况而扩大或收窄。《商标法》偏向于“激励创造型”规则,包括规范商标注册秩序、管理商标注册活动、保护注册商标权等诸多目标。“与商标侵权构成相比较,不难发现不正当竞争重在对行为本身的价值和法律评判,商标法重在考察被告的使用是否落入商标权人的财产专用权控制范围。”(31)李士林:《商业标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整——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6 条》,载《法律科学》2019年第6期。
因存在上述立场差异,“混淆条款”判断商业标识是否达到“有一定影响力”的思路亦应存在差异。然而“混淆条款”基本遵循《商标法》适用思路:先判断商业标识权利边界,再判断被控行为是否进入了该边界,最后判断被控行为是否具有混淆可能性。这种套用的思路并不恰当。混淆条款是在缺乏“注册制”的情形下适用,与注册商标存在注册类别、在全国范围有效不同,其待保护的商业标识的边界的不确定性更强:原告商业标识使用类别不一定清晰,也不一定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法院无法先静态确定商标权类别与地域边界,再根据商标实际使用及消费者认知情况,扩大或收窄边界。故在适用“混淆条款”时,对如何确定有一定影响力的类别及地域范围、如何处理与《商标法》第13条、第32条、第59条的关系则面临更多争议。(32)譬如有观点认为“有一定影响力”在“混淆条款”、《商标法》第32条、第59条的含义与认定相同。参见拓野科技有限公司诉恩倍科微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46794号民事判决书。
既然适用“混淆条款”时,原告商业标识的边界不易预先确定,更恰当做法是先确定被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业标识的类别与地域,再回头看原告的商业标识是否在这些类别与地域具有一定影响力——这是一个先根据被告使用情况、再回看原告使用情况的倒置思路,突出“混淆条款”致力于规制行为而非赋予权利的属性,有着独特的语境。“‘一定影响’的语境转换带来的后果既有相关语词意义的不同,也包括意义验证方法的差异。”(33)刘继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定影响”的语义澄清与意义验证》,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换言之,应注意到“混淆条款”所称有一定影响力不存在一个先定的标准,承认判断具有动态性。“‘一定影响’的认定需要更多地结合个案而不是演绎式的法律规范及定义……在法律的明确性和判决结果之间的社会妥当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34)肖顺武:《混淆行为法律规制中“一定影响”的认定》,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5期。
采取倒置思路至少有两方面好处:一是保持认定具有充分灵活性。原告商业标识可能在相当狭窄的类别或地域范围有一定影响力,被告的混淆使用行为则可能恰好在该狭窄范围内破坏商业标识指代功能,从而破坏相关公众利益、危害该市场的秩序,值得规制。二是降低诉讼活动的繁琐性。在现实司法环境中,原告因担心其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遂尽可能找更多证据证明其商业标识的影响力,原被告在举证质证、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均面临压力,有种“无的放矢”意味。若采取倒置思路,法院仅需判断原告商业标识在被告实际使用的类别与领域是否达到有一定影响力,争议焦点将更聚焦。采取倒置思路意味着判断原告商业标识有一定影响力的标准不高,若横向比较《商标法》,它既不要求达到《商标法》第13条在全国范围内知名程度,也不要求达到《商标法》第32条阻碍他人商标注册程度,只需要达到类似《商标法》第59条在先使用抗辩程度——即只需在被告使用商业标识的类别与地域有影响力,下面分而论之。(35)本文此处认为“混淆条款”所称有一定影响力的程度大致与《商标法》第59条相当,是指所要求的证据证明力程度相当,而不是指其两者适用思路一致,第59条显然不采取“倒置思路”。
从类别看,有观点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受‘类’的限制——‘他人商品’可能存在‘类’的相同或近似,条文上的‘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则不要求‘类’。”(36)刘继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定影响”的语义澄清与意义验证》,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本文不认同这种观点:(1)“混淆条款”未明确将类别近似作为适用因素,但这不能否定类别近似的作用。“混淆条款”的目标是保护商业标识所具有的指代关系,从而维持市场秩序。不同市场主体在各个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商业标识越远离某市场主体的核心或主要经营领域,指代功能越弱、影响力越低,其他市场主体的使用行为越不容易造成混淆。在这个分析链条中,类别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认为不需要考虑类别,可能已经不是旨在规制“混淆行为”,而是更宽泛地禁止对某种智力成果或声誉的利用行为。(2)基本共识是划分类别不是依据《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或其他类似分类表。换言之,划分不是依据静态的、法定的分类,而是依据动态的、基于市场情况的分类。划分既要考虑消费者的选购认知,也要考虑市场主体的营业方式,确定商品或服务之间、市场主体营业之间的实际替代程度或相关程度(即实际联系),分析消费者是否会合理认为商品或服务、市场主体营业会发生扩张并导致重叠(即心理联系)。这种正确的做法增强了考虑类别的正当性。(3)即便在以混淆可能性作为根本标准、将其他条件作为推导混淆可能性的因素的美国,法律适用仍离不开结合类别近似性判断混淆可能性。第二巡回法院采取的“Polaroid”测试法第3、4项分别为“产品的邻近性、在先使用者会弥补产品差异的可能性”(37)Polaroid Corp. v. Polarad Electronics Corp., 287 F.2d 492, at 495 (2d Cir. 1961).,第3项是决定混淆可能性的三大核心之一(另有商标的强度、商标的近似程度)。(38)Mobil Oil Corp. v. Pegasus Petroleum Corp., 818 F.2d 254, at 259 (2d Cir. 1987).第九巡回法院采取的“Sleekcraft”测试法第2、5、6、8项分别为“产品的近似性”“使用的营销渠道”“货物的类型和购买者可能的注意程度”“扩张生产线的可能性”(39)AMF, Inc. v. Sleekcraft Boats, 599 F.2d 341, at 348—349 (9th Cir. 1979).,并认为特别具有证明力的因素是“标识的近似性”和“产品的近似性”。(40)Stone Creek, Inc. v. Omnia Italian Design, Inc., 875 F.3d 426, at 432 (9th Cir. 2017).联邦巡回法院采取的“Du Pont”测试法第2、3、9项亦考量了对商品或服务近似性、销售渠道近似性、使用或不使用该商标的货物类型(41)In re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476 F.2d 1357, at 1361 (C.C.P.A. 1973).值得注意,“Du Pont”因素适用于联邦商标注册程序中,但无论是“事前”的注册还是“事后”的侵权,均系围绕混淆可能性展开。,商标委员会认为判断混淆可能性两个关键的考虑因素是商标之间的近似性和商品或服务之间的近似性。(42)In re Guild Mortgage Company, 2020 WL 1639916, at 2 (T.T.A.B. 2020).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尽管法院最终需要考量的是混淆可能性,但假如连类别近似性都作为一个仅具有参考意义的因素,判断混淆可能性将变成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损害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从地域看,在原被告经营地域与从事行业一致时,法院可直接在该范围内判断影响力,争议不大。譬如,原被告均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从事服饰销售,法院只需在该类别和地域内考虑原告店铺装潢是否有一定影响力。(43)参见深圳中院判决百分百感觉服饰公司诉百分百女人内衣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982号民事判决书。若原被告展开经营的地域或行业存在不同,情况则相对复杂,法院需引导双方证明原告商业标识的影响力是否扩张至被告类别或地域(继而决定是否要禁止被告行为)。譬如,被告的饮用纯净水主要销售于上海地区,原告已证明其“清泉纯水”牌饮用纯净水在江苏启东地区有一定影响力,法院在承认饮用纯净水生产销售具有较强地域性、跨区域销售较少的情况下,未分析原告商业标识知名度是否已扩张至被告销售区域,却认定存在混淆可能性,分析链条有所欠缺。(44)参见启东清泉有限公司诉上海解放饮用水有限公司等擅自使用区域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0201号民事判决书。相反,有法院认为楼盘的知名度往往与楼盘所处地域相关,楼盘的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也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因原告“星河湾”楼盘仅在广州、北京,被告在安徽池州以“星河湾”作为楼盘名与销售商品房,原告未能证明其“星河湾”楼盘影响力已扩张至被告经营地域。(45)参见广州星河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与淮北金淮海置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皖民三终字第00029号民事判决书。另外,有观点可能认为在互联网营销日益发达的市场环境中,地域性限制已经消失,这种观点不正确。前述饮用纯净水、楼盘显然是地域性很强的产品,袋装啤酒、散装食物、冰淇淋等产品,家政服务、琴类舞蹈教学等服务同样具有很强地域性,互联网营销只构成辅助营销的一环。在B2B领域,部分商品或服务依赖于当地特别的自然、人文、市场、政策环境,远途寻找交易对象、达成交易、输送商品或服务等均可能面临交易成本显著上升。因此,法院可承认互联网营销是商业标识知名度扩张的渠道之一,但不能直接据此否认地域性,需考虑:“(1)双方是否都将互联网作为重要营销渠道?(2)双方商标是否用于该网络(所营销)的产品之上?(3)双方营销渠道是否存在其他重叠?”(46)Kibler v. Hall, 843 F.3d 1068, at 1077 (6th Cir. 2016).美国第六巡回法院提出该分析的语境是考虑“共同的营销渠道是否会加强被告使用原告商业标识有混淆可能性”,这是因为美国司法实践几乎将全部考量因素放在“混淆可能性认定”之中,而非独立分析原告商业标识的影响力。本文是借鉴该分析的原理:通过考察原被告营销渠道重叠性,判断原告商业标识影响力是否超越地域、扩张到被告营业范围内。
至于判断有一定影响力的具体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从“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知悉程度,商品销售的时间、区域、数额和对象,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标识受保护的情况等”几个角度提供了指引,《商标审查指南》关于“具体在先权利的审理审查”的规定亦可作为证据指引,自不赘述。
三、“混淆条款”规制的行为类型
“混淆条款”规制“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12条将“特定联系”进一步解释为“包括误认为与他人具有商业联合、许可使用、商业冠名、广告代言等特定联系”,对比2007年版本第4条“包括误认为与知名商品的经营者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可发现现行司法解释对特定联系的具体类型作更宽泛理解。混淆包括来源、赞助、关联关系混淆,下面分而论之。
(一)避免来源关系混淆
规制“混淆行为”,核心是要规制那些破坏商业标识来源或品质指代功能的行为,避免经营者商誉投资落空和消费者搜索成本提高。“引人误认是他人商品”正是错误利用他人商业标识来源或品质指代功能导致的。
众所周知,保护商业标识的法律起源于反欺诈,这种欺诈行为既可能通过不当使用商业标识实现,也可能通过其他错误陈述实现。规制的核心是考察经营者有无欺诈意图,当经营者带有欺诈意图作出相关行为,这就应受反欺诈法律规制。这种法律适用与当时市场环境有关,市场主体主要在本地向顾客提供商品或服务,既是生产者亦是销售者,产业链较短,市场主体之间往往具有直接竞争关系,消费者则可直接识记相关市场主体而作出选购,对各类商业标识的依赖程度较低,法律规制欺诈已足够。随着技术进步与市场环境变化,商品或服务的远距离提供成为可能,产业链越来越长,产品各部分由不同市场主体生产,经组装后再由多层级经销商向更宽广地域的消费者提供,消费者不易直接识记市场主体,各类商业标识的经济功能在消费者选购环节中便凸显:某市场主体通过各类商业标识向消费者表示,无论产品由谁实际生产或销售,使用特定商业标识的产品由该市场主体控制,保持一致来源或品质。商业标识反映稳定来源或品质的指代功能逐渐在消费者之间建立,消费者可在各个地域范围、销售渠道“认牌”购买相关产品或服务,不需要再仔细考察生产经营者是谁、他们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反欺诈的法律逐渐演变为保护该等具有指代功能的商业标识的法律,规制范围拓宽,既不要求商业标识使用者具有攀附恶意,也不限定在市场主体之间直接竞争情形。(47)See, 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 Unfair Competition, westlaw edition, 2022, Chapter 5, section 5.1 & 5.2 & 5.3.“混淆条款”与《商标法》的发展历史密切关联(48)值得注意,我国是先有关于注册商标保护的《商标法》,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后,《反不正当竞争法》才产生,并与《商标法》一同发挥着保护商业标识的功能。以上论述是基于美国商标与不正当竞争的历史发展,但考察这种历史变迁能加深对我们商业标识保护制度功能、作用、目标的认识。,两者禁止来源混淆的理由一致,均旨在保障商业标识品质保证功能的实现,并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方面,保障了市场主体在广告和宣传等方面的投资准确性,促进市场主体围绕商业标识作商誉投资;另一方面,消费者搜索成本得到控制,消费者能通过商业标识快速记忆、比较质量、价格、售后等因素,作出更明智选购行为,并进一步激励市场主体妥善营业,提高市场整体效用。(49)See, 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Trademark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30 J.L. & ECON. 265, 269—270 (1987).
以上关于制度渊源与功能的分析在我国背景下亦适用,被告一切攀附原告身份或其商品或服务品质、作错误表示来源的行为均应受“混淆条款”规制,应适用《商标法》判断混淆可能性的规则(尽管“混淆条款”更宽地规制主体身份混淆):混淆指是否有混淆的较大可能性或混淆之虞,可根据相当部分消费者的认知状态得出结论。(50)参见王太平:《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相似性与混淆可能性之关系》,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判断相关公众应结合商业标识使用的实际场景,考察是否面向特定消费群体、应用于特定细分领域,譬如面对儿童等注意力相对欠缺的群体,或销售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物品等。(51)参见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诚佳和商贸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203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艾腾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与深圳市博林达科技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036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从业范围越接近、产品或服务之间竞争越直接,被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业标识越有可能导致混淆可能性(52)参见北京旭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与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1504号民事判决书。,但判断混淆可能性不以原被告之间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或相同的经营范围为前提,上下游或相近领域的混淆亦受规制。(53)参见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0046号民事判决书。消费者投诉、具有科学性的消费者调查报告等实际混淆证据可用于证明,但并非必要。(54)参见杨祝顺:《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中的实际混淆证据》,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4期。若被告已长期使用特定商业标识,原告提供实际混淆的证据则更有说服力。判断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采取客观标准,被告带混淆意图使用商业标识,不当然意味着存在混淆可能性,但混淆意图可用于增强混淆可能性成立的判断。(55)参见姚鹤徽:《主观意图在商标混淆侵权判定中的定位与适用》,载《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有关具体判断因素,则可从商业标识的读音含义与形态、产品销售的形式与分发的渠道、消费者的属性与他们的注意程度、知名度的高低等角度展开。(56)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侵害商标权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第3.2条,2020年12月29日发布;《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第6条,2021年12月发布;《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的审理指南》“四、商标侵权判定—(四)混淆的判定”,津高法〔2016〕3号,2016年1月12日发布。这些方面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不赘述。
(二)避免赞助、关联关系混淆
在当今市场环境中,商业标识功能不断扩张,不仅发挥指示来源或品质功能,也可能具有彰显美学意义(直接展示玩具形态的透明外包装)、表达身份认同(校徽、队服)等功能,如何理解“特定关系”存在更多分歧。在商业标识具有多重功能的环境下,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不一定认为使用特定商业标识的商品或服务表示某种来源或品质,也可能仅是对商业标识本身或商业标识所联系主体的喜爱与支持而发生“移情效应”,商业标识实质发挥着与来源或品质无直接关联的广告宣传功能。这时是否应认定存在混淆可能性、存在怎样的混淆便充满争议:一些消费者可能会认为市场主体之间仍存在来源或品质控制关系,不规制将使消费者搜索成本增加;一些消费者可能并不关心商品或服务是否是官方提供或控制品质,规制将使该领域的竞争被消除。
为回应商业标识功能的扩张与混同,实践对赞助或关联关系混淆的认定越来越宽泛,笼统地使用“特定关系”概括。有观点批评道:“在过去一个世纪,商标法已经剧烈扩张至一个点,即禁止公司的行为看起来不太可能以任何实质方式混淆消费者……我们认为问题是法院假定消费者已经混淆了,这是有问题的。”(57)Mark A. Lemley & Mark P. McKenna, Irrelevant Confusion, 62 STAN. L. REV. 413, 446—448 (2010).这种批判是正确的,赞助或关联关系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即便事实上存在这些关系或消费者认为存在这些关系,这不一定意味着消费者认为产品来源于该市场主体,或由其控制品质,消费者此时作出选购决定更大程度上是商业标识其他功能在发挥,很难认为这种市场利益应分配给商业标识所有者。本文认为,“混淆条款”认定赞助或关联关系混淆时,仍应以规制破坏商业标识指示来源或品质功能为根本,注意区分情形:不能宽泛地认为只要消费者产生“看到A商业标识会想到原告”的认识,就认定使用A商业标识的被告“错误地建立起原被告之间存在赞助或关联关系”,应受“混淆条款”规制。应考虑被告使用商业标识的方式,衡量消费者作出选购决定的场景、原因,分析“赞助或关联关系是否反映出特定来源或品质”“消费者是否因认为该等关系存在而作出选购决定”,譬如考量消费者是否认为被告商品或服务的主要部分来自于原告、被告生产经营活动由原告安排或监督、原被告之间存在投资控股关系等。“仅在消费者将混淆商品误认为仍受被混淆的生产者所管控和品质担保时,方可认定构成间接混淆,出于这种误认的担保才会出现潜在的刺激消费以及商誉失控。”(58)刘继峰、黄滋淇:《〈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间接混淆标准的重构》,载《天津法学》2021年第3期。
以上分析表明,不是利用商业标识任何功能或声誉的行为均应由“混淆条款”规制,“混淆条款”不是保持某市场主体与商业标识的唯一联系,其他市场主体利用商业标识吸引公众选购、与之展开市场竞争,发挥商业标识除指代来源与品质的其他功能,不被“混淆条款”禁止——否则“混淆条款”将变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诱发逃逸适用。典型如消费者购买校徽胸章,是因为其他图样均不能直观、简明地象征学校,可认为消费者是因校徽所具有的身份彰显功能而作出购买决定,至于校徽的来源或品质是否出自学校官方,似乎不是消费者关注焦点。类似地,即便市场主体在同人作品中使用他人知名作品中的作品元素,消费者是因作品元素所呈现的故事情节、角色特征、世界观设定而受吸引,消费者亦不通过这些作品元素来识别原作或同人作品。若“混淆条款”此时宽松地认定存在赞助或关联混淆,实质上将使学校独占垄断学校纪念品销售市场、使原作作者垄断(甚至可能超出著作权法所承认的)同人作品创作市场——无理由认为这些市场由学校、原作作者控制会使得纪念品、同人作品品质更高,规制这种“混淆”亦不会保障与改善消费者“认牌购物”过程。因此,对“混淆条款”所称“存在特定联系”的理解,应按照前半句“误认是他人商品”限缩,即这种联系不是基于美学意义、技术意义、描述意义等其他联系建立起来,而仅指消费者能合理认为品质被他人稳定控制或直接来源于他人,正是基于这种稳定品质或来源而足以使消费者作出选购决定。此时可结合原告商业标识是否有其他意义,被告是否大量、突出地附有自己的区别性商业标识,原被告使用该商业标识的场景异同,消费者对原告商业标识各意义的认知情况等作判断。
四、“混淆条款”兜底条款适用
兜底条款的适用应当注意其边界。“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是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时增加的,理由如《修订草案表决稿说明》所述:“实践中还存在其他形式的混淆行为,建议增加兜底条款,以防止挂一漏万。”划定兜底条款适用边界,需结合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法背景。2017年修法为分流第2条一般条款,既增加了第12条“互联网专条”这一总结既往司法实践的类型化条款,也在原各类型化条款中增加兜底条款或采取开放性的法条表述,包括在“混淆条款”中增加兜底条款、将“误导条款”表述“广告或者其他方法……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改为“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这些修改体现出立法者试图改变法律适用过度依赖一般条款的状况——一般条款所维护的商业道德与市场秩序更为模糊,各类型化条款所维护的商业道德与市场秩序则相对清晰,将待规制行为“合并同类项”并“避免向一般条款逃逸”,这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指引。当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类型化划分并不如《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权利法对权利内容的类型化划分那般“泾渭分明”,必然有着更高的重叠性与模糊性,这也是应当承认的基本特征。
从这个思路看,兜底条款的适用不能只看一项行为是否在文义上落入兜底条款,而是要澄清它与一般条款及“误导条款”之间的关系。前者较容易得出结论,即兜底条款仅规制指代来源或品质方面的混淆,对竞争利益的一般性盗用与侵害,譬如使用他人作品元素、盲从模仿他人新上市产品、淡化或丑化他人商业标识等均交由一般条款规制(这有待我国相关方面的案例群演进)。后者则较复杂,从最广义看,“误导”的手段既包括通过商业标识实施混淆实现,也包括通过商业标识混淆以外的手段实现,“误导”的行为类型丰富。“误导条款”具有涵摄规制“混淆行为”的能力,“混淆条款”与“误导条款”之间长期具有密切关系。(59)参见[德]弗诺克·亨宁·博德维希主编:《全球反不正当竞争法指引》,黄武双、刘维、陈雅秋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5页。不过,法律理性是一个不断从一般规则中抽离出个性规则的过程,朝着规范精细化与分门别类化的方向持续努力。在各国法律实践中,对混淆使用商业标识行为的规制越来越多地独立于对其他误导行为的规制,甚至演进出承认商业标识财产权属性、规范商业标识权利取得的专门法律。(60)譬如欧盟《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第6条2(a)特别规制标识混淆型误导,与第6条其他类型的误导行为区分,并通过《统一商标规范》专门管理、保护欧盟注册商标。因此,现时法律适用既要承认“混淆条款”与“误导条款”的密切关系,又要强调它们的区别:“混淆条款”专门规制市场主体不当利用商业标识指代来源或品质、致使消费者产生错误的来源、赞助或关联关系认识的行为;“误导条款”则规制市场主体实施的其他一切误导行为,对行为手段与结果均不作一般性限定,只要行为足以使相关公众作出错误选购决定,便应受规制。
通过以上对比并结合前两部分分析,兜底条款的适用边界便能得到澄清:(1)若原告竞争利益不反映在商业标识上,即被告的行为完全不涉及使用商业标识的情形,兜底条款便不适用。(2)可受保护的商业标识类型丰富,各种新类型商业标识均可能获得保护。但保护不应阻碍正当竞争,且实际能获得保护的商业标识应具有指代来源或品质功能。(3)被告大量使用表示他人身份或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商业标识,在商业标识方面作全面模仿,法院可降低各商业标识有一定影响力的证明程度,只要这些商业标识是特有的,即它们具有指代功能就足够了。(4)应结合具体场景考虑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在竞争激烈发生、消费者高度重合的环境下,更容易认定存在混淆可能性,譬如在他人原址使用相同或近似商业标识从事同类业务。(61)参见自贡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与自贡康立耳鼻喉医院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知民终759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既往存在赞助或关联关系,亦更容易认定存在混淆可能性,譬如被告在特许经营关系终止后继续使用原装修装潢。(5)被控行为因具有混淆可能性而受规制,混淆包括来源、赞助、关联关系混淆,它们是对商业标识指代来源或品质功能的利用。被控行为不产生这种混淆效果,不受规制,即便其利用了他人其他竞争利益。
司法实践对兜底条款的适用持积极态度值得肯定。有适用兜底条款保护各种新类型商业标识。譬如有法院认为“xiaodu xiaodu”语音指令是用户在使用小度智能音箱时必不可少且频繁出现的特定语音指令,该语音指令已与百度公司及其产品建立起了明确、稳定的联系,并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故被告在杜丫丫学习机中使用“xiaodu xiaodu”语音指令进行唤醒和操作会使用户错误认为这是百度公司或百度公司提供产品,应受兜底条款规制。(62)参见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子乐科技有限公司等其他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3253号民事判决书。亦有法院认为微信APP投诉页面整体风格已为公众熟悉,涉案公众号在微信平台页面使用相似投诉页面,会使用户错误认为被告页面是官方投诉渠道,应受兜底条款规制。(63)参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诉杭州科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浙8601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书。有适用兜底条款规制混淆使用商业标识的新行为形态。譬如有被告在招投标活动中提供宣称是原告出具的授权书,并在合同附件中使用标有原告商标和企业名称的《品质保障书》《售后服务书》作为背书,该行为受兜底条款规制。(64)参见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等与马媛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知民终4号民事判决书。也有被告在其视频网站《明明是ta先喜欢我的》搜索结果页面底部“相关搜索”栏目下推荐电视剧《明明是ta先喜欢我的2》,但点击该推荐链接跳出的结果是被告电视剧《明明就是喜欢我》,该行为亦受兜底条款规制。(65)参见江苏宝资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知民初1527号民事判决书。
结 语
若将“混淆条款”理解为是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尽管这种观点并不存在错误(因为未注册商标确实可以落入“混淆条款”的保护范围内),但既未注意到“混淆条款”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类型化条款之一而有着相对独立的适用立场、思路、规则,也简单看待“混淆条款”与《商标法》之间分别作为行为规制法与权利保护法所具有的复杂关系。市场行为复杂多变、层出不穷,《反不正当竞争法》始终要在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的权衡中维持各种市场秩序,做到灵活性与可预测性兼具一直是法律适用的重点、难点。本文从内部与外部视角出发,结合国内外情况,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类型化条款“混淆条款”的适用思路,分别探讨了可受“混淆条款”保护的客体类型、“混淆条款”所规制的行为类型、兜底条款的适用思路,籍此为“混淆条款”提供更清晰、准确、有效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