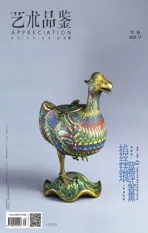音乐理解的历史性分析
2022-02-23梁业涛星海音乐学院
梁业涛(星海音乐学院)
音乐理解俨然是音乐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关于感性接受,同时关于理性认知。在学术界中,人们常说音乐理解有多解性和不确定性,以此说明并不能形成一种普遍有效的“正确理解”。在大众观念中,多解性常被极端化,被描述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变成了一种完全的相对主义。诚然,由于音乐无法具体地表达外在事物,理解根本无法统一。但这不等同于理解是主观任意的。穆索尔斯基的作品《图画展览会》中的选段“两个犹太人——一穷一富”,可能会被理解成大狗熊和小兔子的对比,也可能会被理解成是大灰狼和小兔子的对比,但绝不会有人将之理解为对美好事物的赞颂。理解虽多样,却总是“有限度”的。正如柯扬指出:音乐理解是有限差异,而不是随意解释的。也就是说,理解总是被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这种限制主要来自此在所始终具有的“前理解”,并表现为音乐理解中的历史性。由此,本文将在哲学诠释学提出的“前理解”概念基础上阐述音乐理解的历史性。
一、理解与前理解
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他认为,“时间性存在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及其意义的开显与解释的前提。另一方面则表明,只要此在的存在是时间性存在,它就不得不让他者显现而开显他者、解释他者”。理解不是众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而是被嵌入此在的存在结构中的,所有活动都本然地以理解活动为基础。于音乐活动来说,即指无论欣赏音乐抑或是分析音乐都在一定程度上以理解为基础。
海德格尔谈道:在任何理解活动发生前,都有着一种“前结构”。这种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前有、前见以及前把握。这三种结构后来被诠释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所吸收,并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将之整合成“前理解”。前理解可以被看作是此在的先入之见。例如,生活中常见的“地域标签”——“四川人很能吃辣” “广东人什么都吃”等便是常见的先入之见。这些见解常被看作是一种“偏见”,并被打上贬义色彩。流俗的观点认为它阻碍了理解的发生,因此理解活动往往意味着要清除自身的先入之见,以留下事情本身展现的空间。伽达默尔指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它本质上是不可清除的。不仅如此,前理解甚至是理解可以发生的条件。无论是何种程度的理解都不可能无端发生。一个对音乐毫无概念的人不会将他聆听到的音乐理解成音乐,而只会理解成一种声音。但这不是说理解活动不过是坚持自身的前理解。
在很多情况下,盲目地坚持前见只能造成误解,或是对原文的扭曲。如果一个人坚持用现代的词义理解古代的文献,那么他根本不是正在理解文本内容,而只是徘徊在他固执的己见之中。理解活动的核心并不在清除抑或坚持前理解,而是保持前理解的开放性。
理解活动就是筹划,此在根据先行的前理解抛出对文本内容的筹划,并在理解的过程不断地根据事情本身调整、修正自身的筹划。因此“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做出正确的符合于事物的筹划”。保持前理解的开放就是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对其进行调整。理解就像是一场谈话,谁想理解对方的意思就必须细心聆听对方的意见,考虑对方话语的力量。并在此过程中检查自身,使自身顽固的前理解被暴露和开放。
虽然前理解属于个人,具有个体性,但它不是完全主观的。“支配我们对某个文本理解的那种意义预期,并不是一种主观性的活动,而是由那种把我们与传承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所规定的。”这就是说,此在的前理解不是主观随意捏造的,而是来自于我们所理解的对象在历史上的延续。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概念正能说明这个问题。所谓的“效果历史”除指被理解物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外,还包括对被理解物本身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通过社会教化不断渗入我们的生活,并组成了前理解的核心部分。例如我们今天对贝多芬的判断,与贝多芬的作品在19 世纪初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且由此引来的对贝多芬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于是他指出:“当我们力图从对我们的诠释学处境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距离出发去理解某个历史现象时,我们总是已经受到效果历史的种种影响。这些影响首先规定了:哪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研究的,哪些东西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这种现象说明,前理解在其形成之初就具有历史性,并且作为传统延续的痕迹烙印在此在的理解活动当中。因此,理解活动从来不是一种主观的活动,它受到传统的限制并带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性。那么,这种历史性是否在音乐理解活动中出现?应该如何理解音乐理解中的历史性?这是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二、音乐理解的历史性
阿伦·瑞德莱在其著作《音乐哲学》讨论关于音乐本体问题时,为指出学界讨论的“音乐同一性问题”与实际的聆听经验无关,曾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某个名叫马丁的人突然从天花板上下来,置身于音乐厅之中,而此时在音乐厅里进行着对如此这般一部作品的首次演奏。对于音乐、音乐作品和演奏,他都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使所有这些东西能被理解的那个语境。”在此情况下,他认为马丁根本不可能提出音乐作品同一性的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了解或者语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理解。
这个假设不仅指出了同一性问题讨论本身背离了实践经验,更指出了音乐理解所得以形成的条件。对于马丁来说,他听到的不是一种音乐,而只是一种声音。对于理解音乐这一活动而言,前理解本质上也是不可消除的。参加一场音乐会时,主办方常会为听众准备一些小册子介绍作曲家以及作品的基本信息,方便听众更好地理解音乐作品。其中预设了一种表现主义的美学态度,它默认了理解音乐作品与理解作曲家两者间有着重要联系。参加音乐会时需要注重音乐会礼仪,保持安静,不得在乐章之间鼓掌,自然与音乐作品需要凝神观照的审美态度有关。这些不同的活动内都隐含着一种前理解,使得一般的听众与“马丁”有所不同。而这些前理解提供的正是一个场域,在其中音乐得以被听见。
若对形形色色的前理解进行深究便可发现其历史性。表现主义美学兴盛于18、19 世纪,虽然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少的批评和质疑,但在今日,其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以至许多听众认为将作品与作曲家的生平联系理解不仅毫无疑问,而且“自然而然”。对于17 世纪的听众而言,这种联系却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其时,音乐家虽然也强调音乐与情感有着重要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以作品表现作曲家内在自我这一方式确证的。音乐与其说是“表现”情感,毋宁说是“模仿”情感。这个时期音乐家的任务是以声音展现情感的特征,使听众在理智层面“认出”声音中的情感,而不是在感性层面“感受”到某种情感。因此,这时期既不需要音乐家在音乐中透露自我,更不需要听众袒露心胸任凭音乐在其中激荡。就如达尔豪斯所说:“作曲家更像是一位美术家,他在描画另一个人的感情,而不是在展示自己的感情。”
这些历史事实表明:表现主义的美学态度远不是一种“自然态度”,而是在历史展开中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音乐术语学的研究同样表明前理解的历史性。当我们毫无疑问地使用奏鸣曲、交响乐或者是快板等术语时,不应该忽视的是,这些术语有着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例如,“交响乐”(symphonie)一词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其本意为“和谐”。在毕达哥拉斯的论述中,主要指音程的和谐。而在1600 年左右,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声乐作品内的器乐间奏曲或者后奏曲。直到18 世纪在萨玛蒂尼等作曲家的努力下才形成了今天的意义。尽管这些术语的发展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但可以肯定,今天对这些术语的理解和接受与其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关联。
即便是一位不仅对音乐术语毫无了解,也对应该如何欣赏音乐没有任何头绪的听众,同样不得不受限于前理解的历史性。当一位听众将某种声响看作音乐,或者说将之理解成音乐,他便展露了对“音乐本身”的前理解。在今天,流行的说法是将“音乐本身”看作是“纯音乐”,歌曲往往被看作是由“歌词”与“音乐”两个部分构成。但在17 世纪前,带有文辞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器乐只是“不完满的形式”这一观念却从未遭到真正的质疑。然而,在19 世纪,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经过“器乐形而上学”的确证后,器乐成为真正的音乐,而歌曲被理解为混合艺术。这种转变由此取得了主导地位,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些例子正表现了前理解本身具有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首先表现为听众前理解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连续性,它使音乐理解不至于完全陷入主观当中,并使其有了共同性。虽然这种历史性大多时候并未被个人所察觉,但其仍然不可避免地发挥作用。所以音乐理解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视域下进行理解的,这正是音乐理解历史性的第一重含义。
在这个层面上谈论的历史性仍然只是被动的。然而,理解活动本身不是要求此在“被动”接受历史视域,任由自身的前理解所摆布。否则,理解者只是固执己见,把音乐作品作为证明自身前见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就像一位在谈话中漠然对待他人意见的人,理解活动根本无从谈起。为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点,不妨探寻一下“原创性”的观念。原创性是评价一部音乐作品价值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一部作品若有着抄袭的嫌疑,无论其如何悦耳,总会被理解成只是一部低劣之作。然而当这个标准面对更加久远的音乐时,却似乎并不适用了。众所周知,亨德尔不仅在他自身的歌剧创作中常借用旧作的旋律,甚至还常使用其他作曲家的旋律。
正如一位对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语言、文化语境没有丝毫了解的听众无法理解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理解音乐必须自觉意识到前理解的历史局限,并以理解历史为前提,这正是音乐理解活动历史性的第二重含义。同时,这充分说明:单纯强调审美的直接性是有问题的,所有的直接性实际上都隐藏着某些历史因素。但这绝非意指了解某一时期的历史或者某一音乐家的生平可取代对音乐作品的聆听。否则,甚至可以得出理解音乐作品根本不需要聆听的结论,这显然是荒谬的。前理解固然限制了听者所能筹划的意义,但是理解活动本身却是超出己身前理解的过程。
理解与前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关系:理解的发生意味着前理解被超出,这种超出最后又变成一种前理解。这种循环指明了音乐理解活动历史性的第三重含义:音乐理解不仅在历史视域中进行,受到历史视域限制,而且它本身在延续,发展着历史。正因如此,对音乐的理解便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可能产生永恒、普遍的“正确解释”。特莱特勒在《关于音乐意义的辩论》一文中指出:对肖邦的理解在历史上曾有许多不同,在19 世纪肖邦被认为是一个表情丰富、效果辉煌的作曲家,注重炫技却不是一个乐思深刻的作曲家。而在20世纪初期,肖邦却被认为是一个其音乐具有“永久价值”的大师。在其后一段时间,他又被认为是一个“悲剧性”的、罗曼蒂克式的人物。总之,肖邦在历史中曾经展现出了许多不同的“面孔”,这些都影响着对肖邦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一点说明的恰恰是音乐理解本质上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使音乐理解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
三、结论
本文阐述了音乐理解具有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建基于音乐理解本质上具有的前理解之上的。前理解虽然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却是理解所必须得以发生的条件。这种前理解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尽管未必能被听者清晰地意识到,却仍然构成听者理解音乐作品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性首先表为一种连续性,它指出听者对音乐的理解是在一定的历史视域下进行的。历史视域的存在又指出,听者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并不是完全“直接”的,而是受到其限制的。因此,历史性在此表现为一种局限性。理解活动本身又要求其超出自身的前理解,以形成新的理解,所以历史性又表现为延续性。它本质上是处于不断变化当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