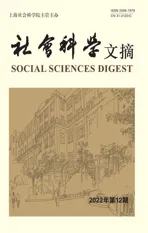复杂性科学与国际关系理论
——反思与创新视角下的探究
2022-02-23刘孟强
文/刘孟强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通过引入复杂性科学成果进行理论创新的趋势,这种创新趋势衍生出了两条具体路径,分别是国际关系下的复杂性探究路径和复杂性思维下的国际关系探究路径。尽管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国际关系在引入复杂性科学的过程中还存在些许问题。本文将在提升学界对复杂性、复杂性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在理论建构上长期存在的机械性世界观进行反思,并尝试提出复杂性视角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思想框架。
复杂性科学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科学史的视角来看,科学本身作为认知复杂性、解决复杂性的演化过程,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古代科学、现代科学、新型科学的发展路径。人类社会中的复杂性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旧有的复杂性减弱或消失,新的复杂性随之出现。复杂性科学是认知、探究复杂性的最新科学分支。复杂性科学在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应用存在两种思维路径:一种是国际关系下的复杂性探究路径,另一种是复杂性思维下的国际关系探究路径。其中国际关系下的复杂性探究路径力图在维护国际关系既有理论框架和学科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复杂性科学的成果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现象进行分析和探究,进而修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缺点、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战争、结盟、秩序等问题是研究的重点,国家行为体的独特地位和主权仍被强调。系统效应、折中主义是其中的代表。而复杂性思维下的国际关系探究路径是以复杂性理论为主,国际关系理论为辅,将国际关系置于复杂性视角之下。该路径下的成果包括“混沌理论”“后人类主义”理论等。
国际关系的机械性内核
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都反映出科学发展的主线脉络,那就是认知复杂性、解决复杂性。在认知和解决复杂性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成果会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进程,结果是国际关系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吸收了大量机械性科学观的思想和方法,并形成了与科学评价标准相关的机械性内核。随着时代的发展,机械性世界观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难以满足解释、预测国际关系现实的需求。这里将对三个国际关系领域典型的机械性内核进行列举和分析,复杂性科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需要突破这三个机械性内核的禁锢。
(一)“范式简化”倾向
随着牛顿经典力学的成功,“范式简化”成为科学标准。从本质上看,“范式简化”原则就是在与事实相符的基础上,对完美、方便甚至优美理论的追求。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对“范式简化”的追求逐渐变为对“简化”的追求,这导致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在国际关系领域,“简化”倾向体现在具体的外交政策层面,比如文化对国家行为体“角色”的塑造造成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固化;再比如“阴谋论”的盛行,当事情的发展偏离了设想,人们通常会简单地设想出一个全能的敌对力量,而原本的复杂性内容被忽视,这种阴谋论的“简化”倾向长期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层面,“范式简化”在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让“简化”成为科学与否的标准,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偏离。对“简化”的盲目追求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在自身发展中出现了诸如对人文的排斥、学科内部的分裂与自闭、理论对现实的失能等一系列问题。
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看,国际关系作为复杂性系统,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规则,这决定了在国际关系领域,“范式简化”在本质上是不适用的。另外,在国际关系领域“范式简化”的前提与目标呈现本末倒置的状况,这种因果倒置的处理方式让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知逐渐扭曲,这背后是学界对确定性和可控性的盲目崇拜。
(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演绎逻辑
在文艺复兴之后,辩证逻辑被抛弃,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成为正统,形式逻辑与还原方法相结合构成了现代科学的逻辑方法,即以微观的“元理论”为基础,通过演绎逻辑路径创建无矛盾性的知识体系。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看,将形式逻辑演绎方法作为科学标准是存在问题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了逻辑演绎系统不能同时满足完备性和自洽性,演绎逻辑在塑造封闭系统的同时,决定了理论的局限性。正确的事物不一定是可证明的,尤其是在复杂性领域之中。
总的来看,由形式演绎逻辑方法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三种困境。首先,演绎逻辑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本身存在完备性与自洽性的矛盾。其次,以西方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演绎逻辑无法塑造从微观至宏观的完整开放体系,演绎逻辑下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实现国家层次的突破,并只能将“无政府状态”、主权等作为理论构建的演绎基础,众多复杂性内容被忽视。最后,众多游离于演绎逻辑体系之外的经验事实被忽视。由此,演绎逻辑塑造的理论体系存在着与经验事实相悖的风险,以及价值观割裂带来的意识形态对立的风险。
(三)战争的初始条件(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路径)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学科永恒的主题,但这种主题的设定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战争的核心是暴力,暴力为战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在观念要素与物质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在人类社会普及。战争并不意味着永恒不变,战争应该被理解为特殊时空条件下的系统间关系,是观念系统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表现出来的特定适应性现象。这种适应性结果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中表现出不断加强的正反馈效应,国家行为体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相应的战争文化被强化,直到二战结束。
战争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至少有两点。首先是“无政府状态”思想的出现。国际关系学者出于解释战争的需要,通常会追根溯源,将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基础,但任何政治理念的提出都会受到相应时代背景的影响。其次是国际关系理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演化。从战争出现到1945年,征服行为通常都会取得成功,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得以维持的关键。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成功推动了国际关系系统的演化,导致国际关系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随着国家数量的减少和国家力量的增强,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防御成为国家行为体的可行选项。国际关系的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在战争状态的转换中找到了相应合理性。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内核
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看,国际关系学科未来发展的关键是如何识别和处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复杂性,在这方面,机械性世界观下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达到了瓶颈,适时引入复杂性科学成果以及运用相应的复杂性思维是未来的趋势,作为探索复杂性的最新科学分支,复杂性科学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应用需要确立相应的复杂性内核,本文针对性地列出三点,分别是“归纳方法”“国际关系系统状态的复杂性特征”“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
(一)归纳方法
从归纳方法本身的特点来看,归纳方法是探索复杂性的自然方式。人类大脑就是通过归纳方法进行建模,并对经验证据中的多数情况进行认知推理。长期的归纳导致层级结构的产生,这具有两个重要优势:第一,让系统能够对新事物做出反应;第二,系统可以通过类比进行推理,进而获得了学习、演化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人类可以探索未知事物、认知未知事物,进而获得知识。另外,归纳方法的优点还在于其开放性,即对所研究对象的领域范畴、经验材料的时空维度以及最终的观点结论持开放态度,这对复杂性研究至关重要。复杂性事物的领域范畴呈现出跨领域的特性,不同领域中存在相似的复杂性内容,不同领域的复杂性经验都是复杂性研究的宝贵资料,不同时空维度的经验事实材料对于复杂性的研究都具有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归纳方法可以得出内在的适应性模型,随后通过运用内在模型来决定应对环境所应采取的行为方式,内在模型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这对复杂性的探索是十分合适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归纳逻辑的强调,就是对经验事实的强调。在历史和案例的归纳中,国际关系中国家发展的多样性被发现,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被挖掘,“无政府状态”下的体系决定论被打破,国际关系中不同行为体依据自身情况采取适应性策略的观点出现。
另外,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意味着多重因果性,这些因果彼此之间以“导致”“使得”“塑造”“抑制”等诸多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因此从方法论上来看,参照规律的决定论并不适合研究开放的、非线性的世界。归纳的作用在于知识、经验的积累,而国际关系的大理论范式大多采用演绎的方法并寻求确定性的路径,强调塑造相对完美的逻辑体系,但完美逻辑体系的最终指向是封闭系统,这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复杂性现实之间的背离,进而阻碍了国际关系学科有关复杂性知识、经验的积累。
总的来看,归纳方法似乎永远也无法得出决定论意义上的普适性结论,这似乎意味着国际关系领域的经验归纳是一项无穷尽的重复劳动,国际关系似乎永远是一个“不成熟学科”。这不是归纳方法的问题,而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如此。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本质说明了国际关系将会始终处于不断演化的状态中,因此需要人们不断通过归纳方法进行经验总结,不断更新学科知识,不断确立阶段性理论核心。这正是复杂性视角下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科特性,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关系是一个“永葆青春”的学科,这足以使每个国际关系学者感到兴奋!
(二)国际关系系统状态的复杂性特征
国际关系的系统状态是复杂且多变的,就战争来说,其本身是不断演化的。在一战之前,反战运动已经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战争观念的分水岭,在反战运动的影响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剂催化剂,让反战观念深入人心。反战观念的形成塑造了新的国际关系系统状态,至少在欧洲范围内,和平成为主旋律,每个人都渴望和平而厌恶战争,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在观念上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系统状态完全不同。但很快这种刚刚出现还不成熟的和平状态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二战之后,科技进步带来了物质上的极大丰富,电报、电话以及今天互联网的出现,让信息快速传播普及,导致国际关系的观念系统出现了适应性变化。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观念,战争的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战争走向衰落,是国际关系系统演化的结果。物质、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有效的政府运作、国家行为体的审慎思维,以及在一些无法明确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关系的系统状态被改变。当然,战争只是国际关系系统状态转变的一个方面,国际关系系统状态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国际关系系统的多层次、观念物质基础可替换、整体形态可塑造等方面上。一个恰当的比喻是,这个时代的国际关系系统状态好像是一块可自由拼装、任意形变的“乐高海绵”。
(三)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
国际关系机械性内核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背后隐含的科学标准,但在当下复杂的全球性时代,这一科学标准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复杂性科学的引入与矛盾的解决,在本文来看目标上是一致的,其前提就是把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具体包含如下几个内容:
首先,应该明确国际关系中复杂性思维可应用的客体范畴——国际关系中不知道、不可控且用线性思维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领域,这就要求将传统国际关系所简化和忽视的个人、自然环境、科技,甚至是国家等内容重新拾起,在此基础上通过复杂性的方法和理论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分析,最终实现“以复杂性的方式应对复杂性”。
其次,在观念上如何把复杂性问题简化而不是简单化是问题的关键。一种文化的创造能力,一种文化复杂性的方法,对于复杂性问题来说将是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传统的机械性世界观对“范式简化”的推崇是人类盲目追求可控的结果,这塑造了以可控为目的的价值标准,而一旦当理论的结果无法导向可控,就会被质疑“这有什么用”。但复杂性科学的成果展示了能对复杂性领域做到知道就已经非常不易,事实上很多事物在本质上无法实现可控。因此,在对国际关系复杂性领域的探究中,知道与可控都应该作为科学性的评价标准。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将复杂性、复杂性科学的成果和思想引入到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盲目追求可控性而导致的最糟糕局面。当控制成为最主要目标,会导致复杂性朝着脱离人类控制的方向发展。在国际关系领域,对权力、发展的过度追逐会导致自然环境恶化、国家间恶性竞争等问题,控制最终会导致失控,进而产生无法挽回的系统性风险。而以知道为目标,则会在认知复杂性的过程中尊重复杂性,从而避免陷入控制风险的悖论当中,这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尤为重要。这就要求人们不应该在面对复杂性事物和难题的时候畏缩不前(在问责制下,这似乎是一种普遍性的“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应该充分发挥适应性能力,理性地认识到“照常行事”的作用,以及可以在必要时突破“照常行事”,进而解决“照常行事”所带来的复杂性困境。这需要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拥有者能够在信息不完善、充满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采取适应性行动,而不是忽视复杂性。没有人能够在复杂性的时代以墨守成规的方式掌控一切,人们只能在不断的适应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