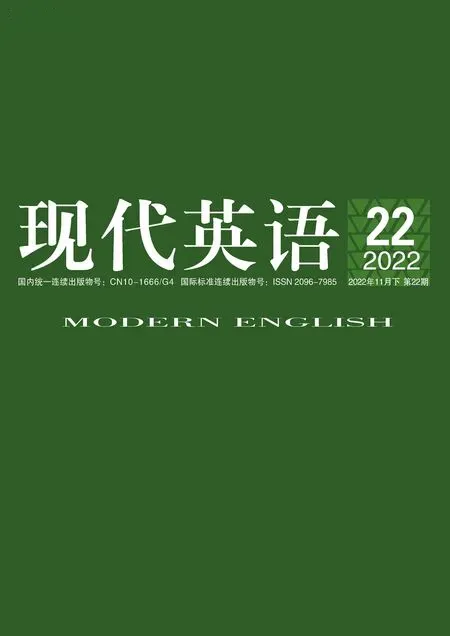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2022-02-23廖银叶
廖银叶
(成都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自1972年霍姆斯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三届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发表翻译学学科奠基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以来,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回首半个世纪的学科发展史,翻译活动、翻译现象、翻译研究三者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属性日益加剧了翻译学研究者学科背景的混杂程度和研究成果的无序状态。迄今为止,“冠以‘××翻译学’或‘翻译××学’之类的‘交叉学科’有61种之多”[1],这使一个新兴学科从表面上看似百家争鸣、花团锦簇,可实则“研究问题的视点散乱,学科边界模糊,学科自身的独立性漂浮不定”[2]。翻译学正面临严重的学科泛化危机,此危机轻则遏制译学的高质量发展,重则令译学分崩瓦解。要消除学科泛化危机,翻译学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明确自身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特征,即划定学科本体疆域,并将自身的本体理论尽可能地数学化,使译学理论逐渐从概念体系向定律体系突破,以此精简优化译学基础理论,最终使翻译学获得可叠加式发展的生长力。
二、何为译学本体理论
方梦之[3]将译学发展的时空路径归纳为“一体三环”,即自古到今的翻译原理、策略、技巧作为译学本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的语言学途径研究作为译学内环,七八十年代起的交叉学科途径研究作为译学中环,九十年代起的文化技术途径研究作为译学外环。其中翻译原理、策略、技巧是译学基本组成部分,即译学本体。人类语种繁多,不同语对的语际翻译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翻译原理、策略、技巧,所以译学本体应该建立在不同语对翻译原理、策略、技巧的普适性理论之上。因此,译学本体理论的构建注定是个漫长而浩瀚的大工程,但是学术共同体可以从最常见的语对入手开始构建,尤其是汉英互译。
三、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的必要性
现代科学的成功依赖两个要素:实证方法和数学方法。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和认知翻译学取得较快发展的原因就是在研究中采用了实证方法,而当下翻译学的学科泛化趋势亟需数学方法的介入。自然语言是由人驱动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它虽然不完全具备自然属性,但自然语言和语言符号转换都属于信息的范畴,都可以用数学方法加以研究。翻译学的发展经历萌芽、初创、兴起、稳定后,目前正处于深入阶段,学科共同体内部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但由于翻译学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者庞杂的学术背景,这些译学理论目前还处于零散、重复和无序状态,学科一体化的趋势不太明显。此时亟需具有较强信息整顿能力的方法论介入,而数学是秩序的科学,是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基础学科,具有化繁为简、能建构公理化理论体系的功能,当下的翻译学可尝试用数学的方法精简和整顿译学本体理论,让译学理论从硬态试错体系演进到科学体系。
(一)数学方法强大的信息整顿功能
翻译学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往往会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阐释,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即便得出本质上相似的研究结果,最终也会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理论表述。比如,据芒迪[4]统计,有关翻译策略的术语就至少有9位理论家提出了9对不同表述,分别是施莱尔马赫的“顺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奈达的“功能对等”和“形式对应”,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维奈和达贝尔内的“间接翻译”和“直接翻译”,诺德的“工具性翻译”和“文献性翻译”,豪斯的“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图里的“可接受性”和“充分性”,赫尔曼斯的“译文倾向”和“原文倾向”,以及韦努蒂的“归化法”和“异化法”。其实这9对术语大同小异,都是要么基于目标语的翻译策略取向,要么基于源语的翻译策略取向。而9种不同的说法一直充斥在不同的学术表达中,类似这种冗余的译论形态无疑是一种学科内耗,延迟了翻译学的学科一体化进程和高质量发展。翻译学研究者可以尝试将这对翻译策略的数学本质剥离出来,呈现为公式样态,以此固化和标准化翻译策略的学术表达。数学方法具有化繁为简、直击问题本质的特征,利用数学方法对翻译学内部积累的理论进行精简和压缩,势必可以起到助推学科一体化的作用。
(二)数学方法的公理化体系建构功能
除了语料库翻译学、认知翻译学等少数采用了实证方法的翻译学研究途径,大部分译学研究途径都属于人文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人们为了抓住事物的属性,往往先建立定性的概念,然后用例子或者实验阐明事物所具备的属性及其特性。大部分人文学科的研究往往就停留在这个层面。”[5]翻译学也不例外,译学理论的研究焦点经历了从文本字词、句子、篇章、社会文化语境,到译者惯习、多模态、实证化、数据化等的转变,目前学科内部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共识,这些知识形态目前还处于无序零散状态,加之各个学派缺少互动和融合,学科泛化趋势亟需加以遏制。“当一门科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知识,需要按照逻辑顺序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时候,公理化方法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6]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即演绎法,包含实体公理化、形式公理化、纯形式公理化三种发展阶段。翻译学可以从自身的本体理论入手,通过初阶的公理化方法构建坚实的翻译学基础理论,从而让译学理论获得可叠加的有序生长能力。我们相信“只有抽象程度高的理论形态得以较好的发展才是学科成熟的一种标志”[7]。
四、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的可行性
具有远见卓识和一定数学素养的译学先行者们早就进行了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的尝试。早在二十世纪末,范守义[8]就曾用数学公式的方法量化表达了译作与原作接近的程度,范守义[9]和穆雷[10][11]曾尝试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译文进行定量评价。可在翻译学蓬勃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初,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的进一步探索却在花团锦簇的各式研究路径中偃旗息鼓。此时,我们有必要再次追问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到底是否可行。
(一)机器翻译领域早已理论数学化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活动不可逆转地朝着人不同程度介入的人机耦合式翻译模式演变,为了提高翻译效率和降低成本,机器翻译成为翻译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主要的翻译形式。自1949年韦弗在其翻译备忘录中提出用密码学方法进行语际翻译的设想以来,伴随方法的革新与迭代,机器翻译经历了基于规则、基于统计、基于神经网络三种模式,目前最优的基于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工作模式有两个主要支撑,分别是计算机可读的语料数据以及算法程序。其中算法程序是核心,而“机器翻译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表示一个句子?统计机器翻译把句子的生成过程看作短语或者规则的推导,这本质上是一个离散空间上的符号系统。深度学习把传统的基于离散化的表示变成连续空间的表示。”[12]也就是说,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核心工作原理是将句子表达为一个实数向量,翻译过程被描述为一个可用梯度下降等方法进行优化的连续空间模型。因此,这样的工作原理“具有很好的数学性质并且易于实现”[13]。由此可见,在真实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机器翻译已率先实现了理论数学化。
(二)人工翻译可从句子层级入手进行理论数学化
不管出于信息安全考虑,还是出于文学翻译等的人文需求,人工翻译在真实的翻译活动中终将占有一席之地。在句子层次,机器翻译过程可以被表达为用梯度下降等方法进行优化的连续空间数学模型,人工翻译也可以根据源语和目的语各自的句子生成机制及句子转换机制构建翻译的基础理论。比如,汉语句子是个形式相对松散的意念流,英语句子是个相对主从分明的形式框架。英译汉实际上是个去形式化的过程:“词、词组、小句转换成汉语的各种词组结构,这些结构再以话题为龙头、以意合方式为主呈显性铺排开来组成句子。”[14]而汉译英则是个形式化的过程:“将汉语原文的各种词组结构进行逻辑分析,以确定英译的主语和谓语、各种并列及修饰成分的从属关系,从而构成层次分明的形式构架。”[15]至此,对汉英互译基础理论的定性分析已经达到较为凝练的程度,即在句子层级,英译汉是去形式化的过程,汉译英是形式化的过程。但这种理论表述只能算作硬态试错经验总结,无法让翻译理论获得可叠加式发展的力量。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将英译汉即去形式化过程、汉译英即形式化过程的数学内核剥离出来,最后用数学建模的方法将其呈现为公式样态的定律。这样翻译学理论才能从概念向定律方向突破。当然,要落实这一步,要将硬态试错经验升级为软态逻辑模型,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当的认知水平和数学素养。
(三)向语言学借鉴数学化成果与方法
语言学科学化是语言学研究者在大数据时代的追求。狭义的翻译即语际翻译,其本质是语言符号转换,虽然在文本外领域,语言学途径的解释力会被稀释,但不论何时,“翻译之文本目的乃译者的根本目的”[16],翻译学的本体研究都应该围绕语言符号转换开展。“翻译研究之所以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正是由于运用跨学科研究成果,尤其是语言学及其跨学科理论,使翻译研究从‘封闭的、狭隘的小圈子’走向与现代学科相结合的道路。”[17]即使经历了后来的文化转向,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数据转向、认知转向、社会转向,语言学依旧是翻译学的母体学科,“语言学这座‘矿山’也还没有被充分开掘,还有很大的应用空间”[18],因为语言学本身也在不断地精进和拓展。数学性质较为明显的语料库语言学、计量语言学、依存语法等语言学分支已获得大量可被翻译学借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有待具备相应跨学科素养的研究者进行鉴别、移植、整合、简化。翻译学的研究重点看似在不断转移,其本体理论和基础研究始终都应该围绕语言符号转换进行,向语言学借鉴成熟的数学化成果与方法将是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的必经之路。
五、结语
目前,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面临两重阻力,即研究者的学科一体化意识不足,以及研究者的数学素养不够。首先,在翻译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由于翻译本身的复杂性和翻译研究者的多元学科背景,学科一体化的趋势不明显。研究者要有明确的学科一体化的意识,研究者的心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科发展的进程和走向。[19]其次,由于翻译学学者大都出自人文社会学科,不具备较高水平的数学素养,这导致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者的认知水平无法解释和描述真实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相信随着文理分科教育制度的改良以及研究者自身的认知拓展,翻译学学术共同体的数学素养会逐步提高,译学本体理论数学化能得到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