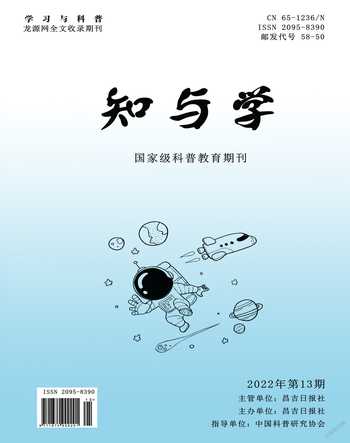中韩古代小说自我评点的比较分析
2022-02-23刘亮君
摘要:《聊斋志异》与《天倪录》是中韩二国古代文言志怪作品的主要代表,二者在作品正文后面通常都附有作家的自我评点。通过对比二类评点作品,其共性就是评点具体内容都是对正文叙事的补足,并反映了作者的个人。不同之处是《聊斋志异》在评点具体内容上选取富含象征意义的神话故事,饱含强烈的社会情感色调,敢于批评社会现实;而《天倪录》则是着重考虑神话故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并遵循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思想。而产生这些不同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除去作者作家的个人原因外,还涉及成书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和所处的小说发展阶段不同等原因。
关键词:《聊斋志异》;《天倪录》;评点
一、《聊斋志异》与《天倪录》自我评点之比较
1.1作品的自我点评往往具有画龙点睛之效,即是对故事内容的补充与引申。作家在叙述了作品正文的故事内容之后,再对自己所创作出的艺术形象进行了点评,又或借题进行引申开去,有助于引领阅读更深入地认识作品的正文。比如,在《聊斋志异》许多故事篇末,异史氏曰成为一种固定文体,如《促织》中的评论就尤为精彩:“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能忽也。”这些评语虽简单,但却极大推进了叙事的主旨。在《天倪录》中也是这般,《御史巾帼登筵上》和《提督裸裎出柜中》,两位朝廷官吏都被嫖妓所耍,而作家在评价中则重点是突出官吏本人的坦荡,耿直才是关键问题:“人苟非介狄,何以至此,凡遇妖冶者,盖以此為鉴,勿为其所误矣”。
1.2作品的自我评价观点鲜明,充分表现了作家的审美情趣与魅力。评论通常附于作品尾部,其时间长短不拘,但内容与风格也不限,因此作家们常常都可以借此直抒胸臆,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聊斋志异》的主要作家蒲松龄,饱经仕途之崎岖,也亲眼目睹了社会之各种丑陋,所以他的评论中也多含有“孤愤”之语,文风犀利豁达,而对待一些真善美的事物,作家又丝毫不掩饰自已的热爱之情,正如他评点中亲切地称谓婴宁为“我婴宁”。总之,这些评点本来便是作家作品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内涵上的深度,而透过这些还能够更进一步地理解作家的特点。从对《天倪录》的评论中,你可以看到作者的幽默也反映在对两个故事的评论中:《阎罗王托求新袍》和《菩萨佛放观幽狱》,均写着阎罗王,不过两个故事中的阎罗王形象亦非相同人,所以评论中调侃说“何其数易耶?”作者顺带又说:“据释氏之说,则天堂放在天上,地狱放在阴间,而洪乃范见地狱去天国只有几百步,何其近耶?此二说余听而断曰:荒唐。”作品观点鲜明,而又不乏风趣。
二、两书自我评点差异之原因分析
2.1《天倪录》与《聊斋志异》二书的社会创作背景存在差异
儒家思想文化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而朝鲜半岛在公元4世纪开始就和我国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儒家思想对其社会文化也有重要影响。
《天倪录》一书的作家任埅,是生在这段时代的一种传统文化士子,而儒家思想对他的创作影响也自然深刻,所以对他的作品评点都遵循了儒家道德传统,宣扬封建教育,而不会有过多的个人追求和反叛思想,也自然就易于掌握了。
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创作于清代,科举制度和功名意识牢固,蒲松龄本人的日常生活经历及其黑暗的中国社会生活实际却促使他更加富有反抗精神与奋斗的意识,个人情感更加强烈,并勇于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批评蒲松龄饱受的生存艰辛和科举向隅;常年困于场屋,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把阅读、教书当作生命的重要内容。从十九岁后,屡应乡试均不中,年近古稀时才援例取个岁贡学生的科名。所以他对科举利弊的感觉特别强烈,再加上当时中国社区贪污受贿、吏治腐朽等官场现状普遍,所以在《聊斋志异》里的一些评点中不遗余力地对社会现象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2.2从文学传统来看,二书所处的文学发展阶段存在差异
我国通俗文学发展在明清时代即达到了高峰,明代长篇小说的四部奇书、三言二拍等,均是社会影响巨大的佳作,而《聊斋志异》则是我国继初唐传说以后,文言短篇发展的巅峰之作。而反观朝鲜半岛,它的汉文小说创作也有了相应的进展,而《剪灯新话》的东传直接影响了朝鲜传奇体长篇小说《金鳌新话》的诞生,而《太平广记》的刊行也促进了笔记体短篇小说集的诞生,小说《天倪录》中的“评曰”对叙事真实性的强调,显然应该追溯到史记文化,代表正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手法。依据现在的某些资源记录,任堕也的确对《史记》推崇备至,并将其作为了教学散文艺术的好样板。
对比中韩二国同时代的作品,能够明确知道各自文学所处的各个发展水准阶段。和我国的长篇小说繁盛时期一样,及至壬辰之乱以前,朝鲜长篇小说写作还处于初创阶段。《天倪录》中的“评曰”对叙事可信度的强调,其实质便是长篇小说写作中常触及到的虚实向题,类似的提问在唐传说中就已经大批存在,作家“有心为之”地叙述了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在结尾处作家却还不忘记地向读者一再交待,这是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果只是通过对明清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来看,这一提问就不再是我国长篇小说写作中最重要的困感。《天倪录》由于受小说发展客观水准的约束,不但风格还未到达纯熟的境地,其点评也更多地停滞在叙事的真相这一层次,未作深入的探索。而《聊斋志异》则处在我国文言短篇小说艺术发展的最成熟阶段,叙事的内涵也不仅仅停滞在单纯的野史趣谈记录,文章中语体多样化,进一步探索更深层的道德伦理思想,并勇于批评真实事件。可以说,“异史氏曰”的形式虽源于史传文体,但正是对这种史评样式的突破和发扬。
三、结语
经过对《聊斋志异》和《天倪录》自身评点形态的对比就能够发现,它们之间都具有共性,而这种共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自身评点这一形态基本特征的表现。而对二者的区别以及成因的剖析,我们能够从一个较小的侧面发现中韩小说之间不相同的发展道路,以及二国经济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所以本文也期望借助这样的案例比较,来引发更多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李苗苗 王士祯、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比较[D]. 牡丹江师范学院.
[2] 金盛姬.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比较研究[J]. 韩国语教学与研究, 2020.
作者简介:刘亮君(1992.11-),女,河北沧州人,韩国全州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东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