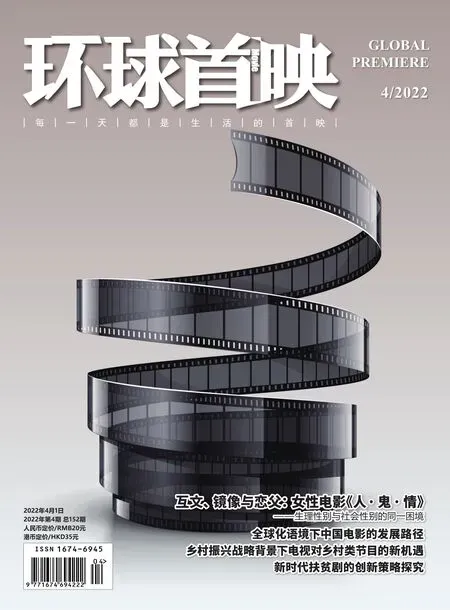互文、镜像与恋父:女性电影《人·鬼·情》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同一困境
2022-02-18王美丁湖南师范大学
王美丁 湖南师范大学
黄蜀芹导演的影片《人·鬼·情》以其对女性——人物原型裴艳玲的生命体验的深刻感知,曾获得了“当代中国影坛上,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女性电影’的唯一作品”[1]的高度评价。影片展现了女主角秋芸的童年记忆与戏剧表演生涯,以传统戏剧《钟馗嫁妹》作为索引,确定影片核心喻象为“钟馗”即秋芸心中的理想男性,并成为秋芸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无法被指认为一致的困境开端。
一、多重互文与性别心理
法国作家波伏娃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首次阐释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雏形。[2]序幕中,秋芸在姣好的面容上用油彩勾勒粗犷的钟馗男性脸谱,纤细的身姿逐渐被敦实的男性角色戏服所掩盖,直至秋芸的外在女性特征无法辨识。画面中,镜子前凝视的主体在扮成钟馗的秋芸与未成妆的秋芸之间不断转换,镜中画面逐渐呈现扭曲形态。镜头摇移,两种形象陷入混乱,无法分辨主体的性别。由此,序幕统摄全片,与秋芸性别困境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第一重互文:女性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矛盾。
以钟馗形象为索引,这一男性角色根植于秋芸的童年记忆——父母联袂演出的《钟馗嫁妹》。戏剧桥段中钟馗召唤妹妹,父亲召唤母亲,二人相拥,感人至深。此时,秋芸凝视着钟妹,心中种下了向往爱情、圆满得嫁的种子。舞台之上有钟馗的长兄如父,父母的爱情佳话,舞台下更有她的美满家庭。此时秋芸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在钟馗妹妹这样一个依靠男性的角色上,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上并未产生分歧。
而母亲的偷情迅速打破了爱情与家庭的圆满神话,并给她带来无法逃离的童年创伤与社会评价——有一个“跟人跑了”的母亲。这使秋芸带有了一种“劣根”,所以,她认为只要拥有一份正当的爱情就能打破这种标签。不幸的是,她终于要和张老师建立起爱情时,得知张老师已有家庭,这让她几乎要重蹈母亲的命运,被拉回到“劣根”噩梦中。事实上,秋芸没有实质上的越轨行为,但同事口中“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社会评价,早已“坐实”了秋芸的偷情。父母爱情的破碎结局与秋芸爱情的错误发生形成另一重互文。
幼年时,作为女孩,秋芸的“劣根”使她在以男孩为主体的同伴中受到排挤。此时的一重互文关系体现在:同伴小二娃曾与秋芸分享着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被男孩们围追堵截时,她希望小二娃承担拯救者角色。而小二娃“叛变”加入了嘲弄秋芸的队伍,秋芸和小二娃扭打,却被完全压制。这是一个具有充分社会隐喻的情节,面对一群男性时,哪怕一个男性她都无力招架,她深刻地体认到了作为女性首先在生理性别上的体格差距,其次是在面对社会评价时,她因社会性别为女的弱势与失语。这也是她要求扮演男性的原因之一。
成年时,作为女人,秋芸偷情的“事实”使她被“劣根”所完全标记。由此不被社会评价肯定、长期饰演男性的她,彻底游离在社会所规定的性别范围之外。于是,在秋芸与钟馗的形象上形成一重“灰色”互文——秋芸处于社会性别范围的灰色地带,钟馗处于阳间与阴间的灰色地带。
二、镜像与同一困境
《钟馗嫁妹》的情结深深根植于秋芸内心,影片中通过多个秋芸“凝视”的特写镜头来展现。这种欲望的“凝视”,不同于劳拉·穆维尔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所说的:“女性即影像,男性即看之载体”[3],也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学脉络中,以男性作为分析主体,女性作为男性精神分析注解模式。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的观看行为,投射女性的欲望,是影片《人·鬼·情》可以作为女性电影被解读的基础视点支撑。借用学者戴锦华在《电影批评》中对拉康镜像阶段理论及“凝视”的阐述:“当我们不只是‘观看’,而是在‘凝视’的时候,同时携带并投射着自己的欲望”[4]可以对电影文本中的多重镜像以及秋芸的性别困境的形成过程做以下分析。
儿时,秋芸将爱与家的欲望投射在钟妹身上,她的传统性别意识滋生。这奠定了钟馗及父亲分别在她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拯救者地位,解释了她拒绝母亲而拥抱父亲的行为。她拥抱的是美满家庭的维护者,被母亲辜负的家庭英雄,更是曾经完整的家庭记忆。
秋芸的性别意识真正形成于伙伴的羞辱中,并使她认识到因携带母亲的因子而被社会唾弃。这是她被迫自我指认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时刻,“他已然能在镜子中辨认出他自身的影像”。[5]伙伴背叛,钟妹作为理想自我的被拯救愿望落空。“婴儿会痴迷于自身镜像,并做出一系列的动作与之互动,以一种游戏般的方式不断探究镜像与自身、镜中影像与现实环境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6]只要秋芸承认自己社会性别为女,就会召唤她“劣根”的历史。于是,有了钟馗喷火的镜头,这既是她期望拯救者出现,也是她希望获得强大的力量。
少女时,秋芸初次扮演了传统男性角色。在舞台上她展示出的戏剧才能不仅赢得了观众的掌声,而且使她感受到借助男性角色便能获得正面社会评价。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其论文《表演性行为与性别建构 关于现象学和女性主义理论》中指出社会性别是有“表演性”的。[7]秋芸的男性角色演出具有双重性:既是一种舞台角色扮演,也是一种社会角色表演。在社会活动中出演男性意味着淡化女性社会性别。这是秋芸为逃避社会评价而陷入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一致的第一步。
在不断地塑造各种传统男性戏剧角色的过程中,秋芸体会着角色身上的力量、智慧以及“男子气”。在扮演过程中,她首先认同于角色的性别气质,进而获得了理想男性、理想社会评价中理想自我的画像。
根据拉康镜像阶段理论,婴孩在镜前构建自我时将镜中的“理想自我”误认为真实自己,这正是一种自恋的生命历程。[8]学者戴锦华亦在著作《电影批评》中通过自恋与理想自我投射对偶像崇拜进行了阐释:“那是再次把自我投向他者,将他者想象为理想自我的实现的心理机制。”[9]秋芸表演着心目中拯救者应有的样子,以此表达对拯救的渴望。她享受自己与理想男性形象上的高度接近、生命体验上的高度融合,更享受舞台成就和掌声,使她在理想男性拯救者庇护下暂时逃逸了社会评价。因此她同样迷恋着扮演理想男性时的理想自我。自恋性认同使秋芸的钟馗情结始终根深。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霸王别姬》中小豆子:“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性别认同错位,秋芸的性别困境从来不是社会性别的自我指认,而是社会性别无法被他人指认。她首次遭遇社会性别不被指认是厕所门口的窘境。她被指责是男孩冒闯女厕时,张老师作为男性拯救者在社会中指认了秋芸的性别。
成年后,“谁是假小子,我是真闺女”的困境依然困扰着秋芸。张老师对秋芸的爱护唤起她最初的被拯救愿望,社会性别被指认的欲望也愈发强烈。凝视着张老师:男性拯救者与男性拯救者戏剧角色的高度重合,爱欲让她摘下胡须,勾勒花旦的妆容。这是秋芸社会性别彰显要求的显露。张老师对其容貌的称赞指认了秋芸的社会性别,同时,张老师又肯定了秋芸出演武生的“男性大美”。爱情激励秋芸内心性别意识的高涨,又助推着秋芸继续扮演男性。于是在内部意义上,秋芸的女性意识成长,将更加渴望社会性别得到指认;在外部意义上,坚定出演男性角色的决心又反作用于秋芸的社会性别指认,困境进一步加深。
拯救者的工作张老师始终无法承担。已有家庭的张老师给秋芸留下的不仅是无果爱情的创伤更是流言席卷。社会评价的阴影复现,舞台上的尖刺如对“偷情”女子的惩罚,扎伤秋芸。尽管周围同事都投以关切的目光却没有一人伸出援手。绝望境地中,秋芸陷入抓狂,而钟馗此时作为主体凝视着她。钟馗的出现意味着秋芸始终被放置在客体位置,等待被救却无法得救。此前理想自我的“自恋性认同”不过是“自我通过认同于与自身相异化的镜像而将一个他人引入了自己的形式结构中[10]”,不过是对镜像的误认:“自我即是一个他者[11]”。
失去拯救者意味着失去社会性别被指认的可能。在秋芸提出合演《钟馗嫁妹》后,她将最后的被拯救可能寄托在父亲身上。然而,秋芸的被指认愿望被彻底驳回——接生婆道出父亲曾热烈期许得到的是一个男孩。
影片中几乎隐形的秋芸丈夫,在“扮男的,他嫌丑;扮女人,又担心”的陈述中对秋芸的身份不予肯定。不论是二娃、张老师、父亲还是丈夫,秋芸生命中的男性角色都无法承担拯救角色。因而在尾声中秋芸凝视着钟馗,投射着被救之欲;钟馗凝视着秋芸,印证着拯救无望。“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使秋芸达成自恋,而最终“嫁给舞台”,并因此永远凝视着理想自我的虚像,性别永远陷于困境。
三、恋父情结与叙事策略
恋父情结又称厄勒克特拉情结,指的是“女孩子常迷恋自己的父亲,要推翻母亲取而代之”[12]。秋芸在影片中多次表现出恋父倾向以及为逃离社会评价而淡化社会性别的举动,印证她的恋父情结。她所恋之“父”不仅是父亲,而是一种以钟馗为集中体现的拯救者形象,父权体制下传统的大男子形象。
她最初的欲望始终是被拯救,于是她把凝视投向钟妹而崇拜其兄;发觉母亲偷情后,渴望被安慰,她投入父亲怀抱并拒绝母亲。在秋芸的少女时代,她与父亲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后台父亲为秋芸画眼描眉、家中父女亲昵地相拥凝视。此时父亲是秋芸的钟馗,但这并不是她的生父。厕所门口的解救与演艺生涯的引导、爱情的诱发,使张老师成为秋芸的精神之父,但这并没有为秋芸带来爱情。面馆中她虽与生父相认,但这是一个为秋芸带来永久创伤且隐形的男性。
秋芸对这些男性或眷恋、或爱恋,这种恋父情结更直观地表达为:女性无力作为行动主体时,选择男性盔甲的社会行动策略,是女性由于长期处于“第二性”而难免将自己先在地放置于被动困境中的心态。伴随社会性别被指认要求得越发强烈,占据着社会话语权的男性自然成了秋芸投射期许目光的群体。但这样一群诞生于父权社会的男性中没有一个人能为秋芸提供拯救。她只能通过扮演拯救者来呼唤救星,实际上自己却时刻需要被救,矛盾无法弥合。
作为一部女性电影,却塑造了一个将自己寄托于男性的女性形象,这似乎使影片出现裂痕。实际上,这与导演的女性主义观有着密切联系。黄蜀芹谈道:“如果把南窗比作千年社会价值取向的男性视角的话,女性视角就是东窗。”[13]它并不是激进的男女社会价值取向二元对立,而是谋求女性社会价值取向与男性价值取向同等地位的显现。这是一种相对柔和的性别要求,也是导演在影片中采取的迂回叙事策略。
四、结语
女性电影《人·鬼·情》在多重互文的叙事结构下反映以秋芸为代表的女性所面临的社会性别指认过程中的社会评价危机,与应对评价而产生的性别心理。影片中秋芸因拯救者的始终缺席而将被指认之欲通过扮演理想男性加以表达,表现了秋芸通过自恋性认同在理想男性身上建立理想自我的完整镜像过程。最终由于无法兼任拯救者与被救者而始终陷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困境之中。
由于秋芸先天的被动与“第二性”位置,预设了秋芸的恋父情结与依靠男性力量获救的空想在传统父权社会中的必然失败。这反映出导演非二元对立的朦胧女性意识及时代背景下逐渐增长的女性意识彰显要求。在影片创作的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与发展,外来事物与观念大量涌入,女性主义思潮渗透大众文化视野,并开始进入并影响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创作。《人·鬼·情》中秋芸所携带的传统女性文化基因与性别意识彰显着导演意志与时代脉搏、女性的社会性别指认诉求,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逐渐升级的性别困境与愈发强烈的发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