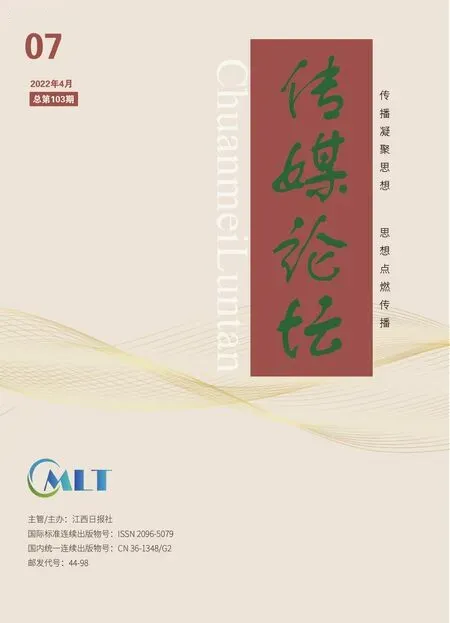保守进步共存、类型表演与身份重合
——联华影片公司明星现象研究
2022-02-18胡晓钰
胡晓钰
中国的明星研究起步较晚,在尚未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规范的当下,被大力书写的一类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早期上海电影中的女明星,另一类是颇具“断代史”意味的享誉世界影坛的华语明星个案研究。前者更多地从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上海城市文化景观入手,聚焦早期电影女明星的身体表演、服饰修辞以及视觉政治,通过对女明星的研究以点带面地勾勒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意义;后者则契合了近年来国外电影学者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研究兴趣,黄柳霜、胡蝶、李小龙等具有“东方他者”代表性的华语电影明星成为窥探中国电影文化不可或缺的镜像。在当前国内明星研究现状之下,联华影片公司明星现象研究有其独特意义。联华明星现象作为一个模糊性别界限的群像研究范本有助于我们真实还原20世纪3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中明星现象的建构与形成。本文即采用明星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全面剖析1930—1937年间联华明星群像,以拓展联华影业研究的思路视角。
一、意识形态交错下的联华明星
联华作为20世纪30年代主流电影公司,其高层与当局政府有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1932年,左翼电影渐兴之时,国民政府电影审查委员会便给予了联华公司“特殊关照”。意识形态的强制干预直接导致了1932年—1937年间联华电影创作的复杂性——既有表达进步意识的左翼电影,又有响应当局“新生活运动”政策所拍摄的表述传统民族文化意蕴的旧市民电影。保守与进步共存的意识形态交错下,也催生了联华明星群像里的两种现象。
(一)延续保守形象的联华明星
传统的礼教美德在流畅而现代化的电影语言中将观众缝合进一个唯美虚拟的“现实”。宣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适当地冲破礼教束缚获得理想主义婚约,联华初期的旧市民电影迎合了主流观影群体审美趋向的同时,也以鼓励和娱乐观众为最终目的。因而明星在影片中的角色都是配合经典叙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审美的正统形象,他们的银幕形象、本体形象基本趋于一致,男性明星多谦谦君子,女性明星多贤妻良母,成为下层市民欲望投射的焦点和改造自我的范本。其中,汤天绣和周文珠正是作为符合旧市民电影审美情趣的典型的联华明星代表。
汤天绣和周文珠都曾所属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在《儿孙福》《连环债》等影片中多次合作。1930年加入联华后,汤天绣、周文珠继续合作了《自由魂》《爱欲之争》《恒娘》《海上阎王》。两人在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一静一动、一善一恶而互为表里,成功塑造了传统男权社会下依附男性意志生存的农村贤妻/城市荡女形象,其明星定位符合20世纪30年代初期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美学。
汤天绣生于绅商世家,成年后嫁做人妇,作为资深影迷终日痴迷电影,1926年大中华百合公司新片《儿孙福》的演员招聘启事促成她如愿以偿进入大银幕。黄漪磋所作《汤天绣小史》中评价:“天秀富有表演艺术天才,并庄重与浪漫两派而兼能之。然除服务影场而外,绝少交际。迥非时下一般佻健浪漫之明星可比也。”[1]可见汤天绣不但成功塑造了乖巧少女、泼辣少妇、富贵慈母等多变但保守的银幕形象,而且还坚持以人妇身份在纷繁复杂的影坛中克己复礼,在事业和家庭生活中找到了平衡点,其银幕形象与个人私生活的高度契合,成为职业明星隔绝绯闻八卦的天然屏障。
1931年后,汤天绣的形象开始出现变化,而要论述其明星形象的嬗变不可不提供周文珠作为她们两者银幕塑造的参照坐标。汤天绣自1931年《自由魂》始,与周文珠在《爱欲之争》《恒娘》《海上阎王》影像文本中结成城市荡女/农村贤妻互为表里的银幕形象。《自由魂》剧本乃孙瑜有感于广州黄花岗起义而创作,电影中周文珠饰演不畏强权而被杀害的罗超(高占非饰)之母绿娘,懦弱无力被恶霸欺凌的李雪花则由汤天绣主演,这是入联华后的汤天绣、周文珠首次合作,更是两者银幕形象走向异质化的肇始。《爱欲之争》讲述传统男性接触城市花天酒地后良心责备,进而与前妻重修于好的故事。周文珠、汤天绣分饰农村贤妻周婉贞、城市荡女李丽华。可以看出,周文珠与汤天绣两者形象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明星形象正是20世纪30年代新旧意识形态交替之下观众审美多元化的体现。
如果说汤天绣明星形象的转变是主流意识形态面对女性意识觉醒而不得已作出的让步,她在联华进入左翼电影创作阶段后再次回归贤妻良母的安全区域——《都会的早晨》《渔光曲》等左翼电影中多演少妇/母亲角色,正是意识形态操控明星塑造的绝佳范例。那么周文珠从影伊始便塑造贤良淑德的传统伟大女性的高度统一性,则体现在她和王次龙(《自由魂》《爱欲之争》《海上阎王》导演)的夫妻关系上。在周文珠与王次龙合作的影片(包括两者作为演员的大中华百合时期)中,可体会到后者企图对周文珠进行的控制。似乎王次龙安排周文珠所饰演的无一不是温婉贤良且甘于牺牲自我的贤妻良母形象,颇值得考究的是《自由魂》罗绿娘这个角色,周文珠一以贯之的顺从形象由绿娘反抗德祥贝勒的霸占打破,但细思恐极——《自由魂》中的三个女性形象分别是敢于反抗统治阶层性骚扰的绿娘、逆来顺受被欺辱的雪花(汤天绣饰)以及不服管教对抗父权的香香(叶娟娟饰),周文珠为何能出演绿娘这个角色至此一目了然。而这种被丈夫或者说是男性意志所操控的明星形象,延续了周文珠的一生,依附性的懦弱人格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行乞街头的悲惨厄运。
(二)初具进步意识的联华明星
伴随左翼文艺战线联盟不断深入各影片公司创作腹地,左翼电影于1933年迎来了创作峰值。在观众强烈要求电影应表现时代风貌的新变化面前,公司运营者罗明佑当然不可错过商机,响应当局政令拍摄主旋律电影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夹缝中举步维艰地推进左翼电影创作。包括国防电影在内的1932—1937年间,初具进步意识的联华明星形象有如下表现:
健美活泼的新女性。在系统化现代教育的普及等多方作用下,催生了以实际行动反抗宿命论和反映社会底层苦难的新女性,在左翼电影运动中她们纷纷走上银幕,凭借健美向上的身体展示和叛逆反抗的行为方式,横扫长期占据影坛的倾向保守而又克己复礼的传统明星形象,改变了当时电影明星的固有印象。黎莉莉——甜、王人美——野、陈燕燕——娇,创刊于1947年的戏剧、电影综合画刊《艺声》曾经这样描述联华的三位当红花旦。梳理她们的从影经历不难发现:青春活泼的黎莉莉、野性泼辣的王人美形成了一种开放式健康女性美,这与表演跨度较大以哀怨温婉为标志性特质的陈燕燕内敛式都市少女气质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健美活泼的新女性典型。
百态丛生的新男性。左翼电影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百年中国电影史上女性不曾被置于被看客体的短暂时期,百态丛生的“新男性”配合健美活泼的新女性,一起构建了银幕上进步鲜活的视觉观感。郑君里是联华影片公司进入左翼电影创作阶段后第一个推出的“新男性”明星。他1932年初入联华影业之时恰逢左翼电影创作洪流席卷上海电影界,其外表俊朗、温文尔雅的小生形象引起了孙瑜的关注,自《野玫瑰》出演城市街头画家小李开始,郑君里在联华期间共拍摄14部影片,具有进步思想意识的热血青年和城市知识分子是他左翼“新男性”的主要银幕形象。其中尤以《火山情血》里为父报仇的冷面小生宋柯、《共赴国难》中参加义勇军的热血新青年、《新女性》中生活贫苦却意识前卫的文学编辑余海涛以及《大路》中慷慨就义的修路工人郑里四个鲜活进步的角色使人印象深刻。郑君里极具正义感、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热血青年银幕形象彻底将旧市民电影时期恪守礼教、优柔寡断的传统男性打入历史尘埃。对比此时银幕上呈现的明星形象,积极向上敢作敢当的男性明星同健美活泼野性泼辣的女性明星成为反应左翼电影潮流最为直观的表现载体。
二、全产业链电影格局下的联华明星
联华影业用时短短三年便建立起制片、发行、放映于一体的垂直整合产业链,这对于签约联华的明星们来说,公司上下联动的资源配置间接使他们获益无穷。类似于同时期经典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将演员放置于流水线作业之上,类型演员的涌现是其必然结果,而众多联华明星也在公司制片、发行、放映的一体化经营策略中得到磨练,成为影史上最早践行“演而优则导”的明星。
(一)类型演员的涌现
喜剧演员的尝试与探索。在类型演员丛生的联华影片公司,以韩兰根、刘继群、殷秀岑为代表的喜剧演员成为一道独特又别具意蕴的景观。联华早期的喜剧电影以滑稽短片为主,其中韩兰根、刘继群于1933年合作《清道夫》形成固定搭档,至1937年联华停业,两人共完成《如此英雄》等十五部喜剧电影的拍摄,逐渐形成联华喜剧电影的创作格局。因擅长滑稽表演以及一胖一瘦的外形体征,刘继群、韩兰根被联华有意识地往中国的劳来、哈代方向培养,而另一位以胖为辨识度的演员殷秀岑也在1935年加入这对喜剧组合。三人先后拍摄《天作之合》《联华交响曲·三人行》等开始摆脱单一闹剧转向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生存悲喜的现实主义喜剧电影,其中殷秀岑在刘继群病逝后代替其位置与韩兰根重组昔日黄金组合,他们承袭卓别林“笑中带泪”表演精髓,辅之劳来、哈代式滑稽肢体动作共同将中国早期喜剧电影推向了新高度。
蛇蝎美人与反派小生。在三七卷发、西装革履成为20世纪30年代社会风尚的大众潮流里,明星作为视觉观感的呈现载体,他们以崭新的摩登形象和前所未有的豪放不羁的言行,成就了早期电影银幕中以谈瑛、黎灼灼、梁赛珍、貂斑华为代表的蛇蝎美人,以何非光、袁丛美、章志直、洪警铃为代表反派小生形象,他们共同建构起20世纪30年代明星形象百态丛生的多样化图景。极度叛逆的“黑眼圈女郎”谈瑛、风流爽辣的摩登名媛黎灼灼、妖冶舞姬梁赛珍以及擅长利用媒体炒作的貂斑华常年在都市经验的浸染中受到好莱坞电影文化的影响,达成了现代意识上的共鸣,“在她们的思想意识里,客观地说,现代主义的女性思维多于左翼文艺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政治倾向性”[2],这些魅惑与危险共存的都市女性以蛇蝎美人的反派形象成为贯穿联华整个创作周期的明星形象补充。而与蛇蝎美人遥相呼应的是何非光、袁丛美、洪警铃等反派男性明星形象,买办商人、纨绔公子、刁钻小人、市井流氓以及玩弄女性的恶魔是反派男性的主要银幕形象。尤其章志直、洪警铃等老牌男星进入联华影业后,继续发挥各自早年的表演风格也创造了百态丛生的反派角色。
(二)演员/导演双重身份的重合
联华影业集制片、发行、放映于一体的垂直整合产业链之于公司内部明星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一在于产业格局合理化引导表演走向成熟,促生类型演员的涌现;其二则是演员转型导演导致创作者双重身份的重合现象,反映出联华在创作人才发掘上的灵活性与开放性。演员/导演双重身份的重合作为早期中国电影屈指可数的产业现象,体现了影片宣发推广策略上的高瞻远瞩,再次成为电影全产业链格局下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艺人经纪的最大商业价值的实例。从联华走上电影制作道路的明星们,以公司制片环节的便利性打通了电影艺术探索的实践空间,通过具体的影片拍摄反而丰富了联华电影创作的层次性。
第一位借助联华平台进入导演创作生涯高峰的明星导演是王次龙,1930年他在拍摄完成《马戏女》后随大中华百合一起并入联华二厂。受国片复兴运动影响,王次龙进入联华后执导了《义雁情鸳》《爱欲之争》《共赴国难》《还我山河》《孤城烈女》五部或渲染婚姻自由、或唤起民众反抗的影片。他在联华早期初执导的影片呈现出海派文化浸润的明显痕迹,随着左翼电影思潮的勃兴,1932年《共赴国难》后他执导和参演的电影明显带有进步导向。王次龙之后,于联华影业运作的七年间进入导演领域的还有袁丛美。以反派小生著称的袁丛美先后执导滑稽短片《清道夫》、反映进步大学生投身革命洪流的《铁鸟》,联华期间的导演功力为其后在国统区抗战电影的拍摄积累经验。
纵观联华影片公司艺人名单,不难发现除王次龙、袁丛美这些在联华运作期间完成由演员向导演身份转变的明星外,郑君里、韩兰根、何非光、蒋君超、刘琼、欧阳红樱这些联华明星也成为影史“演而优则导”的典型。虽然联华并未提供给他们具体拍片操作的实践空间,但优秀类型演员的有意培养以及全产业链电影格局下资源共享的产业观念成为他们日后在导演领域厚积薄发的隐形资本。
进步与保守共存、类型明星的涌现以及演员转向导演的身份重合,构成了联华影片公司明星现象的主体表现。由于联华带有垄断特质的现代化企业运作模式,电影学界一直对其保持高度关注,产业研究成为剖析联华现象的重点研究途径,而明星与产业之间却有着休戚相关的纽带,因此从明星研究的理论路径切入联华公司研究不失为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