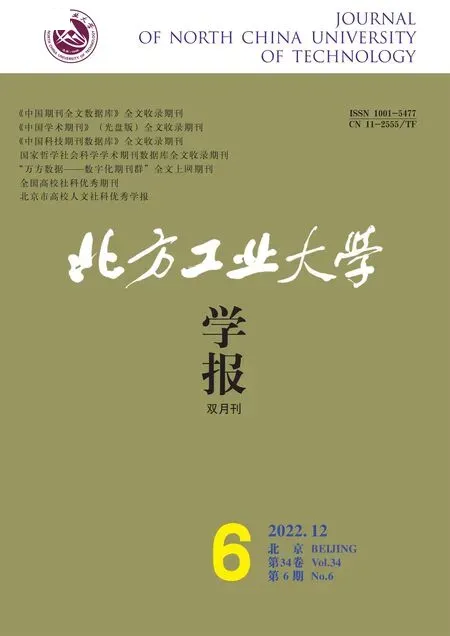影响与超越:从果戈理《彼得堡故事》到鲁迅《故事新编》*
2022-02-09李家宝
李家宝 何 力
(西安翻译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710100,西安)
《故事新编》是鲁迅研究的难点之一,围绕该作品展开的研究主要有三大方向:一是植根中国传统文学,寻找创作渊源;二是与本国作品的比较研究,如与施蛰存、郭沫若历史小说的比较;三是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比较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夸大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合理,但相较于前两类研究,第三类研究还比较薄弱。《故事新编》的创作主要受到日本和俄国文学的影响,如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便有与《故事新编》相同的“古为今用”的特点,但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早期,且偏于形式,而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对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影响则贯穿始终,且从形式上的模仿上升到了思想情感的共鸣。《故事新编》的总体意蕴和艺术形式都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不同的先锋性,开展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比较研究能为读者洞察鲁迅的创作动机,探寻《故事新编》艺术形式的来源提供新思路,同时也有利于明确鲁迅对世界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1 果戈理小说对鲁迅《故事新编》的影响
果戈理小说对鲁迅《故事新编》的影响,可集中见于鲁迅对创作《故事新编》态度的两次重大转变。1922年,鲁迅发表《补天》后“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可是1926年9月避难到厦门后,他又决定“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1]这是鲁迅创作态度的第一次转变。鲁迅创作态度的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晚年,这时他对《故事新编》的创作从动摇慢慢变成了坚定,他直言“此后也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2]鲁迅创作《故事新编》两次态度的转变都与果戈理小说对他的影响有着密切关联。
1.1 创作困境中的形式启发
从《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可以发现,鲁迅第一次创作态度的转变与未名社的信有关,1926年10月4日他在给未名社的信中写道:“我竟什么也做不出。”[3]10月7日,他收到了好友韦素园寄给他的果戈理的《外套》。[4]鲁迅极其珍视此书,他在《忆韦素园君》中写道:“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5]鲁迅的《铸剑》正是在1926年10月完成,而《奔月》也紧接着在12月完成。《故事新编》与《外套》创作形式上的相似可以证明,果戈理的小说在鲁迅从“什么也做不出”到很快完成《铸剑》和《奔月》的创作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给予鲁迅艺术灵感启发,帮助鲁迅重拾起创作《故事新编》的信心。此外,鲁迅这个阶段正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略》讲义,[6]整理阅读旧书也为他借鉴《彼得堡故事》形式进行古为今用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2 文学翻译中的精神契合
1934—1936年是鲁迅在世的最后三年,这一时期鲁迅除创作《故事新编》后期的五部作品(《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和写作一些文学评论、杂文外,主要精力都用于翻译果戈理的作品。1934年9月鲁迅发表了果戈理《鼻子》的译文,并附上了《〈鼻子〉译者附记》,如果将该附记与鲁迅1921年翻译芥川龙之介的《鼻子》时所写的《〈鼻子〉译者附记》进行对比,就会发现鲁迅创作态度的明显变化。鲁迅写第一篇附记的整体态度是基本中立的,他指出人们对芥川龙之介不满之处,就在于他多用旧材料。[7]而第二篇附记却旨在赞赏,他认为果戈理的《鼻子》“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8]读者对果戈理小说采用旧格式的认可,给予鲁迅继续创作《故事新编》的动力,这是鲁迅第二次态度转变的外在原因。
鲁迅第二次态度转变的内在原因在于与果戈理精神的契合。1935年11月鲁迅翻译出版了《死魂灵》第一部,12月他出资复印了《死魂灵百图》,1936年2月他开始翻译《死魂灵》第二部,据许广平所做《死魂灵》附记,鲁迅在临死之际,拖着病重的身体,“桌面铺满了书本,专诚而认真地,沉湛于中的,一心致志的”翻译《死魂灵》。[9]无论是出资复印还是抱病翻译,都反映出晚年鲁迅对《死魂灵》的看重。同时,这种看重也更加证明,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已经从形式上的借鉴上升到了精神情感的共鸣。翻译《死魂灵》的同时,鲁迅完成了《故事新编》后期几部作品的写作,他在果戈理小说中看到了与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相似的现象;他欣赏果戈理的讽刺才能,并把“含泪的微笑”运用到《故事新编》的写作之中;当他的讽刺被误解或扭曲后,他也能在果戈理小说中找到慰藉和坚持本心的勇气。
2 鲁迅《故事新编》的接受与超越
2.1 现实与幻想时空的建构
鲁迅《故事新编》双重时空的建构主要受到果戈理中期小说《彼得堡故事》的影响。果戈理小说早期爱写乌克兰的怪谈,但后来逐渐向人事转移,成为一种兼具现实与幻想双重时空的现代神话,因故事背景在彼得堡,因此被称为“彼得堡现代神话”。这种彼得堡现代神话“虽然在思维方法上借用古代神话的模式,但这些新神话往往与传统神话的内容已经相距甚远。作者通过神话模拟,实际上是通过神话化的方法来抨击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10]果戈理在创作《彼得堡故事》时,往往从现实的彼得堡时空写起,建构起涅瓦大街那样的真实环境,并塑造真实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之后却又逐渐走向怪诞。譬如将神话传说里幻化成独立人形的鼻子(《鼻子》),魔鬼寄身的画像眼睛(《肖像》),夺人外套的冤魂(《外套》)等注入现实时空。但幻想时空并不会掩盖现实,反而具有映射现实的穿透力。因为只有在幻想与现实、天堂与地狱、美好与丑恶的强烈对比中,读者才能更加清晰地窥探到下层文官对权利潜在的欲望(《鼻子》),才能从魔鬼的眼睛中体察到金钱对善良人性的摧毁(《肖像》),才能对暴死冤魂的悲惨命运产生更加深刻的反思(《外套》)。
鲁迅说他的《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1]这种演义与《彼得堡故事》有相似也有超越。在形式上,《故事新编》和《彼得堡故事》都建构了现实与幻想双重时空,不同点则在于果戈理是先建构现实时空,再注入幻想时空,虽然两者最后会融为一体,但两个时空有明显的割裂感,这束缚了文学的表达空间,削弱了小说的艺术张力。《故事新编》则用幻想时空中的人或事去观照现实,这种观照体现在各方面,有对现实时空中人的观照,如冯蒙隐射高长虹(《奔月》),鸟头先生隐射顾颉刚(《理水》)等;也有对时事的观照,如“文化山”隐射文人建议设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理水》),“募捐救国队”隐射国民党政府以“救国”的名义强行搜刮民脂民膏(《非攻》)等。由于古代故事没有现代那样明确的时空概念,因此鲁迅可以把现代人、事、语言穿插到古代故事中去进行调侃,呈现出古今杂糅,浑然一体的效果。总之,在形式上《故事新编》所构建的双重时空比《彼得堡故事》更加自然和完整。
在艺术目的实现上,《故事新编》与《彼得堡故事》都以构建幻想时空来为现实服务,最终在双重时空的对比之中凸显对现实社会的观照。作为一个狂热的基督徒,果戈理所建构的幻想时空常带有神秘主义和宗教信仰的色彩,《彼得堡故事》中的魔鬼形象就削弱了故事的现实批判力。而《故事新编》则是彻底的古为今用,用古代故事为现实批判服务。为达到这样的目的,鲁迅有意消解了原本故事中主人公身上的崇高感,他将女娲、后羿、眉间尺、大禹这样的英雄写成凡人,甚至将伯夷、叔齐、老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写成虚伪小人。人物形象古今、虚实的强烈对比,给读者带来巨大的认知冲突,这不仅能凸显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丑恶,还能唤起读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2.2 写实与怪诞手法并用
鲁迅多次称赞果戈理的写实本领,特别是他塑造“典型形象”的能力。鲁迅说:“《外套》里的大小官吏,《鼻子》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预见的。”[12]受果戈理创作的启发,《故事新编》的晚期作品尤其注重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而这时他正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如同果戈理扯去贵族身上高贵、华丽、文明的“外套”,将其肮脏、虚伪的魂灵赤条条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一样,鲁迅《故事新编》的晚期作品也致力于通过塑造典型来解剖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面。鲁迅说他《出关》中的老子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13]同样,《采薇》和《起死》也自然不全在讲伯夷、叔齐和庄子,而是将其作为儒、道两家的典型来进行批判,在“刨掉那些坏种的祖坟”之后,儒家的仁义道德便现出了伪善;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哲学则变成了空谈。
卓越的写实本领是果戈理和鲁迅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却并不是他们最为独特之处。果戈理小说和鲁迅《故事新编》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写实手法和怪诞手法的并用。怪诞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文化的基督时期,用来指一种把“人、动物和植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壁饰画风格。[14]它的基本特点是“不调和”,即对立物的合成。[15]这种“不调和”的特色可见于果戈理小说中异化的人物形象,如把外套当作恋人的巴施马奇舍(《外套》),与狗对话,偷狗的信件,并说信件“狗腔狗调”的狂人(《狂人日记》);分不清是男是女,被金钱异化的守财奴泼留希金(《死魂灵》);还有兼具天使和魔鬼特性的女性形象等。《故事新编》中也有异化的人物形象,如《铸剑》中被砍下却具有独立生命,并可以进行战斗的“眉间尺的头”,其实就和果戈理笔下的“鼻子”一样,是主人公被压抑的潜在不屈人格的外化。与异化人物相互交织的是情节上的怪诞,如《起死》中庄子看见路边的骷髅,揣测他的死因,还反复发出“橐橐”怪声的情节,就和《死魂灵》中乞乞科夫一边看购买的死魂灵的姓名,一边编造死魂灵一生的情节如出一辙,他们皆站在优人一等的角度,对一个死去的符号评头论足,甚至横加指责。这一方面创造了滑稽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对人物的讽刺效果。
怪诞手法的介入可以弥补写实手法的不足,因为用写实手法塑造的典型形象容易被读者合理化,如果戈理所说,许多人是满足于做一个乞乞科夫的,“我们只要一放下书本,就又可以安详地坐到那全俄之乐的我们的打牌桌子前面去了”。[16]因此,作者便让怪诞介入现实,将平凡的生活陌生化,用夸张与变形来冲击读者认知,使人产生厌恶、恶心甚至是恐惧之感。其次,典型形象纵然有透视现实的好处,但在“白色恐怖”年代常常会使作家陷入危险或遭遇不测打击,鲁迅就曾在书信中抱怨“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几乎无处发表”,[17]这时作家就需要用怪诞去间接表达自己的讽刺意图。
虽然果戈理的小说和鲁迅的《故事新编》在怪诞手法的使用上具有相似性,但果戈理的小说更加保守、传统,而《故事新编》则更具有现代主义特点。鲁迅曾说:“《死魂灵》作者的本领,确不差,不过究竟是旧作者,他常常要发一大套议论……”[18]因此他摒弃了果戈理叙事中的大段议论和抒情,而将怪诞手法直接运用到叙事之中,如《出关》中孔子两次拜访老子的重复叙事;《补天》中女娲和脚下小人文不对题、机械重复的对话;《铸剑》中黑衣人所唱的意义不明的歌等。鲁迅写法上对果戈理的超越一方面来自时代的影响,鲁迅与果戈理的时代相差了将近100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使鲁迅对怪诞手法的使用更为大胆和直接,但这种超越主要还是得益于鲁迅高度的文学自觉。鲁迅说《铸剑》中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19]这说明鲁迅已经对传统文学有了有意的反思和创新。
2.3 悲喜交加的讽刺主题
果戈理的小说被称为“含泪的微笑”,鲁迅说这种含泪的微笑“在别的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20]这是鲁迅晚年转向“油滑”,并且宣称要一直保持这种“油腔滑调”的重要原因之一。果戈理钟爱喜剧,他的小说中也有许多喜剧的滑稽成分存在,这与上文提到的怪诞是密不可分的。雨果认为怪诞“一方面创造了畸形与可怕,另一方面,创造了可笑与滑稽”。[21]这种怪诞中的滑稽在人物一出场时就显露出来了,首先是人物的姓名,鲁迅说果戈理非常擅长给人起名号,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人是谁,其关键就在于“夸张这个人的特长”。[22]比如巴施马奇金:鞋(《外套》);科长:长脚鹭鸶,小姐:金丝雀(《狂人日记》);科罗皤契加:箱子、小窝,梭巴开维夫:一匹中等大小的熊,农奴:母牛屎、母牛砖、驴子(《死魂灵》)等。《故事新编》中鲁迅充分地学习了果戈理起名号的技巧,如《理水》中的“鸟头先生”,《出关》中“好像一段木头”的老子,《非攻》中“高脚鹭鸶”似的墨子。果戈理还有一个取名“诀窍”,即用形容词直接取名,如让乞乞科夫笑了很久的泼留希金的外号“打补钉的”,这在《故事新编》中也有运用,如《补天》中直接给一个学者取名“一个脸的下半截长着白毛的”。[23]
人物语言也能制造笑料,因为外语、谚语、脏话的引入能打破小说原本的严肃认真,使其呈现出诙谐讽刺的特色。果戈理说俄国人为了使俄国话更加高尚,说话往往只说一半,剩下的一半便去法国话里找。[24]这在《故事新编》中也大量存在,如《理水》中的文人见面就说“古貌林”“好杜有图”,聊天用“OK”,还会胡造一些“维生素W”这样的词。可见过去的俄国人和中国人其实都有崇洋媚外的心理。《死魂灵》中还有大量的俄罗斯谚语,他常将“如谚语所说……”穿插在故事当中,如作者用“如谚语所说,他成为了掌珠了”[25]来体现被愚弄的N市人对乞乞科夫的喜爱。《故事新编》中的方言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如《出关》中账房所说的“来笃话啥西,俺实直头听弗懂”[26]夹杂南北方言,书记的话“写子出来末,总算弗白嚼蛆一场哉啘”[27]是苏州方言。脏话在果戈理和鲁迅的小说语言中也有重要地位,《死魂灵》里的贵族看似高雅,但他们总爱在心里骂人脏话。如乞乞科夫就给予了车夫“贱胎、昏蛋、恶棍、强盗、猪猡、海怪”等一系列的“称号”。鲁迅对中国的脏话颇有研究,他甚至写过《论“他妈的”》来探讨“国骂”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故事新编》中的脏话颇多,如后羿刚以“放屁”起头回应了侍女(《奔月》);禹太太便用“这杀千刀的!”咒骂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理水》);接着庄子在给骷髅讲大道理时又得到了“放你妈的屁!”的回应(《起死》)。至于那脏话反说的,则更为生动滑稽,如强盗把暴打伯夷叔齐的威胁说成是“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采薇》)。
怪诞的目的是将讽刺隐藏于滑稽,以此揭示社会人生的悲剧。作者将宏大的社会问题捏碎,再将其洒落到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笑料之中,以此达到《死魂灵》中“无事的悲剧”那样的效果。由此,稍用心的读者便会发现,社会人生的悲剧,并不只存在于英雄故事中,更存在于人们身边那些平凡的人,平常的事,甚至一句普通的话语之中。“要人”的一句威胁不就要了巴施马奇金的命吗(《外套》)?伯夷叔齐的死不也和他们所信奉的千古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关吗(《采薇》)?因此,鲁迅说:“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28]平常的事并不平常,它足以毁掉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无事的悲剧也并非无事,它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每叙述完一件事后,都要以“我们俄罗斯……”开头进行一段议论或者抒情,并且喜欢将其与法、德、英国进行对比。通过《死魂灵》中人们关于乞乞科夫是拿破仑的揣测,可以看出,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一方面还沉浸在因打败拿破仑而产生的巨大的民族自豪感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崇拜西欧国家民主自由的文化,羡慕甚至恐惧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一部分人开始为国家的发展寻求改变,于是发生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但却惨遭失败,尼古拉一世借此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贵族又回到了纸醉金迷的堕落生活,而劳苦百姓依然愚昧麻木。果戈理的小说画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俄国社会的众生相,表达了对小人物含着悲悯的嘲笑,以及对官场小丑、虚伪贵族的讥笑和耻笑。但同时他又无法找到社会人生的出路,于是将《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陷入了迷茫与彷徨。
鲁迅和果戈理一样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时也有一样的矛盾与彷徨。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时,中国正陷入比果戈理时代的俄国更加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重,这时国内学生发起爱国运动,工人罢工反抗,而许多文人却躲进了书房。他们有的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去自己的空想社会里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议直接把北平设为“文化城”;有的满口仁义道德,成了伪满洲国的走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是国家的主心骨,他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而在鲁迅的时代,文人们却把传统文化作为叛国的借口,利己主义的工具。鲁迅怒骂:“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29]于是便有了女娲脚下满口胡话的小东西(《补天》);有了“文化山”上与现实脱节甚至相背离的学者(《理水》);有了喝了鹿奶后还要吃鹿肉的伯夷叔齐(《采薇》);有了真正无为的老子(《出关》);有了陷入自己辩证哲学圈套里的庄子(《起死》);而英雄只能末路(《奔月》),真正的救国者只能遭受冷遇(《非攻》)。《故事新编》中的文人和《死魂灵》结尾果戈理所批判的“所谓的爱国者”有相同的品性。果戈理说俄国有这样一种“所谓的爱国者”,他们“一向静静的研究着哲学,或者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富的增加,不管做着坏事情,却只怕有人说出做着坏事情来的”。[30]鲁迅小说中的文人便是“所谓的爱国者”,他曾抱怨检察官爱禁别人的文章,并反问:“但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不是救国的非英雄,而是卖国的倒是英雄吗?”[31]鲁迅批判文人时的激愤,来自他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他用毕生的心血铸成铿锵的文字,希望以此启蒙庸众、振奋国人、强国兴邦,但在临死之际,他仍看不到任何曙光,甚至堕入更加黑暗的深渊。《故事新编》以女娲的由生到死开篇,由骷髅的起死回生结束。看似是美好的喜剧,实则是回到起点的悲剧。就像鲁迅弃医从文,希望拯救国民沉睡的灵魂,到头来醒了的骷髅依然守着陈旧的思想,赤条条的身体依然未寻找到依靠,这是怎样的痛苦和绝望!但是,既然骷髅已经醒来,就不能说没有生的希望。这份全新的生的希望,是鲁迅奋战一生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在创作思想上,鲁迅学习了果戈理小说“含泪的微笑”的特点,但笑料背后的悲剧色彩更浓,讽刺意味更强。果戈理具有很强的阶级局限性,比如他缺乏对农奴的同情,《死魂灵》中农奴绥里方曾说“农奴是应该给点儿鞭子的,要不然就不听话……”[32]可见,在果戈理心中,农奴缺乏健全的人格,是愚蠢并且无药可救的。鲁迅说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他认为《死魂灵》中的地主“讽刺固多,实则除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33]而鲁迅则一直秉承着“为人生”的创作思想,是一位坚定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因此《故事新编》总是极尽讽刺之能事,鲁迅不仅批判当下时事,更反思传统文化;不仅揭露个体罪行,更深挖国民劣根性;不仅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忧虑,更自觉承担起了文人的使命担当。
一言以蔽之,《故事新编》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到了果戈理小说的影响,但却不是机械模仿,而是结合民族传统和时代特征的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