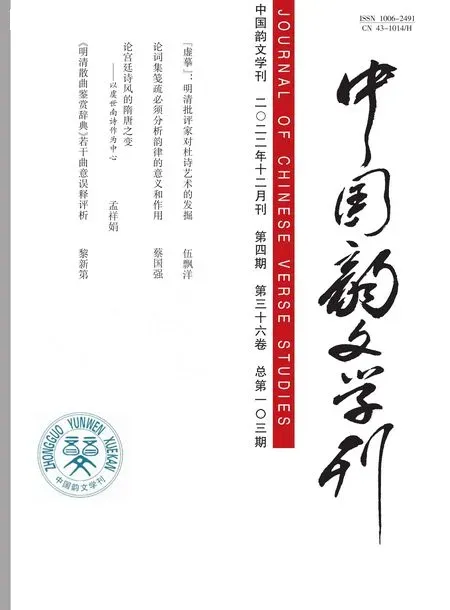《诗》学“赋”义考论
2023-01-19汪进超
汪进超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除了作为“体物而浏亮”“劝百而讽一”的文体外,“赋”也是《诗》学中的重要概念。无论是《周礼》的“六诗”之“赋”,还是《毛诗序》的“六义”之“赋”,抑或是《左传》中的“赋诗断章”与郑庄公的“入而赋”,都展现出“赋”与《诗》的密切关联。就《诗》“赋”之义,朱子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1](P4)这代表了以“赋”为“表现手法”一派的观点。郑玄的“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可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2](P566),则是以“赋”为“诗体”一派的认知。
近代以来,对于《诗》“赋”含义的讨论仍在继续。其中,以“赋”为表现手法的观点居于主流;但也有如章太炎《检论·六诗说》、郭绍虞《六义说考辨》等文章力主“诗体说”。在“诗体说”与“表达手法说”之外,尚有一些学者从“用诗方式”的角度来理解“赋”:张震泽《〈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一文从“赋诗言志”立论,指出“赋”最初是在宴会等场合直陈己意的一种应对之法;章必功《“六诗”探故》认为“赋”为周代国学的一种诗歌教授方式,其义为朗诵;此后,王昆吾在《诗六义原始》中对章氏观点进行深化,论明“赋”为声教的项目,是《诗》的一种传述方式,在国子之教中,“赋”相当于吟诵;在瞽蒙之教中,“赋”则为雅言诵。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来理解《诗》“赋”: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详论“六诗”与“六义”,认为“赋”本来是一种合唱方式,在后来的演变中,又有了“自唱或使乐工唱古诗”及“自作诗”等义;鲁洪生在《诗经学概论》中提到,“赋”本是一种用诗方法,自汉代开始,则又演变为一种表达方式。(1)上引诸说参见:章太炎《检论》卷二,《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郭绍虞《六义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张震泽《〈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章必功《“六诗”探故》,《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王昆吾《诗六义原始》,《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版;鲁洪生《诗经学概论》,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二人对于“赋”的《诗》学意义的演变以论述为主,至于“赋”字本义及其如何与《诗》建立起联系等问题,则语焉未详。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不足:李蹊认为赋税制度中将赋品记录在册的行为是“赋”获得语言功能的关键。[3](P1-4)贾晋华从语义延伸的角度,探究了“赋”字由本义“武”向组诗《武》的诗体意义的演变,再由“赋”与“铺、布、敷”等字的假借关系,推断其修辞手法、诗歌技巧、作诗与献诗等诗学意义的来源。[4](P6-23)陈韵竹从“赋”征敛与献纳的本义谈起,认为“赋”之本义为制度性的征敛与献纳。[5]马银琴分别从“贡赋”与“王命使赋”的角度考察了“赋”的制度性内涵与“直陈其事”的言说功能,梳理了《诗》“赋”的意义演变。[6](P66-77)可以说,在概念的历史流变中对“赋”字本义及其制度性本原的关注,尤其是语义学研究视角的引入,当为理解《诗》学之“赋”的正途。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观点及方法进行整合与梳理,尝试进一步充实与弥合上述论证的简略及矛盾之处,以求更为明晰地揭橥《诗》学之“赋”的制度性内涵、言语功能及诗学意义的关系。
一 赋税与赋政:作为制度的“赋”
《说文解字》曰:“赋,敛也。从贝,武声。”[7](P282)考《尚书·禹贡》有“厥田为上中,厥赋中中”,《左传·成公十八年》有“薄赋敛,宥罪戾”,可证“赋”有“敛取”之义。论者多据此认定其本义为“敛”,如《汉字源流字典》即曰“赋”字本义为“敛取、征收”,又因其“从贝”,自当与财物有关,故当为敛取、征收财物之义。[8](P1437)但此字又有与“兵役、士兵、军队”等相关的意义,如《左传·襄公八年》载:“君命敝邑,修而车赋……悉索敝赋,以讨于蔡。”《论语·公冶长》亦有:“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其中“赋”字便当作“士兵、军队”解。贾晋华认为其本字为“武”,“武”字既是“赋”的声旁又是义旁。故“赋”本义当是“兵役”,延伸为士兵和军队之义,而“敛取、征收”则是后起的定义[4](P6-23)。此二义关系究竟如何,尚无定说,本文拟先就此展开讨论。
(一)“赋”字本义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二年》有“讥始用田赋也”。何休解诂曰:“赋者,敛取其财物也……悉赋之礼,税民公田不过什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9](P5109)可知“赋”应是当时的一种税收制度,又可分为税民之“赋”和军赋。在具体的计算中,税民以田为单位,军赋以井为单位。而其所云财物者,当是税民之谷与军赋之乘。关于这一制度,精通礼学的郑玄在《周礼》中有更为详尽的注解。《周礼·大宰》有“以九赋敛财贿”,郑玄注曰:
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师之职亦云“以征其财征”,皆谓此赋也。……自邦中以至于弊(2)弊余,嘉庆阮刻本经文他处为“幣余”,孙诒让《周礼正义》此处为“幣”。孙氏《正义》以唐石经本和嘉靖仿宋本为底本,知古本为“幣”。然据孙氏考证,“幣余”即“敝余”,“幣”为假借,可知其本字为“敝”义,未详是“敝”“弊”“幣”三者可通用,抑或是阮刻本此处刊刻之误,姑阙疑。余,各入其所有谷、物,以当赋泉之数。[10](P1394)
郑玄解“九赋”之赋为“口率出泉”,意即按人口缴纳钱税,“泉”即钱也。九赋者,按地区或职业标准分为九种口赋方式,虽说是“口率出泉”,但有些人也可用谷或其他物品抵当应缴纳的钱数。可知这一口赋制度早有规定,无论是出泉(钱),还是谷、物,从国家制度规定者的角度来说,确有“敛取财物”之义。关于“军赋”,郑玄亦有详细注解,《周礼·小司徒》中“以任地事而令贡赋”下,郑玄引《司马法》注曰:
赋,谓出车徒给徭役也。《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10](P1533)
其后贾公彦疏曰:
赋谓军赋,出车徒之等……云“赋谓出车徒给徭役也”者,以其采地之内,无口赋出钱入天子之法,故以赋为车赋解之。……故《礼杂问志》云:“稍、县、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于王也。邦、国都无口率之赋,唯有军赋,革车、匹马、士徒而已”,是也。[10](P1534-1535)
由以上注疏可知,按原本规定,各地皆当“口赋出钱”以入于天子。而之所以有“军赋”,则是邦、国都等地方“无口率出钱入天子之法”,所以才规定以“革车、匹马、士徒”等作赋,此即“军赋”。可知军赋制度是为了弥补口赋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不足而新出的。也就是说,“赋”字本义当是统治者敛取财物的赋税制度,与军事有关的“军赋”之义,以及后来的“士兵、军队”之义,皆晚于“口率出泉”的本义。
(二)制度之“赋”
以上探究明确了“赋”之本义当为赋税制度,“军赋”则是其引申义。当然,无论是口赋还是军赋,“赋”都是国家从人民那里征取财物的一种制度,皆当作“敛取”之义解。这种财物的自下而上,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是“敛取”;而站在征赋对象,亦即民众的角度来看,便是“献纳”。如《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下,孔安国即注曰:“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11](P308)所以在理解这一制度时,需同时兼摄这两层含义——在上者的“敛取”和在下者的“献纳”。虽然如此,但其毕竟仍是与财物有关的一种制度,它和《诗》究竟如何建立起联系的呢?或者退一步说,赋税制度和语言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其间转换的关键又在于什么?这是历来讨论的焦点之一。
针对以上问题,有研究者提出从制度的角度进行探讨,如台湾学者陈韵竹《论赋之缘起》探讨了“赋《诗》”的制度性根源及制度与言语的关系:
“赋”既不是“诵诗之义”,也不是“创作之义”或“六义之一”的“铺陈”之义,……先秦两汉“赋”仍执守于“征敛献纳”之意义,往往附带有“典制性”之指向。[5](P346)
此文认为“赋诗”当是具有制度性、仪式性的“征敛诗”和“献纳诗”。作者着意提取其“征敛”与“献纳”的意义,考证古之圣王有征敛言语、民间亦有献纳言语的典制。马银琴则从制度与仪式的角度探讨了“赋”的“制度”与“言语”的意义关联。她认为“贡赋”制度表明了“赋”从最初就具有严肃的制度性内涵,而“王命使赋”则又使“赋”获得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赋”就从“赋税”“赋政”和“纳言”的制度逐渐成为一种盲人乐官“直陈其事”以进谏的方式。此后这种“直言其事的语言表达方式”被广泛运用于外交场合中,义为直陈诗篇以表达意志[6](P66-77)。二人从制度与仪式的角度来探究“赋”与“诗”之间关系的思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相关的研究中的焦点既是作为财政制度的“赋”如何转变或是引申到言语制度的“赋”义,陈韵竹的“先王典制说”却未揭示出为何使用“赋”这一财政层面的字来表示言语,反而将“赋”与“咏诵”“创作”“铺陈”等意义的关系拉得更远;马银琴的“赋政纳言说”从《大雅·烝民》中天子“明命使赋”的具体内容是“出纳王命”的角度展开,又进一步从《尚书》中找出当时的职官“纳言”以印证《诗经》中“赋政”的制度性特征,从而使“赋”获得言说的意义。同时又从毛传、郑笺等训诂条例中寻找“赋”到“铺陈”之间的联结,这一论述揭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但仍未较有说服力地论明“赋”从“敛取财物”到“赋政纳言”的转变过程。
总而言之,以上两篇文章揭示了赋税之赋与言语之赋的重要关联在于制度、仪式等内容,这无疑是通往答案的一条正确道路。但与此同时,也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一是无论敛取还是献纳,都是财物的自下而上,而“赋政”又显然是政令的自上而下,这一自上而下的指向又是如何得来的?二是为什么这一“从贝”的字会被用来表示与言语有关的“赋政”制度,“赋”和“铺陈”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的?故而仍有必要循着二人所指示的“制度”的方向,带着上述问题在先秦典籍中做进一步的考察。
“赋”本义为财物的“敛取”和“献纳”,但无论是敛取还是献纳,都表示的是财物从民间集中到国家,是有固定的指向的,即自下而上。但在一些训诂学著作中,已经指出了财物的自上而下亦可称为“赋”,如《尔雅·释言》曰“班,赋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说道:“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7](P282)因此,“赋”兼有“敛之”和“班之”两层含义。但“班之”一义从何而来?这一训诂现象的原因何在?以上著作都没有进一步说明,继续考索则能够找到一些制度性线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玨部》曰:“班,《周礼》以颁为班,古颁、班同部。”[7](P19-20)可知在《周礼》中,班、颁二字可以通用,这在训诂中是一常例。进一步翻阅《周礼》,可以发现“赋”与“颁”的关联,且此二者与当时的制度有关。《周礼·天官冢宰》载:“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二,……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据此可知,依周时制度,“赋”乃是自下而上地缴纳财物,由大府掌管其中的一部分,即“受其货贿之入”。但随后便又“颁其货”“颁其贿”,将所敛之财贿又依“九式”之别分发给不同机构,以供其使用,这是国家财富集中之后的分配制度。除大府之外,《周礼》还有“职岁”一职,其负责的工作也是“掌邦之赋出”。所以从制度上来说,“赋”虽是在上者敛取财物于民,但最终仍要将敛取之物颁发于下,以维持国家不同机构的正常运行。这一制度同时兼具“敛”和“颁”两层意义,又因“颁、班”二字通用,所以“颁其货、贿”亦即“班其货、贿”。因而“赋”义便具有了自上而下颁发的指向。
虽然“敛”和“班”都可称为“赋”,但正如此字的义旁所示,“赋”的内容是财物。而《大雅·烝民》中“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诸句则表明,仲山甫是作为王的喉舌以“赋政于外”的,赋政的内容则是王命,王命的表达形式是具有规定性的言语,因而此处所“赋”的内容是言语。为什么本来用来表示颁布财物的“赋”在这里可以用来表示颁布言语形式的命令?这种用法的依据从何而来呢?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理解《诗》“赋”意义的关键。
二 从赋税到赋政:古音通假与“赋”的言语功能
关于“赋”的财物之义与言语之义如何建立起联系的问题,李蹊从赋税制度出发,认为该过程中贡品的铺列、汇报及记录是其“铺陈”之义的来源,也是“赋”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的原因;同时也提到先秦文献中“敷”“赋”“布”“铺”混用的语言现象。[3](P1-4)随后贾晋华则明确指出“赋”在先秦文献中被用为“布”“敷”“铺”的假借字,以致逐渐获得修辞手法与作诗、献诗等义。[4](P6-23)至此,从“赋税”到“赋政”的意义延伸,或曰“赋”的财物之义与言语之义建立联系的原因已然渐明——先秦语言文字使用中的“通假”。上述二人的研究,李蹊微启其端,但点到即止,未展开论证;贾晋华虽有所考论,却仅以秦汉以后的训诂阐释为论据,对于先秦文献中的相关例证则缺乏关注。因此,仍有必要对先秦文献中“赋”与其他词汇的通假现象进行归纳总结,更为清晰地呈现其获得言语功能的过程。
《烝民》一诗有“天子是若,明命使赋”等句,其中的“赋”与“赋政于外”的“赋”当是同义。毛传曰:“赋,布也。”郑笺曰:“显明王之政教,使群臣施布之。”[2](P1225)可见毛、郑皆用“布”来训“赋”,赋政就是布政、施布王命之义。而《尔雅·释言》中:“班,赋也”,郭注云:“谓布与。”[12](P5623)知郭璞训“赋”为“布与”。由此可见以“布”训“赋”似乎是一训诂通例。不仅如此,在前人的训诂中,“敷”“铺”等字也同样可以训为“布”。如《周颂·赉》一诗中有“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郑笺:“敷,犹遍也。”孔疏曰:“敷训为布,是广及之义。”[2](P1304)知孔氏将“敷”训为“布”。《广雅·释诂》亦曰:“铺……布也。”[13](第221册,P439)合而观之,似乎赋、铺、敷等字都有一个共同的意义指向。前人也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小尔雅·广诂》曰:“颁、赋、铺、敷,布也。”[14](第695册,P331)因为这几个字的意义相同,都含有“布”的某些意义,所以在古人的注疏中也可以互训。但需要注意的是,训诂著作中说它们的意义相同,不一定是它们的本义相同,更多情况下是指它们的某些引申义有相同之处,但本义可能不相关。古人训诂所依据的是字词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有其例,辄有其义。但需要注意的是,现象无法解释原因,这种训诂实例不能呈现字义复杂的演变过程。故而需要结合音韵、字形等方面综合考察这一训诂现象背后的原因。
在现代汉语体系中,它们读音有些差异,除声调不同外,最显著之处就在于声母有别,“赋、敷”声母是唇齿音;“布、铺”二字声母为双唇音,但也不是同一个双唇音。也正是这些差别,导致了很多对“赋”义进行溯源的学者忽略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关联。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它们的读音应当非常接近。清代学者钱大昕“古无轻唇音”的观点已基本上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他说:“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15](P90)也就是说,先秦时期没有“非、敷、奉、微”这一组轻唇声母,所有的唇音声母都读重唇音,即“帮、滂、并、明”四纽。据此可以推测,“赋、布、铺、敷”这几个唇音字在先秦时应都读重唇音。而据王力先生《上古声母及常用字归类表》,“赋、布”属帮纽,“敷、铺”属滂纽,俱属重唇音,可证钱说不虚。此外,据王力《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赋、布、敷、铺”四字同属鱼部。至此可知,该四字因声母相近(重唇音),且又在同一韵部(鱼部),故其读音十分相似。
古人在文字使用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王力先生称之为古音通假:
所谓古音通假,就是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同音或音近的字通用和假借。语言里的“词”是音义的结合物,古人在记录语言里的某一个“词”的时候,往往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书写,有时写成这个样子,有时写成那个样子。两个字形体不同,意义不同,只是由于声音相同或相近,古人就用甲字来代替乙字。[16](P546-547)
古人在书写中对有些读音相同的字存在一定的混用,这一点在先秦典籍中确实有不少例证。基于此,似乎可以对“赋、布、敷、铺”这四个读音相近的字是否在使用中存在这一现象提出疑问。而通过广泛考察,也的确能够发现一些例证:
(1)《尚书·益稷》:“敷纳以言,明庶以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以上两处,“敷”“赋”通用。
(2)《尚书·舜典》:“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周礼·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以上两处,“敷”“布”通用。
(3)《周礼·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大雅·烝民》:“赋政于外,四方爰发。”《商颂·长发》:“敷政优优,百禄是逑。”以上三处,“布”“赋”“敷”通用。
(4)《周颂·赉》:“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左传·宣公十二年》:“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以上两处,“敷”“铺”通用。

以上诸例足可证明在当时书面文字的书写中,“赋、布、敷、铺”四字互相之间有假借通用的现象。而本节所要探讨的从“赋税之赋”到“赋政之赋”的意义转变的原因也可能正蕴于其中。上文提到的“明命使赋”“赋政于外”,即“赋”与言语的搭配仅出现于《大雅·烝民》中,在先秦文献中,除了后起的“赋诗言志”外,“赋”在其他地方出现时仍与其本义“敛取财物”相关。而据以上所举例证可知,“赋政”与“敷政”“布政”同义,由此可以推测“赋政”中的“赋”很有可能是“布”“敷”等的通假字。因为在先秦典籍中,“布政”(包括“布命”等)和“敷政”(包括“敷训”等)含有一定制度性意义的词语较为多见。先看“布政”类: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
(《尚书·仲虺之诰》)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
(《周礼·天官冢宰》)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
(《周礼·地官司徒》)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
(《周礼·夏官司马》)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
(《周礼·秋官司寇》)
敢布腹心,君实图之。
(《左传·宣公十二年》)
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以上仅列举部分“布政”类记载。由此可见,当时确实有将天子的政令传达到各地的制度,一般多用“布”字表达,此时制度的呈现形式为语言文字。而《诗经》中的 “赋政”当是“布政”,只是在书写中假借了“赋”字。但这一假借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使得“赋”字在不断的使用中逐渐获得了布政之“布”的意义,这对于“赋”与言语产生关联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看“敷政”类:
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尚书·舜典》)
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
(《尚书·盘庚》)
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尚书·洪范》)
钦哉!往敷乃训,审乃服明,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尚书·微子之命》)
何天之龙,敷奏其勇。
(《商颂·长发》)
由以上诸例能看出,“敷政”也有着和“布政”同样的意义,当然“布”“敷”二字之间可能也存在着假借情况,但总体而言,在“赋政”之外,先秦典籍中更多的情况是用“布”和“敷”来表达下达政令之义。还需要注意的是,“敷”字除下达之义外,还有“广布”之义。如“文命敷于四海”,是说大禹的文德、教命广布于四海,这与“布政”稍有不同,“布政”“敷政”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和制度性,而“敷于四海”所说的则是一种广布的状态。“极之敷言”中的“敷”显然含有“敷陈、陈述”的意义。同样,“敷心腹肾肠”和《左传》“敢布腹心”中的“敷、布”当是同义,皆有表达、陈述之义。又由于“赋”“布”“敷”等字的特殊的通假现象,所以“赋”也有可能在使用中逐渐获得以上意义。因“铺”字与“布”“敷”等字也可以通用,故同理可知,“赋”也可兼有“铺”的意义,此不再赘述。正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所说:“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17](P101)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正是因为声音相近,又有某些意义联结点,才使得“赋”字在某些层面具有了与其读音相近的字的一些意义。当然,“赋”的言语层面意义的确立,不是因其与“布”“敷”“铺”等字可以通用就立即具备的,而是在不断的使用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而获得的。
至此可以对赋税之“赋”到赋政之“赋”的意义转变有一大致了解:“布政”“敷政”等在周代是一项含有制度性的规定,即由某些特定的人或机构来直接传达天子的相关政令。此时“布”“敷”是下达政令(言语)之义。二字除下达政令之义外,还有“广布、敷陈、陈述”等意义。而“赋”字本义为敛取和颁发财物,与政令(言语)本没有关系。但先秦时期的语言使用中,存在着“古音通假”的现象,即读音相近的字有时候会通用和假借。“赋”与“布”“敷”“铺”等字本来就读音相近,且其还具有“颁发”的意义。所以在文字的书写中,“赋”字很有可能就被用来代替“布”“敷”“铺”等字。这种通假的语言现象又会使得“赋”字逐渐获得“布”“敷”“铺”等字的某些意义,即“赋”除了“财物的敛取、献纳与颁发”的本义之外,又获得了“下达政令、广布、敷陈、陈述”等意义。
三 从言语之“赋”到《诗》之“赋”
梳理了从“赋税”到“言语”的意义延伸过程后,在《诗》学范畴内关于“赋”的讨论便也可以继续开展。对于《诗》“赋”的阐释,历来聚讼纷纭,上文已大致罗列。整体而言,对于《诗》“赋”这一有着丰富内涵的诗学概念的阐释,应当着眼于其从“言语”到“诗”的意义嬗变,做动态而全面的理解。“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及“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二句,是郑玄对《诗》“赋”所作出的重要解释,借之可大体把握“赋”的诗学意义。以下即从“造篇”“诵古”“直铺陈政之善恶”三个方面分别论之。
(一)造篇之“赋”
周代早期的大师(太师)在仪式中以记叙、陈述为主的“赋唱”,以及春秋时期诗人作诗以言志的“赋诗”,是“赋”在“造篇”层面的主要内涵。也正因这一意义层面包含的创作性,“赋”也逐渐成为一种特征鲜明的写作方式与艺术表现手法。
据《周礼》可知,大师基本上负责一般仪式中的乐与诗有关的部分(3)据王昆吾《诗六义原始》总结,大司乐也负责仪式中的音乐、舞蹈等部分,其所教授的对象是国子,所适用的场合为规格较高的典礼。而大师教授对象则为瞽蒙,负责一般活动中的音乐部分。。除演奏外,大师还会参与乐曲的筛选和编审工作,并管理乐谱。《国语》中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的记载,《荀子·王制》中“修宪命,审师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等话语更是可以看出大师对国家典制的音乐负有的重要责任。当时崇尚以礼乐治国,乐在国家典制中有重要作用,礼的尊卑有序在某些方面也需要用音乐来体现。且仪式中不仅有乐器奏乐,还需同时配以不同的诗。如《礼记·仲尼燕居》中便有孔子论乐之所用:“客出以《雍》,彻以《振羽》。……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其中“升歌《清庙》”便是指歌《清庙》之诗。孔子所说的几首诗均见于《周颂》(4)据孔疏,《雍》即《雝》,《振羽》即《振鹭》,《维清》奏《象武》也。,而细读诸诗便可发现,这些诗本身即作于仪式之中,是对整个仪式的描述,如《清庙》中“於穆清庙,肃雍显相”等诗句是描述祭祀场面,《雝》中“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则似乎是对主祭者的祭辞进行记录。纵观《诗经》,能够发现还有不少类似的诗篇。如《周颂·有瞽》一诗是对祭祖时瞽蒙作乐场景的描述,对乐器的摆设和音乐特征都有细致的描述。这些诗皆与仪式有关,且以祭祀居多;且这些作于仪式中的诗的内容是对整个仪式描述和记录的,有些是对受祭者的生平功绩进行颂扬,有些是对祭祀场景或过程进行描述,有些则对主祭者的祭辞进行记录,有些则对祭品进行铺陈。概言之,这些为仪式而作又复用于仪式的诗歌,表现出铺陈性、记叙性以及还原性等共同特征。李辉认为这是一种专业性的乐工“赋唱”的方式,即乐工逐渐从仪式中独立出来,对仪式的内容进行一种平面化的描述与铺陈[18](P41-67)。结合上文所论,“赋”字在与“布”“敷”“铺”等字音近而义同,皆有铺陈、陈述之义,这种认为仪式中乐工对仪式内容进行的陈述和敷陈是一种“赋唱”的观点颇有一定道理。《大雅》和《颂》中的不少诗歌都表现了一种敷陈与记录的特征,且描述者多有一种“大观视角”,似乎独立于整个事件之外,以诗的语言形式描述事件过程,记录事件中的言语,并对事件形态进行一定的评价。如《大雅·灵台》一诗,第一章首先对灵台的修建过程进行描述,第二章则描述文王游乐于灵台之事,第三、四章则继续陈述燕游之事及礼乐之盛,卒章末尾的“鼍鼓逢逢,蒙瞍奏公”可以看出蒙瞍也身处其中,并对灵台厥成之事进行歌奏。盖蒙瞍虽目不可见,但因其审于音律且深谙作诗之法,故在视瞭的帮助下(5)《周礼·春官宗伯》:“视瞭:凡乐事,相瞽。”视瞭是瞽蒙的助手。,能对当下之事进行适宜的“赋唱”。此事在齐景公之时尚未断绝,《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由孟子之言能够看出两个信息:一是大师的职责包括为君主演奏适合主题的音乐,如《徵招》《角招》,可作为君臣相悦之乐。二是在奏乐的同时,大师也负责创作与主题相符的诗,以陈述或评价其事。所以,大师在仪式等事件中,需负责指挥演奏合适的音乐,同时也需要用特定的诗的语言对事件的过程和内容进行敷陈,一者可以记录事件,二者可以传布于四方以宣扬天子礼乐之盛备。虽然大师为盲人,但因其深谙乐理,所以在视瞭的帮助下可以创作出与音乐相协的诗篇。可以说,大师在仪式中以诗化的、有节奏的语言来陈述、记录重要事项,这样一种包含着史、乐、礼等要素的诗歌创作行为,或许是早期“赋”与“诗”建立关系的方式之一。
在春秋时期,“赋”则直接被用来表示“作诗”。《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与其母姜氏“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后各自作诗之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孔颖达疏曰:“赋诗,谓自作诗也。”[19](P3726)二人诗中皆有“大隧”,故其诗当是因事而作,非称引前人之诗。《左传·僖公五年》记士“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杜预注曰:“士自作诗也。”[19](P3895)由以上二例可见,春秋时期,“赋”已明确具有“作诗”之义。《左传》中尚有几处“赋诗”的记载,其文如下: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
(《左传·隐公三年》)
狄人伐卫,……宋桓公……立戴公以庐于漕。许穆夫人赋《载驰》。
(《左传·闵公二年》)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左传·闵公二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左传·文公六年》)
文中明言《载驰》为许穆夫人所赋,考诸历史,知闵公二年(前660)狄人灭卫,宋桓公立戴公于漕邑,月余即死。许穆夫人为戴公之妹,意欲吊之,故诗有“载驰载驱,归唁卫侯”诸句。然当时礼制,女子既嫁,若未见休,则不可归国,因此许穆夫人无法离开许国,故有“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之句。又因许国国力微弱,无法救卫,故诗有“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从诗和史的关系中,基本上能够确认此诗为许穆夫人所作。如此,则《左传》所言“赋《载驰》”之“赋”,即是作诗之义。其余三例未确言作者身份,但诗中内容也大致与历史记载的相符,其中的“赋”也分别为卫人、郑人、秦人因事而作诗。由以上六例可知,到春秋时期,“赋”的诗学内涵已从仪式中大师的“赋唱”行为,扩大至日常中诗人的“自作诗”。
当然,无论是“赋唱”,还是“自作诗”,所“赋”诗作都以描述和记录事件、表达心声与情感为主要诉求,体现了“赋”因古音通假所涵摄的“敷陈、描述”等意义。就此而言,“赋”也逐渐被视为一种以直接叙述为主要特征的诗歌写作方式与艺术表现手法。魏晋以来,文人对“赋”的诠解,显现出艺术化、审美化的趋势。钟嵘《诗品序》便关注其“直书其事,寓言写物”[20](P25)的艺术风格。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强调其“丽词雅义,符采相胜”[21](P27)的美学特征。概言之,“赋”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以其敷陈、叙述、直接表达等特征,在诗歌的叙事纪实、体物状景、记言写人、说理陈情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二)诵古之“赋”
如果说“造篇”是一种诗歌创作,那么“诵古”便是对诗篇的运用,属于诗的传播与接受范畴。早期的诵古之“赋”指瞽蒙在仪式中的诗歌讽诵行为以及大师的诗歌教学工作。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外交场合对于诗歌的广泛称引,“赋诗断章”成为此时“诵古”的主要内容。
《周礼·春官》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可见“六诗”是大师所教授的内容。又由“凡国之瞽蒙,正焉”的规定知其所教的对象是瞽蒙。而教学的目的,则是为了让他们在不同的仪式中配合音乐而歌诗。《周礼》中对瞽蒙的职能的规定为:
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可知瞽蒙作为大师的下属,在仪式活动中的职能具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负责演奏乐器和“歌”,这一部分是由小师负责教授的。郑玄将“歌”解释为“依咏诗也”[10](P1720),即依于琴瑟而有节奏地歌咏诗篇。第二部分是“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郑玄注曰:“讽诵诗,主谓作柩谥时也。讽诵王治功之诗,……虽不歌,犹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10](P1721)第三部分是歌“九德、六诗”之歌,以配合大师。需要注意的是引文中出现的“歌”和“六诗之歌”,以及“讽诵诗”和“六诗”。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六诗”当是“风赋比兴雅颂”,由大师所教。但“六诗之歌”的“歌”究竟是何义?既然有“讽诵诗”的形式,则“六诗之歌”中的诗是否也能够讽诵?仅从此处文献的记载难以回答这些问题。王昆吾曾在《诗六义原始》一文中对“六诗”做过较为详尽的考证,他认为《周礼》中的“六诗”所代表的是《诗经》成型之前的“风、赋、比、兴、雅、颂”的观念,在西周的乐教体系中是六种诗的传述方式,亦即大师对瞽蒙进行语言和音乐训练的六个科目。其中“风”与“赋”是两种诵诗方式,“风”是方言诵,“赋”是雅言诵。[22](P342-343)若依其说,再结合郑玄将“歌”解为“依咏诗”以及讽诵时犹鼓琴瑟的说法,似乎可将“赋”看作歌的一种形式,其表现方式是在某些仪式中依于琴瑟的节奏用雅言咏诵。这是瞽蒙在仪式中的工作,而因瞽蒙是由大师指挥,且平时由大师教授,故而这种“赋”的方式自然也为大师所熟练掌握。所以从声乐的角度而言,“赋”乃是一种诵诗方式,它不仅运用于祭祀等仪式中,也在大师所负责的瞽蒙之教中起到重要作用。
至于春秋之际,“赋诗断章”与“赋诗言志”则成为聘问宴飨等仪式场合中常见的一种用诗现象。其中“赋诗”之“赋”乃称引诗歌以交际的行为,此是“诵古”的另一种含义。考诸文献,可援以为证者颇多,现列两例以见之:
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左传·文公十三年》)
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
(《国语·晋语四》)
首先,引文中子家所赋的《载驰》为《鄘风》中的一篇,其作者为许穆夫人,《左传》及四家诗说均已明言,当无可疑。可见“子家赋《载驰》”之“赋”为“称引”之义亦属无疑。其次,当时对于诗的称引,或如“文子赋《采薇》之四章”,只引某诗之某章;或如“公子赋《河水》”,称引全诗。盖交际中的“赋诗断章”有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有时称引诗篇中的某一章,取其义而用之;有时称引某诗之全篇,而义在其中的某一章或某一句。[23](P45)概言之,称引已有的诗歌以取其义或“断章取义”的行为被称为“赋诗”,此时的“赋”为称引,亦即“诵古”之义。台湾学者黄振民统计,“古人赋诗,据从《左传》《国语》所获资料,自僖公二十三年至定公四年(前637—前506)约百年间,共赋诗六十七篇次,用诗五十八篇。计《颂》一,《大雅》六,《小雅》二十六,《风》二十五篇。计往来交际之国,共有鲁、晋、郑、宋、齐、秦、楚、卫、曹、株十国”[24](P294)。可见当时“赋诗”现象之普遍。
无论是大师对瞽蒙的以雅言咏诵诗歌的教学方式,还是春秋之际的士人在聘问宴会等场合以“断章取义”为目的的诗歌称引行为,皆与早期“赋政于外”的赋政制度中的言语之“赋”有着重要的意义关联。其中的“赋”都包含了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有固定的规则与形式,二是对既有言语内容的重复。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诵古”层面上的“赋”从言语范畴向《诗》学范畴的意义拓展。
(三)直铺陈政之善恶
从礼乐仪式和大师的职能来看,“赋”是一种作诗行为及作诗方式;从瞽蒙之教和“赋诗断章”的现象来看,“赋”则是一种诗的教授与运用行为。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三百篇》之中,尤其是《国风》之诗,多采自民间,是在上位者观知民风的重要途径(6)《汉书·食货志》描述“采诗”制度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这一点从孔子 “《邦风》其纳物也,溥(7)据马承源解读,“溥”字本为“尃”,《说文解字》:“尃,布也。从寸,甫声”。容庚《金文编》:“尃,孳乳为敷。《毛公鼎》:‘尃命于外。’”可见尃、敷同,且同样有“布”义,又《毛公鼎》“尃命于外”与《大雅·烝民》中的“赋政于外”相似,且读音相近,未知此二字是否存在通假的可能。且孔子所云《邦风》的特征有“纳物”“敛材”,与“赋”字本义几乎相同,故此字似可作“赋”解。若如此,则对“风”与“赋”的含义及关系似乎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或许对于揭示“六诗”真正含义有着重要意义。观人俗焉,大敛材焉”[25](P129)的评价也能看出。实际上,从民间采诗陈于天子而使其了解民风,在周代便是一项重要的制度,《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这一采诗、陈诗制度于天子而言能观民风。而对百官庶人而言则是规谏天子的重要途径。《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之言: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谏,工执艺事以谏。”
师旷是当时著名的瞽师,了解有关的音乐制度,他所说的“瞽为诗”即是瞽蒙陈诗或作诗以谏君上,且其所引《夏书》中的遒人采诗、官师相谏等事也说明采诗、陈诗的制度确实存在。从《诗经》中也能看出百官庶人作诗规谏的痕迹:“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中的“诵”表明,有些诗在初作时可能仅用于讽诵,亦即徒诗。但大师采集这些诗歌后,可能会对其进行一些韵律化的处理,使它们能合于音乐节奏,进而上陈天子以讽谏。在这一制度中,大师似乎成了上下相通的重要枢纽,他能够收集、筛选、整理一些百官庶人为规谏天子而作的诗,有时还能自己作诗表达意见。此时,如何选择民间诗歌,或如何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创作诗歌,以使规谏的效果最佳,便成为大师需要考虑的问题。从作诗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事情和情绪,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言说方式;而从采诗的角度来说,需要对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作出分辨。郑玄在《周礼·大师》“教六诗”下将“赋”解释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8)《周礼·春官·宗伯》对比、兴的注解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后孔颖达也强调“赋”能“通正变,兼美恶”,无所避讳而得失俱言。这种从诗人讽谏之旨与大师规谏善恶的角度来阐释“赋”的政教意义,确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结合大师在政教方面所担负的重要职责,能够看出,“赋”作为一种规谏方式,是在诗中直接地、如实地铺陈当前政教的善恶。大师需要辨明这一方式,选取有代表性的诗篇,上陈天子,以示民情。而大师自作诗时,也可采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意见,以规谏天子。就此而言,不加隐晦,直接铺陈政教善恶的表达方式便是“赋”。
综上所论,《诗》学之“赋”兼“造篇”“诵古”与“直铺陈政之善恶”的意义。由言语之“赋”向《诗》学之“赋”的意义延伸与流变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言语之“赋”的记录、陈述、铺陈等义逐渐向诗学领域延伸,在周初形成了制度性、仪式性的大师“赋唱”行为,使得言语之“赋”获得了“造篇”的诗学含义。二是言语之“赋”的“赋政”所体现的规范化的对既定言语内容的复述之义逐渐向诗学领域延伸,形成了仪式中诵诗、瞽蒙之教中大师授诗以及聘问宴飨中“赋诗断章”等用诗行为,使得言语之“赋”获得了“诵古”的诗学含义。三是从言语之“赋”的陈述、敷陈等意义与大师的诵诗职能而言,“赋诗”在周代采诗观风的制度中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直言善恶”的意义特征,使得“赋”获得了“直铺陈政之善恶”的政教功能。当然,以上虽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但需要注意的是,言语之“赋”向《诗》之“赋”的意义延伸过程并非单独而割裂的,而是复杂、动态而全面的。
余论:《诗》“赋”之于赋体及诗歌的意义
以上对《诗》“赋”的意义生成与演进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呈现。概言之,“赋”由“财物的征敛与献纳”的本义向“政令的颁布与陈述”的言语之义的转变,其关键在于“古音通假”。即“赋”与“敷、布、铺”等词读音相近,在使用中存在着通假现象,进而,这一与财物有关的概念“假借”了敷陈、铺陈、广布、陈述等意义,获得了与政令有关的言语功能。随着其主要意义从“赋税”到“赋政”的演变,以及表示记录、陈述的言语意义的涵摄,“赋”也逐渐进入诗学领域,与《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作诗角度而言,“赋诗”是以韵律化的语言陈述和记录相关事件。从用诗的角度来看,“赋诗”则有在仪式中咏诵、在教学中传授和在交际场合中称引等含义。而在政教层面,“赋诗”则更侧重于“言志”,亦即“直铺陈政之善恶”。可以说,从赋税制度到赋政制度,再到《诗》学概念,“赋”的意义延伸与流变体现了制度、言语与诗的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当然,这一概念不仅在诗经学领域内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对于后世的赋体文学和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诗》“赋”与赋体虽为不同概念,但二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与何种程度的关联,乃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公案。班固曾说:“赋者,古诗之流也。”[26](P21)刘勰亦言:“赋自诗出。”[21](P27)可知一般观点认为《诗》与汉赋之间确乎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但这种稍显笼统的说法也容易造成汉赋是由类似于《诗》中的“赋辞”拓展而成的误解。诚然,汉赋中的对事物的敷陈和铺排的确有类于《诗》“赋”,但汉赋追求的“极尽铺陈之能事”,与《诗》“赋”的记录、陈述、铺陈等写作方式有着颇为明显的区别。此是其一。其二,刘熙载曾言:“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蒙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是也。”[27](P95)据刘氏所言,知《三百篇》时代的“赋诗”行为和两汉时期的辞赋创作有着重要联系,体现在“讽谏”和“言志”等方面。不可否认,两汉文人之赋,的确有着“讽谏”的追求。但在社会形态、国家制度、君臣关系等发生转变的大一统帝国时期,其言语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因时而变”。汉赋的主要特征,乃是“劝百讽一”与“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27](P103),与《诗》“赋”之直抒胸臆和“直铺陈政之善恶”的品格相较,实有较大区别。故虽同名曰“赋”,而其言说形式和讽谏方式却难等而视之。有研究者指出,汉赋中运用更多的表现手法是“比兴”,后者的“替代与类推”的感知模式对汉赋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8](P35-67)。也就是说,相较于《诗》“赋”的直言善恶,比、兴所表现出的“主文而谲谏”的艺术特征,对赋体文学的影响更大。因此,谓“赋自《诗》出”固可,言汉赋源于《诗》“赋”则非。
再看“赋”之于诗学的意义。后世诗人多彰“比兴”而贬“赋”。如明人李东阳曾言: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29](第1482册,P441)
其言“比兴”有所寓托与长于感发等特征确为事实,但在彰扬“比兴”的同时贬抑“赋”,并借之以指摘“赋”法之“正言直述”特征的态度却值得商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赋”的方式写就的诗作可能更符合儒家的诗学传统。一方面,“赋”的记录与陈述的叙事特征,与诗学史中的“诗史”类诗作的历史纪实性有一定的相似性。孟棨《本事诗·高逸》曰:“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30](第1478册,P240)确如其言,杜甫的《兵车行》《北征》以及著名的“三吏”“三别”等诗作,皆以“赋”的笔法从某些角度记叙了当时的现实,将之置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背景下,庶可视为某些历史场景的“赋现”。钱谦益曾力扬这种以诗为史的写作追求:“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他认为此类诗作足可“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31](卷十八)与天宝之乱相比,满清入关、明朝覆亡的这段历史对于士人内心的冲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们对诗史颇为重视,主张在诗歌中反映这一世运升降之际的重大史实,并借之以表达内心复杂的情绪。吴伟业、黄宗羲、屈大均等人对历史的重视以及对杜诗的推崇皆可证明这一点。可以说,《诗经》时代便已颇为成熟的“赋”的写作方式,以其历史性、叙事性的特征对后世形成的“诗史”传统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赋法”直言善恶的特征对后世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现实主义虽是《诗》的整体特征,但具体到“赋、比、兴”三者的表现特征,则又颇有不同,其中“直言无害”者为“赋”。直言者,既包括直接叙事,又可理解为直接陈情和议论。其内容则以反映当前政教之善恶、社会之治乱、民生之安苦为主。揆诸诗歌史,此类诗作可谓众矣。作为“诗之余”的“词”,在文体逐渐成熟后虽基本上以比兴寄托为主要追求,但在清初阳羡词人的倡导下,也逐渐开始有意识地以“赋”的手法作词,努力地赋予其经、史的功能[32](P192)。可以说,在“比兴”广受关注、大行其道的诗学背景下,“赋”对于诗歌乃至文学的作用实际上也毫不逊色,其“叙事写物”的基本文学功能,与“直铺陈政之善恶”的讽喻品格,在古典诗歌中俯拾皆是,与“比兴”共同建构了中国的诗学传统,塑造着中国的诗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