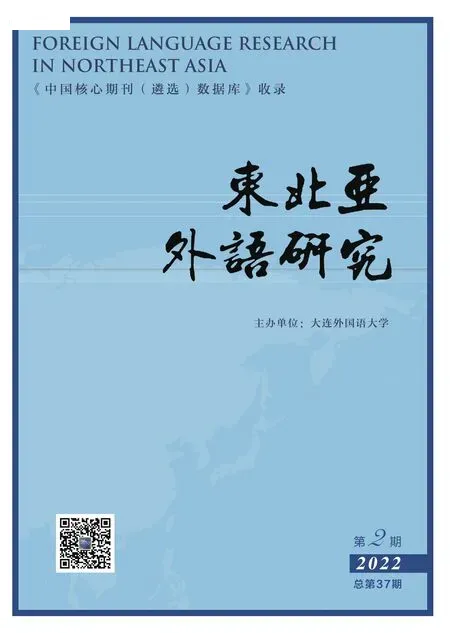变异学视角下的中日《法华经》灵异记
2022-02-05刘九令
刘九令
(长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重庆 涪陵 408100)
《法华经》全称为《妙法莲华经》,被誉为“经中之王”,是早期大乘重要经典之一。《法华经》诞生之后,在印度、尼泊尔及中亚地区广为传播,后来也传到东亚,被古代亚洲各国民众所持诵。《法华经》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该经典为主体的佛教灵异文学,即“法华经灵异记”。那么,何为“法华经灵异记”?学术界尚未对此做明确定义,这里根据故事的内容特征,笔者权且将此理解为:因诵经、持经、转读、写经等行为而产生的和《法华经》相关的诸种灵异记录。《法华经》灵异记在亚洲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变异现象。正如曹顺庆和李甡(2020:2)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文学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流传影响过程中,既有共同性,也有变异性,有时甚至更多的是变异性。”本文从变异学的视角,以印度佛典《法华经》、中国类书《太平广记》、日本的佛教说话集《本朝法华验记》为研究对象,宏观考察日本说话文学中《法华经》灵异记与中国文学中《法华经》灵异记的关联性与差异性,追溯两国作品与印度佛典之间的内在渊源关系,并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文学变异的原因。
一、法华灵异之源:法华功德
《法华经》灵异记作为传播经典乃至佛教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于持经、诵经、听经、写经等功德的极力渲染来吸收信众。笼统地讲,东亚所有《法华经》灵异记的祖源均为佛典《法华经》,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大多取材中国佛教文学,而中国佛教文学则基本上依据佛典教义直接演绎而来。换言之,印度佛典《法华经》的核心要义规定了东亚各国《法华经》灵异记中某种共同的原始基因。而这种核心要义便是《法华经》鼓吹的法华功德。在探讨《法华经》灵异记之前,本文将首先对法华功德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阐释。
第一,天童相伴。《法华经·安乐行品第十四》:
尔时,师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前略)读是经者,常无忧恼,又无病痛,颜色鲜白,不生贫穷,卑贱丑陋,众生乐见,如慕贤圣,天诸童子,以为给使,刀杖不加,毒不能害。 (赖永海,2010:339-340)
佛典《法华经》中师尊为了宣传读经的利益,称读了此经会受到众生的尊重,像敬仰圣贤一样,甚至天童都服侍周围。天童是天上的童子,一般侍奉在佛和菩萨左右,天童围绕身边、保护在左右,是为了凸显读经者的功德。
第二,疾病治愈。《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
此经能救一切众生,此经能令一切众生脱离诸苦恼,此经能饶益一切众生,充满其愿。(中略)此《法华经》亦复如是,能令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痛,能解一切生死之缚。(中略)此经则为阎浮提人之良药。若人有病,得闻是经,病即消灭,不老不死。 (赖永海,2010:463-464)
“药王菩萨本事品”说《法华经》是婆娑世界中人的良药,听此经可以灭除“一切苦、一切痛”,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说明祛病种类无所不包。“病苦”是佛教“四苦”之一,无论高低贵贱,人人都难以逃脱,佛经中宣称诵持该经可以远离各种疾病,对于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吸引力。
第三,躲避灾难。《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
善男子,汝能于释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读诵、思惟是经,为他人说,所得福德无量无边。火不能焚,水不能漂,汝之功德,千佛共说不能令尽。汝今已能破诸魔贼,坏生死军,诸余怨敌皆悉摧灭。 (赖永海,2010:463-464)
另外,《法华经·观音菩萨品第二十五》: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中略)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锁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赖永海,2010:483-484)
“药王菩萨本事品”和“观音菩萨品”中均有关于法华经功德躲避火难、水难、贼难、兵难等功能的记载。与其他品不同,观音品对于经典功德的种类进行了细化,涵盖了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灾难。
第四,唯舌不朽。《法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子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得二百舌功德。(中略)若以舌根,于大众中所演说,出深妙声能入其心,皆令欢喜快乐。又诸天子、天女、释梵诸天,闻是深妙音声,有所演说言论次第,皆悉来听。 (赖永海,2010:421-422)
“得二百舌功德”是法华经中对于读经、诵经、解经等舌功德的夸张,并且声称诵此经声音优美,且诸天来听。基于舌的强大功能,中日两国文学都创造出了各种各样舌不朽的故事,虽然具体的故事情节似乎和法华经原典教义没有直接关联,但可以推测出来,是以此为宗旨进行了大胆的创作和演绎。
第五,动物转生。《法华经·譬喻品第三》:
见诸众生为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之所烧煮,亦以五欲财利故受种种苦。又以贪着追求故现受众苦,后受地狱、畜生、恶鬼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间,贫穷困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如是种种诸苦。(中略)舍利弗,佛见此已便作是念:“我为众生之父,应拔其困难,与无量无边佛智慧乐,令其游戏。”
(赖永海,2010:119)
“譬喻品”中提到在“火宅”中的众生有的受到了畜生之苦,舍利弗作为众生之父,要将其从火宅中挽救出来,脱离苦海。畜生道为三恶道之一,因前世之恶业化为诸种动物,要想摆脱畜生道之苦,需要作善业方能转生其他善道。
《法华经》所言上述五种功德虽然只是众多种类的一部分,但这为其后东亚各国《法华经》灵异记的创作提供了思想来源。
二、 型相类趣同归:中日法华经灵异之“大同”
在日本佛教说话集中,除《日本灵异记》和《今昔物语集》收录了《法华经》灵异记外,《本朝法华验记》是专门的《法华经》灵异记。《本朝法华验记》又称《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亦称《法华验记》。此书作于平安中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说话集,作者为首楞严院的僧人镇源。全书分上、中、下三卷,记载了共计129个与《法华经》相关的灵异故事。据学者考证,该书多个故事取材于《日本往生极乐极记》《三宝绘》《日本灵异记》《叡山大师传》《慈觉大师传》等日本前代作品。除了借鉴本国文学元素之外,该书还与中国有着深刻的渊源。关于创作机缘,该说话集在序言中写道:
窃以法华经者久远本地之实证,皆成佛道之正轨。(中略)故什公译东之后,上宫请西以降,若受持读诵之伴,若听闻书写之类,预灵益者推之广矣。而中比巨唐有寂法师,制于验记流布于世间。观夫,我朝古今未录。余幸生妙法繁盛之域,镇闻灵验得益之辈。然而或烦有史书而叵寻,或徒有人口而易埋。嗟呼,往古童子铭半偈于雪岭之树石,昔时大师注全闻于江陵之竹帛。若不传前事,何励后裔乎?①(鎮源,1974:510)
序文中,作者盛赞《法华经》为“佛道之正轨”,普化众生。指出鸠摩罗什译经、圣徳太子讲经注疏以后,持经、诵经、写经获益匪浅。又语带危机地说,唐(宋)的义寂法师著有《法华验记》,而日本没有,因此要效仿先贤,编撰此书,以“励后裔”。可以说,其创作的重要动机就是受到了中国说话集创作的影响,甚至可能在故事层面受到直接影响。
尽管作品取材于日本的前世说话集,但诸如《日本灵异记》等前世说话集本身也大多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本朝法华验记》的创作除了动机之外,其故事结构、故事类型、叙事模式、作品素材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这也可以作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中国的《法华经》灵异记则在《法苑珠林》《冥报记》《高僧传》等各种佛教文学作品中均有辑录,《太平广记》也在第109卷之<报应八>中集中收录了21条此类故事,对于前世佛教作品中的故事进行了转录,并由此反映出中国唐代及唐代以前《法华经》灵异记的基本特色。这里不再拘泥每个故事之间的出典关系,只做整体类型层面的对比分析。囿于篇幅限制,不能穷尽所有故事,下面将对照上述《法华经》五种功德分析中日两国文学的共性。
第一类,天童相伴型。《太平广记》“释弘明条”中弘明诵经习禅定时,“每旦则水瓶自满实,感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②(李昉等,1961:742),天童为其供养。《本朝法华验记》第11、21、68、79、87段等属于此类。如某持经者在深山里修行,修行期间“天诸童子,以为给仕”(鎮源,1974:519)。沙门光日年老时在太子山修行诵法华经。后夜宿八幡宫,并诵法华经。有人梦见有八个天童礼拜光日,并以妙花洒在其身。沙门行空迷路之际,“天童示路”(鎮源,1974:542)。信誓阿阇梨诵经之时,有天童来听法华经。关于“天童”,《佛学大辞典》解释为:“(天名)护法诸天现童形而给侍于人者。<释门正统>八曰‘天童给仕’。<法华经·安乐行品>曰‘天诸童子,以为给使’。”(丁福保,1991:474)可见,天童是护法的化身,而“给侍”或“给仕”都是指服侍他人的人。两部作品中的天童虽然具体行为不同,但都侍候他人。
第二类,疾病治愈型。《本朝法华验记》中的第88、91、122段和《太平广记》的“费氏条”“释慧进条”“彻师条”都属于“疾病治愈”的类型。《本朝法华验记》第88段中的莲照法师苦行,将衣服施与他人,身体聚集了各种寄生虫。法师却不肯听人劝说而涂药,以免杀生。于是诵法华经,后梦见有一贵僧盛赞其行,然后用手抚摸其伤痕,其病痊愈。第91段盲僧妙昭法师为他人诵经“病恼之人,闻盲僧经,除愈病患”(鎮源,1974:553)、“乃至摄念受持,两目开见一切诸色矣”(鎮源,1974:553),虽然本人眼病未能治愈,却可以为他人治愈各种疾病。第122段,筑前国有一盲女,盛年之时眼睛忽然失明,于是请一尼姑为其诵经。后来梦见一僧人,僧人“即以手指摩开两目。梦觉已后,两眼忽开,见色分明”(鎮源,1974:565)。《太平广记》中常年诵法华经的费氏患上了心痛病,梦见佛以手摩其心口,随即病愈。慧进诵法华经,后生病,于是发愿造百部法华经,积攒了一千六百文钱。贼来抢劫,于是慧进将这些钱给贼看,贼被吓退。他最终实现了造经的愿望,病也忽然痊愈了。彻师禅师遇见了一个生疮癞的人,将其救下,教其诵经。可是此人愚笨,学习比较慢。于是梦见有人教授诵经,后有领悟。生疮癞之人渐渐病愈。
第三类,躲避灾难型。《太平广记》的“释慧庆条”中的慧庆常年诵法华经。一次乘船出行,突遇狂风雷电,所乘之舟几乎倾覆,忽觉船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后平安抵岸。《本朝法华验记》第40、54、57、71、72、107、113、114、115段等属于此类。沙门平愿常年念法华经,一次在房屋坍塌之际,突然有神人前来搭救,将其从危险中救出。沙门珍莲在被大火围困的紧要关头,专心念法华经,火突然熄灭,免死。年轻的持经僧人在恶鬼来袭的时候,一心念法华经,毗沙门天王前来救助,杀死恶鬼。真远法师被官吏莫名绑缚,于是心念法华。该官吏夜里梦见普贤菩萨样子的神人乘大象过问真远被缚之事,官十分惊恐,当夜便释放了法师。沙门光空被人造谣与兵部郎中妻子私通,被绑缚起来,并被人以箭射之。光空高声念法华经,箭自折。兵部惊恐,放了沙门。光空后来梦见是普贤替他受箭。大隅掾纪某因上司怨恨,被派遣远地戍边,并被遗弃在无人岛之上,后念法华经,有人驾舴艋舟前来搭救。捕鹰者遭同伴背叛,身处险境,于是诵法华经,观音菩萨化蛇前来搭救。盗人多多丸子从小诵法华经,偷盗被捕获之后,被士兵射杀,箭不着身,后来得知,是观音前来搭救。周防国判官从少年开始诵读法华经,后遭政敌怨恨,被半路偷袭,结果得三井观音救助,免死。
第四类,唯舌不朽型。《太平广记》中的“沙门法尚”“释志湛”“五侯寺僧”“悟东寺僧”“释道俗”“史阿誓”条均属舌不朽类型。而《本朝法华验记》中仅第13段清晰地表达了舌不朽的情形。此类故事大多讲述因持经者潜心诵经,故而死后舌头不朽,甚至依然诵经不止。《本朝法华验记》中的沙门壱睿受持法华经多年,后参诣熊野,宿完背山,夜间听见诵法华经的声音:
明朝见有死骸骨,身体全连更不分散,青苔缠身,经多年月。见骷髅其口中有舌,赤鲜不损。 (鎮源,1974:519)
后来壱睿问该骸骨因缘,骸骨的灵魂回答说本人叫“元善”,生前发愿转读六万部法华经,活着的时候只读了一半,死后接着读经。《太平广记》中的舌不朽情节与上面故事有一定差别,但是都有对舌头的描写,如“东山人掘土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舌,鲜红赤色”(沙门法尚条)(李昉等,1961:742)、“骸骨并枯,唯舌不坏”“余骸并枯,唯舌不朽”(五候寺僧条)(李昉等,1961:743)、“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悟真寺僧条)(李昉等,1961:747)、“身肉都尽,唯舌不朽”(释道俗条)(李昉等,1961:748)、“见其舌根,如本生肉”(史阿誓条)(李昉等,1961:748)。这些故事都将灵异重点放在了舌不朽,并通过骨骸和身肉的枯尽及“鲜”“赤”“润”等形容词反衬、刻画舌头鲜活如生。
第五类,动物转生型。《本朝法华验记》中的第24、25、26、27、30、36、37、53、58、77、78、89、93、126段等。《太平广记》中仅录一条“石壁寺僧”。此类故事中的动物因造诸种恶业,化身为各种的动物,如牛、野干、蚯蚓、蛇、狗、黑马、虫、蟋蟀、猿、鹆。这些动物又因为听经、驮经等功德,转生为人。这些故事往往借助梦境叙事,叙述各种生前事、转生事。
上述五种类型均为《本朝法华验记》和《太平广记》所共通的法华经灵异类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类型故事,本文由于篇幅有限,暂不一一列举。通过上述整理可以发现,中国的文献和日本佛教说话集中存在大量话型相通的《法华经》灵异记,即类型层面的“大同”,不仅如此,描写语句和情节雷同之处颇多,故事的旨趣都指向宣传法华经的神奇灵验。这种类型、语言、情节、旨趣上的相似和相通绝非偶然,这是直接或间接吸收中国文学的结果。
另外,从前面的考察可以看出,上述诸多类型的故事大多在佛典中能够找到基本教义原型,只不过表现程度有所差异,有的是直接、清晰的,有的模糊、暧昧的,不管故事距离佛经的言说距离有多远,其在更深的层面是一致的。
总体来说,中国的佛教文学创作者依据法华经的基本教义,立足本土文化语境进行文学虚构,并添枝加叶、敷衍情节,演绎出了一个个鲜活具体的《法华经》灵异记,这些又被后世的《本朝法华验记》直接或间地接吸收,并经过二次或三次创作,产生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故事。
三、文化语境促新生:中日法华经灵异之“小异”
何为“文化语境”?严绍璗(2000:3)对其定义和内涵这样论道:“‘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从文学的发生学的立场上说,‘文化语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因此,无论是哪国,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都会立足于本国文化语境,对其进行适度改造,使其适应新的文化土壤。基于此,以下将从文化语境分析中日《法华经》灵异记细节上的变异,进而揭示文学传播过程中变异背后的原因。
首先,佛教故事中土著信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固有的民间信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和融合,这在《太平广记》中的《法华经》灵异记中有多处表现。如“释昙邃条”中晋僧人昙邃住在白马寺,“蔬菜布衣”(李昉等,1961:738)并能诵经、解经。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听见有人敲门请他诵经,邃起初拒绝了,后来在其一再邀请下,梦中身往白马岛神祠中,为其讲经:
神送白马一匹,白羊五头,绢九十匹。呪愿毕,于是遂绝。
(李昉等,1961:738)
这里“神”“白马”“白羊”是值得仔细研读的关键词。文本最初并没有交代是谁请僧人诵经,后来故事结尾才出现是“神”。这个“神”是白马岛神祠中供奉祭拜的神祇,属于中国固有的民间信仰对象。“神”为了答谢昙邃诵经,居然以白马和白羊供养。神完全是依据民众对他供奉的神馔来供养僧人。马和羊作为荤腥食物奉献给僧侣以为表达了自己极大的诚意,但是对素食的僧侣来说,这是犯了最大的忌讳,恐怕会令昙邃哭笑不得。这其实体现了神对外来佛教教理教义的不甚了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在晋代,中国民间对佛教依然存在误解。但在另一个方面,神请僧人诵经也证明当时一般民众虽然一知半解,但却囫囵吞枣地信奉佛教。在“赵泰条”中,这一点说得更加直白。赵泰进入冥界之后,冥官用生死簿查阅人生前所犯罪恶时指出:
人死有三恶道,杀生祷祠最重。 (李昉等,1961:740)
“三恶道”指的是“畜生”“饿鬼”“地狱”。而通过杀生祭祀和祈祷则是最大的罪业,佛教反对杀生,这是最基本的戒律。这其实也是借助冥官之口,对中国民间杀生祭祀行为的一种警告,从根本上说是外来信仰体系和本土信仰体系之间的冲突。
佛教传到日本,自然也会和日本原有的宗教发生摩擦与交融。《本朝法华验记》第81段某橝那欲立宝塔,每次都被雷电击毁,反复多次。沙弥神融为其诵经护塔:
即住塔本诵法华经。爰叆叇布云,细雨数降,雷电见曜。愿主作是念:“雷破塔相也。”悲叹忧愁。神融上人立誓,高声诵法华。时有一童男,从空下落,见其形体。头发蓬乱,形貌可怖,年十五六岁,被缚五处,流泪高声,起卧辛苦而白言:“持经上人,慈悲免我,自今以后更不破塔。”时神融法师问破坏因缘,雷白圣言:“此山地主神与我有深契。地主语曰‘此塔立我顶耳,仍无住处,为我可破坏塔。’依地神语度度破坏。而妙法力不可思议能伏一切。依之,地主移去他所,我敬恐避由此。”当知愿主足,圣人誓言实。神融圣人告雷神云:“汝随佛法不作违逆,发起善心,不破宝塔。尤当利益汝。但见此寺更无水便,遥下谷汲水荷登,雷神此处可出泉水,以为住僧便。汝若不出水,我缚汝身!” (鎮源,1974:548)
这是一个表现佛教与神道冲突的典型故事。因为立塔,本地的地主说“此塔立我顶耳,仍无住处”(鎮源,1974:548),抱怨佛塔侵占了自己原有的生存空间。于是请另一位好友雷神击毁佛塔,赶走佛教。神融不仅用法力降服雷神,而且语带威胁地告诉他,这里不仅要住僧人,你还得让这里泉眼出水,否则就绑他,体现了佛教的强势进入。可以说,故事用具体事件,表达了一个庞大的隐喻主题。橝那立佛塔,象征着佛教的进入,地主神的抗拒象征着本土神道的抵抗。最终神融打败雷神则象征着佛教战胜了神道。与这个激烈对抗的关系不同,《本朝法华验记》第80段则缓和很多。故事中明莲法师好诵法华经,但奇怪的是,只能背到第七卷,八卷无论如何也背不下来,他愁苦不已,于是:
祈乞佛神,应知此事。即笼稻荷百日祈念,更无其感。长谷寺、金峰山,各期一夏,更不得应。诣熊野山,百日勤修。梦想示云:“我于此事力所不能及,可申住吉明神。”沙门依梦告参住吉社,百日祈祷。明神告言:“我亦不知,可申伯耆大山。”沙门参诣伯耆大山,一夏精进。大智明菩萨梦告言:“我说汝本缘,勿疑!” (鎮源,1974:546)
作为佛教弟子的明莲,为了弄清背不下来第八卷的因缘,求助于佛祖或菩萨。可他却偏偏去了稻荷神社、住吉神社,祈请神明给予明示。这些神明都不能解释原因,最终从“大智明菩萨”那里得到答案,说明佛教系统中的菩萨法力还是高于神道的,暗示在本土神道教与佛教的较量中,佛处于上风。但不得不说,明莲起初求助于神,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当时人看来,神佛本是一家,神即是佛,佛即是神。平安时代中期以前,就有所谓“本地垂迹”的思想了。表现神佛融合的佛教说话故事还有第86段。道命阿阇梨诵法华经受到了信众的追捧,甚至诸多神明亦来听经:
有一老僧,笼行其寺。梦见堂庭及四邻边,上达部贵人充塞无隙,皆合掌恭敬,向寺而住。又从南方遥见有音,皆人闻言:“金峰山藏王、熊野权现、住吉大明神,为闻法华来至此所。”皆悉讫,一心顶礼,闻阿阇梨诵法华经。住吉明神向松尾明神而作是言:“日本国中,虽有巨多持法华经人,以此阿阇梨为第一。闻此经时,虽生生业苦,善根增长,仍从远处每夜所参也。”松尾神言:“如是!如是!” (鎮源,1974:551)
故事中,日本著名的神金峰山藏王、熊野权现、住吉大明神、松尾明神都远道而来,聆听阿阇梨诵法华经,这其中表明的是神道向佛教的归附。特别是借用住吉明神和松尾明神之间的对话,揭示听经的功德,即“闻此经时,虽生生业苦,善根增长”(鎮源,1974:551),说明当时神道中的众神已经接受了佛教宣扬的业报思想,体现了本土宗教与外来佛教的融合交汇。
尽管上述对比的故事不属于同一类型,却都是《法华经》灵异记。故事中的某些情节,甚至是细枝末节都凸显出了两个国家文化语境的差异。僧侣创作者们将弘扬佛法视为己任,都试图从本国的文化背景出发,用本民族所熟悉的文化场景和宗教语言来揭示佛教的特点,努力改变固有信仰中与佛教教理相冲突的部分,进而推动佛教在本国民众中的发展。
其次,僧侣礼佛仪轨创举。佛教虽然从中国传入日本,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这种变异在说话集的文本中则演变成一种文学的变异。如,礼佛方式方面出现了新的样式。《本朝法华验记》第6段中延昌僧正在入灭之前,“右胁以枕卧,前奉安置弥陀尊胜两像,以线系于佛手,结着我左手,把愿文右持念珠,结定印入灭”(鎮源,1974:517)。第51段境妙法师,勤学法华经,临终前“沐浴身体,着浄衣裳,以五色线着弥陀佛手,以其手线系我手,向西方坐”(鎮源,1974:536)。第99段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比丘尼释妙诵法华经又称念弥陀:“临迁化时,手取五色线,一心念佛。正历三年端坐入灭”(鎮源,1974:556)。故事中尽管没有涉及释妙用线系于佛手,但是也象征着这种行为。另外,在《日本灵异记》《拾遗往生传》等佛教说话集也有类似记载,而这种用线连接佛手和自己手的例子在中国佛教文学中并未见到。关于以线系佛手的礼佛方式,日本学者原田行造(1974:296)对平安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梳理,指出:“与平安中期用华丽的五彩线系于九体佛手不同,奈良时期用的是简朴的绳子。系的地方也未必都是佛手,也有系在足背的情景。并且,平安中期具有作为来世迎请证据的个人救济之含义,而奈良时期则为实现得度愿望和致富愿望这种极为现实的情形下使用的。”从原田行造的考察可以看出,净土宗传入日本之后,礼佛形式有了特殊的创举,并在当时广泛实行,这恰好被镇源运用到故事的创作中来,使得故事更加符合日本佛教发展的真实状况。
再次,僧侣修行规范的突破。在修行规范中的饮食方面,日本僧人也有了某种新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禁盐方面。如相应和尚“和尚天性极大精进,志念勇进,断谷断盐,厌世美味”(鎮源,1974:516)、应照法师“断谷断盐更不食甘味”(鎮源,1974:517)、莲坊阿阇梨“常以断食为业,又断盐诵法华”(鎮源,1974:522)、沙门良算“永断谷盐只飨菜蔬,诵读法华”(鎮源,1974:535)。在《太平广记》中昙邃“蔬食布衣,诵法华经”(李昉等,1961:738)、慧进“蔬食布衣,诵法华经”(李昉等,1961:741)。两部作品中的僧侣在修行过程中均为素食,这是佛教基本戒律规范,但是日本僧人竟然发展到“断盐”的程度,这也体现出在修行要求方面,日本僧人更为严格。作者通过当时断盐的行为凸显日本高僧修行的虔诚度,用以区别中国修行的特征。因为作者运用了真实的佛教修行习俗,主观上满足了当时信众的阅读亲近感,客观上使得中日两国故事表现出细微的异样风情。
最后,僧侣生活样式的差异。《本朝法华验记》的故事中出现了僧侣蓄养妻子的现象。第62段姓名不详的僧人“具足妻子”(鎮源,1974:539)、莲秀法师“牵世路虽具妻子,心犹归信法华大乘,每日读诵观音经一百卷”(鎮源,1974:542)、寻寂法师“虽具妻子,犹期菩提”(鎮源,1974:553)。在中国佛教界,结婚生子是被禁止的,但是佛教传到了日本,僧侣的生活样式却产生了新的变化。从描述莲秀法师和寻寂法师的语句可以看出,虽然养妻子,但丝毫不影响诵经,两者并不冲突,甚至还成为了故事发展的必须情节。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发现,《本朝法华验记》为了突出本民族特色,特意将日本佛教的特有仪轨和礼俗融入到各个故事中,这一方面让本国读者感觉到灵异故事就在自己身边,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作者创作“本朝”法华验记的目的,这体现了文学变异过程中主观因素。
四、结语
《法华经》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集中反映了古代印度的轮回思想、业报观念,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信马由缰的文学想象力。《法华经》作为亚洲文学的种粒,随着佛教的传播来到了中国和日本,并在异域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为《法华经》灵异记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或间接依据佛典而作,因此两国的故事都呈现出反映共通主题、相似情节的类型化特征,这是由《法华经》倡导的基本教义决定的。
当然,无论中国亦是日本,在诵持、阅读、传抄《法华经》的同时,均立足于本土接受语境,重新认识了这部外来教典。为了便于本民族的民众接受《法华经》思想,中日两国的创作者将信众熟悉的本地习俗和信仰融入其中,使得故事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并由此体现了文学的变异。文学的变异性根源于创作者的创作观、生活体验、历史背景等综合的文化语境。可以说,从宗教传播看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亚洲文学乃至文化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从故事细节的差异我们则可以深刻地追溯各民族相异的文化底蕴。
注释:
① 原文用变体汉文写成,依据文意及汉语习惯,笔者重新句读,并将日语汉字改写成汉语简体字。
② 原文为繁体字,且句读用“。”表示,本文将繁体改为简体,句读根据文意改成当代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