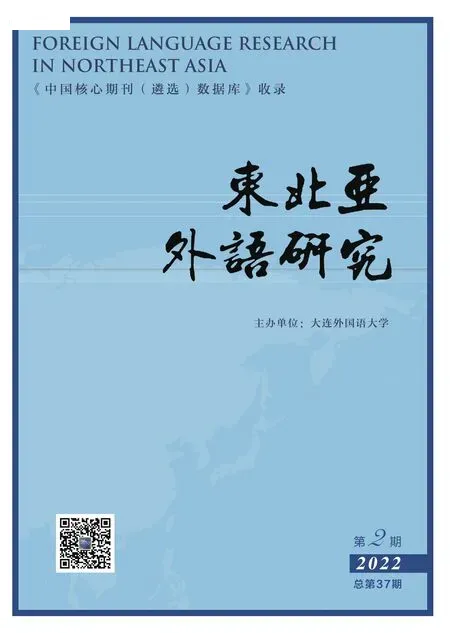道家与生态之维:苗建时的汉学研究探析
2022-02-05华媛媛姜缘辰
华媛媛 姜缘辰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20世纪环境运动以来,西方生态研究出现了重要转折,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道家等东方思想在当代生态伦理建构中的价值。汉学家苗建时(James Miller)生态视角的道家研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苗建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致力于道家、生态的交叉研究和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为西方汉学及环境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论建构。
苗建时认为,道家的思想中蕴藏的生态智慧对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他对道家的探索不仅拓展了生态研究的边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理解而言,苗建时的视角也具有新的时代意义。正如他在《中国的绿色宗教:道教与对可持续未来的追求》(China’s green religion: Daoism and the Ques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中所说,“道家为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了一套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James,2017:33)。他的汉学成就也为中国道家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他山之石”。
一、苗建时汉学研究的背景
(一)越境与跨界①:苗建时的汉学道路
苗建时于1968年生于英国,先后求学于英国杜伦大学、剑桥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取得了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荣誉学士、神学和宗教研究博士等学位。后从教于加拿大皇后大学,专心从事对道家、中国和生态的研究,陆续出版了六本与道家相关的著作,包括《道家与生态:宇宙景观的内在之道》(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Girardot等,2001)、《道家:入门指南》(Daoism: A Beginner’s Guide)(James,2003)、《当代社会的中国宗教》(Chinese Relig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James,2006)、《上清道:中古道教中的自然、视觉与神启》(The Way of Highest Clarity: Nature,Vision and Revelation in Medieval China)(James,2008)、《中国的宗教与生态可持续发展》(Relig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 China)(James等,2013)、《中国的绿色宗教:道教与对可持续未来的追求》(China’s Green Religion: Daoism and the Ques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ames,2017)。他还担任国际期刊《世界观:全球宗教、文化和生态》(Global Religions,Culture,and Ecology)的主编。2018年,苗建时受聘于位于苏州的昆山杜克大学,担任首届人文教授、跨学科战略首任副院长和DKU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纵观苗建时的学术生涯,有两个关键词贯穿始终——“越境”和“跨界”。
苗建时的汉学道路曾多次“越境”到中国,且重合轨迹越来越多,经历了从留学生到访问学者再到中国高校专职教授的身份跃迁。与中国结缘,始于苗建时少年时期对汉字的好奇,这驱使他在大学时期选择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归功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交流学习的经历,他不仅以优异的口语成绩毕业,而且中国浓厚汉语学习氛围让他接触到了文言文,研读了《老子》和《庄子》等道家典籍,由此走上了道家研究的学术道路。攻读博士期间,他师从专攻道家经典译介和研究的汉学家孔丽维(Livia Kohn),还有“波士顿儒家”学者白诗朗(John Berthrong)、南乐山(Robert Neville)、现代新儒家代表学者杜维明(Tu Weiming)等西方汉学界大家,他的汉学研究传承了他们衣钵并有所突破。博士毕业后,他还曾两次到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中国期间,他热衷于参加各大学术会议和高校讲学,与国内学者进行交流互动。作为一名西方学者,他的跨文化研究不是出于后殖民主义的凝视和猎奇,而是对中国的热爱和肯定,他的汉学理路没有停滞于陈旧的古代视野,而是更贴近中国当代现实。
苗建时专攻生态与道家的交叉研究,但他的学术视野“跨界”了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等多个学科,他本人也不只是教授和学者,还兼职法律咨询和高级学术管理。苗建时十分推崇跨学科的方法,他曾提到1996-1998年参加的哈佛世界宗教与生态系列会议:“宗教学者、气候科学家、生态学家和环保活动家坐在一起,研究全球宗教传统如何发挥作用,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改造我们的社会。大家讨论的结论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社会意义。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昆山杜克大学,2020)这场会议既是他从事道家和生态交叉研究的滥觞,也让他见识了跨学科知识足以改变世界的巨大能量。这个信念还被他应用于汉学研究中,他将可持续问题放在环境伦理和文学批评的双重视域下进行考察,并从审美、政治等多个角度设想未来。跨学科这种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指导他跨越传统的汉学理念和方法,为实际问题打造创新的解决方案。
苗建时的汉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扬举(2015:140)认为,苗建时从“宗教与生态”的角度关照道家可谓独具慧眼,“这方面的特点正是现代环境哲学所缺少的。而且按照现代环境哲学的运思,很难产生道家道教那种精神生态的思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李家銮(2021)高度评价了苗建时关于道教生态理念的研究对当今世界的价值。著名生态学家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对苗建时集汉学的高度、生态批评的广度以及跨学科的经验为一体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称他为“世界道家与生态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Mary,2018:269);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师文德(Hal Swindall)评价道,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生态学角度分析中国宗教的汉学家,苗建时在将古代哲学应用于当代生活方面成就卓越(Hal,2016);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亚那瑞拉(Ernest J. Yanarella)认为,通过对道家哲学的精湛重建,苗建时的著述已然成为东方思想,尤其是道家研究领域的最强音(Ernest,2018:259)。
(二)西方生态研究的“道家热”
20世纪以来,在西方传统自然观无力于应对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西方生态研究开始寻求自身以外的力量。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儒、释、道等蕴含丰富生态哲理的东方文化,产生了大量学术论述和成果。而在这些东方哲学中,道家学说与生态的关系最为紧密,便形成了西方生态研究的“道家热”。
西方环境伦理学家认为,道家用“物我为一”的观点看待自然,以“无为”的方式对待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深层生态学的理念存在本质上的联系。深层生态学之父阿伦·奈斯(Arne Naess)将深层生态学的哲学基础归功于道家等东方传统文化(Arne,2005:12)。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赞誉道家为“传统的东亚深层生态学”,在西方从传统自然观的二元论走向现代环境伦理的整体论的过程中,道家有机、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其提供了形而上学模型,使其能够在理性层面展开思考的维度(Baird,1994:209)。西尔万(Richard Sylvan)和贝内特(David Bennett)对道家思想与深层生态学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他们指出,齐物论等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人类沙文主义”倾向,消解了人类干预自然的特权,为深层生态学“顺应自然”的社会模式提供了实践基础(Richard & David,1988:148、155)。
西方环境美学家也从道家思想中找到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美国生态诗人斯奈德(Gary Snyder)将道家的精神注入其诗歌的自然审美观中。他指出,“‘道’指的是真理的本质和门径”(加里·斯奈德,2014:165),在道的指引下他走向荒野,寻求人类复返自然的途径,由对自然的审美欣赏生发伦理的自觉。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认为,诠释了道家自然观的中国园林美学兼顾人与自然的需求,将包括他提出的“参与美学”等环境美学观付诸了实践(Arnold,2012:137)。他还致力于推动西方环境美学走向中国式的生态美学(阿诺德·伯林特 赵卿,2015)。塔克(Mary Evelyn Tucker)进一步推进了他的想法,试图用道家和儒家思想弥合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鸿沟。在类比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环境美学后,她肯定了道家所体现的人在自然中的诗性生活与环境美学的契合,她希望在生态实践中综合体现道家的自然生态观和儒家的社会生态观(Mary,1994:159)。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也越来越关注道家,他们的“伙伴伦理”“雌雄同体”与“交叠性”等观点与中国道家思想中的“物我同一”“知雄守雌”和“无中心主义”观点高度吻合(华媛媛 李家銮,2020:5)。华珊嘉(Sandra Wawrytko)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审视了《道德经》中自然和女性,将之与生态女性主义联系起来(Sandra,1981:65)。吉特·纳宁格(Jytte Nhanenge)则视东方哲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为人类文明的出路,并借用道家的阴阳学说解构了男性压迫女性和自然的二元对立逻辑(Jytte,2011:xiv)。
除此之外,还有后现代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禅学大师铃木大拙(D.T.Suzuki)和艾伦·瓦茨(Alan Watts)等众多从生态角度研究道家的学者,他们的著述也一同建构起了20世纪道家在西方的生态化。
如上事实表明,道家思想在当代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生态理论和研究,而苗建时以道家思想为对象的汉学研究正是在环境危机年代的“生态化”和生态研究的“道家热”中应运而生的。
二、苗建时的道家研究
(一)渗透(Pervasion):生态视角的道家研究
综观苗建时生态视角的道家研究,“渗透”可构成其研究视域的突出视点,由此辐射出自然的主体性(the subjectivity of nature)、流体生态学(liquid ecology)和身体的多孔性(the porosity of the body)等概念。
首先,苗建时通过阐释“自然的主体性”勾勒出道家自然理论的基本轮廓。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是人的特性,只有人类可以理解并塑造自己,而自然是只能被动地遵循规律的客体,存在于人的身体之外。与之相对,道家则主张“主体性”为包括人类、自然在内的一切存在所共有。自然的主观化意味着自然成为一股具有参与性和存在感的力量。这一方面要求人们从进化的角度去认识自然:“‘自然’的自然性在于它是持续进化,且不断产生新的复杂的形式和物种的……它有一种自我生成的创造力”(James,2017:33)。另一方面意味着,正如人生活于自然之中,自然也存在于人的身体之内,或者说自然与身体是休戚相关的。
接着,以自然的主体性为基础,苗建时进而提出“流体生态学”和“身体的多孔性”。流体生态学可以理解为“气的生态理论”(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qi)。作为这一理论的来源,道家术语“气”被总结为一种“流体的活力”(liquid vitality)。
面对压力时,固体的反应是变形,而流体通过流动来对抗。基于自然的主体性,这种活力既存在于人体内,也流动于自然景观之中。人通过呼吸、修道(daoist body cultivation)等形式交换自然与人体之间流体活力,协调身体内部动态与宇宙环境动态,从而达到健康和幸福的状态。而这种自然与身体的相互渗透,是以身体的多孔性为前提的。苗建时指出,皮肤是一层向世界开放的多孔膜,外界的“气”经由它涌入多孔体(James,2017:65)。
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也研究了作为万物本源和物质存在形式在中国哲学里频繁出现的“气”:“不同形态的‘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万物因此而呈现出一个单一的流动的过程”(杜维明 刘诺亚,2004:88),“人体最优秀和最精细的‘气’与自然界的万物自始至终保持着惺惺相惜的关系”(杜维明 刘诺亚,2004:91)。因而由“气”组成的宇宙是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世界也可解释为“不断发展和转化的动态过程”(杜维明 刘诺亚,2004:91),而自发自生的生命进程也具有了包容万物的特征。“气”的学说表明了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即“把物质和思维合而为一”,杜维明由此概括出中国人的自然观——“存有的连续性”。
无论苗建时的“流体生态学”,还是杜维明的“存有的连续性”,都指向通过流体活力对多孔的身体的渗透,溶解人与自然的界限。“道家的身体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肉体现象,更是一个生态过程,通过多孔的皮肤与宇宙流体活力所广泛分布的环境相联系”(James,2017:105)。这意味着,生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是身体的问题,生态危机极大地威胁着被渗透的身体,人类的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由此渗透进生态关系的网络中。
(二)修身(Daoist body cultivation):生态美学的践行方式
虽然距离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已过去半个世纪,但生态问题至今仍亟待解决。苗建时认为,环境保护运动的失败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传统二元论的沿用,在这种思维中,不仅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的理性思维与被视为“他者”的身体之间也是分离的(James,2017:152)。这便形成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缓冲自我(buffered self)”。泰勒认为,“缓冲”可视为现代背景下的人类自我关闭内部(思想)和外部(自然、物质世界)之间可渗透的界限的一种转向(Charles,2007:27)。
对此,苗建时不吝以一针见血的笔调进行批判:“随着这种气候变化事件被更广泛承认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威胁,泰勒所说的‘缓冲自我’的现代社会想象越来越有可能崩溃”(James,2017:20)。他进一步从道家思想中寻求出路,探究如何正向强化这种联系,以产生生态学上的积极效果。如上一节所述,苗建时强调通过“气”的渗透实现身体与自然的融合,而作为“渗透”发生的主要场所,身体便成为克服“缓冲自我”的突破口:“身体与世界间本质存在的多孔性意味着可以构建一种生态敏感性,这不仅基于世界对身体的渗透,还有人体对世界的渗透”(James,2017:125)。进而,他提出进行一种道家传统中“修身”的实践。
苗建时认为,修身的目的在于消融身体与自然的界限,因而可以作为一种培养生态敏感性的方法(James,2017:117-118)。他以东晋到道家门派上清派的冥思练习“存思”为例来进行佐证。《天隐子》有云:“存,谓存我之神;想,谓想我之身”(司马承祯,1937:7)。“存思”通过意念的专注在体内产生丰富的知觉经验,使知觉具体化,从而达到内外如一。这种实践中身体体验的习得不是直接来自世界观或伦理理论,而是来自对世界的经验和这种经验所产生的知觉,因而证实了训练身体以带来一种经验式的意识的可能性。对自然风景的“存思”、观想将山水的外部景观与骨骼、内脏、血液和呼吸的内部世界联系起来,使得人的身体能够“共情”自然的“身体”,生态意识和生态敏感性应运而生,这对于环境保护运动而言有很大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苗建时倡导的修身方式是多样的,它源于但不限于道家的冥想、太极等修炼方式,还包括瑜伽、禅修、武术甚至舞蹈等关于身体的学科,而最便捷的是对自然风景的观赏与思考。
(三)整体繁荣:生态建设的道家伦理
论及道家与生态建设的具体联系,苗建时提出将道家作为一种可持续性的文化,以取代现代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无法将人类的繁荣融入地球的繁荣,而事实上人类与地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James,2017:12)。这里的可持续不是一个单薄的概念,而是一个整体框架,包括审美、道德、政治等多个层次,它们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走向——整体繁荣。
“整体繁荣”的可持续愿景来源于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世界性的生态”(Cosmopolitan Vision of Ecology),即新的绿色现代性需要一个新的繁荣愿景,这个愿景不是完全由经济增长决定的,而是整体上的“福祉”(Ulrich,2010:262)。
审美层次上的繁荣是建立在修身的实践之上的。在论述了修身的实践何以成为生态敏感性的美学基础后,苗建时又援引Debbie V. S. Kasper“生态习性”(Ecological Habitus)的概念进一步阐发。生态习性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由与生态相关的性格、实践、认知和物质条件(可感知为一种生活方式)组成的持久而多变的系统,且与社会生态环境相互塑造”(Debbie,2009:318)。所以,修身所培养的生态敏感性可以有效转化为塑造生态环境的审美敏感性,从而达到一种审美繁荣。
道德层次上的繁荣以道家伦理为基础。身体对于自然的多孔性意味着,人只要活着就必然涉及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转化,当代消费主义更是从本质上合法化了这种消耗,自然被认为是纯粹供消耗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关系伦理的一部分。因此,多孔的身体需要一种道德伦理。苗建时认为,如果诉诸道家,无论是遵从“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陈鼓应,1984:188)“兵者不祥之器”(陈鼓应,1984:191),即将暴力掠夺最小化的伦理规范;还是推崇“天人感应”,即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伦理价值,都能促成一种对生态保护切实有效的道德伦理的施行。“中国的生态环境大可从其基于宇宙万物相互影响理念(如‘感应’)的本土价值观中受益”(James,2017:159)。道家的伦理规范成为苗建时实现道德繁荣的出路。
政治层次上的繁荣要实现城乡、贫富间的平衡。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日益不平衡的财富模式,富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自己免受生态危机的影响,而工业污染、资源枯竭等环境成本更多由穷人承担。因而,生态危机也是一场正义危机,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审美、道德这些个人层面的努力,政治上也需要转变。苗建时认为,这需要通过地方空间的民主来调和(James,2017:162)。道家讲求“以道观之”,人类的幸福在于对自然界集体主体性的幸福。当给予农村、偏远地区等现代意义上地域中的“他者”一定的政治权力,实现城市的多数人和农村的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将有助于将城市现代化的政治纳入宇宙权力生态的整体运作中,确保城市的生活生计依赖于农村的同时,城市精英做出的决策也符合农村地区的利益。
三、苗建时道家研究的价值
(一)走向“新汉学”②
以16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算起,汉学阅尽了四百年沧桑。从早期以法国汉学为代表的传统汉学走向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学”,从重人文科学和学术精神的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到重社会科学和实用性的现代中国研究,汉学已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而在当下的21世纪,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早已日新月异,正如苗建时所说,“它(中国)越来越排斥被传统学术研究的主要问题所框定,尤其是西方的汉学研究方法”(James,2017:142)。因此,学界正面临着“新汉学”的转向,而苗建时突破传统汉学的道家研究具有一定的建构意义。
第一,传统的汉学研究热衷埋头于文献考据的历史资料,以呈现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轮廓。这种史学角度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文献的陈述,很难把握中国思想的深度。台湾大学教授黄俊杰(2008:293)就曾指出,以儒学研究为例的战后美国汉学界着重于思想内容之研究,较少涉及背后的思维方式或理论基础等。而苗建时从文化范式的角度理解道家:“我对道家的实践、文本和语境的生态批评旨在揭示自然是如何在道家的想象中产生、如何参与道家思想的建构,并如何直接作用于实践的”(James,2017:146)。他试图阐明道家的自然观在其文本和观点中产生的过程,从而借鉴其中的思维方式,推究文化传统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传统的汉学研究方法并没有在为中国设想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效力”(James,2017:141),他的论述中也不乏对传统汉学壁垒的突破,和对道家当代价值的探寻。
第二,传统汉学倾向于从过去的角度理论化中国,通过把握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主题、价值观来定义其特征,并用于理解今天的中国。现代人习惯于把文化传统想象成陈旧的遗产,主要用于产生民族主义价值观,或者作为道德教化、尤其是规避消费社会影响的来源。
所以,西方把中国盖棺定论为建立在“儒家价值观”的国家,便忽略了道家、禅宗等文化传统是如何在当代中国不断自我改造,超越西方霸权,重写现代性话语的。苗建时却透过“可持续性”的放大镜,关注中国是如何试图通过建设“生态文明”来绘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苗建时认为:“这个术语(生态文明)比传统的技术科学方法更能全面地解决环境问题”“这将使中国能够在即将到来的生态挑战中生存下来”(James,2017:150)。同时,他的论述大多以中国的环境时事为例证,以展示道家观点与当代问题具体交叉。苗建时在中国访学、长期生活、工作的经历使得他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更真实细致,这与新汉学致力于把全世界的汉学学者请到中国,推动世界对中国进行多方面的认知和理解的诉求不谋而合。
苗建时还强调“可持续性”对其汉学研究的当代转向的作用:“当可持续性成为一种文化的导向性问题时,这种文化就不能再从过去追溯和定义其身份。相反,从一个尚未存在但人们希望会存在的时代的角度来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模式都呈现不可持续的当代,基本的导向框架必然来自未来”(James,2017:140)。换言之,可持续性视角的研究是由对未来世界存在的不可想象的希望驱动。可持续性的概念从根本上将苗建时的学术模式转变为兼顾过去、当下和未来。
(二)东方主义的逆转
传统汉学家在阐释道教时不免落入用现代西方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讨论道家的窠臼。例如李约瑟从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角度来评判道家等中国文化,而科学显然属于西方文化范畴。这种学术模式并非没有价值,但本质是东方主义的(转自胡传胜,1999)。
作为走在前沿的汉学家,苗建时十分强调对道家的非殖民化解读:“这种对道家的解释不应该被解读为浪漫主义的东方主义者试图复兴‘美丽’或‘传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已经在现代性中丢失了”(James,2017:15)。
首先,他主张从“对抗阐释学(confrontational hermeneutics)”的角度来阅读道学;“对抗性诠释学”是汉学家迈克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提出的一种针对道家文本的解读策略。指读者以开放的态度阅读与自己思维模式或观念不同的文本,并允许该文本对自己既有的文化框架进行消解和重构(迈克尔·拉法格,2008:48)。这一方面要求当代读者思考文本在其原始历史环境中的意义,而非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的牵强附会。另一方面还要用文本中的价值观颠覆自身,苗建时的道家研究正是从道家思想的可持续性反思当代西方的自然和环境观念。
其次,他审思了道家思想本身反主流、反中心主义的特质。中国历史上的道家相对于儒家而言是个边缘的流派,从一开始就充当了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作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替代品。因此,道家不仅作为一种精神传统,更作为一股削弱主流的力量发挥作用。苗建时认为:“看到道教不和谐的一面,就是看到其非殖民的一面”(James,2017:xviii)。现代社会同样需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而道家有能力通过延续其边缘的价值观来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逻辑。
最后,他结合道家概念讨论西方思想中的有关生态的关键词,这是东方主义者从西方理论中解释亚洲传统的程序的逆转。苗建时用丰富的例证实践了他的逆转模式,比如“创造”和“建模”的区别(James,2017:33)。道家认为,宇宙中不同维度之间的是“建模”的关系。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指人、自然和道在一定的等级框架中相互遵循或被效法,而作为终极规范的道是“无为”的,它塑造了人和自然以及道自身的主体性,一种自我创造的力量,这是宇宙间万物和谐共生的基础。而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了世界,现代西方文化也否认自然的主体性,因而人类可以无止境地滥用乃至破坏自然,这是生态危机发生的文化背景。
(三)作为方法的道家思想
现代性批判是当代西方汉学家们的关注点,因而使西方汉学研究附着了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有学者就将安乐哲(Roger T. Ames)、郝大伟(David L. Hall)等对中国哲学美学研究的立场视为一种后现代(郑家栋,2004),与西方相比,中国思想是一种另类的思想模式,向西方显示了一种非本体论思维的可能性。
就如何看待中国思想而言,苗建时的立场显然也是后现代式的,他对作为西方生态不可持续性根源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加批判。但他的汉学研究又因道家这种外在性批判手段而区别于西方后现代——后现代时常被诟病囿于欧美的内在思路而无法真正对欧美产生批判的意义。他指出:“我希望它(道家)能引起全世界的共鸣。推翻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对规范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构建的计划需要世界各地人民的参与”(James,2017:139)。这里,中国不再仅仅成为研究对象,而是彰显出其作为理论的方法意义。
苗建时批驳下的现代社会秩序,是在社会功能上失调,经济上失序,生态上不可持续的。因而,他以这些现代性的弊端为指导,提倡一种新的伦理框架,即可持续性框架。“同样作为文化范式,可持续性并不像现代性逻辑那样‘产生’思想流派。相反,可持续发展的范式是探寻能够产生人类乃至宇宙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模式”(James,2017:142)。如前所述,道家思想在自然观上强调相互渗透的关系、修身的实践和整体繁荣的愿景,大可成为可持续思想来源的巨大宝库。
苗建时还提出了作为方法的道家的三方面优点:以道家为认识论,能更好地理解进化科学、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以道家为世界观,有助于加快生态危机和可持续性建设等问题的解决;以道家为实践观,可以促进整体繁荣在美学、伦理、政治等方面的实现(James,2017:18)。
值得一提的是,苗建时所致力于的可持续性方法,既来源于道家,又“不需要局限于道家或中国”(James,2017:146),“考察中国文化传统的原因不是为了道家而研究道家,也不是为了中国而研究中国,而是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论化道家”(James,2017:141)。因而,道家成为他审思现代性危机的迂回点,从而构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
苗建时之所以以中国为方法论,是因为他坚信中国是一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的思想资源。对于具有比较文化专业背景的他而言,中西的比较也是一种方法,一种启发。这也表明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西方汉学研究是一种基于西方视野而展开的比较研究。在此过程中,道家等中国思想也被纳入到了当代的问题视域里,被当代化,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
由于在思辨性、逻辑性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思想文化向来被认为是难以融合的,但是苗建时从生态维度阐发道家概念,中国传统思想反而成为对启蒙以来的自然审美观念的补充,面对生态危机的全球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又同现代西方哲学形成了平等对话。道家思想是这样一种可以为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新路径的智慧,正如苗建时所相信的,它有推翻现代性的力量,也足以产生能引起国内外人们共鸣的见解(James,2017:139)。
在这种中西交融的认知之上,苗建时的汉学研究则打破了一种闭门造车式的惯例,呈现出双向对话交流、关注当下中国等“新汉学”的态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苗建时的汉学研究对当代我国的道家研究也具有一定启发。中国传统思想只有在挖掘当代价值和与世界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
但苗建时的汉学研究也存在局限,他极力挖掘道家的生态思想,却对儒家思想不乏贬损。他将道家生态思想视为替代西方现代性和儒家的失败统治的参考框架(James,2017),忽略了儒家思想的生态性。将儒家界定为与西方现代性相当的反生态价值观,这种论调在海外汉学界时有存在,唐丽圆(Karen Thornber)就曾以韩愈的《天说》为例论证儒家学说的人类中心主义(Karen,2012:32)。事实上,儒家思想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塔克就曾提出儒家强调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是实现自然生态稳定与和谐的前提(Mary,1994:159)。因此,在跨文化难以避免误读的今天,汉学的重心亟待回归中国,纠偏与重释将寄希望于“新汉学”的建构。
注释:
① 指学科的“跨界”研究,即跨学科研究、学科的交叉研究。
② “新汉学(New Sinology)”的概念最早由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2005年提出(Ge-remie,2005),后又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推向西方主流话语体系(Kevin,2010)。而中文语境下的“新汉学”是由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大发现时代”催生新汉学》一文中首次提出(李学勤,2010)。2012年,国家汉办设立资助海外青年学者来华学习合作的 “新汉学计划”,“新汉学”一词开始进入中国官方话语系统。同年,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正式打出“新汉学”的旗号。(Geremie, B. 2005. New Sinology [J].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Newsletter,(3) :4-9;Kevin, R. 2010. A New Sinology——Australia Needs to Engage in a More Sophisticated Dialogue with Chin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0-4-28;李学勤. 2010. “大发现时代”催生新汉学[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