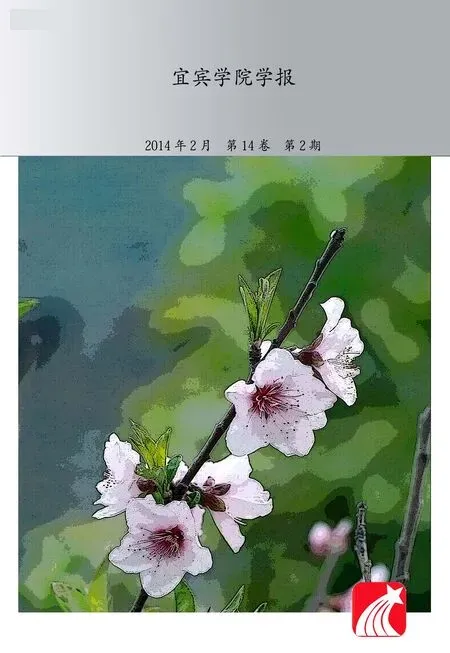留学生身份与“越境”行为
——被忽视的现代留学生小说的典型之作
2014-03-12王国杰
王国杰
(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自高自大的清政府在对列强的战争中接连失败之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转而向列强学习,于1872年首度派遣留学生,寄望他们带回西方先进技术的秘密为我所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青年掀起了留学潮,从被动的差遣,变为主动要求,满怀寻求救国之道的热情出走他乡。这些囿于孔孟之道的中国青年,进入全新的文化环境中,眼界大开,言行也少了约束,演绎出丰富多彩的留学生生活,留学题材很快成为中国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容闳《西学东渐记》、苏曼殊《断鸿零雁记》、陈天华《狮子吼》、向凯然《留东外史》等都曾使得洛阳纸贵。进入民国以后,留学生人数倍增,涉足地域更广,从事文学创作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如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及创造社诸君,留学英国的徐志摩、许地山、钱钟书,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冰心、林语堂、朱湘,留学德国的冯至,留学法国的巴金、李金发、李健吾、李劫人,留学苏联的蒋光慈等,这就为留学生们生活的记录提供了便利。而“留学生文学”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使用,也亟待清理归纳。
一 “留学生小说”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留学生文学”的内涵大多语焉不详,缺乏精确的定义,一般把作品中是否存在留学生人物作为标尺,因此留学生文学概念比较模糊。江曾培主编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则把异国经历作为衡量标准,不仅选了留学生的作品,还选了访问学者的作品,“精选留学生(访问学者等)写的留学题材的作品”[1]。这两种标准都使失于宽泛,而使得留学生文学概念更加模糊,例如留学生的恋爱经历、求学等,与国内人无异,与其留学前也无不同,并未受到其留学行为的任何影响,也被算在留学生文学范围内,便有鱼目混珠之嫌,再如留学生、访问学者的异国见闻与普通游客的异国见闻也相差无几,把其算作留学生文学,也是名不副实的。
要给留学生文学下定义,必须凸显其根本特征。留学生身处异邦,自然会见到许多奇闻异事,也会有生活、恋爱等方面的苦恼,这些都不是他们所独有的,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两国文化交叉的部分,正如叶维丽所说,“留美学生的经历最令人感兴趣之处恰恰在于它发生在跨文化和中美两国历史交织的背景之下”[2]7。董炳月的定义便抓住了这一典型特征,“在我看来,‘留学生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创作,在此前提之下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其一,作者(创作主体)为留学生;其二,以留学生活为描写对象;其三,表现起源于‘留学’这种越境行为的异国、异民族、异文化之间的冲突”[3]。留学生身处异邦,时空的变化使得他们的中国人身份凸显出来,异邦人对他们的态度,折射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同时中国文化与新接受的异邦文化之间的差异,必然在他们的思想上造成激烈的冲突,这种异邦的生存处境和文化交叉现象就是他们的独特之处。以董炳月的定义来看,现代文学史中严格意义上的留学生小说并不多,即使如郁达夫《沉沦》和《银灰色的死》这样著名的小说也把重点放在青春期的性苦闷和爱情渴望,缺少对留学的越境行为所导致文化冲突的表现,难以称作留学生小说代表。与此类似,大多数讲述留学生活的小说,往往都避重就轻,写成了恋爱小说、轶闻小说或革命小说等。1928年,四川学子陈铨也加入留学生队伍,在美国奥柏林大学期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冲突》,这篇小说以恋爱故事为主线,透视了身着西装的留学生们的思想,讲述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可谓现代文学史上留学生小说的典型之作,然而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它都缺乏重视,对陈铨小说的研究都集中在《天问》上,《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未收录陈铨的任何小说或散文,就连杨义先生把陈铨小说单列一节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独独漏掉它。
二 外新内旧的留学生群体
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不可小觑,留学生社团也随之增多,但是这些社团与先前的社团已经大不相同,之前的留学生社团更多地强调理想追求,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此时的留学生社团却日渐没落。1922年初到美国留学的闻一多曾说,“关于支加哥,现在只讲这些。我要再告诉你们这里中国学生团体生活的情形。这里的学生政治恶于清华。派别既多,各不相容,四分八裂,不可收拾。有一人讲得很对:处处都可以看见一个小中国,分裂的中国”[4]52。陈铨在《冲突》中细致讲述了芝加哥学生社团的内部状况。
1917年成立的“十字架与宝剑”(Cross and Sword,简称C and S)兄弟会是一个著名的留美学生社团,它模仿美国的兄弟会形式,兼具中国古代民间帮会的色彩,对成员的言行有严格要求,总体方针是努力改良社会,曾经担任过此社团负责人的洪业回忆说:“当年我们年轻得很,要效法耶稣,以教育与政治来转化社会。十字架,是由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句话而来;宝剑,则指中世纪的十字军。我们采用了一些欧美共济会的仪式,意识下要恢复《三国志》里桃园三结义的道义精神。”[5]51社团章程中规定:“(一)目的:包括研究、计划、合作提高中国的地位;会员间应增进兄弟如手如足精神,相互团结、协助、照护,同样仿效美国兄弟会惯例,各兄弟誓约对一切会务均须严守秘密。(二)会员:任何中国男人均可入会,但必须具备下列三条件,优良品德,对终生有确实目标,领袖的特质。”[6]55-56《冲突》中刘冠成提到自己的兄弟会名称为“十字架与枪”,显然是模仿“十字架与宝剑”,“宝剑”与“枪”之差,正是善恶的分别,十字架与宝剑有着内在联系,宝剑是指受基督教教义引领的十字军,有着正义的追求目标,而枪却只是武力征服的代名词,与十字架放在一起具有反讽效果,象征着刘冠成一帮人的恶俗和滑稽。他们在戏院里看够女人大腿后,就聚在一起喝酒搓麻将,互相之间稍有口角就大打出手,毫无兄弟友善之情,分明是一群无赖流氓。
留美中国学生会是当时留美学生社团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社团,它曾积极尝试现代民主政治方式,比如代表会议制度、年会制度,并邀请中国政府官员、美国教育家和美国官员等到会演讲,引领过时代改革风气,但是到20年代,它也没落了。《冲突》中讲述了位于芝加哥的中部学生分会的情况,会长刘冠成是无赖之流,他聚集一帮人把持社团工作,不与他同流合污的委员大都是书呆子,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因而社团被搞得乌烟瘴气。王良魁以考察名义到欧洲为混战的军阀购买军火,又预备到美国游说借外债,这都是典型的助纣为虐行为,刘冠成不但不反对,反而借机讨好,他以留美中部学生会会长名义打电报表示欢迎,派人前往接洽,同时筹备欢迎会。陆率周等人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同学签名召集大会,希望用合法方式阻止这种恶劣行径,但是由于社团日常管理早已懈怠,组织涣散,无法再实行有条不紊的民主会议,最终导致留学生大会现场混乱不堪,双方大打出手,桌椅横飞,一件事都没有形成决议,留美学生会尚且如此,其他社团状况更是可想而知了。
除了学生社团中帮派和没落外,陈铨还提到了留学生们的各色形象:“从来不剪发的艺术家;整半年坐在小屋子里观察宇宙人生的哲学家;拉坏峨璘把旁边屋子的人急得破口大骂的音乐家;跳舞把脚指头跳肿了,痛了三天三夜的跳舞家;隔二十英里可以嗅得着他身上的香水的修饰家;吐黄痰扭鼻涕不用手巾的自由主义者;三年大学读了两个半积点的打破学校制度的急先锋……”[7]122陈铨并不是采用戏剧化的小说手法,闻一多对留美学生的消极心态深有同感,“我观察这里的中国学生,真颓唐极了。大概多数人是嬉嬉笑笑,带着女伴逛逛而已,其余找不到女伴,就谈论品评,聊以解嘲而已。高一点的若谈到正当的serious的事,也都愁眉叹气,一筹莫展。总而言之,他们没有一点振作的精神”[4]52。叶维丽分析当时留学生群体没落的原因,受到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留美学生对政治的冷淡也反映了一次大战后美国大学校园的普遍风气。那一时期的美国男女大学生醉心于寻欢作乐,追求‘现代派’的生活方式,政治上不求上进甚至趋于保守。”更关键的是他们被中国社会的遗忘,“学生们由(清末)想象中的中国改革参与者变成了军阀时代失望的旁观者”[2]43。也就是说,在武力角逐的时代,他们有心无力,实际上已经成为零余者了,故而他们远离世事和没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冲突》中,我们看到的是陈铨对留学生文化心理的审视。这些留学生是从众多人选拔出来的佼佼者,肩负着国人的期望来到异邦,在美国还时常以高等华人自居,然而他们学到的却只是新潮外衣,拒绝西方文化的深层洗礼,里面包裹的仍然是封建时代的糟粕文化。没有是非观念,讨好军阀走狗;尔虞我诈,原本是西方民主象征的会议形式,却成了中国留学生斗殴的场地等,这些表里不一的反差构成一种强烈讽刺效果。
三 从伦理婚姻到自由爱情:异邦文化的浸染
异邦各种文化都会对留学生们的既有观念造成冲击,其中最强烈的莫过于爱情观念。留学生中的男青年占绝对多数,他们大多孤身来到异邦,正值性欲旺盛的青春期,年轻女性的魅力难免会成为他们心中的蛊惑,郁达夫的《沉沦》便是对留学生性苦闷的淋漓描写,但是郁达夫仅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心理,陈铨的《冲突》不仅注意到了青年的性欲问题,更把它与中国伦理道德构成一对矛盾关系,在冲突中表现留学生思想上的文化交叉现象。
西方文化中推崇的爱情,更强调人的生物性本能因素,是非理性的,弗洛伊德认为它源于性本能,“我们所说的爱的核心内容自然主要指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爱以及诗人们吟诵的爱)”[8]99。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强调理性约束,推崇伦理道德和责任,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要求。小说中陈云舫在留学之前的婚姻是典型的中国婚姻,其中虽然不乏激烈的性欲冲动和对婚姻好奇等非理性因素,但更强调的是理性因素,即妻子貌美而聪明,凄楚身世令他同情,并可借此安慰母亲,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促成了他的婚姻,这也是中国人的婚姻观。陈云舫之前在学堂里因家书频繁而引起朋友取笑,他丝毫不放在心上,足见他自己也是满意的。但是出国以后,他接受了西方文化,家庭和婚姻观念转变了,例如对母子关系看法改变了,不再承认母亲的养育之恩,而是认为母亲抚养儿子是出于自私的考虑;他隐瞒自己的婚史,而与刘翠华谈恋爱,要和妻子玉英离婚,理由是西方文化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其实他所谓的爱情又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说,“爱情是建筑在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同时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而对象则将主体的一部分自恋性自我力比多引向它自身。这是一个只能容纳自我和对象的情况”[8]157。刘翠华对陈云舫的吸引,便是性的吸引,他孤身在外,性欲得不到满足,有着梨花一样白的脸和媚人笑的刘翠华的出现,便成为他的欲望的散发对象,“翠华又太可爱了”,这种“可爱”便是性欲作祟。中国留学生中的男青年们,很多都有陈云舫一样的心态,小说中提到纽约的留学生相互攀比,办奢华舞会捧女王的奇谈,名义上是“爱美的精神”,其实都是力比多在作祟,由于留学生中女生稀少,男女比例严重不均,他们性欲旺盛,无处散发,故而推出一个女王作为众人意淫的对象。
中国道德文化对陈云舫性欲望的否定,是采用梦境的形式显示的。他梦见母亲诉说自己的凄凉,妻子诉说他的负义,醒来后冷静地一想为自己不顾一切的恋爱行为忏悔,觉得对不起家庭,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心中又占据主导位置,“他还有什么资格谈恋爱神圣?他自己就是他已爱的妻子不忠实的叛臣!他还有什么资格讲男女平等?他自己就是一个压迫女性的暴虐者!他还有什么资格讲救国救民?他对他最亲爱的家庭,都没有一点同情心”[7]85。梦醒后他还不顾身体虚弱立刻写信回家,以表示自己的忏悔,这是他内心的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抗拒,但是这种抗拒能力也有强弱之分,弗洛伊德认为,“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抗拒有着程度不同的能力,它们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是挡住还是接受他的性对象选择(erotic object-choices)的历史影响的程度”[8]180-181。陈云舫的抗拒能力,并不是源于个人的反思,而是由于刘翠华的拒绝使他感觉绝望,退而寻求心理安慰,才产生忏悔心理,一旦刘翠华再次来到他面前,暗示他成功的可能性之后,他受到蛊惑,会又回复到爱情观念上来,他的性欲望与西方文化中的爱情观念相唱和,他立刻把自责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再看一看翠华满面的泪痕,活像一株带雨的梨花。她娇嫩鲜红的嘴唇,着雨以后,更艳丽极了。”接着立刻抱住她,说爱她,并用爱情为自己的背叛解脱,“恋爱是神圣的,他爱翠华是没有错的。他同他妻子不过是旧式的强迫的婚姻,他当然应该脱离的。脱离不但他自己认为应该,他妻子方面,也应当认为应该,他们彼此如果还想当‘人’——当有自由意志的‘人’——拿道义来说,拿责任来说,都是应该脱离的”[7]139。女留学生刘翠华也深受恋爱观念的熏染,把其置于伦理道德之上,“恋爱是神圣的,自由的,不应该受任何束缚的。旧式婚姻,是一点价值没有的,我们处在新时代的人,还管它作什么?”[7]50东西方婚姻的要求,一个是要求理性地承担家庭责任,一个是顺从生物学本能要求,两者的差别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别,陈云舫在婚姻和爱情之间的抉择,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鲜明体现。
四 “叔本华味”的小说人物
1928年陈铨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留学,由于对德国哲学的爱好,1930年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后,向清华大学申请将五年留美计划,改为两年留美、三年留德,获得批准后于当9月转赴德国基尔大学学习,跟随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理查德·克罗纳尔(Richard Kroner)系统钻研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等德国哲学家著作,还参加了德国的青年黑格尔学会,1933年方才转入柏林大学。在陈铨赴德国之前,即1928至1930年间,虽然未得到导师系统指导,但他已经非常喜爱德国哲学,《冲突》也正是写于这期间,小说中穿插的哲学观念也具有这一阶段性特征。
1944年陈铨出版哲学著作《从叔本华到尼采》,书中把尼采哲学观点分为对叔本华哲学观点的赞成时期、过渡时期和反对时期,这也可以视作陈铨自己的哲学思想历程,他后期的作品都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然而早期的他,却是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首先,《冲突》中的人物就做了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传声筒。刘翠华在为是否继续爱陈云舫纠结时,感到生活的痛苦,张明琼便向她阐述叔本华的哲学:欲望是痛苦的源泉,活着就要受欲望支配,自杀并不能摆脱欲望,仍然是基于欲望,彻底消灭痛苦便要彻底消灭欲望。而超越这种悲观主义的方法,张明琼说只能凭借个人的领悟才能,其实是当时的陈铨也不甚了了,当陈铨思想由叔本华悲观主义转向尼采乐观主义时,他也才超越了这种狭隘意识,正如他在《从叔本华到尼采》中所说,“尼采渐渐的感觉利用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危险,因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虽然能够使我们清楚认识人生的痛苦,推翻肤浅无聊的乐观主义,然而大家因此很容易对人生颓废悲观,失掉了对人生的勇气,甚至于根本抛弃人生”[9]90。尽管陈铨后来转而崇尚尼采,但是在早期创作中是赞成叔本华观点的,《冲突》中黄则凌的行为也是悲观主义的体现,他追求刘翠华失败,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于是充满痛苦,悲观至极,便在陈云舫和刘翠华的婚礼上开枪击毙他们,自己也一起灭亡。
除了人物思想上的悲观主义,小说也体现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观点。“叔本华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意志’。意志是宇宙人生的泉源,是推动一切的力量……意志完全是盲目的,没有目标,没有理性,我们不知道它从何处来,也不知道它从何处去。它强烈地支配一切,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拒绝它,停止它,消灭它。”[10]124-125陈云舫是带有叔本华味的人物,他受叔本华启发发明了冲突哲学,因为叔本华就把意志看作宇宙人生动力的源泉,他要推翻自己先前的宇宙人生,便想到制造意志冲突,把母亲当做具体的冲突对象,借此冲突消灭宇宙人生,痛苦也就不存在了。
陈云舫的爱情抉择是意志哲学的体现。陈云舫头脑中的爱情观念是模糊的,是受叔本华所谓意志驱使,可以说他头脑中有两个爱人,一个是妻子张玉英,他曾经不怕被同学取笑而频繁寄家书,当刘翠华抛弃他之后,他又在昏迷中梦见了妻子,为自己的背叛而忏悔自责,可见他是爱妻子的;另一个是出国后爱上的刘翠华,他被她的白皮肤和笑容吸引,当刘翠华到医院看望他并向他示好时,他又立刻抛弃了背叛妻子的自责,与刘翠华重归于好。陈铨把陈云舫的反复无常,看作是其意志的驱使,无论是夫妻责任,还是恋爱自由,都只是他为自己的行为所寻找的借口,“他自己有时还不知道,他的主张后边,完全是人类自私自利的冲动在支配他一切”[7]138-139。陈云舫的爱情抉择正是叔本华意志哲学的典型表现。
结语
陈铨的《冲突》,不仅写到了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将留学生身上的文化交叉现象细致地表现了出来,并从外表新潮的留学生身上审视国民劣根文化的痕迹,可谓是对留学生的深入透析,从他小说创作中也体现出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因此这部小说可看作是留学生文学的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
[1] 编辑例言[M]//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 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董炳月.《留东外史》的历史位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1):12—23.
[4]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 陈毓贤.洪业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 吴昶兴.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M].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
[7] 陈铨.冲突[M].上海:厉志书局.1929.
[8]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9] 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M].上海:大东书局,1946.
[10]陈铨.文学批评的新动向[M].重庆:正中书局.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