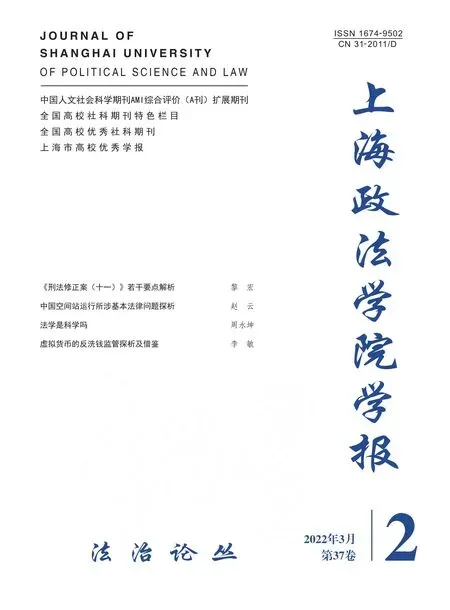航天商业化背景下空间资产融资的法律问题与规制路径
2022-02-04蒋圣力
蒋圣力 戴 苑
一、航天商业化背景下空间资产融资活动开展的前景与风险
(一)商业航天与航天商业化
商业航天是以市场为主导,采用市场手段、运用市场机制、依据市场规律开展的航天活动实践样态,是传统航天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发达航天国家及其航天企业便已将目光投向了商业市场,使得原本具有完全的国有属性、军事属性的航天活动开始出现民营化、私有化的发展趋势,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航天活动及其产品、应用、服务更是快速步入商业化、产业化,进而促使商业航天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①参见巨效平:《国外商业航天发展模式概论》,中国宇航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从基础功能看,商业航天能够完成包括航天器的设计、建造、发射和运营在内的一整套完整周全的航天业务;从核心特征看,商业航天较之传统航天具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对商业市场感知敏锐、对高新科技反应迅速,以及能够更加可靠地实现客户需求等诸多优势。由此,商业航天在当今国际航天市场中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并已成为支撑航天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和促进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①参见蒋圣力:《中国商业航天投资的实践与问题简析》,《国际太空》2019年第7期。
具体及于“商业航天”的概念内涵,其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航天”的实施主体通常为国家航天企业,具体实施方式为过往只为国家政府和军队提供服务的国家航天企业(包括制造企业和系统运营企业)为商业市场提供服务,并将过往限于国家政府和军队所需用途的航天产品和设施设备投诸商用领域;同时,国家政府和军队作为“客户”进入商业市场,就所需开展的航天活动进行招标和采购。与之相对,狭义的“商业航天”的实施主体一般为依照市场化规则成立的私营航天企业(主要表现为私人投资、私人建设、私人运营、私人受益的私营模式),具体实施方式为私营航天企业通过市场化规律从事投融资、招投标、研发、制造、运营、合作等生产经营运作,开展各类商业航天活动。②参见贾睿:《照见未来:一本书读懂商业航天》,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当前,中国的商业航天产业正处于上述广义的“商业航天”即“航天商业化”的发展阶段,表现为由国家航天企业作为主导开展商业航天活动,并在此过程中越发开放地与民营航天企业进行合作,以及越发广泛地吸收社会金融资本。应当认识到,由国家航天企业承担开展商业航天活动的主要功能,实则是现阶段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所应具备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全局看,由国家航天企业承担开展商业航天活动的主要功能,更加符合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从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的要求看,以国家航天企业作为主要实施主体开展商业航天活动,也与军民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在航天领域的具体实现,即航天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要求更相一致。③参见蒋圣力:《中国商业航天金融模式的健全与创新略论》,《国际太空》2019年第1期。而与国家航天企业在现阶段中国商业航天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相适应,大量民营航天企业的快速涌现以及在星箭制造(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发射)和卫星应用(主要包括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两大领域的活跃表现,同样为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④参见曾占魁、史敏辉:《国内商业航天机构调研分析》,《中国航天》2018年第1期。
(二)商业航天投融资与空间资产融资
依托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蓬勃兴盛,商业航天投融资已然成为时下最受社会金融资本关注的热点之一,无论是传统(国家)航天企业还是初创(民营)航天企业,在开展商业航天活动的过程中也均会不同程度地吸纳社会金融资本。就国家航天企业而言,随着所开展的航天活动的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其已不再完全依赖于政府订单的扶持(即资金来源不再是单一的政府投资),而逐步形成了政府订单与商业市场订单(即由社会金融资本投资提供资金)并存的融资模式。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依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在2017年12月18日完成的12亿元人民币的A轮股权融资,即被业界视为由此拉开了国家航天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序幕。⑤《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完成12亿元A轮融资,引入社会民营资本》,https://pe.pedaily.cn/201712/424764.shtml,2021年7月9日访问。就民营航天企业而言,经过商业市场多年的检验和自然筛选,其中一定数量的优质企业也已探索出了能够保障可持续的盈利创收和切实可期待的投资回报的航天业务领域,并进而具备了稳定可靠的融资能力,越来越受到社会金融资本的青睐。例如,2020年8月,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完成了11.925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①参见《蓝箭航天完成新一轮12亿元融资》,http://www.landspace.com/news/shownews.php?id=185,2021年7月9日访问。; 2020年9月,北京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宣布完成了12亿元人民币的C+轮融资②参见《星际荣耀完成近12亿B轮融资,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领投》,http://www.i-space.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3&id=43,2021年7月9日访问。。
在商业航天投融资如火如荼的现实背景下,鉴于空间资产作为开展商业航天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载体的重要地位,针对空间资产的投融资无疑应当是商业航天投融资的一项关键内容;并且,在实践中除了政府投资这一传统资金来源渠道之外,越来越多的社会金融资本通过空间资产融资的方式向商业航天市场的涌入,也着实为商业航天活动主体,尤其是民营航天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③参见杨少鲜、李宏伟:《我国商业航天投融资分析》,《卫星应用》2017年第10期。不过,由于空间资产所固有的移动性和跨界性等特殊属性在客观上造成了针对空间资产融资的法律适用和权利保护往往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因此,空间资产融资对于相关当事方、尤其是债权人(投资人)而言,仍然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基于协同推动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需要,确有必要就空间资产融资设立专门性规则以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从而通过切实保障相关各当事方的合法权益,使空间资产融资能够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更加积极地发挥之于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空间资产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一)《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关于空间资产概念的规定及其争议
在外层空间法/航天法中,“空间资产”并非一项已经具备明确定义的法律概念。事实上,时至今日,国际社会也尚未能够就“空间资产”的具体概念内涵形成确定的统一意见。对此,应当认识到,“空间资产”概念的提出及其持续演变的过程,实则正是从一个侧面客观反映了国际社会基于商业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对作为开展商业航天活动的重要载体和进行社会金融资本融资的基本对象的“空间资产”的认识和理解的不断进步。
作为现行外层空间国际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定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各项联合国外层空间国际条约并未对“空间资产”有所提及,而是一致使用了“空间物体”(Space Object)这一与“空间资产”具有一定对应关系的概念。其中,1972年《外空物体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④“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Space Objects”, adopted b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 its resolution 2777(XXVI), opened for signature on 29 March 1972, entered into force on 1 September 1972.和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⑤“Convention on Registratio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 adopted b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 its resolution 3235 (XXIX),opened for signature on 14 January 1975, entered into force on 15 September 1976.还特别明确了所谓“空间物体”的范畴,即应当包括空间物体及其组成部分,以及用以发射空间物体的载具和载具的组成部分。⑥“The term ‘space object’ includes component parts of a space object as well as its launch vehicle and parts thereof.” See the “Liability Convention” , Article 1 (d), and the “Registration Convention”, Artide(b).不过,针对“空间物体”概念的确切定义,上述外层空间国际条约则未予以明确。
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制定国际公约的方式试图消除世界各国之间在开展国际融资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障碍,并为解决可能产生的相应法律争端提供可以统一适用的国际规则。基于这一趋势,统一国际私法协会(UNIDROIT)于1989年启动了据以专门规范和调整航空器、铁路机车和空间资产等三类具有较高成本投入需要和经济价值,且具有显著跨界性的移动设备的国际融资活动的国际公约研究和起草,并最终制定了《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开普敦公约》)及三项议定书——《航空器设备特定问题议定书》《铁路机车车辆特定问题议定书》《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①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the Cape Town Convention), signed at Cape Town on 16 November 2001.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 in Mobile Equipment on Matters Specific to Space Assets (The Space Protocol), signed in Berlin on 9 March 2012.
基于《开普敦公约》第2条第3款第(3)项的规定,“空间资产”(Space Asset)的概念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被正式提出。而根据《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第1条第2款(k)项的规定,空间资产是指,太空中或旨在发射进入太空的任何唯一可识别的人造资产,包括航天器、可能需要单独登记的有效载荷(无论其功能和用途),以及可能需要单独登记的航天器或有效载荷的一部分和所有相关的数据、手册、记录。②“Space asset means any man-made uniquely identifiable asset in space or designed to be launched into space, and comprising……” Article 1.2 (k),The Space Protocol.不过,虽然上述《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的规定对空间资产的概念作出了较为明确的释义,但由于《议定书》本身关于空间资产国际融资的多项规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要来自人造卫星制造商和运营商的强烈抵制③“Comments and Proposals Submitt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pac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Communities”,UNIDROIT 2010 C. G. E./ Space Pr./4/W. P. 4 rev.,并且,多数发达航天国家政府也始终未能积极、充分地参与到对《议定书》相关规则的讨论和制定中④“Interim Report on the Criteria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ace Assets to Be Employed in the Preliminary Draft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on Matter Specific to Space Assets”, UNIDROIT 2009 C. G. E./ Space Pr./3/W. P. 7 rev., Annex I.,因此,《议定书》对空间资产的概念所作的释义还远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
事实上,《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关于空间资产概念的规定本身的确立过程也经历了相当的周折。1997年,统一国际私法协会即邀请商业航天法律领域专家Peter D. Nesgos领衔成立工作组,负责《议定书》文本的起草工作;而2001年《议定书》草案的最初版本则正是由该工作组完成拟定的。⑤“Preliminary Draft Protocol on Matters Specific to Space Property”, April 2001, UNIDROIT 2001 Study LXIIJ- Doc. 6.值得注意的是,《议定书》草案最初同样并未使用“空间资产”的概念,而是代之以“空间财产”(Space Property)这一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表明了草案起草者希望将尽可能多的“财产”纳入可予进行国际融资的对象范畴的立场——既包括已经处于太空或将被发射进入太空的物体,也包括用以发射或回收空间物体的运载工具;既包括在地球表面制造的物体,也包括直接在太空进行生产和组装的物体;既包括完整的空间物体整体,也包括空间物体中“可独立确定的”组成部分;既包括“空间财产”本身,也包括基于“空间财产”衍生出的其他收益。⑥Article 1.2 (f), “Preliminary Draft Protocol on Matters Specific to Space Property”, April 2001, UNIDROIT 2001 Study LXIIJ- Doc. 6.
针对上述《议定书》草案,统一国际私法协会于2003年至2010年间先后召开了四次大会,并就空间资产的概念等特定问题多次召开专门性会议,由世界各国政府与航天业界(主要为人造卫星制造商和运营商)、金融界、学界代表共同进行讨论和修订,取得了以“空间资产”概念取代“空间财产”概念①“Report prepared by the UNIDROIT Secretariat to the UNIDROIT Committee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Draft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on Matters Specific to Space Assets”, First Session, 15-19 December 2003,UNIDROIT 2004 C. G. E./ Space Pr./1/Report rev., Appendix III.、制定新的可选文本作为据以进一步讨论确定《议定书》正式文本的基础等阶段性成果②“Alternative Text of the Preliminary Draft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on Matters Specific to Space Assets”, UNIDROIT 2010 C. G. E./ Space Pr./4/W. P. 4 rev.。不过,《议定书》(包括其草案的多个版本)关于空间资产概念的规定虽几经修订,但却仍然无法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造卫星产业界的一致认可,尤其是其中的空间资产衍生收益问题、有效载荷的概念界定问题,以及发射/运载工具与正在生产、制造、组装过程中的空间物体的认定问题等,始终存在较大的争议。③参见夏春利:《论空间资产特定问题的法律框架——〈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草案的进展、争议焦点及前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二)空间资产的基本特征
根据上述《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关于空间资产的概念及其国际融资活动的规定,并结合国际学界和航天业界针对《议定书》相关规定发表的观点和意见,笔者认为,虽然确立一项能够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空间资产的概念定义在目前看来难以实现,但作为国际融资活动客体的空间资产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却相对更加清晰和确定。
首先,空间资产应当是人造物,而不包括频轨资源和天体矿物资源等太空自然资源。当然,倘若太空自然资源经人为改造、加工转化成为其他物体或物质,那么则也可以被视为人造物。④See Mark J. Sundahl, The Cape Town Convention: its application to space assets and relation to the Law of Outer Space,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3, pp. 35.其次,空间资产应当是以应用于太空活动为目的的,既包括已经处于太空的物体,也包括已经完成制造并将会被发射进入太空(可能处于地面仓储、运往发射途中、位于发射台上准备进行发射的各个阶段)的物体。⑤See supra note④.再次,空间资产应当具备可识别性。这是因为但凡交易活动的标的物都应当是特定物而非种类物,所以,作为(国际)融资活动的标的物的空间资产应当是根据相应标准而被特定的。⑥根据《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第7条第1款的规定,对空间资产的描述如包含以下内容的,则应当认为空间资产具备可识别性,具体包括:项目的描述;类型的描述;对协议包含了目前和未来全部空间资产的声明;对协议包含了除特定项目或类型外的目前和未来全部空间资产的声明。不过,上述《议定书》关于空间资产识别标准(所应具备的描述内容)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模糊,并无法在实践中具体指导对空间资产的识别。最后,空间资产应当具备被用以进行(国际)融资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特征又可以细分为三项具体内容:其一,空间资产应当是可予单独登记的,因为一件无法单独登记的附属物显然无法满足独立作为(国际)融资活动标的物的前提条件;其二,空间资产应当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这是《开普敦公约》及其议定书本身专门适用于高价值移动设备国际融资活动的立法旨意使然;其三,空间资产应当具备被用以进行(国际)融资的现实需要和实践可行性。倘若一件物体因为法律政策或经济市场等其他客观原因而不得或不适宜被用以进行(国际)融资,那么从根本上便没有将其作为空间资产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即便是在尚无法就所谓“空间资产”的概念作出精确的、并且能够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界定的情况下,也至少应能对其内涵达成以下初步理解:首先,除下文将阐释的特殊内容外,空间资产应当从属于空间物体的范畴;其次,在此基础上,空间资产应当是具备可识别性以及被用以进行(国际)融资的现实需要和实践可行性的空间物体。由此,针对“空间资产”与“空间物体”在概念内涵上的关联与差异,还应当尝试进行进一步的明确界分——一方面,“空间资产”与“空间物体”的共性在于,两者均应为经人为生产、制造或改造、加工的人造物体,均包括完整的物体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以及用以发射或回收物体的运载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资产”与“空间物体”的差异又在于,首先,如前所述,“空间资产”应当具备(国际)融资的价值和意义,而“空间物体”则无需满足应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得以被用以进行(国际)融资的内涵要求,这就使得例如失效的空间物体,以及空间物体因自然解体或碰撞、爆炸等原因所产生的空间碎片无法构成“空间资产”;其次,“空间物体”侧重强调得以被用以开展航天活动的功能,其范畴应限于已经处于太空的物体,以及已经完成制造并即将被发射进入太空的物体,而“空间资产”则侧重强调得以被用以进行(国际)融资的功能,这就使得与上述物体相关的数据、手册、记录,以及正在制造过程中的上述物体,倘若具备(国际)融资的价值和意义且同时符合“空间资产”的其他特征要求,那么,即便不属于“空间物体”的范畴,也应当构成“空间资产”。①参见郑派:《论〈开普敦公约〉项下的空间资产概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三、空间资产融资的特殊性及其主要法律问题
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发展,融资作为各类经济主体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资金筹集或贷放的一种主要经济手段,在实践中已相当常见且成熟。而空间资产融资最为突出的特殊性则源自作为融资对象的空间资产本身,以及基于这一特殊的融资对象而形成的特殊的利益风险和法律关系。
(一)作为融资对象的空间资产的范畴问题
就作为融资对象的空间资产而言,在欠缺精确的、能够为业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概念定义的情况下,一项具体的空间物体能否成为被用以进行融资的空间资产往往会引发较大的分歧。在此,列举几项争议较为集中的问题并做简要阐释。
就尚在制造或组装过程中的空间物体能否成为空间资产这一问题,由于在针对空间资产的融资担保实践中,空间资产的所有权往往直到空间资产完成制造、组装并经过入轨测试从而被正式发射进入太空之后方才转移至债务人,而尚在制造或组装过程中的空间物体(实际为空间物体的零部件或辅助系统)的所有权并不向债务人发生转移,并无法独立地成为融资担保的标的物(也正是因为此,严格意义上,在制造或组装期间,根本不存在担保标的物)②“Report of UNIDROIT Committee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Draft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on Matter Specific to Space Assets: Sub-Committee to Examine Certain Aspect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Space Assets”, UNIDROIT 2009 C. G. E./ Space Pr./3/W. P. 7 rev., Annex III, II.,因此不具备被用以进行融资的实践可行性。
就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发射工具(主要为运载火箭)能否成为空间资产这一问题,由于世界各主要航天国家的国内立法鉴于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涉密性,往往会对本国航天发射技术的对外传播予以相当严格的限制,使得实践中得以被交易的通常仅限于依靠发射工具提供的航天发射服务,而不包括发射工具本身①“Report of UNIDROIT Committee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Draft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on Matter Specific to Space Assets: Sub-Committee to Examine Certain Aspect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Space Assets”, UNIDROIT 2009 C. G. E./ Space Pr./3/W. P. 7 rev., Annex III, II.,因此,对于无法进行交易和转让的航天发射工具相应地也无法进行融资。
就空间站能否成为空间资产这一问题,基于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空间站建设国际合作的事实,空间站的正常运行依赖于各国提供的舱段、模块的密切配合,而其上所有权、管辖权、控制权的分配往往十分复杂,使得倘若将空间站整体作为一项空间资产,势必将引发各国关于相应权益归属的争议;倘若将空间站的各个舱段、模块分别单独作为空间资产,则又有可能对空间站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由此,将空间站作为空间资产进行融资的实践可行性明显较低。②See supra note①.
(二)空间资产融资所涉及的复杂法律关系问题
以《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的相关规定为参考,开展空间资产融资的交易方式至少包括抵押担保、所有权保留(附条件)的分期付款销售和租赁等。由此,空间资产融资法律关系也相应地至少包括基于担保协议的担保权人与担保义务人之间、基于所有权保留销售协议的附条件卖方与买方之间,以及基于租赁协议的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③参见李剑刚:《〈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中国航天》2012年第3期。,并且,上述各项法律关系中的双方主体之间以及与其他相关当事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已十分复杂。此外,根据《议定书》第27条关于公共服务救济限制的规定,空间资产融资中的债权人利益还可能与相关国家利益产生冲突。倘若在针对为公共服务目的所需的空间资产的融资活动中出现相对方违约的情形,相关国家有权对债权人寻求救济的方式、手段等加以一定限制,以满足本国公共服务目的的需要。而这就使得债权人的利益面临着相当的不确定性,甚至间接构成了“由相关国家单方面决定补偿标准的政府征用”④“Comments and Proposals Submitt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pac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Communities”,UNIDROIT 2010 C. G. E./ Space Pr./4/W. P. 4 rev.。
同时,又由于空间资产(作为空间物体)所固有的功能性和军民两用性,一方面,空间资产融资可能将引发空间资产所有权与相应频轨资源使用权之间的矛盾——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相关规则,国家对特定频轨资源享有的使用权并不得依其意愿转移至其他国家。即便一国债权人通过融资自另一国债务人处取得了空间资产的所有权,且债务人所属国也因此而不再享有空间资产所对应的频轨资源的使用权,但债权人所属国却无法基于空间资产融资而当然地取得相应频轨资源的使用权,从而可能导致空间资产所有权与相应频轨资源使用权(可能为第三方国家取得)的分离;⑤“Comments on the Alternative Text Sub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UNIDROIT 2009 C. G. E./ Space Pr./3/W. P. 13.另一方面,军民两用性的固有特征使空间资产往往与国家的国防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并使其即便完全由民营/私营实体控制运行、完全在民营/私营实体之间流转且明确设定为民用、商用目的,也仍然可能与相关国家利益产生牵连(例如,商业遥感卫星对地球表面任意目标的观测和图像、数据获取)。因此,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通常会对针对空间资产的各类经济活动予以严格的规制,甚至干预,导致在本就相当复杂的空间资产融资法律关系中,还有可能出现作为行政管理主体的国家(政府)的介入。
(三)国际法律规则与国内法律规则的适用冲突问题
诚然,截至目前,直接明确以空间资产作为标的物进行融资的国际和国内实践尚且十分有限①无论是国外私营航天企业如SpaceX,还是前文述及的国内民营航天企业如星际荣耀、蓝箭航天,其开展商业航天融资的主要手段为通过股本融资的形式取得社会金融资本,用于推动空间科技、产品、服务的研制、应用或企业经营所需的其他用途,而鲜少直接明确以一项具体的空间资产作为标的物进行融资。参见冯晨翔:《商业航天的资本困局》,《卫星与网络》2017年第4期。,并未能够形成任何通行的交易惯例,从而使得专门针对空间资产(国际)融资进行立法似是“为未来立法”。并且,部分发达航天国家和航天业界代表还提出,既有国内法律规则已经足够满足对空间资产融资活动进行法律规制的需要,而额外设立相关国际法律规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反而会对空间资产融资的顺利开展,乃至整个商业航天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妨碍。②“Letter Addressed to the UNIDROIT Secretariat by the Satellite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3 November 2009”,UNIDROIT 2010 C. G. E./ Space Pr./4/W. P. 4 rev., Annex II.
不过,虽然滞后性是法律的固有特征,但这也不意味着但凡立法活动便必须遵循“事后立法”的原则而一概地被禁止“超前立法”。事实上,倘若立法活动能够在必要且合理的限度内发挥未雨绸缪的作用,预先地为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实践制定法律规则,那么对于更加及时且充分、有效地对相关实践进行法律规制而言,无疑将更加有利。与此同时,一国国内法律规则在对以具有显著跨界性的空间资产作为标的物的(国际)融资活动进行规制时,终究会囿于立法技术水平局限或国内法的法律拘束力空间范围所限而受到较大的制约。相较之下,诸如《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等在全球范围内制定的、吸收了两大法系相关法律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的国际法律规则,将能够更好地解决因空间资产(国际)融资活动而产生的国际利益冲突,并为世界各国制定或修改本国相关国内法,以及提升国内法的立法技术水平提供借鉴和启示。③参见张稚萍、邹娅:《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的立法意义》,《中国航天》2012年第2期。
是故,国际和国内法律规则同时适用于对空间资产(国际)融资活动的规范和调整本身是切实可行的,而因为两套平行的法律规则同时适用而可能引发的法律冲突问题,则在进行相应法律制度构建时着重予以关注和处置。
除了国际法律规则与国内法律规则的适用冲突问题之外,对于同样均作为国际法律规则的《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与现行外层空间国际条约体系中的若干相关规定之间的协调也应予以高度关注。根据《议定书》第35条的规定,对《议定书》的适用不得影响基于联合国框架下的现行外层空间国际条约的规定所确立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尽管《议定书》并未就可能产生的适用冲突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但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学界均普遍认为,作为规范和调整国际外空活动(航天活动)的基本法的现行外层空间国际条约相关规定应当优先于作为空间资产融资领域特别法的《议定书》予以适用。④“Position Paper Submitted by the National Space Agency of Ukraine”, UNIDROIT 2009 C. G. E./ Space Pr./ 3/ W. P. 18.不过,制定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现行外层空间国际条约终究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使得其在新兴的商业航天和空间资产融资领域中的适用难免会导致不合情理的结果。例如,根据1972年《责任公约》第2条、第3条的规定,作为空间资产发射国的债权人在将空间资产所有权转移至债务人之后,仍需承担空间资产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又如,根据1967年《外空条约》①“Treaty on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Use of Outer Space, including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its resolution 2222 (XXI), opened for signature on 27 January 1967, entered into force on 10 October 1967.第8条和1975年《登记公约》第1条的规定,仅作为空间资产发射国的债权人得以作为空间资产的登记国,并由此享有空间资产的管辖权和控制权,而债务人即便在实际取得空间资产的所有权之后,也仍然因为并非空间资产的登记国而至少在应然层面无法取得空间资产的管辖权和控制权。由此可见,倘若在不进行适当协调的情况下,一味地坚持现行外层空间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当然地优先于《议定书》适用,无疑将对空间资产融资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债权人、债务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明晰造成极大的困扰。
四、中国空间资产融资法律规则制定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在一系列国家层面利好政策的推动下②国务院于2014年11月1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防科工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编制,并经国务院同意于2015年10月26日印发的《国家民用空间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等国家政策文件均对商业航天产业发展、乃至商业航天投资予以了明确支持。,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已进入“快车道”。国家航天企业与民营航天企业各依其特色和专长,在商业航天领域积极作为。同时,与商业航天产业如火如荼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商业航天投资在2016年下半年即迎来了首个“黄金时期”,并在经历了短暂市场调整之后,始终保持着持续上升的热度,刺激商业航天企业对社会金融资本的吸引力不断提升。③除前文述及的国家航天企业和民营航天企业外在商业航天投融资中取得的成绩外,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所属单位共同出资成立的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3月17日完成了26.32亿元的新一轮融资,创造了行业单笔融资额的最高记录。由此,尽管在目前已有的中国商业航天投资的相关经验中,尚未大量出现直接明确以空间资产作为标的物进行融资的实践,但如前所述,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先就空间资产融资这一未来极有可能普遍发生的实践,构想据以对其进行规范和调整的法律规则,无疑十分必要。基于此,目前就中国空间资产融资法律规则的制定而言,其应当符合若干必需的基本要求。
(一)有关法律规则应与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客观现实相适应
国内业界一直不乏观点认为,所谓“商业航天”与“航天商业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仅依照市场化模式成立的民营(私营)航天企业根据市场化规则开展围绕商业航天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航天”④参见操秀英、刘雨菲:《对商业航天意义和发展道路的再认识》,《卫星与网络》2018年第7期。。对此,应当认识到:如前所述,基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全局的部署和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的需要,由国家航天企业作为主要实施主体承担开展商业航天活动的主要职能的“航天商业化”,方才符合当前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所应具备的本质特征。并且,就当前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看,无论是服务于国家政府和军队的航天项目,还是纯粹民用、商用的航天项目,其仍然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政府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并在此前提下鼓励社会金融资本投资,以及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为参与星箭制造和卫星应用等航天业务领域的民营航天企业提供扶持。①参见《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第24条规定。这与美、欧等世界其他发达航天国家的商业航天产业运作模式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正应当坚持走符合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客观实际的、“自力更生”的道路,不需要、也不应当照搬或模仿他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既有实践。
基于上述认识,依托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而形成的空间资产融资实践的开展,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则的制定,同样应当符合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所处的“航天商业化”阶段的特征要求。具体而言,对于国家航天企业和民营航天企业为开展商业航天活动而进行的空间资产融资,有关法律规则均应予以规范和调整,并根据上述两类实施主体在商业航天产业发展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发挥的不同功能,以及对于社会金融资本的实际需求(包括资金金额、需资用途、收益目标)等方面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分别制定相应的具体内容:针对国家航天企业开展的空间资产融资活动,应当重在保障社会金融资本为国家航天企业实现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促进国家航天企业顺应市场变化以调整和完善产业链;而针对民营航天企业开展的空间资产融资活动,则应当重在为民营航天企业自取得客户订单、获得社会金融资本投资,至完成客户订单、取得盈利创收、满足投资回报要求的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设计尽可能周详的行为准则和操作办法。②参见蒋圣力:《中国商业航天投资的实践与问题简析》,《国际太空》2019年第7期。
(二)有关法律规则应对国内外空间资产融资活动的规制予以不同侧重
针对本国主体相互之间开展的国内空间资产融资活动和与外国主体开展的涉外空间资产融资活动,有关法律规则在明确作为融资标的物的空间资产的范围以及采取的融资手段等重要细节时,在立法技术上应当给予不同的侧重。
针对前者,作为兼及航天法和金融法的综合性特别法,有关法律规则应当注意与国内现行相关法律规范(包括航天法领域的既有法律规范,如《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金融法领域涉及投融资问题的法律规范)以及正在立法进程中的《航天法》协调、配套,尤其应当在确保与其中作为上位法的法律规范不相冲突的前提下,制定进一步的具体规则内容。
针对后者,有关法律规则一方面应当注意涉外空间资产融资活动对国家在航天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由此应特别与国家关于航天产品、技术出口管制以及涉外金融监管的法律规范相适应,另一方面则还应注意规避或解决与相关外国国家立法可能产生的法律冲突,以及有效应对和处置外国国家立法基于空间资产的来源地、实施主体的所在地、发射服务的行为发生地、相关协议的缔结地、融资款项的支付地等因素可能对涉外空间资产融资活动的监管产生的影响。③参见《空间资产融资:您应知晓的6件事》,https://www.chinalawinsight.com/2020/07/articles/finance/,2021年7月9日访问。
(三)有关法律规则可以审慎地借鉴国际法律规则的有益成分
自2003年起,中国便委派代表参加了统一国际私法协会专门就《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召开的5次政府专家委员会会议,以及2012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就《议定书》草案文本进行审议的外交会议,积极表达了中国国家政府和航天业界针对《议定书》及其相关问题的立场和意见,由此表明了对《议定书》这一关于空间资产融资活动的重要国际法法律规则的重视。虽然《议定书》目前尚未正式生效,且对中国生效的《开普敦公约》针对移动设备(动产)融资交易所确立的制度安排和具体规则又与中国现行相关法律规范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动产担保权利的成立、登记、法律效力、优先顺位和执行等方面的差异尤为突出,但《公约》及《议定书》中仍有值得在制定中国空间资产融资法律规则的过程中予以审慎借鉴的有益成分。例如,基于空间资产融资国际利益的非占有物权属性而创新设立的国际利益登记制度、优先权制度和违约救济制度,对于促进消除空间资产融资中债权人利益的不确定性便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①See Lutfiie Ametova, “International Interest in Space Assets under the Cape Town Convention, Acta Astronautica”, 92 Acta Astronautica 2,213(2013).
根据《开普敦公约》第7条的规定,所谓“国际利益”,可以被理解为移动设备之上因(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书面形式达成的)合意而产生的、具备担保债务履行的功能的物权,涵盖了基于担保合同而产生的担保物权、基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而产生的物权,以及基于租赁合同而产生的物权。②参见高圣平:《中国融资租赁法制;权利再造与制度重塑——以〈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为参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据此,具体及于空间资产融资国际利益,其即是指作为债权人的担保合同中的担保权人、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以及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在可识别的空间资产之上所享有的各项利益。
在确立空间资产融资国际利益的基础上,《开普敦公约》和《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还创设了多项侧重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制度,包括:国际利益登记制度,即债权人根据《公约》和《议定书》的相关规定,通过向国际登记机构进行利益登记并公示,使任何第三人查询了解特定空间资产之上的利益状况;国际利益优先权制度,即在先登记的国际利益优先于在后登记的或未登记的利益,且有效设立的国际利益一经登记便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在先登记的国际利益主张优先受偿的权利;违约救济制度,即在债务人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作为债权人的担保权人、(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的)卖方和出租人均享有特定的救济途径。此外,《公约》和《议定书》还规定了最终裁决前的救济、破产救济等救济措施。以上各项围绕空间资产融资国际利益创设的重要制度,为债权人利益提供了一套较为周全、完备的保护机制,有利于增强债权人开展空间资产融资活动的信心,降低融资成本,且同时使债务人(商业航天活动的实施主体)也能够基于融资取得更大的惠益,从而促进整个空间资产融资活动的稳定和有序开展。③参见李剑刚:《〈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中国航天》2012年第3期。
此外,又因为空间资产融资国际利益本身是直接基于《公约》和《议定书》的相关规定而确立的“国际(法)上所承认的物权”,具有自发性,使得对其的取得既不来源于、也不依赖于国内法的规定,所以,至少从应然的层面看,空间资产融资国际利益及其各项重要制度与中国现行相关国内法律规则不存在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冲突。④参见孙建华:《〈开普敦公约〉中的国际利益问题研究》,《武大国际法评论》2016年第19卷第2期。有鉴于此,在充分考量《公约》及《议定书》对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和空间资产融资实践开展可能产生的各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基于维护中国在航天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需要,有关法律规则确实可以通过审慎地借鉴上述国际法律规则的有益成分,将其转化成为完善中国动产融资法律制度,制定中国空间资产融资法律规则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