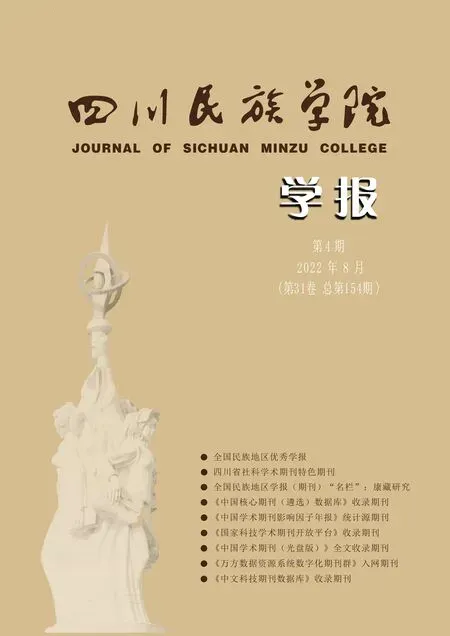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二元互动关系
2022-02-04郭浩地
郭浩地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互动与渗透,促进了整个法学学科的发展。但在当今学界,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性质并没有清晰定论,尤其是法理学的内涵与外延始终模糊不清,法理学的意义与作用始终不被重视,且法理学与各部门法学的关系也始终处于割裂状态,具体表现为法理学与政治伦理、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走得更近,而距离各部门法学较远。但事实上,法理学作为各部门法学的凝练,始终在反哺着各部门法学的知识系统,部门法学因为其固有的实践面向,又不断从实践中汲取养分,不断将实践性质的知识向法理学输送。理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是法学学科体系融贯化与结构优化的根本性要义要求,也是对法理学的性质与重大历史使命的重新定义,再次突显了法理学作为各部门法学的统领性学科的不可或缺性。意欲厘清法理学与各部门法学的关系,需要明晓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概念与范畴,抓住其根本区分点——是否超越或拘束于制定法文本,并通览西方法理学学术史,才能逐步探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
一、什么是法理学与法哲学
法理学的英文称呼为Jurisprudence,法哲学的英文称呼为The Philosophy of Law。前者指法的一般理论,该概念多应用于英美法系国家,后者指“法的哲学”,该概念多应用于大陆法系国家。考夫曼认为:“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1]法哲学本质上应当是一门哲学学问。按照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理论,所谓哲学就是哲学思想史,是哲学思想史文本。从古希腊哲学、经院哲学到古典哲学,再到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共同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体系与骨架。笔者认为,法哲学与哲学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赞同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将哲学视为哲学思想史,将法哲学视为法哲学思想史。哲学思想史与法哲学思想史经典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均是某一种社会思潮的合流,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学与法哲学思想流派、思想家。但法哲学与哲学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充斥着法制度、法实践与法文化的因素,而后者更倾向于哲学思辨与玄思。法哲学思想史涵盖三个主要流派,分析实证主义、自然法学流派以及法社会学流派。其中分析实证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将法律本身作为一个封闭的客观实在体系,代表人物从边沁、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到拉兹;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必然联系,法律与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息息相关,“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2]113,代表人物从奥古斯丁(经院自然法哲学)、霍布斯(古典自然法哲学)等到现代的富勒、菲尼斯等;法社会学派将法律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将法律看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而非仅仅局限于成文法本身,代表人物有埃利希、卢曼以及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本文简明地回眸法哲学的思想流派与思想史,赞同法哲学即是法哲学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法哲学思想史——的观点。如果说成文法文本构成了法教义学的骨架,那么法哲学思想史文本则构成了法哲学的骨架。
至于法理学,其内涵与外延较之于法哲学则更为广义,故被称为“法的一般理论”。法理学在包括法哲学的同时还包括法政治学、法伦理学、法经济学等在内的多重维度。譬如,在我国,法理学还包含了中国古典礼法制度、“本土资源论”[3]、中国本土法家思想[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等多样现实与理论维度。在学科体系上,法理学(学科命名为法学理论),应当作为法哲学方向(也可被非官方地称作“三级学科”)的上位学科,其内含了法哲学,但在学术范式上又与法哲学迥异:法哲学类同于哲学范式,强调对思想史经典文本的研究,而法理学的范式则相对多元。从本体论意义上看,法理学与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居于制定法文本之上,其思维与研究范式难以受任何制定法文本的拘束,是纯粹地超越法律并回望法律,其终极目的便是解决什么是法律以及法律存在的应然性问题。例如,奥斯丁将法律定义为以制裁为保障的主权者的命令;[6]凯尔森则将法律定义为“人的行为的一种秩序”[7]29,并将这样的秩序定义为多重层级的规范系;美国大法官格雷则将法律定义为“一门探讨法院应然判案原则的科学”[8]292;布兰代斯则认为在制定法文本与法官造法之外还存在一套独立的“living law”(活法);[8]312拉德布鲁赫则将法律定义为法律理念服务的法律事实。因此,法理学与法哲学不受制定法文本的拘束,具有较强的想象自由性,对于法律的解释既可以来自成文立法本身,也可以来自作者个人的学术传统与学术想象。
从方法论意义上看,法理学是法学方法论的上位学科,法学方法论为各部门法教义学的适用提供了判准,统领、指导着各部门法学的开展。法学方法论偏重各部门法学的适用、运行技术,法哲学则偏重思想文本,二者之间相对独立,但都是构成法理学体系的重要部分。
故而,本文认为,所谓狭义层面的法理学,即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论的相加;所谓广义层面的法理学,则是在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论基础之上,包含法文化、法经济学、法人类学等在内的,具有文化、政治与历史特征的浩渺体系。
二、什么是部门法学
本文所指称的部门法学,即各部门法教义学,国内留德学者通常称法教义学,[9]而留日学者通常称法解释学,但二者都基本表达了相近意思:即围绕成文法的建构、解释与加工活动。[10]部门法学除了法教义学,还有部门法哲学——是部门法教义学成果、理论与实践的抽象,但在理论体系性方面相较于法理学还难以望其项背。部门法哲学中发展最好的当属刑法哲学,刑法是直面人性之恶、悲天下人之悲、关涉人的底线价值的学问,其部门法哲学理论具有极致性、深邃性、形而上学性、悲怆性。由于各部门法哲学发展的不均衡性、未成体系性与不饱满性,本文暂不对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的关系做过多探讨,主要立足于法理学与部门法教义学的关系。关于法教义学,雷磊精辟地比喻道:“如果我们将整个法教义学体系想象成一个瓶子的话,那么实在法就好比装入瓶中的石子,而其余的空间则被沙子所填满,这就是未被实在法化的教义学部分。”[11]简而言之,法教义学是对成文法进行加工、建构、解释所形成的规范、封闭、金字塔化、理性的理论体系,主要立足于制定法文本,但又轻微地超越实定法。“法教义学的对象被明确为现行实在法,成为围绕现行实在法展开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12]
在民法法系国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中国,各部门法教义学均具有金字塔般的概念体系,形成了逻辑自洽的教义学系统。譬如,刑法教义学是从总论到分论、从人到行为的一整套完善体系;民法教义学是从民事主体、物法、债法、人格权法、家事法、侵权责任法等构成的自洽体系(比如物权能够统领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商法是从商行为到商主体的一整套完备理论体系;各程序法教义学是依托于诉讼程序所构成的解释序列。在体系构造上,法教义学类似于自然科学结构,依赖于人的理性从上位概念推导出下位概念,甚至从上位概念中发现、构造出下位概念——萨维尼的占有理论便是其一,并通过合理的解释手段来保证整个概念金字塔的逻辑自洽(尤同于科学中从公理推导出定理)。所以西方法学界自“莱布尼兹-沃尔夫”的理性体系以来,存在法学是否是科学的论争。基尔希曼否认法学的科学性[13],拉伦茨则赞同法律的科学性[14]。可以窥见,各部门法学并非各部门成文立法文本,而是围绕成文立法,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解释手段,人为建构、解释、加工、塑造而成的理论体系。在欧陆世界,这样的理论体系还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
在我国,无论争论几何,各部门法教义学的阐释对象不只局限于制定法文本本身,还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在内的多元法源。本文在此暂不对其法源地位作过多探讨。受制于中国法治进路的“建构理性主义”特点与强大的未经国家力量解构的大量民间交往规范,我国的立法采取了“立法保留”模式。成文法在市民社会的贯通、在司法领域的实现,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以此来避免解释恣意与司法任性。本文暂不过多讨论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地位,但本文认为,它们与制定法文本一道,同时包括法规与规章在内,是中国大陆地区各部门法教义学的解释、建构对象,是教义学瓶中的“石子”。
就法教义学的建设成果来看,作为承袭民法法系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典的解释依赖于学理层面。“大陆法系成文法的解释工作主要通过法学教授的法律评注和教科书编撰工作来完成,法学家的著述也就成为法官在理解和适用法律中的重要参考资料。”[15]131各部门法教义学的承载、表达对象就是广大法科学生日常接触到的教材,包括通说教材与大教科书在内。通说教材通常有高教版红皮,人大版蓝皮,法律出版社版黄皮以及各政法院校自编教材。“大教科书”则是具有研究意义的学者个人著述,往往价值立场更为鲜明,譬如朱庆育《民法总论》、程啸《侵权责任法》等,成了具有诠释意义与整全性特征的重要一手材料。教材体系是教义学解释体系的系统建构,各部门法学的学术文章则构成了法教义学体系的分层建构,是在已有体系上的增添、删减、修正与改善。
总体看来,所谓法哲学,即法哲学思想史文本;所谓法理学,即内含了法哲学与方法论的关于法的多元化的一般原理命题;所谓部门法学,即各部门法教义学。法理学与各部门法学区分的关键在于制定法文本在英美法系也应该包含法官造法,二者的勾连节点同样在于制定法文本,制定法文本区分了二者的同时又将二者紧密连接。法理学与法哲学是能够超越制定法文本的理论体系,能够在制定法文本之内外自由穿梭、跳跃,而各部门法教义学则几乎是拘束于制定法文本之内,其体系建构不可能全然抛弃制定法文本而单独开展。是否受制于制定法文本拘束、能否超越制定法文本,是法理学与各部门法教义学的本质、关键区分。此外,各部门法教义学与法理学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还表达为二者之间的深刻而广泛的二元互动,深刻体现出人类文明史与制度史的辉煌图景。
三、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特点与联系
第一,法理学与法哲学具有形而上学性、宏大叙事性、极致性,各部门法学则具有具体性、微观可视性、可操作性。法理学忧虑的是人类的整体命运,承担的是人类进步事业的宏大使命,拷问的是“什么是法”以及“法将往何处去”这样的本源性命题。法理学具有高度的深刻性、强烈的使命感以及宏大的历史叙事性。如富勒的“事业论”[2]113,菲尼斯的七个“人类善理论”[16],伯尔曼的宗教与法律的二元合一论(伯尔曼的核心观点即“宗教的法律化与法律的宗教化”,主张法律与宗教的二元融合,但又并非政教合一)[17],德富林的“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18],均表达出了对于人类命运、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刻忧思。法哲学,尤其是自然法学派理论,敢于超越历史叙事的桎梏,回溯人类的制度文明史,深切忧思着人类整体的前进步伐。伯尔曼自1050年的教皇革命起,回眸西方法律史近千年,用四十年的时间著成《法律与革命》,对“脱神祛魅”后的后现代世界表达出了深刻忧虑,并希冀通过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合一来剔除自19世纪末开始盛行的“虚无主义”,重新塑造“价值主义”。拉德布鲁赫在二战后目睹了生灵涂炭,修正了自己的“休谟原则”——“应然”只能从“应然”中得到,“实然”只能从“实然”中得到。拉德布鲁赫依照二元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否认命题”与“不能容忍”命题。他认为,“除非实证法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作为‘不正当法’的法律则必须向正义让步。”“在所有正义从未被诉求的地方,在所有实证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否认构成正义之核心之平等的地方,法律不仅是‘不正当法’,而且尤其缺乏法律本性。”拉氏公式以“不能容忍命题”“否认命题”在保证法安定性的前提下提出了对于实定法的否认理论,[19]并在后世的“柏林墙射手案”“怨毒告密者难题案”中得到应用,[20]修正了实定法文本的僵化性与非正义性。
法理学的超越性、思想自由性、思考极限性能够为人类的前行方向提供指引,引导各部门法学的完善与自净。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学界,同样会发现相应的影子。在20世纪末,我国法学界存在“义务先定论”[21]与“权利先定论”[22]、法治与人治、本土资源论与法教义学论之争,这些争论对之后二十余年的部门法走向与司法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权利先定论为国家保障国民自由与权利奠定了基础;法治优位于人治论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理论保障;本土资源论使我国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大调解”实践。本文持法教义学的立场,主张以人的理性为主导的“建构理性主义”,注重实定法的安定性、权威性、实效性,反对盲目的“本土资源理论”,但并不否认“本土资源理论”在节约诉讼资源、加快解决纠纷方面的积极意义。海内外法学界均有相似情况:看似抽象的理论争议会通过具体的司法实践表现出来,司法、国民交往实践所遇见的问题又会上升为理论争议点。
而各部门法学则能够在现行法体系之下实现定分止争,解决现实纠纷,保证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保证法体系自身的安定性。支撑社会良好运作,维持安定秩序的是各部门法学而非法理学,具体执行抽象价值的也是部门法学,法理学的抽象意义通过具体司法实践来得以表达和实现。譬如,人权价值在刑诉法领域能够表现为“无罪推定”原则,自由价值在私法领域能够表现为“法无禁止即可行”,作为部门法学的抽象价值又进一步通过各部门法教义学与司法实践来表现。博登海默认为,法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与正义,各部门法学的重大使命就是通过其教义学体系来保证国家与社会秩序,使社会的各部分如同法的概念体系一般有序运转,使人的精神得到安守。人本能地具有需求秩序的心理根源,“人类神经系统在节省能量与减少紧张方面的需要,解释了人对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见取向。”[23]在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各部门法学无疑是排头的、重要的。
第二,法理学在哲学、伦理与思想方面牵引着各部门法学的发展,各部门法学反作用于法理学的发展。笔者赞同拉德布鲁赫的三大法理念论,即将法的安定性放在法理念的首位,只有当其根本违反正义直觉的时候,方能适用“否认命题”,故本文没有使用惯常的“指导”而使用“牵引”一词来描述法理学对于部门法学的积极意义。法理学对于各部门法教义学的作用只能是较为缓慢地渗透、影响,故而雷磊认为,法理学与各部门法教义学的三重关系只能居留于各部门法哲学之间,因为二者大体处于理论之抽象层面。[24]18但本文认为,法哲学与各部门法教义学是能够沟通的,只是这样的沟通是长时间的、缓慢的,故本文使用“牵引”一词。依照雷磊的提法,法理学与各部门法教义学确实不在一个层面。譬如,在外部证成方面,法理学能够轻易证立大前提,却不能够轻易否定大前提,对于大前提的否定必定是长时的、缓慢的、经过多方论证的。在任何国家,成文法文本都是刚性的权威,如同引力,牵引着法理学理论的恣意逃逸,法理学本身也形同引力,牵引着制定法文本的改善。法理学对部门法的牵引是缓慢的、长时的、多元的,需要较长的过程才能改变部门法的立法现状。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提到善良违法理论,认为公民有权基于宗教、信仰以及成文法的非正义性而选择不遵守国家法律。[25]该理论针对的是当时许多美国青年因越战的非正义性与其他原因而拒服兵役的情况,其知名代表人物是拳击手穆罕穆德·阿里。阿里于1967年拒绝服役而被判处5年徒刑(未服刑)与三年半禁赛,直到1971年才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这其中有赖于美国法学界就“善良违法”理论的呼声,也有赖于美国自身对其战争非正义性质的反思。“善良违法”理论正式进入并适用于司法领域(在美国主要是判例),就阿里个人都长达四年之久,而且这还是在美国从越南仓促撤退的背景之下。由此可见,法理学对于部门法学的修正、贯通是一个浸润式的牵引过程,这种牵引不能够立马改变部门法,但可以在长时间的过程中改善部门法的发展,促进人类制度的向善。19世纪末,出现以普赫塔以及潘德克顿法学派为代表的概念法学派,主张编撰具有金字塔结构的法典体系,该思潮促成了《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的诞生,并在19世纪末奠定了现代法典的雏形,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长达百余年。20世纪初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为法律的彻底祛魅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凝聚力的提升与世俗法的成长。20世纪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德沃金的权利理论均主张不得依照“大多数的人的善的总量增加”而否认个体权利与自由,不得因为多数人的利益而任意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后现代西方世界的福利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因此,作为法哲学轴心的思想史文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部门法学的改变与发展,这样的影响虽然是缓慢的、浸润的,但也是根本的、长远的。此外,各部门法学在其实践中也能够不断反作用于法理学。[24]4譬如,对于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拷问,最早来自西欧各地区的法典编撰,形成了类似从公理到定理的逻辑结构。法律层级与效力规范之间的冲突,最早表现在中世纪欧洲的多元立法时期,经过后世的理论演绎与归纳,最终形成了凯尔森的层级规范理论[7]193-243。
第三,法理学在方法论领域内统领、指导部门法学,各部门法学又修正、改善法学方法论。法理学所统领的实践于部门法教义学的法学方法论,在经年累月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专一化学说。就法律规则而言,主要思维模式有三段论涵摄模式与图尔敏模式,目前,三段论模式是通行模式。就三段论推理模式来看,大前提的确立要求寻找具体规则而非抽象规则,并尽可能寻找具有针对性的裁判规则。[16]131作为小前提之一的法律事实由生活事实上升而来,能够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应受到证明规则规制;作为小前提之二的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的行为;作为小前提之三的法律关系,是指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15]132-135而后是大前提与小前提的连接,通过“目光在案件与事实之间的往返流连”确定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得出相应的法律效果。[15]219-226现行法律解释方法一般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当然解释、反面解释、目的解释、限缩解释、扩张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合宪性解释。[15]361-465在“作为最佳化”命题的原则领域,则适用权衡模式,即两个法律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取舍原则。比如在“泸州二奶案”就会产生私法自治与公序良俗原则之间的取舍。其具体操作方式是“重力公式”,即在原则的受侵害程度与相冲突原则的满足的重要性程度之间取商。[26]主流法学方法论作为指导性原则贯通适用于所有部门法学,部门法学所遇见的难题又会反过来促进法学方法论体系的完善。除了我国主流的法学方法论,其他法学方法论也在指导着各部门法教义学的开展、完善。譬如,暂不具有主流地位的“图尔敏”模式,其推理过程是经由data,经过warrants、backing到(modal qualifiers)conclusion的过程。[27]可见,法理学下辖的方法论具有高度的统领性与指导性,指导着部门法学的司法适用。除此以外,法学方法论还具有规范相关官方文本法源地位的能力,比如,法学方法论能够证立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的地位的作用,使各部门法能够形成自洽的逻辑体系。[28]
就部门法学在方法论领域对于法理学的修正作用而言,现当代的原则权衡理论最早源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实践,在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体系化和精致化的原则权衡理论”[25]7。部门法学的方法理论能够抽象为适用于所有部门法学的一般化理论,而法理学层面的法学方法论有能为所有部门法学提供统一化的指引,形成法学领域的刚性、统一性理论体系。
四、法理学的不可或缺性
人类社会已经具有了依靠人的理性设计出的各部门法教义学,能够为芜杂繁复的人类社会提供秩序与判准,其制度设计的精巧程度足以媲美自然的造物,没有法理学的世界同样会运行流畅。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法理学呢?这看似不经意的一问实质上反映出人类虽甘愿服从制定法文本,但又对人造的法律始终抱有的怀疑与警惕,对于正义的“普罗透斯式”的面孔怀有不安与惊悸,追求不为人造之物所永恒拘束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实定的法律是暂时的产物,是利益衡量的副产品,难以成为永恒的真理。假如没有法理学的加入,人类将会把制定法文本奉若神明,永恒地拘束于实定法文本之下。因为有了法理学的深邃,人类自古希腊以来便始终思考着文明与个体的价值,不断探求着正义的本来面目;因为有了法理学的自由,人类的法律从宏大的叙事历史中看,是不断变动的、前进的,而不单一是“权威的命题”,真正成为一项有目的的事业。[2]169法理学解决的抽象问题、理论问题,但却是每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方向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决定全球人类的命运。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以哈耶克为领军人物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即一种积极、冒进的自由主义,也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甚至主张“政治去中心化”。[29]由于80年代后国际形势对于英美的向好,新自由主义为英国与美国带来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度经济繁荣。但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政治去中心化”的制度困境,英美首当其冲,在新冠疫情期间导致百余万人死亡。与哈耶克理论相异的是卡尔·波兰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0]主张保守的自由市场经济,该理论后来为中国理论界借鉴、消化、吸收、运用,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具备经济繁荣的同时,中国具有更高的政治稳定性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政治后盾,从而使得华夏民族能够安然渡劫。
法理学类同于理学,部门法学更类似于工学。[31]理学解决的是世界的构成问题,是认识世界的问题,工学解决的是改造世界的问题。人类文明的前进依赖的是基础理学理论的进步,法治事业的彰显同样依赖于法学基础理论的进步与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