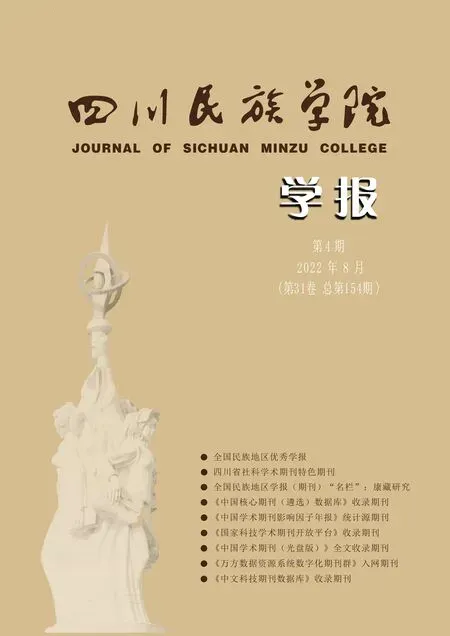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及演化路径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2022-09-22胡易雷程遂营程卫进
胡易雷 程遂营 程卫进
(①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②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③桂林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发展民族村寨旅游是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乡村振兴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1]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省份相继对民族文化村寨进行开发,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拉开序幕。[2]于是,在“合理利用民族村寨、古村古寨,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旅游小镇,建设一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3]的背景下,民族村寨旅游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民族村寨不仅仅有特定环境、独特的特点所赋予的民族文化内涵,并且是立足在少数民族的原住地、移居地或在原住地基础上改建或扩建的村寨。[4]具备旅游的基本要素,是民族文化旅游最好的物质载体。[5]随着国内旅游的发展,民族村寨旅游日益得到消费者认可,已然成为我国民族旅游的一种独特形式。[6]
民族村寨旅游是以民族村寨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村寨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与生活、享受乡野田园风光为动机,融观赏、考察、体验、度假、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活动。[7]尽管已有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进行了综述,但是这些研究在时间范围上较为有限,没有纳入近几年涌现的大量文献,并且在研究内容方面局限于对研究阶段和主题的浅显探讨,缺乏对民族村寨旅游多维视角的分析。鉴于此,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基础,借助CiteSpace软件,采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法,对1993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间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及演化路径三个层面总结和归纳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进展和趋势,以期为后续学者的创新性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高级检索模式下,以“民族村寨旅游”为主题,对1993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间的文献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出相关文献1300多篇,其中期刊文献917篇,硕士论文170篇,博士论文19篇。为更好地得到有效数据,剔除了英文扩展、报道、重复文献以及其他无效文献,共得到1106篇有效文献作为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的数据来源。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一款由陈超美教授及其团队研发的一款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能够有效地反映特定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等情况。本文主要选用CiteSpace 软件V.5.8R2(64bit)版本,对已筛选的1106篇文献进行处理,生成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相应知识图谱。在CiteSpace的实际运用过程中,Time Slicing参数设置为1993-2022年,时间切片为1年,将Node Types分别设置为Keyword。
二、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现状
(一)研究文献年份分布
整体而言,国内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见图1)。从期刊文献来看,2005年之前,国内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超过3篇。在2005年至2016年期间,发文量快速增长,而在2016年以后研究文献数量有所下降,但年均发文量仍然在60篇以上(不包括2022年1月份)。从硕博文献来看,2004年以前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硕士论文处于空白状态,并且在2004年至2010年间,收录于中国知网(CNKI)的硕士论文不高于5篇,2011年之后的硕士论文年均11篇以上,到2019年达到了26篇。而与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有关的博士论文最早收录时间在2007年,自2012年起每年至少有1篇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博士论文。总体上,这些研究文献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阶段性明显,学术性不断加深,研究案例地较为集中,且省际高校之间存在着交流与合作;二是各高校对民族村寨旅游关注明显,主要体现在对民族村寨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图1 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文献年份分布
(二)核心作者与合作分析
利用CiteSpace软件生成可视化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见图2),该图中作者节点N共有483个,说明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研究学者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其中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19,意味着研究者之间合作交流较少,很多研究学者处在孤立研究的状态。而连接线E有217条,表示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在这些合作的作者中,以殷红梅、陈志永、吴忠军、吴建国等为主的合作最为突出,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为贵州师范学院的陈志永,共发文20篇,其次是殷红梅(19篇)、吴忠军(13篇)、吴建国(9篇)等,这些作者的发文量均在9篇及以上。进一步分析得出,这4名作者所隶属的机构皆隶属西南地区高校,且存在着交流与合作,但主要在其所属高校内部单位进行,而不同地区高校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较少,尚未形成跨校际的学术团队。

图2 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三)核心机构与分布特征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运算得出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3),研究机构节点N共有393个,连接线E共有3条,网络密度Density为0,说明在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机构众多,但是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并不紧密,仅有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图3中机构名字的大小与其发文量多少息息相关,其中节点最大的为贵州师范大学,这表示其发文量最多,自1993年以来共发了68篇,然后依次是桂林理工大学(62篇)、凯里学院(49篇)、西南民族大学(47篇)、中南民族大学(39篇)等等。进一步分析发现,从事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机构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并且区域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较少,尚未形成高凝聚力、跨地区、跨学校的合作交流群体。

图3 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机构网络图谱
(四)多视角下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得益于多学科的参与,才致使其研究主题逐渐丰富,研究层次逐渐呈现多元化。总的来看,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主要呈现以下视角。
1.旅游学视角
从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演变历程来看,早期的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内容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基础性探讨。如金颖若讨论了贵州民族文化村寨旅游发展问题。[8]罗永常从参与性发展理念和社会性的旅游发展等层面,探讨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对策。[9]江晓云以临桂东宅江瑶寨为例,对少数民族村寨生态旅游开发进行了初步研究。[10]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在旅游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展开,为旅游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历探索期后,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主题和内容开始多元化,衍化出更多的旅游研究视角,如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旅游品牌建构、民族文化保护、旅游发展模式、旅游扶贫、乡村振兴等。其中陈志永介绍了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11]吴忠军等提出旅游发展的经济收入影响居民对开发旅游的态度。[12]简王华认为民族村寨应树立主体品牌意识,培育民族文化旅游品牌。[13]肖琼对民族旅游社区文化生态环境困境成因及其保护机制作了探讨。[14]黄亮等针对西双版纳傣族园提出了“公司+农户”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模式。[15]辛纪元等指出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链接现行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强调要突出扶贫部门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战略中的地位。[16]曾韬等基于手段—目标链理论构建分析了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引导乡村振兴的路径。[17]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旅游发展中的实时需求,理清了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思路。
2.民族学视角
从民族学角度进行的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是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需求。其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民族村寨民俗文化、风俗习惯、婚姻家庭等方面。例如,张欢深入挖掘民族村寨文化内涵,提出不同民族村寨有不同民俗文化,要针对不同民族村寨文化进行旅游规划、打造特色旅游品牌。[18]常丽娟客观分析了民族节日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认为传统体育的开发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促进旅游发展。[19]徐燕等认为语言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建筑文化、精神文化影响不同阶段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不同民族村寨应该选择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20]巴丹以少数民族箐口哈尼族民俗村为案例地,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在没有得到村民认可下,利用当地“寨神信仰”和“神林崇拜”进行旅游开发,刺激了当地村民以巫术活动的形式表达不满。[21]总之,在民族学理论指导下,学者们对民族村寨旅游进行了积极探索,寻求民族文化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以更好地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村寨文化保护。
3.社会学视角
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社会学研究,学者们紧紧围绕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社会阶级、社会分层、社会问题等展开,分析其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进而分析民族村寨内、外的群体如何生存发展,彼此互动为旅游带来的影响。例如,王旭旭基于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文化变迁等,揭示了民族村寨在社会治理结构、经济结构和观念体系等各个方面逐步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22]史梦薇发现镇山村社会阶层主要分化成旅游管理者阶层、旅游服务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外出打工者阶层,阶层利益两极化差距较大,不利于旅游发展。[23]胡家境基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提出社会认同、精英信任、契约信任和人情信任是民族村寨自组织治理顺利运行的有力保障。[24]
4.人类学视角
人类学研究主题基本覆盖了民族村寨社区家庭、生计变迁、生计模式、精英阶层、文化认同、婚姻状况等内容。如尚前浪认为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和资本进入会造成旅游开发地社区和家庭生计发生变迁。[25]孙九霞从生计方式变迁角度分析其对民族旅游村寨自然环境的影响。[26]殷红梅等探析了西江苗寨“生计模式”和“生活支出”两个经济要素,发现该地生计模式呈现“外出务工与农耕混合—外出务工—旅游生计”的规律,经济支出呈现由村寨核心区向村寨边缘区递减的规律。[27]吴其付从人类学视角探索了村寨社会精英成长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旅游发展的影响。[28]王伯承等以贵州省郎德上寨为例,探讨了民族村寨旅游对婚姻家庭习俗变迁的影响。[29]总之,民族村寨旅游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围绕民族村寨的生活生计进行,进一步衍生出精英阶层、文化认同、婚姻状况等研究主题,并讨论这些主题与旅游发展的相互关系,为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不断开辟出新的视角。
5.法学视角
从法学视角对民族村寨旅游进行研究的成果也颇为丰富,包括民族村寨内部主体保障与旅游客体的法律保障,对民族村寨旅游法规、章程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各方社会主体助力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提供了保障。如方勖平认为少数民族村寨相关政策落实情况,需要借助法学相关理论,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村规民约保护体系。[30]曹务坤发现旅游扶贫法律机制尚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民族村寨民事主体、财产、金融等法律制度。[31]而卢丽娟从法治视角发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扶贫监管制度存在缺陷,完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扶贫开发监管制度尤为重要。[32]
三、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往往是文章的凝练部分,能够很好地反映文章所代表的研究领域,分析其研究的结构状况、发展进程、互动和衍生关系,有助于把握当下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前沿热点等。在CiteSpace的实际操作中,将网络节点设置为“key words”,阈值设定为(15,5,104)、(15,5,30)、(10,5,25),对1106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依据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选取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14个,绘制出关键词共现可视化视图,能够清晰地看到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文献关键词聚合、辐射情况、反映主题,以及研究热度等(见图4)。

图4 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关键词共现可视化视图
在图4中,网络节点N=567个,网络连线E=1171条,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73,说明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主题比较集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关键词可视化视图研究内容,根据关键词共现频次、中心性(当关键词中心性数值≥0.1时,被认为是高中心性关键词,热度比较高),以及首次出现年份等,选取排名前十的高频热点词(频次在25以上)(见表1)。关键词频次大小、中心性高低常常被用来反映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中心性往往能够反映节点在关键词网络结构的重要程度,中心性越大传递出的信息和作用越突出。

表1 民族村寨旅游研究高频关键词及中心性(频次>25)
第一,“民族村寨”出现的频次,达到了364次,中心性为0.87,在排名前十的关键词中最高,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节点。与“民族村寨”等同的关键词为“少数民族村寨”,也具有较高的出现频次(62)和中心性(0.11)。这与本文以“民族村寨旅游”为检索词具有直接关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选择具体的民族村寨进行案例研究是当前盛行的研究方式。
第二, “旅游开发”位居第二,其出现的频次为115次,中心性为0.19,是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重点领域,“旅游”与“旅游业”可归为一类。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研究的文献整体上阐释民族旅游开发的理论问题,以及描述某一民族区域的旅游开发现状、路径与策略等。
第三, 以“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为关键词的文献基本上属于同一主题的研究,前者出现的频次为58,中心性为0.14;后者出现的频次为38,中心性为0.06。此类主题的文章主要探讨如何促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以及其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的重要意义。例如,薛承鑫等提出了“DSIAS营销模型”[33],并阐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刘红梅指出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能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34]
第四, “旅游扶贫”和“社区参与”是一对关联性较强的关键词,二者出现的频次分别为51、41,中心性分别为0.04、0.03。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核心在于推动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和促进社区参与,因此“旅游扶贫”和“社区参与”也成了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前沿热点。与“旅游扶贫”相关的研究重点关注旅游扶贫效应、监管制度、法律保障、冲突与治理、实施路径等问题。而与“社区参与”相关的研究则侧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特征及内涵、内生动力、利益保障机制、困境及治理路径等话题。
第五, 关键词“民族文化”出现的频次为35,中心性为0.05,也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例如,李欣华等剖析了贵州郎德苗寨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成功实践。[35]吕宁兴等讨论了贫困地区民族村寨的整体性文化保护困境与振兴发展策略。[36]
总之,上述关键词具有较高的出现频次和中心性,说明这些方向在关键词聚类视图(图4)是关键节点,辐射程度较大,属于民族村寨旅游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
四、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演化路径
分析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领域的演化路径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这个领域研究的总体脉络和发展方向。因此,利用CiteSpace 的Timeline和Timezone功能对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文献进行研究路径分析,得出研究演化路径时间线图(见图5、图6)。

图6 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演化路径的Timezone视图
基于文献年度分布情况和演化路径时间线图等信息,对文献进一步梳理和分析,发现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步探索阶段(1993-2004年)、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1年)以及深入拓展阶段(2012年至今)。
(一)初步探索阶段(1993-2004年)
此阶段全民旅游需求量不大,旅游发展规模较小,研究层次也比较低。民族村寨旅游总体上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旅游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全国上下逐步发展民族村寨旅游以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在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基于旅游产业所带来的效益,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尝试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这一时期民族村寨旅游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基本上在“摸着石头过河”。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特点:关注度不高、研究主题单一、研究成果较少,以初探性的基础研究为主。
(二)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1年)
在Timeline(图5)和Timezone(图6)视图中,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关键词明显增多,辐射面广,主要是得益于民族村寨旅游前期研究成果,为后进学者提供了借鉴和研究方向。该阶段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基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实践需要。一方面,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过程中新的冲突与矛盾不断凸显,亟待调节和处理,使得多元视角介入,跨学科交流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对民族村寨旅游的认识不足和对现有理论的漠视和背离,需要多学科之间互相交叉和相互论证,以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发展。
(三)深入拓展阶段(2012至今)
随着信息时代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还是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国内旅游需求巨大,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入了繁盛时期,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日益兴盛。尤其在2012年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迅速,文献数量众多,研究成果丰富(见图1)。在2012年至2020年之间,国家先后发布《关于促进旅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关于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这些方针政策为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指明了方向。于是一些学者逐步将视角转向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将其与国家政策结合,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提出有效的建议。同时,在跨学科理论指导下,对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内容不断丰富,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持续深入。
五、结论和展望
首先,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与积淀,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形成了以陈志永、殷红梅等为代表的研究作者团体和以西南地区高校为引领的研究机构群体;其二,随着跨学科研究视角的不断介入,有效地刺激了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纵深发展,并提供了相关理论基础;其三,出现了旅游开发、旅游扶贫、社区参与、民族文化、乡村振兴等热点主题,为后续的民族村寨旅游学者提供了参考方向。
其次,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不同阶段的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主题和内容不断拓展、丰富。从单一理论视角的后劲不足到跨学科多元理论结合的欣欣向荣,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成果斐然,更加贴近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实践需要,不同阶段的实时政策与多学科理论视角,为民族村寨旅游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驱动力。
再次,自1993年以来,尽管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成果突出,但依旧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研究局限。一是研究机构和研究区域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中西部高等院校和民族地区,且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缺乏深度的交流与合作;二是研究内容缺乏创新,已形成一定的“范式”,多数研究者的研究主体和内容出现套用话题,以不同地区为案例点进行同质化研究,使得选题、内容的重复较大;三是旅游研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成果稀少,描述性成果颇多,导致旅游研究特色还不鲜明。总之,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在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下,需要更多更新的理论成果,为深化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结合上文分析,对未来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供学界参考。
(一)拓展“虚拟现实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民族村寨旅游研究
近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产业遭受了巨大打击,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现代信息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对民族村寨旅游进行整合、储存、传播、记录,对现实进行虚拟,旅游者不用到达旅游目的地便可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短视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呈现途径之一,能有效地给旅游者带来视觉、听觉上的另类感受。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9.34亿,占网民整体的90.5%,[37]这为“虚拟现实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奠定基础。近些年,伴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从传统场域到新兴场域的变迁,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着巨大变化。[38]可见,“短视频”在互联网上成了传播人们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不仅给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带来机遇,也为民族村寨旅游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如何利用好“虚拟现实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应对当前新冠疫情维护和宣传好民族村寨旅游形象,是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发展实践。
(二)加强机构合作,不断创新研究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村寨旅游迅速发展,相关研究成果也呈爆发式增长,研究主题和内容日趋多元化,但仍需在机构合作和研究方向创新等层面进一步加强。一要积极“走出去”,进一步强化不同区域间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形成稳定的跨区域的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共同体夯实基础。二要大力“引进来”。一方面要适时举办与民族村寨旅游有关的高端学术论坛,邀请其他研究机构的学者前来研讨交流,加强联系;另一方面,在开展民族村寨旅游相关学术研究和项目工程时,邀请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加入研究队伍,主动与其他研究机构共享学术研究资料和数据库,合作撰写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等。三要树立创新意识,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创新研究方向,推动新时代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纵深化发展,突破同质化的研究困境。
(三)聚焦研究主题,深化多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旅游研究
目前,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基本实现多学科交叉,但是多数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没有及时结合时事对子系统进行实证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学者们对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主题长期泛化,没有形成稳扎稳打的“扎根式”研究局面,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也难以指导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实践。并且多数研究无法“以小见大”,停在表面,没有切实把握民族村寨旅游需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因此,要鼓励和引导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其研究领域稳稳扎根,对民族村寨旅游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研究结构,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四)把握研究趋势,注重民族村寨旅游实证研究
从关键词聚类视图可以看出,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乡村振兴、旅游者、保护、民族文化等是未来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趋势。因此研究者要关注研究趋势,结合实时政策不断拓宽研究范围。如电子商务、智慧旅游、女性权利、全域旅游等主题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拓展。尤其是民族村寨旅游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应对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挑战。此外,如果一个领域长期缺乏实证研究会逐渐脱离实际,使得学术研究失去现实基础,难以深入发展。因此,研究者要注重实证研究,更好地为民族村寨旅游提供智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