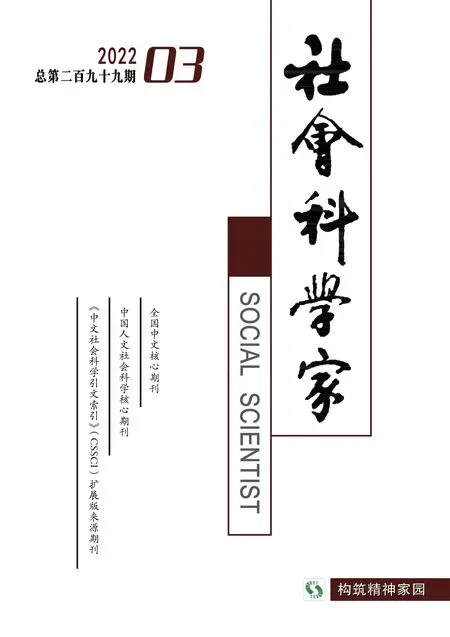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苗怀明教授访谈
2022-02-03苗怀明王先勇
苗怀明,王先勇
苗怀明(1968-),河南平舆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创办人兼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先后出版《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风起红楼》《吴梅评传》《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等学术论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及随笔等数百篇,其中《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被评为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著作。
王先勇(以下简称“王”):苗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苗怀明(以下简称“苗”):我的求学经历比较简单,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都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完成的,然后在1999年到南京大学做了2年博士后。我基本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我的学校教育。如果我们把20世纪的学人分成几代的话,我应该属于第5代学人。这一代学人的特点是,接受过完整的、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我的整个求学经历中,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没能在多所学校就读。我认为比较完整的教育,应该是本科、硕士、博士3个阶段的学习在不同的学校完成。
当然我的整个受教育过程都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度过,也是有好处的,那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在一所学校,我对于北师大的学术传统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在我的求学过程中,对我学术帮助最大的就是我的导师张俊先生,我的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都是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张老师做学问的特点是特别注重文献,注重实证研究。我个人治学受张老师的影响比较大。
王:您认为不同的教育阶段应该选择在不同的学校完成,这应该是为什么您会让自己的硕士报考其他学校读博士的原因吧?
苗:是的。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每个学校的学风也都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学校求学,可以转益多师。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在,所以我带的硕士研究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跟我读博士的,我会让他们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去接受不同学术风格的熏陶。
王:您的研究历程是从小说开始的,您在小说研究领域也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请您谈一谈小说研究的体会。
苗:小说应该算是我接受硕士、博士教育阶段学习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实,我的专业方向完整的名称应该是元明清文学,当时我的导师张俊先生就提醒:“你的专业不仅仅限于小说,而是元明清文学。”但是因为导师张俊先生主要研究小说,尤其是研究《红楼梦》,所以他给我们上课,对我们的学术训练,小说部分的讲授比较多一些。因此张老师的学生,我和我的师兄弟们大部分也就都做小说研究了。
就我个人而言,小说研究是我学校教育以及“出道”以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从1999年博士毕业,到现在,也有20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做小说研究,没有间断过。当然,中间在有的阶段研究重点也会有所变化,比如我到南京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重点就转向了戏曲,最近这些年重点又转移到说唱,但是我对小说的研究并没有停止过。小说研究的体会,我个人感觉是越来越难。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小说方面的研究,取得的进展非常大。研究进展大了也就意味着小说研究,当然不限于小说,已经走入了一个瓶颈期,要想取得突破就会越来越难,小说研究的门槛越来越高。
王:您的小说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这些经典名著,而这些作品研究者众多,研究的角度广,研究程度也很深,对于入门的研究者,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您认为还能再以这些名著作为研究对象吗?可以的话,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研究呢?
苗: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来说学术界差不多思考了20多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郭英德先生,曾经在1999年第2期《文学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他当时就提出这个问题。这些名著,比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研究者多,关注这些名著的,许多都是重量级的学者。那么,他们对于名著中的问题,无论是文献方面,还是文学、文化方面,都有很多开掘。现在要想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或者取得突破,变得非常之困难。“不悬置名著,就无法打破传统的英雄史观和等级思想,彻底更新明清小说史写作的历史观念;就无法摆脱观念的束缚和先验的模式,直接面对明清时期活生生的小说史现象;就无法真正衡定名著在小说史上的价值。”因此郭英德先生就提出,中国古代的小说有三四千部,与其在这有限的几部名著方面原地踏步,再重复劳动,不如把精力用在研究二三流小说,或者研究其他更多的小说作品。但对于郭老师的观点,还是有争议的。因为作为一个硕士生、博士生,对于这些名著,不能不下功夫,我认为这是研究入门的一项基本功。作为一名研究古代小说博士生,你如果对《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没有精深的了解,显然是不合格的。
对待研究名著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对于这些名著,研究还是要慎重,如果说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比如没有新的文献发现,比如文本研读得不是更精细的话,那就会在很多方面重复前辈研究者的劳动成果。但是,如果愿意下更大的功夫的话,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做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儒林外史》,这部小说过去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但是最近十几年来,《儒林外史》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很大程度上跟发现《儒林外史》的新材料有关。比如从清代人的文集中发现了关于《儒林外史》的记载,这就给我们研究《儒林外史》带来新的研究空间。再比如说《聊斋志异》,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些名著的研究,我认为第一要慎重,第二还是可以研究的。这种研究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看有没有新的文献发现;第二个要看有没有新的研究角度,比如说现在研究《西游记》《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研究其翻译,其跨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另外研究小说名著,我们还可以研究其插图,研究图文关系,这都是过去研究当中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因此,如果有新的视角,拓展了新的领域,我觉得还是可以研究的,但与其他的小说研究相比,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如果下定决心要研究名著,那么就要做好花更多的时间,下更大工夫的心理准备。
王:根据您论著的发表时间,发现您在求学阶段主要是以小说研究为主,博士后阶段却转向戏曲研究,那么在博士后阶段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研究转向的呢?
苗:戏曲研究确实是我博士后期间的一个转向。因为1999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了南京大学跟随俞为民先生进行博士后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俞为民先生主要研究的是戏曲。虽然我可以继续做小说,但当时转向戏曲研究,主要考虑到几个因素。
首先,我个人认为单纯研究小说的话,研究领域太过狭窄。通俗文学研究领域,我们知道主要包括小说、戏曲和说唱,其中很多问题,如果仅仅是研究小说是不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在做小说研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对戏曲、说唱予以重视了,只是当时没有专门的机会。来南大跟随俞为民老师读博士后,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转向。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缺少跨视野的探索。当时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太窄。比如小说研究中,研究文言小说的不研究白话小说,研究《三国演义》的不研究《水浒传》。我认为这种人为的分割,使得很多学者目光变得非常狭隘。我想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再次,学者不能固守研究的“舒适区”。很多博士毕业之后,就往往吃老本,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不停地发表,然后再做相近的题目。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学者,应该是不停地转换领域,比如说在通俗文学研究内转换。这样可以做到不重复自己,而且能够完善、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每做一个新的题目,都是一个挑战。
你可以看到,我在博士论文做的是公案小说,当时已经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我如果吃老本,最起码10年、20年一直做公案小说研究也没问题。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在毕业之后,除了把博士论文出版以外,我没有写一篇关于公案小说的文章,马上转到戏曲研究。而且后面也不停地在转换,每隔几年就会转一个大致的研究方向。这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自己知识结构的完善,自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视野变得开阔之后,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与过去相比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由于读博士后的机缘,以及自己对完善知识结构的需求和对自己的要求,我从小说转向了戏曲。因为戏曲研究那么多年并没有人从学科角度对戏曲进行研究,所以我从小说转向戏曲,就有意识地做学术史,做文献的梳理工作。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就是写的《戏曲文献学述略》。通过做这项工作,我对戏曲文献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那么我再进行戏曲研究,入门就相对容易多了。其实我转向戏曲文献学研究的结果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学术界很多人最早知道我,是因为研究公案小说,但是在小说范围之外知道我的人,更多的是因为知道我研究戏曲文献学。
王:您说到了戏曲文献的研究,能具体讲一讲您戏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哪些方面吗?
苗:我关注的戏曲方面,主要跟我的学习有关,因为当时来到南京大学之后,我想将研究点转移到戏曲。转移到戏曲研究的话,虽然小说和戏曲都属于通俗文学,但实际上如果要达到专业研究的水平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刚到南京大学的时候,我很苦恼,不知道应该怎么入手,所以我在报博士后出站题目的时候想了很多,后来才慢慢找到方向。我认为从文献入手是进入一个学科的最佳方式。因为其他的学者在展开论述的时候,除了新发现的文献,大部分也是依据这些文献来研究论述。你了解掌握了这些文献之后,首先就可以掌握整个学科的“家底”。第二,你在读其他学者的著作时,就不会特别陌生,所以戏曲文献学就成为我关注的一个方向。我关注戏曲的另一个方向,主要是学术史方面,这也跟我的学习有关。既然你要了解一个学科,了解了它的基本文献,那么它的研究进展情况,即它的研究史也是必须要了解的。所以,除了戏曲基本文献,我对戏曲研究史特别关注。博士后出站之后,我写了《吴梅评传》《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这基本上属于我对戏曲史的一个研究。
当然,我的戏曲研究也有缺憾,就是对戏曲本体部分的研究不多。我对本体研究多的是小说,我认为戏曲的本体研究比小说要求更高。因为你要懂舞台,懂演出,还要懂曲律,而这方面,以我的知识结构来看,并不是特别完善,所以在研究的时候我就有意避开了。当然,我会通过多听戏,多看戏曲方面的资料来逐渐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总的来说,我个人研究戏曲重点放在戏曲文献和学术史方面,我认为每个研究者不可能是全才,只能做自己擅长的部分,我在戏曲文献和学术史上的研究比较擅长,也就主要做这两个方面了。
王:您已经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和《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我看到您在2021年又出版了《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海外学者论中华曲艺》两本新书,您是否又将研究重心转移到说唱艺术了呢?能具体谈一谈您现在的研究情况吗?
苗:最近几年我确实将研究重心又转移到说唱文学方面了,陆续发表了几篇说唱方面的文章,比如2015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中国说唱文学研究述略》、2016年发表的《欧美地区中国说唱文学文献研究述略》《宝卷文献研究述略》、2019年发表的《台湾、香港地区说唱文学文献研究述略》《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中国说唱文学研究的成就及特色》、2020年发表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欧洲地区的翻译与研究》《日本敦煌说唱文学研究的历程与特色探析》等等,2021年又出版了两部这方面的专书,即《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海外学者论中华曲艺》。
为什么要转到说唱文学研究?这也是我治学的一个转向,我差不多用了10多年的时间研究小说,又通过10多年的时间研究戏曲,那在通俗文学这一领域,我还缺一大板块,就是说唱文学。因为过去的了解都是皮毛,要想达到专业的研究,差不多也需要十年的时间。我大概从2010年就开始在硕士课程中开设了一门《说唱文学文献学》的课,通过这一方式来进入说唱的研究,最近这些年研究的精力也主要用在这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跟我研究的戏曲比较接近,也是从文献和学术史两个角度进入这个学科研究的。《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是一个体系,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说唱文学进行了梳理之后,出的一本通俗文学文献学的概论或通论性质的专著。另外一本是《海外学者论中华曲艺》,是对海外汉学界研究曲艺情况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两本书,对文献和学术史的研究之后,我应该对说唱文学达到了入门水平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打通这些方面,把小说、戏曲、说唱打通。当然,将来我也有可能会研究民歌、民间文学,再补上没有涉足的其他通俗文学作品类型。这样打通了之后,我认为对通俗文学研究才有发言权。2017年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恢复和建立视野开阔的大通俗文学观——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我个人认为,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从王国维、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赵景深这些学者开始,他们从来没有只做戏曲或只做小说。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把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纳入了一个大的俗文学观念中。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现在已经把小说、戏曲、说唱都做了分割。这些年来,我一直倡导要恢复这个学科开创之初大的俗文学的概念。我自己现在正在实践,但是确实很难,需要几十年时间的付出。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疑惑,为什么我们普遍认同第1代、第2代学者具有开创性,这是因为他们首先视野很开阔,现在研究把视野放得太过狭窄,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和成就。至少在大的俗文学观念这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反思,现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我们有专才,但是缺乏通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王:说唱艺术有很多种类,您的说唱研究主要关注哪些呢?
苗:说唱艺术,我主要关注的还是文献方面。为什么关注文献方面,前边我已经说过,一方面文献是一个学科的基础;另一方面我觉得从说唱文学学科方面来看(当然现在它还不是一门学科,还没有得到学界的承认),一个学科的建设,首先是从文献开始的,而说唱文学的文献研究还非常薄弱。到目前为止,说唱文学文献还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概念,而且也没有人来做。所以我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不是具体地研究某一说唱门类,而是涵盖所有的说唱形式。
我所做的工作,比如说有哪些重要的材料被发现,有哪些目录、索引的编制,有哪些重要作品集的整理、影印、出版,有哪些重要资料集的编纂,以及有哪些文献的研究等等。实际上等于是对整个一百多年的说唱研究情况总的梳理,这既是对之前这一领域研究的总结,也是在为一个学科的确立做基础性工作,更是为后来研究者提供线索。不然的话,许多想要进入说唱文学研究的学者根本找不到书,也不知道从何处开始看书。所以目前我做的只是个基础工作,从学科的角度,从文献的角度对说唱文学进行梳理。后面我可能会对具体的作品进行研究,对说唱史进行整理。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空间还很大,因为面对异常丰富的资料,研究者还是太少了。目前来说,还是以基础工作为主。后面的话,我可能会编纂说唱文学资料汇编,或者说唱文学研究的论文集,也可能会编一些目录,也可能会对说唱作品、说唱发展史上重要的问题做研究,但这差不多又需要10多年的时间。
王:总体来看,您的小说、戏曲、说唱研究,文献方面的研究占了很大的比重,您是怎样看待通俗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呢?您认为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异同?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苗:小说、戏曲、说唱研究,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文献学研究呢,除了这是一项入门的基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我研究的深入,我发现通俗文学的文献与经史、诗文的正统文学的文献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他们之间文献产生的背景不一样,他们存在的文献载体不一样,他们保存、流传的形式也不一样。因为通俗文学的文献都不是有意保存的,往往自生自灭,抄写的形态也比较简陋。
当然按照一般的文献学原则,比如说要编目、要整理,这与传统文献学还是相同的,但具体到细节部分,应该说现在的文献学研究对通俗文学文献的研究,没有针对性,因而也没有更多的指导性。比如我们研究经史诗文文献,我们可以找最好、最早的底本,要跟其他的版本对校,而通俗文学,我们根本找不到底本,有的时候底本的年代也根本不知道,就是一个孤本、一个抄本,也没有办法校对。再一个,校勘的原则也不一样,经史诗文方面的文献,古人改动很小,而像戏曲、说唱呢,往往文无定本,每一次演出都有不同的本子。再一个是编目录,传统经史、诗文集的目录,列出作者、版本、卷数就可以了,但是小说、戏曲、说唱等通俗文学则肯定不可以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小说、戏曲、说唱的书名完全一样,内容则不同,体裁也不一样,那怎样把他们区别开?肯定要加上故事梗概,要注明文体,甚至有的时候要将回目标明。所以说整理的原则、编目的方式都有不同,研究的情况也不一样。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要重新建立通俗文学自己的文献学。
关于通俗文学文献学的问题,过去没有人重视,对研究通俗文学的人来讲,听文献学的课基本感觉到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他们总结的文献规律对通俗文学并不完全适用。所以在完成小说、戏曲、说唱文献研究的述略之后,我会完成一部通论、概论性质的书,来总结、概括通俗文学文献的特点,就是概括它本身的特点,它哪些大的方面与经史诗文文献学有相同之处,它的个性所在是什么,而后边的它的个性所在才是重点。随着这些年的研究,我对这些问题有越来越深的体会了。
如果建立了通俗文学文献学的话,那么就会找到适合通俗文学研究的方法。因为方法都是跟着文献走的,文献不一样,方法自然也就不一样。现在比如说,通俗文学的研究方法肯定跟经史诗文研究不一样,因为经史诗文都是按照经典式的研究法,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每个人都可以研究作家、作品的个性特点,而小说、戏曲、说唱等通俗文学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往往是集体创作。作品经过多少年,师傅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孙,因此作家是谁,作品产生在什么年代,我们无从得知,甚至作品从什么地方开始流传我们也无法考证。而且这些作品本身也没有太多的个性,因为都是艺人集体创作,不像诗文作家如李白、杜甫等一样个性那么鲜明。因此如果按照研究李白、杜甫的方法来研究说唱文学作品显然是不适用的,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正是拿着研究经典式的研究法来研究说唱,所以就没办法研究。这跟什么有关呢?我们受经史诗文研究的影响特别大,没有建立适合通俗文学自身的研究方法。所以这是我要努力从事的一个方面。
王:从小说、戏曲到说唱,可以说通俗文学的三个方面您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当然,说唱艺术还有很大的空间,而其他的小说、戏曲两个方面面对现在的研究瓶颈,您认为接下来的通俗文学研究应该如何继续下去?
苗:确实如你所说,说唱的研究空间相对较大一些,中国有三百多个曲种,受到重视的除了弹词、宝卷、木鱼书之外,90%左右的曲种还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所以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但正如刚才所说,因为文献的工作没有人做,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法,所以好多人想研究而不知从何入手,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小说、戏曲的研究经过100多年学者的耕耘,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厚的学术累积,在这方面来做,门槛变得非常高。当然仍然有可研究之处,这种可研究之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要精耕细作,虽然前面的学者也研究过,但是还不够精细,可以做得更精更细,在这方面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有突破。第二是需要做得更广,因为必须比别人视野更开阔,眼界不一样可能才有新的发现。比如说我们可以打通通俗文学,把小说、戏曲、说唱放到一起,或者是跨学科,比如把通俗文学和法学结合起来,或者把通俗文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所以要视野开阔,才能做出新东西。当然这里的视野开阔既是指学科视野,也可以指地域视野,比如说将视角从中国扩展到东亚、亚洲,甚至整个世界,可以做中国小说在西方的传播,做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可以做得更深更细更广。
另外当然也需要换一种理论视角,做小说、戏曲研究,虽然我是偏重文献的,但我也强调要有理论素养。如果没有理论素养的话,就不容易发现问题,所以理论方面也不能放松。因为有了理论,就可能有了新的角度和视角,这样才会有突破。还有一点是从时间上来讲,小说、戏曲、说唱通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时代越往前越不好研究,第一材料少,第二研究的人多,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往后研究,事实上近代小说、近代戏曲已经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所以在时段选择上我认为可以往后来研究,这方面还是有空间的。
虽然小说、戏曲研究,说起来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其实不光是小说、戏曲这类的通俗文学,诗文研究一样进入了瓶颈期,比如研究李白、杜甫、苏轼,同样很难。因此,对于后来的学者来讲,要比前人付出更多的劳动。空间还是有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第二找到了空间你有没有能力去做出来。因为学术研究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知道这个题目很好,但事实上不可做,为什么呢,因为缺乏文献,没有材料,或者是个人驾驭不了。所以我觉得要能够发现问题,同时要有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
王:现在的研究生越来越多,对于准备从事通俗文学研究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呢?
苗:对于准备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我的忠告是:像练武术一样,入门一定要正。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练好童子功。我们的童子功就类似于像武术中的扎马步一样,首先对文献要重视,只有熟悉了基本的文献,你才能了解一个学科的情况,你才可以跟学者对话。第二,你要把这个学科里的经典著述都看完,了解这个学科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初学者要大量地读书,通过读经典的论著,通过读文献,对这个学科先了解,了解完之后,才有可能发现问题。在这个入门基础中,我个人认为要对重要程度排序的话,首先是作品,因为我们研究文学最重要的核心还是作品。现在的学生呢,好多人宏观地论述还可以,但一牵扯到具体作品的分析,文本细读的能力就很弱。所以针对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我觉得一定要培养文本细读的功夫。因为只有对文本细读之后,才会对作家的风格、对作品有深的理解,才会有与他人不一样的看法。否则的话,对作品读得不细,就容易人云亦云,这是年轻人比较欠缺的一个方面。总之,首先从文献和学术史入手,其次要以作品为本,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入门才正,后边的学术道路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