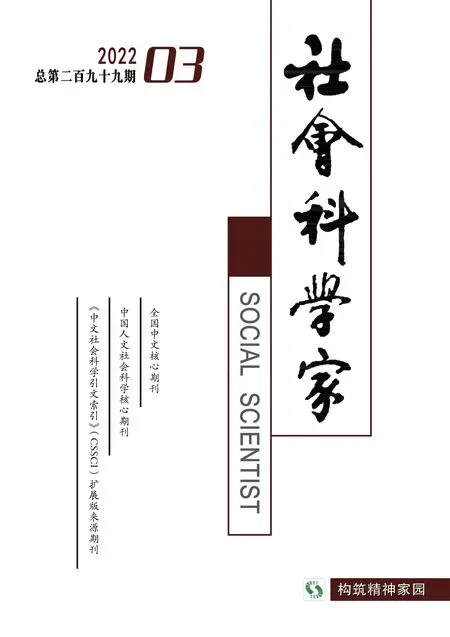四重证据法的文化科学方法论基础
2022-02-03户晓辉
户晓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近年来,文学人类学一派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但在方法论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显然,与那些陷入朴素的实证主义幻想而“对他们自己的方法甚至对他们的行动的本质缺乏认识”[1]的经验论者相比,当下的文学人类学学者们不仅具有明确的方法论革新意识和建构能力,而且试图让四重证据法能够“被成功赋予人文科学一般方法论的意义”[2]。这一派锐意创新的人文学者们充分自觉地意识到,只有具备一般方法论所应该具备的理论规定性和逻辑要求,四重证据法才有资格成为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论。为此,他们已经对该方法的学理性和证明方法(原则)的合理性做出论证。[3]本文从卡西尔的文化科学方法论立场对四重证据法的逻辑步骤加以先验还原和理论重构,进一步阐明该方法的文化科学方法论基础和一般认识论资质。
一、“文化”概念的方法论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为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中聚讼纷纭而又难以破解的种种谜题,叶舒宪提出综合研究的“三重证据法”,把中国传统的文字训诂考据看作第一重证据,把王国维揭示的出土文献看作第二重证据,把人类学、民族学的参照材料看作第三重证据。2005年,该派学者进一步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概念,将中国出土的古代文物和图像资料当作第四重证据,由此提出“四重证据法”。[4]四重证据法初看起来容易被误解为各种证据的简单叠加[3]或单纯的实证研究方法,实际上却是一种以跨学科的“文化文本”概念为基础的人文科学方法论。所谓“文化文本”是超越单纯文字典籍的大文化概念。正是基于这个概念,四重证据法才把人们以往根本想不到会发生关联的证据关联起来,才能够“从古代遗留的实物及图像中解读出文字文本没有记录的文化信息”[5]。
具体而言,四重证据中的第一、第二重证据可以称为“文字”证据,第三重证据的口传文化可以称为“语言”和民俗证据,第四重证据可以合称为“物象”证据。无论哪一重证据,都属于文化概念的范畴。文字、语言、民俗、物象等等形态各异的东西之所以能够被同时用作四重证据,恰恰因为它们都是文化的不同形式及其内容,也恰恰因为文化概念是能够统摄四重证据并且构成跨学科研究基础的核心概念。从更加宏观的层面上来看,“文化概念对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都有巨大牵引力和穿透力。文化概念提供的宏观整合性视野是文、史、哲、政、经、法等所有学科都没有也都需要的,因而自然发生了超越学科界限的新知识整合与重建过程”[6],因此,我们可以把人文科学更加具体地理解为以各种文化形式及其内容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按照卡西尔的理解,文化是产生人的历史的那些行动的总体。[7]即便摆在我们面前的四重证据看似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僵死之物,但它们都是前人的行动和精神劳作留下来的文化符号,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精神产品,它们构成的符号世界处于被两个方面的界限加以限定的领域之内:一方面处于符号的物质性(die Materialit t des Zeichens)之内,另一方面,这种物质性又是通过意义的纯粹形式性(die reine Formalit t der Bedeutung)来加以划定的。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意义的显现方式,也构成我们所谓的“文化”。[8]文化符号的意义生产不仅离不开具体的物质性,而且是由具体性体现出来的抽象性,是在个体性身上表现出来的普遍性,也是通过自然的因果关系反映出来的人文的意义关联。
文化概念之所以对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具有先验的统摄作用和奠基作用,恰恰因为文化的一切内容都不仅仅是单纯的个别内容,而是在普遍的形式原则中得以奠基,因而以人类精神的本源行动为前提条件。所以,文化概念的内容与精神创造活动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方向不能分离,而且从先验层面来看,人类的一切精神能量都具有相通甚至相同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方向。[9]这就为四重证据法对不同证据形态的跨学科和跨文化使用提供了先验理由和哲学根据。因为严格说来,卡西尔所谓的象征符号①由于卡西尔的“Symbol”概念兼具“象征”和“符号”双重含义,所以本文暂取“象征符号”的译法,以区别于“Zeichen”(符号)。关于把卡西尔的“Symbol”概念译为“象征”或“符号”的得与失,参见石福祁《“符号性孕义”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页,注释②。并非直接等于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也不直接等于四重证据法中被视为证据的各种文化文本,而是在先验层面上为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文本奠定基础并且是它们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简言之,象征符号是文化的先验基础,它既蕴含在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文本之中,又“超出”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文本。
文化作为象征符号具有两个基本的维度:感性的维度和精神(概念)的维度。[7]所以,文化科学需要同时应对象征符号的感性维度和精神(概念)维度,并在方法论层面处理好由这两个维度产生的感性与精神、特殊与普遍、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能否恰当地应对和处理这些关系,是判断四重证据法是否具有人文科学一般方法论基础的客观依据。
二、四重证据法如何化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方法论矛盾
进而言之,由于作为象征符号的“文化”与作为有机物的“自然”的存在方式根本不同,所以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在基础和方法论等方面也就存在着根本差异,这些根本差异相应地决定了以文化文本的象征符号为研究对象的四重证据法所具有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特质。
首先,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文化的存在(das Sein der Kultur)不同于有机物的存在(das organische Sein),文化的变化不具有纯粹植物式的特征,文化不是从现成的胚胎中生长出来并且静谧地开放出来的东西,而是借助于个体能动的造型意志(Gestaltwillen)产生出来的东西,这种造型意志只有使用现成的种种形式才能把这些形式本身再次当作材料来加工。[10]正如李凯尔特形象地比喻的那样,“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根据这一点,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11]。文化虽然不是从自然自身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却是由人的精神产生的东西,是由于人的精神、为了人的精神而产生并保存下来的东西。自然物的本原在于自身,而文化物的本原却不在自身,而在于创造出文化物的人,所以文化物才先验地具有“象征符号的孕义”(symbolische Pr gnanz),因而不仅仅需要因果关系方面的解释,更需要理解和阐释。文化的存在取决于文化自身不断创造出新的物体,文化最终就是它从自身当中摆放出来的文物整体(das Ganze der Monumente),这些文物并非有形的物体,而是仿佛记录着发生事件并且有待抢救的记忆符号。但这种抢救的成功途径并非让人逆时间之流而动,而是一再沉入时间之流,从常新的个别行为中赢得某种不会消失的东西。文化的持存就仅仅在于文化自身的这种塑造活动和改造活动当中。[10]
其次,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这些不同对象的感知方式有所不同。自然知识的基础是“感官知觉”(Sinneswahrnehmung),文化科学的基础则是“表达知觉”(Ausdruckswahrnehmung)。所谓“表达”就是一种承受(Erleiden),是在感动之时的被感动(Ergriffenwerden),因而“表达知觉”就是一种由情绪(Affekt)规定的知觉方式,在这种知觉方式中,知觉主体并不作为主体与被知觉的东西保持距离,而是在情感上觉得受到被知觉东西的感动。[7]这就至少从两个方面决定了文化科学的知识性质:一方面,文化科学的知识离不开人的主观情感;另一方面,文化科学的这种带有主观情感的知识需要具有一种能够普遍传达和共同分享的交互主观性才能成为一种客观的知识。也就是说,虽然“表达知觉”与“感官知觉”的划分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类型意义上的本质区分,但这种本质区分决定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需要以不同的路径来达到各自的客观性。自然科学追求规律的统一性和存在极(Seins-Polen),对个别现象进行分类并把这些分类放到特定的规律之下;文化科学追求活动极(T tigkeits-Polen),它直观到的首先是既不断变化又具有恒定性的象征符号及其形式。文化科学需要在这些形式的变化和持存中来把握和理解它们的意义和内容。文化科学就像一个圆周,要停留在同一个平面之内,同时又不断向外蔓延和扩展。文化科学研究者追求的客观性是精神的现象及其形式的总体,而对这个总体的直观总是把自我保持为圆周的中心点。自我扩散到大量的形式中去并由此为自己赢得新的、普遍的广度,但自我并不在这种广度中迷失自己,否则就会毁掉作为文化符号的客体本身。[12]这也就相应地决定了文化科学对符号客体的认识和理解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或交互主体的关系,因为所谓符号客体不过是他人精神活动的结晶和结果,因而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它”,而是以物化形式体现出来的“你”,对符号客体的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就是一种“我与你”的对话关系,而不仅仅是“我与它”的认识关系。更确切地说,在这种认识和理解中,“我与它”的认识关系要服务于、服从于“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正因如此,这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对话性阐释在四重证据法中的方法论基础地位。
再次,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知觉与概念的联结方式有所不同。既然对文化的理解和认知离不开人的主观性,那么,一方面,对文化的经验认识所具有的规定性和客观性就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处于变化之中,也就是一种可规定性(Bestimmbarkeit)[13];另一方面,对文化的经验认识的这种可规定性又不能停留在单纯个人的主观性上,而是需要具有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和逻辑性,由此使这种经验认识成为普遍可传达的有效知识与科学知识,而不至于沦为主观猜测和臆断。这就需要文化科学在通过知觉与概念的联结而形成知识时具有相应的方法论。我们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重要关系方面考察四重证据法是否具备文化科学方法论所应该具有的学理性与科学性:
第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从先验哲学的层面来看,文化科学是一种关乎人类精神生活赖以发生的种种形式的学说。这种形式的逻辑内容所孜孜以求的既不是自然科学的规律概念,也不是史学的事件概念。因为即便掌握了一切普遍的规律,即便把事件的全部结果的一次性个别进程尽收眼底,我们在所有这些东西上面仍然不能对文化的基本形式达至任何理解。[10]抽象地说,这些形式的恒定性与可变性、持续性和不断变化构成文化科学的中心主题。文化科学的一般任务就是赢得越来越丰富和越来越细致分化的形式概念和风格概念的整体。[10]卡西尔的这种先验的形式理论为文化科学的方法论以及四重证据法奠定了哲学基础。然而,四重证据法不仅涉及文化形式,还要涉及文化内容。文化形式是一种普遍东西,文化内容则是一种特殊东西,二者共同构成具体的文化象征符号。所谓的四重证据都是以这种形式加内容的方式构成的象征符号,因而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四重证据法并非盲目地增加证据,也没有被各种各样的内容所限,而是从内容的变化中看出不变的和恒定的形式,并且在形式的引导下直观到内容的文化含义。在这方面,该方法的重要特征和主要目的恰恰是在整体形式的引导之下寻求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因果证据和意义证据。
第二,自然科学的因果证据和文化科学的意义证据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四重证据都是由人创造和生产的文化形式及其内容,四重证据法恰恰试图寻求这些文化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意义关联,只不过从性质上来看,其中虽然也有自然的因果关系,但更重要和更本质的是人为它们赋予的意义关联、目的关联和价值关联。也就是说,该方法所使用的证据,既非单纯的人文科学证据,也非单纯的自然科学证据,正如叶舒宪所指出,人文学科的“证据”与自然学科的“证据”之间的区别在于四重证据法的证据“仍然带有一定的阐释性,观点与论据之间更多的还是一种阐释性关联(explanatory connection)”[14]。该方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释’,四重证据彼此形成交叉观照,发挥出整体证明效力,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中聚讼不已的无解、难解之题,提供了重破译、再阐释的可能”[2]。由此可见,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让自然科学证据服从于人文科学证据的文化科学证据,它“把实证研究当作一种诠释手段”[15],其中的因果关系方面的证据不仅是为了意义诠释服务的,而且是围绕着意义诠释而展开的。
第三,特殊现象与普遍概念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因果证据的解释和意义证据的诠释都涉及现象的特殊性与概念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堪称四重证据法在方法论上的最大亮点。一切文化劳作都是在其一般形式中呈现出来的,只有通过沉浸到经验材料中去才能找到这种形式,而且只有在某种历史的形式中才能让我们接近这一点。[16]四重证据法主要面对和解释的历史现象恰恰不是完全特殊的、一次性的文化形式及其内容,而是反复出现的、历经变化却相对稳定的文化形式及其内容。该方法的实践者对特殊现象与普遍概念的辩证关系的处理方式恰好符合卡西尔提出的那条认识的基本原则(das Grundprinzip der Erkenntnis),即“普遍东西始终只有在特殊东西中才得到直观,特殊东西始终只有在普遍东西的视野中才得到思考”(sich das Allgemeine immer nur im Besonderen anschauen,das Besondere immer nur im Hinblick auf das Allgemeine denken lt)[9]。这条认识原理所蕴含的基本理念是:在概念的统一性与现象的杂多性之间,必须为概念的优先性创造一种关系。这就意味着概念并不能从杂多性中被推导出来,而是必须被理解为杂多性本身的生成原则(generatives Prinzip)。因此,概念的普遍性并非通过抽象得来的,也并非通过抽空概念内容的事先操作来达成的,相反,普遍的概念被规定为功能原则(Funktionsprinzip),以便能够对看似没有关联的特殊现象做出解释,并且在指出其共同性的同时又不忽略其特殊性。[8]尽管四重证据法更加偏重经验层次,而卡西尔更加注重先验层次,但四重证据法在经验层次对理想类型概念的本质直观同样以卡西尔的先验层次为哲学基础。在这方面,叶舒宪提出的“玉教”概念与瑞士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提出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mensch)概念在本质直观的方式上具有相似之处。正如卡西尔指出的那样,布克哈特试图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体以及独特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但他的这个整体“面貌”不是单纯通过经验的普遍化得出的类概念,而是通过对特殊东西的历史描述来展示出来的普遍特征。“文艺复兴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并非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都能够完全体现出来的特征,也并非单纯的经验研究所能够发现的特征,而是布克哈特通过把他们的所有特征都统一起来而形成的“特征标记”(charakteristischen Merkmale)。也就是说,从方法论上来看,布克哈特并非仅仅通过个案的经验比较来进行归纳,而是对大量的历史材料采取一种“综观”(Zusammenschau)或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观念化抽象”(ideirende Abstraktion)的方法。虽然这种“综观”或“观念化抽象”的结果不一定时时处处都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取得一致,但它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人物的变中之不变,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人物的“一与一切”。即便它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人物在存在上的统一性,也是他们在方向上的统一性。[17]这就表明,作为概念的理想类型来自对文化符号的杂多现象的“综观”和“观念化抽象”,也就是通过一种类似于现象学本质还原和“观念化分析”(ideierende Analyse)[18]的方法而得出的。它与单纯的经验归纳方法所得出的概念的区别恰恰在于,理想类型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不是数量上的平均数,而是性质上的本质特征。
如果说布克哈特研究的“文艺复兴人”是从历史材料中直观到并且还原出来的形式特征,那么,四重证据法所面对的同样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的世界,叶舒宪提出的“玉教”理论就像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人”概念一样,具有理想类型的“一般化概念建构”(generalisierende Begriffsbildung)价值[19],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能够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在某种意义上,四重证据法之所以能够“重构人类文化史和俗民生活史”[20]并且取得“类似于现象学所主张的那种‘直面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方法之认识效果”[21],恰恰因为它采取了一种类似于“综观”和“观念化抽象”的现象学本质还原法,只不过现象学的本质还原虽然“也以单个事物为出发点”却“摆脱众多个体的事实性出现(经验变更)”[22],而“玉教”概念的本质还原却并不“摆脱众多个体的事实性出现(经验变更)”,而是从“众多个体的事实性出现(经验变更)”中还原出保持不变的本质概念。这种还原与单纯经验归纳的区别在于,单纯经验归纳所得出的普遍性往往不一定是现象的本质,而四重证据法却能够把彰显本质的纯粹现象(reines Ph nomen)[23]视为各种经验现象的基础,“用语境还原的方式,尽可能去解读考古实物的文化意义——让无言的‘物’自己去‘说话’”[24],由此“便可大致还原出中国史前信仰的共同核心和主线,揭示作为中国最古老宗教信仰和神话的玉教底蕴,及其对华夏礼乐文化的根本性奠基作用和原型编码作用”[25]。在通过本质直观和本质还原得出“玉教”的普遍概念之后,叶舒宪要用四重证据来验证这个普遍概念是否与特殊的现象相符。在这个过程中,叶舒宪巧妙地、综合地按照认识原则“证据间性”来处理普遍概念与特殊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与单纯因果关系的实证模式相比,多重证据法的论证模式是一个动态复合的论证系统,多重证据经过归纳与演绎组合到一个证明过程当中时,这一问答逻辑本身就包含了多种因果关系的归纳与演绎,由此汇集而成的证据链并非单线的,而是多线的或者网状的。众多证据链之间通过此消彼长并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复合证明力,自然强于单纯的因果关系实证”。[3]不仅如此,叶舒宪还指出,“在利用证据间性进行相互阐发方面,可以展开两种推理范式。其一是顺向推论,即根据历史的先后顺序展开推论。其二是逆向推论,即依据后代的较为完整或较为明确的神话形象和神话母题,反推更早时代的不完整或不明确其功能的神话图像”。[26]由此可见,四重证据法的这种综合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论具有异曲同工的科学步骤和中介环节:
马克思在这里给我们揭示了一条很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人们对一个社会进行考察时,必须通过对一个典型的社会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例如像马克思对英国所作的分析,通过分析揭示出作为一个社会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本质的东西之后,才能走向对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进行综合,使一般的东西具体化。所以,真正科学的综合,并不是把这个共同的、一般的、本质的东西硬套到特殊的、个别的东西上面去,而是要以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作为指导方法,去具体地分析“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以便从中找出从一般走向个别的综合的中介环节。这样从一般走向个别的综合,才能成为具有内在联系及其运动机制的综合,这样的综合才能体现出同一性的差别性,而不是生搬硬套的、纯粹外部联系的综合。[27]
从方法论上来看,经验认识和理解之所以需要“以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作为指导方法”,恰恰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普遍概念的引导,具体东西的单纯变化和消亡就会沦入偶然性的深渊,就会变成凌乱的盲目性和单纯的杂多性。这样一来,经验研究不仅可能迷失在细节之中而舍本逐末,甚至根本就看不见重要的事实细节。所以,卡西尔指出,在认识历史现象之时,只有在某种持续背景的映衬之下,历史的细节才鲜明地突显出来并且在其特有的轮廓中变成可见的。[10]由此可见,文化科学与历史学的知识,既非“规律设定性的”(nomothetisch),也非“个体描述性的”(idiographisch),而是研究以特殊东西表达普遍东西的象征系统(Symbolik)。[10]正因为有了“玉教”概念的普遍引导,四重证据法才能避免盲目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从而突显中国文化象征系统的某些本质特征,从这些证据内部区分出孤证、旁证和能够“上升到思维普遍规则或者文化通则的例子,其证明效力非一般旁证所可比拟,具有演绎推理阐释的有效性”,而对“这种思维规则或文化通则的发现,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研究经验所能企及,而是古今中外众多学者打通式理解的长期积累的结果”。[20]所谓“打通式理解”恰恰是一种类似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和本质还原的方法。这样一来,四重证据法不仅超越了单纯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得以全面和整体性地关照”[28],而且“将实证科学和证据科学的科学性,与人文学科特有的理解和阐释特性,通过四重证据的间性加以调和、完善,在方法的运用中既摆脱唯科学主义,也力求避免人文研究中过度主观化的经验主义倾向,让四重证据所连带着的四种学科面相之间,达成相互促进和相互制衡的有机关联,形成人文研究中的相对科学性和科学研究中的人文阐释的对接、结合、涵化、再生之效果”,从而比较成功地调和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一对老矛盾”。[5]
三、结语:四重证据法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价值
本文的简要分析和论证可以表明,从一重证据到四重证据并非只是证据量的增加和研究视野的扩大,而是方法论上的理论提升。四重证据法虽然由文学人类学学者提出,但绝非仅限于一门学科的某个领域,因为它不仅“既能够显示出其人文学科的文化价值,又具备了社会学科的实证性”[7],而且在逻辑上潜藏着人文科学一般方法论的学理性与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