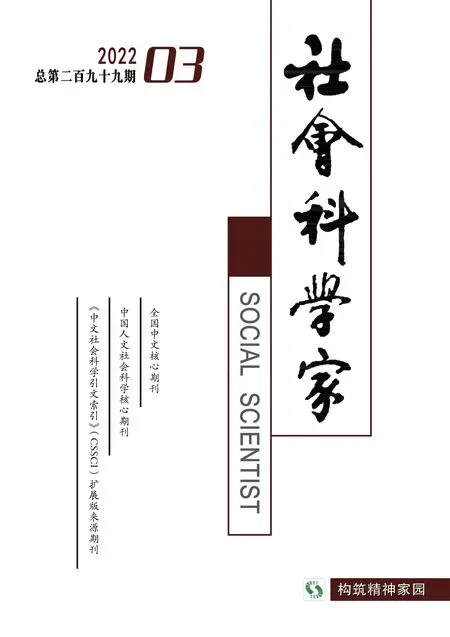作为新文科方法论探索的四重证据法
——以策展咸阳博物院“仰韶玉韵”展为例
2022-02-03叶舒宪
叶舒宪
(1.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一、作为新文科方法论探索的四重证据法
文学人类学这个跨学科研究的流派,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发而松散的个人性探索,逐渐汇聚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学术团体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有组织的规模性学术群体效应,以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再到21世纪初形成新兴交叉学科。回顾这个新学科的发生发展历程,其学术创新的领先标志成果,是对人文学科新方法论的持久性探索,并由此引领这一批学人逐渐打开与时俱进的知识更新局面①作为新学科的文学人类学如何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孕育而出,请参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为《文学人类学教程》写的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如今,在国家开启新文科建设战略的当下语境中,总结和拓展文科研究的新方法论体系,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倡导新文科的基本宗旨,就是要打破旧文科流行日久的分学科壁垒的教育培养模式,努力创造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互通桥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设立跨学科研究平台、鼓励跨学科项目的研究立项,并在课堂教学中拓展交叉学科的自觉意识。数十年来,文学人类学倡导者们积极整合多学科的知识资源,在促进各人文学科间的融合发展方面,充分发挥出某种先锋和示范作用。
从1994年率先提出人文研究新方法论解决方案的“三重证据法”,即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之上增加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将口传的活态文化作为第三重证据,再到运用实践积累十年之后的再度升级改造,于2005年正式确认“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系统理论[1]。至今,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探索和研究实践已有近三十年的经验积累。正是在多年坚持本土化的发展方向和解决中国学术重大理论问题的自觉追求中,四重证据法经历多年应用研究实践和不断调试、修正,目前可以提供成功解决研究难题的案例,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突破研究瓶颈的学术攻坚效应。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案例,即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该项目不仅以24部著作和译著的宏大规模完成结项并全部出版,还获得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并两次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文化外译项目,得以向国际学界推广。目前,该项目的后续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也已顺利结项,其成果于2019年出版四部专著,其中包括《四重证据研究》一书。同年,这套丛书也整体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文化外译项目。近年来,笔者根据对四重证据法的实施运用经验,再提炼总结出两个关键性原则,即“证据间性原则”和“物证优先原则”。
关于“证据间性原则”的讨论,整体呈现在编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文集的过程中,该文集出版时书名为《重述神话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文本论与证据间性视角》[2]。关于“物证优先原则”,则首次以专论形式发表在《国际比较文学》2020年第3期,题为《物证优先:四重证据法与“玉成中国”三部曲》。本文以下,拟围绕这个原则的拓展性运用实践展开讨论,集中说明其在上海市社科特别委托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体现,及其所潜含的对文献叙事和考古文物的“双重激活”作用。
二、物证优先原则与“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
自从国家有关方面在20世纪末期强力推动两个重大国家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学界围绕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学术瓶颈,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突破,严重影响着相关研究者的积极性。那就是对神话传说时代的重要领袖人物(盘古、鸿蒙、倏、忽、混沌、伏羲、女娲、黄帝、炎帝、颛顼、帝俊、帝喾、尧、舜、鲧、禹、启、羿、桀、夔、祝融、共工、西王母、河伯、防风氏等等)无法获得有效证明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效法当年的法国语言学会在召开年会之际特别挂出一面招牌,声明“本会不接受讨论语言起源问题”的相关禁忌。之所以要公开表明对某类学术问题的回避,为的是让当事人明确眼下的知识条件,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以免陷入无休止的架空争辩,却根本无法达成学术共识。挂出这样的学术“禁令”,其实也是为保护研究者,以免在似是而非的争论中大大浪费学界的有限资源[3]。
同样道理,物证优先原则的公开倡导,也是笔者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策划立项的设计初衷。该课题立项宗旨是:通过神话学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打通和结合,将研究中华创世神话的学术视角拓展进入史前文化期,即从过去有限的文献材料之束缚中解放出来,也从纯文学的视角中解放出来,充分利用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的一手材料,特别是近年勃兴的史前玉文化研究的大量材料,实现对国学知识观念的与时俱进的大改造,用实证性的文物材料的充分解读,说明华夏创世大神盘古之精髓化为珠玉的历史秘密,并努力追索其史前史的深厚底蕴。
鉴于目前已知中国境内的出土玉器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所以我们将依据玉文化提供的万年视野和万年以来的实物资料,将中华创世神话的主题引入文化原型研究的空前领域之中,贯彻落实到以往的文史哲学科都不可企及的历史纵深处,从根本上说明后世由汉字记录下的创世神话文本的史前发生脉络问题。万年中国的理论命题之提出,对于整个文科研究而言,具有十分积极的前瞻性意义。
具体而言,本项目要在万年中国的新知识视野下,通过几种重要的玉礼器或玉石种类的溯源性探究,分别说明:盘古是否存在目前根本无法求证,但是开天辟地之斧的发生学原理,可以从工具斧到礼器钺的九千年演变线索中,得到相对完整的实证。尤其是斧钺与神圣开辟的创世联想模型如何形成的问题,得以深度地诠释。还有,在华夏传统中,被创世神所开辟的世界,为什么被先民想象为天圆地方的几何结构,并通过内圆外方的玉琮象征符号,在五千年前长三角地区率先形成一种模式化的玉礼制度,随后则辗转传播到中原地区,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文明之中,乃至出现在商末周初的古蜀国祭祀语境中,呈现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同出的玉璧、有领玉璧、铜璧、玉琮的组合体系。这就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仁湘研究员为本项目撰写的专著《方圆一体:玉琮的故事五千年》的内容。
同样,黄帝的存在目前无法求证,但《山海经》所记黄帝播种玄玉的千古之谜,却可以通过考古发现的玄玉礼器加以验证。即说明五千年前中原文化最早的玉器生产使用的是什么玉料,其来源为何,其传播路线又是怎样的。女娲的存在无法求证,但女娲补天所用五色石有怎样的文化原型,却是有充分实物可以梳理的。其中的赤玉即琼玉,如何是从商周之际接受的外来文化传播与影响的产物,即红玛瑙自南亚和中亚等古老文明通过前丝绸之路而输入中国的全过程。对赤玉的崇拜如何改变华夏原有的玉文化色谱体系,从而自西周时代开始确立“中国红”的制度化崇尚。正是出于这种回避人物求证,而让物证优先的策略考量,“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玉成中国”系列共设计为七部专著,以一万年至九千年的深度历史认识为主线,向下涵盖主要的创世神话主角人物的相关物质内容,几乎全覆盖夏商周即上古三代的神话历史展开线索。
具体来看,本项目对华夏共祖黄帝的论证,主要采取避虚就实的策略,回避对相关神话叙事中无法证明的虚构成分的探讨,而聚焦到可以从考古新发现中找出实证的物质要素方面,给神话讲述的圣物文化内容找出新知识可以有效链接验证的部分。于是,选取玄玉这种只和黄帝神话发生密切关联的圣物对象,撰写出《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对夏代的探讨,集中在夏王朝创世英雄先祖大禹的神话圣物,即《尚书》等文献有关天神恩赐禹玄圭的叙述,根据考古发现,找出玄圭的史前原型,即距今四千年以上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黑色玉圭实物,兼及龙山文化时代至夏商周时代的各种深色玉圭文物谱系,说明这个重要圣物母题在后世的创世神话观念中的原型塑造作用,透析圭璋礼器的文化再编码过程。这就是项目成果先出版的第二部书《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的内容[4]。
对于夏代之后的商代,则依据河南安阳殷墟等地出土大量高等级遗址和墓葬的玉礼器情况,尽可能对这个时代的玉文化发展做出全景关照,特别是与商代创世想象相关的玄鸟生商族源图腾神话的考古学求证。这就是本项目中的子课题《玄鸟生商:商代玉器故事》一书内容。对于上古三代中的周代,则集中探讨前人没有任何相关知识的全新物质文化领域——六千年前在南亚次大陆发源的红玛瑙珠,如何先传播到整个中亚和西亚古文明,再辗转通过新疆一带而最终输入中原地区,促成我国西周时期玉组佩新形制的一代风尚,即白玉青玉制成的玉佩和批量红玛瑙珠相互串联而构成完整的玉组佩情况。并由此而阐释古代经典礼书文献《礼记》所记“周人尚赤”说的文化底蕴,“中国红”美学构成的历史基因方面的溯源研究。是为易华研究员撰写的专著《周人尚赤:红玛瑙珠传播中国的故事》之主旨。至于玉斧钺和玉柄形器,也是两种具有典型性文化符号功能的华夏史前圣物,二者的出现一直贯穿到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的全过程。《盘古之斧:玉斧钺的故事九千年》与《祖灵在天:玉人像与柄形器的故事五千年》二书,也希望能够全程审视史前大传统到早期文明神话观念的连贯性,关注文化传统如何不曾中断的延续方式。将今日中国家族祠堂中依然在供奉的祖灵牌与四千年传承的玉柄形器,对接成一个首尾圆贯的完整故事。并重点说明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造成华夏文化传统中偶像崇拜与非偶像崇拜并存不悖的现实特质,为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研究打开一个新天地。
总之,遵循四重证据法的物证优先原则,催生出上海市社会科学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其突出的学术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两方面:
其一是学术攻坚,突破文科研究瓶颈。以新时代上海市文化建设重大工程——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为引线,以努力满足国家需求为研究宗旨,将项目设计理念围绕当前国家最需要的学术攻坚方向: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和证明。这样就可以保证丛书出版的学术突破意义和文化再造意义。同时兼顾与创世神话内容的有效衔接:从创世的文学叙事研究,拓展为对华夏文明创始过程的研究,从而凸显出通过神话学探索华夏文化基因的学术宗旨。
其二是运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七部研究著作的内容,基本都不是在众所周知的常识层面进行探讨,而是依托考古新发现的物质资料,调动物的叙事潜力,专门探索以往知识界所没有的全新内容。利用文化大传统理论和四重证据法所倚重的实物证明模式,逐一解析每一种玉礼器作为考古对象的神话学蕴含,揭示其特定的信仰观念的支配性原理,钩沉性地重建出一整套以往未知的中国故事。
三、四重证据法的双重“激活”效应
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取向是要打破学科本位主义的束缚,发挥学科间交叉融合的知识整合优势。文学人类学派倡导的四重证据法,它和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充分调动传统国学知识中所没有的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知识,形成文化文本多级动态编码的研究思路①关于文化文本,参看李继凯、叶舒宪主编《文化文本》创刊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关于文化文本多级动态编码理论,参看叶舒宪、柳倩月、章米力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二章N级编码论;第三章编码的符号学,第33-68页。,即从史前文化大传统新知识,重审文字小传统的以往知识,从而获得查源知流的文化解码效果。而四重证据彼此之间的证据间性,则潜含着重要的再解读与再阐释的方法潜能。有效发挥此种潜能,可以带来对文献和文物的双重激活作用。
第一重激活,是指对上古文献叙事中未知究竟的哑谜的再阐释,给远古名物的记载带来一种重新唤醒的作用。以《楚辞·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叙事和《山海经·中山经》所记熊山熊穴为例,古往今来对这个古书中记录的神熊动物内容,始终没有清晰明确的认知。一旦运用四重证据法找出辽宁建平县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女神庙中的神熊偶像作为第四重证据,文献中熊穴出神人叙事哑谜,就彻底打开了重新思考的深远而巨大的历史空间。再辅之以第二重证据楚帛书创世神话叙事以“天熊”开篇,第三重证据有华佗五禽戏中的熊戏,其每一修炼招式都是模拟熊的动作。四重证据之间的互动互证能量,足以重建出一整套华夏“天熊”信仰的文化史脉络[5]。
再以“玄玉”为例,这本是《山海经·西山经》有关黄帝叙事中的一个名物母题,古往今来的注释家们或回避,或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原因主要在于,谁也没有从科考的意义上找出玄玉这个名称所指称的实物,因而不明白玄玉是怎样的一种物质。注释家们对玄玉一名能够加注的内容,无非是根据训诂原理,以黑色来训解“玄”字的意义:玄玉即黑玉。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组织的第九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在甘肃天水武山县鸳鸯镇找到至今还在开发使用的玄玉玉矿标本,其地矿学名叫作“蛇纹石”。一般将蛇纹石也算作广义的玉料。其呈色特征是墨中透绿,常常为墨绿相间的斑纹状,类似蛇皮。我们根据出土文物认识到这种玉料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得以开发利用,并沿着渭河展开最早的西玉东输路线。这样就终于揭开玄玉物质的神秘面纱,并根据黄河中游地区各市县的文物普查情况,组成一个完整的史前玄玉玉礼器的证据链条,有效建构出一个延续一千五百年之久的史前中原的“玄玉时代”,为华夏文明史的先于甲骨文字的更早阶段,找出圣物符号的传承系统。
玄玉时代,作为史前史研究的一个理论假说,一旦获得更为系统的证据链支持,就从理论建构的假说形态转化为可实证的理论命题,引领进一步的广泛应用研究。在这方面,第二重激活的效应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发挥出连锁性的作用。由此可知,四重证据法如何引导着新理论命题的提出。而理论命题的作用,是对以往的史前史认识缺环,发挥出弥补和再衔接的功能,还能够让常年沉睡不醒、“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珍稀文物、得到重新认知和重新鉴定的契机。
2021年初,上海市项目成果先出版的第一种《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问世仅有一个多月,笔者便又在陕西省咸阳博物院的史前石器展品中,发现有类似仰韶文化玄玉玉钺的文物。随后委托西安的王伟硕士展开入库调研和鉴定工作,结果表明,该博物院在1957年文物普查工作中在渭河边的一个重要仰韶文化遗址(尹家村遗址)采集的一批文物中,约有十八件作为玉礼器的玉石斧钺。这是自1921年仰韶文化被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一百年来,最大数量的一批玉礼器。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当即联合咸阳博物院和咸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单位和《人文杂志》《中原文化研究》《丝绸之路》等刊物,于2021年5月22日策展咸阳博物院“仰韶玉韵”文物特展,为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献上新文科研究实绩的一份纪念厚礼。同日还在咸阳召开玄玉时代专家论坛,邀请北京、上海、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市专家就仰韶文化玉礼器群的再发现,展开热烈讨论。①关于“仰韶玉韵”特展及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玄玉时代”专家论坛,请参看《文汇报》记者韩宏的报道:《距今5500年至4000年,以黑色玉料为主的玉礼器流行中原!“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见文汇报客户端:2021年5月28日。http://www.myzaker.com/article/60b0b66c8e9f092c8c7bfae3/笔者在论坛上宣读论文《仰韶玉钺群初探——灵宝西坡与咸阳尹家村出土玉器的对比分析》,展示四重证据法作为新文科方法论在融合多学科知识并引领学术创新方面的作用,给中原玉文化发生的第一个时代为“玄玉时代”的理论命题,做更加全面的论证,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新方法论的解决案例。同时还提示,对炎黄至尧舜禹的神话传说人物研究,目前的可行策略是选择相关叙事中的物质文化方面加以求证,而尽量避免陷入对人物本身的无谓争辩。事实表明,物证优先策略会催生怎样的突破瓶颈效果。
从2007年的天熊神话与熊图腾信仰研究,到2020年的玄玉时代研究,再到2021年春第一次仰韶文化玉器特展在陕西咸阳博物院揭幕,文学人类学派将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大发现所得史前玉文化分布系统知识,援引到对文献叙事哑谜的释读方面,给出一个4.0版的西玉东输运动的系统认识谱系[6],从而有效“激活”所有相关文献叙事的现实底蕴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有效激活深锁在博物馆库房里的一批又一批的沉睡文物。
若再通过比较文明史的关照,说明五千多年前仰韶墓葬的玄玉玉钺加黄土陶灶,如何给华夏文明千家万户所崇奉玉皇加灶神的普遍信仰模式,奠定其史前原型。也给华夏宇宙观的天玄地黄模型,奠定文化文本的意义原型。如果说古埃及文明的标志是金字塔,其功能是引领葬在金字塔下的法老木乃伊之灵魂升天,那么同样是五千年前的华夏玄钺,之所以模式化地出现在仰韶文化墓主人头顶上方,不是同样发挥着引魂升天的神话职能吗?[7]五千年文物一旦经历比较神话学的激活,其所承载的先民信仰的精神世界,也就会依稀地向我们当代人招手了。
唤醒沉睡五千多年的中原顶级玉礼器群,打捞被历史尘封久远的史前文化信息,成为文学人类学派正在努力尝试的学术方向。希望能为启发当代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供以往所未知的深度中国故事。
以下援引为咸阳博物院“仰韶玉韵”特展撰写的策展说明,作为本文结尾:
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时间从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延续两千年之久;其空间分布在中原及周边地区,堪称孕育中华文明的重要母胎。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自仰韶文化发现百年来,一直没有规模性的玉礼器发现。21世纪初,在以河南灵宝西坡和陕西高陵杨官寨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遗址中,先后发现深色蛇纹石玉钺的批量生产和使用。这一发现揭开了中原玉文化发生的序幕,改写了中国玉文化的历史,对于认识文明国家起源具有标志性意义。
咸阳尹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渭河岸边,早在1957年已被发现,但出土的一批深色蛇纹石玉斧钺长期以来沉睡在博物院文物库房里,标注为石器。2021年2月,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专家团队在咸阳博物院协助下辨识出这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墨色、墨绿和绿色蛇纹石玉斧钺多达15件,超过灵宝西坡和杨官寨两地出土玉钺的总和。这批玉石斧钺的制作年代或在仰韶文化半坡期到庙底沟期之间。这是六十四年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中原文化五六千年之瑰宝,是迄今所知玉礼器登场中原文明的第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