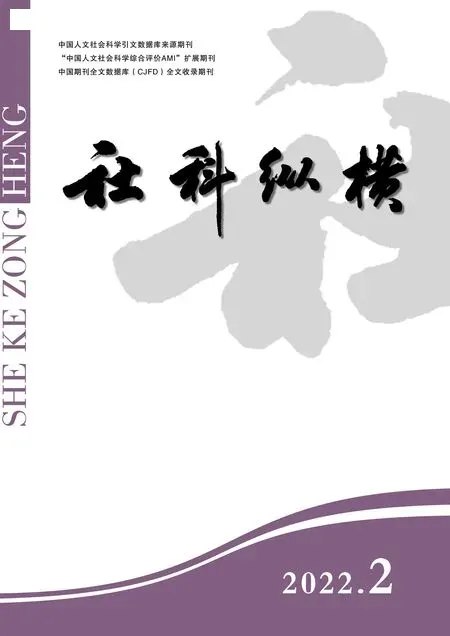《京尘杂录》的道德价值及情感两难
——兼论民间戏曲史书写中的乐教
2022-02-03钟艳艳
钟艳艳
(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阳明先生指出:“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1]113清人钱麟书也认为“今之戏,古之乐也”[2]274。按《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古义,戏曲天然地承担着端正风俗的任务,亦即“乐教”。中国古代伦理史上,乐教向来是与礼教相配合的教化支柱。作为“乐”变迁形式之一的戏曲,其首要内涵是作为一种审美内容给观看者提供审美情趣,这才符合“乐以教和”的审美理想。戏曲具有多元化的“美”的形态,当文人在创作剧本时,主观上对道德现实和道德理想间差异的弥合,又赋予戏曲以教化之功能,这即是戏曲中的乐教。在19 世纪的中国,清廷通过对戏曲选择性地支持得以成功控制商业戏园内的道德价值观[3]。反映到民间,文人的民间戏曲史书写在爬梳伶人、曲段以及梨园掌故的基础上,以树立伶人道德形象来间接参与国家教化,民间戏曲史的书写也由此成为与官方互为补充有时又互相对立的历史材料。
杨懋建,字掌生,号尔园,别署蕊珠旧史,“道光辛卯恩科举人,官国子监学正,著有《留香小阁诗词钞》。掌生聪明绝世,年十七受知阮文达,肄业学海堂……癸巳春闱已中会魁,总裁文达以其卷字多写说文违例,填榜时撤去其名,遂放荡不羁,竟以科场事遣戍。”[4]25-26据幺书仪推论,杨懋建应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 年)死于咸丰六年(1856 年)左右,享年不及五十岁[5]。道光十二年(1832 年),25岁的杨懋建进京应试,自此开启了他的京城旅居生涯,也由此得以深入接触京城优伶,写就总名为《京尘杂录》的具有民间戏曲史性质的作品集。
《京尘杂录》由《长安看花记》《辛壬癸甲录》《丁年玉筍志》和《梦华索簿》四卷组成,前三卷是以伶人为对象的纪传体作品,第四卷记载了京城梨园规模、戏班组织、演出概况、梨园掌故、士伶交往概况,在结构上是对前三卷的补充。《京尘杂录》作为民间戏曲史作品,在创作时作者保有“史线”的责任感与自觉。杨懋建尝言:“倘今不及撰定,恐更十年后,无复有能道道光年太平盛事者矣。”[4]279在记叙名伶时他以“以佛法过去、现在、未来命之”,实际上串联起嘉庆末年至道光时期的三代名伶。就《京尘杂录》的结构和内容看,这部作品基本符合民间戏曲史书写的规范。据杨懋建自述,他撰写《长安看花记》的志向就是将之与《莺花小谱》《日下看花记》等民间戏曲史类作品并肩。将文人们创作的民间戏曲史作品串联起来不仅能对梨园生态有连续性的记录,还能以文人修养给予一般民众以戏曲上的审美指导。以杨懋建《京尘杂录》为研究对象,可以看出民间戏曲史书写中的教化元素和戏曲的乐教功能在清中后期的嬗变,以及杨氏在参与建构儒家教化认同时的自觉与犹豫,而这皆与清中后期的礼学发展史同步。
一、侠伶与荒伶:以伶人故事为中心的教化形象树立
在《辛壬癸甲录》中,杨懋建将人分为六等:人、鬼、神、仙、佛、侠,以此为参照系,伶人形象也有了较为清晰的道德层次。杨氏笔下的伶人形象鲜活,有雅致的书墨高手如小桐,时人追捧小桐笔墨,“有不能致小桐手迹者,自惭为不登大雅之堂,自惭为不韵”;有耿直果敢的小蟾,“往往高谈雄辨,惊其座人,顾好讦直,以招人过,人多不能堪,其侪偶咸嫉之,我辈亦多恨者”;当然也有擅长挥霍的破落户形象如陈金彩。但这些形象只停留在“人”的阈限内,侠才是杨懋建心中理想人格的最高样式,杨法龄就是他心目中的伶侠。
杨法龄,早脱乐籍,在京师戏曲界小有名气后离开京师。他不蓄弟子,偏居一隅,认为此前生活受“无量恐怖、烦恼”,今“幸得解脱,登清凉界”。杨法龄脱籍后也主动摆脱梨园氛围,“一洗金粉香泽习气”,“超然蝉脱,吸露吟风”,众人也因此以为他将“不复出来”,但不久后杨法龄复来京师,自言“今日孑身入京师,固十年前故我,吾舌尚存,何害”。他重回京师是为重操旧业讨生活,而生活困顿的原因是“所挟数千金已尽散诸宗族亲戚闾之贫者”。杨法龄称:“吾十余岁,家贫无所得食,父母卖我,孑身入京师。幸而载数千金以归,念吾宗族亲戚闾之贫者,犹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日之事保不复见于今日。”[4]285杨懋建认为,杨法龄脱籍后的恣意状态显露出佛气,而散金济贫又表现出侠气。从“自幼酷嗜”的《红楼梦》中寻找人物与杨法龄做对照,杨懋建发现了刑岫烟和尤三姐。
刑岫烟家世清贫投靠在贾府邢夫人处,平日与心性高洁的“槛外人”妙玉交好,她的佛气很大程度上是受妙玉感染。刑岫烟的佛气正如她的诗句“浓淡由它冰雪中”一般,是对自身清贫家世的淡然和对以邢夫人为代表的世俗观念的超然。对照来看,杨法龄脱籍后有着虽短暂但彻底地对梨园氛围的告别,他摆脱了戏曲带来的世俗烦恼而得以生活在向往而自得的“清凉界”。后来杨法龄将十年间从艺所得千金散给宗族贫困者的行为本身是对世俗物质判断标准的挑战。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想,杨法龄散尽千金的行为或许有将从业十年间“无量恐怖、烦恼”一起丢弃的象征意蕴。杨法龄后来再度孑然一身入京,潇洒重做“十年前故我”的心态符合杨懋建心中的侠气。与《红楼梦》里符合“侠”之标准的尤三姐相比,尤三姐有着明艳的美且性格刚烈,出于生计考虑,她不得不周旋于贾珍等贵家浪子之间,而贾府众人对她“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的评价则反映出尤三姐对以自己为取乐对象者的反抗。反观杨法龄,他进入戏曲行当是为生计所迫,在物质相对富足时又主动从物质牢笼中超脱出来,不为金钱所困。也正如尤三姐以随意对待贞操来反对礼教世界中的贞洁观念一般,他也以对待金钱的自在态度获得在世俗世界坦荡行走的伶侠风骨。
梨园中虽有杨法龄一般超脱自在的侠伶,但也不乏沉湎于绚烂世界的“荒伶”。陈金彩原名元宝,掌管三庆戏班后更为现名,在梨园中也算独占一角。有一定身家后的陈金彩热衷于赌博游戏,如摴蒱、六博与投壶。摴蒱是投掷五颗颜色不同的木子并以颜色全同为胜的游戏。汉代时摴蒱还是仅供上流人士娱乐的游戏,魏晋时才流行到下层百姓之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曾记述参与摴蒱者“狎比淫朋,缠绵永夜。倾囊倒箱,悬金于崄巇之天”[6]420,由此也能想见陈金彩参与其中的沉沦模样。六博是由12 颗棋子组成的以吃子为目标的棋类游戏,投壶则是从古射礼演变而来的赌酒游戏。陈金彩每入博场“辄散数百金”,常以“金缠臂跳脱数十支,但供投壶一笑”。陈金彩妻子对他“苦谏,不见听”,于是私下里将京城的房舍、店铺等贱价出售决心回乡,陈金彩无奈也只能一同返乡。可归乡后的陈金彩已不再能接受故土生活,他“不惯家食”,不仅无事可做也无所适从,于是又独自回到京师于旅店寄身。这时自由的陈金彩“裘马翩翩。甚丽都,好摴蒱六博如故”,但不久就因此负债累累,不得不“泻囊货骑,尽偿戏债”,最终,竟沦为饿莩[4]290。正是“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
从对杨法龄与陈金彩经历的反差书写,作者对二人的褒贬态度言下立现。杨法龄在梨园中来去自如的洒脱,他对金钱的淡然、对过往施恩者的倾囊相报,无不彰显出伶人的高洁品质,为礼教所鄙的他们也具有礼教歌颂的侠义品质。而陈金彩在戏曲之外现实之中的落魄结局与戏台上的大团圆结局也形成了鲜明对比。朱光潜先生指出:“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7]210大团圆反映出人们审美意趣的理想化,但美好结局总需要一个关键人物的出场来扭转前情。因此,大团圆戏剧中贵人对遭难者命运的转折意义也为伶人平淡的生活埋下了遇见“贵人”的希望。不可否认,伶人们的经济来源大多来自为他们捧场的达官显贵们,这也使得一些伶人即便脱籍后也难以彻底切断与贵家子的联系。杨懋建也认为,伶人虽然有接近“贵人”的捷径,但上层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始终像是从“海上望三神山”,山是缥缈模糊的,“但见云气往来,可望而不可即矣”[4]288。陈金彩也正是在虚幻的戏曲世界中,只看见金银带来的奢靡快乐而忽视了真实生活。有学者指出伶人心底始终有一种自贱心态,无论他们与上流人士多么过从甚密,多么擅长诗画书墨附庸风雅,但在骨子里始终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梨园中小有名气的陈金彩不再能接受原本的乡间生活,他沉湎于博戏时的豪掷百金也仍有为取得观看者惊叹的心理,这种行为的本质是以己娱人,他仍是供人取乐的玩物。
戏曲在承担宫廷中政治性的娱神使命之后,又流布到民间成为娱乐性的娱人活动。伶人作为这项活动的主角不仅是戏曲故事的表演者,也是戏曲内涵及价值的传达者,生命等于戏剧、人等于角色是伶人生活艺术的隐喻。杨懋建笔下的杨法龄与陈金彩是反差极大的两种伶人性格,正是通过这样的性格对照,作者含蓄地表达出他对儒家道德价值的弘扬态度,他树立的伶人形象也在作品刊行流布中给阅读者们提供了可参考的两种人格取向,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道德选择,流传于群众间的戏曲也在群众中发挥着教化使命。
二、笼中鸟的自白:梨园“礼”失落背景下的伶人选择
潘光旦先生曾言:“自以伶业为可以矜贵的伶人,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例。伶人在同业之间,尽可以取恃才傲物的态度,尽可以有同行嫉妒的心理,假如自己是出自一个梨园世家,更可以鄙薄那些暴发与乘时崛起的伶人……但无论如何,对于同业以外的一般社会,一个伶人就决不能用绝对对等的人格,出来周旋。”[8]257即便如杨懋建这类为伶人作传的文人,在不自觉的意识深处也存在着对伶人的轻薄态度,他曾流露出赞赏之意的春山,就是因为其善于周旋在各类观戏客人之间,能使每个人都“欣然开口而笑,莫不各得其意以去”。伶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注有时被掩盖在流转交际之下,但他们仍希望凭借自身努力将自己从失序的梨园生活中解放出来,汤鸿玉和韵香就是这样心路相仿但命运迥异的伶人。
汤鸿玉师出名门,系徐桂林“天馥堂”的弟子。在脱籍后汤鸿玉离开京师往嘉应娶妻生活,后来又回到京师。杨懋建认为“鸿玉色艺亦止中人,在后来诸郎中无大出色”,但众人“特以其系出名门,故多刮目相待”[4]341。同样以《红楼梦》为比照,杨懋建认为龄官与汤鸿玉可堪一比。《红楼梦》的龄官是在元春省亲前贾府买来唱小旦的,同一众伶人住在梨香园。小说中的龄官不仅在眉眼上与林黛玉相像,“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个性也极清高并以只唱自己本角戏来表现自己的清高。通过贾蔷送龄官笼中鸟的故事可以对照理解杨懋建对汤鸿玉命运的沉思。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蔷送龄官一个雀儿笼子,“上面扎着个小戏台,里面装一个会衔旗串戏的雀儿”,龄官却说:“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9]481笼中鸟即是龄官自身处境的写照,被贾府买来安置在梨香园供人玩乐,她心中有对贾府外自由世界的向往。而汤鸿玉虽在略有名气时脱籍并离开京师娶妻生活,但后来又重返京师,以前述杨法龄对照来看,汤鸿玉很有可能因生计问题重回梨园讨生活。
杨懋建对汤鸿玉的记述反映出他对伶人命运单一性的惋惜。大多伶人因家贫而被卖入梨园,自小浸润其中使他们即便不喜欢却也只掌握了伶人的技能。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认为,伶人大多来自卑微的社会阶级,他们生存的大环境“所养成的神经系统,往往是不很稳健而极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激”,“再加上穷困、生活的不规则、青年时代职业的卑微与变迁不定、正式教育的缺乏、普遍社会道德约束力的薄弱等等”,都会使伶人除了戏曲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条适宜他们的路[8]124。汤鸿玉因戏曲生财而离开戏曲,后来又可能因生活所需重返梨园,自由与不自由的尺度有时并不掌握在伶人手上。此外,作者还表达出对汤鸿玉色艺只及中人却因师出名门就被刮目相待状况的不满。他指出,名望显扬如汤鸿玉的师父徐桂林,虽然在“天馥堂”之后自名居室为“雲仍书屋”以“自别于乐籍中人”,但“人固当知天馥堂,无有知雲仍书屋者。虽翘然自异,思比幽兰,不欲与众草凡卉伍,固未易得矣”[4]341。以此烘托出他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社会现实的无奈,以及对普罗大众“但以门第征辟,能有几人张目”观念的惋惜。
韵香是杨懋建表达极多惋惜之情的伶人。韵香与蕊仙、冠卿是京师梨园的鼎力名角。杨懋建评价韵香“虽在香天翠海中,往往如嵇中散土木形骸,不加修饰”,既无烟火气又无尘土味。三年期满时韵香准备脱籍离开,他的师父却暗中与韵香父亲联络并私下交易八百金,意图强留韵香。而韵香索性召集贵家子筹募三千“出笼”金,后得以脱籍。脱籍后的韵香定居在臧家桥玉皇庙侧,居室自名为“梅鹤堂”。倾慕者往来频繁,韵香“言笑晏晏,诚升平之乐国,欲界之仙都矣”。只是好景不长,韵香“愁恨久种,病境已深”,不久即离世,这时的韵香年仅十八。杨懋建暗示韵香生前的“愁恨”与“病境”皆是戏曲带来的,“韵香以成童之念,始来京师。从师学无几时,即以其色艺倾倒都人士。从此宾筵客座,招邀无虚日。油壁锦障,六街九陌,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过市,日日如坐云雾中”。成名后的纸醉金迷使得韵香失去提升技艺的独立空间,导致他“进亦愁,出亦愁”。韵香的死也是“求速”的结果,病中的韵香曾购买阿芙蓉膏(即煮成膏状的鸦片),“以是日日在氤氲世界中”,不久就去世了[4]281-282。
韵香的死反映出清代戏曲走向娱乐化后,在戏曲的政治性、伦理性成分逐渐褪淡的大背景下,由梨园混乱秩序催生出的伶人光彩生活表面下隐藏的心灵空虚。梨园秩序由伶人身份秩序与观戏者礼仪规范共同维护,杨懋建指出早期戏班中就有对伶人身份秩序的规范:“伶人序长幼,前辈、后辈各以其师为次。兄、叔、祖、师,称谓秩然,无敢紊者。如沙门法嗣然。”[4]355这种身份秩序规范虽然使得门派出身成为衡量伶人价值的刻板标准(“天馥堂”中色艺并只及中人的汤鸿玉即是这种由固化秩序繁殖出的刻板标准的受益者),但无疑发挥着维持梨园生态的功能。后来随着“伶人经济”勃发,伶人成为戏园的经济命脉。贵家子弟们购买“楼上最后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的豪客官座,却往往等不及观看整场戏,只在他们追捧的伶人下场时便离场奔赴,伶人们也“各自归家梳掠薰衣,或假寐片时,以待豪客之召”[4]354。据杨懋建记载,京师将客人私访伶人的活动称为“打茶围”,伶人提前备好小纸灯,当步行来访的客人晚间离开时,伶人就赠予一盏小灯,以致胡同中有“入夜一望荧荧如列星”的景象。这些现象无疑扰乱了梨园的原有秩序,在外在身份和内在心理上都扭曲了伶人的生活感受。
在观戏礼仪层面,梨园赏戏起初亦有其规范。杨懋建称京师有戏庄宴客礼,戏庄“先期计开宴者凡几家,有客若而人,与乐部定要约。部署既定,乃告主人,署券为验。主人折东以告客曰:‘某日集某所,乐演某部。’届期衣冠必庄,肴核必腆,一献之礼,宾主百拜。自朝至于日中昃,肃肃雍雍如也”[4]349,这种观戏礼仪是宫廷观戏礼在民间的变形。从礼的角度看,观戏时的诸种仪节能够在举手投足间将观戏者行为约束在得体范围,进而在戏曲熏陶中形成由外及内的温文尔雅。但无论是从观戏礼的淡出看,还是从杨懋建记述时期的戏曲内容和风格看,试图借用戏曲以培养民众修养的乐教环境都不复存在。
杨懋建在以伶人经历及其价值选择为中心构建戏曲的乐教内涵时表现出对伶人生命的同情式理解。从其字里行间的记述可以看出,即便是对荒淫的伶人他也并未表达出直接的批判态度,反而将他们的生活境况归结为将伶人们架置于空中楼阁的富贵观戏者。韵香成名于戏曲,他的死在根源上也是由纯粹以经济为导向的戏曲导致。脱籍后的韵香虽然离开戏曲的大环境,但身边结交的仍是在梨园中结交的贵士,他的生活样貌并没有太大改变,购阿芙蓉膏以求麻痹而速死即是梨园中纸醉金迷生活的延续。这也反映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伶人“尽可以改业,但是一天不停止唱戏,一天不教弟子改行,一个伶人便一天要受一种特别的身份的拘束,这种身份一天不能摆脱,他要结交朋友,选择配偶,便一天不能跳出同业的范围”[8]158。韵香的速死也恰恰说明他以逃离梨园来掌握自身命运的努力仍以失败告终。
三、乐教的升格:寻找儒教之外的教化机制
伶人们在儒家道德体系中表现出的两极取向无疑给杨懋建的作品书写带来一定困扰,他既希望以伶人们符合儒家价值标准的形象建立起戏曲的乐教形象,又对违背儒家道德取向且结局凄凉的伶人报以同情式的理解。在杨懋建民间戏曲史的书写过程中,他面对着如何在符合乐教的伶人故事与违背乐教精神的伶人形象间做取舍的情感两难。作为折衷,杨懋建搬出儒家精神之外的佛道信仰作为扶植伶人形象的佐助,并借此抒发他对伶人情感上的补偿。具体来看,这又是从伶人对戏曲行业神的敬畏和伶人在心理及行为上对仙佛信仰的向往展开。
行业神一般在发挥保护推动行业发展功能的同时还起着监督行业内部生态的作用,戏曲行业神即是如此。戏曲行业神一般以老郎神或二郎神为崇祀对象,伶人对行业神的祭祀有的源于崇拜英雄形象,如二郎神的原型多为于百姓有实际贡献的李冰父子等,但就个人经历看他们与戏曲并无关联;有的是认同崇祀对象对戏曲行业的功劳,如老郎神,老郎神一般被认为是唐明皇,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中也有伶人崇祀唐明皇的记述。杨懋建在《梦华琐簿》中转述了《比目鱼》剧作中反映的二郎神崇拜。“《比目鱼》入班出宾白:‘凡有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一我做戏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释家的如来佛,道家的李老君。我们这位先师,极是灵显,又极是操切,不像儒、释、道的是主都有涵养,不记人的小过。凡是同班里面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大则降灾祸,小则生病、生疮。你们都要紧记教心,切不可犯他的忌。’”[4]373这大有戏曲神对从业者在品行上的监督意味。不过杨懋建认为老郎神才是戏曲行业神的主角。他不知老郎神为何人,有伶人告诉他“老郎神耿姓,名梦。昔诸童子从教师学歌舞,每见一小郎,极秀慧,为诸郎导。固非同学中人也。每肄业时,必至。或集诸郎按名索之,则无其人。诸郎既与之习,乐与游。见之则智慧顿生。由是相惊以神,后乃肖像祀之”。这是戏曲神之于戏曲行业的特殊意义:老郎神是伶人在戏曲表演时的智慧、灵感泉源。杨懋建称“每入伶人家,谛视其所祀老郎神像,皆高仅尺许,作白晳小儿状貌,黄袍被体。祀之最虔”[4]373-374。就此来看,崇祀老郎神在伶人群体确有其普遍性。
可以假设,伶人崇拜老郎神或二郎神的心态大概率会促使他们产生演绎神明故事的戏曲创作与表演冲动,但这却是为官方禁止的,因之与清代禁演帝王故事、禁扮圣贤形象、禁演佛仙戏的政令相抵牾。乾隆时《大清律师》明文禁止“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与同罪”[10]569。后来,甚至是以惩恶扬善为主题《目连戏》,即便其一度在宫廷中被“析为十本,谓之《劝善金科》,于岁暮奏之”[11]77-378,但在民间依然因其佛教背景而遭到禁止。官方禁演佛仙戏本质上是对神圣力量的独占,在结果上却波及伶人以儒教信仰模式为底色的行业神崇拜。一条抒发信仰的路线被阻塞促使伶人寻找新的信仰路线,于是仙佛向往成为伶人抒发情感的出口。
从戏曲界的混乱秩序看,伶人对仙佛气质的附丽实际上寄托他们逃离戏曲生活的愿望,杨懋建就认为伶人莲舫“跪奉千名佛经,顶礼膜拜”的行为“慨然有成佛升天之想”。除了在仙佛中寻找寄托的伶人,还有在仙佛之外另寻他路的“异类”伶人小蟾。小蟾相信在仙佛之外有一魔道,魔道与仙佛共同组成三教,并常说“阿修罗与我佛比肩而立”,以此表达自己不为世俗所拘的自在精神。
戏曲与宗教中都存在着一个想象的世界。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距离感有时将伶人抽离于现实之外。概之,杨懋建在儒家气质之外,以佛、仙气质角度刻画的伶人形象,从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戏曲的乐教功能层次,且伶人追求的仙佛气质及意境,无形中成为观戏者竞相模仿的热潮。杨懋建通过对此类形象气质的书写,将仙佛气质中与儒家道德价值的相通点更为立体、鲜活地结合起来,杨法龄的侠义与清净心即是此间代表,也正是依托伶人拥有的儒道佛三教中共通的美好品质,杨懋建内心深处对伶人命运与教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心理才得以疗愈。
四、结语
潘光旦先生指出,我国以前没有研究伶人的作品而只有叙述伶人的作品,而这类作品的叙述目的是以伶人为书写对象去纪念、劝惩、揄扬某种价值理念。杨懋建以树立伶人形象、记叙伶人故事作为强化戏曲之乐教责任和功能的方法论,他的作品既有对伶人符合儒家道德的赞许,也有对伶人试图超越儒家价值体系努力的欣赏。在此过程中还能看出他对伶人们的平等关怀视角:虽然伶人历来被轻视在“正统”之外,杨懋建却将他们天然地安置于教化之中。世人伦常不接受伶人,杨懋建却要赞颂他们自觉超越名教的侠气。在将伶人崇尚的仙佛气质与儒家道德品质相联结的过程中,杨懋建对戏曲乐教之维的构建也获得了更为立体的表达。
从杨懋建对戏曲乐教功能有意识地建构可以看出落寞士人潜在地参与伦理教化的主动性。但需要指出的是,《京尘杂录》在本质上也是文人以“文字”捧角的产物,因而他的态度很难保持客观,同时,在杨懋建“尊重”伶人的同时也存在着视伶人如玩物的普遍思维。抛开其作品的教化旨趣可能对读者品评伶人时造成的“误导”不谈,我们在看待多样的伶人性格时可以采取潘先生的包容与自省态度:我们以前瞧不起他,甚至于狎侮他,是我们有负于他,不是他有负于我们[8]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