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小说中的“怪物”研究
2022-02-03包啟飞
包啟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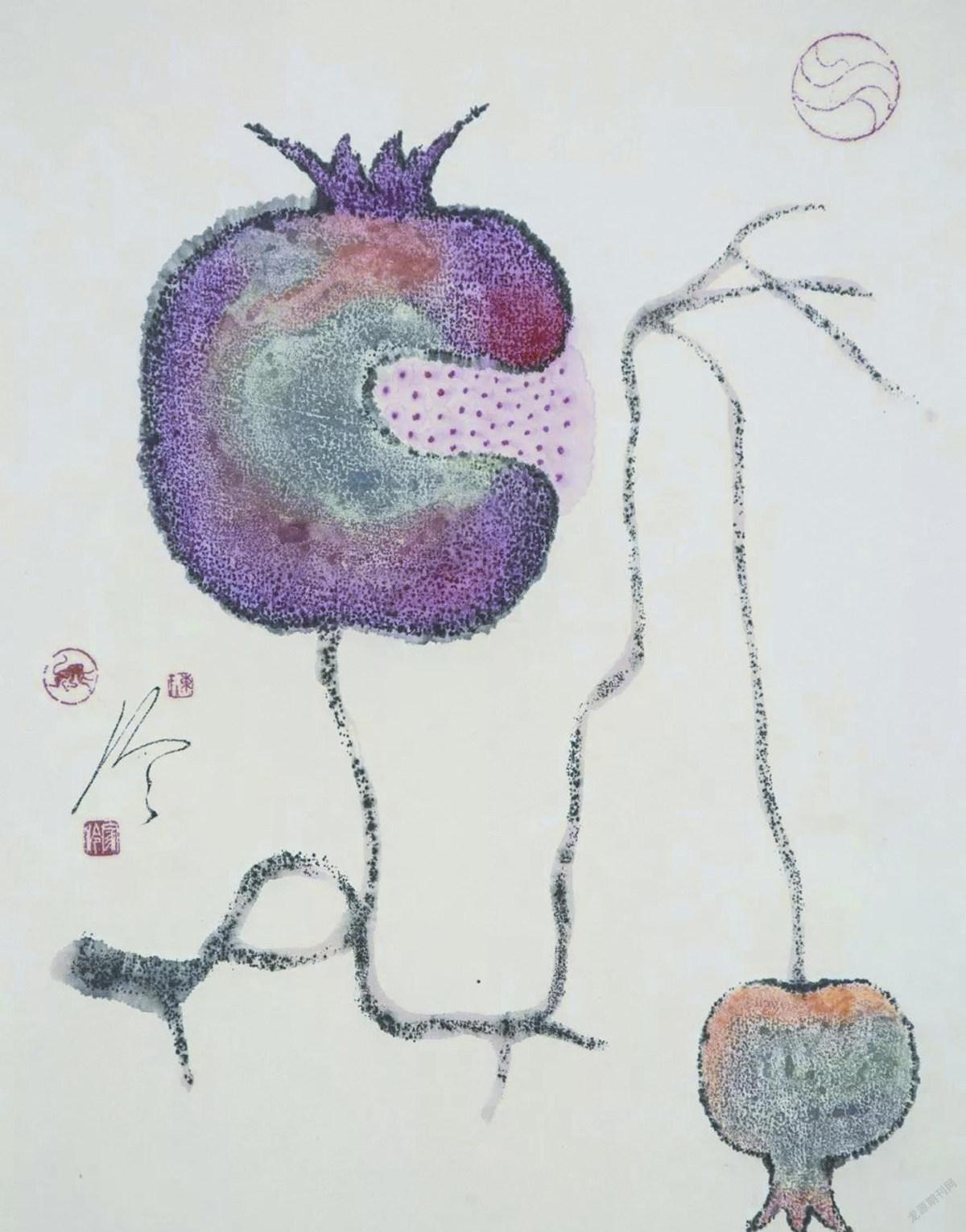
现代水墨画/陈家泠。陈家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吸收中国古代壁画和外国水彩的技法,且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和实践,创造出了具有中国哲理性,兼有印象派、抽象派及表现主义特点的现代国画新流派。
摘要:孙频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怪物”。他们并不是形体怪诞可怖的“怪物”形象,而是心理极度扭曲变态的“怪物”。“怪物”不仅是指人的心理的扭曲变形,而且是指小说叙事的策略的怪诞。在残酷压抑的世界中,人逐渐丧失了生命的活力,退化为物。孙频敏锐地发现了人的这种“生命力的退化”,并以奇崛残酷的比喻和阴森恐怖的意象,展现了“阴阳人”怪物、动物性怪物、植物性怪物以及“女博士”等四种“怪物”。
关键词:孙频 “怪物” 植物化 女博士 “比喻之坟”
中外文学中历来不乏“怪物”,如西方神话传说中的异类、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物”,中国《山海经》中的怪物、神魔小说以及《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媚等异类。但这些作品中的“怪物”多是形体怪诞可怖的形象,而青年作家孙频极力展现的却是现代社会中心理极度扭曲变态的“怪物”。在这个残酷压抑的世界中,人逐渐丧失了生命的活力,或如惊弓之鸟般的小动物,或沦为几乎没有行动能力的植物。孙频敏锐地发现了人的这种生命力的退化,并以奇崛残酷的比喻展现了一出出光怪陆离的“怪物”传。在这里,“怪诞”不只是某种具象怪物,而是作家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种认识透露出作者对世界的某种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怪诞”是不可见的,亦是失语的,它无法现身说法。但孙频的小说书写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追踪“怪诞”痕迹的方式 :以具象化的“怪物”形象追踪“怪诞”。
一、“怪物”铸就的世界
孙频的小说乐此不疲地展现了数量众多的“怪物”。《祛魅》中介于“男人和女人之外的第三种性别”的李林燕,《乩身》中“残缺”的常勇(常英)、杨德清,《无相》中惊弓之鸟般的于国琴,《东山宴》中“眷恋”坟墓的阿德,《我看过草叶葳蕤》中“以性为生”的李天星、杨国红、无名女人,《色身》中的杨红蓉、白志斌,《圣婴》中的宋怀秀、胖姑娘,《抚摸》中的张子屏,《柳僧》中的倪慧母女,《丑闻》中的张月如等等。“怪物”的塑造在《松林夜宴图》中达到顶峰。孙频在这篇小说中描绘了怪物群像。这里有不断给死去的朋友寄送物品的外公,有诱奸男学生的大学老师李海音,有常年失踪的艺术家罗梵,有不断借钱不还的行为艺术家常安……孙频甚至为北京宋庄的艺术家们画了一幅群怪图。从某种程度上讲,孙频的小说世界正是由这些“怪物”构成的。本文将孙频笔下的“怪物”形象做了分类处理,以研究其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在孙频的小说文本中,人异变为阴阳人“怪物”、动物性“怪物”、植物性“怪物”以及特殊的“怪物”——女博士。
关于阴阳人的记录,最早见于柏拉图的《会饮篇》:“那时,人的性别不是今天这样的两种,而是本来有三种;这三者是男人、女人,以及男人与女人合一,这男女合一的,有一个与其双性对应的名称,当初是真的存在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阴阳人’一词如今也就变成一句骂人的话。”[1]柏拉图认为只有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人才是完整的。但在孙频的小说中,“阴阳人”是一种男权社会下对女性性别压抑而产生出的“怪物”。《乩身》中,“爷爷”收养了因眼盲而被遗弃的“常勇”,却为了保护她而压抑其女性性别并教之以算命为生。在男性性别压抑和女性性别认同的双重压制下,常勇变为一个雌雄同体的“怪物”。“她只能算半截人,另外的半截只能是介于鬼神之间的一种生物。”[2]而“杨德清”因遭受性行为的强行中断和羞耻而丧失性功能。这两个人做过马裨之后沦为彻彻底底的“怪物”。“因为无法准确归类,人们只好给常勇单独开辟出一个新的人种,那就是雌雄同体的阴阳人。” [3]无独有偶,《祛魅》中的李林燕在遭遇多次遗弃后背负着“作家的摇篮”的侮辱性的称号,但她反以无耻和剽悍防身。虚无感使她逐渐变成一个烟不离手、穿着军大衣的“怪物”。“当然,她不可能真的变成一个男人,那就是说,她将变成一个男人和女人之外的第三种性别的人,她将变成一种全新的生物。”[4]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女性性别的压抑,她们无法获得男性身份,但女性性别又得不到承认,只能沦为“阴阳人”。
动物性“怪物”也是构建孙频对现代世界中人的处境的独到发现。这种人的异化主题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有独到表现。正如格里高尔·萨姆沙异化为“甲虫”一样,孙频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也异化为动物、野兽。《无相》中的于国琴从山西小山村来到江苏读书,却因贫困受助于退休的老教师,在对无偿的资助和对母亲拉偏套的愧疚中,终日战战兢兢,就像卡夫卡《地洞》中的小动物,时时刻刻处在深深的恐惧和焦虑中,“像两只伸出触角接头的蜗牛”。《鲛在水中央》中的梁海涛在杀人后隐姓埋名、独居深山,像离群索居的孤鸟一般在逃亡和愧疚中度日,独自承受着罪与罚的煎熬。《因父之名》中的田小会因父亲的突然消失而饱受教师的欺凌,后竟主动寻求与残疾而丑陋的李段媾和。《我看过草叶葳蕤》中的李天星、杨国红、无名女人,皆像孤独的野兽,性爱是他们反抗绝望的唯一方式,是他们存在的唯一憑证。尤其是无名女人,她像一个流连在城市街头的猎人,猎取那些落魄的男人,通过不断的性爱来讨好他们,以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恐惧。当然,孙频的小说没有直接表现人的身体的变形,而是通过人的心理的异化隐喻性地展现“怪物”。
这些“怪物”在现代世界中的异化源于其深刻的恐惧体验。恐惧意识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的新的发现。在现代社会的运转机制中,人沦为卑微脆弱的小动物。卡夫卡甚至说,“我的本质是恐惧”。面对生活的动荡,这些脆弱的“小动物”只能嚎啕大哭或是泪流满面。孙频的文本中,每一篇都会出现“嚎啕大哭”或“泪流满面”等词,这正反映了其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认识。
如果说动物性“怪物”表现了人的异化主题的话,植物性“怪物”的塑造则体现了人的生命力的退化的主题。这在《色身》和《柳僧》中最为典型。《色身》中的杨红蓉屈身于丑陋的小商人白志彬,白志彬发现妻子不光彩的演员经历之后多次偷情,在一次意外车祸中成了“介于人和植物之间的一种奇异的生物”。杨红蓉在经历了恐惧的遐思、为了房子“出卖肉体”、为救治母亲花光所有积蓄终无法挽回其生命以及照顾植物人的丈夫之后,渐渐退化了生命力,成为一种“植物”,最终舍弃了追求一生而隐忍所得的房子,出门远去。这篇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刘亚丽。她是照顾植物人丈夫的第七个保姆,是杨红蓉的互补形象,母亲病逝时未能陪伴在旁,后因愧疚辞职以照顾病人为业。这两个女人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柳僧》中水暖村的人死后要在坟堆上插一根柳枝,千年以来,吸收了死人骨血的柳枝早已长成参天大树,这片坟场也早变为一片茂密的树林。动物性的人退化为植物性的人继续存活,暗含着作家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命力退化的独到发现。
此外,孙频的小说中还有一群特殊的怪物——女博士。《丑闻》中的梁姗姗、《光辉岁月》中的张月如、《自由故》中的吕明月等女性都是高学历的文学博士,但却都迷失在性的压抑和焦虑中。梁姗姗“失宠于”文学院院长,却堕入酒吧老板的桃色圈套。张月如在读博士时几番沦为情妇,返回家乡小县城后却再度陷入与文化局长的情爱纠葛中。吕明月为反抗学术圈的肮脏和平庸,退学后孤身逃亡德令哈,却也难逃沦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在这些小说中,“女博士”成为一个怪异的群体,她们失去了其作为女人的身份,沦为男人发泄社会阶层不满的兽欲的突破口。学历差距造成男性病态的情欲,当那些低学历的男人压着女博士的身体时候,就像“对着一顶博士帽在做爱”,隐藏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崇敬”。而高高在上的“女博士”成为男人眼中顶着一顶博士帽的怪物。然而,这些女博士也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她们敏感多疑、恐惧周围的一切,将自我内化为“怪物”。
二、“怪诞”意象的叙事策略
孙频的小说书写吸收了古典诗词的创作方式,构造出一个个鲜艳残酷而蕴含深意的意象。她似乎迷恋于使用“鱼”“坟”“尸体”“白骨”“不明生物”“蛇”“琥珀”“血色夕阳”“标本”“四只脚的怪物”“植物”等阴森恐怖的意象。这些“怪物”意象营造出一种残酷压抑的氛围,为怪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在《鲛在水中央》中多次出现了沉潜在湖底的“白骨”和“鱼”的意象描写。多年前,“我”和三个工友谋杀了工厂老板范柳亭,并将他锁在石头上沉入深山无名湖中。“我”外出奔走多年,却一直背负着杀人凶手的包袱,后来孤身一人隐居于深山废弃矿场,但却时常假借借书之饰看望范柳亭的老父亲。在潜逃与愧疚的双重压抑下,异化为一个在深山和小镇中穿着洁净的西服的怪物。
“在这湖底还有一具人的尸体。那具尸体在这么多年里一直就沉在这水底,是因为,他身上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是石头把他锁在了湖底。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完整的、新鲜的,还是一个人的形状,呈现出石灰一样僵硬的滞白。等我第二次再潜入湖底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变得残缺不全,鱼儿们把他身上脸上咬得坑坑洼洼的。他的一只眼睛被鱼吃掉了,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大洞。右手上的肉已经被鱼啃噬干净了,露出了雪白的骨头,那只露出白骨的手就那么在水中安静地张开着,还有几只一寸长的小鱼正叮在那手骨的缝隙里觅食。”[5]
在这里,“白骨”的意象将“我”对自我罪孽的恐惧与惩罚实体化。这种恐惧与惩罚甚至实体化为锋利的凶器,仿佛“我”只有裹紧身上的西服才能掩藏自己,才能躲过自我心灵的拷问和现实世界中的追捕。在这种极度的压抑下,“我”甚至对鱼也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源于恶心,而这种“恶心”又与萨特《恶心》中那种甜腻而不适的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
“鱼”的意象在《因父之名》中得到了更为令人窒息的阐释。在田小会看来,那两只长着四只脚的古老生物就像四脚怪物一样默默地注视着她。为了充饥,青色的鱼吃掉了伙伴的四只手脚。怪诞的气氛立刻充斥着整个世界,恶心和恐惧吓得田小会嚎啕大哭,嚎啕大哭成了她应对恐惧的唯一举措。《东山宴》中生长在粪池中的鲇鱼在臭气熏天的粪池中竟长得十分肥美,惹得山外的人十分羡慕。村民们感觉站在粪池边看鱼就像站在湖边观鱼,“风雅得很”。这里的“鱼”又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暖水村的人竟将其当作红白喜事中餐桌上的美味。尤其在白氏去世后,村里人为了纪念白氏喂养鲇鱼的功德,将所有粪池中的鱼都捞出来煮了,美美地享受了一顿“东山宴”。这里透露着作者对死亡的深切关注。
在《柳僧》和《东山宴》中,“坟”的意象得到了充分地展示。《柳僧》中的水暖村,每个去世的人都要埋葬到树林中,并在坟堆上插根柳枝。“所有的柳树都是从一个坟堆里长出来的,这样看上去这些树好像是从坟堆里爬出来的巨蛇,正相互交错着向半空爬去。”[6]這里的“坟”更像是对人的生命本质的探索,人最终融入土地,在柳枝上延续新的生命。在这里,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动物性退化为植物性,人沦为带有植物属性的“怪物”。植物也变成吸收了人的血气的“怪物”。而“母亲”和水暖村的人们却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习以为常。高大葳蕤的柳树仿佛是人的旺盛生命力的象征,又像是人的生命退化为植物的暗讽,体现着作者对生命的独特沉思。《东山宴》中的人更是住在坟堆山头的对面,只要抬头就能看到对面西山上的那些新坟和旧坟。傻子阿德终日流连在坟场追寻母亲的遗温:
“可是,这傻子只要一看到往土里埋人,就立刻两眼放光。谁家办丧事往坟地里抬棺材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个闻着气味跟过去,辛勤地像蜜蜂一样一路叮着,跟到坟地里一直看着棺材埋进去。等到众人都散去了,他还戳在那里不肯走,像坟前的石碑一样肃穆安静,是所有葬礼中最忠实的看客。每次,他站在人堆里,大睁着眼睛,伸长着脖子,嘴半张着,粉色的舌头像狗一样半耷拉出来,一眨不眨地盯着每个葬礼的细节。他表情贪婪狂热地看着这个埋葬死人的过程,就像一个学徒抓住一切时机在偷窥师傅的绝技,一心要早日学到自己手里。”[7]
最终在唯一的亲人——祖母——去世后,阿德像鸵鸟一样一头扎进了祖母白氏的坟堆,开启了死亡之旅。在这里,“坟”的意象展示了盘旋在人们头顶的死亡焦虑,仿佛死亡才是获取救赎的唯一道路。
正是这些“怪物”意象群拓展了小说表现的向度,构建出一个极度变态压抑的怪诞的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中,孙频笔下的“怪物”才有了生存环境与依据。这些意象也是人物心灵感受的外化,只有以这种“怪物”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世界才是扭曲的、怪诞的。也只有借助这些意象我们才可以走进“怪物”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怪物”的人与“怪物”意象的相互塑造中,我们才得以管窥作家对现代世界的某种真相的认知。
三、“比喻之坟”:“怪物”的生成
“怪物”意象的叙事策略之外,怪诞奇崛的比喻也是小说中“怪物”生成的重要机制。孙频的小说文本中充满铺张的比喻,如“她像某海报深处一个巨大的孤单头像一样每天在他们面前招摇,仅供他们瞻仰和揣测”[8]。血色的夕阳、形形色色的怪物、变态的性欲等构建出一个声色张扬的荒诞世界。这样一个变态、扭曲、怪诞且充满着怪物的世界,只有在铺天盖地的怪诞的比喻中才能得到充分展示。在这种视域之下,一篇篇小说就是其构筑的一座座“比喻之坟”。孙频的比喻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有意识地塑造怪物形象的基本策略,是一种怪诞世界的组织形式,更是其作品中深刻的现代主题的独特呈现方式。琳琅满目的比喻,恰好说明了这种深刻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具体而言,其比喻主要有以下几种功能。
一是塑造怪物形象。如对《丑闻》中的张月如的描述:“在那十分钟里,她全身的毛孔张开,像一株植物一样吸收着那间办公室的呼吸、声音和光影。”[9]对《杀生三种》中的伍娟的描述:“她愿意守着这种缓慢的日子,感觉自己就像被装进一种容器,容器是什么样的,她就跟着长什么样。”[10]对《骨节》中的夏肖丹的描述:“她就是一颗从这城堡里长出来的植物,不管她的枝叶能长到哪里,她的根就囚禁在这城堡里。”[11]又如对《假面》中的李正仪的描述:“甚至在雨中急走了几步,像是刚刚嫖完的嫖客生怕被人认出来一样。”[12]前文所述“怪物”的“恐惧意识”和生命“退化现象”,正是通过这些鲜血淋漓的比喻隐喻性地展现出来。孙频小说中的“怪物”在形体上与常人无异,但心理上却极度变态扭曲。作家在对“怪物”心理描写之外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即是通过比喻,将人物内心的扭曲外化出来。
二是将人对世界的感觉实体化。如在《醉长安》中的描述:“这缕不安像若有若无的蚕丝一样绕着她,缠绕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13]对《松林夜宴图》中的外公的描述:“这兴趣(对吃的兴趣)长在他身上,像身体上发育出了一只硕大无比的畸形器官,简直要比四肢比脑袋还要显眼。”[14]在《同体》中的描述:“原来,她对他的依恋已经像巨大而邪恶的树一样牢牢地把她吸附住了。”[15]在《因父之名》中的描述:“她所惧怕的东西就这样逼真地现形了,并在她面前缓缓长出了手和脚,如一个新的可怕物种。”[16]这些怪物都具有近乎变态般的敏锐的感觉,他们时刻能感受到世界的恶意,并在这种恐怖的感觉中卑微地苟活。通过夸张的比喻,人对世界的感觉变成了实体,而且与人的身体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产物便是“怪物”。
三是营造一种残酷血腥的氛围。孙频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夕阳都是“血色”的,而这种血红色的夕阳几乎出现在每一篇小说中。如在《鲛在水中央》中的描述:“我想起了那天站在黑龙峰上看到的无名湖,它像一面小小的镜子一样裸露在大地上,反射着血红色的夕阳。”[17]在《天体之诗》中的描述:“金色的木马背后是月球一般荒凉的工厂废墟,废墟的背后是一轮血红色的夕阳。”[18]在《因父之名》中的描述:“前面就是县城边上的鱼塘了,整个血红的夕阳都要掉进水里了,整面池水泛着粼粼血光。”[19]在《光辉岁月》的描述:“似两个不要命的骑士,纯为了追逐那马上要落山的血色夕阳。”[20]在《东山宴》的描述:“这个黄昏,夕阳壮硕如血。”[21]这些艳丽的比喻构建了一个血淋淋的世界,为怪物们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也只有在这样残酷压抑的世界,才会产生这些怪物。这些比喻营造出的残酷氛围,使小说弥漫着一种沉闷压抑而怪诞的气质。
总体来看,孙频的小说创作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和20世纪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怪诞的创作特征,而又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具体而言,其笔下的“怪物”和卡夫卡《变形记》《地洞》等小说中的格里高尔、无名小动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孙频完全放弃了“卡夫卡式”的形体上的异化叙事,而是关注人的生命力的退化,并以奇崛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其创作可能更接近“新感觉派”的那种声色张扬的“上海现代小说”。怪诞的“怪物”意象、奇崛的比喻以及残酷的叙事,共同构建出生存于怪诞世界中的一个个鲜血淋淋的“怪物”。这些“怪物”的呈现,透露出作家对现代世界的某种认知以及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意]翁贝托·艾柯.丑的历史[M].彭淮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07-130.
[2][3][4][7][8][16][19][21]孙频.盐[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2,5,199,59,331,341,328,98.
[5][17][18]孙频.鲛在水中央[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7,103,121.
[6][9]孙频.疼[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201,220.
[10]孙频.裂[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62.
[11]孙频.骨节[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52.
[12]孙频.假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
[13]孙频.鱼吻[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1.
[14][20]孫频.松林夜宴图[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8,130.
[15]孙频.无相[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201.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