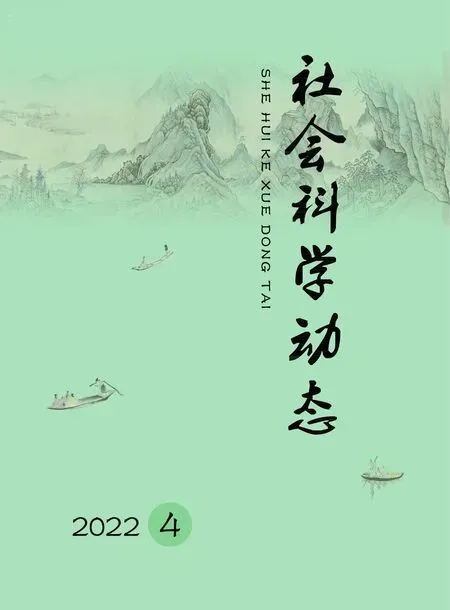我心中的好老师
——冯天瑜先生指导我学习思考的点滴回忆
2022-02-02张艳国
张艳国
在中国传统话语语境中,“老师”(或称“师父”)是一个内涵丰富、崇高而神圣的字眼,具有极强的社会生活意义和文化学意义。没有人能够生而知之,也没有人能够无师自通,都需要老师指导、教诲和训练,得到人格提升和技能提高。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论述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①这是从教与学关系的一般意义上讲老师的职责和功用。若要从更高的意义和价值上衡量老师,察考其师德、师技、师能和师长,像我国伟大的教育先行者、思想家孔子那样,“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②,教育人的文化,塑造人的品性,培育人的忠厚,格律人的忠诚,并且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③,这则是“老师中的老师”,堪称“好老师”的美誉了。“好老师”当然是教师中的翘首,如先师章开沅先生所说:“这种无声的师,不自以为师而人尊之为师的师,乃是最高层次的教师,潜移默化的教育,其精英堪称万世师表。”④
我追随冯天瑜老师学习已久,从1985年我入职《江汉论坛》杂志从事史学编辑算起,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从“门外”追随冯老师,到“入门”请益冯老师,冯老师留给我感人、温暖、受益的场景历历在目,这些都一一有序地温润地储存在我的脑际,随时有用。每当回忆冯老师指导我学习思考的点滴片段,体会自己从中所受的教益,我非常感恩有幸受到冯老师点拨教化,总是感叹:“遇到冯老师真好!得到冯老师教育培养,真是我一生的造化!”而冯老师在我眼中,是一位“德艺周厚”、具有古时儒者之风的老师⑤,我将冯老师视为当代教育界的“好老师”。
2001年初夏,经过章开沅先生、严昌洪老师三年悉心地指导、培养,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当时,冯老师既被章先生礼聘为我的博士论文《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的评审专家,又是6月4日本届博士论文答辩会主席。5月20晚,我将论文送到冯老师府上,请他审阅。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紧张的。冯老师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紧张情绪,招呼我坐下后,并不急于与我谈论文,而是与我交谈近来的工作。在我的情绪稍稍平复后,他才慢慢地翻阅起我的论文来,表现出一种温和而严肃的表情。在翻阅中,冯老师就他感兴趣的问题询问我,其间不乏肯定和鼓励我的话语,足足交流了半个多小时,还询问了我出席此次答辩会的其他专家,并嘱咐我认真准备,努力答出学术内涵来。从冯老师家出来,我紧张不安的情绪一扫而光,受到冯老师温和关切的情致感染,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充满自信和轻松的感受。
6月4日的答辩会分为上午和下午2个半场进行,我的论文被安排在上午半场答辩。在上午的答辩过程中,冯老师作为答辩主席掌握会议的节奏和调理会议的气氛,很有艺术性,效果很好,会后受到章先生赞扬和感谢。应邀参加我们答辩的老师,个个都是饱学之士,而且学风严谨,对于这场答辩做了充分准备,个个精神饱满,特别是校外专家更是精气神十足,对于他们认为研究不充分、表述不准确或者论文挖得不深不精的问题,往往抓住不放,穷追不舍,刨根问底,而学生最后在“禁不住问”的时候,自然面有羞色,难免流露尴尬之情。这时,也正好是阶段性落场之时,冯老师进行总结。只见冯老师微笑着温和地说:“老师追问的问题,正是有待继续研究完善之处,这是一种有益的提示和强化性强调,不必难为情。学无止境,贵在精益求精。”经冯老师这样一说,整个会场如同春风吹过,满屋子冷峻的气氛回归平和。现在想来,答辩中专家追问,唇枪舌剑是必然的,无可厚非;像冯老师作为主持人这样温润智慧,也是必要的。因为,再精彩的大戏,也需要剧情整合和合理调节。我因为在答辩前得到导师组老师较多肯定性评价,原以为答辩能“轻松过关”,不想在答辩中也遭遇了猛烈的“学术炮火”。开始时颇为慌张,慢慢才跟上答辩节奏,进入状态。对于我开始时的紧张情绪,冯老师也像对待其他同学那样,时有善意的提醒:“不要紧张,更不要慌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就好。”这对于答辩人稳定情绪、保持定力,还是很有效果的。也可能由于专家们对我的论文选题感兴趣,在提问讨论环节,汇总起来,有20多个问题。数量较大,这让我显得为难。能否扼要准备,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正在我犹豫不决之时,还是冯老师给了我好的建议。他微笑着说道:“艳国,这样吧,综合各位老师的评论和提问,你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再结合你的论文准备一下吧。第一,你在文中说‘全盘反传统论’是近代西方文化哲学模式与历史哲学模式影响的结果,那么,这种模式为何物?你是否建立了一种‘破与立的文化模式’?第二,你在文中说要给予五四时期评孔批孔文化运动予以时段划分,这样‘更可靠些’,是何指?第三,你在文中说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不为研究者所重视,是何确指?第四,你在文中关于杜亚泉文化观的评价与当前学术界的一些评价有所不同,为什么?你看这样好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简直太好了!在问题集中后,我便认真进行思考、梳理;在学生答辩陈述环节,我的回答得到老师们肯定。
答辩结束时,冯老师代表答辩委员会宣读了评议结果,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特别珍贵的是,我的论文答辩决议,是由冯老师亲自起草的,词语中洋溢着对青年学子的激励和爱护之情:“论文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宽阔的视野;占有材料比较丰富,对材料的勘比、剖判也颇为用心,加之文笔畅达、富于生机,使全篇较好地实现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的相济。总之,这是一篇成功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博士论文”⑥。正是因为答辩专家们的肯定,我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年度优秀学位论文,我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并获得了“野泽丰奖学金”。更为关键的是,冯老师的“专家评语”和代表答辩委员会宣读的“答辩决议”,激励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坚定地走下去。
在答辩过程中,我再一次受到冯老师谦和、博雅的君子之风熏陶和教育。他既不放松答辩要求,而又体现出对学生的同情共感。他在答辩中勉励我“将答辩中讨论的问题作为今后研究的思想题材,多加留意,予以深化”,是指导我完善论文的重要意见,我十分珍惜。在整个答辩过程中,冯老师都是既严肃认真,而又温和包容的。这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难道这就是我们常说“好老师”所具有的儒雅,“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吗⑦?
我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心想着做博士后研究。我心中的理想导师是冯老师。为了慎重稳妥起见,我专门征询了我的博士导师章开沅先生和严昌洪老师的意见⑧。他们一致认为,冯老师是合适的人选。特别是章先生说:“你在冯老师的指导下,一定还有大的进步。”这句话鼓舞着我,坚定了我跟随冯老师做博士后研究的选择。在章先生、严老师的推荐下,我专程拜访冯老师,当面表达我的申请。因为有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期间感受冯老师对我关怀的经历,我这次提出申请,还是蛮有信心的,一扫上次送呈博士论文时的紧张和惶恐。冯老师在批准我的申请后,对我做博后研究的思想准备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冯老师说:博士后研究,重在研究,贵在创新,不要做一般性研究,不要为了“做博士后”而“当博士后”。下决心做博士后研究,就要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找准问题意识,深化下去,取得有厚重感的学术成果。冯老师的语气平和,但要求明确,指向具体。我理解,冯老师平静的指导,具有鞭策我前进的千钧之力。这次谈话,使我明确做博士后研究的科研方向,围绕博士论文与博士后研究选题的对接口做足文章,在寻找问题意识和突破口上狠下功夫。
在冯老师的指导下,入站手续办理是顺利的。特别是进站评议会的准备,冯老师特别指导我,要逐一登门请教参会评议的老师,提醒我在登门请教时主动报告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以及在读期间取得的研究进展,并适当介绍进站后的科研准备。在冯老师指导下,我三次登门向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朱雷教授进行深度请教,每次都得到朱雷先生的亲切鼓励和热心指点。因此,我的进站评议会开得很成功,老师们都对我进站研究表示了欢迎,提出了要求,提点了问题。我能够顺利进站,这与冯老师周全地考虑,特别是冯老师一贯要求自己克己待人、谦逊低调的作风学风,是密不可分的。那时,一些博士说,武汉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门槛高、要求严、进门难。他们常有畏难情绪流露。可见,人的主体作为,是要辅以积极条件的。而我得以顺利地入站,能够在充满喜悦的情绪下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不能不说得益于冯老师在学问之外对自己严格要求,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生态和人际环境,他对博士后流动站其他导师发自内心的尊重真诚和待人处事的周到细致,一直得到他的同事们好评。这对我来说,终生有益,终生受用,人生的大智慧往往体现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上。
进站后,我和冯老师就博士后研究的问题意识很快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博士论文研究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思潮围绕孔子学说进行“破”的问题,博士后研究就是围绕五四时期文化新人所做的“立”的工作,将破与立结合起来,形成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思潮演进展开的一个对立统一的完整体相,形成一个五四时期思想演化新陈代谢的个案亮点。冯老师在明确问题意识、目标导向和研究进路后,在选题的拟定上,显得很慎重,与我多次交流讨论。冯老师说,从学术话语表达上,围绕“立”,使用“开启现代之门的理论借取”,就突出了“借取”这个关键词;从指向明确上,显示“立”,使用“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唯物史观思潮互动性研究”,就突出了“立”的载体与表现——唯物史观。冯老师表示,如何定选题,由我思考后自己定。我感受到,在指导我的研究中,冯老师既是严谨认真的,又是民主开放的,他鼓励我比选,而不代替我决策,有利于我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我做好全过程研究,在敬畏学术、潜心学术方面,是很有教益的。
在冯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经过三年研究,“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唯物史观思潮互动性研究”报告最后顺利完成。2006年1月9日下午,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时,冯老师担任中心主任)举行了博士后研究报告答辩评审。历史系和中心的敖文蔚教授、陈锋教授、张建民教授、李少军教授和谢贵安教授应邀参加,他们在冯老师的主持下,组成了答辩评议委员会。老师们充分肯定冯老师指导我在研究中,问题意识强,博士后研究报告与博士论文联系紧密,重点突出,有时代感,对于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具有新的、积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体指出了一些有待深入研究之处和值得商榷的问题。冯老师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既综合了各位老师的意见,又突出表达了他对我这份研究报告的评价:“艳国的研究做得比较深入,是短时段思想史研究的结晶。研究报告围绕五四思潮的充分展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意识与思绪思路在破与立上展开,解证问题的深度与厚度相兼顾,思想理路清晰可见。问题的选择具有现实性、实践性,研究走向与时代思考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学术研究与现实性研究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要善于从现实的思想纷扰中摆脱出来,要重视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角度研究思想史、文化史问题,不要过多地回答现实理论问题,坚定明确地做‘史’的研究。譬如说,还有一些值得深究的学术问题:李大钊从日本学者那里学习了哪些概念、知识,他是如何运用的?明治时期日本学者所做相关性研究的程度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鲁迅曾对李大钊作过一个评价:守常先生的学术未必精当,但却为社会所需要;他的遗文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如何对此进行学术定位?唯物史观为什么会在李大钊身后风靡中国学术界?对于这种现象的描述,值得进行更加深层次地研究。特别是当时关于科学与迷信的讨论,也值得我们关注进来,加以研究。总之,这篇研究报告值得肯定之处甚多,为深化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希望艳国继续推进,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多成果。”
冯老师的这段话,我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踏踏实实地装在自己的脑海里储存起来,生怕有所遗漏。冯老师和专家们对我的研究报告给予充分肯定,研究报告也被评为“优秀”等级、我被评为武汉大学年度优秀出站人员并获得奖励。这既是冯老师精心培养教育我的成果体现,也是我继续前进的新的起点。更为重要的是,冯老师为我在出站后继续在学术研究上探索前行,站在更高的学术视野上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指明了正确的努力方向。从已有的研究开始,坚定地走深走远,对于一名青年学者准备献身学术研究来说,这是最为紧要的,也是最有意义的。
2016年寒假、2017年春节前夕,我从江西师范大学回到武汉,赶往冯老师所在的湖北省人民医院住院部病房看望他,特地带上了我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上题为《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的长篇论文。尽管冯老师重病在身,但他一如既往地处在思考、写作的状态之中,丝毫没有因为身患重病的疲惫倦乏与痛苦不堪。当时,他的兴致很高,在接过我手中的杂志后,非常高兴地翻阅着,还将他感兴趣的文字读出声,望着我笑,表情十分慈祥,释放的情绪十分饱满、给力。他说,“你带来的杂志及其发表在上面的大作,是对我最好的新年祝福。”我说:“感谢老师的教诲,我的小作受到了您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的深刻启发。”⑨冯老师连忙打断我的话说:“不,不。看得出来,你的这篇大作,是你博士后专题研究的继续深化。这些年来,你还没有放弃,继续深入研究,功夫没有白费啊。可喜可贺!”冯老师既谦虚,又看得很准,可谓一语中的!真是“了解学生莫如其师”啊!
这些年来,我牢记冯老师在博士后出站答辩评议会上的总结讲话,遵循冯老师关于学术研究要重视“后续研究、继续推进”的教导,锲而不舍,终于收获了劳动成果,尝到了接续努力的甜头。冯老师对我的教育培养,充分体现了做一名“好老师”“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深厚情怀⑩,所谓为师者要有仁者之心,做到教学相长1⑪,无非是在提升自己的同时,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看问题想办法,通过教育达到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目的。在实践中感悟我的亲身经历,这对我传承冯老师“好老师”的育人精神,具有示范意义。
冯老师成名很早,学术成果丰硕,赢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尊敬和尊重。在常人看来,冯老师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极大成功,一方面源于冯老师的勤奋努力,他常年孜孜不倦,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师母刘老师曾不无诙谐地评论他说:“冯老师做起学术来,有瘾”;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冯老师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反应力,他的朋友们常常不无羡慕地评论说“冯老师聪明绝顶”。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这样认为,觉得做学问要勤奋+聪明,甚至认为具备超强的记忆力,在治学中是主要的。直到前不久,冯老师在来信中对我进行训示,使我顿开茅塞,明白了做一名出色的职业历史学家,究竟应该具备什么?2020年9月4日上午,冯老师在来信中,这样说道:“艳国君好!做史学研究,诚如你言,记忆力重要。然不必过多地寄望于天赋的记忆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感悟力也至关紧要。而这种感悟力的获得,除部分凭记忆力赐予外,更多地则是依靠研史实践中理性思维的锤炼。至于史学撰著,记忆力提供某些基础,更赖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你在这三方面皆有优势,再下功夫定可再上层楼。”
这既是冯老师对我的教益,更是冯老师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进行自我总结的经验之谈,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学术研究中,使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有机结合、相互融通,这是中国学术史上大家、名儒素来提倡的学术理念、学术门径,也是冯老师一贯坚持的学术指向。早在1994年,冯老师在应邀撰写的一篇学术总结性自述中,专门论述了他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理解、重视和坚守:“清人姚鼐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从姚氏之言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一个以学问为事业的人(史学工作者自然也在其列),应当有理论准备,得以攀登时代的理论高峰,对错综的研究对象获得理性的真解和创造性的诠释;应当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占有丰富的材料,并具备辨析材料的能力,所谓‘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记无不达也’;应当锤炼语言,长于词章,有一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追求。姚鼐提及的‘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是我近十年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的所在。……‘义理、考据、词章’不仅各具独立价值,而且,理论指导、材料辨析、文字表达等三个方面的能力缺一不可,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相济’而不得‘相害’。以史学而论,忽视史料的占有与考证,其义理不过是空中楼阁,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没有理论思维,所占有的史实也只是一堆原材料,无以建构伟岸的大厦……此外,有义理与考证功力,如果文章苍白乏力,也难以成就良史,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反之,擅长文章表达,却缺乏义理考证功夫,则不过是花拳绣腿,上不得真阵式,而且还会以文坏史。古来忌文人修史,文人修志,即是防范这种情形。”⑫
难怪冯老师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都着重强调“义理、考据、辞章”在治史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价值,这实在是他承续古人而又发扬光大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由此看来,勤奋也好,聪明也罢,包括超群过人的记忆力,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外功”,而不是“内力”;治学,真正的内力乃在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有机结合,有了这个内力,外功才起作用。这应当是治学,特别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法门和应予遵循的学术准则。
“好老师”当然也是老师,但是,他的确比一般的老师要高明得多,要了不起得多!冯老师在言传身教中所彰显的“义理、考据、词章”相互融通、相得益彰的这一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实际上贯通了古往今来一切优秀学者所坚守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方法⑬,具有打通古今、超越传统的重要实践意义。这对我们所产生的教益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更值得我们在治学的实践中细加体会,随时遵循,学以致用。
在与冯老师交往、追随冯老师求学求知的几十年历程中,我既受到冯老师严谨治学的学风影响,又受到冯老师诲人不倦的人格魅力熏陶。作为个体人物而言,冯老师具有“好老师”的品质情操和文化内涵,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存在。但是,冯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热爱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他既有历史感,“追究历史”;又有现实感,“考察现实”⑭;而且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觉性和自豪感归宿感,坚信“中华民族正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诞敷文德’”⑮,他像古人的史学情怀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⑯,这就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了,而应该就是一种必然产生了。在冯老师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历史、文化发展与士、君子道德承载的必然性,无论如何,都是任何一个时代一切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心向往之”的。
良师之风是教师长期积累的善美风尚,内涵品德、情操和育人理念。“教师的良好风范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功能,而是长期刻苦磨砺形成的优秀素质,包括思想作风、道德操守、文化素养、生活情趣等各个方面。”⑰良师之风又会风行草偃,春风化雨,润物发生。俗话说得好,“一落叶而知秋,一滴水能成冰。”尤其是在冯老师身上所映现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德、“天梯度与有志人”的君子之风、“终生追求从不懈怠”的君子之行,把“好老师”的使命担当扛在肩上的教育实践、文化实践,理所当然地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具标志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典范,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应予珍视的榜样。
衷心地祝福冯老师八十华诞!老师健康,学生幸福,学术界大幸!
注释:
①⑯[清]吴调侯、吴楚材编:《古文观止》下,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246页。
②③⑦⑩⑬张艳国:《〈论语〉智慧赏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114,125、139、110、116页。
④⑰章开沅:《春风化雨 桃李芬芳——向第一个教师节献词》,参见周挥辉、曾艳编注:《20后寄语90后——章开沅小品文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⑤张艳国:《〈颜氏家训〉精华提要》,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72页。
⑥参见张艳国:《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附录二,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⑧ 《礼记·学记》说:“择师不可不慎也。”此之谓也。
⑨冯天瑜:《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⑪ 关于“教学相长”,如《礼记·学记》所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⑫冯天瑜:《地老天荒识是非》,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4页。
⑭⑮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8、8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