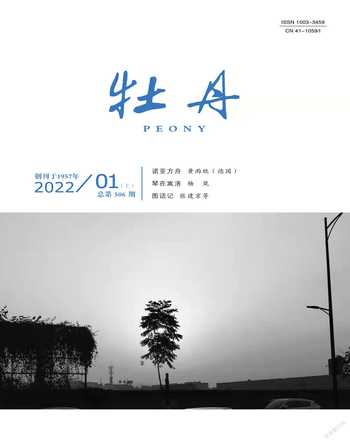让鸟雀飞
2022-01-20卢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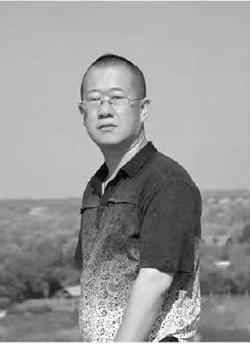
燕子
村民说,如果一只鸟儿愿意把巢建在自家树上或者屋里,那是家人的福气。就是这样口口相传的朴素观点,让一代代村人,种树庇荫,与鸟为善。
燕子飞来的时候,乡村就进入了三月,或许是在某场细雨后,你一抬眼就发现眼前有一团黑色的剪影,伴随着“唧唧”的几声鸣叫,迅速地掠过。而此刻,柳枝已抽出了绿芽,风也柔和了许多。它们灵动、轻盈、俏美的身影,给乡村这幅静美的水墨画卷带来了生机。我们无法说得清,整个冬天燕子去了哪里,但它们跋山涉水的归来,依旧识得旧时的窝巢,总令人生出几分敬畏。在乡村,燕子是众所周知的益鸟,它们以蚊、蝇等昆虫为食,它们巢于檐下,房顶等处,秋去春来的燕子被视作吉祥物。只要有燕子在屋内筑巢的人家,不管何时出门,总会把门留条缝儿,以方便燕子飞进飞出。
乡下有句俗语叫“宅子现四喜,家中出能人”。四喜指的是,枯木发芽,铁树开花,堂前飞燕,蜘蛛吊丝;而堂前飞燕被村人看作四喜中最大的喜事。为此,凡是有燕子筑巢的人家,即便外出也会把家门留条缝儿,以便燕子进出。诗人笔下的燕子颇多溢美之词。宋诗人葛天明《迎燕》写到:“咫尺春三月,寻常百姓家。为迎新燕入,不下旧帘遮。翅湿沾微雨,泥香带落花。巢成雏长大,相伴过年华。”诗人笔下的燕子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主人也“不下旧帘遮”,热情地迎接燕子的归来,和刘禹锡笔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颇有异曲同工之效。
这些腹部白色羽翅辉蓝色的燕子,因为在村民屋檐下筑巢,所以也叫家燕。春天,乡下村民的屋檐下确实有燕子成双成对地衔泥筑巢,咿咿呀呀,你侬我侬,给人亲切自然之感。可燕子娇贵,也有“不进寒苦门”的说法。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因为家中穷困,我家的茅屋土房里,从未有燕子光顾。而邻家的青砖瓦房的屋檐下,每年都有燕子出入。这对于家人来说,是件难堪的事。
杜甫在《绝句漫兴·其三》写道:“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 江燕明知主人的茅斋低小,却频频进扰,连主人也难以容身。而且它们衔来的泥污、飞虫,时常落在主人身上。杜甫发出燕子好像也欺负人的感慨,颇耐人寻味。不过燕子在屋内筑巢,弄脏墙壁,粪便落到屋内或者人身上确实是常有的事。为此,村民会在燕子巢下,挂上一个简易的挡板遮,可效果并不太好。令人奇怪的是,如果一只雏燕从窝巢内掉落到地面,即便主人将它再次送到窝巢,它的父母也不會接纳它,依旧会把它清出窝巢。这只雏燕是因为争食遭到惩罚,或者因为弱小被挤落而自然淘汰,还是它沾上了人的气味所致?这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居住的这座城里,还有一种燕子叫雨燕。春日里很少见到它们,夏日闹市中,尤其在雨前或黄昏时刻,时常可见它们成群结队漫天飞舞的身影,它们离人很远,很难看清它们的模样。它们一生总在飞行,速度极快,大约是世上飞行最快的鸟儿,只有在繁殖季,才会短暂躲进闹市木质阁楼的暗缝中繁养后代。据说,执行夜间飞行任务的飞行员,曾发现雨燕在高空边睡觉边飞行。我对这些鸟儿充满了好奇与敬畏,总感觉它们天生带着一种神秘而来,它们从不会辜负翅膀的使命。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在我看来,家燕是天生具有小市民气质的禽鸟,它们没有麻雀近人,没有鸽子清明,也没有乌鸦率直。它们软语呢哝、莺莺燕燕,借人檐下却不易让人接近。它们更像是生动的一个点缀,不管是在偏远的乡村还是在水墨画卷中。
麻雀
那日下楼,被一阵急迫扇动翅膀和扑通的撞击声音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误飞入楼道的麻雀,急着出去,把白白的玻璃当作了出口,结果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旋即又慌乱地飞入楼道,四处飞蹿。因为十分了解麻雀的脾性,我急忙打开窗户下了楼,希望这只麻雀可以幸运地飞出去。
童年在乡村度过。麻雀,鸟类的平民,乡村的邻居,我喜欢它们落叶色的玲珑身体和机灵劲儿。乡村有了它们而充满生机,童年有了它们而变得生趣。童年的乡村是清瘦的。稀落的村庄,高低起伏着同样稀疏的草房,多的是高大的树木与一簇簇狗尾草,有些长在草屋顶上,但同样活得生机勃勃,让人心生妒忌。大多的日子,农人们荷锄、担水、施肥,忙于生存。他们把孩子像动物一样放养,任由着孩子跌、摸、滚、爬。孩子们自会寻找乐趣,于是和麻雀成了朋友。
那时,地里的收成不是很好。往往一年,一家人也就收获几百斤麦子。在农人的眼里,那些黄黄的麦粒,显得尤为珍贵。每次,母亲把麦粒用水淘洗,待干后去磨面。淘洗后晾晒的这段时间,我便会被母亲派去看着麦粒,不被那些唧唧喳喳、时时觊觎麦粒的麻雀吃了去。那时,我便是麦粒的忠实守护者,麻雀则成了我眼中最大的“敌人”。最终的胜利者属于我,那些麻雀们毕竟胆小,一哄也就散去了,但这些偷食者们也有得逞的时候,偶尔得到几粒麦粒,也会兴奋地在树头上欢唱。
在农村,麻雀有很好的住处。草房的屋檐缝里是它们做巢的最佳地方。春天的时候,它们衔草安家,与人为伴。农人们日子很清贫,面对这有些吵闹的邻居,也不会有意地去侵犯它们。麻雀也怡然自得和农人们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日天刚亮,它们便开始了一天的欢歌,太阳落山时就会挤在树头相拥而眠。只是顽皮的孩子们,时常会踏着高凳,把手伸到草屋檐下,去掏它们的巢,有时会掏出几枚麻雀蛋,有时会掏出些小麻雀。只是这些小家伙们很难养活,它们的“气性”很大,往往养不了几天,它们便绝食死去,更别说成年麻雀了。
我一直无法说清,麻雀,这乡村忠实的陪护者,这些在我上小学、初中时,还一直在我上学路上唱着欢歌的精灵们,是何时悄然淡出我们视野的。清晰地记得,在我上大学一年级后的暑假,由城市回家乡时,我第一次有了警觉,乡村的路宽了、直了、硬了,草屋,狗尾草不见了踪影,树木也少了,也没有了它们成群飞来飞去的身影。即便有几只聚在一起,也变得胆怯,和留守在乡村的老人孩子一样成了乡村寂寞的背景。
麻雀纷飞的日子,越来越远了。在城市,我所遇到的麻雀,都是警觉的,不与人亲近。它们瘦弱而缺乏灵性。一年四季它们在城市高楼的夹缝与草木间穿行,它们将巣安放在石缝甚至高楼外壁挂空调里,仅为了生存就耗去了它们全部的精力。
麻雀,这乡村朴实的平民歌者,它们低微地蜷缩在城市的角落。在城市,我还真说不清,有哪种鸟儿愿意为一条喧闹的街道歌唱。
黄鹂
黄鹂鸟是真正的歌者,它们具备歌者所需的特质,除了具有美丽的外形外,它们音色完美、歌声婉转,且懂得知止。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是我最爱的诗句之一。我觉得,它传神地写出了乡村水墨画般动与静和谐之美。黄鹂鸟属中型雀类,体型比麻雀大出很多,麻雀是留鸟,黄鹂只有在春夏之交时,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身上长着橙黄色的羽毛,翅膀上的长羽是青褐色的,眼角和头部也有一圈黑色短羽,很漂亮。它们鸣声响亮悦耳,很是招人喜欢。尤其对于夏日赶路走累在树下休息的人们,听到黄鹂的鸣叫,那真不啻于一盏凉茶,令人平心静气。但黄鹂是一种警惕性很高的鸟儿,它们栖息在树上,以昆虫、浆果为食,几乎不停留在地面。当你循声去找寻它们时,它们要么闭口躲藏起来,要么迅疾地飞走。
美丽的黄鹂鸟和它醉耳的声音,时常成为诗人笔下歌咏的物象。诸如,“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新泥”等,莺歌燕舞,花香鸟语,万紫千红的自然风物场景总是令人愉悦的。但黄鹂鸟的啼叫声也会惹人心烦,“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黄鹂鸟清脆动听的歌声,对于一个思妇来说,是闹心的。它越是欢鸣,越让人内心不得安宁。不得不说,这世间的褒与贬,有时很难分辩。
黄鹂的筑巢技术十分高超,它们的巢是吊篮状的悬巢。它们胆子很小,它们不会选择显眼的高枝来筑巢。奶奶在我小时候,时常告诉我,不可以掏鸟巢,尤其是黄鹂鸟的。奶奶说,鸟天生就会除虫护林。乡村不能没有鸟,没有鸟的乡村是死寂无趣的。有的鸟,比如杜鹃鸟自己不筑巢,把鸟蛋下在其他鸟的窝里,让鸟妈妈代养。有些鸟是雄鸟筑好巢,吸引雌鸟前来交配、产卵。而黄鹂鸟是雌雄鸟一同筑巢,边筑巢边恋爱。有些鸟类在小鸟刚学会生存技能的时候,就会弃之不顾,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去了。而黄鹂鸟不会这么无情,它们和人类一样会时刻惦念着孩子。即使孩子已经能够独自生活了,它们依然会继续照料。这样就能够大大提高幼鸟的成活率,让幼鸟能够更加安全地成长。
有趣的是,黄鹂鸟有着很好的记忆力,它们会把曾经伤害过它们的人牢牢记住,并予以报复。村子里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个张姓村民,经常会受到黄鹂鸟的突然袭击,而和他同行的妻子卻丝毫没事。原来,几年前,张姓男子曾爬树掏了黄鹂鸟的孩子,当时黄鹂鸟夫妇,只能惊慌地在四周哀鸣。从此以后,黄鹂鸟产生了报复的心理。
村里的老人说,很少有鸟儿会主动攻击人。平常它们和人类和谐相处,但它们知好恶,爱憎分明。有的鸟儿对于伤害过它们的人,除了会袭击人还会往人的身上撒鸟粪。《诗经》写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看来,哪怕面对一只鸟,人也要时常反省自己的行为,与鸟为善,不为恶行,才能积累福德。
喜鹊
喜鹊是天生的喧闹者。
冬日萧冷。大多与人为邻的鸟儿都隐匿了身影。草灰的麻雀三五成群在小区低矮细密的花木枝丫与厚厚的落叶间寻觅食物。若不是偶尔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你很难发现它们。喜鹊却高调得多,它们扑腾肥硕的身体,油光锃亮的毛羽,时而立在光秃的枝头,时而在楼顶喳喳大声地鸣叫。即便是在微曦的清晨,它们也会在楼前屋后“喳喳”的追逐嬉闹,丝毫不在意与之为邻、善待它们的人是否被吵醒。“海边书托文鳞便,户外诗来喜鹊鸣。”“姓名已入飞龙榜,书信新传喜鹊知。”得益于有个好听而吉祥的好名字,在它们飞过头顶,它们响亮的叫声并不招惹人烦。人们往往会不由地搜寻它们的身影,内心暗暗自喜,今天我是不是好事将近了?
喜鹊聪明。它们最为聪明之处在于,它们与人为邻却并不与人靠得太近。
乌鸦喝水我未曾亲见,喜鹊喝水我是亲眼目睹过的。有人将大半瓶矿泉水放在马路边离鹊巢不远的树下,一只喜鹊飞来,它先是警惕地绕着瓶子观望,不一会儿便蹦蹦跳跳地跑到绿化带树坑出口叼颗石子,投入瓶子内。如此往复几次,喜鹊顺利地喝到了水。在它满足地拍着翅膀飞离时还留下喳的一两声愉悦的叫声。其实,鸟巢离湖水并不远,隔条马路就是,扇动翅膀不出半分钟,这只喜鹊就可以轻而易举喝到水,可它偏要费了气力,衔来石子对着瓶口饮水,实在匪夷所思。
喜鹊将巢建在荒无人烟的野外高树上,也建在离人很近的小区高树,也或高大的铁塔上。“鹊登高枝”寄托着美好的寓意,也是朴素的常识。从前乡村树木繁多,并不缺少高大的树木供喜鹊筑巢。但时过境迁,不知何时乡下粗壮的树木屈指可数了,鸟雀也渐少了起来。喜鹊将巢安在低弱的树上,老人们见了总不免叹息一番,毕竟覆巢之下无完卵。乡野嘉木渐少,就连鸟雀也免不了将就。老人眼里,鸟雀像一面镜子,它们的一举一动折射的是大地真实的影像。
我见过有人将鹦鹉、八哥、金丝雀等当作宠物来养,却鲜见有人养喜鹊。喜鹊与人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小区树木间有不少鹊巢,冬日,可供喜鹊食用的食物变少。小区内一块硕大的石头台面上,经常有些居民将半块面包、剩米饭等投掷在上面。放置不久,就会陆续飞来几只喜鹊啄食。可尽管如此,想靠近它们并不容易。往往离它们尚有段距离,便警觉地跳跃,拍打翅膀,飞到枝头或房顶上。
小区里的鹊巢,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初春,树木枝条尚秃,一只勤快的喜鹊忙着给老巢添砖加瓦。任是谁也无法知晓个中原因,这只喜鹊为何会喜欢上了一支尚有火星的烟头,并将它叼到巢内。巢最终轰轰烈烈燃烧了起来,所幸空巢里并没有雏鸟。鸟巢在燃烧近一半时,火熄灭了。支撑起鹊巢的枝丫被烧成黑乎乎的一片,那只喜鹊不见了踪影。没人知道,在以后的岁月,它是否会想起这个与它而言有些悲剧的春天!
喜鹊的领地意识极强且争强好胜。在野地,我曾见到在一处鹊巢附近,一只凶猛的红隼费了一番气力,抓住了一只倒霉的麻雀,停留在树枝上稍作喘息。这时一对喜鹊夫妇飞了过来,它们十分默契地用锋利的尖爪从红隼的头部和尾部发起进攻,红隼虽然凶猛,依然不敌喜鹊,最终抛下了口中的麻雀落荒而逃。喜鹊夫妇抢得了麻雀,一只叼着飞向窝巢,另一只则愉快地“喳喳-喳”的鸣叫,似乎在向他鸟宣告,谁才是这里领地的主人。
喜鹊也捕食麻雀、鸡仔等禽类。在我七岁时一个春日午后,母亲叮嘱我看管好一窝鸡仔,不要被野猫、野狗叼走。我搬了个凳子,拿了根竹竿坐在屋前,看着母鸡欢快地带着鸡仔们四处啄食,其乐融融。春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不一会儿我就放松了警惕。仅仅是一瞬间的工夫,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喜鹊,它迅速地落到一只毛茸茸的鸡仔跟前,用它的利嘴用力啄了那只鸡仔头部几下,随后抓起鸡仔便飞了起来。待我反应过来,那只喜鹊已经飞远,空留下懊恼的我。后来在我翻看有关鸟类的杂志得知,雄喜鹊在追求配偶时,时常会捕捉麻雀、鸡仔,或叼啄漂亮的花朵向雌喜鹊献殷勤。这确实是件有趣的事。
去年一个夏日午后,我在小区树下纳凉。听见一只喜鹊,一直“喳喳、喳喳”不安地叫唤。树下,一只狗儿在树四周搜寻着什么。忽地,那只喜鹊从树上俯冲下来,对着狗儿的头部一阵乱啄。见狗儿依旧没有离开的意思,那只喜鹊索性落到地面,一直跟随着它“喳喳”地警告,还不时用它尖尖的喙继续驱赶狗儿。
我很是好奇,抬眼望去,见在结有鹊巢的树上,几只小喜鹊扑棱翅膀不稳地飞跃。我内心满是钦佩。原来,喜鹊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乌鸦
在城里,我从没有见过乌鸦的身影。
至少,在我居住的這座城市,二十年来我未见过它们。离我见他们最近的一次,是三年前的春天,在贺兰山小口子。它们硕大乌黑的身影和呱呱的叫声,在明媚的春日阳光下,在突兀的群山间,显得尤其奇诡但合理。
因为,它们虽然不招人喜欢,但这世间总有一个地方属于它们。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乌鸦是种不吉利的鸟,老人认为它通常代表着死亡。五岁时,我认识了一只乌鸦,那是在奶奶坟地边的一棵大树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田野染上了一层苍茫的暮色,父亲跪在坟前。我眼前狂舞着燃烧后的冥币,像一群黑色而悲凉的蝴蝶。那只长满黑羽毛的大鸟站在树枝上,冲我转动着圆溜溜的大眼珠,我被吓哭了,它却异常神气地抖动丰满的双翅呱呱大叫着振翅而去。自那刻起,我知道它叫乌鸦。
上了小学,我见到一只聪明的乌鸦,在寓言《乌鸦喝水》里,那只乌鸦利用小石子,如愿以偿地喝到了原本喝不到的水。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篇称赞乌鸦的文章。自此以后,乌鸦总出现在凄惨恐怖的氛围中,比如“枯藤老树昏鸦”、比如鲁迅先生的《坟》、比如某些关于这战争的影片……
入冬,落了雪。老家只剩下三种留鸟。离人最近的是麻雀,不疾不徐地蹦跳觅食,它们的家在人的屋檐下。村庄外的杨树林子里,住着喜鹊也住着乌鸦,它们和人保持着距离,黑黑的巢擎在树枝上。而今,在我写着喜鹊与麻雀的文字时,我总不自觉地会想到乌鸦。只是,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乌鸦是不会来的。倒是人们喜欢的鸽子在楼层之上成群结队的飞翔。小区对面的楼顶,就住着一群鸽子。它们每天清晨都会呼啦啦地拍动翅膀一起飞起,盘旋,然后飞远,傍晚又飞回来。一年四季,从不爽约。我和门房那个看门的老头,争论过很多次。后来我承认,他说得对:鸽群看着还是那一群,但它们一定已经并继续经历着轮回。
说起乌鸦,人们总有贬损。什么乌合之众了,乌鸦落在黑猪上,还有乌鸦嘴等等。一种普通的鸟儿,被人加以不祥的寓意,和喜鹊相比乌鸦背的黑锅着实不轻。在日本的一所大学附近,有成群的乌鸦,它们在路上等红灯,红灯时把胡桃放在汽车的轮胎下面,红灯再亮,它们飞到轮胎下找压碎的浆果美餐。看来,乌鸦实在是一种聪明的鸟。《说文解字》里说:乌者,日中之禽。这样的解释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在古人眼里,乌鸦或许是得到太阳精华之鸟。有人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有人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人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也有人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哪怕面对同一个事物,人们总有不同的看法。人们为何厌恶乌鸦?在我看来,是因为乌鸦会给人们带来沉重。有多少人愿意直面沉重?
在荒无人迹的野山秃枝上,乌鸦除了出声粗俗不懂遮掩外,它们飞行甚是敏捷,飞起来的姿态也有些像雄鹰。只是它们不太懂得像人类那样选择生存环境,而是栖息在陡生凄凉的荒野也或墓地。试问,有多少鸟敢于直面这样的生存空间?有多少鸟敢于承认自己真实的灵魂?又有多少人能够面对痛苦的环境而坦然自若?
乌鸦能。它们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每一个抬头仰望天空翅膀的人,生命还有一种令人痛苦的形式,你永远绕不过它。
《夷坚志·驯鸠》写道:盐官县庆善寺明义大师了宣退居邑人邹氏庵。隆兴元年春,晨起行径中见鸠雏堕地,携以归,躬自哺饲,两月乃能飞,日纵所适,夜则投宿屏几间。是岁十月.其徒惠月复主庆善寺,迎致其师于丈室之西偏。逮暮鸠归,则閴无人矣,旋室百匝,悲鸣不止。守舍者怜之,谓曰:‘吾送汝归老师处。’明日。笼以授宣,自是不复出,驯狎左右,以手摩拊皆不动。他人近之辄惊起。呜呼!孰谓畜产无知乎?”一只熟养的斑鸠不但知近疏,且懂利害,不得不说,有着晶莹剔透羽毛、清澈明亮眼眸的鸟儿们自有灵性,是这世间的一面镜子。
让鸟雀飞,其实是同万物回归本性,一任自然。让心摆脱束缚,清明自在。
责任编辑 杨 枥
卢永,宁夏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当代》《星星》《散文百家》《朔方》《安徽文学》《美文》《六盘山》等刊,作品被《思维与智慧》《特别文摘》《少年文摘》等转载,入选《中国乡村诗选编》《稻花香里》等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