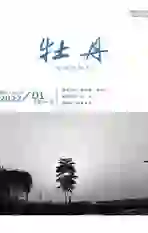秋风辞
2022-01-20陈元武

一
一切都松脆如干透的泥土,日子还在天上缓缓移动,秋天像一片黄叶般飘下。站在一棵树底下,能够充分感受到秋的悲伤之气,秋风像鞭子似的抽打着每一棵草,每一片树叶。
芦苇在秋风中瑟瑟发抖,它更像是谦卑的哲人,低下沉重的头,那硕大的花穗更像是即将收获的作物。像高粱,或者是糜子,或者稻穗。秋天就这么严肃低调,芦苇弯下身躯,弓成一道弧线。我试着问自己:倘若生命也如这秋天般悲壮而仓促,那么,生何有意义,死又何有意义?
宁静的空气流动起来,触碰到物体,就发出尖啸声,风就是这种流动的空气与草木相搏击的结果。秋天能够让人警醒:时光如水,人如漂浮的树叶,随波逐流,无一例外。有的人只是乘坐着高船大舰而已,依旧在河流之上。
季秋之际,阳光依旧热辣难耐,晒在身上,有些滚烫,带着锋芒。河边的漆树叶子已经开始发红,芦苇的花帜更像连绵的灰色的云,随时可能随风飘去。漆树籽红得像朱砂,堆集在枝梢,喜庆而惊艳。
地上的草已经失去了滋润的颜色,渐渐老去,落叶在脚底下窸窸窣窣。一枚石子飞起,沿着斜切线飞向河面,被反弹起来,又落下去,再反弹起来,反复数下,飞弹到对岸的草丛里不见了。河面留下一圈圈涟漪,在渐渐扩散。一条船空无一人,拴在一棵临水的大树上,任河水载着它左右浮荡。
漆树和另一种树长得像孪生兄弟——盐肤木,盐肤木也结穗状籽,秋后枯萎成灰白色,着一层灰色的粉,那就是盐,尝一下是咸的,微带着些苦涩。小时候,山里人煮盐卤,要放点盐肤树籽,在卤缸里浸一下就取出,那样的卤水就澄亮透明,否则就浑浊不堪。漆树籽有毒,只是红得好看,没有什么具体的效用。山上有人收漆树脂,有人割漆树,秋后,漆树脂才是上好的,水分少,浓稠,品质上乘。
割漆树要两个人一起上,一个割一个盛着,在树上斜切一条沟,沟底用一只漆碗接着,乳白的漆树汁一点点流进碗里,像一碗牛奶似的,靠近才闻到一股苦涩的气味,漆咬人就在这时候,刚流下来的漆树汁像毒蛇一样可怕。收漆的人不怕,他们已经习惯了,沾在手上也无大碍。怕漆的人,远远闻着漆树汁的苦涩味就昏厥过去,抽搐不止,得马上送下去,灌甘草水解毒。
漆树和大青是相生相克的,还有一种大蒿菊,一丈高,叶大如掌,放在水里煮一下,洗接触过漆树汁的身体部位。漆疹就能解了,更多的人,解不了,药喝下去,好一阵,漆疹依旧如春雨后的草芽般冒出,久久不会愈合,漆树可能是乡村最让人又爱又恨的树。漆疹愈后,皮肤像花斑豹似的,脸上脖子上,胳膊和手上,一圈圈铜钱般的疹斑给了经历者许久的记忆。
漆树汁封存在一只陶罐里,贮满了,就送到城里漆坊里,熬漆也是一门手艺活,火候不能太大,轻火文熬,大约一个多时辰,水就蒸发得差不多了,熬好的漆晾凉了,要配大料:有牛角粉、白垩细粉、和颜料,矿石颜料为主,石青、苏麻离青、朱砂、辰砂为上,孔雀石绿、钛红、铅黄、锌白、铝粉、锰闪石粉等。配好的漆要马上刷涂,漆器以青铜器为模本,福州漆器主要以鼎、彝、簋、盘、尊、罍、甗、鬲,叫铜器设,以瓷器为模本的叫瓷器设,有瓶、壶、尊、觚、觯等。漆器有脱胎漆器之说,有个模子,通常是硬蜡模,上纻布片,一层一层上漆浸涂,里层不用颜填料,光用清漆,涂满一层,晾干,再敷一层,直到器成。最后描彩上色,有漆里色和漆面色,漆里色,就是将颜料混到漆树脂里,做出来的器,里外均匀一色,不易掉色,脱漆也不会出现明显的破坏。漆上色就简单了,像绘画一样,漆好未干时,上色,最后再上一层清漆,漆面色的好处就是颜色鲜艳,节省颜料,工艺品漆器多以此法,传统漆器仍然坚持漆里色,比如“乌溜古”漆器即是,器成,千百年不变色不脱皮,缺点就是色彩不鲜艳,暗沉如铜铁。漆艺坊里的人也上山自行寻漆,割漆收漆。
不过,现在这样的艺人很少了。我认识的红帆兄就是一个这样的漆艺人,他还是诗人。红帆是个老帅哥,快五十了未结婚,也没有明确的结婚对象。他说,这辈子,能够谈得来的人少之又少,喜欢做同一件事情的人更少之又少,而能够跟你过日子的人更是可遇不可求,像我这样生活无规律,无房无车,只有这乱七八糟的漆器作坊,气味难闻,谁愿意跟我生活过日子啊?他养的狗都被漆咬跑了,养过三只,跑了三只。后来,他改养猫,猫也不喜欢漆器味,养过的都跑了,只有一只流浪猫留了下来,估计是鼻子受伤失灵的缘故。
他作漆画的时候,猫就在他脚边看着,他一笔笔地涂抹,漆汁变成了光亮的器物,器物上有花草虫鱼,人神仙人物松柏鹿鹤,猫耐心地看着,偶尔喵——叫一声,似乎是对他漆艺的赞许。 红帆扎着小马尾辫子,留着短髭,感觉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红帆的漆艺是无师自通型的,他的漆画不追求具体的物、形、态和色,他总是随心所欲地做他的漆器,他将“乌溜古”漆艺术用在他的器物上,有彝或者簋的混和物形,有鬲、甗或者鼎的混合造型,器物表面多了些水磨的叠彩纹。天珠纹需要更复杂的工艺过程,术语叫堆彩水磨法,漆料不仅要加颜料,还要堆彩,厚漆堆彩不太容易做出来,少了纻麻这一物,只好在漆中添加冰蚕丝,还有一种云母粉,各种漆层层堆上胶结后,再水磨、抛光,直到器物出现无数天眼状的回线纹,惊为天工之物。
红帆还喜欢茶,我跟他的交集先从茶起,直到漆艺。他的诗歌我当然也接受了,比如他的《巷》:“幽幽的,從无数层的漆底打捞出来的岁月/ 红颜易老,比如一条巷/都是如此不堪,曲折通幽/没有标志的日子,在树上挂着/直到秋风,唤醒,这些陈旧的物件/铿然落地,水从天上借来了几朵云/风从鬓边借来了几点霜痕/作为点缀,繁杂如雪般,在沙地上凸现。”红帆的歌喉也不错,带着些男性沧桑的磁性嗓音。他活在他的世界里,用他的话说,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与他人无关。
二
铜艺师A跟红帆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同属艺术家性格。铜艺师A是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他是国美雕塑专业的硕士生,现在在一家艺术品公司做主创。他不修边幅,胡子刮得倒干净,头发总是乱成风吹的模样。A才四十岁不到,两个孩子,先后娶过两任老婆,前妻是同学,也是同行,最后无果而终,两个孩子是后妻的。她是寻常人,不懂艺术,更不懂铜雕艺术。A有台电脑精雕机,他说,还可以3D打印,不过那是批量订单时的作品,通常手工雕的作品不外售。
他的工作室更像是冶炼炉,四台电冶炉散发出浓郁的金属味道,室内烟气弥漫,不时得抽换空气,室内热得惊人。夏天,这些炉子要搬到专门租来的仓库里,这里就做最后的雕饰处理。紫铜锭先锯开,切割成若干小块儿,再熔成铜汁,入模范铸出初始形态,再用手铣机铣去多余的部分,表面还需要一些专门的刀削处理,让雕塑更加逼真,也有工艺品性质的,表面完全光亮,无一点瑕疵,那不是艺术品了。现在有的人图省事,上激光机雕刻,虽然快,但艺术的粗糙感和灵性没有了,看上去那么死板、那么假。铜锭熔铸初胚,行话叫设胚,胚上雕刻,就是雕胚,最后表面处理,叫完器,三道工序少一样不行。
铜锭在冶炼炉里迅速熔化,橙红色带着绿色光焰的铜汁注入模范中,稍冷却,启模,初胚就完成了,接下去开始雕刻,手铣机能够将铜胚上的多余部分切掉,铜屑四下散落,铜软,有一定韧性,如果是青铜件,还需要添加锡和铅,青铜就硬多了,雕刻起来更费工费力。A的作品多为骏马群雕,除了动物,还有一些神仙佛老的造型,那是客户特定的作品。A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没办法,客户只需要这些古板而无味的东西,因此,他都舍不得手工完成,多半交给了机器。手工作品却往往克人问津,那些作品他不想卖了,卖了可惜。比如有件《鹤》,只雕了鹤的身体,脖子和脑袋却不见了,他说,鹤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脑袋和脖子,还有细长腿。这件鹤作品给人一种神秘和无奈,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天在何处?在人的内心里,鹤鸣何处?也在人的内心里,并没有太多的想像空间,鹤声高亢而奋唳,在艺术家眼里,那都应该让读者自己想像的,而无足轻生的鹤身躯却展现给众人,鹤其实很庸常的,和一只普通水禽并没有多大区别。他故意夸张了鹤身躯的肥硕,简直忍无可忍。A说,这就是他需要表达的东西,让你着急。还有一件《琴》,更加离奇:杂乱的树木堆积成一架古琴,或者说是一把上好的古琴斫成了一堆乱柴。琴者雅音之器,桐木以为之,蚕丝绞而成弦,七弦六徽,龙池凤沼雁足,轸池、岳山,一切都乱了,这哪是一把琴啊?我问他,A笑而不语,说,琴在琴的相之外,琴有相,而琴音无相,这分明是嵇康弹过的那把琴,被摔碎,刀斧加身。A说,难道这不是古琴吗?
他这么一讲,的确有点像古琴,是古琴的那些零部件依稀可辨。轸碎龙摧,凤沼不复,岳山倾倒,弦丝断绝,好的事物总是让人想像不止,而触目惊心的事物往往让人不知所措。这的确是嵇康的那把琴,他表达的是伪现代潮流对传统文化的摧毁。他让琴木的断茬尖利无比刺穿了参观者的眼睛,让他感到无比惋惜和悔恨。我想到了在挖掘机面前倒下的一栋栋老宅旧屋,随之倒下的那一段漫长的岁月往事,烟消云散了。我认可了A的创意,但这把琴至今无人问津。
我观看了铜艺作品《秋风》的创作过程:铜锭在冶炼炉里消融成一滩亮晶晶的黄色液体,带着太阳的光芒,那本来应该是一团无古的火,从地底下涌出,像岩浆般奔流。然而,它很快就凝固了,在倒进水池的瞬间,水花四溅,蒸汽升腾,水与火一番抟搏后,作品就出来了,那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铜汁凝固块,无形无态,像裂帛,像散开的竹简,像被风吹破的书页,像岁月碎散一地的样子。它像树叶,不特定哪棵树,哪种叶子,像枯萎的葡萄叶,像吹断的芦苇叶,像纷飞的花序,像无规则的云层间迸射出来的阳光。它闪亮,带着些彩虹的光晕,它暗淡,像枯死的叶子般憔悴。它更像是徐渭笔下的墨葡萄枝叶,像他画中的枯荷残芰,仿佛看到五百年前徐文长坐在秋日的画案前,疾速挥舞着一支半秃半干的笔,笔尖开叉,他全然不顾,蘸着浓墨,在纸上点点划划,墨洇开了,成一墨团,又旁逸出一条曲折的蔓络,随意点染几棵瘦细的葡萄。秋风将葡萄枝蔓拉扯得像一面鼓,像拉开的弓,仿佛要将他内心里烦懑全发泄出来。他画毕,手在颤抖不已,将画随手一团,扔到了墙角。然后他低声啜泣,气息抽噎。我喜欢徐文长的墨葡萄,也喜欢他的芭蕉画,他的芭蕉画是那种秋后的芭蕉叶,破碎无状,一绺一搭,奓着肩,拖眉耷脸。秋风吹起,残破的蕉叶吹弹出一曲人生的悲歌。
三
秋凉如水,夜里的云像铅块似的伫立不动。我看着红帆的漆器艺术和A的铜雕作品,感觉异样的悲凉如水般拍来。这些不会动的艺术作品仿佛开口说话了。
漆器的精美和变幻莫测的纹理让我陶醉,A的铜雕却让我猝然惊心,那种感觉对立矛盾,却不是无法调解的。漆器幽幽地透出远古的一种美学存在,纹理、色差对比,光泽、委婉的曲线,在灯下的漆器,仿佛是从内心里走出来的一种美。像宝石上的光芒,细腻的漆层里,矿物和时光凝固一起,形成一个整体。
那种无法分开的胶着感,那种沉稳的色调,虽然有些红或者黄的亮色突兀而出,总体是沉稳而幽暗的。我想到米沃什的诗《猫》:“它从暗处闪出,像闪电般/它钻进黑暗,像闪电般/没有细节,无法追述/没有黑暗的夜晚,星光遍地/月亮碎成沙子,银河直插进后院/猫胡子张开,夜的四维/网一样,所有的暗和明亮都一样,成为鱼。”夜作为最大的包容体,容纳下宇宙天地万物,恒河沙数的世界里,无数的暗和亮互相对立交融着,像阴阳两仪,说不出的一种鲠在喉咙的感觉。夜晚的秋风应该是沙哑的,隐没低沉的,樹或者在动,或者不动,并不能确定。铜雕应该像冰一样,或者像云一样可变的,不定型的,铜雕刻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得到不同的视觉。
粗粝的表面,像岩石的质地;细腻的表面,则柔滑如肌肤。这也是两种对立的感觉,对立的两个面,就是世界了,宇宙中有量子纠缠理论,对立的两个面,是互相纠缠的,没有东就没有西,没有上就无所谓下。方或者圆,都可以形成回路循环,只是路径不同罢了。等周长的回路,所需要的周游距离一样,速度一样的话,总时间也一样。太极的两仪,阴鱼和阳鱼,在纠缠和对立过程中最终互换。阴阳变化,像天地,像四季。说话间,已经到了季秋了,秋天已经走完大半路程。
想起不久前听琴师老骆的演奏,那时候,秋天刚刚来到,天依旧热得难受。骆老师的一曲《高山流水》,像淙淙的瀑流,从心间淌过,那一勾一抹,一挑一切,声音从丝弦间流向四周的空间。阴阳四理,有阴处阳生,有阳处阴生,这个过程毫无间断,没有缝隙,只有黑与白不断交替过渡。秋风扫落叶,轻轻地一声叹息,是一个季节的结束,也是另一个季节的开始。
远处的山看上去显得寂寥无极,但那是我的感觉,山依旧是那山,天依旧是那天,秋风吹过,落叶一地,而冬天的芽已经开始孕育中,冬深的时刻,芽苞饱满,即将绽开。美生于死亡,死后而有生机。握着红帆的漆器,那种凉沁是短暂的,握着A的铜雕,那种凉意绵长无极,仿佛手心的热量一点点被抽走,不知去向。铜雕那表情冷穆而寂静,无从得知热为何轻易被它吸走。
铜是天地间的灵物,漆器也是,只是换了个面孔。秋风起兮,就想到了古老的诗歌,或者,从来没有生,也没有死,只有来和去。秋则为去,春则为来。万物都要来一遭,然后淡然而去。一棵枫树在春天夏天时何其美妙,秋去冬来,枫依旧美妙似火,枫还是枫,枫叶从红色到红色,刚好走了一个轮回,因此,从某一处回到某一处。只是,时光不会有这样的回路,那条无尽的流沙河,浮叶或者大木一样的流逝,不会重来。
仿佛诗一般,一声落叶,一声叹息,秋风幽然而过。
责任编辑 杨 枥
陈元武,现居福州。在《广州文艺》《十月》《山花》《天涯》《青年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散文》等多家杂志发表多篇作品,曾经获得孙犁散文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