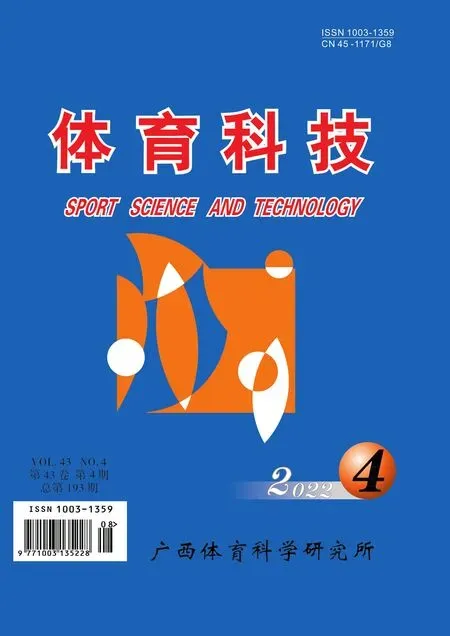全媒体时代中国武术传播:机遇、挑战及风险防范
2022-01-18徐学怀郭桂村
徐学怀 郭桂村 李 臣
全媒体时代中国武术传播:机遇、挑战及风险防范
徐学怀 郭桂村 李 臣
(长江大学 教育与体育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文章运用文化学、传播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以“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国家意志为引领,对全媒体时代中国武术传播的特征、机遇、挑战及风险防范路径进行了学理性分析。认为,在媒体融合呈现出新态势的当下,中国武术要高质量承担起推动中华文化深入“走出去”的典型载体使命,必须明晰全媒体赋能中国武术传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更应防范中国武术传播媒介“去中心化”态势对中国武术典型载体正向效能的消解,规避传播内容“碎片化”问题对中国武术传播主体话语权威的解构,以及消解传播方法“解构化”矛盾对中国武术身份认同及核心竞争力的遮蔽。
全媒体时代;武术传播;文化自信;风险防范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发生深刻变化,同时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产生着重大影响。
中国武术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动力源泉,且能够展现激励人们“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精神提振”等价值共识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武术以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特殊本质,反映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即“刚健有为、入世进取的拼搏精神;重视人际关系的特殊人文精神;排斥神学宗教体系的世俗化精神;‘天人合一’的崇尚自然精神;重视血缘关系、血缘团体的宗法精神”[1],才使得它在长期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始终绽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光芒,并由此形成少长皆宜,且集健身、技击、娱乐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独特中华传统文化体系。
因此,在信息技术发展和媒体深度融合呈现出新态势的当下,依据“文化就是传播”“文化的传播依赖于媒介的发展”学理认知,要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武术,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展现出“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厚植家国情怀”[2]的爱国主义教育载体正能量,彰显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极效益的黏合剂效应,以及高质量承担起推动中华文化深入“走出去”的典型载体使命,除了明晰全媒体赋能中国武术传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之外,尤应规避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凸显的“人人都有麦克风”客观现实对中国武术传播造成的“去中心化”“碎片化”“解构化”等窘境所延展出的潜在风险,才能促使其在全媒体时代从传播理念到传播实践得到有效更新。
1 全媒体赋能中国武术传播面临的时代景观
处于全媒体时代的当下中国,因技术变革引发的媒体融合已呈现出全景式爆发之势,深刻影响着社会各领域的舆论生态。这其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武术,面对技术推进中武术传播涌现出的诸多复杂生态,势必会对其传播格局、话语权威和价值理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1 全媒体视域下中国武术传播的显著特征
当今时代,全媒体之所以爆发出惊人能量,除了源于它是“在信息、通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各种新旧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借助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表现手段进行深度融合,产生的一种新的开放的不断兼容并蓄的媒介传播形态和运营模式”[3]之外,更表现在其凸显的数字化、交互性、个性化和风险性等显著特征,对传播内容多样化表达、传播方式交互性转换、分众化对称性个性信息提供,以及开放性媒介交流权利赋予,所产生的助推各类信息借助大众媒介所彰显的与时俱进创新力。
正因如此,进入新时代,在“文化是一种力量”共识性论断作用下,中国武术因获得了国家层面系列政策支持(如在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更是迎来了其厚积薄发的突破口。也因此,在媒体融合已成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背景下,中国武术传播主体理应积极主动作为,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对武术传播媒介“去中心化再中心化”,武术传播内容“互动性、碎片化、娱乐化”,以及武术传播方式“智能化、解构化、个性化”等武术传播机制各要素的影响,同时,更应积极建构以中国武术资源为核心、以各类新媒体平台为支撑的中国武术全媒体传播体系,从而使其以“文之道,时为大”的历史使命,积极融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之中。
1.2 全媒体赋能中国武术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这是一个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中华文化有作为且一定能够有所作为的时代,更是一个中华文化借助形式各异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展现其蕴含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等核心内容的“机”与“危”并存的全媒体时代。毋庸置疑,中国武术面对这场全媒体“大考”也同样需要以理性的思维,审视其在“机”与“危”并存的新时期,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
中国武术在“万物皆媒”时代要应势而动,抓住全媒体赋能中国武术传播带来的超越时空、强化联系、凝聚合力等新机遇,更要因势而谋,思考其话语权威“去中心化”、传播方法“解构化”等方面遭遇困境的应答策略。具体而言,在全媒体时代,中国武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武术传播权利的全民化,武术传播者、受众和把关人之间身份位置的互相转换等特点,既使人人皆可成为武术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变为现实,又满足了武术目标受众细分武术信息的需求,更推动了武术信息的多向度传播,进而形成助推中国武术复合势力(如文化的、教育的、产业的)“全景式”传播的连锁性效应。
事实上,事物发展具有两面性,新媒体传播的“双刃剑”效应,不仅能够使中国武术传播主体借助新媒体平台,增强武术受众的参与性,创新多样化的武术传播形式,而且还因中国武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威被解构以及传播内容呈现的碎片化、娱乐化和浅表化等负面影响,对中国武术的核心竞争力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消解。如当前在抖音、快手App等各类新媒体平台,不断爆出小范围内的“武术圈”功夫比试、格斗狂人叫嚣整个中华武林“谁敢应战”的偏激言论以及“某某”武术大师运功治病等短视频,迫使中国武术职能管理部门接连出台关于“武术赛事举办”“武术产业拓展”“武术行业自律”等方面的指导性文件,才使得中国武术的整体运行能够保持在正常行进轨道上。
2 全媒体时代中国武术传播的风险防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在十九大修改后的党章中,给予文化以重要的分量。改写或增写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4]条款,充分说明进入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创新工作上升到了国家法律保护层面,更警示着中华文化传播主体在推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要时刻保持风险防范意识。同理,华夏子孙在利用当下发展态势迅猛的新媒体手段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更应当防范新媒体传播对中国武术发展造成的不同程度消极影响。
2.1 防范传播媒介“去中心化”态势对中国武术典型载体正向效能的消解
处于全媒体时代的当下中国社会,媒体融合呈现出的移动化、智能化、视频化趋势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方式。传播媒介“去中心化”态势,正在消解着中国武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提振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典型载体综合效能。如“近期一些伪‘大师’、假‘掌门’,为了追逐个人名利,随意自创门派、自封称号,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传统武术的喜爱和关注,通过‘约架’等方式进行商业炒作,给中华传统武术形象带来严重损害”[5]客观事实,俨然已经成为现阶段制约中国武术良性传播的最大壁障。
正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武术作为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健康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且又成为当今人们健身、防身、修身养性、自娱娱人等多功能的良好手段”[6],它的传播事宜和管理责任理应由国家层面及相应的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但在当下的传播媒介“去中心化”态势影响下,中国武术的传播方式却产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传播媒介对中国武术的重大议题设置、典型事件报道、代表性人物访谈等重要内容生产仍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但在“粉丝就是财富、流量就是金钱”导向驱使下,原本由专门机构负责的中国武术内容生产传播环境,被海量涌入的自媒体平台肢解着武术内容生产的话语权,由此导致武术界“恶意攻击”“私自约架”“虚假炒作”等违法违规活动信息铺天盖地的充斥着各类新媒体传播平台,从而对中国武术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损害。
对于此,作为监管中国武术高质量传承发展的主要政府职能部门,尤其应当履行好自身职责,在强化主流媒体传播中国武术的主导地位同时,并依法对各类新兴媒体进行适度管理,以扭转中国武术整体形象受损局面。这期间,中国武术主管部门除了依托主流媒体宣讲中国武术在关键历史节点展现“‘从武师到民族英雄’的近代侠客,维护广大华人文化圈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拯救国难的武学宗师,所彰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镜像”[7],还应借助《中华武术》纪录片、《中国功夫探秘》节目,以及诸如日本人拍摄的《惊异的中国武术绝技》等多维宣传形式,讲好中国武术故事。并且,还要阐释好其“使现代社会的人们通过中国武术的传习,明晰从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的调整身心功效、领略在浮躁的社会让其归自然的武化力量”[7],以及中国武术海外传播过程中“由单纯武术技术传授向‘治未病’武术运动处方设计”转变,给海外民众实施“送健康”传播策略的价值功能,对于新时代中国武术推动中华文化深度国际化传播的独特载体效能。
与此同时,中国武术职能管理部门,在肯定各类新兴媒体对中国武术宣传推广贡献的(即时互动、精准推送、产生共鸣等)新型智慧同时,还要直面武术传播内容信息把关不够所生发的丑化武术、诋毁他人、互争正宗等激诈行为,对中国武术传播的公序良俗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破坏。如,近年来,有一部分中国武术圈的习练者,他们利用智能手机的信息便捷传播功能,把个人对于中国武术发展的整体评判,以激烈的言论、微视频以及“下战书”等形式,广播于朋友圈、微博等媒介传播平台。“一石激起千层浪”,刹那间,“格斗狂人武术打假、自由搏击者与武术大师私自约架、太极大师隔空震瓜、散打选手瞬间KO太极大师”等讯息在整个武术界乃至全国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面对此种损害中国武术良性发展的不当行为,中国武术主管部门理应借助主流传播媒体旗帜鲜明的对此类传播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与管理,以消解他们对中国武术传播造成的潜在风险。
2.2 规避传播内容“碎片化”问题对中国武术传播主体话语权威的解构
自中国武术与互联网融合以来,业界研究者围绕该主题展开的不同维度的学理性探究为中国武术借助媒体新技术拓展自身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发展进入下半场,以及“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出现,使得迅速走俏的新兴媒体加剧了中国武术传播的“碎片化”趋势。因为,“全媒体时代用户主动性更强,信息获取需求更高,且多样化的信息内容、形式、渠道等都各有特点”[8]的鲜明特征,不仅催发着全媒体语境下中国武术传播主体的武术传播策略要有针对性,凸显差异化,体现“用户思维”,而且还拷问着中国武术传播与媒介融合所呈现的内容生产的核心竞争力,更警醒着中国武术传播主体坚持“内容为王”把关方式,展现有效汇聚中国武术“全景式”传播文化自信底气的核心要义。
因此,基于碎片化理论是“将原先在一个场所进行的生产活动分解为多个生产模块(block),并分散建在适合各个生产活动的地点”[9]学理认知,要使作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来源,且流传于中华民族各地区的中国武术呈现出源流有序发展之势,有效传承与传播应是中国武术不断创造新辉煌的制胜密码。如,一个太极拳从陈王廷起,到后来不断涌现的杨式、吴式、孙式、武式、和式等多种太极拳流派,既合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彰显着精英传承和谱系传播推动其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但是,事物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中国武术在其不断变迁的演化历程中,不同拳种除了传递着中国武术共有的规律性内容之外,部分中国武术传播主体还不时流露出偏离中国武术质的内在规定性,主观随意,致使中国武术的发展出现偏差。
这一点,对于处于波涛涌汹的移动新媒体场景中的中国武术来讲,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碎片化的场景中有意无意地获取碎片化的信息”[10],已成为身处信息碎片化时代的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迫使信息时代所谓的中国武术传播主体(以不同形式唱衰中国武术的各类复合体)对新媒体的依赖性剧增,从而使得中国武术传播主体的碎片化肢解着中国武术传统的话语权威。如,一些中国武术爱好者抑或习练者,由于个人喜好、利益驱使等原因,通过文字、图片或短视频等形式,散布对某些中国武术从业者、拳种负责人和知名功夫巨星的不和谐言论;武术传播内容的碎片化导致目标受众过多关注于不同拳种一招一式的技法传习,缺少对中国武术“精、气、神”整体提升的本真体悟,进而延展出有人说现在的武术是“花拳绣腿”偏激评论;中国武术传播空间的碎片化,使得传播主体将中国武术与个人关注度提升、娱乐消遣、商业炒作等内容联系起来,从而导致人们对中国武术的价值认同降低。
鉴于此,要规避中国武术传播内容“碎片化”问题对中国武术传播主体话语权威的解构,借助媒体新技术有序开发中国武术资源、增强中国武术传播内容叙事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应是全媒体时代实现中国武术良性传播的关键之举。这其中,在技术与中国武术、技术与武术传播主体、技术与“武术的共同体”的互动逻辑中,我们在赞叹技术的强权逻辑对中国武术发展空间拓展给予的媒介赋能同时,更要警醒不同历史时期,因过分追求中国武术的弘扬“唤醒了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华儿女,激发了广大民众尚武救国的精神斗志”[7]等独特价值效益,而对阻碍其高质量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置若罔闻。再者,新兴媒介、中国武术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宏大愿景相连时,理应彰显其“为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制造着文化仪式”[11]的典型载体优势,更应展现其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健康中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黏合剂效应,以推进中国武术经世致用效益合于时宜守正创新的初心延续。
2.3 消解传播方法“解构化”矛盾对中国武术身份认同及核心竞争力的遮蔽
面对新时期媒体融合所呈现的前所未有之变局,倘若武术人不能够在急剧的技术变革中及时重塑中国武术的主体性,势必会使中国武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典型载体使命、强化中外人文交流合作的融通效益、激发民众“尚武强身、以武育人、精神提振、卫国保家”等责任担当先行优势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新时代,被各领域盛行的解构主义所异化与歪曲。这一点,诚如有学者所说的,“正如过往的人类传播史所呈现的,媒介的迭代是呈加速度进行的,如果没有一个前瞻性的视野,任何社会、群体和个人都会被极速变迁的媒介环境所边缘化”[11]那样,中国武术必然会被抖音、快手、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生产出的解构中国武术的本质、规律及身份的各类微视频肢解其在武以成人、激发潜能、疾病防御、延年益寿、民心相通等方面所展现的独特中华身体智慧正能量。
对于此,虽说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武术传播主体借助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形式,关于中国武术被解构的现象屡有发生,如“在清代,神传仙授、托圣附贤、无限夸大技击功能等意识渗入武坛,给本来注重实践、讲究实效的武术蒙上了一层神秘玄虚的色彩”[12],对当时社会大众习练中国武术,激励斗志、强种报国、抵御外侮等尚武意志有不同程度地削弱。但真正从科学研究层面,且利用大众传播形式(如报纸、期刊、图书等)对武术发展进行的解构化记载,应当是“西学东渐”风气较为盛行的民国时期。如,听驼在1938年《体育月刊》第五卷第六期题为《对于国术应有的认识》中是这样述说的,“缘来关于国术之研究,分‘不屑谈’与‘不欲谈’,所谓‘不屑谈’者,以为吾国凡百事物均无足道,练习国术者又多江湖卖艺之流,甚至自炫其说,自秘其技,行动粗鲁无文,逈非士大夫所喜接近。加以无聊文人,编为奇怪事迹(‘飞剑杀人’‘隔山击牛’等),均不合于科学,特神其说,以求学者之信仰,其实自损其价,反为识者所窃笑。因之不屑加以深刻之研究”[13]。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不胜枚举的中国武术被解构化事实的存在,致使中国武术在近代的“土洋体育”之争中屡屡折戟,并被涵括为体育学科的一个运动项目,从而开启了其体育改造化进程。
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武术虽被多位国家领导人给予高度评价并作出重要批示,但由于受到文革时期整体形势影响,武术运动被戴上“传播封建迷信的工具”的帽子。尽管改革开放新政实施,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武术热”,并引发了全球性的中国武术习练热潮(特别是电影《少林寺》热播),但“为抢夺生源所导致的诋毁对手的行为常有发生,使海外习练中国武术的受众难以分清武术传播者‘孰真孰假’”[14],以及国内部分拳种负责人打着重振某某拳种的旗号,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不同的大众传播形式,对自身拳种的“前世今生”进行组合式的历史拼凑行为,已给中国武术的健康有序前行植入了身份认同矛盾。
步入21世纪,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武术更是在“文化强国”国家意志成为时代强音的当下,迎来了其厚积薄发的突破口。在加快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方面,如“鼓励地方根据当地自然、人文资源发展特色体育产业,大力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扶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15],“创新社会力量举办业余体育赛事的组织方式,开展武术、搏击等项目赛事;打造武术、龙舟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竞赛表演品牌项目”[16]。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方面,如“支持中国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17],“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重点支持武术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18],以及“实施中华武术‘走出去’战略;通过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平台,推动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国际化发展”[19]。正是这些国家层面颁布的、关于中国武术资源产业转化的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合作的系列政策性法规文件对中国武术国内外高质量发展提供的新型动力支持,才使其在新时代迸发出文化的、产业的、教育的等多元势力。
当然,也正是源于国家层面系列政策性文件对中国武术资源新业态开发、人文交流合作典型载体效益提升展现出的深度关切,致使部分“所谓的武术人”,利用中国武术国际范围内受宠的机会,借助微信公众号、抖音和快手视频直播平台等新媒体资源,对中国武术展开合于自身利益的多维度解构。如,“2013年8月在新疆某县举办的天山武林大会,主办方首先考虑的不是活动质量,而是自身的利益和政绩,最后弄得如闹剧般草草收场”[20]的尴尬结局;再者,因“徐雷约架”短视频的爆出,催生人们对中国武术被解构化的事实,“长期以来,武术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伪装者’,他们有的以敛财为目的,但并不掌握真的格斗技巧和武术真谛,打着传承传统文化瑰宝的幌子行招摇撞骗之实”[21],进而引发对中国武术重新振作的深入思考(如武术竞技的定位、民间武术的投入、中国武术何为等问题)。
由是观之,中国武术因其传播方法方面存在的“解构化”突出问题,使得其在激发尚武精神、承担社会责任、塑造国家形象等复合价值表达过程中,遭遇着长期的错位和失位困扰。但就其面临挑战的整体状况来看,增强其传播表达的亲和度应是破解此种困扰的归位选择。因为,就全媒体时代的技术变革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来说,“全媒体是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大、技术手段最多样、媒介载体最全面、受众面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22]客观事实,已然对中国武术的深度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其中,既要利用好新媒体技术增强中国武术传播的密度、强度和频度优势,又要使武术传播彰显出传递正能量的温度,展现出弘扬精气神的态度。
具体来讲,就是要发挥好新媒体技术对于中国武术发展的国家政策方针精准解读的传达效益,表达好其阐释中国武术回应社会现实需求的价值体现形式,传递好其塑造中国武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平台增值功效,以及凸显其跨时空、破屏障、建联系、聚合力等优势,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其展现出“以时为大”的历史使命。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武术、太极拳、健身气功等运动方式,因其对人类个体的身心健康展现出的形、神、意、气锻炼独特效益,使得它们借助新媒体平台实施有效传播的认同度被再次提升。并且,“在疫情期间,孔子学院为保证学生‘停课不停学’,印度尼西亚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把教学全部转为线上,推出了中国武术、书法、剪纸等系列文化课程,使得学生通过网络孔子学院、中文联盟等在线平台,获取了海量学习资源,并促使这些网络课程在孔子学院师生和家长中获得了众多粉丝”[23],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着中华文化(中国武术)的核心竞争力。
3 结语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武术人拥有的武术传播信息优势、理论优势和技术优势逐渐丧失,传统的中国武术传播方式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万物皆媒的新时期,要规避传播媒介“去中心化”态势、传播内容“碎片化”问题、传播方法“解构化”矛盾对中国武术高质量发展整体效益的消解,增强武术传播主流媒体(如国务院官网、国家体育总局官网、中国武术协会官网和“学习强国”APP)的权威引导力,讲述好中国武术文化资源多维转化的完全性,传递好中国武术服务现实社会需求的亲和力,以及精准定位武术传播目标受众的个性化需求。这既是巩固武术传播主体话语权、多向度开发中国武术资源、弘扬中国武术文化和增强中国武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新时代中国武术借助技术创新和主流媒体的交叉合力,促进其“治未病”健康功效、“民心相通”效益和传递“和而不同”文明价值理念,有序植入海内外目标受众心中的应然选择。
[1]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武术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19-22.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12/content_5451352.htm,2019-11-12.
[3]李春杰,李丹,陆璐.信息技术专题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142-143.
[4]李忠杰.党章内外的故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317-318.
[5]叶道.中国武协倡议加强行业自律[N].中国体育报,2020-07-09(01).
[6]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1.
[7]李臣,郭桂村,张帆.新时代中国武术传承发展的困境与消解[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53(7):65-70.
[8]张晓锋,程静.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趋势与创新路径[J].传媒观察,2020(1):5-11.
[9]王虎.产业内贸易:结构、分类及差异化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44.
[10]陆新蕾.“碎片化”阅读并非洪水猛兽[J].新华文摘,2020(5):169.
[11]廖祥忠.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J].新华文摘,2020(7):152.
[12]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309.
[13]听驼.关于国术应有的认识[J].体育月刊,1938,5(6):3.
[14]李臣.中国武术海外传播与价值反思[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8-01(008).
[15]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20/content_9152.htm,2014-10-20.
[1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12/21/content_5350734.htm,2018-12-21.
[17]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6(006).
[18]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7-12-22(001).
[1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2019-09-02.
[20]张頔.被糟蹋了文化遗产[N].经济日报,2013-08-18(008).
[21]陶风.赶走“伪装者”,武术不妨出神坛进市场[N].北京商报,2017-05-03(002).
[22]王存刚.全媒体时代外交专业研究的挑战与应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8-10(004).
[23]徐伟.患难见真情 共同抗疫情[N].人民日报,2020-06-16(18).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Wushu in Omni-Media Era :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Risk Prevention
XU Xuehuai, etal.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China)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ATY011);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9Q043)。
徐学怀(1996—),硕士生,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
李臣(1980—),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