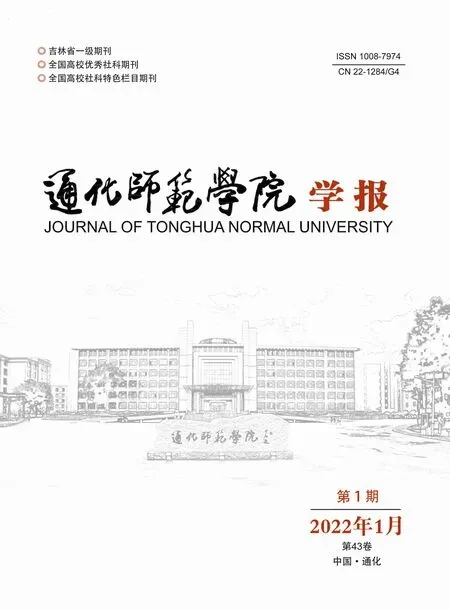赵之谦山水画艺术取向探源
2022-01-12方克朋
方克朋
赵之谦(1829—1884年),浙江会稽人,字撝叔,又字益甫,号冷君、悲庵、悲翁、无闷等,斋名二金蝶堂、苦兼室、悔读斋、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等。纵观赵之谦一生游历,做官和做学问是其一生最大的追求,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书画篆刻艺术方面成就斐然。在绘画南开海派之先河,北对陈师曾、齐白石等都有重大影响。
赵之谦志在考取功名,报效朝廷,然而仕途坎坷,迫于生计,多作花鸟,故山水画传世作品较少。从目前存世作品可以看出其山水画水平不在花鸟之下,其中不乏精品,风格多样。赵之谦学习山水画较早,同治三年(1864年)为景初作《山水》团扇题款中说:“不画山水已十五年矣,景初必欲画此,勉强成之,可笑甚也”[1]176。同治三年这一年赵之谦三十六岁,说“不画山水已十五年”,可知赵之谦二十一岁后便少作山水,早年山水画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而后忠于仕途,鬻艺捐官,为迎合市场需求便“不画山水”,为此我们感到惋惜。赵之谦山水画与书法、篆刻以及花鸟画的艺术成就相比,稀见页册,难被论及,也许与仅仅存世数十幅作品有关。但笔者认为,赵之谦作为一代著名艺术家,其山水画作所彰显出的卓尔不群之风,无不透露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的积极影响和深厚滋养。而当下关注于赵之谦山水画的研究者寥寥无几,是赵之谦艺术成就研究的缺憾,本文就赵之谦山水画艺术取向试作分析探源。
一、思想文化背景与其山水画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赵之谦身为封建时期的文人,精研儒学,思想文化底蕴深厚。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其艺术特征早已外化在山水画作的浩荡线条中。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赵之谦的“独善其身”体现在:生活中,他重视人品和学问两者兼顾,“意中人必品学两字皆有之方可”[1]470;他强调言行必须一致,“弟凡说出者必做到,否则即自说前言之非,久而改之有不可也”[1]264;他主张忠孝“情之一字,推而广之,极于忠孝”[1]533;他涉猎宽泛,“围棋鼓琴,俱入能品”[1]1247,在撰写《勇庐闲话》时,以“一物不知,儒者以为耻”[1]1281。赵之谦的“兼济天下”体现在:“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学,固天可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1]133。赵之谦的远大抱负志在考取功名,报效朝廷。然而“四试礼部而不第”,后经捐官谋江西县令一职,尽心尽责,关心国家大事。“中俄事万无战理……即不得已而战,战而大胜,乃无足为喜。外国胜中国,则中国兵费,只须一二人驻此,大家俯首听命,分文不断。外国败中国,有一人能责赔兵费乎?即使责赔而彼竟不付,中国有法能取之乎?”[2]254“越南事虽不妥,然有此小胜,亦足以豪;即亡,犹过于面缚衔璧也。”[1]372赵之谦身处僻远之地,又非高官显贵,始终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拥有满腔的爱国情怀。
赵之谦山水画艺术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他在艺术创作中把“中和之美”的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谈及学习书法时他说:“求仙有内外功,学书亦有之。内功读书,外功画圈”[1]1170的认知;在谈论用笔与境界时说道“天地间凡尽境皆同始境,圣贤学问,极于中庸”[1]1173。在致魏锡曾信札中说道“学问中事,非顿须渐”[1]268。这些都体现了儒家“中和”之美的思想。儒家“中和”之美的思想,也是赵之谦山水画的文化底色,这在他的山水画作中可以寻到清晰印记。同治十一年,赵之谦为王晋玉①王晋玉(瓒公),即西垞,生卒年未详,江苏溧阳人。作《沐箫泉图》(图1)山水团扇,同治八年(1869年),赵之谦曾游乐清城西沐箫泉,而作此图时已是三年之后。凭其记忆,戏写大略。画中丰富而充实的林木、山石,严密而厚重,山石多运用披麻皴,加之层层渲染,使其更加地圆浑与厚重,增加山石的体积感。看上去繁复,细节的处理却透露着简练的笔法,笔墨间透出浓重的“中和”意味。山石并不陡峭,瀑布随着山石的走势,经过四五转折,流入溪中。于近处溪畔茅庐内,欣赏远山瀑布,不失为幽静、纯朴的所在。最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峰,于云雾中渐行渐远。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古淡、静谧、中和之美的氛围。

图1《沐箫泉图》
(二)道家思想的影响
赵之谦在治印中认为:“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1]217。在论及书法意境时谈到:“书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1]1170。赵之谦所说“斑驳”“浑厚”“天质”“神秀”皆属自然天趣,体现了道家精神之“妙”,道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其艺术成就的发展。赵之谦信奉道家的风水之说,其山水画主题、意境皆深受道家精神之“神妙”“道法自然”的文化滋养。

图2《梦蜴图》
同治八年秋八月,赵之谦为曹籀②曹籀,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字葛民、竹书,号柳桥,钱塘诸生,平生致力于经学、小学,与魏源、龚自珍交善,自言为龚氏畏友,道咸间与戴熙等结红亭诗社,互有唱酬。有《谷梁春秋释例》《尚书古文正义》《三家诗传诂》等。所作《梦蜴图》横幅(图2),整幅作品如“梦中境也”,由于水墨自然氤氲的效果,自然呈现出石室、黑影人、蜥蜴、云雾等物象,葛民先生认为是天成之作、神来之笔,该作品表现出了水墨氤氲的技法与道教主题的关系。赵之谦加以题赞:“纸为泼墨,将弃之矣。葛民先生取而谛视良久,曰:此天绘吾《梦蜴图》也。其上为岩,有石室焉。石室尽处有黑影人立者,梦中身也。其右若藤萝者,皆蜥蜴也。其间方卦,则霹雳开天图也。岩以下皆云气,梦中境也。为之歌曰:霹雳开天天开图,蜥蜴百万为追呼,独窥灵秘握神符。安有华山道士之愚诬,不曾梦见,忽言有无。七百余岁成榛墟,赖此须臾挽斗枢。赵之谦书”[3]66-67。初视作品云雾缭绕,如至仙境的梦幻景象,细细品读,趣味横生,处理水墨氤氲的效果与金石用笔的巧妙结合,体现作者高超的创作能力。整幅作品大部分用水墨自然氤氲的效果,墨色虚实分明,层次淡然有序,画面上部采用金石用笔的线质所绘岩石,寥寥数笔,笔简形具,乃画龙点睛之笔,整幅画面生动有力,使观者在浑然天成的墨韵中产生了无限遐想,表现出道家精神之“妙”“道法自然”的意境。
赵之谦又为曹籀作《龙门山卜营寿藏图》,此图反映了道家“妙不可言”的玄妙色彩,题款:“既登广果天,胡入龙山门。野化藏鸟鸢,寿营一倒删。卜营胡为者,委蜕乃大还。画图亦多事,宜掷摧烧间。请公下转语,持此叩禅关。广果天待者法座。娑婆世界凡夫作”[1]160。赵之谦信奉道家的风水之说,“卜营胡为者,委蜕乃大还”。幽冥杳漠,更加体现了此幅作品道家之“神妙”意境。
(三)佛禅思想的影响
赵之谦又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为容吾所作的《行书诗》注中说道:“往与老友曹葛民(籀)及邵阳魏先生①邵阳魏先生即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道光进士,官至高邮知州,与龚自珍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曾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今人辑有《魏源集》。有念佛之约,今魏先生化去,而葛民又陷贼中,存亡莫问,孑然此身,无补世用,行当削发入山与木石居耳”[4]216。可知赵之谦事佛的时间较早,早年便与曹籀、魏源有“念佛之约”,魏源卒于公元1857年,赵之谦事佛则应在公元1857年之前,可推测出赵之谦二十九岁之前便事佛。赵之谦艺术成就则在其佛教的信仰中不断展现,为其山水画艺术创作提供了题材和内容。
同治二年(1863年),篆书书写“阿弥陀佛”,画阿弥陀佛像,并题记:“壬戌十二月在海上遇风,舟几覆,诵佛号,满万声,波平浪息。念佛征印,此为最显,稽首皈依,书以祈报”[1]134。赵之谦以“念佛征印”“书以祈报”,把能够得以生还,全归结为佛祖的保佑,使他愈加笃信佛事,勤礼佛事已成为赵之谦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治六年(1867年),为曹籀刻朱白文佛经句两面印,又为其书写佛教华严经句“各见十种一切宝香众妙华楼阁云”横幅等等,以上均受勤礼佛事的影响。
同治八年(1869年),赵之谦为曹籀所作《石屋文字无尽灯图》轴(图3),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如题款中所说“佛言安心竟,任行止坐卧”。这显然是一幅受佛教题材影响的山水画,画上题诗也是禅味十足。“是石不可屋,是屋非石作,即石即是屋,小石屋亦大。无名名之屋,有石石立破。佛言安心竟,任行止坐卧。得不坠文字,万万古一唾。不论灯是火,常寂光法座。无尽无无尽,尽从无尽过。此中真实意,解者有一个。”[1]156赵之谦性格“尚异好奇”,毕生对禅亦是参悟不已。同治八年再赴温州时,为蔡枳篱书禅宗语,又作禅诗六首,自谓是“口头机锋,不足道也”,但却典雅庄重,饱含了世情和哲理。下录其中二首:“我曾不见佛,我先不见我,见我向镜中,不如人见我。佛以我见我,我自人见我,我能不见人,见佛无不可”[1]37。“窗外东山小,门外东山高,屋外东山大,登山东山逃,人在山之腰,山下人看山,已关登者劳。”[1]37在佛禅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佛禅的参悟,为赵之谦山水画丰富了创作内容和题材,也是赵之谦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赵之谦身为封建时期的文人,思想文化底蕴深厚,精研儒学,旁通佛道,思想文化背景是其山水画艺术取向的重要源泉。纵观其山水画作品,在题材和内容上所展现的山水画风,深受儒家“中和之美”的境界、道精神之“神妙”“道法自然”的文化滋养、佛禅思想之韵味十足等诸家思想文化融合的影响,也体现了赵之谦思想对文化自由精神的追求。

图3《石屋文字无尽灯图》
二、师从的影响与其山水画
(一)师从友人
赵之谦早年便对金石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十七岁那年,拜塾师沈霞西①沈复粲(1799—1850年),字霞西,自署鸣野山房,山阴人。为师,专心研习金石之学。“之谦十七岁,始为金石之学,山阴沈霞西布衣复粲第一导师也。”[1]772沈复粲虽为一介布衣,却积藏书籍甚富,是位嗜金石、好收藏、著书甚多的饱学之士。鸣野山房藏有众多帖目,方便于书、画、法帖的查阅。赵之谦拜沈复粲为师受其影响,加之鸣野山房内众多的书画藏品打开了他的心灵窗户,是其山水画艺术取向的重要方式。
赵之谦的交际圈十分广泛,在早期追随缪幕期间结识好友繆梓、周白山、戴子高、胡培系、丁文蔚、胡澍、王瓒公等。避乱温闽之时常与来往者有钱松、傅以豫、江湜、魏锡曾、秦如虎等。客居京师期间与沈树镛、舒梅圃、曹籀、邵芝岩、翁同龢、潘祖荫、张之洞、王懿荣等人多有交往。在此期间也是赵之谦山水画创作的高峰时期,以上诸友或为学术俊贤,或为书画名家,或为达官显贵,对赵之谦生活上给予诸多帮助,官场上给予照顾,在交流往来之中,促进了视野的开拓,增长了见识,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赵之谦山水画艺术取向的形成。在其师友书画圈的影响下所完成的山水画作品有《积书岩图》《芝岩图》等。
(二)师从元人
在赵之谦山水画题款中经常会出现“临元人画”,如:为鹤年作《山水》团扇;“摹梅道人法”如:咸丰五年(1855年)为稷芝作《山水》轴;“临黄鹤山樵”如:同治三年(1864年)为景初作《山水》团扇;“略拟云林”如:为恬盦尊丈大人画《拟云林山水》折扇等等,可以看出赵之谦山水画艺术取向主要师从元人,元季四家王蒙、吴镇、倪瓒等是赵之谦师法的主要对象。
黄宾虹在《讲学集录》中说道:“渍墨。法出董巨,至吴仲圭为最妙”[5]。他认为吴镇善用渍墨为最妙,“化枯为润,补笔之不足”。从赵之谦绘画作品《摹梅道人山水》《积书岩图》之中所表现出粗重的用笔,厚重的点苔,浓淡湿润的水墨效果,渴笔则苍厚而不虚淡,在平淡中求奇险的构图意境,均出自于梅道人之法。
赵之谦绘画笔法的运用与王蒙也有着极大的共性。程邃在题画中曾这样评价王蒙:“黄鹤山樵画法纯用荒拙,以追太古,粗乱错综,若有不可解者,是其法也。盖能纯以草隶作画,笔力劲利,而无怒张之态,黑气酣厚,而无痴肥之病,于奇峭之中,得幽深高淡之趣,诚古今绝作”[6]268。王蒙绘画中的“纯用荒拙”在赵之谦看来则为:“南北两宗极至地位,无不归拙字”[1]1174。“画家拙与野绝不同,拙乃笔墨尽境”[1]1173。王蒙作画的“粗乱错综”,赵之谦则为戴子高作“无理画”《山水》折扇;王蒙“以草隶作画,笔力劲利”,赵之谦则有“以篆隶书法画松,古人多有之,兹更间以草法”;王蒙作画以“于奇峭之中,得幽深高淡之趣”,赵之谦则在绘画中表现为“平中取奇,险中求稳”和“宏肆奇崛,内蕴秀丽”[7]76。通过两者在绘画用笔上的对比,可见赵之谦山水画深受王蒙的影响。
倪瓒作山水画善于运用偏锋,用笔苍劲有力,常以干笔渴墨皴擦为之。他作画主要表现自己的“胸中逸气”,又有“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的心得体会。赵之谦在绘画题款中也曾说道:“聊作心影观,不求形迹似也”。倪瓒山水画呈现出疏而不简,简中寓繁,气韵荒寒的景象。赵之谦作画则有:“学由博反约,画以繁入简”[1]171的独到见解,可见倪瓒山水画的思想在赵之谦这里得到了很好地传承。简约之美,荒寒之气也可从赵之谦绘画作品之中读出。
(三)师从造化
赵之谦在山水创作中既注重传统、融化古法,又重视师从造化。赵之谦是浙江会稽人,古来便闻名遐迩的江浙山水,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创作素材,即便在今天仍是众多艺术家流连忘返之所在。赵之谦一生游历丰富,广闻博见,踏遍青山,拥有优越的山水画写生条件,其山水画写生现存世数幅。如同治元年(1862年)客居温州时为陈子馀①陈宝善(1821—1889年),字子馀,安徽歙县人,历任黄岩、钱塘、归安、山阴、会稽、永嘉、西安、临海等县知县。作《瓯江记别图》团扇描写瓯江一带的景象,画面构图别出心裁、拙野异趣,呈现出深远的意境。整个画面,空灵别致,笔墨所绘极少,近处坡石简笔勾勒而成,几株杂树交映生辉,扇面中心大块空白,异常空旷的江面上有一叶扁舟,江面远处露出汀渚一角,石坡上送行的两人与江中扁舟遥遥相望,以寄离别之情,达到了“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自然效果。笔简意长,回味无穷,给观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游乐清城西沐箫泉为王晋玉作《沐箫泉图》(图1)山水团扇等都是赵之谦师从造化的写生之作。由此看来,师从造化也是赵之谦山水画艺术取向的重要源泉。
综合来看,赵之谦山水画在其师从的影响下广收博采,而不拘泥于某一家。在追随缪幕期间、避乱温闽之时、客居京师期间,不同时期的经历都深深地影响着赵之谦山水画的形成;并以元季四家王蒙、吴镇、倪瓒为主要师法对象,在山水创作中既注重传统、融化古法,汲取各家所长,而不被传统所束缚;又重视师从造化,游历丰富,踏遍青山,为其山水画创作创造了条件。再加上赵之谦自身独到的理解和创作方式,从而产生别具一格的山水画风貌。
三、金石学的渗透与其山水画
(一)金石之缘
金石学是指对商周以来铜器上的文字和秦汉以来刻石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问,用来考证历史资料的真伪。黄宾虹在《论道咸画学》中说:“至清道咸,其学大昌,金石之学,始于宣和,欧、赵为著。道咸之间,考核精确,远胜前人;中国画者亦于此际复兴”[8]346-347。“直到道咸,金石学发达,一时名手如包安吴,赵撝叔辈亦数十人,不可谓非绘事中兴”[9]43。黄宾虹认为道咸年间,金石学发展兴盛,考核尤为精确,道咸年间中国画的复兴源自于金石学的兴盛。金石学在绘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石学的繁荣,带动了书画的发展,促使书画的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金石学的影响而致使“绘事中兴”,赵之谦则是受金石学影响的重要画家之一。
赵之谦作为“金石画风”的重要画家,自然受周围金石书画家群体的影响。十七岁时,开始专心研习金石之学,拜塾师沈复粲为师。而后追随缪幕拜学识渊博的缪梓为师,在缪幕中,闲暇之余,常与幕友周白山、胡培系、胡澍、王晋玉等有金石学考辨之事。而后避乱游走温闽,又结识影响自己一生的金石好友魏锡曾。赵之谦三十四岁左右入京,客居京师的十年,金石友对其影响巨大。赵之谦以其在金石文字考据学上的突出成就而立身于官场,金石鉴赏家和金石书法家的身份让赵之谦与程谦吉、沈树镛、潘祖荫、翁方纲、王懿荣等巨门公卿及收藏大鳄有了更好地交往。赵之谦不断丰富自己的金石之圈,在金石学的影响下,对山水画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将金石之气带入山水画中。
(二)金石成就
同治二年(1863年)赵之谦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白文印,款曰:“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1]215。赵之谦、魏锡曾、胡澍、沈树镛四人同时汇聚于京城,皆癖嗜金石。于京城构成最为核心的金石圈子,在京城所见金石甚富,让赵之谦大开眼界,为他金石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条件。在京城期间赵之谦相继完成《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等金石学著作。吴昌硕曾跋《天一阁宋拓刘熊碑双钩本》有云:“撝叔书画往往粗枝大叶,而金石之学考究极精,名不在巴君①巴慰祖(1744—1793年)安徽歙县人,工八分书,收藏金石甚富,在“徽派”印学地位很高,对赵之谦影响巨大。下”。吴昌硕认为赵之谦在金石学考究上的能力要高于巴慰祖,可见赵之谦在金石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赵之谦在金石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受此影响使之在绘画上有着不同的审美特点,正是山水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金石画风
蔡星仪在评戴熙山水画中说道:“其山水画笔墨效果仿佛近似碑版拓片的泐痕和青铜拓片的锈蚀印迹”[10]43。而赵之谦则是继戴熙山水画之后,“将这种源于新型金石学的审美观完全落实到笔墨形式、造型和色彩等绘画的外形式上,完成了这一个革命性的大转变”[10]43。赵之谦将金石画风在笔墨形式的运用上呈现出一种新高度。吴隐在《悲庵剩墨》序中说:“余嗜书画,尤嗜悲庵先生书画,鹤庐所嗜与余正同。悲庵工抚魏碑,于规矩严谨之中,极神明变化之妙。其所为变化,即其画笔之超群轶伦、不可方物者也,则书中有画也。悲庵善山水、花卉,以秀逸之笔,寓朴穆之神,其所为朴穆,即其书势之还醇敛锷,静与古会者也。则画中有书也,要非其人植品高,读书多,弗克以臻此。此悲盦之书画所为可贵也。”[1]2307赵之谦“画中有书”“书画相生”将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融合。他在篆刻上又有着超高的造诣,又将篆刻融于山水画之中另辟蹊径,打开了新的局面。形成了“古茂沉雄,戛戛独造”的山水画金石之风。
同治十年(1871年)为潘祖荫作《积书岩图》轴(图4),作品强烈的视觉效果,显示出赵之谦山水画高超的创作能力,足以看出是碑派笔法的影响。作品在用笔上,干笔与湿笔兼用,既有俊秀又有苍厚,山脚之下,虽空间狭小,水流奔腾而过,气势浩荡。所作水纹线条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用干笔复加淡墨,突出了水流的动感。同时赵之谦又以作松树之法“鱼鳞皴”的表现手法来画岩石,所绘岩石用墨浓淡枯湿交相使用,陡直的峭壁险峻无路,用笔苍劲斑驳、兼工带写,笔致迥与人殊,这是前人画家所未有的独创。山腰之上,嵌有一处洞穴,洞穴内石壁的纹理,纵横交错,依稀可见,远远望去犹如积书万卷的藏书库,所绘此图与史书中所说积书岩的形象如出一辙。作品寓意深厚,《水经注》中有云:“层山石室中,有书卷矣,而世士罕有达者。因谓之积书岩。”[11]积书万卷,“世士罕有达者”,为潘祖荫作此图来形容他藏书巨富,收藏之广,这也是众多金石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吧!山崖石间松树挺拔,枝干盘曲,葱翠欲滴。山脚之下溪水奔流不息,使人感到画面的威严庄重。画面构图布局,疏密对比极为强烈,可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这显然是得益于他在篆刻章法上的独到思考与见解。题款用最具金石意味的隶书和魏碑两种书体,庄严神秀。赵之谦此幅山水画作品将书法、篆刻与绘画相互融合得恰到好处,画面中表现出魏碑般的神韵,独特的个人风貌,表现了赵之谦在山水画上极具创新的一面。
赵之谦将其金石用笔巧妙地融入山水画中,打造出具有开创性的新风格,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仅如此,赵之谦还将其山水画带入篆刻边款中,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同治六年(1867年),赵之谦客居杭州,为曹籀刻朱白文两面印,白文“西京十四博士今文家”,朱文“各见十种一切宝香众妙华楼阁云”,刻印章边款时,见石有碎裂剥落,遂改造成挥洒丹青,就势刻就《石屋著书图》,“使刀如笔,视石如纸”制成写意山水,妙趣天成。

图4《积书岩图》
赵之谦是受金石学影响的重要画家。年少便结下金石之缘,并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金石之圈,为其金石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赵之谦巨大的金石学成就及周围金石书画家群体的影响之下,其山水画饱含金石之气。将金石碑派用笔带入其山水画中,并将其山水画带入篆刻边款,使刀如笔,视石如纸,形成了“古茂沉雄,戛戛独造”的山水画金石之风。
四、结语
综合来看,赵之谦山水画艺术取向广收博采。在思想文化上深受儒、道、佛、禅诸家思想自由精神的影响,在题材和内容上所展现的山水画风,有儒家“中和之美”的境界、道家精神之“神妙”“道法自然”的文化滋养,还有韵味十足的佛禅思想;其师从不拘泥于一家,既有不同时期书画友人深深的影响,又以元季四家王蒙、吴镇、倪瓒为主要师法对象,注重传统、融化古法,还重视师从造化,游历丰富,踏遍青山,都为其山水画取向创造了条件;年少便与金石学结下金石之缘,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金石之圈,在金石学巨大成就及周围金石书画家群体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古茂沉雄,戛戛独造”的山水画金石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