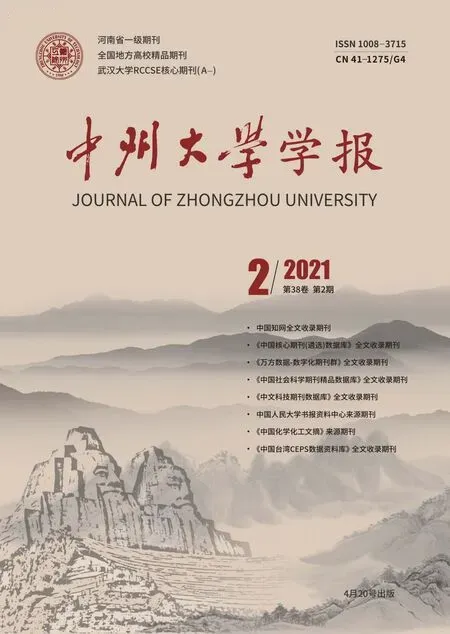论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
2022-01-01张翼
张 翼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19世纪中后期,现代科技进入中国社会的速度明显加快,触发了晚清科学小说的创作热潮。《月球殖民地小说》《新石头记》《新法螺先生谭》《电世界》《发明家》等科幻小说,《元素大会》《蚊之友爱》等科普小说相继问世。天文学、化学、物理、医学等科学知识,电灯、电话、火车、汽车、飞船等科技发明在小说中频频现身,一批行状传奇、性格特异的科学家形象也竞相出现在读者面前。
科学家现身晚清小说的意义非凡。首先,科学家的出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对象。古典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以儒家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并不适宜科学的生长,因此科学技术很少受到文学的关注,与科技紧密相关的科学家也很少出现在文本之中。晚清小说中科学家形象的大量涌现,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对象。其次,科学家形象承载了晚清知识者复杂的现代科技认知。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不同于古典的文人墨客,他们不再以才志情思取胜,而多凭借科学知识、科技发明创造奇迹,力挽狂澜,偶尔也因为过分依赖技术而表现出谬误偏执,成为被嘲笑的丑角或怪人甚至暴徒。形形色色的科学家形象,凝聚了晚清知识者面对外来科学文化、面对现代科技冲击时的微妙情绪。最后,书写科学家推进了晚清小说叙事形式的变革。晚清科学小说叙述科技如何影响民生、改造国民时,多依赖科学家的行动、心理推进情节,叙事重心向科学家倾斜,呈现了晚清小说由故事向人物、由情节向性格演进时的某些关键环节,也将限制视角带入小说叙事之中。
一
科学家必与专门知识紧密关联。晚清科学小说中,科学家的专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物理、医学、天文等方面。
晚清科学小说中,掌握物理知识的科学家不在少数。电学、光学、力学等原理赋予他们神功伟力,帮助他们创造了种种超自然奇迹,建构出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图景。《电世界》里的“电大王”黄震球就是一位精通电学的科学家,他利用“电”缔造了完美的“电帝国”。他致力于发明各种高效率的电学工具、机械,在他的万余种发明中,作为交通工具的“自然电车”速度“比沪藏铁路火车的速率增加五千倍”[1]3;作为筑路机械的“平路电机”“每小时可以平得十里五十丈阔的长路”,“滚过处没有不荡平如砥”[1]29;作为农用机械的“电犁”则“可以入地七八尺深。一耕便可二三百亩。”[1]32借助工具,他不断挑战自然极限。譬如他制造的“电翅”,能帮助人摆脱地球引力,飞升自如。他发明的“鈤灯”,能散发超乎想象力的光与热,使南北极终日长明,温暖如春,将苦寒极地转变为宜居沃土。他设计的“消雨云电车”可以将雨云吹散或聚拢,自由控制天气阴晴、降水多少。黄震球还将电学运用于国家治理。他创办电学大学堂,通过电筒发音机、电光教育画等教具刺激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率,普及教育,教化民众。他推行“电光审判”,用强光照射罪犯,使罪犯在强光刺激下供认不讳。他凭借“电翅”和“电气枪”,单枪匹马战胜了西威国装备精良的舰队。黄震球不仅仅将“电”应用于具体事务,还从“电”中抽象出价值观念,向民众渗透电的精神,即“积极的”“新生的”“光明的”“永久的”“缜密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1]55。
黄震球凭借现代电学获得无穷力量,也不得不见识电学所带来的对文明和人性的破坏,并最终陷入难解的困惑之中。为了斩草除根,黄震球一举引爆西威国的都城,看到战火摧毁城市、百姓痛苦挣扎,黄震球既为胜利而激动喜悦,也因残酷而内疚自责。此后他一直陷于被复仇的恐惧,引发了关于复仇是否合理的困惑。在他的主导下,“电帝国”仓廪实、衣食足,然而民众却渐渐滋生出奢靡纵欲之风,原本用于改善民生、造福大众的电学发明却成为犯罪工具。面对人心沦丧,黄震球有心改良却屡屡受挫。《电世界》终结于黄震球要去金星探险,虽然名义上他此去是为了寻找解救社会沉沦的良方,实质上却是避世归隐。
医学家也是晚清科学小说中常见的科学家类型。《生生袋》中的“客”,《月球殖民地》中的白子安、哈克参儿,《介绍良医》中的“医学博士”都具有医者的身份。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医学家医术精湛,面对种种疑难杂症往往能药到病除。《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医生白子安就是这样一位全才医生。当龙孟华乍闻妻子儿子仍活在世上,惊喜交加昏厥倒地时,白子安将几瓶药水“红的白的,黄的绿的,配搭均匀”[2]250,灌送下去,使得龙孟华即刻便苏醒过来。白子安还掌握了解除睡意的药水,克制毒气侵害的药水等等。他还具备高超的检验技术,利用分析仪器,通过药理分析,洞察死者的真正死因。
以常识观之,白子安的医术已属高超,但在晚清科学小说的众医学家中他并不突出。晚清科学小说青睐的是对人进行全面身体置换、进而进行彻底精神改造的医学家。他们并不拘泥于治疗人的局部病痛,而是要用手术等医学手段、器械等医疗工具使人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新法螺先生谭》里的“造人术”体现了这一类医生的神奇。“造人术”是将已死老者的头颅打开,取出旧物,灌入新质。它的效果惊人,“齿秃者必再出,背屈者必再直,头发斑白者必再黑,是能将龙钟之老翁而改造一雄壮之少年”[3]12。遗憾的是,此番描述重在介绍神奇的“造人术”,忽略了主导手术的非凡的医学家,仅以“二三人”一语带过。这一遗憾在短篇小说《介绍良医》里得到了弥补。《介绍良医》中的神奇手术是“换脏腑”,配套机械为“换脏腑机”,小说不仅对“换脏腑”这一手术方法、手术效果给予展示,还分出笔墨着重描写了主持这场手术的外国医学博士。他的外表迥异于中国人,“一身青衣裤,头上戴顶拿破仑帽,足穿一双高筒皮靴,黄黄的胡须,高高的鼻梁,凹凹的眼睛,拿着一根手杖,在椅栏上敲得砰砰的响”[4]50。他的见识更是异于中国人,他发明换脏腑的机器,目的是要将受毒化的脏腑取出,换上完好的,以“恢复天然的精神”[4]51。换人脏腑已然惊世骇俗,但洋博士并未止步于此,他发现世人心肠大多已被破坏,反倒是动物精神饱满,于是他大胆提出将动物脏腑替换给人,并通过各种努力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晚清科学小说显然更推崇这些通过置换脑汁、脏腑对人进行全面改造的医学家。这一点在《月球殖民地小说》的人物设置上也有明显体现。白子安的药唤醒了龙孟华,却难从根本上消除他的心魔。等龙孟华再次遭遇大喜大悲失了方寸,小说只字不提白子安,偏偏安排众人不远千里寻到了哈克参儿医师。哈克参儿擅长的恰恰就是类似于“造人术”“换脏腑”的“洗心术”。最终哈克参儿彻底治愈了龙孟华。小说从不吝啬对白子安神药的渲染,但危急关头每每遣出的却总是哈克参儿。如此人物设置、情节构建,显然是为了强调哈克参儿及其所擅长的全面置换、彻底改造的医学方法更胜一筹。
天文学家是众多科学家形象中格外引人瞩目的一类。借助天体构造、运行规律等专业知识,这些天文学家拥有了“宇宙”的观念,认识到是“地球”与其他星球共同构成了“宇宙”,不断思考着“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地球”与其他星球、“地球人”与外星人之间的结构关系。《新法螺先生谭》(1908)中的“余”熟谙地球、月球、金星、水星等天体的性质与规律,所以当他因宇宙间各星球的吸力而灵肉分离,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顺势而为,借机游历宇宙,有了一番奇遇。穿行于浩瀚宇宙之间,“余”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角度去观看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地球。他发现地球原来并非如自己所想的是宇宙之中心,而只是“如盆子口大小”[3]11。地球之外的诸多外星球,也刺激“余”油然而生比较的意识,他好奇地望向外星,观察地球所未有之物,积极学习地球所未经之事。当他与水星相遇,暗暗思忖的是“正可细心考察,比地球有若干差异之点”[3]11。初见金星,他想到的也是“必将他星球奇异之术,学成一二”[3]12。宇宙间的遨游、星际间的探索共同开阔了“余”的视野,当他构建交通版图时想的就不仅仅是“地球”,而是要建立“从太阳至各星球,及各星与地球,各开通往来之航路”[3]16。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天文学家经历宇宙间的“奇遇”,展示着他们豪迈雄壮的一面,也总是遭遇因天体碰撞而引发的世界“末日”,流露出他们感伤通透的一面。《世界末日记》描述了月球将与地球相撞,众人慌作一团,嘈杂纷纭的乱象。饶有趣味的是,月球逐渐逼近,海啸冰暴席卷地球的危难关头,小说特意安排一位天文学家向大众发布消息。这位天文学家,一方面依据天文学知识从学理上宣告了地球必将毁灭,另一方面又从精神上抚慰惊恐不安的民众,向众人指出:世界毁灭虽令人惊恐,但却是进化的一种形式,是会蜕旧易新的。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并不会消散,“渺渺天空,宁无寄我精灵之地,一念及此,又何用增其悲怀耶?”[5]天文学家的这番表述既有颓势难挽的伤感,也包含着劫后新生的期待。
二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掌握的科学知识各有侧重,外貌性情、举止行动千差万别,但其在叙述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外乎以下三种:
首先,科学家承担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晚清科学小说往往借科学家们的言谈,向读者介绍各种专业术语,解释各种科学原理。《水底潜行艇》聚焦20世纪的新型武器潜艇。为向读者介绍潜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小说最初通过“我”的视线将潜艇的说明图引入叙述之中,然而对于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初见潜艇的读者而言,即便看到详细的说明图也很难了解潜艇究竟为何物。于是小说特意安排一位青年博士登场,向众人进行宣讲,以便再次向读者介绍潜艇的发展历史,解释潜艇的工作流程,以解说的方式强化读者记忆。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先向围观的众人介绍潜艇的历史演进、设计标准与各国的潜艇数量、种类,接着便细致讲解潜艇构造,陈述包括“空气装置”“电炉装置”“安全装置”“磁针装置”“潜望装置”“武力装置”“通信装置”“水柜装置”“推进机械装置”等部分的名称与用途。随后,他以鱼鳔作比,阐明潜艇升降的原理。末了,他特意指出潜艇所适用的动力为“内燃机”,尤其是“最新式的内燃机,又名狄瑟机”[6]。“说明图+科学家”的情节结构,其意在向读者解释科学、普及新知。较之不能开口说话的“说明图”,能表达、有表情、有情感的“科学家”显然更贴近读者,也因此更适合承担这一叙事功能。
晚清科学小说不仅借科学家之口使读者熟悉专业术语、科学原理,更借科学家之思培植读者的数理意识、实证精神。科学家受其专业影响,数理意识突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这一特点。譬如《新法螺先生谭》中的“余”,观察描述事物多采用数字与比例,形容自己的灵魂之人是“用一万万亿之显微镜始能现其真相,其重量与氢气若一百与之一比例”[3]2,形容此灵魂所散发之光热则用“其光力之比例,与太阳若一万与一,与月若二百万万与一”[3]3。科学家也具有实证精神,他们不再执着于义理与情绪。《元素大会》里的化学家“我”向读者郑重宣称:“某之好为散步田间者,以有科学的兴味也。默识平日之所闻,一一证诸其事。”[7]“我”刻意地要挣脱传统文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思维模式、情感结构,见花即分析花所属之门纲目科,陈述其繁衍方式、实用价值,见山则分辨其岩石种类、地质类型,见水偏想到水中所含的无数微生物,告知读者为保障健康必须饮用沸水。
其次,科学家引导读者认识中国现状。《新法螺先生谭》的作者徐念慈陈述自己之所以写科学小说的原因是:“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8]徐念慈道出了大多数晚清科学小说作者的心声,他们陈列展示种种科学知识,其意却在剖析中国现状、探寻恢复强大中国的良策,科学新知、科技发明都只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因此,科学家解说知识原理是晚清科学小说的表层结构,小说的深层用意是要借科学家提醒读者关注时局政事,启发读者思考文明竞争等问题。
晚清科学小说中不乏直接参与政事、介入时局之中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往往还兼具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如《电世界》中的开创“电帝国”、以一己之力抵御外寇入侵的黄震球,《新纪元》里的统帅水陆大军远征寰宇、大战白种联军的黄之盛。但更多的科学家是通过类比、隐喻的方式提示、启发读者的。譬如《新法螺先生谭》中“余”,就是用“光”“迷梦”指代希望与现实。“余”欲借其灵魂之身所散发的光芒警醒中国人的“迷梦”,使中国人能够“奋起直追,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欧美人,而使黄种执其牛耳”[3]5。但中国民众仍是“嘘气如云,鼾声如雷,长夜漫漫,梦魂颠倒……而置刺眼之光明于不顾”[3]5。图强意愿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余”陷于愤怒、焦躁之中,甚至想与之同归于尽,以自身之毁灭破解中国之“迷梦”。“余”时而振奋、时而失望的焦灼情绪,贯穿小说始终,仅仅陈述自己的经验不足以纾解,“余”还就“迷梦”问题与他人展开对话。与“余”对话的是居于地心中国旧址的一位白发老者。此老者姓黄名祖,虽子孙众多,流布广泛,但多依赖祖宗,鲜有振者,大多“消夜方酣”[3]10。老者已经垂垂老矣,欲唤醒子孙却心有余而不力,他希望“余”能代自己传语子孙,打破子孙的迷梦。老者作为“中国”的化身自不必解释,“余”与老者的对话,老者对“余”的希望,也隐含中国民众萎靡不振、科学家“余”肩负唤醒国民重任等多重意蕴。
再次,科学家见证科技的负面与恶果,引发关于“现代”的反思。晚清科学小说并非一味地畅想科学昌明、科技发达,它们也没有忽略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负责普及新知,也必然见证科技恶果。战争是晚清科学小说用来刺激各类科技发明诞生的重要引信。《新纪元》描写了百年之后的黄白之战,它一方面反复强调科技已然发达,战争不再是斗力,而是斗智、斗学问;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回避战争,无法解释战争仍然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战场成为各种科技发明的竞技场,也成为绞杀无数血肉之躯的屠宰场。那些水底潜行雷艇、可化水为火的药水、能产生巨大热量的日光镜越是先进,杀伤力也越大。被潜行雷艇击中之后的战舰“震作数十块,并合舰的兵弁、器械纷纷然如蝴蝶一般飞起来,有的直飞到半空之中然后落下,只见满海面尽是黑雾浓烟,弥漫不散,把那一片坦平如镜的海水震得巨浪如山,掀腾不已。可怜舰上的一众兵弁,有的被震得血肉模糊,有的虽不曾受伤,然被它震到半天之上,又跌落海中,不保性命”[9]。虽然小说中也提到各国设立战争公约的情节,希望借规则限制武器使用,也通过刘绳祖因化水为火的药水杀伤力惊人,所以不向任何人透露药水的制作方法的情节,传达道德或可约束残酷行为。但战火如荼,人心炽烈,远非规则、道德所能控制,白种联军仍然使用了公约不允许使用的氯气,尸体横陈的惨烈场景在小说中仍十分触目。
科技的负面不容忽视,科学家也并不总是英雄。一些科学家凭借科技作恶,成为科学狂魔,如《消灭机》里哈味借“消灭机”随意使人消失。另有一些科学家成了丑角。他们为提升效率、解决问题发明种种器物,但他们并不能完全控制局面,甚至会受制于自己的发明。《发明家》里的施门士,热衷于机器发明,但他总是弄巧成拙。邻居黑莲夫人使用他所造的扫地毯机,结果在地毯上留下了无数小孔。另一位邻居司葛氏,使用他所造的宰鸡器,结果直接将鸡一分为二。施门士为制造机器耗尽家财,所造之物却使他逐渐成为众人厌弃、嘲弄的对象。终有一日,他误触机关,被自己发明的擦鞋器涂了满脸的鞋油。虽然小说的主旨是告诫科学家们必须要将科学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以发明一大有用于世界之物,则利用厚生,为惠滋大愿,勿为此琐屑之发明也”[10]。但是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科学家的意义远远大于此。滑稽的施门士透露出了晚清知识者在崇拜科学、排斥科学之外的第三种态度。
三
科学家形象一方面是由小说家们召唤而来的,用于呈现晚清科学技术、科学观念的发展动向,寄托小说家们关于中国与世界、时局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思考;另一方面,科学家形象自身也具备主动性,一旦他们进入叙述,就会向小说家们提出如何塑造他们,又如何处置他们与其他叙事要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阿英在论及晚清科学小说时认为:“大都是以小说的形式,说明科学的原理,作提倡科学、启发冒险精神的运动。惟就艺术上讲,殊无成就可言。”[11]阿英对晚清科学小说文学价值的否定已成定论,后世研究者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判断。然而从小说叙事形态的流变考察,晚清科学小说还是提供了某些演进的动力,尤其是科学家形象的出现促使小说出现了从故事到人物的叙事重心的倾斜,从全知到限制的叙事视角的转变。
不能否认,晚清的科学小说仍以“讲故事”为主,叙事的主要目的是要“输入文明思想”[12]。可是所谓“科学”毕竟是“分科之学”[13],晚清以来涌入中国的科学知识、科技发明种类繁多、体系庞杂,加之作家们介绍新知、输入文明的愿望极其迫切,要想真正使唤科学小说成为“启智秘钥,阐理玄灯”[14],小说家们必须直面如何尽可能多、尽可能全地向普通读者推介科学原理的难题。小说家们纷纷选择人物连缀来拼接科学知识、组合科技发明,科学家形象由此深度参与了文本叙事。如果说种种新知、新技术是一颗颗明珠的话,科学家就是串联明珠的丝线,使原本独立的科学知识、散落的叙事单元融汇为统一的整体,共同服务于教化民众、富强中国的叙事目的。如《新法螺先生谭》既涉及天文学的“星球”“宇宙”“卫星”,也包含物理学的“爱涅耳其”“离心力”“堕物渐加速之公纽”,还囊括化学的“氧”“氮”,更有一些很难被归类的、亦科学亦玄虚的“造人术”“动物磁气”“脑电”等等。作家本人缺乏对这些知识的深入研究,他获取概念的方式本就零碎①,唯有通过科学家“余”的经历,这些天文学、物理学、医学、化学的只鳞片爪的知识方才得以融会贯通,并突破各自的学科界限共同成为打破“迷梦”的工具,甚至突破具体“知识”的藩篱而试图构建新的道德体系。
晚清科学小说以人物为线索黏合叙事单元,或许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镜花缘》《水浒传》《儒林外史》已然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然而,晚清小说的人物连缀自有其新质。较之古典小说多依赖人物的行踪、言谈串联情节,晚清科学小说还不时地借助科学家的心理、情绪进行缝合,由此形成一明一暗两条连缀线索,明线是科学家的行为,暗线则为科学家的观念。《新法螺先生谭》《元素大会》等文本均明显表现出了明暗双线结构。科学家的心理活动因此被带入到叙事之中。《新法螺先生谭》开篇即是科学家“余”自述其科学观,之后“余”的喜怒哀乐与新知、新技术紧密交织在一起。如其身体一分为二后,“余于此时,不觉大喜,想从此考察一切,必易为力;然有一困难之问题也,因量过轻,不能留于空气中,则此身不知漂泊何所;将若行星之旋转空中乎,抑被大力者所吸,而牢固附丽于一处,将成永静性乎。余思及之大惧,幸也”[3]2。惊惧与侥幸的交错,物理定律与天文知识的融汇,孰重孰轻,已经很难分辨。通过这样的叙事安排,小说在普及知识的同时,也隐约呈现出一个血肉饱满、性情淋漓的“余”,表现出叙事重心由故事向人物的倾斜。
科学家本就在晚清科学小说中举足轻重,一旦他获得了性格,就不甘心只充当故事中被叙述的人物,而要成为讲故事的人,通过故事的讲述更深入地影响读者。出于解说科学的目的,不少科学小说都是让科学家充当叙事者,为增强科学故事的可信度,文本又总是会安排科学家们以“我”的身份发言。作为人物的科学家,了解诸多常人所不知的专业知识,甚至掌握着宇宙间的奥秘;然而作为叙事者的科学家,却只能说出自己看到的,而且只能从自己的角度陈述这一切。仍以《新法螺先生谭》中的“余”为例。“余”穷尽高山、极地,游历宇宙、地心,与形形色色的人事遭遇,看似无所不至、无所不知,但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是,他的所知所说全然来自他的个人经验,丝毫不涉及那些他所未经之事。比如灵肉分离这一匪夷所思的事件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些奇特的外星景观、外星生物是他亲眼看到的;玄妙离奇的脑电也是他本人学会并熟练加以运用的。但凡涉及他人的故事,文本就需要借助对话将“余”代入其中,如地心老者黄祖的所思所想,就要以“余”与老者相遇为契机,以“余”与老者的对话为主要形式,才得以展示。“余”执着地以自己的信用保证所言非虚,文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切发生的。这种极力想证明真实的叙事视角的确立,恰恰说明:“余”已经不再是古典小说里那个可以了解所有人、掌控一切事的叙事者了,他必须也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叙述故事。
当然,此时的“余”还与五四时期那些成熟的、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第一人称存在着差距。“余”还带有明显的“说书人”的痕迹,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召唤读者出场。《新法螺先生谭》开头,即以新法螺先生的名义提醒读者关注“余”的探险经历:“‘诸君乎,抑知余之历史,其奇怪突兀,变幻不可思议,有较甚于法螺先生者乎?诸君其勿哗,听余之语其事。’”[3]1之后,当灵肉分离发生之后,“余”一边描述自己由恐惧到超脱的情感变化,一边不忘向读者解释:“诸君乎,余灵魂之四分之一,爆出于数十丈外者,果何往乎?”[3]5但“余”与传统的说书人也不尽相同,他敢于向读者承认,自己经验有限,并非无所不知。如“余”来到了金星,一边感慨景观奇特,一边自知所知有限,于是他向读者说:“诸君乎,余所见仅一隅,实令人不可思议。”[3]12他也不掩饰自身局限,坦陈存在着他也无法解释之事。如《新法螺先生谭》结尾处,“余”分离的肉身与灵魂重新合并,他实在无法解释此事,只有告诉读者:“诸君,诸君,余已昏晕,实不能再举两身合一之原因,以报告于诸君之前。”[3]17
“余”既不同于五四的限制式的第一人称,也不同于传统的全知式的第三人称,他就处于二者的夹缝之中,呈现出过渡的色彩。“余”是无所不知的科学家,又是有所不能言的叙事者,这一独特的叙事特征也可以理解为隐喻:所知愈多,所能言者、所敢言者愈少?此种心态不仅仅属于“余”,也应该是晚清知识者的苦恼吧。
总而言之,科学家在晚清小说中的频频现身,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引发了文学表现对象及叙述形态的变化,也是一份蕴藏丰富的思想资料,留存了晚清知识者面对外来科学知识、文化冲击时的复杂情绪,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据考证,徐念慈很有可能是从《政艺通报》等报刊上的科普文章获知了以上概念。武田雅哉.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J].复旦大学学报,1986(6):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