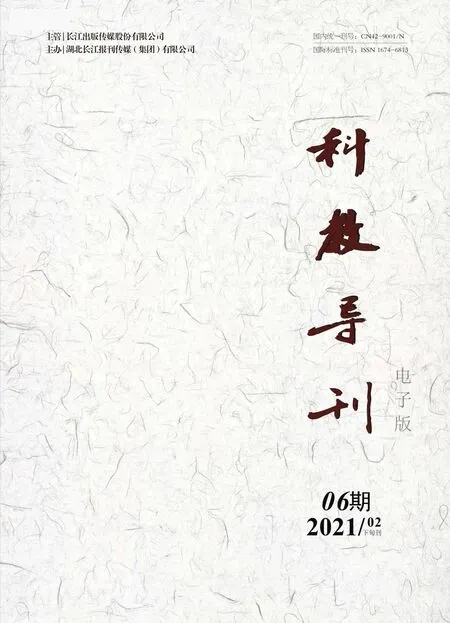从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谈宗璞的《红豆》
2021-12-31徐梓婷
徐梓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0 引言
文本世界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世界建构元素和功能推进命题是文本世界建构的两个组成部分,前者为文本世界提供背景,后者推动文本世界向前发展。在第三人称叙事中,有不用于第一人称的两个性质。首先是“非人格性”,第一人称是从“我”出发进行相应的叙事,而第三人称则是从他人视角来见证整个事件的过程。这里的“他人”就具有“非人格性”。在未知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第三者“直接”出现在小说中。读者在这样的视角下进行阅读无疑是为小说增加了神秘感的。其次就是“间离性”,这种“间离”指的是叙述客体和叙述主体之间在心理空间上拉开距离,这种拉开的距离会随着时间距离的缩短乃至消失作为陪衬。也就是说第三人称叙事是完全的“主人公故事”,“完成式”的故事情节与现在的时间是不会产生关系的。然而这样的心理距离却可以让读者听到叙述者内心的声音,没有所谓的“即刻性”,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一点对于读者的文本世界建构有了心理和情感上的补充,进而让读者在全知视角下体验到不同于第一人称的文本感受。宗璞的《红豆》就是基于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而展开的,对于小说主人公江枚的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都有全面的展开,同时还站在读者角度将男主人公齐虹与江枚的爱情故事通过江枚心理情感的辗转表现得甚是出彩。小说《红豆》可以说是在读者文本世界的建构上做得较好的作品之一。
1 第三人称的“非人格性”对读者文本世界建构的影响
第三人称的“非人格性”是不同于第一人称的“我”来展开叙述的一种“他人”视角。这里的“他人”可能是不存在的某一个具体人物,也可能是人们常说的“上帝”。在第三人称视角里,叙述者身边存在着一双看不见摸不着的“眼睛”,这双“眼睛”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或是心灵上的距离。这种“非人格性”使得读者可以自由的游走在被叙述的对象之间,从而拥有了比第一人称视角更大的叙述空间。例如《红豆》中的这样一段话:
江枚站起身来,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像怕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手,怔了一会儿,后来才用力一揿耶稣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墙上露出一个小洞。江枚踮起脚尖往里看,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她低声自语:“还在!”遂用两个手指,箝出了一个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
在该段文字中,读者可以清晰的看到江枚这个人物的动作全过程,包括心理的反应“像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触发的动作“伸出手又缩回手”。这样的过程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是难以看到的。当身为第一人称“我”这样进行描述时,会容易让读者产生“跳戏”的感觉,同时,也有违正常的叙事方式,会产生一种“突兀感”。相对比茹志娟的《百合花》,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例如:
唉!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在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不同于第三人称叙述的视角。《百合花》中的“我”只看到“他”的动作,而我自己的动作更多的是通过自我阐述的方式来展现给读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中就能听到叙述者本人的心声,甚至可以自然而然的表述出来,而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描述自我的心理就显得有些刻意。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本来是对江枚的动作描写而后自然转变到江枚的心理描写,相比较之下,第一人称的描述在动作到心理的描写上就具有一定的过渡过程,“自然感”大大的减少了。正如凯伦·赫斯所说:“第一人称叙事的一个主要弊端是不能有效地运用在描写人物心理的故事里。”因此,第三人称视角在逗留于人物的外部做观察时,还能潜入人物的内心做心理透视。在这一点上,读者的文本世界建构因为从外界到人物内心的距离缩短而得以完整。
2 第三人称的“间离性”对读者文本世界建构的影响
米歇尔·布托尔曾提出:“只要人物面对的完全是第三人称的叙事和没有叙述者的叙事,那么在小说中的事件与包含这些事件的时间之间就显然不存在距离。这是一个稳定的叙事,不论是谁,也不论什么事件给读者讲故事,叙述自身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其存在实体。”其意旨在说明在第三人称叙述中主要以“完成式”的方式讲述的事件,这对于读者所处的时空来说是与文本时空脱离关系的,读者可以在现有的时空里见证整个事件,同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完善小说中没有提到的细节之处,这样一来就会营造一种让读者不忍离去的“依恋感”。例如小说《红豆》中的这一段文字:
她还是天天去弹琴,天天碰见齐虹,可是从没有说过话。本来总在那短松夹道的路上碰见他。后来常在楼梯上碰见他,后来江枚弹完了琴出来时,总看见他站在楼梯栏杆旁,仿佛站了很久了似的,脸上的神气总是那样漠然。
在这段文字中读者仿佛可以从文字中看到江枚对于齐虹的那种在短短的时光里萌芽的爱情以及面对爱情的那种羞涩。通过“上帝视角”对齐虹脸上神情的观察,间接表露出江枚对齐虹的暗恋,但是彼此又有一层窗户纸从未被捅破似的,然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对两人动作的描写却透露出了这一点。这样的叙事方式与表达两人关系的视角只有通过第三人称叙事才能向读者呈现。这也利于读者因为对整体的把握而产生想象,从而让其文本世界更加的丰富。对比第一人称的叙述,第一人称下的事件叙述就让人缺少了“现实感”与“想象性”。例如: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下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茹志娟的《百合花》均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展开的,上述文字就是女主人公“我”对男主人公“通讯员”产生情愫的过程以及心理描写。这一段文字写得很委婉但也不难看出“我”对“他”的爱恋之心。然而在这段叙述中是通过“我”的视角对“他”的描写,对比第三人称叙述的角度就缺少了“我”这一环的动作描写,给读者呈现更多的是“我”对“他”的关注,而“我”自身与“他”的具体关系却难以让人捉摸,这就让读者缺少了“想象性”的支撑点,进而也缺少了文本世界的整体建构性。读者在阅读这段文字时得到的只是单一的心理或动作描述,身为“旁观者”的超脱感完全被第一人称的“我”给丢失了。在这种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给人以不动声色、不露情感的人物故事展现,在这种叙事里作者对叙事者的把握和读者对叙事者的理解是共通的。它为读者对叙事者的情感投入提供了有效地途径,因而增强了读者对文本内容的画面感,这种“反主体性”的输入有利于读者文本世界的建构。
3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文学叙事语篇中,叙事人称和叙事视角会影响读者的文本世界建构,而通过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三人称的叙事之下,文本世界能更好的展现在读者眼中,同时还扩大了读者对于文本理解的广度与宽度。全知视角会让读者跟随叙事者的眼光而改变,但同时也会让读者更好的进入到角色中,从而理解人物动作,透支人物心理,建构自己的文本世界。全知第三人称叙事者虽然在故事之外,但却可以在小说任何层面的文本世界中存在。当叙述者转换叙述视角时,阅读者的目光也会随之转换。《红豆》中的双重叙事,即对革命与爱情的叙事,就是在这样的视角转换中得到大众的认可与关注。无论是小说中体现的“非人格性”叙事还是“间离性”的叙事,都在全知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带领下,让读者体会到《红豆》中的情态世界。首先是对齐虹的整体塑造,其次是江枚的最终选择。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作者采用的叙事视角均是第三人称叙事,也只有用“他人”的眼光,才能使读者读出齐虹身上的温柔多情与江枚最终选择中的人情味和现实性。正是由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者位于小说之外,读者常常把作者当做语篇世界的作者,把叙述者角色可及世界当成是语篇世界参与者可及世界。简而言之,就是读者在阅读《红豆》时,会不自觉的将作者当成小说中的主人公,而会把自身当成是与主人公有关的人物带入到小说情节中,这就形成了读者感官上对于小说的深层次理解,第三人称的“间离性”对读者文本世界建构的影响得以体现。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在小说《红豆》中随处可见,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被作者宗璞展现了自身的优势,但其分裂了语篇时间与现存时间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肯定的。小说的叙事是“完成式”的叙事,读者在体会文本时的心态却是“现在式”的,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导致小说《红豆》在不同的时代对读者的影响力是不同的。然而大多数应时代而生的作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宗璞在小说《红豆》中对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出彩运用与展现使得该部小说经受住时代浪潮的汹涌,在新生代作品的翻滚中脱颖而出,稳住一席之地。小说女主角江枚的人情观与人物成长历程正是在宗璞第三人称叙事的角度下,使读者印象深刻,展现了新一代女性的情爱观,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给予读者最清晰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