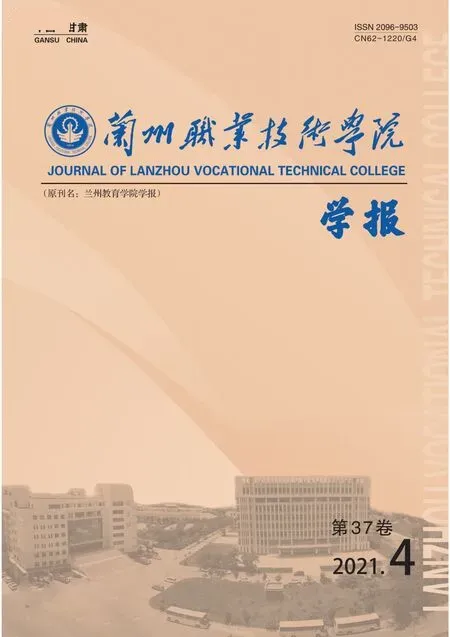审美空间下意境的构成方式
2021-12-31孔祥睿
孔祥睿
(青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从词源上来看,“意境”是“意”和“境”这两个词在分开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本文拟将“意”和“境”分开来探讨。从“境”入手,探讨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境”逐渐带有的空间性含义。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的“象”,不仅是简简单单的物理性质的存在,这些“象”早就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是带有创作者主观意志,也可能是创作者的触“象”生情,这个时候就会有氛围的产生,“意”开始崭露头角。“意”不仅指的是在世间的我们所具有的主观情感,而且还包含着我们的理想、志向和精神的升华,在此基础上,意境、意象也就随之产生。
一、“境”的空间性
现如今高校各个版本的教材中“意境”的定义如此:“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能诱发和开拓出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的整体意象。”[1]这种对于意境的定义过于单薄,忽视了“境”在其中所具有的空间性,从而使“境”不再立体化、动态化,而流于平面化、静态化。不得不说,这个定义显然是受到了王国维先生关于境界的解释,在《宋元戏剧考》中,他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2]可见王国维强调的“境”是由情、景、语言构成的平面结构:情深切、景真实、语言自然。然而,他却很明显地忽视了“境”的空间特色,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于“境”的空间性的理解,同时也与“境”甚至是意境的形成历史过程不符合。
“境”的本字是“竟”,“竟”在古代汉语中有三层含义:一个是音乐的终了,后来由音乐引申到领土、疆域和边界的意思,再后来又上升到精神和心灵的领域,如在庄子《逍遥游》“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3]中,便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层含义,人们在“竟”的旁边加上了个“土”字就变成了“境”。其次是所处地方的意思,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最后才是意境的意思,如在《世说新语·排调》中:“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到了唐代王昌龄的《诗格》第一次提出以“境”论诗,随后皎然、刘禹锡、司空图都沿用了这个概念,到了宋代以后,以“境”论诗、以意境论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直到清代的王国维,成了“境界说”的集大成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对待“境”这个概念的认识大多简单地停留在:“境”是人们的一种外在对象所带来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还分为实境和虚境,并且更多的偏向于虚境,正像清人方士庶《天慵庵随笔》云:“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4]136
清代的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说:“须知意境中有海阔天空气象,有清风明月胸襟。”[5]593其中的“海阔天空”“清风明月”已经略带有空间之感了,显而易见,古人好像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境”含有空间之意,但是总还是不经意之间透露出一二,直到宗白华先生才真正认识到“境”所带有的空间性质,他提出:“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特征,是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内身化,这是艺术境界……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6]59-60“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6]63可见,意境并不是平面化的,而是立体空间性的,“境”带有特殊的空间性。
二、说“象”
既然“境”带有审美空间的性质,意境必定会有高度、深度和广度,那么,在艺术创造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象”的不同排列组合方式,将“境”这个空间填满。
(一)“境”中跳跃性的“象”
所谓跳跃性,就是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所提到的事物从表面并不能很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们的关系是潜在的,正是这些在表面上看起来丝毫没有什么关联的事物,在深层次却能够将紧密联系的事物组合起来,既扩大了“境”的审美空间,又能够达到期望达到的审美效果。举例说明,温庭筠《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在这首诗当中“象”很丰富,“晨”“客”“故乡”“鸡声”“茅店”“月”“板桥”“人迹”“槲叶”“山路”“枳花”“驿墙”“杜陵”“凫雁”“塘”,这些“象”一个一个来看,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性,但是在一些动词的连缀之下,却显得格外有感觉,比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句,并没有像其他句子一样运用动词进行连接,而仅仅只是三个“象”的简单排列,就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了出门时听见鸡鸣,走出茅店,天边挂着晓月,山路上已有新足迹,木板桥上一层薄薄的寒霜。凄楚悲凉的情感油然而生,正是因为这些散碎的“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审美空间,即“境”。
“鸡声茅店月”这一句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没有运用动词对“象”连缀,具体什么样的鸡鸣、什么样的茅店、什么样的月以及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都不得而知,反而留给了读者无限创造的空间,这也就是不同的“象”构成不同的“境”,反而是越带有跳跃性的“象”,越能激发和牵动出更多的审美空间,同时,“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句诗只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象”,在“象”和“象”之间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而这些空白之间的联系正是潜在的、隐秘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虚”,总结来说,就是在艺术创作中象的跳跃性,进而产生“虚实相生”的效果,带来更多及不同的审美意蕴的“境”。
(二)“境”中有序性的“象”
“象”的组织方式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上文已经说到的“境”中跳跃性的“象”的排列组合方式;另一种是人们有意而为之的“境”中“象”的排列组合方式,我们称之为有序性。有序性是指在“境”这个空间之中,所有的“象”不仅要遵循情感的原则进行排列,而且还要遵循空间的原则:不管是有序的横向安排,还是有序的纵向安排,都要使得“境”具有空间所具有的宽度、深度和广度,具有“境”独特的审美氛围。同时,在“境”中的“象”也要具有混沌一气、浑然天成的气质。举例说明,杜甫的《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其中“万里”“台”是空间上的一种延伸,为的是扩大审美空间,“百年”“秋”是时间上的开拓,为的是深化审美意蕴,这一句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错,构成了“境”深厚宏大的审美特征。再如《登楼》中:“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在“境”的空间营造中,同样深得时间的开拓和空间的延展之妙。可见,在创作过程中,“象”的横向延伸和纵向开拓构成的是“境”的三维空间的拓展,由此确定“境”的氛围和情感。
在“境”中的“象”,不仅仅具有扩大空间意蕴的作用,同时这些“象”之间又要保持混沌一气、浑然天成的气质。换句话讲就是:将整个“境”中的每一个“象”进行归纳、连接、整合,最后成为闭环,使其形成一个完满独特、内在精神丰盈的审美空间,借此显示出“境”的空间之中所具有的浑然天成的审美意蕴。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到:“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5]585强调的就是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具有鲜明的混沌天然之感,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整首诗运用“前”“后”“古人”“来者”,带有闭合性,形成环抱式的混成自然的效果,在封闭式的“境”中具有特有的审美氛围。再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诗“象”的运用总是被后人称道,开头接连使用了丰富的景象展开整首诗,末尾的两句是情感的深化。随着景物的展开,诗所要呈现出来的缠绵悱恻、气势恢弘的“境”亦然展现出来,最后由景化情使得整个“境”闭合空间,才可以说作品臻于完成,创作主体的情感在所形成的“境”的情感氛围中回环荡漾。
在“象”和“象”的排列组合之中是留有空白的,我们将其称为虚实;同样,在“象”所构成的“境”中,一样要留有空白才能证明“境”,也就是审美空间的存在。苏轼曾讲:“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5]282在这里的“空”并不是“无”的意思,而是空间中的空白之意,就好似老子讲过的“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方熏在《山静居画论》中评论石涛的《风雨归舟图》时说:“石翁风雨归舟图,笔法荒率,作迎风堤柳数条,远沙一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处?仆曰:雨在有画处,又在无画处。”[7]在这幅《风雨归舟图》中,并没有刻意的画雨,却好似画了雨,有妙笔生花之感、无中生有之妙。可见,不管是“象”和“象”之间的空白,还是存在于“境”之中的空白,都是“境”带有审美空间性质的一个有力证明。
三、审美氛围的产生
“境”带有鲜明的空间性,并且在“境”之中有“象”的存在,不管是“象”的跳跃性排列组合方式,还是有序性的排列组合方式,最终都是为了“境”能够带有韵味,而我们就将这种韵味统一称之为审美氛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氛围”的解释是:周围的气氛和情调。可见氛围所强调的是全部而不是局部的特定的气氛和情调的融合,也就是“象”的组合方式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境”也就顺势带有了气氛和情调,即,产生了一种新的情境,创作者在这样的情境中便会有情感的变化、心灵的起伏,而产生不同的感知和情绪,所有的“象”和空间的“境”都只是外部条件,最终为的是凸显人物的情感变化。不管是外在的“境”还是内在的“象”都只不过是条件,创作者特意去营造一个氛围,为的是将情感和“象”融合,甚至和“境”融合,而更好地阐述“意”。
例如,在《牡丹亭·惊梦》中,杜丽娘学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便开始游览后花园,看见春色满园,心中是对无限风光的流连忘返,但是转头又看见断壁残垣,不免生出伤春之感。由此可见,在“境”中的“象”能够营造一种审美氛围,身在其中的人物是会受到整个氛围的影响而产生与之相应的情绪的。而后面杜丽娘做梦、在满园春色中与柳梦梅“紧相偎,慢斯连”,再一次营造了缠满悱恻的甜蜜氛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审美氛围是依赖着“境”中之“象”生发出来的,王夫之就说过:“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8]根据上面的说法,“象”是情之“象”,情是“象”之情,不管是梦前还是在梦中,都能看出有“象”“境”和深陷其中的人们之间的完美融合,为的是表达他们的情,为的是抒发他们的“意”。
四、说“意”
在上面我们谈到审美氛围的时候说到了:审美氛围的产生有利于创作者、读者甚至是主人公情感的抒发,有利于“意”的产生,但是这并不代表情感就是“意”的全部。
“诗言志,歌咏言”是中国最早的诗歌理论,但是对于“志”的理解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总的概括起来不外乎有那么几个:理想志向、人们心中的情感以及记忆。在我们日常的使用中,更多偏向的意思是理想志向和人内心的情感,鲜少用“记忆”这个含义。《诗大序》对“诗言志”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9]唐代的孔颖达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10]如此说来,“意”是介乎于“情”和“志”之间的一种存在,与“志”相近,但是更偏重于“情”,其实在许多的诗论、词论中,将“意”和“情”当作是等同的来使用,但是其实不然,“意”的含义要比“情”的含义丰富、复杂得多,“意”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不难理解:在“境”的空间里由“象”构成的审美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整体上把握作品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趋向,像明代黄展肃在《诗法》中就强调:如果你要作诗,必须先要立意。宋代的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提出:“常为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4]120由此可见,“意”不仅不能等同于“志”,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情”,不管是偏向于“情”还是偏向于“志”,都是创作者在“象”和“境”的基础上、在整体的审美氛围的熏染下所形成的一种主观意志,是非常重要的,要放在首位的。
“意”的生成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不光有“象”和审美氛围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受到创作者本身的影响,“境”中的氛围烘托出创作者的胸中之“意”,那么这个“意”便带有了志、情两个方面的内涵,创作者胸中之意就是志、情两者的结合体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在这里论述“意”,更多侧重的是创作者的胸中之志和触“象”生的情在审美氛围中相互作用、互相激荡最终生发的“意”;另一种是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已经不再是纯粹客观的了,而是渗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志、主观情趣,这时候就是“境”“象”和审美氛围以及“意”的完美融合。换句话讲就是,创作者胸中之“意”一旦碰到“象”就会成为意象,“意”一旦碰到“境”就会变为意境。例如在杜甫的《秋兴》中:“雨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这首诗借用“雨露”“枫树林”“巫山”“巫峡”“波浪”“塞上风云”“丛菊”“白帝城”等一系列的“象”,配上“凋伤”“萧”“阴”“泪”“寒”等形容“象”的词语加以点缀,再配上“刀尺”“砧”等声音,在整个“境”中给人带来的是一种风萧萧兮、动荡阴森的氛围,同时彰显出的是感慨万千、悲凉豪壮的“意”。
作品审美氛围的形成,不仅仅是由“象”所构成的,更多的是受到创作者的胸中之“意”的直接影响,比如我们还是上面所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氛围,进一步,“象”和诗人的“意”结合在一起相互转化,诗之意就开始出现,接下来就出现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佳句,诗中的氛围喷然而出,诗中之意也就油然而生。
五、结语
意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境”中可以给欣赏者带来广阔的审美空间,在这里面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去想象、去创造,不留有空间的“境”,也就不再有“意”可言了,一部作品如果留有的空间越大、越深、越广,往往它就越富有韵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还有“象”的存在,不仅要有带着创作者主观意志的“象”,还要有能够引起我们胸中之“意”的“象”的存在,而这些意象总是能勾起人们的某种情感、理想甚至是志向,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氛围,让人享受其中、沉迷其中,更加有利于情感的进一步喷发,更好地表达作者心中的“意”,也让作品更带有“意”,最终形成意象、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