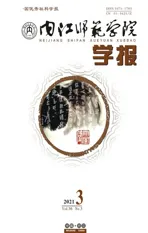近百年来郑孝胥研究综述
2021-12-31林昊,潘崇
林 昊, 潘 崇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亦作苏堪、苏勘),号太夷,又号海藏,晚年号夜起庵主,福建闽县人。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复杂,涉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领域,集政治家、诗人、书法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且交游广泛,人脉丰富。政治上,他早年出使日本,归国后游弋于张之洞、岑春煊、端方、锡良等人幕府之中,充任幕僚并投身各项改革实践。清末时期曾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倡导宪政并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进入民国后,他以“遗老”自居,视民国为“敌国”。晚年则遗憾变节,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帮凶。经济上,他曾入股大生纱厂、商务印书馆,创办日辉呢厂。文化上,他工诗善书,是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有“海藏诗派满江湖”之誉,著有《海藏楼诗集》,其书法亦自成一派,声誉显著。教育上,他曾出任中国公学监督。郑孝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多栖历史人物,在多领域留下深刻人生印迹,其人物研究亦长期以来受到学界重视。笔者梳理总结百年来有关成果,以期彰明成绩和不足,从而裨益于郑孝胥研究的纵深发展。
一、1949年前的郑孝胥研究
早在清末民国时期,郑孝胥尚在世期间,时人即对其人品、诗歌、书法等方面展开评论,相关文字散见于各类笔记、诗话、报刊之中。
1903年,郑孝胥随同两广总督岑春煊入桂,督办广西边防。1905年,孟森担任郑孝胥幕僚时,曾随郑氏视察广西边事,后参考公私笺奏、函牍等资料,撰成《广西边事旁记》一书,涉及广西边防、军事、经济、教育等内容,对研究郑孝胥在桂期间的活动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沃丘仲子(即费行简)1922年出版《当代名人小传》,将郑孝胥归于“清室遗臣”一类人物,认为其人“与张謇齐名”,但“孝胥所谋辄败,是不尽系人事也”[2]。胡思敬称郑孝胥“好为大言”,天下大乱实因其铁路国有和借债修路之献言而起[3]。金梁评价郑孝胥“识力、议论皆好,较叔衡、子培伉爽”[4]。甘簃(即陈灨一)将郑孝胥视为钻营投机之“政客”:“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数数预谋,实一政客也”[5]。伪满洲国成立后,时论多不齿郑孝胥与日本狼狈为奸,将郑氏与历史上的严嵩、蔡京等人相提并论,斥其为汉奸、卖国贼、丑角、傀儡[6]。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抵制郑孝胥售卖书画的呼吁[7]。1938年,叶参、陈邦宜、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这是最早的一部郑孝胥传记著作。该书站在伪满洲国的立场上全力吹捧郑氏,认为正因郑氏坚守王道学说、“始终疾恶共和”,“全国各地之治安、建设、产业、教育等等,无不蒸蒸日上”,故称其“献身国家,造福民众,其丰功伟绩,指不胜数”[8]。
关于郑孝胥诗作和书法,时人也多有评价。1912年,与郑孝胥往来密切且有同乡之谊的陈衍对其诗作评价极高:“苏堪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榭,浸淫柳州,又洗炼于东野。沉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9]大可通过考察郑诗渊源、诗格、诗功、题材,认为郑诗“早年主涩,晚年主浅,而要皆以真为贵”[10]。陈士廖将郑孝胥诗作从内容上归纳为郑重九、郑龙州、夜起庵、怀人亭、濠堂与欧榭盟、咏花木、磨墨诗等类别[11]。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晚年政治变节,极大影响了世人对其诗歌的看法。1932年,陈衍对郑诗做出迥异于以往的评价:“专作高腔,然有顿挫亦佳,而少变化,更喜作宗社党语,极可厌。近来行为益复丧心病狂,余与绝交久矣。”[12]汪国垣(即汪辟疆)曾将郑孝胥比作水浒中的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赞其“早岁文章近老成”、“义宁句法高天下”[13]。后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则认为:“诗自是射雕手,然晚节不终,非惟不可与钤山堂并论,且下阮圆海、马瑶草一等矣。”[14]潘伯鹰将郑氏诗歌与其行事结合起来考察,认为郑氏“负奇振异自命不凡”、“不择手段遂行其不凡”、“中年作官的心最热”,其所作诗篇对上述内容有淋漓尽致的反映[15]。1930年,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对郑孝胥书法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郑书“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16]。1942年,推崇郑孝胥书法的张谦在天津刊印《郑海藏先生书法抉微》一书,指出:“先生之书,豪迈浑穆,深得汉、魏,六朝碑版神髓;茂密俊逸,得力于晋、隋诸贤,故可谓为集近代碑学帖学之大成者。”[17]
综上,清末民国时期时人对郑孝胥的评价褒贬不一,多数因其晚年变节将之称为汉奸,而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对其诗作的评价,不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郑孝胥的诗歌成就。这一时期留下的相关评论,普遍简略且不乏主观倾向,尚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因是当时人记录当时事,具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
二、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郑孝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风气逐渐转变,郑孝胥研究开始步入学术正轨。80年代,出现两篇探讨伪满时期郑孝胥的研究文章。杨照远梳理了郑孝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将之论定为洋奴汉奸[19]。赵聆实则着重揭露了郑孝胥王道思想的欺骗性,认为该思想是伪满“建国精神”的基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20]。此外,赵沛霖在稿本《记女怜金月梅母女事迹》中发现郑孝胥两首佚诗,并分析了郑孝胥与金月梅的情感纠葛[21]。
1993年,随着郑孝胥书法作品、日记等史料的出版,为学界进一步展开郑孝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中国书法全集》大型丛书,当中第78辑为“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卷”,收录郑孝胥《苏戡手抄太白诗》《郑孝胥赠善甫三兄四条屏》《郑孝胥跋翁同龢函札》《郑孝胥王道书院讲稿》等书法作品。该书主编王澄评述了郑孝胥书学思想及其楷、隶、篆、草四书的取法,认为他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可资借鉴的东西”。但遗憾的是,因“人品不齿于国人”,致其艺术地位与艺术成就并不相称,给后人留下“引以为戒的惊叹号”[2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对郑孝胥书法艺术做出系统讨论的文章。同年,更引人瞩目的则是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由劳祖德整理的《郑孝胥日记》的出版。该日记起自光绪八年(1882),迄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仅小部分有缺。劳祖德对郑孝胥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生当封建末世,颇知民生疾苦,早岁奋发有为,深思力学。……平素自许过当,好为严刻之论,……终则以贞事一人为节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由遗老沦为国贼,助桀为暴,身败名裂。”[23]《郑孝胥日记》的出版,极大推动了郑孝胥研究的深入。
整体研究方面,周一良依据郑氏日记将郑孝胥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是杰出诗人又是主张维新的政治活动家;辛亥革命后二十年,誓忠于清王朝,甘为遗老,在溥仪小朝廷任职;1932至1938年,则沦为卖国的大汉奸[24]。这种分阶段评述郑孝胥的思路为后来学者所认同和继承。罗继祖根据郑氏日记分析其人政治得失,赞同劳祖德用“国贼”一词代替“汉奸”来评价其人[25]。此外,有学者赏析了日记中“独特的妙语”,肯定了该日记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资料的价值[26]。
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对郑孝胥早年政治活动展开研究。周劭认为对比于黄遵宪,郑氏用“汉文化和他们(日人)酬酢”,不算是真正的文化交流。在诗歌创作上,郑氏的影响力和地位则不及黄氏[27]。李白凤考察了郑孝胥1903-1905年在龙州期间实施的“应革应兴事宜”,肯定了郑氏为保卫边疆所作的贡献[28]。汤志钧考察了甲午战后郑孝胥在张之洞授意下赴京窥探政局以及与帝党人员往来的情况,批驳了郑氏早年出驻日本期间即与日本相勾结的说法[29]。徐伟民通过分析甲午战争时期郑孝胥的活动与言论,指出郑氏坚决抗战、反对割辽割台,表现出较强的民族自尊心且初步形成变法思想[30]。陈来幸指出郑孝胥任职神户兼大阪理事期间对中华会馆的创建起到了指导性作用[31]。此外,沈必晟从艺术学视角探讨郑孝胥书法,认为郑氏早年重帖学,善正、草、隶、篆、行书,楷书及行楷书最显个人风格,其书学观突出表现为“碑帖互重”和“执两用中”两方面内容[32]。李侃聚焦郑孝胥在伪满洲国建立初期的所作所为,强烈批评其为历史罪人和民族败类[33]。
综上,得益于相关史料特别是郑氏日记的出版,加之学术风气的转变,这一时期学界对郑孝胥的研究,开始摆脱历史人物研究中形而上学、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普遍开始分阶段地展开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郑孝胥在甲午、戊戌年间的早期活动轨迹做了富有价值的探索,标志着郑孝胥研究开始步入正常学术轨道。
三、21世纪以来的郑孝胥研究
21世纪以来,学界对郑孝胥的研究渐趋客观多元,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笔者统计,近二十年来,涌现郑孝胥研究专著两部,论文达到百余篇。笔者拟分门别类,从整体研究、政治活动研究、诗歌研究、书法研究四方面着眼,对相关成果做一系统论述。
(一)整体研究
2003年,徐临江出版《郑孝胥前半生评传》一书。该书采用“文化为主导的论史衡人多维评价系统”,考察了郑孝胥成长环境、出使日本、入幕张之洞并参与维新运动、广西筹边以及参与立宪改革、清末路政等活动,认为郑氏人生历程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成长起来的保守型文化精英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抉择[34]。2018年,李君出版《1931年前郑孝胥》一书。该书共七章,涉及郑孝胥家世、清末仕宦生涯、辛亥革命前后活动、遗老生涯、复辟努力、人生哲学“行藏”和“节义”,尤其重点分析郑孝胥的个性气质、心态情感、学问思想等在其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作者认为,郑氏一生,“既独立不惧,特立独行,又干谒竞进,宦游俯仰,趋近功名”[35]。该书史料翔实,论述清晰,客观地把握郑孝胥在时代变革下的个人遭遇,展示出其人生状貌的“变”与“不变”。总的看,两本论著皆试图以新的研究思路,呈现郑孝胥这一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但不无遗憾的是,两本论著或择取郑氏前半生、或截止郑氏参与伪满洲国之前的历史时段展开具体论述,回避了其晚年更为复杂的一面。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广州好教育的美好愿景,将广州“好教育进行时”进行到底,实现这个美好愿景已为期不远了,我对此充满信心!
近年来,若干部学位论文从人际交往视角展开郑孝胥研究,反映了学界的新动向。曾祥明以郑孝胥晚年社会交往与政治选择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郑氏与革命党、北洋军阀、遗老、外国人的交往,认为郑氏从文化遗老到政治遗老的转变过程受到其新旧杂糅、中外混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36]。朱静梳理了清末民初郑孝胥与政府官员、立宪派、“同光体”诗人、晚清遗老等群体的交往关系[37]。郝惠谋探讨了郑孝胥与封疆大吏、师辈、名士、日本人、书法家的交游对其书风形成的影响,认为郑孝胥“艺术生命的立体性正仰赖其一生广泛的社会交游才得以建立”[38]。
(二)政治活动研究
1.郑孝胥与晚清政局研究。学界进一步梳理和分析郑氏在甲午戊戌时期的言论与活动,关注到郑氏作为立宪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相关研究重视时代环境对郑孝胥的影响,普遍不因其晚年变节而全面否定其早年作为,相关结论更趋客观。
李振声考察了1891-1894年间郑孝胥出使日本期间的活动,认为郑氏“尽了一个职业外交家应尽的责任”,展现出“甘于任事、践履切实”的精神[39]。王鸿志梳理郑孝胥协助张之洞在两江地区设立商务局以及利用入京之机请托王鹏运上奏讲求商务折的相关史实,肯定了他在戊戌年间商政改革中的作用[40]。李君考察郑孝胥在“丁未政潮”中与主要人物岑春煊、端方等人的关系,认为他为岑春煊居间设计,进而又入端方幕府依附之,意在“好风凭借力”,从而实现政治理想[41]。马陵合分析了郑孝胥的借债救国观在国会请愿运动和铁路国有化中的作用,指出以郑氏为代表的部分立宪派将借债筑路视为“把中国引向政治改革之路的媒介”[42]。于宏威考察了1906-1908年间郑孝胥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以及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的过程,认为上述活动集中体现了郑氏鼓吹立宪、抵制革命、启迪民智、速开国会的宪政主张[43]。张亮探讨了甲午至戊戌期间郑孝胥及其士绅朋友圈的政治主张和态度,认为甲午战争中他们主张迁都、毁约、再战,在戊戌变法中他们虽支持和同情变法,但“并未有与朝廷、旧制度决裂的想法及表现”[44]。
郑孝胥的人际关系也为学界所关注。潘静超考察了郑孝胥与严复的交往活动,认为两人初识时惺惺相惜,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是两人关系的蜜月期,辛亥革命后因对革命态度的差异导致两人关系恶化[45]。李君梳理了1894-1903年郑孝胥与张之洞的交往,认为两人关系经历“初试”“疏而复密”“最为密切”三个阶段[46]。李君还探究郑孝胥与张謇的关系,指出两人均以经世为追求,郑氏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张氏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辛亥革命后因时局和个人志向不同,两人最终彻底分裂[47]。朱静则考察了张謇与郑孝胥两人对农工商、实业与教育及股份制的认识和实践,认为“实业救国”是两人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深入交往的纽带[48]。黄新宪考察了郑孝胥参加福州乡试、北京会试的过程,认为郑氏通过科举考试结交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积累了丰富的人望[49-50]。
2.郑孝胥“遗老”身份研究。郑孝胥作为晚清遗民群体典型代表,吸引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透视其生活状态,探讨其政治选择的复杂性。
傅道彬、王秀臣从文化遗民角度着眼,指出郑孝胥没有像其他文化遗民“以文化担当使命”,而是从“文化对立上升到政治对抗”,将“自身人格的劣根性同旧文化的劣根性交在一起”,是以变成政治投机者并最终走向政治变节[51]。周晋华从解读《郑孝胥日记》所载重九诗入手,认为郑孝胥选择“遗老”身份,既出于忠义观念,又有“寻求具有延续性的、稳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目的[52]。王蒙认为郑孝胥虽与其他遗老有相似的价值取向,但他又有“与之不同的行为”:投身商界、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情节重于文化情节、对西方先进文化抱有好感[53]。近年来,亦有学者认为郑孝胥算不上真正的清遗老。桑兵指出,郑孝胥对清王室并无多大忠贞,只是将清朝当做实现个人政治野心抱负的凭借,之所以“不讳言以民国为敌国”,也仅表明不与之为伍,尚未到“汉贼不两立”的地步[54]。
民国后郑孝胥寓居上海达二十年之久,其在沪生活情况也为学界所重点关注。李庶民梳理了郑孝胥在沪的书法活动和鬻书情况,认为书法是郑氏脱离官场后重要的日常生活内容,他通过出售书法作品获得可观收入[55]。张笑川指出郑孝胥通过任职商务印书馆、卖字等途径获得优越生活,而参加读经会以及遗老组织等活动,则使他成为上海遗老圈的重要人物[56]。李君认为郑孝胥遗老生活“优裕而从容”,他虽高度标榜“不仕”的政治态度,但人际交往达及社会各层面,形成复辟圈和遗老同志圈两个交往圈[57]。范军认为郑孝胥作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配合张元济等人在处理该馆重大事务上发挥了一定作用[58]。胡欢欢指出,任职商务印书馆是郑孝胥在沪期间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该馆也成为他与文人交谊往来的重要场所,助其迅速融入上海文人圈[59]。陈占宏指出郑孝胥对五四运动冷嘲热讽,“谋复辟、仇共和、傍日本”的思想和行为其时已然凸显,他日后沦为汉奸国贼实有源自[60]。周逢琴考察了郑孝胥与章士钊的交往,认为两人在1913年于上海会面,后章氏有郑氏学诗,两人情谊加深。面对日本侵略者,章氏加入国难会议,郑氏参与伪满洲国,显示出两人节操的差异[61]。
3.郑孝胥参与伪满洲国研究。参与伪满洲国的经历及其王道思想是郑孝胥研究越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课题,学界突破以往从“汉奸”角度解读郑孝胥王道思想的窠臼,立足于郑氏“遗民”身份具体分析其王道思想的渊源、内容及失败原因。
周明之以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为例,从“忠”和“现代化”两个维度解读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就郑孝胥而言,作者认为其王道思想来源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以皇帝之政治本位和孔子之文化本位为基石,意在通过弭兵与博爱使全世界达到王道境界,并且将伪满洲国建成彻底的儒教专权的社会[62]。林志宏则从政治文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清朝遗民的政治认同和态度。作者以郑孝胥为例揭示清遗民面临的时代问题及应对理念,认为郑孝胥王道思想满足了清遗民“防共”的心理需要,不仅有利于他们确定满洲的正当性和塑造“中华世界秩序”,同时也是他们“抵抗西方文明价值和体制的武器”[63]。彭超认为郑孝胥王道思想初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观念,同时吸收西方政治模式形成“列强共管”的思想,后被日本关东军所利用,最终融入殖民统治理念[64]。程太红认为郑孝胥王道思想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并结合对时局的认识,构建成“内圣”与“外王”两部分,它失败的原因在于本身缺乏学理上的正确性且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扶持和利用[65]。秦燕春认为郑氏虽以“揭孔孟之道因以阐扬旧学”自任,但他对儒学“并非深自有得”,误解儒学传统概念导致其王道思想“处处荒诞不经”[66]。张冉认为郑孝胥王道思想涵盖国家治理、个人修养、世界蓝图构建等各领域,郑氏以该思想抵制西方政治文明,“反对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建立的民国”,但该思想违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故从未真正实现过[67]。赵秋萍认为郑孝胥王道思想的核心是复辟帝制和追求孔孟文化,通过将郑氏王道思想与传统王道思想、日人橘朴的王道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它在具体内容上已“偏离传统内涵”且“过于附和日本”[68]。
陈芳字指出郑氏在附逆期间以“三共论”“门户开放论”“王道论”等思想作为其政治活动的主要支撑[69]。陈秀武从郑孝胥撰写的《满洲建国溯源史略》一书着眼,分析了郑氏对“满洲国自古以来乃独立国家”之说的建构,作者认为该书是郑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延长线的一种存在[70]。彭超、王联众指出伪满时期郑孝胥于1932年、1935年两次辞职皆有其因,前者为了在伪满政权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后者则迫于日本压力[71]。贺莹新翻译和分析了庄士敦发表在《英文评论》上的《满洲国和它的总理》一文,庄文指出:郑孝胥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目的是反对革命,而非追逐名利,他不把日本当作唯一的依靠,而是追求“列强共管”。作者认为庄文所论具有一定客观性[72]。曾祥明考察了郑孝胥汉奸之路及其晚年心理,认为他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后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对于与日本的屈辱合作其内心无法释怀[73]。张子惠认为郑孝胥对于自己晚年卖国的行为有自知之明,因此产生自我逃避与自我反省两者交替出现的畸形心理[74]。
此外,张冉着眼于1923-1938年期间郑孝胥与溥仪关系的变化,将两人的交往分为郑氏获得信任(1923年8月-1924年11月)、郑氏渐得信任(1924年11月-1931年11月)、双方背道而驰(1931年11月-1938年3月)三个时期,认为两人关系因政治形势影响而由陌生到亲密再到疏远[75]。学界也对郑孝胥的日本观做出初步探讨。张建以郑孝胥诗歌为分析文本,认为他对日本的态度历经轻视、取法、联合依靠、绝望的转变[76]。朱静认为郑孝胥从早期访日到为实现复辟拉拢日本再到完全依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其对待日本的态度经历由轻视到平等合作再到妥协讨好的演变过程[77]。
(三)诗学成就研究
进入21世纪,郑孝胥史料出版又有新成绩。2003年,黄珅、杨晓波对丁丑年(1937)版《郑孝胥诗集》十三卷做了整理点校。该诗集蕴含着郑孝胥的人生感悟及诗学思想,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2013年,增订版《海藏楼诗集》再次出版,新增诗篇包括郑孝胥与金蓉镜、吴保初、陈曾寿、梁鸿志的唱和之作四首,日本爱知大学图书馆霞山文库所藏的《使日杂诗》影印件,以及梁如冰与马国华辑录的海藏楼散佚诗作百余首[78]。该诗集的出版,拓展了郑孝胥研究的领域和广度。总的看,学界从郑孝胥诗学思想、诗歌特色、评价及影响等多方面展开讨论,较为深刻地剖析了郑孝胥诗歌的艺术价值,肯定了他在清末民初诗坛上的地位和文学贡献。
1.诗学思想。贺国强从感时伤世和记录个人灵魂两大主题考察郑孝胥诗学,认为郑氏以“晚唐的辞藻色泽树北宋之神理意味”[79]。侯长生认为郑氏的宋诗观表现为:重诗之性情与尚意相贯的气势、重学问而深入浅出[80]。葛春蕃将郑孝胥作为清苍幽峭派的代表诗人进行讨论,认为郑诗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外清内厚的艺术追求,其诗学观主要表现在诗歌要深抱远趣、“兴象才思”和“两相凑泊”、贵涩三方面[81]。马国华认为郑氏早年诗学“遍及六朝三唐”,后转向推崇宋调,倡导同光体,其仕隐情节则从督师龙州到隐居沪上期间逐渐显露[82]。官剑丰从诗本论、诗风论、创作论三方面总结郑孝胥的诗学体系,认为郑氏以真性情和诗中有事为诗本,其诗风源于唐宋诸贤,在创作上熔铸了“唐宋诗的清隽意趣与峭折筋节”,形成“唐宋以来颇具个人特色的一种诗学综合”,“不失为一个大家”[83]。
2.诗歌特色。杨晓波认为郑孝胥博采众家之长而自成风格,其诗“平澹高远,清寂幽深”“语质而韵远,外枯而中膏”[84]。纪映云认为郑诗具有“清苍幽峭”的艺术特质,同时考察了郑孝胥与同光派其他三位重要诗人陈衍、陈三立、沈曾植的交游情况[85]。郭前孔考察了郑孝胥诗学宗趣,认为郑氏宗宋而不废唐,对唐宋诸家皆有宗尚和取舍[86]。马国华和陈伟庆认为郑孝胥从宗唐到祧宋是受到金陵诗学的影响,他所代表的同光诗风,某种意义上也是金陵诗学宗尚的拓展与新变[87]。刘洋认为郑孝胥对“艰险”诗学的追求,体现在“激急抗烈的个性色彩、‘坚齿漱寒石’的语言风格和参差对照的美学手法”[88]。
3.诗作内容分析。孙爱霞分析了郑孝胥的《述哀》诗七篇,指出他用朴拙的技法传达出撕心裂肺的伤悼之情,成就其“工于哀挽”的名声[89]。同时,她也探析了晚清时期郑孝胥因维新变法、庚子国变、光绪驾崩等家国大事而写的诗作,认为这些诗作中蕴含着强烈的家国之悲、时事之感[90]。李剑波认为郑诗表达了郑孝胥对清王朝的忧患、绝望的末世心态及自我感伤情绪,这种末世心态造就郑诗清苦幽寂的风格[91]。孙艳以郑诗为文本剖析郑孝胥人生的心路历程,认为郑氏早年自命不凡踌躇满志,而中举之后到辛亥革命前功业无成,革命后他入歧途,助纣为虐且至死不悟[92]。张煜认为郑孝胥的“重九诗”和“夜起诗”是情景交融、感事言志的佳作,同时也指出因其热衷名利、投靠倭寇,以致很多诗歌读来颇觉虚伪[93]。丁伟从郑诗中提炼出“重九”“夜起”“王道”这三个意象,并借此考察郑孝胥后半生的心态变动,即从“重九诗的愤懑不平”,到“夜起诗的不甘沉沦”,再到“王道诗的有所行动”[94]。
4.诗作影响及评价。李寿冈对《海藏楼诗》的艺术价值持批评态度,认为“一个人名声瓦裂,其区区文艺不值得称道了”[95]。朱兴和从人格特质和诗学品格的角度着眼,认为郑氏品节的缺憾表现在对个人能力的过度自负、面对日本强权的心理失衡及自我期妄,这导致他晚年在政治上失足。这一政治抉择直接影响到郑诗品质,即缺少正大刚直之气,不能成为清末民初诗坛的正宗[96]。孙爱霞也指出郑孝胥好名利、好大言、重私心的品性在其诗作中屡有表现[97]。张元卿分析了学衡派诗人吴宓、胡先骕对郑孝胥诗歌的认知,认为两人都受到郑孝胥的影响[98]。李晨冉从学术史角度梳理了1880年至2017年期间郑孝胥诗歌的研究成果,指出目前郑孝胥诗歌研究逐步打破政治瓶颈,但在诗学贡献、郑诗的价值、影响及诗风变化等问题的研究上则有待于扩展[99]。
此外,学界也对郑孝胥与同时代诗人的交往活动作出了初步考察。胡迎建探讨了郑孝胥与陈三立的交往以及两人在诗学观念上的异同,认为因思想境界和个性特征的不同,郑氏堕落为大汉奸,陈氏则绝食殉国。在诗风上,郑诗主观意图显露而激迫,不如陈诗来得深厚[100]。白敏敏考察了郑孝胥与李希圣在湖北的交往经历,指出两人在诗学主张方面极为投机[101]。窦瑞敏梳理了郑孝胥与顾云的交往始末,认为两人的交往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契合,而非诗学主张的一致[102]。
(四)书法成就研究
郑孝胥书法自成特色,影响及于今天。学界着重从书法作品鉴赏、书学思想及实践、书法评价等方面展开探讨。
1.书法作品鉴赏。仇志宏从“形质”和“神采”两方面鉴赏郑孝胥的行书联,评价其行书气度庞大,纵横取势,笔力雄强,笔法精妙[103]。赵鉴钺分析了郑孝胥行楷作品,认为他在书法创作中讲求“法”并深得传统之“法”,注重情感的流露和精神状态的释放[104]。潘如丹认为郑孝胥书法作品之所以在市场上有较高价值,在于其书法流畅飞动、劲道十足[105]。王秋菊指出郑孝胥为签订《日满议定书》所书写的祝词手稿,在艺术上“堪称上品之作”,但在历史上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东北的实物证据[106]。姚田对郑孝胥的三件扇面藏品楷书作出鉴赏,认为三幅作品既有颜体的磅礴,又有赵孟頫的灵动,亦有杨凝式的飘逸,肯定了郑孝胥书法的影响力和收藏价值[107]。
2.书学思想及实践。颜凌晖指出郑孝胥继承了清代以来的碑派传统,以浓墨和羊毫为书写工具,以碑帖结合方式创作出具有个人风貌的作品[108]。黄杰钦评析了郑孝胥楷、行、篆、隶四体,认为其楷书以欧书为主,行书最具个性,篆书则以小篆为主,与隶书一样未有明显突破[109]。祝童认为郑氏最重隶书,擅长小篆,行楷是其成就最高的书体,其书学思想的核心是“雅俗论”[110]。宋玖安认为郑孝胥标榜碑学而终生未脱帖意,试图意与古会而又未能走出时人局限[111]。程梁指出郑孝胥在碑帖结合、楷隶相参、师古出新、重神理轻描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学书思路[112]。徐徽、宋玖安分析了郑孝胥书法五体的取法渊源,认为其楷书早期取法褚遂良后则渐尚碑派,隶书早年受邓石如、吴让之影响后则取法何绍基,篆书终生未能摆脱邓、吴影响,草书则受沈曾植、《流沙坠简》启发[113]。
3.书法地位与评价。信志刚、李颖伦皆对郑孝胥的书法艺术成就给予肯定,认为理应在近代书坛上占有一席之地[114-115]。亦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崔自默分析了郑孝胥的行楷书及楷隶相参的书法主张,认为郑氏书法的实际水准与其应得艺术地位相对照,“远不至于令人扼腕长叹”[116]。甘中流则指出郑孝胥、康有为等人虽有集碑学帖学之大成的理想,但在艺术实践上则未有成者,故不认同张谦赞“(郑孝胥)集近代碑学帖学之大成者”一语[117]。朱正伦、刘住总结了20世纪初至2010年期间的郑书研究情况,认为相关研究存在史料挖掘不够和研究视野比较狭窄等问题,提出应加强郑氏的家学和交游研究[118]。此外,有李石生探讨了郑孝胥与沈曾植在书学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关系,认为两人共同寻求书体“复古”之路,为他们的创作带来更多的创新[119]。宋玖安考察了吴昌硕与郑孝胥的交往,认为郑氏对吴氏篆刻的评价经历从“未尽典雅”到主动请吴氏操刀的转变,而吴氏亦对郑书及郑诗极尽赞美[120]。徐徽、宋玖安考察了郑孝胥和沙孟海的交往,认为郑孝胥对沙孟海早期的书法和诗歌多有影响。然因沙氏注重人品,晚年在修改《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时则删除了与郑氏相关的文字[121]。
四、几点展望
综上所述,学界对郑孝胥的研究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但总体看,呈现某些问题诸如郑孝胥与晚清政局、人际交往、诗学思想等研究较为深入,某些问题诸如郑孝胥在伪满时期的活动、郑孝胥的日本观及其书学思想等则有待进一步推进。笔者认为,今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郑孝胥研究:一是加强史料挖掘整理。在清末民初的杂志、报刊、档案、地方志以及张謇、沈曾植、陈宝琛等同时代人留下的文字中,潜藏着大量与郑孝胥相关的史料,需要进一步搜集整理,从而丰富和拓展郑孝胥研究的史料范围;二是加强多学科的协作研究。郑孝胥一生复杂多变,涉足多个领域,需借鉴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视角,从而全面客观地透视人物;三是加强人物整体性研究。目前郑氏前期和后期的人物研究尚未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打通郑氏早期和晚期研究的学术藩篱,方能全面、立体、客观地展现郑孝胥的人物形象;四是加强人物与时代关系研究。郑孝胥一生大体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如何通过郑孝胥研究展示晚清民国历史变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这是未来郑孝胥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