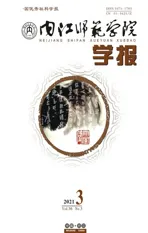论金代诗学的北地特质
2021-12-31张晋芳
张 晋 芳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金代诗学尽管不如同时期的南宋那么体制周全、声名卓著,但在百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形成了金源特色的理论思考,为后世元代文学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鲜明的北地特质更值得学界重视。其具体表现是:在诗旨上,以真情为内核;在诗用上,以实用为指向;在诗美上,以刚健清新为特征。这是受北疆地理环境、女真为主的北方民族性格及文化风尚等综合因素深刻影响而成的。作为统治民族,女真人最早生活在我国北疆的白山黑水之间,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其气候干烈凄寒,山川浑莽恢阔,因而孕育了女真人直率淳厚、富于进取、刚健质朴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不拘礼法、不尚虚饰、自由奔放的文化风尚。后来随着其政权中心的南移,胡汉两种地理文化也随之不断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金源文学、诗学独特的北方特色。
一、在诗旨上:以真情为内核
“情”作为文学发生的动力,是中国诗学一个古老的命题,从屈原“盖自怨生也”,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再到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穷而后工,情感是文学源发动力的理念,始终被历代文学批评家所继承和发展。金人也不例外,他们对“情”的认识自是继承了汉文化传统的文学发生论,但又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金人建国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粗朴原始,人们性格简单,直来直去。据《松漠纪闻》载:“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音蒲,膞肉也。以余肉和藄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1]这种不拘小节,质朴适意的交往习惯正是金人“真性情”的表现。又如世宗常常告诫臣下真淳的重要性;“事当任实,一事为伪则丧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实也。”[2]191这种“真性情”直接影响了金人以“情”为核心的诗学观念,他们为人真诚,为文亦然,主张“真”与“诚”是文学发生的基本动力,这是金代文坛最重要的诗学理论。
但是,关于“真情”是文学发生与旨归的思考,金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代人不断探究、实践的结果。而这过程中,北方的地理文化、胡汉文化的碰撞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金代初期,借才异代,羁留北地的许多北宋文臣为金代文学播下了最初的种子,也奠定了金源诗学的理论基础。如宇文虚中、朱弁等北宋文家,就十分强调文学创作是真情流露的产物,并在各自的诗话、诗论中或隐或显地伸张这一诗学主张。宇文虚中有《余留平城,赵光道自代郡来,相聚旬日而归,各题数句以志其事》诗曰:“穷愁诗满箧,孤愤气填胸。……莫言竟愦愦,作书怨天公。”[3]13诗人说胸中的真情无处可发,只好书之以诗书。同样的理念还可在其诗题中见到:“郑下赵光道,与余有十五年家世之旧,……昔白乐天与元微之偶相遇于夷陵峡口,既而作诗叙别,虽憔悴哀伤,感念存没,至叹泣不能自已,而终篇之意,盖亦自开慰,况吾辈今日可无片言以识一时之事邪!因各题数句,而余为之叙。夜将半,各有酒,所语不复锻炼,要之皆肺腑中流出也。”强调文学是发自肺腑、真情流露的产物。朱弁亦持此论,其在金地所著《风月堂诗话》流传甚广,在金代文坛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十分推崇钟嵘的“自然英旨”:“可以表学问,而非诗之至也。观古今胜语,皆自肺腑中流出,初无缀辑功夫,故钟嵘云:‘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4]19对“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可见,作为金初的两位代表性文家,宇文虚中与朱弁都秉持着“为情造文”这一古老诗学命题,为金代诗学观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及至金朝中期,“国朝文派”崛起,文人们关于“情”的认识则侧重在“真”上。随着政权的稳固,女真民族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逐渐被统治区域内的人们所接受,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的汉族人,身处“地雄河岳,疆分韩晋,重关高压秦头”的环境,亦有刚烈、豪迈之气。落实在文学艺术上,对于“情”字的理解就更强调情真意切。这种“真”,即如北人性格一样,直接,坦荡,不婉曲,不假饰。如蔡珪、刘迎、周昂等“国朝文派”代表人物,或在创作上,或在理论上,都以“发乎真情”为旨归。蔡珪虽未明确提出“发乎真情”的主张,但其诗歌中喷薄而出、不加掩饰的诚挚情感,以及作者本人不拘礼法、真情外露的性格正是最佳的证明:“南山有奇鹰,置穴千仞山。......锦衣少年莫留意,饥饱不能随尔辈!”[3]459(《野鹰来》)这种追求质朴真情的诗人还有刘汲:“西岩逸人以天为衢兮,地位席茵。青山为家兮,流水为朋。饥食芝兮渴饮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渑。世间清境端为吾辈设,吾徒岂为礼法绳?”[3]479(《西岩歌》)狂放之语的背后是对本真的追求,对不假外饰真性情的书写。这一时期,成就最著的文学理论家是周昂。他的名言是:“文章以意为主”“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周昂所谓的“意”即指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因此在“意”的表达上,他追求质朴纯真的文学内涵,认为唯此方可打动人心。同时他还强调:“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失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5]192明确了对“经营、雕琢”等“伪技”的拒斥,这也从反面道出了他对“真情”的追求。即使是北人气质稍弱,以文雅为尚的国朝文宗党怀英也“提倡真率、自然成文的文风,反对矫揉造作。”[6]他有名言曰:“为言但当多读书,不求于工应自工。……果如公言读尽世间书,必如真龙出九重,一洗万古凡马空。”[7]
金室南渡后,在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人的倡导下,“真情”的诗旨追求随着金源文学的成熟与定型也得到了深度认可,成为风格各异的诗家们共同的诗学选择。正如诗学家刘祁所言:
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予曰:“古人歌诗皆发其心所欲言,使人诵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絶少。不若俗謡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飞伯以爲然。[5]530
真情才能动人,这是刘祁的最主要观点。此期文坛领袖赵秉文更是此种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指出:“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文,不尚虚饰,因事遣词,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闲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8]75没有外在修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章才是至文。这自是对文学发生要发乎情,发乎真的一种理论伸张。又如主奇创的李纯甫,他所倡导的“惟意所适”的“师心”论,也直接言明文学创作是发乎真情的产物,因此他的诗歌以直抒内心情感为主,不拘礼法,直抒真情,气盛辞奇。金代后期著名诗评家王若虚更是看到:“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正理也。”[5]197这都表明以“真情”为内核的诗旨成为金人普遍的审美追求。且统观南渡文人对“真”与“情”的强调,可发现这一时期的“真情”除了指文学创作规律的本质,还关联了作家创作态度的端正、人格的高尚、价值观正确等一切向善的伦理审美追求,这也表明,南渡后文人们的“真情”诗旨已被升华,开始向“诚”发生转向。比如赵秉文在其文论中就强调:“学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诚之,其去古人也不远矣”[9]2287;“而诚由学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五者,所以学夫诚也。”[9]2175正是这样的积累,才有元好问集大成式的“以诚为本”理论:“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8]177这种“诚”沿革了《庄子》的“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发而和”[10],“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真诚,形成了在金代末期诗学的新变。至此,金代诗学以“真情”为诗旨的理论形态完成了定型。
总之,以“真情”为内核的理论探究贯穿了金代诗学史的始终,并在金末得到了确认。它不同于南宋诗学将“情”转向“理”的发展路向,是金代诗学家们对中国诗学的独特贡献。而这种以“真情”为内核的诗学理论与金源特殊的地域文化,以及此文化语境所塑造的民族性格、胡汉文化交通融合等因素关联最大,即如杨义所说,这“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11]4
二、在诗用上:以实用为指向
强调文学的实用性,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其起源当然是儒家的文艺观。但金代诗学中的“实用”特质并非完全从儒家文化与“借才异代”之北宋文家手中获得,其北方民族心性、地域文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女真民族是一个富于进取精神、重实际轻玄想的族群,这种民族心性与严峻的北方地理环境有关,夏日曝晒,冬日苦寒是北地的气候特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稍有懈怠就会缺衣少食,生存艰难,所以北疆居民以游牧、渔猎为生产方式,奔波劳碌是其生活的常态,故其生活态度重实际,尚实用。这样,“务实”就成了烙印在金人骨子里的价值观,反映在艺术上也就是以实用为指向的功能论。
早在立国以前,女真就有对文学实用性的认识。史载:“后(多保真)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桓赧、散达偕来,是时已有隙,被酒,语相浸,不能平,遂举刀相向。后起两执其手,谓桓赧、散达曰:‘汝等皆吾夫时旧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与小儿子辈忿争乎?因自作歌,桓赧、散达怒乃解。’”[2]1500这表明,“歌”作为一种口传文学,在女真早期的生活中是有着劝和、化解族人冲突矛盾的实际作用的。有时“歌”还被用于求偶婚配等场合。据史载,女真女性往往借歌来自我推介以求偶:“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2]女子及笄,为求婚配会用歌来诉说自我境况,表达求婚的诉求,这样口头的说唱文学就成为女真族联结婚姻的重要手段。再次,女真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而其中的萨满巫歌往往具有预言功能,比如预言军事的胜败、诅祝生老病死等,因而女真人对此信奉不疑。这样,化解矛盾冲突、婚配自我介绍、预言战争生活等大小事宜,都可以证明女真早期文学观念的实用性特征。这样的艺术观念当与同样重视文学实用功能的儒家文化相遇时,可谓一拍即合,并随着对儒文化的不断接受,这种追求实用的观念发展成维护统治、以诗立功、以诗存史等新的功能论。
完颜氏开国以后,他们有了明确的以文学维护统治的意识。这首先表现在借助北宋文人学士来建设、完善政治制度,维护其统治的国策上,即所谓“借才异代”。据史料记载,金人灭宋时掳掠了大批图书典籍、文人工匠北归。同时,他们还劫掳、羁留了一些北宋文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文才,金人更看重这些人的治国才能,所以像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吴激等这样的仕金宋人,多在金廷中枢任职,为金朝制定典章制度、创设科举文教等,宇文虚中甚至被金人称为“国师”。这些北宋文人作为向少数民族传播汉文化的载体,在各自的文章之中,提倡儒家道统,主张恢复社会秩序,强调仁政爱民,倡导教化伦理等,充分伸张了唐宋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可以说,这批北宋文臣为金朝统治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最实用的制度建设与治理服务。其次,这种维护统治的意识还表现在:诗文水平成为金朝科举选士的标准;诗词歌赋成为金朝君臣日常互动、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和谐的手段,诗歌甚至还被统治者用作唤醒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的手段等。比如据《金史》记载,世宗皇帝看到女真人汉化程度日益加深,猛安谋克舞文弄墨,沉湎其间,以致女真淳实的旧风多被遗忘的情形,他为此感到担忧,于是在皇族的宴会上作女真本曲,踏而歌之,其意是为了唤起族人们尚实际、轻玄想的女真传统。可见,以武力征服、经营中原的女真统治者,已将统治策略转变为“以文治国”,正如赵沨诗话中所言:“方今贡举之法,既取诗赋以振天下英雄之气,又谈经义以传先哲渊源之学,使放荡者退而有所拘,空踈者望而不敢进,其所以笼天下之俊造,无所遗矣。士生此时可谓厚幸。”[9]1756诗赋经义用于振气传道,拢天下才俊,使文学的政治功能得以大大强化。除政治功能外,金人对文学实用功能的追求还表现在以诗立功、以诗存史等方面,这在周昂、党怀英的文章中多有表现。周昂在告诫后学时表露了他对立功不懈的追求:“自三代而降,言士之贤,莫如两汉。然西汉之士,辞章典雅,而志节未胜;东汉之士,风义高烈,而文采有惭:盖未敢知其优劣。然士之所信者,孔子也。孔子称其门人之所长,自颜渊、闵子骞至于子游、子夏,有次第。本朝自天辅以来,专用文章取士,士之致力于文也久矣,奚患其不至?独所谓志节风义,使学者皆知内此而外彼,高视远蹈,期无媿于古,而又推及于乡人,以至于列郡远邑、深山穷谷之民皆奋于德,然后知庙学之有功于人也。”[13]他认为像孔子所作的饱含志节风义的文章典籍,是由己推人的立功不朽之作,也应是本朝文人应有的追求。党怀英于大定十九年作《重建郓国夫人殿碑》曰:“吾夫子(孔子)出,著术六经,实纲而纪之,以垂憲百代,故后世推尊以为人伦之首,而阙里旧宅,四方于是观礼。”[9]1499对文学的教化功能予以了肯定。不过,这种文学对实用功能的标举,直到南渡后才转变成明确的诗学主张,如赵秉文在《答李天英书》中说:“至于诗文之意,当以名王道、辅教化为主。”[5]145提出诗文应承担明王道、辅教化的作用,明确主张文学的实用功能。李纯甫也叙述过自己学文以求实用的心路历程:“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义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9]2616他还指出《老》《庄》《诗》《书》《礼》《易》等文学典籍之传道功用:“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为表里如符券然。”[9]2616此期著名诗学家王若虚,其《滹南诗话》中更是明言诗书所载大义的重要功用:“呜呼,伊尹圣人,其大义贯乎天地,诗、书载之,孔、孟论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诬者。”[14]这种关于文学实用的理论思考,李治在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作引时做了明确的阐释:“滹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逑,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以为传注六经之蠹也,以之作六经辨;论孟圣贤之志也,以之作论孟辨;史所以信万世,文所以饬治具,诗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后也,各以之为辨。而又辨脰代君臣之事迹,条分区别,美恶着见如粉墨然,非夫独立当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与者与诸人,能然乎哉。呜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惛,而巧者以徇,欲传者如是,受之者又如是。尖纤之逞,而浮诞之夸,吾将见天下之人一趋于坏而巳耳。如先生之学,诚处之王公之贵,赖以范世填俗,其庶乎道复明于今日也。”[14]李治高度肯定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关于文以明道的重要功用。再次,以赵秉文、李纯甫为代表的文家们在南渡后十分不满于明昌、承安年间出现的尖新之气,不约而同地提倡风雅,使文学回到反映现实、救亡图存的正确轨道上来。刘祁《归潜志》载:“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5]510他们之所以批评尖新文风,主要是不满于文人雅士为追求浮词美文而专于尖新雕琢之功,不再看重文学的实际功用,耽于吟风弄月,纵情享受,从而造成社会风气的颓靡积弱,气节殆尽,最终导致国运的衰颓。这种不满尖新之风而追求文学实用功能的变革,表现在诗学上就是诗评家们反复提倡的平实朴素文风,如赵秉文推崇欧阳修文风:“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优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8]75(《竹溪先生文集引》)李纯甫大力斥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髙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可笑情形;而王若虚对浮丽文辞恨不得禁而快之:“骈俪浮词,不啻如俳优之鄙……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14]不仅在诗论上如此伸张,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进行质朴、刚健的创作,以期借此回归文以载道的传统。此外,这一时期,金人关于文学实用功能的探讨,还表现在以诗存史上,这以金代文宗元好问为代表。1213年蒙古军大举南下,并在此年三月屠城忻州,元好问经历了兄长和乡亲惨遭屠戮的悲惨事件。面对蒙军的残暴,国家的衰朽,百姓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等人间惨象,他写下《箕山》《八月并州雁》《内乡县斋书事》《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癸已四月干十九日出京》等一系列丧乱诗,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悲愤痛苦之情,另一方面也记录了当时百姓的苦难与惨烈的社会状况。金亡后,元好问以遗民身份编纂《中州集》、编写金史,志在为金源一代保留文脉,以诗文存史。由此,文学的实用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从以诗歌劝和、求偶、预言,到借其维护统治、以诗立功、以诗存史等,可以见出,重视诗文实用功能是金代文学批评的一贯追求。而这样的诗用指向,显然是苦寒严酷的北疆地理文化环境赋予金人追求实用、富于进取的民族心性与儒家“兴观群怨”务实追求“对话”的结果。
三、在诗美上:以刚健清新为特征
清人陈匪石指出:“金据中原之地,郝经所谓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南方之文弱。国势新造,无禾油秀麦之感,故与南宋之柔丽者不同。而亦无辛、刘慷慨愤懑之气。流风馀韵,直至有元刘秉忠、程文海诸人,雄阔而不失之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卓然成自金迄元之一派,实即东坡之流衍也。此选虽兼收绵丽之作,而气象实以代表北方者为多。”[15]这段话尽管是对《中州乐府》美学风格的评判,但用于概括金源文学整体美学风格亦切中肯綮。金代文学中虽然也兼有绵丽之作,但“气象实以代表北方者为多”,呈现出“雄阔而不失之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的风格特征,而迥异于南方之柔丽文弱。形成这一美学风格的原因是金代文学家深受北疆地理风物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性格之特有追求。北国干烈奇寒的气候,浑茫壮阔的山川,质直开朗的风俗,劲激粗犷的艺术,孕育了金源文学“海角飘零”的豪气与“谁挽银河”的磅礴,驱动着他们以刚劲且壮美,清爽且刚健为特征的诗美追求。当然,刚健清新的诗美特征也并不完全是北方文学的特产,生活于南方的苏、辛也有豪迈阳刚的气韵。但从整体来看,北方文学以刚健清新的审美风格为主,南方文学以柔丽精致为主,则是普遍的共识。所以“苏学盛于北”—苏学风尚贯穿了金源文坛的始终,其内在原因是金人与苏学内在气质的暗合。诚如学者所言:“苏轼人格中那种不拘小节的豪健旷达、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风趣,都与这个民族(女真)粗豪乐观、幽默豁达的民族心性相暗合,这正是‘苏学行于北’的根本原因。”[16]
金初文坛,金代诗学正处于开辟草莱的初创阶段,所以并未有明确的“刚健清新”的诗美主张。但不可忽略的是,此期确有刚健清新诗美潮流的涌动,如完颜亮、蔡松年、吴激、宇文虚中等人正是这种诗美追求的代表。尤其以女真皇族作家完颜亮为典型,他的创作最有女真特色,既有刚健之作又有清新之词,如《书壁述怀》《题临安山水》《鹊桥仙·待月》《喜迁莺·赐大将军韩夷耶》《念奴娇·天丁震怒》等,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桀骜不驯、刚烈直爽的审美风格。对此,杨义评价说:“北方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旦采用汉语写作,在学习汉语文学的智慧和经验的同时,总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气质、文化体验和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表现这种特异的气质、体验和阅历的作家假如占有相对的政治地位的优势,或者声气相投而成为群体,便不可避免地给汉语文学染上特殊的色彩,不同程度地超出原有轨道运行。”[11]6随着“借才异代”北宋文臣的凋零,金源本土文人登上了文坛,其“刚健清新”的诗美观念也日渐清晰,这首先表现在“国朝文派”蔡珪、党怀英的诗文创作上。继承乃父蔡松年深厚的家学传统,而又有自我面目的蔡珪,其诗歌多刚健磅礴,展现着金源文家的自信与雄豪,如“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祖龙力驱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3]460(《医巫闾》)“吴侬笑向吾曹说,昔岁江行苦风雪,扬槌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3]460(《撞冰行》)等诗作,语刚辞健,“清劲有骨”[17],成为金朝文风的主导。郝经《书蔡正甫集后》评曰:“煎胶续弦复一韩,高古劲欲磨欧苏。几回细看圣安碑,区别二代张吾儒;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18]道出了蔡珪诗“刚健”的风格特色。而蔡珪之后的“金源文宗”党怀英,尽管其美学风格属清新一类,但其诗歌多有山雨烟云等大自然风光的书写,呈现出迥异于南方柔丽的清新之美,得到了赵秉文的推崇:“公之文有似乎欧阳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体,寄兴高妙,有陶谢之风,此又非可与夸多斗靡者道也。”[19]赵氏点明了党怀英不同于“夸多斗靡”的特点。此外,此期还有其他国朝文士萧贡、刘迎等,如萧贡有“半夜东风搅邓林,三山银阙杳沉沉。洪波万里兼天涌,一点金乌出海心”[3]378(《日观峰》);刘迎有“君不见二牢山下狮子峰,海波万里家鱼龙。金鸡一唱火轮出,晓色下瞰扶桑宫。槲林叶老霜风急,雪浪如山半空立。贝阙轩腾水伯居,琼瑰喷薄鲛人泣”[3]246(《鳆鱼》)等诗,无须多说,都属于与蔡珪、党怀英同类旨趣的审美风格。
对“刚健清新”诗美风格有自觉、明确理论阐述的,是金代末期的文学批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南渡以后,金源文家为变革“尖新”文风,开始以身作则创作质朴、清新的诗文,表现在审美风格上就是对“刚健清新”的自觉追求。刘祁的《归潜志》对金源众多文家及其作品予以了批评。通过归纳,可发现刘祁多以“‘奇气’ ‘奇语’ ‘奇古’ ‘奇峭’作赞语”[20]41,又常以“雄奇简古”“不作浅弱语”“有雄气”“长于雄辩”“闳肆奇古”等论断对诗家个性进行概评。如其评李纯甫曰:“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由此一变”[21]28;论雷渊、宋九嘉说:“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21]29;“公(雷渊)博学有雄气,为文章专法韩昌黎, 尤长于雄辩”[21]8;称王飞伯:“奇士也。仪状魁奇,为文闳肆奇古。”[21]22等等。这些评判一方面体现出金源文家们阳刚的美学风格,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刘祁的审美倾向。并且,与之相应,刘祁本人创作也确实刚健清新,有塞北雄风:“他文学三苏,有清奇磊落之气,无诘屈聱牙之弊”[20]41
李纯甫作为南渡名士,在其诗中曾直言对刚健气质的追求:“男儿生须街枚卷甲臂周弓,径投虎穴策奇功”[3]157,向往男儿本应具有的刚强勇猛、驰骋疆场的雄豪气势。这种刚健理念落实到创作上,更显示了其北地特质的诗美追求,如其《怪松谣》《雪后》《赤壁风月笛图》等诗作意象怪奇,不拘常规,气势盛大。不仅李纯甫,这一时期有着显著北地特质诗美追求的作家还有李遹、赵元、雷渊、李经等人,不妨简略摘取其典型诗句以观其美:“士道凋丧愁天公,阴霾惨惨尘濛濛。三春不雪冬未雨,野桃无恙城西红。”(李遹《赠中山杨果正卿》)[3]274;“凫胫苦太短,蚿足何其多。物理斩不齐,利剑空自磨,老跖富且寿,元恶天不诃。伯夷岂不仁,饿死西山阿。”(赵元《读乐天无可奈何歌》)[3]329;“千古崩崖一罅开,强将神怪附郊禖。无情顽石犹胎谤,贝锦从为苍伯哀。”(雷渊《启母石同裕之赋》)[3]372虽然赶不上李纯甫的诗作气刚语健,但也雄气十足。此期有着明确理论思考的诗学家当属王若虚,其诗话中言及北地气概时说:“花比妇人,尚矣。盖其于类爲宜,不独在顔色之间。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好异之僻;渊材又杂而用之,益不伦可笑。此固甚纰缪者……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复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无乃太粗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谓其白耳;施于酴醾尚可,比海棠则不类矣。”[5]208他认为用花比喻女子不仅仅因为二者美的相似,言外之意即二者在柔弱的气质上也是相近的。而黄庭坚以花的意象来比喻男子,在王若虚看来是不伦不类,十分可笑的。并且,他还质疑了难道“白皙”这样阴柔美的词汇还能用来形容雄壮武夫的气质吗?这说明王若虚对阳刚气质是推崇的。
作为金末文宗的赵秉文,他在创作上主张要各得古人一徧:“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江淹、鲍明远、李白、李贺得其峻峭,孟东野、贾浪仙又得其幽忧不平之气。若老杜可谓兼之矣。”[5]145、“太白、杜陵、东坡,词人之文也,吾师其辞,不师其意。渊明、乐天、高士之诗,吾师其意,不师其辞。”[5]147他所师法的名家,其文风峻峭、浑浩、豪放,正属“刚健清新”之列。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的大家,如果认真统计,就会发现其意象和词汇选取多以北地风物为主,因而营造出刚健质朴的美学意境,足以见出赵秉文对北地刚健特质诗风的钟情。笔者曾对赵氏常用审美意象做了梳理,其频率比较多的有:
蹇驴、断崖、茅屋、萧寺、虚落、荒田、野鹿、沙禽、怪松、幽鸟、草荒、饥鸦、残蕊、幽禽、清霜、霜林、萧条、凉草、霜叶、萧萧、槐老、荒壇、飞雪、霜叶、平野、颓沙、坏壁、荒天、老地、黑山、狐貉、荆棘、寒梅、幽姿、幽窗、断霞、落日、雄驰、天沉、严风、草枯、寒花、老骥、霜鹘、花残、青蛟、骐骥、北尘、孤根、残照、烟村、城断、颓墙、孤城、林黑、饥虎、瘦骨、霜髯、草荒、荒城、冰霜、日曝、万壑、荒郡、簟藤、荒堂、霜雪、饥禽、刓墙、老僧、瘦藤、冰雪。
赵秉文曾在其诗话中主张:“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而上述意象的选取,就反映了他心中对“刚健清新”文学的推崇之意。这些意象营造出了赵氏所追求的自然一派刚健清新的北地审美气韵,这当然也有别于“杏花春雨江南”的南方文学之柔美。在赵秉文的创作中,北雄南秀的边界是十分清楚的。
金代文坛最能代表刚健清新北地审美之风的文学批评家是元好问。作为金代文学的集大成者,元好问的诗学理论也具有集大成的性质,特别是关于金源文学审美风格的思考,具有强烈的北方文化意识,并有具体明确的理论主张。如在《论诗三十首》中明言:“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5]317称赞《敕勒川》这样的北方少数民族创作,说它自然、雄阔,彰显了北方地域天苍野茫的豪迈之气。再有:“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5]316;“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5]316;“沈、宋横驰翰墨塲,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5]317等,都能看出元氏对“刚健”文风的推崇、称赞。郝经、赵翼等人也看到了此种特点,称遗山的创作:“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22]“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盛于苏、陆。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23],道出了其诗美与北方文化特质的深刻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元好问所编《中州集》的本意,一是为存金源一代之文学;二是为与南方文学分庭抗礼,强调金源文学作为中国正统的诗学立场。基于此,他在《中州集》书后写道:“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24]571其意自是力推北方文学。又有“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24]571,强调金代文学作为北方文学的独创性,及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所以,“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24]571,这是对金源文坛以“刚健清新”为诗美追求的最好总结,充分展露着金人阳刚文学的自信与自豪,以此彰明具有“北地”美学特质的金源文学之重要文学史价值!
综上,“无论思想内涵,或是艺术形式,都伴随大金王朝的兴衰而与之融为一体”[25]28的金朝诗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继承中原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独特审美追求,即北方地域文化朴野血液的注入,使得金代诗学呈现出鲜明的北地特色,它明显出脱了北宋后期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闭门觅句,典故堆砌,遣词造句等的铺陈雕琢,也不像南宋文学中过度讲求“法”与“道”而终致“文坛不振”[26]。并且这种特色影响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面貌,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内涵,“为中华民族文艺百花园增添了新的光彩。”[25]28正如杨义所指出的:“由于北方文学的地理和民族等原因,它对中国文学总体格局的参与和改造,丰富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给它增加了不少旷野气息和阳刚之美。”[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