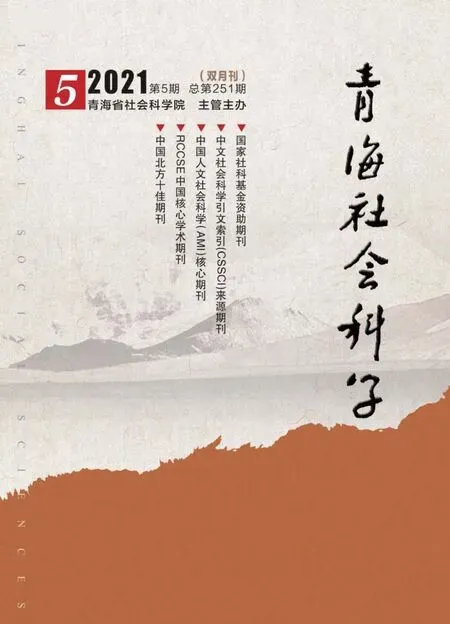论自然主义影响下李健吾客观呈现的文学批评观
2021-12-31范水平
◇范水平
李健吾活跃在批评文坛的年代,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的左翼文艺批评占据着文坛的重要地位。在这特殊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于是,带有倾向性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被供上圣坛;同时,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当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两种批评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二者的政治倾向不同,而批评模式却比较相似。无论是左翼的社会历史批评还是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都基本上把批评看做是一种判断,偏重的是批评的逻辑特征和理性质素。左翼作家的社会历史批评主要把批评看作是生活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则从白壁德抽象的“人的法则”出发,把批评视为“严谨的判断”。梁实秋说,“批评家需要的不是普遍的同情,而是公正的判断。批评的任务不是作文学作品的注解,而是作品价值的估定”①梁实秋:《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浪漫的与古典的》,香港丽明出版社1969 年版,第67 页。,他欲求以一种超验的人性法则来厘定作品与作家。其时,作家彼此之间经常发生笔战,借用作品来打击对方是常有的事情,有的甚至还会发生人身攻击,即使是我们今天看来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学者有时也不例外。对此,李健吾深感痛心:“我厌憎既往(甚至于现时)不中肯然而充满学究气息的评论或者攻讦。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得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匿,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作批评的根据。”①李健吾:《咀华集·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为了纠偏,也是他向来的心性使然,李健吾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很少做出结论,也一再表明他很反感对文学作品或作家做出结论。郭宏安先生将此称之为是“明智的文化保守主义”。而实质上,可以说,这是法国自然主义诗学主张的客观呈现的创作原则被李健吾灵活运用在文学批评当中。
一、客观呈现的文学批评观
左拉一再强调说: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②(法)左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248 页。他认为文学家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呈现事实,描写人物也只做科学客观的解剖。他把“显示自然的本来面目”叫做“现实感觉”,主张小说家应该像泰纳那样,“满足于展览,不作结论。”③(法)左拉:《用在小说上的批评公式》,转引自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载《文学研究》1957 年第4 期。福楼拜也一再重申文学家应该像科学家,写作时应该剔除自己的情感,决不在作品里露面,主张“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④1867 年2 月,福楼拜与某夫人书信,转引自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载《文学研究》1957 年第4 期,第57 页。。李健吾把左拉、福楼拜等提倡的科学客观的创作原则运用于文学批评,这使得他的批评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客观精神。
我们知道福楼拜最著名的主张是“为艺术而艺术”,不准自己出现在作品当中,用作品替自己说话,希望能够尽量做到客观,这让他很多时候受到现实主义阵营的攻击与责难。李健吾对福楼拜的这种文艺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同情,他赞赏道,“和一座山一样,在这样作品的后面,是作者深厚的性格。他决不许书面有自己,这是说,他不愿在他所创造的一群人里面,忽然露出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和读者寒暄,刺人耳目。”⑤李健吾:《福楼拜评传》,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70 页。他自己也承认受到福氏这种“纯艺术”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主张批评家最大的任务是发现作品的价值和不足,而不是做出好坏的结论。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上,他不抱门户之见;在批评方式上,无论批评还是反批评都力求公正和客观,如他与卞之琳之间关于新诗理解的论争,论辩双方的态度都非常严肃而客观。吴小如先生多年后感叹,“从三十到四十年代,文艺批评领域中只有刘西渭和常风两位带有专业批评家性质,彼时写这类文章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⑥吴小如:《李健吾批评文集·序》,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可以说,李健吾所有的文学批评都志在客观呈现科学性诉求。
与同时代的批评家不同,李健吾把英国桂冠诗人柯勒律治的忠告奉为自己进行文学批评时的座右铭:我们首要的努力,是发现事物的美,而不是根据事物的缺点去评判,因为那永远是不明智的。所以,他经常尽可能用心去发现作家作品中有价值的地方而进行科学的客观呈现。⑦李健吾:《咀华集·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他反对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判断,“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⑧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第2 卷第3 期,1935 年9 月16 日。在他看来,“一个批评家不是一部书的绝对的权威。”⑨刘西渭:《答巴金的自白书》,载《大公报·文艺》第72 期“星期特刊”,1936 年1 月5 日。作为一个批评家,应该拥有人性基础上的公正,“他要公正,同时一种富有人性的同情,时时润泽他的智慧,不致公正陷于过分的干枯。”⑩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第2 卷第3 期,1935 年9 月16 日。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自身的限制,所以彻底的公平又很难得到,“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个性,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⑪李健吾:《咀华集·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他不反对用理论去阐释作品,只是,他十分反对先入为主的理论偏见,“一个批评家应当有理论(他合起学问与人生而思维的结果)。但是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佐证,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标准……”①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第2 卷第3 期,1935 年9 月16 日。因为,“标准”在很多时候难免是一种束缚,一种成见。在李健吾看来,“标准”在帮助我们完成表现的同时,也会妨害我们思想的自由表达。因此,批评家不该事先预设一种批评标准,来作为自己从事批评工作的羁绊。
二、批评家与作家自身限制的认识与尊重
李健吾之所以在他的文学批评当中一再强调客观公平公正地对待作家作品,是因为,他从自然主义诗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中看到了人首先是生物,不是神,“人是一个泥土动物,福楼拜禁止自己在作品之中发表意见,他或许尽力做到了,然而把自己从字句之间剔出,由于违背创作原则,他根本就不可能。”②刘西渭:《三个中篇》,载《文艺复兴》第2 卷第1 期,1946 年8 月1 日。完全的客观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有自身的限制。所以,作为批评家自身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如果批评家在批评时放任自己的思想,将会陷入怎样的谬误!批评家的限制不但来自自身生物学意义上的限制,有时还不免为视野所限,有很多自己不及的地方,“不幸是一个批评者又有他的限制。若干作家,由于伟大,由于隐晦,由于特殊生活,由于地方色彩,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心性不投,超出他的理解能力以外,他虽欲执笔论列,每苦无以应命。尤其是同代作家,无名有名,日新月异,批评者生命不多,不是他的快马所能追及,我们还不谈那些左右好恶的情感成分,时时出而破坏公平的考虑。钟嵘并不因为贬黜陶渊明而减色,他有他的限制:他是自己的限制。”③李健吾:《咀华二集·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在李健吾看来,批评家有自由去选择,也有限制去选择。二者相克相长,进而形成一个批评者的存在。因为人是社会上的人,是人群中生活的人,是历史中的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所以我们还会有很多来自社会关系的限制,“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每每打不进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辗转期间,大有生死两难之慨。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着,人世的利害。”④刘西渭:《<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载《大公报·文艺》第36 期“星期特刊”,1935 年11 月3 日不但是人情世故的考虑,还有文学无法回避的现实,“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⑤李健吾:《<八月的乡村>》,《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 年版,第36 页。
不仅批评家是有限制的,同样是“人”的作家也有诸般限制,来自自身物质的存在,来自外界的影响。李健吾说,“对于文学,一切富有性灵的制作,绝对不免相当的限制,这就是说,好坏是比较的,层次的,同时明白清楚,所谓表现,也只是比较的,层次的。”⑥刘西渭:《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载《大公报·文艺》第158 期“星期特刊”,1936 年6 月7 日。艺术也是一样,“艺术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种无情的方法,让它获有生理学的正确,……”⑦李健吾:《福楼拜评传》,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383 页。因此,对于有限制的文学与艺术,我们不能苛求。李健吾认为,对于旧小说家,应该有一个宽容、同情的态度,而不应该是一味指责和高要求,因为,人有时代的局限。他主张对于作家作品的解释和评价,不能脱离开时代的风尚和历史环境而过于苛求。他自己在评论时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在论及罗皑岚的《苦果》时就说:“褒贬这部小说,却应当记住它成书的年月。……专从历史的价值来看,《苦果》自然属于一部创作。”⑧刘西渭:《<苦果>》,载《大公报·小公园》第1755 号,1935 年8 月4 日。李健吾说,“什么是批评的标准?没有。如若有的话,不是别的,便是自我。”把自我作为批评的标准,其结果便是批评的独立,也让我们承认了批评的独立性,王尔德也曾有言,批评本身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柏拉图解释艺术,把艺术看做是模仿的模仿;勒麦特解释批评,把批评看做是一种印象的印象:“作者拿他某一特殊时间在人世所受到的印象记在一件艺术作品里面,同时批评,不管武断不武断,它的趋止是什么,所能做的也不外乎把我们对于作品在某一时间的印象凝定下来。”①转引自刘西渭《自我和风格》,载《大公报·文艺》第328 期“书评特刊”,1937 年4 月25 日。如果按照勒麦特的看法,一个批评家应该不判断,不铺叙,主要是在于了解,在于感觉,在于呈现当下的客观感知。的确,我们研究的对象一改变,研究它的心灵一改变,心灵所依据的观点一改变,我们的批评就随时可能不同。李健吾认为批评是一门艺术,“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②刘西渭:《答巴金的自白书》,载《大公报·文艺》第72 期“星期特刊”,1936 年1 月5 日。。在自己对人性的包容性理解的基础上,最主要的是尊重作家人性的复杂,“所以认识一件作品,在他的社会与时代色彩以外应该先从作者身上著手:他的性情,他的环境,以及二者相成的创作的心境。……批评家容易走错了路,因为他忘掉作者的有机的存在。”他认为,自觉的批评家应该是这样的:“过分自觉的批评家,看见同代的艺术作品,再也不敢武断一句是非。”③李健吾:《从<双城记>说起》,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3 期,1934 年1 月17 日。
如何做到客观公正对于批评家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在李健吾看来,我们最要紧的是先认识自身,“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④刘西渭:《<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载《大公报·文艺》第36 期“星期特刊”,1935 年11 月3 日。然后,“我的工作只是报告自己读书的经验。”⑤刘西渭:《咀华集·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年版。然而对所读的书,我们不要有先验的成见,“在我读到一本新书的时候,我永远不先想到这是左翼,这是右翼,这是时髦,这是潮流。先让那本书涵有的灵魂和我的灵魂互相直接来往。那是一个最愉快的境界。”⑥刘西渭:《与吉文书》,载《世界晨报》,1946 年8 月30 日。他认为批评家是自由的,“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为自由。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⑦刘西渭:《咀华二集·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要想做一个好的批评家,首先还是尊重作者,包括作者的限制。在《与吉文书》中,李健吾说:“我反对带着‘成见’去读书,我是人,我尊敬人家是人,我尊重一切为人类福利服役的精神制作。”⑧刘西渭:《与吉文书》,载《世界晨报》,1946 年8 月30 日。尊重作者的性情,“性情是一切艺术作品的个别的暗潮,朱光潜先生那样通畅而且可爱的一部《谈美》,没有谈起,我引以为憾。”⑨李健吾:《从<双城记>说起》,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3 期,1934 年1 月17 日。作为一个批评家,“在批评上,尤其甚于在财务上,他要明白人我之分。”否则,“稍不加意,一个批评者反而批评的是自己,指摘的是自己,暴露的是自己,”因此,“最大的奸细是你自己。”⑩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第2 卷第3 期,1935 年9 月16 日。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该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以保证批评的公正和公平。因为人首先是生物人的个体,所以是人都有限制,作家和批评者都无可逃避这一事实。因之,批评家在批评时,更应该首先尊重作家人性的多样性的存在,包括作家受人性和现实的限制而给作品带来的限制,不应该攻击或者随意下断语。作家也是如此,批评家因受物质自身和视野的限制而打不进作品的时候,所论有偏差时,作家也应该谅解批评家。好的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在充分认识自己之后,尽可能不带成见地去读书,只报告自己读书所得,竭尽所能去发现作品的价值和优长,不随意妄下断语,这才是客观公正的。
三、客观公正批评的方法:比较论证
对于文学批评的公正性,李健吾不仅在理论上是这样提倡的,还以自己的实践来印证他的理想。为了保证批评的客观公正,他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经常使用比较论证的方法。有学者说,“对三十年代蜚声文坛的作家们的作品及其创作特点做评述、鉴赏的同时,贯之以中西比较,从而体现作者‘真诚的自由’、‘坦率的鉴辩’,是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的特点。”①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2-103 页。李健吾认为单独解释一部作品容易陷于孤立静止难以客观,所以,他很重视在比较中求得公正和全面的认识,“所谓灵魂的冒险者是,他不仅仅在经验,而且要综合自己所有的观察和体会,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关系。也不应当尽用他自己来解释,因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类已往所有的杰作,用作者来解释他的出产。”②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第2 卷第3 期,1935 年9 月16 日。李健吾认为,比较论证是获得客观公正的最好的方法。
比较论证的方法是李健吾文学批评实际操作上的一个最大特色。他所有的文学批评文章里比较的方法随处可见,用来比较的作家也很多。据张大明先生的统计,在《咀华集》《咀华二集》两本不到15 万字的论文集中,李健吾论及的作家有26 个,用来比较的中国作家近50 人,用来比较、作论证的外国人共有80 余人。欧阳文辅虽然不满意李健吾的批评,说他是印象主义腐败理论的宣讲师,但也承认李健吾“在批评方法上能用‘比较’的说明,能用‘综合’的认识”③欧阳文辅:《略评刘西渭先生的<咀华集>——印象主义的文艺批评》,载《光明》(半月刊),1937 年第2卷11 期。。具体来说,李健吾的比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的作家作品相比,一类是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和文学思想的比较。
在大多数情况下,李健吾用的都是第一类比较,即不同作家之间的比较,在比较中见出各个作家的区别和价值。在李健吾的批评著述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最著名的是将巴金与茅盾相比较,因为这还引起过一场笔战,巴金先生曾写过一篇近三万字的文章④即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答刘西渭先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 年12 月1 日。与李健吾一一辩驳。李健吾说,“用一个笨拙的比喻,读茅盾先生的文章,我们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底下也有的是绊脚的石子;读巴金先生的文章,我们像泛舟,顺流而下,有时连你收帆停驶的功夫也不给。”⑤刘西渭:《<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载《大公报·文艺》第36 期“星期特刊”,1935 年11 月3 日。他不但把巴金与茅盾比较,还将巴金与废名做比较,说“废名先生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先生单自成为一种力量。”废名是隐士,巴金是战士,废名把哲理给我们,巴金把青春给我们,“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极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极必反的热,然而同样合乎人性。”⑥刘西渭:《<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载《大公报·文艺》第36 期“星期特刊”,1935 年11 月3 日。充分体现出李健吾清醒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还把巴金与左拉相比,说“巴金先生缺乏左拉客观的方法,但是比左拉还要热情。”最后将巴金与乔治·桑相比较,说巴金与桑一样,把自己放进他的小说⑦刘西渭:《<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载《大公报·文艺》第36 期“星期特刊”,1935 年11 月3 日。。这样多方比较、客观呈现,加深了我们对巴金作品的理解。在论述一个作家时,为了让我们能得到比较充分且客观的认识,他往往把这个作家和几个人相比较。李健吾很欣赏中国现代作家废名,在论巴金的时候已经与巴金相比较过,在论《画梦录》时,又将废名与何其芳相比较,说“不晓得别人有否同感,每次我读何其芳先生那篇美丽的《岩》,好像谛听一段《生风尼》……”⑧刘西渭:《读<画梦录>》,载《文季月刊》第1卷第3 期,1936 年9 月1 日并举出何其芳《画梦录》的一段话,说是与废名的《桥》里面的内容相似。然而,又说到他们之间的不同,“废名先生先淡后浓,脱离形象而沉湎于抽象。他无形中牺牲掉他高超的描绘的笔致。何其芳先生,正相反,先浓后淡,渐渐走上平康的大道。”⑨刘西渭:《读<画梦录>》,载《文季月刊》第1卷第3 期,1936 年9 月1 日还将废名与沈从文相比,“废名先生仿佛一个修士,一切是内向的;他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自身。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个修士。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的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大多数人可以欣赏他的作品,因为他所含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但是废名先生的作品,一种具体化的抽象的意境,仅仅限于少数的读者。他永久是孤独的,简直是孤洁的)。”⑩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第2 卷第3 期,1935 年9 月16 日。
最后对废名前后期的作品进行比较,带领我们去探寻废名前后期作品的风格,“冯文炳先生徘徊在他记忆的王国,而废名先生,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同时他所有艺术家的匠心,或者自觉,或者内心的喜悦,几乎全用来表现他所钟情的观念。追随他历年的创作,我们从他的《枣》就可以得到这种转变的消息。”①刘西渭:《读<画梦录>》,载《文季月刊》第1 卷第3 期,1936 年9 月1 日他将芦焚的《里门拾记》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艾芜的《南游记》相比较:“《里门拾记》的作者带着痛苦,也正是这点儿抑郁不平,这点儿趁热就吃,在某一意义上,让他与《老残游记》的作者近似,而和《南游记》的作者不同,和《湘行散记》的作者的精神越发背道而驰。”②刘西渭:《读里门拾记》,载《文学杂志》第1卷第2 期,1937 年6 月1 日。又将芦焚的讽刺特征与张天翼、鲁迅分别进行比较;在描写方面将其与萧乾比较:“萧乾先生用力在描绘,无形中溶进一颗沉郁的心。他的句子往往是长的。他的描写大都是自己的。芦焚先生的描写是他观察和想象的结果,然而往往搀着书本子气。他的心不是沉郁的,而是谴责的。”③刘西渭:《读里门拾记》,载《文学杂志》第1卷第2 期,1937 年6 月1 日。哪怕是对于同一个文学团体的作者,李健吾也会通过比较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如他将何其芳与同属“汉园三诗人”中的李广田相比,说,“同在铺展一个故事,何其芳先生多给我们一种哲学的解释。但是,我们得佩服他的聪明。他避免抽象的牢骚,也绝少把悲哀直然裸露。他用比喻见出他的才分……”④刘西渭:《读<画梦录>》,载《文季月刊》第1 卷第3 期,1936 年9 月1 日在多方面比较之后,他才说何其芳“缺乏卞之琳的现代性,缺乏李广田先生的朴实,而气质上,却更纯粹,更是诗的,更其近于十九世纪的初叶。”⑤刘西渭:《读<画梦录>》,载《文季月刊》第1 卷第3 期,1936 年9 月1 日他喜欢福楼拜,说“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世界,司汤达剖开了一个人的脏腑,而福楼拜告诉我们,一切由于相对的关联。”⑥李健吾:《福楼拜评传·序》,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原因也通过比较给我们指出:“……巴尔扎克是人的小说家,然而福楼拜,却是艺术家的小说家。前者是天真的,后者是自觉的。”⑦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第2 卷第3 期,1935 年9 月16 日。
后一种比较,即单纯的作家自身前后创作的不同的比较,相较之下运用的场合不多。除了前面论及废名时之外,在论及叶紫和萧军时也使用过。说到萧军,他断言说《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失败的小说(这是我们几乎唯一能找到的李健吾对别人的作品下否定性断语的地方),然而,他并不以一部作品就全盘否定一个作家,而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去分析萧军的进步与各部作品的优点。他说“我们喜欢《八月的乡村》的文字,因为这里孕育未来和希望。”⑧刘西渭:《<八月的乡村>》,《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 年版,第41 页。接下来,他说萧军后来写的短篇小说《羊》相对完美,并说其时萧军正在写的已出两卷的《第三代》十分“切合现代”⑨刘西渭:《<八月的乡村>》,《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 年版,第46 页。。
不论哪种比较都是为了更加科学、更加客观公正地呈现出作品的优劣。邓牛顿先生说:“我们的文艺批评应当学习健吾先生这种科学的比较方法的运用,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培植我们明锐精确的艺术辨析力。”⑩邓牛顿:《关于李健吾的现代文学评论》,载《晋阳学刊》1983 年第2 期。钱林森先生也很赞赏李健吾的比较方法。不过还是杨义等先生说得好:“李健吾突出的比较文学批评观就在于认定批评家应该跳出个人的成见……”⑪杨义等:《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307 页。正是担心囿于成见,要追求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所以,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文章里,几乎没有一篇不会用到比较论证方法。
李健吾常说,文学批评是灵魂与杰作之间的奇遇。而实质上,这是一项十分危险的活动,稍有不慎就会掉入主观陷阱。力主排除主观的爱憎、好恶等情感成分,尽量做到科学客观是自然主义诗学的一贯主张,也是李健吾进行批评活动时的一贯追求,客观呈现的批评观念是李健吾进行批评活动时一直遵循的原则。近年来,学界常有关于文学批评的原则、标准与态度的讨论,李健吾客观呈现的批评观对于我们今天的学界来说,仍有很好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