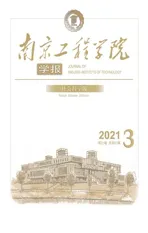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米氏英译本研究
2021-12-31刘迎春
季 翊,刘迎春
(1.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103;2.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6)
航海典籍《瀛涯胜览》为明朝通事马欢所著,记载了他三次亲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见闻,详述了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等亚洲20余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生产和生活面貌等情况,还原了15世纪初中国与西洋诸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友好往来的史实。专注中国航海史研究的英国汉学家、学者型译者米尔斯(J.V.G.Mills)于1970年向西方世界完整译介了《瀛涯胜览》,其英译本是该部典籍迄今唯一的英文全译本。米尔斯的英译本除了原著正文的译文,还有内容极其丰富的副文本信息,包括序言、译者注、导言、注释、后记等众多类型,综合展示了他在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中外海洋文化交流方面的汉学研究成果。我国明史研究专家万明评价米尔斯的英译本为“《瀛涯胜览》最重要的外语译本”[1]。
国内对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的翻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该领域翻译研究的边缘化、碎片化的学术现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目前,除了历史学学者将该译本罗列为重要的郑和研究文献进行综合考证之外[1-2],对其进行翻译研究的论文仅有3篇:张箭(2014)从内容结构、语言特色等角度对该译本进行了宏观的翻译评价,认为米尔斯的译文准确、巧妙、匠心独运,并通过添加丰富的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生物学考证辨析信息,成为一部“集译著、专著、工具书、原始数据书于一体的综合性专著”[3]。迟帅、许明武(2021)梳理了《瀛涯胜览》译本源流,重点从历时视角探究其英译史,并探讨英译本在传播与传承丝路文明中的作用[4]。王海燕、季翊(2020)第一次对《瀛涯胜览》展开专题翻译研究,探讨了米尔斯如何运用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和方法翻译原文地名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地理、文化等信息,将东方文化准确完整地译介给西方读者[5]。米尔斯针对《瀛涯胜览》的翻译研究和实践为开展中国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国内学者对外译介中国文化典籍树立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例。将这部描写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中国航海典籍译介给当代英语读者,米尔斯的翻译活动面临着语言形式、意识形态、文化认知等多重要素构成的复杂翻译环境,需要跨越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文化鸿沟。在很大程度上,米尔斯的译介活动是从原文翻译生态向目的语翻译生态的移植,要实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作为全面记载郑和下西洋史实的航海典籍,《瀛涯胜览》彰显了我国海洋文化之中合作共赢、兼容并包的精神内核。在当今 “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强国”建设的背景下,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的译介研究更凸显其回顾中外交流历史、传播中国悠久海洋文化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生态翻译学与《瀛涯胜览》英译研究的契合
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生态学理论,将翻译视为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进行的“选择性活动”[6],主张翻译活动处于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涉及“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文化、交际、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7]。在这种多元互动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翻译活动恰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动物迁徙与植物移植一样,需要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来确保生存[8]。因此,译者必须对翻译生态环境形成宏观的认识与把握,对原作的语言特色、目的语读者的经验图式、目的语社会的文化背景、价值标准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9]。基于此,生态翻译学提倡“三维转换”的生态翻译方法[6],提出译者应该从语言、文化与交际三个主要维度出发,通过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优化选择来最大限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国内的生态翻译研究肇始于2001年胡庚申首次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尔后经过20年的理论演变与实践应用,形成了如今日臻成熟的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生态翻译学的术语体系也不断完善,在对文本生命、求存择优等翻译概念进行生态阐释的基础之上[10],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翻译环境、翻译群落、翻译生态伦理、语言文化环境等生态翻译概念之下逐级细分的术语体系[11]。而这些核心术语概念,也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内生态翻译研究的热点。例如,通过可视化分析,陈圣白[12](2017)与滕梅、周婉婷(2019)[13]均揭示了国内生态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态势与主题分布情况,发现该领域的发文数量逐年递增,研究类型囊括综述评价、理论探讨、实践应用、翻译教学等翻译研究的主体方向,研究主题也越来越呈现跨学科的研究特性。笔者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做了相关的跟踪研究之后,发现我国学界对于生态翻译学研究业已形成较强的学科意识与完善的学术体系,重点关注领域包括文学经典翻译以及公示语翻译、字幕翻译、外宣翻译、网络流行语翻译等在内的应用翻译。这些研究以多维的翻译生态环境为出发点,考察翻译活动中生态翻译理念的实践情况。总之,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重点,不仅保留了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的语言层面,同时也将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与交际层面囊括其中,拓宽了国内翻译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涵。但总体来看,当前的生态学翻译研究虽方兴未艾,但其应用研究的关注热点仍较为集中,大多数学者主要将生态翻译学运用于文学翻译与应用翻译研究。目前,非文学类的科技典籍英译很少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开展系统的研究,这是该研究领域的一个短板。我们认为,翻译内涵极其丰富的中国科技典籍,译者一方面需要谙熟原作所承载的丰富的语言、文化等信息,另一方面还需要把握好译入语社会的文化背景、目标受众的阅读期待等要求。因此,单纯的语言转换难以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也无法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基于中国科技典籍的文本属性和文化特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于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以中国科技典籍重要组成部分的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的米尔斯英译本为例,其翻译过程需要跨越中英不同语言风格、东西方文化差异、当代西方读者对古代亚洲历史的陌生感等多方面障碍,涉及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科技典籍的阐释和翻译活动,我们可以运用生态翻译理念这一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14],全面解读其汉英双语互动、多元主体介入、多元文化影响的翻译活动全貌。可以说,生态翻译学为研究米尔斯《瀛涯胜览》的英文全译本提供了恰当的理论分析工具。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方法入手,剖析米尔斯英译《瀛涯胜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与方法运用,可以探究其翻译目的与由翻译文化构建的生态理据,挖掘出其运用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生态模式,并重新评估该英文全译本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视角深入解读《瀛涯胜览》米尔斯英译本,挖掘原作与译作所处不同生态环境的特征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米尔斯翻译这部中国航海典籍的语言转换策略、文化交流责任与交际目标,同时指出该项研究给中国典籍英译研究带来的启示。
二、《瀛涯胜览》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米尔斯《瀛涯胜览》英译本体现出其翻译活动中非常明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倾向。首先,米尔斯充分适应原作的语言特色与文体风格、社会背景与文化内涵以及交际目标、信息语境,最大限度地准确传达原作的文本信息,实现了译作文本的立体化呈现。在此基础之上,米尔斯还通过译者的主动介入,优化选择有效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个层面实现从原作到译作的“三维转换”,呈现和谐、平衡的翻译生态环境,促进了目的语读者对原作的更好的理解与接受。
(一)词句书写与语篇构架,促进语言维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意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4]。由于翻译活动首先是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符号转换,翻译方法研究的首要关注点就应该强调译者对原语与目的语所在不同生态环境的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在英译《瀛涯胜览》过程中,米尔斯密切关注中英文在语言形式、语篇结构方面的明显差异,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主要体现在词句与语篇两个层面。
1.巧妙书写词句,实现语言形式的和谐转换
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迥异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在词句层面,米尔斯充分关注语言维翻译生态的重构,对于原文中不符合英语语言习惯的词句结构进行了调整,从单复数变化、词性转换、语序调整以及补充省略成分4个角度进行了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首先,汉语与英语在表达名词数量时存在明显的差异。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其中的名词虽然在逻辑概念上有单复数之分,但这种区别基本不通过语素的变化来实现,因此汉语的词汇形态没有明显变化。而允许词汇变化的屈折语英语,通过内部屈折变化(如单数man变为复数men)和外部屈折变化(如单数language变为复数languages)两种形式,来明晰地表示名词单复数的变化。关注到两种语言的这一区别,米尔斯对原文中逻辑概念上的单复数区别进行了语法层面的转换,分别将标识单数与复数的英语语素内容引入到相应的翻译之中。例如,单数的“建碑”(译为“set upastone tablet”)与复数的“弱水”(译为“Weak waters”)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文中的下划线皆由笔者添加;例子皆选自《瀛涯胜览》英译本)。其次,同样是源于孤立语与屈折语的区别,表达不同的词性时,汉语、英语也呈现出明显的语素构造的差异。米尔斯重视词性转换,首先对古汉语进行单字拆分,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合英语语言习惯与语法规范的词性转换。例如,将地名“天堂”译为“the HeavenlyHall”,将“扇鸡”译为“caponizedfowl”等等。最后,米尔斯进行的另外两种词句层面的语言维转换涉及语序的调整与对省略成分的增译。这是因为汉语作为典型的语义型语言,更注重语义上的逻辑连贯性,形式并非十分严整,语序相对稳定,没有太多变化。有时也会为了维持语言的简洁性而省略掉一部分,但并不影响句意表达的语法结构。相反,作为语法型语言的英语则主要依赖于语序的灵活变化与语法结构的完整配置来实现语义表达的逻辑性。因此,米尔斯根据英语的语言表达习惯进行相应的语序调整,或者对汉语中缺失的语法结构进行补偿性翻译。典型的例子有:米尔斯将原文中的“永乐十年”译为“inthe tenth year of the Yung-lo[period]”,将“有施进卿者,亦广东人也”一句译为“[a person named]Shih Chin-chingwho wasalso a man from Kuang tung[province]”,这两例涉及对原文的语序调整以及省略信息的增译。可见,米尔斯在词句层面的语言维选择性转换,首先依赖于他对于原文语义的精准内化加工,尔后在恰当翻译方法选择的基础上,再将译文外化为适合西方读者语言习惯与审美期待的词句形式。
2.变通语篇构架,促成篇章结构的良性适应
完成词句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之后,米尔斯将语言维生态环境重构的关注重点上升到语篇层面,忠实于英语的语篇形式与思维特征,从韵律处理与语篇衔接两个角度进行了更为宏观的语言维转换。首先,《瀛涯胜览》原作中附有一首马欢写于1416年的《纪行诗》,是其首次跟随郑和下西洋之后有感于途中见闻而吟作的诗篇。该诗作为七言长诗,共计48句,原诗没有固定的韵脚。但在英译本中,米尔斯通过美学加工,将该诗作翻译成为一首流畅、优美的英文诗,具有典型的两行转韵形式(aabbccdd…),体现出英语诗歌严格的押韵结构。例如,翻译原诗句“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时,米尔斯在精准还原语义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进行了韵律维度的诗学创作:“Union under imperial Ming our grand and great land shares;from time forgotten until now no other land compares。”可见,米尔斯不仅将尾韵注入原本并不押韵的原文诗句中,而且还运用押头韵这一修辞手法重塑了英译文优美、灵动的韵律风格。其次,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的处理方面,米尔斯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准确判断原文语段内容与综合考量英译文可读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进行了语篇层面的语言维转换。具体来说,当原文出现新的术语进行内容拓展时,米尔斯自然、灵活地使用英语中的语篇衔接手段进行语义转换。这种语篇层次的语言维选择转换集中体现在众多出现在段首的逻辑连接词的运用方面。例如,“as to/subsequently/thereupon/in addition/in the case of...”等表达方式都自然地出现在米尔斯的译文中。虽然确实都是马欢原作中所不曾有的语义,但米尔斯使用英语惯用的语篇衔接形式,使译文更加清晰、流畅,在语言形式上符合西方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也在语言内容上提升了译文的整体连贯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译文可接受性。
(二)灵活应对翻译难题,成功实现文化维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基于原语与目的语所承载的两种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而提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应“整个文化系统”,实现“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14]。《瀛涯胜览》如实还原了15世纪初期郑和船队所至众多亚洲国家的社会历史面貌,记载了中外在艺术、农业、手工业、造船与航海技术方面的文化交流史实,蕴含丰富的社会、宗教、民族文化,可谓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外文化交流典籍。通过米尔斯灵活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中古色古香的异域风情跃然纸上,被鲜明可感地呈现给西方读者。
1.关照读者,有效提升文化接受度
读者作为翻译成品的直接接受群体,对译者的翻译活动产生间接影响,督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与接受程度。英语读者在经验图式、文化认知、价值观念等方面与中文读者有巨大差异,促使米尔斯将原本面向中国古代读者的《瀛涯胜览》翻译给当代西方读者时,不得不进行文化维的读者关照,为《瀛涯胜览》英译本创设和谐、可读的生态系统。
米尔斯面向读者的文化维转换,首先体现在他对副文本翻译方法的运用上,直言不讳地指明该译著面向的目标读者,向读者发出友好的信号,着力营造和谐的译文接受环境。翻译副文本围绕在译文正文本的边缘,包括标题、封面、前言、序言、后记等形式,用于补充与原作、与译者密切相关的背景信息与观点态度。米尔斯不仅在“序言”中直言,该译著读者对象为“关注航海历史的英国哈克卢特学会会员,包括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在内的相关专业学者,以及对于中国学感兴趣的西方学者”[15],他还在“译者注”中坦言中国古代计量单位的相关内容会对研究货币制度、空间距离的专业学者大有裨益。米尔斯此举旨在积极地向读者靠拢,以译者与汉学家的专业视野激发相关读者的阅读兴趣,示范了通过副文本翻译来构建译者、读者互动平台的文化维转换手法。同时,米尔斯在译文正文中翻译各种东方文化要素时,也擅长巧妙进行信息的挖掘与利用,准确高效地向西方读者传递原作所蕴含的东方文化内涵。例如,翻译原作中描述越南犀牛的句子“头有一角……长者有一尺四五寸”的时候,米尔斯对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进行增译并添加脚注,在正文中将其译为“one ch’ih four or five ts’un [in height]”,并在脚注中对其进行了中英单位换算,译为“That is,about 17 or 18 inches”。如此一来,米尔斯既向英语读者准确解释了犀牛角的长度,又以“高度”而非“长度”的增译内容形象地刻画出犀牛角竖立而非平置的形态,既成功缓解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计量单位理解的不畅,又为读者能够追本溯源地了解东方自然物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如,翻译原作中共计103个亚洲地名时,米尔斯对大部分没有文化内涵的地方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如将“章姑”音译为“Chang-ku”);但当地名存在文化指称意义时,米尔斯则重视指向读者传递文化内涵,灵活采用直译法进行翻译,将蕴含伊斯兰教宗教背景的“天方国”翻译为“the Country of the Heavenly Squar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之,米尔斯在译作的正文本与副文本中都十分重视读者关照,他将西方读者置于东方文化语境之中,引发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进行积极探索的兴趣,在此基础上,通过翻译方法的灵活选择,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有效提升了其译文的文化接受度。
2.求同存异,尽力克服文化不可译
成功构建了关照西方读者的文化场域之后,米尔斯将文化维转换的重心转移到文化内容本身的阐释与传递上。文化融合了民族传统、思维情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众多要素,处于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之中的人们,自然会感受到与他者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同一个文化因子,在东西方文化中会彰显不同的内涵与结构,这就造成了翻译过程中文化的相对不可译性。在《瀛涯胜览》英译本中,米尔斯能够求同存异,对文化的相对不可译现象进行生态还原与调整,将原作的东方文化系统成功移植到译作所处的西方文化系统之中,以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化学习期待。
例如,“中华”这一文化概念与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地理概念“中国”略有差异,彰显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地理文化。米尔斯将其译为“the Central Glorious Country”,既传承了19世纪由来华传教士开创的将“中国”译为“the Middle Kingdom”的西方翻译传统,彰显了原作作为一部典籍的历史厚重感,为读者营造出在历史中追本溯源的学术氛围;又向西方读者传达了中华民族将中正、不偏、君子之道之丰富语义固定在“中华”这一地理概念之中的文化讯息。再如,翻译“观音”与“天妃”这种东方独特的宗教文化术语时,米尔斯首先提供了音译名“Kuan yin”与“Tien fei”,强调了它们所传达的东方韵味;同时又向英语读者靠拢,利用归化翻译策略通俗易懂地示范了两个宗教文化术语在西方宗教文化中类似的指称内容“The goddess of mercy”与“Queen of Heaven”。总之,对待民族地理文化与宗教文化这类东西方明显异质的文化要素,米尔斯注重在契合东方文化价值内核的前提下,从他者文化的内部视角出发,探寻东西方文化的共同主题,捕捉西方读者更易接受的翻译策略和手法,提供了东西方文化链接的通道。米尔斯在文化维求同存异的翻译转换思路,既充分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东西方文化的共在性,积极进行了平衡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构。
3.灵活变通,创新性阐释文化内涵
除了文化异质性导致西方读者对于东方文化的理解困难,米尔斯要面临的另一个文化维转换难题是文化“不对等”现象。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让我们关注两种文化中相对应要素之间的显著差异。但除了这些在两种文化之中能够找到对应要素的文化意象外,还有一部分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中完全不存在。在《瀛涯胜览》原作中,附着于汉语的某些文化意象,在英语文化中就很难找到对应意象。翻译过程中的这种“零对应”会影响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构建。为解决这一问题,米尔斯灵活选择多种翻译方法,创新性地对“零对应”的文化信息进行阐释说明,帮助西方读者消除跨文化交际的陌生感。
例如,“副净”是我国戏曲文化中特有的男性角色行当,一般扮演性格粗豪莽撞的人物。针对这一戏曲文化负载词,米尔斯先使用直译与音译结合的方法,将其在正文中翻译为“the assistant of the ching actor”,既准确表达了原语中“副”这一语素的基本指称意义,又保留了“净”这一文化负载词的异域风情,在不影响读者顺畅阅读译文的前提下,有助于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的兴趣。尔后,米尔斯在脚注中对“副净”进行了阐释说明,称其为“play painted face roles portraying bad characters with vigorous action”,扩展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戏曲文化的认知纬度。又如,针对同为文化群体名称的“回回人”与“唐人”,米尔斯区别对待,分别使用意译法与直译法将其译为“the Muslim people”与“Tang people”,又在脚注中解释了前者源于伊斯兰教“khwei(兄弟)”一词,后者意指由繁盛的唐朝而得名的中国人。米尔斯变通地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让译文浸透了这两个文化群体得名的宗教缘由与历史动因。由此可见,对于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原文信息,米尔斯创新性地混用多种翻译方法,准确地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增译出来,拓展文化阐释的维度,帮助西方读者成功突破文化交流障碍,营造了平衡的翻译生态环境。
(三)呈现交际内容与意图,实现交际维转换
所谓交际维的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就要求译者在准确阐释原作语言信息与有效传递原作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把转换的侧重点转移到交际的层面上,选择合理的翻译方法,保障原作的交际意图成功地“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4]。另外,考虑到翻译是一种译者主动进行的语言与文化的再创造过程,除了原作的交际意图,译者自身的交际意图也应该成为我们解读译作翻译生态系统的重要考量指标。因此,米尔斯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和方法说明其多维的交际意图、阐释其多元的交际内容,共同呈现出其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全貌。
1.说明多维交际意图,承载典籍英译主体多样性
《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旨在通过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与中外友好交流的盛况,彰显明朝国威,“见夫圣化所及”。同时,马欢也希望通过描绘西洋诸国的社会面貌与稀有物产,开阔国人眼界,辅助读者“诸番事实悉得其要”。显然,米尔斯5个世纪之后翻译这部中国典籍时的交际意图会与马欢的上述两个意图大相径庭。他面向特定的目标读者,同时又受到出版商的影响,通过翻译活动中多维的交际意图呈现,构建了兼顾这些翻译主体的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
具体来看,米尔斯《瀛涯胜览》英译本的多重交际意图是通过翻译副文本中的直接说明与译作的正文本中的翻译选择转换来共同实现的。首先,针对读者这一重要翻译参与主体,米尔斯在副文本中将面向读者的交际意图进行了直接呈现。为了让西方读者更透彻地了解这部中国典籍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米尔斯苦心孤诣地在序言中称赞该书是中国航海历史“最为充分也最为有趣的描绘”,能够为众多专门学者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15]。同时,米尔斯在导言中详细介绍了郑和生平、郑和下西洋航线、船队规模、人员配备等信息,还通过介绍马欢的生平信息,刻画出其客观的作家形象。在译作的正文本中,米尔斯并用归化和异化策略,辅以评价、考证、信息阐释等多种脚注方式,运用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实现了面向读者的交际意图。这些相关信息都有效地拓展了译作的外围信息场域,意义归属指向目标读者群体。同时,面向出版商这个翻译主体,米尔斯在序言中也直言,其译作的体例、脚注与附录的编纂长度等,都受到该译作赞助商英国哈克卢特学会的授意[15]。这种直言不讳的交际话语构建,何尝不是一种促进出版商与译者有效交流、互动的有益尝试。总之,副文本等翻译方法的运用帮助米尔斯实现了其译作交际意图的自然流露。面向不同翻译主体的多维交际意图,统摄米尔斯的整个翻译过程,既平衡了其忠于原作、方便读者、利于出版商的翻译初衷,又反映出其构建和谐翻译生态环境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倾向。
2.呈现多元交际内容,成就汉学研究集大成之作
在面向不同翻译主体的多维交际意图引领下,米尔斯适应性地优化选择了有别于原著的交际内容。马欢的原作面向15世纪的中国读者,为了满足原文读者求新、猎奇的阅读需求,自然将大篇幅用来描述西洋诸国的社会面貌、珍稀物产等。但米尔斯的译作则面向20世纪的英语读者,且以关注中国航海史与中国学研究的特殊学者为主要目标读者群,因此米尔斯在《瀛涯胜览》英译中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将涵盖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中外文化交流史在内的多元交际内容一一呈现,成就了这部汉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其创设的和谐的翻译环境中,延续了这部译作“适者生存”的生态价值。
首先,米尔斯全面审视中国能够成就郑和下西洋这一航海壮举的科技优势,综合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明朝的造船、航海与导航定位技术等内容。译作引言中的郑和宝船素描图、附录中的郑和航海图与郑和牵星定位图,都是米尔斯采用多模态翻译方法进行图文解说的具体体现。这些内容描述了中国古代领先的造船与航海技术,给英语读者带来了图文并茂的跨文化交际体验。此外,米尔斯还列出了众多的古今中外相关文献,供意图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读者进行延伸阅读。多样化的翻译手段不仅为米尔斯译文的准确性提供了保障,而且多文本互动还拓展了该部译作的阐释维度与交际空间。另外,米尔斯以其汉学家的学术洞察力,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视角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对中国移民与当地民众的友好交往、郑和协助平定叛乱的史实、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与影响以及中外贸易的繁荣发展进行了翔实的重构性阐释。例如,关于中国与满剌加国(今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交往,马欢原作中记载了明永乐年间派遣郑和在原本隶属于暹罗国(今泰国)的满剌加封王建碑,使其独立身份合法化,并从此建立友好关系的史实[2]。一方面,米尔斯对该段历史进行了准确的信息转换,如通过直译“上(emperor)”“头目(chief)”与“王(king)”等历史文化术语来还原古代中外交往的细节。他深刻洞悉原作文意,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近的阅读体验,不打折扣地实现了原作的交际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在脚注中添加相关信息,米尔斯对这段中外交流史进行了有效重构,在原作信息的基础之上添加了众多参考信息,使交际空间更加广阔。例如,在脚注中论证的历史文化信息“马六甲成为迅速崛起(rapidly increasing)的国际贸易港(entrepot of international trade)”,郑和奉命册封的满剌加头目“拜里米苏拉(Pai-li-mi-su-la)”是“满剌加的建国者与首位国王(founder and first king of Malacca)”等,让西方读者获取了更为丰富、翔实的交际内容,是米尔斯通过扩展交际内容来达成交际维转换目标的最好印证。因此,在有效传递原作交际内容、拓展译作交际内容的过程中,米尔斯成功实现了翻译活动的交际维转换,为其译作开辟了和谐的生存境遇。同时,米尔斯将众多汉学研究成果囊括在其译作之中,着实为该英译本的专业性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就了这部西方汉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三、本研究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米尔斯充分关注跨越东西方语言与文化沟壑的翻译生态环境构建,灵活选用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的生态翻译策略和方法,成功译介《瀛涯胜览》,扩大了中国海洋文化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因此,《瀛涯胜览》英译本成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悠久海洋文化,尤其是郑和远航的重要媒介。米尔斯的此番生态翻译活动为我们深入开展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指导意义。中国典籍翻译研究应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多元翻译主体的和谐共生
翻译活动涉及不同的翻译主体:出版商甚至政府机构负责典籍译本的选题策划与制作发行等工作[16],成为典籍外译重要的发起者,对翻译活动产生直接影响。而作为翻译执行者的译者,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并通过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适应性选择,影响译本的生命力,是翻译活动最重要、处于“中心位置”的主体[17]。位于译事后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的翻译主体读者,是典籍外译成果的“作用对象”[16],其典籍译本的接受程度将影响典籍英译事业的持续发展。
多元翻译主体的和谐共生对于营造稳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意义重大。米尔斯对于读者与出版商的关照就是促进翻译主体和谐共生的一种有益尝试。他在译作的前言、序言等处阐明读者与出版商对其翻译活动的间接影响,并说明了其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是如何满足出版商诉求与读者期待的。如此一来,三种翻译主体和谐共生的翻译生态环境得以成功营造。因此,在未来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中,我们应该关注多元翻译主体的不同诉求与各自作用,确保他们的和谐共生并以此来营造稳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提升中国典籍英译作品的质量和国际传播的效果。具体来说,我国典籍的对外翻译传播应该确保出版商保持浓厚兴趣与持续利益、选择兼具较强语言能力与文化修养的成熟译者、理智区分专门读者的求知欲望与普通读者的阅读热情[18]。只有这样,典籍英译事业才能呼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助力世界文化多样性建设。
2.多重翻译内容和意图的有序共现
翻译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原作文本的“生命”能够在目的语生态环境中得以生存与发展[19]。具体到我国的典籍英译工作,成功的典籍译本既应该充分展示原作历经历史传承而彰显的内在生命力,又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鸿沟而提升原作的外在生命力。这些生命力往往是通过典籍译本中的多重内容来一一呈现的。
米尔斯翻译《瀛涯胜览》的过程,体现了他对原作内容的有效移植与相关信息的创新性阐释,是一个多重翻译内容有序共现的典型案例。他首先通过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完整、准确地再现了原作的基本语义、文化内涵与交际内容,又通过丰富多样的副文本信息创造性地将有利于达成其翻译意图的多重内容进行了添加与处理。米尔斯这种兼顾原作内在生命力与外在生命力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典籍英译水平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典籍英译研究应该密切关注多重翻译内容的有序共现,拓展典籍英译的深度与广度。具体来说,我们应该选择在原语生态环境中具有较强生命力与“较高语言、文化或历史价值”[17]的文化典籍进行翻译,并对其文本内容进行消化、翻译与移植。同时,典籍英译实践要探讨如何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思想,从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等多维视角进行翻译创作,构建一个有序、有效的翻译内容体系与健康的翻译生态环境。
3.多种翻译方法的有效共用
生态翻译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翻译来为在原语中具有生命力的原作创造在目的语中的“新生”[19]。因此,通过翻译方法的有效使用来促进译本的“新生”就成为生态翻译的核心。译者需要通过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操纵有效的翻译方法,选择整合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文[17]。
米尔斯《瀛涯胜览》的英译过程就充分体现了其多维翻译策略与方法的有效共用。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考量米尔斯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不难发现,他综合运用了音译、直译、意译、增译、副文本等多种翻译方法来实现“三位转换”。在共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前提下,米尔斯既保留性地还原了原作的东方语言与文化底蕴,精准地将原作的信息传递给西方读者,又面向目的语的翻译生态环境,在意识形态、社会背景、读者期待等方面,提升了译作的可接受性与传播效果[20]。这对继续推进我国的典籍英译事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灵活选择、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方法,重点解决好如何全面准确传递中国文化典籍中的独特的文化信息,让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作在稳定、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有效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四、结语
作为有较好中文功底并深谙中国航海历史与文化的汉学家、学者型翻译家,米尔斯灵活、变通地优化选用各种合适的翻译策略与方法,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准确传递了原作《瀛涯胜览》的语言信息、文化内涵、交际内容和意图,为《瀛涯胜览》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建构了和谐的译作生态环境。米尔斯成功英译《瀛涯胜览》的“三维转换”模式启示我们,为了开展好科技典籍英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并取得预期的国际传播效果,我们应该实现多元翻译主体和谐共生、多重翻译内容有序共现、多维翻译方法的有效共用。希望本研究能够引起同行专家学者对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的更多关注,从多维的理论视角推动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更快、更深入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