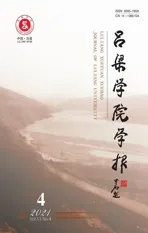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卫生进食”的争鸣
——从公箸到卫生筷到公筷
2021-12-29胡薇
胡 薇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中国式的饭局,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更是一种交际。其中最明显的一种文化指向,是情感连带的象征。佳节之日,亲友欢聚同席,觥筹交错、举箸共食,其乐融融。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围桌会食的画面,人们已经习惯通过共食的仪式加深感情。20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从疾病预防出发,立足于文明饮食习惯和公共卫生角度,开始质疑和诟病传统中餐共交式围食方式。特别是人手一筷、同盘而食所引发的口沫、细菌交叉感染,使得饮食卫生的严肃课题被摆在思考者的面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学校、机关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中共食已不可避免,一筷戳到底的弊病又亟待改革。如何改革,从医界到学界,从民间到官方各种意见纷呈。1922年《申报》常识增刊 “卫生”栏目指出:“卫生之事,千经万纬,而最重要者,尤在饮食中之卫生。”[1]而饮食卫生,主要在进食上讲究,各种相应食器、助食餐具的式样与使用规范成为各方论争的焦点。这场20世纪上半叶基于“卫生进食”目的的争鸣,以公箸、卫生筷、公筷三种进食助具的讨论与施行最为集中。
一、公箸:灾变机制诱发“卫生进食”的初步尝试
1910年11月东北鼠疫引发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反省,随后以伍连德倡导 “卫生餐法”开始,引发了饮食文明、卫生进食的热潮,“病从口入”的疫后阵痛直接导致民众视角的变换。进食助具的改革迫在眉睫,为便于分餐而设的公用筷子“公箸”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追溯 “公箸”讨论的缘起,1915年领导扑灭东北鼠疫的学者伍连德提出的“卫生餐法”不容忽略。为防治肺结核病,伍连德提倡使用公箸,即每菜一箸匙轮流共用,私箸私筷不再进入菜盘的进食方式。清末民初,疫灾和肺病横行,死者不可胜数,人心终日惶惶。伍连德提出公箸、公匙之法,有两个角度的考量。一方面,从传统食俗出发,使用“公箸”能保留同席共食的亲密氛围;另一方面从卫生角度,用专门的公箸搛菜可兼顾防疫需求,减少细菌传播,解决餐桌上的肺病危险。这显然是一种面对国情的折衷办法。但是用公箸分菜的方式并不能完全适应每一品中国菜,而且公箸的轮流使用,执箸之处的接替摩挲不免感染之嫌。国人“对于食法尤缺卫生,吾国相沿习惯,或匙或箸均直接往返由(游)于公众食物盘碗之中,最为恶习”[2]。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平民百姓之家共食碗中菜肴的情况仍屡见不鲜。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现代性的开启,饮食公共卫生的制度化框架也渐次展开。为宣传、普及进食卫生知识,报刊上登载有许多用白话写就宣传公箸的文章。1929年《南开双周》第4期一篇作者署名为大嚼的文章《宣传用公箸》提到:
今年开学以后,第一饭厅南门入口处的食堂规则,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失效了!其实它在以往的时期,还不是有名无实?每月起始的那天,食堂每桌放置一筒公箸,给那些好讲卫生的人们预备着。……。用公箸可以制止抢菜,每个人都用公箸将菜放在自己吃碟内,然后再自己去吃,自然免去连续的攫得,所谓有利大家可以均沾些[3]。
作者明确指出,口沫是导致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夹食同一盘菜极易引起交叉感染。他向大众推荐的“公箸分食法”是指每桌提供若干箸匙以作公用,并倾向认为这样使用公箸将避免传染、确保食品入口洁净、制止抢菜。这便呼应了伍连德所提出的置公用箸的 “卫生餐法”,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其延续发展。但是学生们对“公箸”普遍持无味或无聊的态度,推行使用公箸的食堂规则最终以“失效”而告终。《南开双周》是闻名遐迩的南开中学所编辑的刊物,始于1928年。对公箸的认识和使用,在现代学校南开中学尚且不如人意,引进公箸,在名校南开中学就举步维艰,那么在其他地方其境况将会更为糟糕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变“箸”为“筷”,已有“公共筷匙”的倡议。如1931年的《中国卫生杂志》上刊载了王祖德的短文《共食恶习》,提醒人们注意共餐之恶习,主张使用“公共筷匙”。该文提出:
共食习惯,传染疾病。妨害公共卫生至巨。虽最上等社会,亦不能免。盖相沿既久,已成习惯,不复知其为害矣!……提倡公共筷匙。每人用甲乙两副筷匙。以甲筷取菜,放置自己碗中。再以乙筷送入口中[4]。
此法亦主张各人筷子不再进入菜盘的进食方式,但是与先前不同的是置“甲乙两副筷匙”,一作公用,一作私用。先以公者取,然后以私者纳入口中。作者肯定甲乙双筷之法,但受传统共餐制的影响,时人对于“公共筷匙”仍有所抗拒,认为此法不合乎习惯且更显生分。曾立群曾在《宴客须知》中直言:“国人尝有提倡分食者,其意美矣,未易合乎习惯也。有倡用两副箸匙者,仅许其一副入口,其另一副备供搬运菜羹自盛贮之器入其个人用之碗盏中。手续累赘,法属妥善,亦未宜言普及也。”[5]人们认为一手交替使用两副筷匙显得“手续累赘”,所以“未宜普及”,因此相关倡议在当时只产生了局部性的影响。
用箸卫生的讨论愈发激烈,学界名人蔡元培也出面倡导“特置公共匙箸”,在当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31年9月,庄俞、贺圣鼐合编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为商务印书馆创立三十五年纪念而编印的,分上下卷,收16篇文章,其中有蔡元培1931年6月15日撰写的长文《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文章表示,三十五年来中国新文化受到欧化影响,“生活的改良得用食衣住行等事来证明”,在饮食方面体现如下:
吾国食品的丰富,烹饪的优越,孙中山先生在学说中,曾推为世界各国所不及;然吾国人在食物上有不注意的几点:一、有力者专务适口,无力者专务省钱。对于蛋白质糖质脂肪质的分配,与维太命的需要,均未加以考量。二、自舍筵席而用桌椅,去刀而用箸后,共食时匙箸杂下,有传染疾病的危险。近年欧化输入,西餐之风大盛,悟到中国食品实胜西人,惟食法尚未尽善;于是有以西餐方式食中馔的,有仍中餐旧式而特置公共匙箸,随意分取的;既可防止传染,而各种成分,也容易分配。又旧时印度输入之持斋法,牛乳鸡卵,亦在禁例,自西洋蔬食法流行以后,也渐渐改良[6]。
蔡元培关注到饮食文化的阶段性问题。传统饮食得以改良,主要在营养、卫生两个方面,也就是在吃什么和怎么吃上有了进步。民国期间,战祸、旱灾、洪灾、疫灾等频发,特别是东北鼠疫防控手段的进步,对环境卫生、饮食习惯的转变等有重大关系。随着用箸卫生的倡议不断兴起,民众多能改变其心态,效仿西式分餐、食具必各人分认的做法在民众日常生活也有所渗透。这一阶段,时人开始意识到私箸杂下的不妥之处乃至风险,却又不舍它所暗含的平等化、人情化的交际氛围。事实上,正是意识到了这种矛盾心理,京、津、沪、鄂等诸多中心城市都在讨论饮食卫生,试图推行“公用匙箸”缓解矛盾,不少倡导者适时修正自己的主张,推广“公共餐具”的使用。在京名士中,推行最具影响力的便是蔡元培,他认可“仍中餐旧式而特置公共匙箸”,指出此中餐西食方法,便于随意分取食物,“既可防止传染,而各种成分,也容易分配”。这里,蔡元培采取的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融通简易措施,将改良饮食习俗上升到文化进步的层面,其境界之高当该称颂。在不破坏就餐者的亲密氛围的前提下,又可以避免私箸杂下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可谓进食卫生的中道。他的主张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社会感召力。
二、卫生筷:主流意识形态下“卫生进食”的补救
1934年起,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首都南昌推出新生活运动。“公箸”一词已经罕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卫生筷”的叫法流行开来。当时政府在饮食保健方面显示了异常开放的姿态,突出表现在普及饮食卫生知识、推助文明进餐上。国民政府卫生署还通过“我用我的筷,我用我的碗,自己手巾随身带,一切疾病不传染”的歌谣推动人们注重和自觉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为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卫生进食”的讨论与坚持一直持续中。
为响应新生活运动这一国民教育运动,《卫生杂志》1934年第19期刊发了系列文章,其中有鲁六华的《谈谈卫生筷的利弊》。鲁六华精于中医医道,被誉为“女医第一家”,她的《谈谈卫生筷的利弊》一文指出卫生筷就是分餐制的观点:
我国的烹饪法,讲究鲜美,素为世界所公认。共食制的乐趣,也有存在的价值。不过,在人事日繁的现代,在公共团体生活中,共食制难免有妨碍公共卫生之处,因流弊所及,不得不设法补救。然吃卫生筷,究竟也不是澈(按:应为“彻”)底的办法。这个问题,有关于公共卫生,望热心于社会事业的人,注意研究之。因为吃饭问题,是人生最重大的问题呵![7]
文章先从“我国家族制度发达”说起,指出“我国这种共食的制度确有深长的意义”。她认为在传统中国五代同堂,七世同宗的大家族中,亲属团聚在一起同饮同食,可以共享人伦。随着社会进步,人的社会关系和人情礼仪往往与团体用餐环环相连,团体聚餐已无法避免。如若所有食客都身体健康、干净整洁,不使用“卫生筷”,倒也无妨,可“如遇已坐之中,有一人患肺病或患梅毒的,那筷匙传染,为害非浅”。她进一步指出,有时因苦于纪律关系或职务关系,不得不和病人同桌而食,筷来箸往为病菌扩散打开方便之门。“有先知先觉者,发明一种补救的办法,叫做卫生筷”。所谓“卫生筷”,指的是每餐开饭前,各人将桌上的菜肴分配进自己的盘子中。“卫生筷”既可获共食制的乐趣,又能避免病菌的传染,“所以近几年来,各地团体中,风行吃卫生筷的,也著实不少。在浙江一带,尤其是格外盛行”。当然,也有吃卫生筷的不便之处,像同桌人有早到晚到的情形、客气与否造成箝菜抢夺的现象、汤汁调味不好分享等。仔细辨别,我们能够发现,这里所说的“卫生筷”实际上讲的是分食制,即菜肴上桌后予以分配食用。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尽地主之谊,食客间同桌同食、夹菜劝酒的合餐文化逐渐形成制式,以共食为内核所建构出的“和”意识”,与尊崇“礼之用,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不少倡导者欲借助儒家道德教化的东风,自上而下传播主流的饮食文化。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觥筹交错、举箸共食”的合餐制与“席地而坐、分案而食”的分食制显然有所冲突,所以《谈谈卫生筷的利弊》以“卫生”为由头,称之为“卫生筷”。“卫生筷”立足于分食制,鲁六华本人也觉得这有碍于传统习俗,所以她说“卫生筷”有利有弊以此来试图补救。
《晶报》1936年8月29日佚名《卫生筷》一文则从共食制出发予以讨论。《卫生筷》一文中提及的“卫生筷”,指的是在当年秋季起上海几个市立小学参照儿童健康营的办法,实行“每人备颜色不同的筷子两双,一双是拣菜的,一双是自己夹入嘴内的”。作者认为:
我想这个办法,凡是大家庭或公共食堂,以及在菜馆里请客,都可仿行,这是与公共卫生很有益的[8]。
通俗而言,上面的“卫生筷”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双筷,即一公筷一私筷。但这里的“卫生筷”却源于新生活运动,受德日法西斯思想的影响而提出。在新生活运动中,“以德国和日本为媒介,很多原本并没有联系的元素,得以整合在一起,包装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逻辑。……‘新生活’的内容包括个人卫生习惯、交通规则、公共行为规范等等,都是按照外国人的评判标准来制定的”[9]。政府企图以此追求国民的生活军事化。个人卫生习惯方面,如《卫生筷》说“日本筷子,每餐一副,食后弃掉,也比中国高明一些”,竟然把使用一次性筷子视为高明作法。又所谓“参照儿童健康营的办法”,可突出运动军事化的特征。文章在论述使用“双筷”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时,直言“日本”的榜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日本人食后弃筷的高明做法”在作者看来是高度表现了日本人规矩清洁、迅速果敢的习惯,因此国人也需学习这种习性,才能成为随时流血拼命、誓死效忠国家的良民。如此双筷虽然简易可行,但其思想来源与真实目的难以让国人欣然接受。
《晶报》1936年9月30日发表的芳菲《双筷双匙与各客菜》,从题目来看,很显然是接着《卫生筷》而发表的。《双筷双匙与各客菜》一文醒目指出“因共食制有碍卫生”,在讲述传统共食制有碍卫生的实况后,它谈道:
因此醉心欧化的,便说西洋人的吃法好了,不然就用东洋人的筷子,吃过了饭以后,便把筷子丢弃了。现在上海的菜馆,已有仿照东洋人的筷子的,不过对于共食制度,还是一样[10]。
文章说学习“东洋人”不得要领,抛出“吃各客菜”的方略,“吃各客菜者,每人一份,一汤一菜,都用小碗小碟,菜多的一碟之中,也可以按放几种菜”。稍加比较,我们会看出,“吃各客菜”实际上是袭用了鲁六华的说法,如此分盘而食,有新瓶装旧酒之嫌。《谈谈卫生筷的利弊》尚且意识到“卫生筷”有其弊端而对“卫生筷”有抑有扬,而《双筷双匙与各客菜》则过于抑中扬外,甚至是将使用卫生筷视作西方的舶来品,忽略了卫生筷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原创的事实。“不过据中国老饕家说,中国菜非共食不可,整翅全鸭,宽汤大碗,方显真味,中国的吃饭,要守中国的本位,不能西化咧”,如此态度和行为,必然行之不远。
综上所述,新生活运动中倡导的“卫生筷”,开始主张分盘而食,进而有主张“双筷双匙”的,但是这种吃法很快被否认,而主张“吃各客菜”,不过三者在归位到分食制上则是一致的。蔡元培所倡导的“特置公箸”无可厚非,但是在新生活运动中它竟然被弃之不用,而是背离中国传统和时代发展情形,在“卫生筷”上折腾不已。“卫生筷”的论争,矛盾重重,困难重重,最终只限于论争而已。
三、公筷:作为进食助具领域的建树
20世纪40年代末,“公箸”一词被通俗地称之为“公筷”,“公筷制”正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饮食卫生的讨论和卫生进食的倡议、呼吁,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心态结构的改造 ,行为习俗的变迁起到了催化作用。由于学校是最能形成群从相应、久而成习的社会空间,易于推行公筷,不少有识之士仍着力从学校进入,其间以陶行知的校规制定与上海高校的推行极具影响力。
在民族抗战的艰难岁月,力行者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亲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其中第十条规定“用公筷分菜”,《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中饮食公约之四规定“公筷取菜,另碗分菜”。陶行知所制定的“公筷”的教规与他的教育经历相关。早年陶行知赴美留学,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熏陶,深感欧美科学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教育家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也对陶行知产生了很大影响,学成归国后,他便毅然选择了科学教育并积极从事旧教育的改造。陶行知尤其重视育才学校的科学教育,并领导学校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不断有新的建树。科学教育同样着重饮食卫生学,决定了陶行知改革学生人手一筷一戳到底的决心,坚定了他制定“公筷”的饮食公约。陶行知认为,进食方式的选择与坚持,以认知与自觉行动为前提。陶先生规定每张饭桌上放公筷,并带头使用双筷制,以防止“病从口入”。此后,该校毕业的学生都有了用双筷的习惯。
1948年2月4日,《益世报》有一短讯名为《讲求卫生采公筷制,彻查游击不遗余力》。涉及公筷的这则短讯是这样的:
×桌同学因体格欠佳,于是处处讲求卫生,一早便先至桌前关照,并置公筷二双,他桌亦先后效之,蔚成风气[11]。
上海高校食堂采用公筷制,“公筷二双”虽为“体格欠佳者”的卫生之举,但并未遭受众人排斥,他桌也未觉有不便之处,反而“先后效之,蔚成风气”。由此,公筷逐渐成为一种新习俗。公筷在学校这一群从相应的氛围中推行效果甚佳,但鉴于国人长期用一双筷子吃饭已成习惯,大众移风易俗的自觉性原动力欠缺,公筷真正走进全民日常饮食中去,还是任重道远的。
四、结语
以1915年伍连德倡导“卫生餐法”为标志,艰行20世纪前50年的卫生进食时潮,使得否定人手一筷一戳到底的中国传统进食卫生的陋习渐成社会共识。有关进食助具的改革和试行方法的讨论,集中并影响最大的有公箸、卫生筷、公筷三种方式,并由传染病防御、社会公共卫生向学校教育、餐桌文明等领域渗透。从公箸到卫生筷再到公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讨论与施行被国家力量强力介入,试图对人们的饮食卫生行为规范以法律明文的形式予以界定。此外,一些学者与学校教育组织尊重民情民意,力避冲突,适时调整倡导策略也是促成转变的诱因。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者与社会各界对餐桌卫生文化的关注戛然而止,全社会逐渐回归至“私筷乱夹菜”的旧辙老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激荡,深入到广泛的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传统餐桌文化陋习的被诟病和助食用具改革又重新凸显。但是,社会整体并未引起较大轰动。直至2002年底爆发的非典事件,公筷、公勺等应对性卫生进食助具被专家提倡并施行,曾引起广泛关注。然而随着疫情的结束,公筷制又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灾难中,为防止疫情通过口沫扩散,民众对公筷公勺制的呼声空前高涨。特别是公筷制的倡行已有前车之鉴,这对下一阶段卫生进食的讨论与施行既是机遇也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