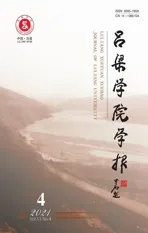抗疫诗歌:生命力筑起的墙
2021-12-29李倩茹
李倩茹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在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看来,瘟疫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1]175,与人类生命共生共存,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干预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瘟疫书写从来不仅仅是文学领域的研究板块,更是一个涵盖生命和文学及其之外东西的社会课题。创作与瘟疫之间向来被视为有最亲密的关系,因为文学的根基在于深入生活,古今中外的瘟疫书写亦无一不在表明,瘟疫和文学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瘟疫重塑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上层建筑与历史命运,瘟疫书写则清楚地再现了人类对瘟疫的恐慌、想象和理解。
诗歌这种独特的题材总是事件或思潮的先声,反观古今诗歌的发展起源,无论是先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心理路程,还是与文学革命相辅相成的五四新诗,都足以印证这一点。当瘟疫出其不意地介入人类实践时,创作主体处在被瘟疫影响的世界中必然会有所思,有所为,将这些形象、观念、意识投射到创作中,或建构或解构,由此构成了以瘟疫或疾病为内容或背景的的瘟疫书写。全民抗疫的热潮催生了抗疫诗歌的热潮,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一种特殊话语资源,抗疫诗歌在当代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诉求和价值指向,而这一切皆基于其本身所拥有以及表达的生命力才得以可能。抗疫诗歌这一类型化诗歌如何呈现生命的状态?又何以展现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关于生命以及生命力又有何新的理解?结合以上问题,联系生命美学,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抗疫诗歌与生命力之间的关系与其内蕴意义所在。
一、抵达生命的真实
“真实”作为文学领域的美学概念之一,在诗歌这种体裁的美学目的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联系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诗歌的见证》中对诗歌进行界定时谈到的:“首先,我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毫无疑问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2]95我们不能否认,语言产生的那一刻,会有言不尽意的可能,但诗歌的魅力即在于以生活的真实为基底而进行艺术转化与升华。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抗疫诗歌直接抵达的是一种超越个人或是集体的生命的真实。身处瘟疫现场内外的人,无一不被这场近乎灾难的事件牵动心弦,在呈现这一宏大而又具体的的历史真实中,诗歌的本质不言自明,生命的力量也从危难中,从细微中更容易见出。
作为驰援武汉奔赴一线的医护工作者的一员,弱水吟的诗歌生动而典型,一首《方舱里的〈萨日朗〉》既诗性地呈现了武汉的疫情,也勾勒出白衣天使们辛苦与奉献的身影与心灵:
武汉方舱
穿白色防护服的你
像一颗子弹
击中了一位美术家的心脏
他以最快的速度
描摹出你的舞姿
像是飞天带来菩萨的救赎
他说距离两千里
也能看见武汉
在雾霾重重的黑夜
从密布冠状病毒的阴云里
透出了一束光
在人与病痛之间,医护人员是最好的隔离屏障,也是人在面对死亡可信赖的护身符。在人与病毒之间依然如此。弱水吟作为方舱的在场者,她感受着眼前的压力也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的认知,但诗中却以“美术家”这样一位非在场者的视角客观地看待她所看到的一切,并将这一切与美术家的身份契合,似乎所描述的已经发生的是一幅画卷里的内容,以“一束光”为结尾所奠定的基调表明了诗人同画者一样,对于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是持积极的态度。于是,在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的叙述中,诗歌中蕴含的生命张力便跃然纸上。
再有戴中平的《逆行者》一诗,宇宙的规律是平衡,有人安享于岁月静好,就一定有人为此而负重前行,诗人并非有意塑造奉献者的形象,只是放眼望去,那些逆行的身影如此耀眼:
今夜你告别了最不想告别的人
收拾起阑珊夜色
眼泪和柔情正值青春
今夜你脚下的路途充满凶险
前方有陌生的病毒复制的恐惧
侵入了尘世的呼吸。而你
仅仅是一名医者,胸怀仁心
唯愿所有冬天的病人都能
在春天醒来
这就够了。今夜你逆行的身影
如一页力透纸背的阵痛
终将被时间长久地阅读
忧虑和恐惧公平地覆盖到每一个人身上,但因为“胸怀仁心”,所以更希望人间有爱,他们的逆行是对生命求生本性的逆反,旨归却是为了拯救更多生命,以这一矛盾为着眼点可谓是全诗的点睛之处。生命之间的帮扶、奉献与牺牲在危难之际展露无遗,大家期待的是同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没有后退没有自私,那些艰难和痛苦都被掩藏在防护服下,那些身影却被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双雪涛在《猎人》的序言所言,“文学不可能站在爱的反面,即使站过去,也是因为爱的缘故”[3]2,可以说,生命的真实是经历难以逾越的困境,而生命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爱,抗疫诗歌将这一切呈现了出来。
二、生命力量的表达
我们无法割断土地,人类之间也无法切断联系,诗歌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守望相助,抗疫诗歌中流露出来的情绪首先是一种勇气,由诗人生成进而传递至大众。诗人在抵达生命的现实这一过程中,在高度凝练的语词中投掷着深沉的感情,在关注个体生存和集体生命困境的同时发挥着语言与文字的指涉作用,在鼓舞人心的同时挖掘着生命的力量。仔细体察,从这一时期的诗歌数量也能看出来,“抗疫自觉”已经基本实现,因为抗疫诗歌的出现就是一种自觉,是自下而上的人民的自觉。这种表达从微观层面而讲,是疏解个体生命体验的强心针;从宏观层面来看,对集体生命经验和生命力量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以生命力共克时艰的愿景。
沈苇在《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就是诗歌的后两小节关于生命力的呈现,他自知疫情的严重性,也坦言诗中所重现的现实中不可避免的焦虑,但是他将更多的勇气和希望也投射其中:
这首诗里有忧心与恐惧
哀悼与痛哭、行动与献身
更有祈祷和祝福——
东湖之水的碧波荡漾
武汉樱花的如期开放
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
这首诗应该快马加鞭
但别忘了为它消一消毒
如果此刻母语感染了病毒
一首诗也会呈现新的恶果
等待湖面平静与樱花绽放这一情景的再现以及“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的希冀,能感受到的诗人的心和血是热的,以手执笔,不能如医护人员等一线战士们与病毒搏斗,但这不影响他们驰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诗歌是情感宣泄的载体,抗疫诗歌更多是情感传递的窗口,没有人比诗人更清楚语言的力量了,免疫力低的身体会被感染,失去能量的语言也会被摧毁。相反,健康的诗歌像药,呈现善果足以医治人心,此刻的诗人和每个岗位上积极抗疫的人没什么不同,他们以临危不惧的姿态守护着诗歌的生命,又以诗歌的生命唤醒着人类的生命。
吉狄马加《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献给抗击新冠肺炎的所有人》一诗中,诗人真切的感受到死神的速度,从出其不意的发生伤害,从被统计的数字不断增加,此时的我们无一不面对着严峻的考验:
然而,这一次!就像有过的上一次!
我们与死神的比赛,无疑
已经进入了你死我活的阶段,
谁是最后的强者还在等待答案。
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
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
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
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
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
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户,将梦剪裁成星星
再一次升起在蓝色幕布一般的天空。
你说死神的速度比我们更快,不!
我不相信!因为我看见这场
与死亡的赛跑正在缩短着距离。
但是相信有相信的力量,不相信也有不相信的力量,人类的生命绵延不息就是因为生命是有力量的,而且是不顺从的力量。病毒在无孔不入,人类也在互相团结,在争取生存空间的战役中,任何生命都需要相互依存,当个体能够坚定且有力地行动,集体的力量无疑更为强大,当成千上万的意志汇聚,人类离胜利的日子绝对不会太远。诗人同样没有被打倒,抗疫诗歌中传达的乐观,是诗人抗疫的呐喊,他以诗歌为旗帜,号召着生命的力量和万众一心的奇迹。
如吴思敬先生对诗人这一特定群体的评价:“诗人总是走在时代前沿,以其特有的敏锐感知,密切关注抗疫战场,以饱满的激情讴歌抗疫前线的英雄——他们是巍然屹立的大山,是普通的医生护士,是街区的守护者,是执勤的士兵……这不是廉价的赞扬,而是对高贵灵魂的仰望,是特殊的春天里时代精神的高扬。”[4]同处时代困境,诗人们也在等待见证命运的结局,他们以客观再现视为战斗到底的方式,面对尽管悲凉但又无法彻底放弃、走向无为的境况,和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是驱使诗歌创作的永恒动力。抗疫诗歌的生命力也由此而来,并将力量传递到每个人和每个角落,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生发更多的精神力量抵御瘟疫。
三、对生命的理解与反思
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疫病与疫情也不断体现在人类文学经典中,其中或是描写人类在面对疫病时的坚强意志和奋争经验,或是呈现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忧患意识,又或是突出人们在苦难面前的搏击和求生意志,以及对救赎的渴望。不管是哪方面的内容,都表明这一事件对个体和人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抗疫诗歌将对生活和生命的重新认识与思考揉进其中,试图在诗性思考中为人类的存在找寻新的基点,因此抗疫诗歌的审美向度与伦理向度不外乎是基于对人类生存与生命发展的关切。而抗疫诗歌的涌现恰恰说明,诗人们坚信一点,即不论现实多么溃败,诗歌中总有至死不渝的东西,可以慰藉自己,关切他人。
颜梅玖的《顺序》,寥寥数语,将疫情期间个体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来,顺序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秩序,“酒精”“口罩”和“消毒”成了日常用语中的高频词汇:
进门后,先用消毒液喷洒全身
以及鞋底
然后用酒精擦拭门把
摘下口罩
洗手15秒
脱掉外套
再洗手15秒
世界寂静
你必须完成这细致的顺序
突然被打破的生活平常被一种新的日常取代,这种被动的改变不分青红皂白地规训着每个人,伴以一种从不适应到习以为常的节奏。诗人是敏感的,他捕捉到这种新的日常化,以时间性概念15秒为单位记录洗手的时刻,重复的次数强调了“洗手”这一日常动作在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性。诗歌也反映了新的陌生化,摘口罩或是脱外套,这些曾经不被关注的行为此时意义深远,当人对这些本该习以为常的细节发问时,个体与宇宙的距离就被拉开,人愈发显得渺小、脆弱,更加不堪一击,求生的本能驱使下,除了完成这细致的顺序别无他法。
应诗虔《避疫的日子》表达了对生命自由的向往,避疫意味着物理空间的封闭,当个体生命的感觉、意志、情感、尊严得到尊重和张扬时,是不会关注于物理时间或心理时间的长短,反之亦然:
关于疫情,
每天都有好消息
和坏消息。
我们还得小心地生活。
今天早上的鞭炮,
一声一声,从天空中褪去的喧嚣
那种开业大吉,一切恢复往日喧闹的假象感
在我们睡梦中醒来的几秒过后,
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这是怎样的一种忧伤:
让繁华失而复得,
是我们蓄积已久的祈盼。
在全民抗疫这一过程中,身处一线的战士们奋力拼搏,普通群众也在为抗疫付出努力。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的规避着瘟疫,隔离使个体消解着自己的天性,选择以一种共性的姿态像大众靠拢,此时的“小我”也是“大我”。在这种语境中,喧闹不复存在,寂静成为常态,鞭炮声显得尤为震耳,是因为孤独在渗透而自由不可强求。繁华在此时意味着不安全,生命求生的本能与向往自由的本性在这一时刻互为悖论,人的选择与期待也不再一如既往。这样的哲学思考在诗中见出,着实难能可贵。
飞白《身体固然没有内心强大》一诗着重强调生命的目的与意义,从中也能看出诗人的反思。身处支援后方,“首先守护好自己”,诗人对一线奉献者的这一声叮嘱真诚而恳切:
那些平时闻所未闻的人们
泥土一样,春耕夏耘
而风雷起时,更多身先士卒的斗士
以燕雀的身躯豢养鸿鹄之志
他们这么浪漫地想,也这么坚定地做
尽管每天下来,已累得不想说话
嗯,那就一句也别浪费
首先守护好自己,其次对付好新冠
倾斜的天平终会回归那个刻度
当春水涨起来时
就可以把狠心剪去的长发好好蓄养
每一寸都是那只不死鸟
应该都在肆意欢歌,仿若生命长久絮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古希腊智者学派的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在瘟疫爆发时似乎并不成立,人并不能左右自己生命的长度,只能赋予生命以或多或少的意义。诗人联系为了更方便地穿防护服女性医护人员不得不剪头发这一实际发生的事件,将人性关怀与社会关怀统一在富于情感温度的诗句中,是对自我实现的褒奖,也是对成就社会的赞扬,生命的意义可以比想象的更宽广。“春水”“蓄起的长发”“不死鸟”这三个意象的内在皆涌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现在不过是天平倾斜的时候,这一过程终将过去,生命的长河永远川流不息。
四、结语
总体来说,抗疫诗歌尽管数量颇丰但质量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疫情是一场突发事件,并不是所有的诗人们都能迅速准确地对此作出反应,抗疫诗歌的生成也不免有粗粝之感。试图哗众取宠的句子不能称得上是诗歌,但抛开语词的平庸和哲思的肤浅,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一些创作主体的勇气与情绪,他们的出发点一定是基于真善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一时代性事件,从而传递着微弱但坚定的力量,只是艺术性或者审美性有所欠缺,但其中内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抗疫诗歌热潮中需要我们关注的一部分。
此外,歌德有言:“人变得真正低劣时,除了高兴别人的不幸之外,已没有其他乐趣可言。”全国上下齐心奋战时,文艺以其独特的方式抵抗着瘟疫,抗疫诗歌中的生命力不仅仅给予人心源源不断的力量,也突显了人之人格的高尚化。无论是何种职业抑或是某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投入了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相较个人主义的狭隘、自私或是冷眼看待,更多的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发挥着团结的力量,也凝聚着生命的力量。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体系中,抗疫诗歌创造了独特的诗歌景观,其以人为本,充斥着鲜活生命力的鲜明品格,可谓是为个体以及集体的生存构筑了一面抵御肆虐疫情的保护之墙。